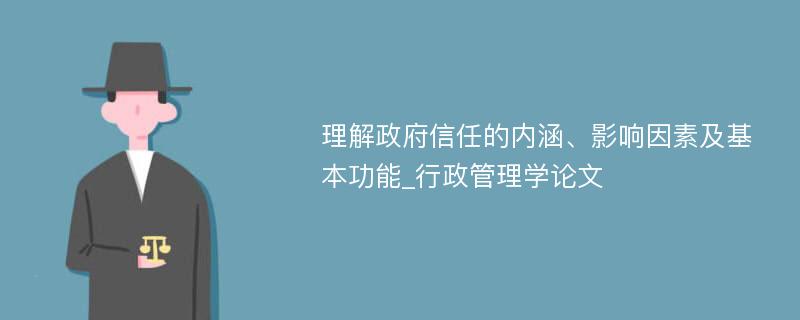
理解政府信任:内涵、影响因素与基本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功能论文,内涵论文,因素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中的重要话题。在西方民主国家,调查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处于较低水平,并从整体上呈现下滑趋势。与西方民主国家相比,尽管我国政府信任保持了相对较高水平,但随着观念变化、社会转型与政治变迁,深刻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政府公信力在一定意义上面临巨大挑战。
政府信任流失的原因有许多。从政府方面看,政府绩效低下、公共服务劣质、治理结构缺陷、腐败蔓延、官员丑闻、利益操纵等都导致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从公民角度看,公民日益希望获得高质量政府公共服务,而这种期望本身可能就是超越政府能力范围。同时,公民虽然希望从政府获取更好的公共服务,但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成本。公民较高期望与政府际实绩效之间的不一致导致形成这样一种流行的观念,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不诚实、浪费和不值得信任的。
维护和增强政府公信力极其重要。政府信任是民主治理的基础因素,是维护和发展治理网络的关键要素,更是社会集体行动和自主治理的必要条件。尽管关于政府信任研究的理论文献非常丰富,但由于信任的复杂性使得对以下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政府信任是什么?什么是影响政府信任的核心因素?并且现有文献较少讨论政府信任具有什么样的功能?通过文献分析与研究,本文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有助于促进诚信政府建设,缓解现代行政国家中政治问责需求与管理裁量权需要之间的内在紧张。
一、政府信任的内涵与构成
信任是理解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核心概念。信任根据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卢曼将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两个层面①;尤斯纳拉将信任区分为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②;祖克则认为有三种信任:基于过程的信任、基于个体特征的信任与基于制度的信任③;托马斯则将信任划分为受托信任、相互信任和社会信任④;还有许多学者则采用了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分类等。
尽管信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从学术文献中可以看到,信任有三个基本要素:认知、情感和行为。首先,信任是个体根据自己的观察评估是否愿意把权力赋予政府的认知决策。这一决策的依据可能因人而异,有人可能基于政治社会化、政治情感形成特定判断,而有人可能根据与政府的互动而形成认知基础。其次,信任是一个情感概念,表示了身处信任关系中的感情。信任的情感基础意味着个体容易受他人行为影响并放弃或弱化监督政府的意愿。最后,信任还涉及行为特征。公民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取决于政府如何处理信任关系,假如政府无视公民利益,违背承诺,就会加剧公众的不信任感,反之,假如政府以公民利益为重,信守承诺,公民就会信任政府。
政府信任是信任的一种具体类型。据此,我们认为政府信任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双向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系统与公共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是公众基于理性认知、实践感知、心理预期、情感因素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机构、政府决策及政府官员行为的信赖⑤,是一个历史的,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政府信任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⑥。伊斯顿将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分为三类⑦:政治团体,即共享政治分工的广义的政治群体人员;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共享的游戏基本规则;当局,即制定和执行政治决策负责的选举和任命的官员。诺里斯拓展了伊斯顿的分类,把政治信任和支持分为五个层面:对政治共同体、政权原则、政权绩效、政权机构和政治行动者的信任。对政府信任类别做出区分是必要的,因为“政权内的不同部分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证等级”⑧。例如,一个人能强烈认同她的政治共同体,但不认同现行政权原则,或者公民可以信任政治机构,却不信任政治家。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遵循一般化的印象还是采取差异化对待呢?一些研究发现公民并不区分政府,对他们而言政府是难以分类的,因而对政府的信任只持一种整体观念。⑨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公民能够区别不同政府机构的绩效等而给予不同的信任水平。⑩从纵向来看,政府信任可以按照政府层级的不同而划分为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而对全国政府的信任度相对较低。在我国,与美国情况正好相反,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较好,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则相对较低。从横向来看,政府信任可以因机构或制度不同,而划分为对警察、议会、司法、政党、教育、卫生等机构的不同信任水平。
通常认为,政府信任的反面就是不信任,这意味着信任与不信任是一个连续图谱。同时,也假定同样的因素导致信任或不信任。但是,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信任和不信任是两个不同概念。“我们可能依赖政府。我们可能发现政府令人宽慰地可以预见。但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利益和情况,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信任或者不信任”(11)。由此,政府信任出现了除信任、不信任以外的第三个维度: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理论概念也在一些实证研究得以证实(12)。这样一种理论建构使得影响信任的因素可能迥异于影响不信任的因素。
二、政府公信力是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的核心
一般认为,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涉及很多,包括公民个体、社会和政府等多个层次。我们认为,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政府公信力是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核心。基于托马斯的研究,我们归纳了可信承诺、诚实、能力、仁爱、公正五个要素,他们构成了一个诚信政府的具体标准,进而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一)可信承诺
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者普遍认为可信承诺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最重要的维度。遵循哈丁的传统,列维把可信承诺看成是“政府行动者尊重她的协议或根据某一标准行动的封装利益(encapsulated interest)。”(13)封装利益和一致性两个概念构成了可信承诺的内涵。哈丁认为封装利益拓展了简单预测。就是说,即使受托人的行为是可预见的,当受托人并不按照信托人的利益而行为,那么信托人也不会信任受托人。根据哈丁的理论,洛克所指的社会契约是政府和公民个体之间信任关系的一种,在这种契约关系中政府应该为了公共利益和保护公民财产而行使权力。
行政官员的一致行为也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当信托人看到受托人在言和行之间具有一致性时,能够大大改善双方信任关系。拉波特等人(14)认为制度一致性是实现诚信政府的主要动力。他们提供了一些维护制度一致性的成功案例,例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商业航空中一致性地保持飞行安全和交通协调,从而赢得公众的信任。政府能够随着时间变化提供同等或更好的服务时,就实现了一致性,从而使公民能够对政府将要做什么有合理的预期和判断。
(二)诚实
公民对政府的抱怨和批评主要是因为对行政官员持有缺乏诚实的印象。毫不奇怪,一些学者认为诚实是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容易被认为是腐败、欺诈和不诚实的。(15)现代行政国家的兴起,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方面保护政府能够有效处理了千变万化的公共问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裁量权滥用行为。例如,凯斯(16)认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职业或组织利益而滥用权力,强化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侵蚀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哈丁(17)提醒,许多行政官员由于受自利动机驱使,增加了失范行为的可能性,尽管这些人员被期望保护公众免受不公政策损害。假如公众知晓行政官员隐瞒了不当行为或以公共利益为名行自利之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就会动摇。总之,政府工作人员没有表现诚实和遵守伦理标准,政府信任就会衰败。
(三)能力
能力是维持政府组织有效运营、提高组织绩效的必备知识和行动技能。政府绩效研究文献表明能力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变量。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由于公众对政府期望的提高,公共机构为了更好运作的压力与日俱增,因而兴起了新公共管理和民营化浪潮。广泛的民营化运动显示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下降。(18)政府机构回应公共问题和服务提供能力的下降,引发了对政府的不信任。
行政官员的胜任能力是维护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行政官员个人能力欠缺,往往会导致公众信任的流失。在现代社会,行政官员的能力发展尤为重要,公共管理职业教育和培训是提升行政官员能力的重要途径。良好工作能力和绩效能够增进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而能力不足和不良绩效则破坏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
(四)仁爱
政府信任是一种理性活动,更是一种道德要求。一些学者指出当公民感觉到政府在本能上表现出关爱、关心公民时,公民倾向于信任政府。例如,泰勒把公信力定义为“权威动机的仁爱”。(19)梅耶把仁爱看成为“除了自利动机外,受托人在何种程度上被认为会为信托人利益而行事。”(20)这种仁爱来源于受托人的情感联结,表明政府及其行政官员愿意帮助公民,即使他们没有法律规定或额外报酬。正如马奇和奥尔森所宣称的,“民主政体和人类精神的本质是努力行善,即使明知这些努力可能没有效果或者会被误导。这就是信念的声明,而不是意义的宣言”。(21)
仁爱行为的准则有助于理解行政官员的角色。哈特(22)强调所谓荣誉官员必须在本质上关心他们所服务的公民。假如行政官员运用权力帮助公民,尊重公民个体,尽一切努力满足公民的需求,公民就会信任行政官员。总而言之,维护政府公信力必须有为民服务的行政官员,他们能够为了公众利益而做出一些牺牲。
(五)公正
许多学者也认为公正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维度。公正意味着政府机构应该恪守原则平等地对待公民,而且这些原则要与公民对政府的一般观念一致。列维认为“政府公正要求这样一种观念,即相关利益已被充分考虑,博弈不是被非法操纵的”。(23)
当行政官员偏爱特定个体或特殊利益团体时,公众对政府公正的印象就会消失。例如,假如行政官员根据社会或地理因素区别对待公民个体,公众信任就会动摇。公民个体期望政府在行政程序和资源分配中是公正的。假如公民认为政府以公正方式在公众之间分配国家资源,他们能够接受更好的要求,包括税收缴纳和部队服役。
三、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与后果
政府信任不仅是一个因变量,而且也是一个自变量。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功能,不仅是政府治理、政府决策的社会基础,而且对公民行为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政府信任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信任危机某种程度就是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政府信任隐含了一切合法统治的共同基础,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都具有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诚信品质,以诚信作为政府合法性的内在诉求。
政治信任对威权体制国家或民主转型国家的稳定性尤为重要。威权体制国家由于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依赖政府,这时当且仅当民众是信任政府的,政治体系才能稳定运行,而一旦主导社会秩序的政府丧失民众对其的信任,政治体系就可能会衰败或崩溃,造成社会动荡和不稳定。
从积极的角度看。信任有助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共享,相关方能够预期从互惠的互动过程中获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可以激励公民披露重要的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有助于政府绩效的提高。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的地方治理进行20多年的跟踪研究,发现诸如信任、规范及网络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提高社会的效率,提升民主制度的运行绩效。(24)而政府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政府绩效的提高则有助于增强政权合法性。
(二)政府信任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变量
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然而这种沟通内在存在一种紧张。政府需要有裁量权以对各类公共问题迅速做出决策。同时,公民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来监督政府权力运行符合公共利益。信任能够通过“扩大公民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而缓解问责与自由裁量之间的紧张。
对政府的不信任会产生对政府决策的抵制。在互不信任的关系中,公民可能担心政府会滥用权力,使得政府决策有害而无利。因而,公民可能会抗拒参与政策执行过程,或者基于原有的偏见强化对政府决策的抗议行动。公民对政府决策的抵制会变成一个关键问题,特别当政府决策会造成公民的潜在损失。在互相信任的关系中,公民会支持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有助于提高政府效率。库珀等人通过对美国地方分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是他们支持分区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25)
(三)政府信任对公民行为有重要影响
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公民不愿在民主治理中投票或参与,而更愿意通过中间组织监督和控制政府行为,并要求加强对政府及政府人员的问责。相反,信任能够使得以控制为基础的监督不再重要,并能够与政府机构形成长期合作,因为相信政府会遵守与公民达成的契约。例如,孙昕等人(26)(2007)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研究中国村民选举参与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发现村民是否参与村级选举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村民对农村基层乡镇党委、政府的政治信任。政府信任不仅对公民的政治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也影响了其日常行为决策。仇焕广等(27)对我国11个城市两次较大规模的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消费者对不同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定量研究了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等因素对消费者接受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
由上可见,信任孕育了善治,信任有助于善治的三个因果机制是:(1)社会—公民原因机制;(2)经济—效率原因机制;(3)政治—合法性原因机制。(28)当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善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政府信任程度高有助于政府治理,反转过来,良好的治理绩效亦会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四、结语
在治理时代,政府信任成为一个重要主题。培育政府信任可以优化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提升公民道德水准,增强政权合法性,促进美好社会建设。尽管维护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面临种种困难,但通过保持可信承诺,实行仁政爱民,加强能力建设,力行诚实廉洁,维护公平正义,就可以实现较高的政府信任水平。
政府信任原则不仅对公民提出了要求,公民需要有良好的品质,自主承担责任与义务,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及行政官员的责任,他们应当成为信任的发起者、维护者和促进者,恢复和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信任关系。具体而言,政府领导人可以通过提高政府绩效、增加透明度、推动公民参与、塑造平等文化、加强反腐败,来实现善治,维护和增强公民对有效政府的期望与信任。
注释:
①卢曼:《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②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Zucker,L.G..Production of trust: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1840-1920.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86 (8),pp.53-111.
④Thomas,C..Maintaining and restoring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ir employees.Administration & Society,1998,30(2),pp.166-193.
⑤刘昀献:《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及其培育》,《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⑥Dalton,Russell J.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Norris,Pippa,ed.Critical Citizen: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57-77.
⑦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
⑧Norris,P.Eds.Critical Citizens: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⑨Stipak,Brian.Attitudes and Belief Systems Concerning Urban Service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7,41(1),pp.41-56.
⑩Klingemann,Hans-Dieter.Mapp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1990s:A global analysis.Norris,Pippa,ed.Critical Citizens: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31-56.
(11)沃伦:《民主与信任》,华夏出版社,2004年。
(12)Mishler,W.& Rose,R.Trust,Distrust and Skepticism: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97,59 (2),pp.418-451.
(13)Levi,M.(1998).A State of Trust.In A.Braithwaite & M.Levi (Eds.),Trust and Governance (pp.77-101).New York:Russell Sage,1998.
(14)La Porte,T.R.,& Metlay,D.S.Hazard and Institutional Trustworthiness:Facing a Deficit of Trust.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6,vo1(56),pp.341-347.
(15)Nye,J.S.,Jr.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In J.S.Nye,Jr.,P.D.Zelikow,& D.C.King (Eds.),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pp.1-1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6)Kass,H.D.Stewardship as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Imag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In H.D.Kass & B.L.Catron (Eds.),Images and Identiti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p.113-131).Newbury Park,CA:Sage,1990.
(17)Hardin,R.Trust in Government.In A.Braithwaite&M.Levi (Eds.),Trust and Governance (pp,9-27).New York:Russell Sage,1998.
(18)Berman,E.M.Dealing with Cynical Citizen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7,vol(57),pp.105-112.
(19)Tyler,T.R.Trust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In A.Braithwaite & M.Levi (Eds.),Trust and Governance (pp.269-294).New York:Russell Sage,1998.
(20)Mayer,R.C.,Davis,J.H.,& Schoorman,F.D..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vo1(20),pp.709-734.
(21)March,J.G.,and John P.Olsen.Democratic Governance.New York:Free Press,1995.p.252.
(22)Hart,D.K.The Virtuous Citizen,the Honorable Bureaucrat,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4,vo1(44),pp.111-120.
(23)Levi,M.A State of Trust.In A.Braithwaite & M.Levi (Eds.),Trust and Governance (pp.77-101).New York:Russell Sage,1998.
(24)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5)Copper,C.A,et al.The Import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Case of Zoning.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8(3),pp.105-112.
(26)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27)仇焕广、黄季焜、杨军:《政府行为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28)布兰登:《在21世纪建立政府信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