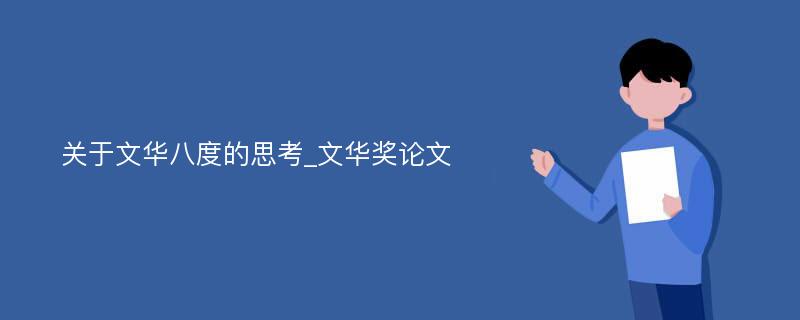
八度文华 几层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层论文,文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年进取,堪回首
文华奖从1991年以来,已经评过八届。前七届共评出文华大奖和文华新剧目奖230个,其中文华大奖41个。大奖中戏曲19个,话剧8个,歌剧7个,舞剧4个,大型歌舞乐舞1个,儿童剧2个。
获文华奖的剧目时代感强,生活气息浓,与时代的脉搏人民的心声相合拍。 七届获文华大奖和文华新剧目奖的剧目230 个, 现代题材的129个,占获奖剧目总数的56%,其中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89个, 占获奖剧目总数的40%。第七届获奖剧目40个,现代题材的27个,其中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19个,占获奖剧目总数的45%。
这些戏取材好,立意深,有的让人久久不忘。《地质师》写几个地质学大学生几十年的生活变化,歌颂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和奉献精神——骆驼精神。《明月照母心》写一个母亲收养孤儿的故事,但写得与众不同,不是一般地为孤儿找个出路,能活下去就行了,而是最后分别为几个孩子找下能让他们受到更高教育的父母,使他们根据各自的特点,成为国家的人才。这个母亲的高大,正反映出作家思考的深远。《高高的炼塔》敢于写在评职称和分配住房当中知识分子遇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无可奈何的窘境,颇为耐人寻味。《山杠爷》写农村干部多年来采取强迫命令的家长式领导,由于不懂法,逼死了人,不仅丢了党籍,还要被判刑,让人看了感到沉甸甸的不是滋味。《水墙》是对经验主义进行批评的一出戏。面对洪水是蓄洪还是泄洪?根据这个地区从来是旱的经验,县长决定蓄洪,结果一场大洪水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戏的情节是感人的,尤其是县长给老百姓下跪的情景,让人落泪。又如广西的《商海搭错船》描述了市场经济大潮下几个人物不同的心态。这个戏的立意很明显,它告诉人们,并不是进入商海就都能赚到钱,也不是说商海全是污泥浊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即所谓“虎上山,龙下海”。
获文华奖的戏可以说处理好了弘扬主旋律的问题。主旋律有一段时间被理解得比较狭窄,以为只有现实的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才是主旋律,其实不尽然。当然,有些作品不必勉强说是主旋律,虽然也是表现美好事物的,艺术上很精致,但毕竟题材是小了点儿。总的来说文华奖主旋律作品占多数。这些戏并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那种直接了当为某一件事、某一项政策服务的,而是一个艺术品。
无论从题材上还是艺术形式上说,文华奖剧目是多样化的,不是都写一个题材,都用一种形式。有的地方曾经规定要唱几歌几戏,唱几个英雄人物,唱几个先进单位。又如有的地方就是强调直接服务,一个工程开工、竣工,都要拔上一些尖子演员去唱,好像这就是主旋律。其实这与大跃进时的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差不多。文华奖的戏不存在这个问题。文华奖有相当一批戏做到了雅俗共赏演出场次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文华奖的戏有三分之一以上演出超过了百场,有的戏超过了千场,如《一二三,起步走》、《鸡毛蒜皮》、《木乡长》等。有的戏好多剧种剧团移植演出,如《三醉酒》、《红丝错》、《狸猫换太子》、《富贵图》等等,这也是文华奖的一个优势。
“三并举”依然是戏曲工作的方针
“三并举”指的是现代戏、新编古代戏、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实际上“三并举”包含五类戏。现代戏的概念很大,张庚同志讲辛亥革命以来的戏都可算作现代戏。1840年以来的反映革命、斗争、爱国题材的戏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则只可称作近代戏,习惯上归于古代了。现在特别强调写现实、写改革、写建设,也就是眼前的题材。这类戏近几年越来越多,第八届文华奖参评的剧目就有7台,《水墙》、 《石角凹》等,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题材。另外一部分戏,如《苦菜花》、《变脸》等,并非现在强调的现实的、改革的、建设的题材。这两部分统称现代戏,但事实上各地强调的是第一类戏。因此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纪念长征60周年几乎没有戏,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好戏不多。而事实上只要不是专为一个纪念活动写的,而是有积累、有感而写的革命历史戏,成功者居多。第一类参加文华奖评选的7台戏曲中选中3台,而第二类参评的4台戏曲也选中3台。至于话剧,获第八届文华奖的剧目第一台就是《虎踞钟山》。因为那个时代的东西经过人们的思考,浓缩了,不是看到一点就写。新编历史戏也有两类,一类是历史上有其人有其事的,如《画龙点睛》、《子血》、《司马相如》、《刘铭传》等,这类戏十分明确,就是历史戏。另一类戏,严格讲只能叫古装戏,穿着古代人服装的无时代、无其人但有故事的戏,如《梨花情》等。这类戏编造起来比较容易,旁人不会深究。所以说,新编历史戏实际上也是两类戏。整理改编的传统戏,严格讲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名剧,公认的好戏,在新的现实条件下、新观众面前,演出也须做些调整,如越剧《西厢记》、赣剧《荆钗记》、昆剧《琵琶记》。另一类是名剧以外的传统戏,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为了保精华也须要改动。获文华奖的改编的传统戏,在推陈出新上下了大功夫。如川剧《刘氏四娘》把一出禁戏化腐朽为神奇,改成了一出很有光彩的新戏。但总的看,这两类戏区别不太大。为什么我说“三并举”实际是五类戏呢?就是强调要实事求是,做些分析,避免片面性,这对创作尤其是演出有利。现实题材固然很重要,但是往往看到一点就写,成功的比例较小。而革命历史题材的戏甚至近代戏,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写起来较顺,不会形成今天写明天否的局面。我讲“三并举”的问题,就是说不要片面地把“三并举”搞成一句空口号,只要一种题材,形成一股腔。
典型化,塑造有棱有角的艺术形象
典型化并不完全是人物塑造,但核心问题是人物塑造。文华奖剧目中出现了不少人物,有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反复讲要实施精品战略,要有精品措施。那么,精品的核心部分是什么,是塑造典型人物,无论是大人物、小人物,还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一部戏塑造不起人物来,最后还是站不住脚。
《地质师》中的骆明,卢静、罗大生、刘仁、曲丹、铁英以及那位不知名姓的邮递员,都各有其鲜明的个性,几个人物身上都闪耀着各自思想的光芒和感人的魅力。无怪那些白了发和秃了顶的评委为之闪出泪花,看完录相又一次为之热烈鼓掌。话剧和川剧《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许多不看小说的人并不知道她。有了这个戏,更多的人知道了。演这个人物的两个演员很年轻,由于剧本的成功、导演的成功和演员的天赋,把这个人物雕琢出来了。楚剧《虎将军》反映的是徐海东长征的故事。徐海东是传奇英雄,他率领的红25军在长征中打通了连接陕北红军和川陕红军、中央红军的中间地带,立了大功。他勇敢、善战、粗中有细,是个极富戏剧性的人物。如果没有这个戏,徐海东这个形象不会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在一些改编戏中再现的人物形象,如花木兰、贾宝玉,都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在新改编的戏中写法不同,也都成功。过去一说花木兰就是打仗,白淑贤的花木兰突出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女人处在男人兵阵中,她怎样生活。她有感情有爱,一场战争摧毁了她的爱,梦破碎了。战争胜利了,边患没有了,皇上要加封,但她却带着伤痛回归了故里,不像豫剧《花木兰》中表现的那样。龙江剧的《花木兰》尽情发挥了龙江剧的特点,小戏作派演出大人物大气派。同样是白淑贤演的贾宝玉,是“荒唐宝玉”。贾宝玉长期生活在女人堆里,他的思想、方法、生活都与常人不同,在大人、“正”人们眼里太荒唐,但荒唐当中有意蕴,在荒唐当中批判了贾政们的“正”,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贾宝玉怪异的特点。不是文质彬彬的贾宝玉,而是疯疯癫癫的贾宝玉。获文华奖的戏,有些演得多,群众喜欢看,不仅由于故事编得好,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几个人物,如上海的《狸猫换太子》、《盘丝洞》等,虽然只获新剧目奖,但人物亦演得活龙活现。川剧《变脸》枝蔓不多,就是在塑造人物上狠下功夫,整个戏就突出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相辅相成,演尽了世态丑恶、艺人辛酸、社会芜杂,水上漂和狗娃的形象也塑造成功了。自然,评奖时,不仅老演员任庭芳得了奖,12岁的小杨韬也得了文华表演奖。
选好有亮点的情节和细节,对塑造人物十分重要。《虎踞钟山》塑造刘伯承元帅,不写他千里跃进大别山,不写他决战淮海,而是写他在解放战争胜利后,从长远地保卫共和国着眼,兴办军事学院,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为我们塑起了一尊伟大的军事家光辉而独特的形象。《三醉酒》中的龙友三次喝酒,醉了三次,三次心情都不一样,但酒醉心明,都是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写好了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支部书记。真人真事、好人好事、活人活事,不一定要写成大戏,写成小戏同样出效果。如徐虎这个人物,事情很多,但最感动人的情节是过年。除夕,在妻子、女儿的反复劝说下,勉强同意由女儿代为查看信箱,看是否还有人家有困难要帮忙。当女儿抱着一大摞信回来时,本以为是求助信,打开一看是一张张精美的贺卡。如果这个情节就写一个折子戏《徐虎过年》,不也很好吗?
在文华奖中评了一些写真人真事的戏,同时也评了一些在生活原型基础上虚构的戏。我们发现,真人真事戏和假人真事戏,都有一些情节细节十分感人,甚至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生命之光》、《爱洒人间》,看过已六七年了,仍然难以忘怀。这些戏的成功,说明作家艺术家关注现实,从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中取材进行创作,是一条应当充分肯定的途径。
但是,有一批好人好事、活人活事的戏却没有评上文华奖,有的评上了也没有多演,印象很快就淡薄了。而一些在生活原型基础上虚构的戏,特别是获了文华奖的戏却与《生命之光》、《爱洒人间》、《孔繁森》一样,印象久不消失,如《天下第一楼》、《明月照母心》、《同船过渡》、《高高的炼塔》,以及革命历史戏《虎将军》、《山歌情》等。仔细捉摸,这些戏的成功,一是塑造成功了人物,二是摸准了当代观众的脉搏,动了真情。这些戏反复告诉我们:创作,不可满足于完成一时的指令性的任务,而要下硬功夫塑造人物形象。
人才,确是艺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一个戏的成功,要有一个好剧本,要精心策划以导演为中心的二度创作,文华奖证明这是极为宝贵的经验。没有杨利民、谭愫、张福先、郑振环、盛和煜、郝国忱的辛勤劳动,就不会有《地质师》、《山杠爷》、《三醉酒》、《天边有一簇圣火》、《山歌情》、《高高的炼塔》等剧目的出现。一批导演、音乐、舞台美术方面的人才,被人公认。导演徐晓钟、马科、余笑予、李学忠、郭小男、顾威、谢平安,舞蹈编导门文元、王秀芳,词作家赵越,戏曲作曲家陆松龄、朱绍玉、刘振球、顾达昌、胡梦桥,舞美设计家吕也厚、金泰洪、蓝玲等,这些艺术家现在到处争着请。如果没有文华奖,没有反复的推荐和得奖,他们不会这么抢手。通过文华奖更加闪耀出他们的光彩。导演温明轩,在山西省晋剧院已退休了,他导的《富贵图》得奖之后,兰州、安庆、山西临汾都请他,他搞一个戏成一个戏。如果没有文华奖,这些老同志可能很少有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了。年轻的导演卢昂已经导过11个戏,他的导演阐述有时比剧本还长,他已经几次获文华导演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女编剧、女导演,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如徐棻、沈虹光、王秀侠、孙月霞、何冀平、燕燕、李亭、董雯,陈薪伊、曹其敬、黄意璘、张奇虹、查丽芳、彭安娜、王佳纳、孙丽清、杨小青、杨晓彦、张曼君等,她们创作极其认真,有的气度恢宏,有的细致精巧,佳品叠出。
文华奖不单评演员,而且在获奖剧目中评单项奖。演员不论是著名的、过去得过大奖的还是无名的新手,只要演好了人物,剧目得了奖,就取得了参评文华表演奖的条件。话剧演员林连昆、谭宗尧、胡庆树、濮存昕、郑邦玉、徐帆、宋国锋、杨青,京剧演员李世济、方小亚、沈小梅、朱世慧、陈少云、孟广禄,昆剧演员蔡瑶铣,地方戏演员白淑贤、茅威涛、马兰、刘芸、涂玲慧、丁凡、张智都是文华表演奖的得主。退休了,演戏演得好,剧目得了奖,照样可以得文华表演奖。比如吉林省黄龙戏演员雷霆、福建闽剧演员林有泉,都是退了休的同志。文华奖使一批老的艺术人才在他们的顶峰时期再一次闪现出光芒,好多中年人才登上了自己艺术的高峰,大量青年人才也涌现出来。
文华奖的实例使我们看到,艺术的兴衰,剧目的成败,好多情况下在于人才。人才,确是艺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有才则有艺,才精则艺精。改革不能只讲“人往哪里去”,也得讲人才从哪里来,人才用在什么地方,人才如何保护。否则,改革和建设都将一事无成。
经过八届文华奖,推出了一批创作和演出人才,以及管理人才。但是表演艺术新陈代谢周期很短,尤其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淘汰率更高,因此,绝不可以满足于现有的这些获奖人才,而应赏荣虑枯,刻不容缓地继续抓紧人才的培养。
普及,为人民也是为艺术
文华奖虽然越来越引起了文化行政部门、剧团和创作人员的重视,但它毕竟还是个新事物,人民群众知道得还不广泛。文华奖的戏大部分还仅限于获奖剧团演出,甚至获奖剧团演得也不多。因此要大力提倡文华奖获奖剧目的普及。抓演出是普及的关键。要适当组织一些文华奖剧目巡回演出,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艺术精品。
为了普及文华奖剧目,应大力提倡地县管的剧团移植演出。文华奖剧目中有相当一批是雅俗共赏的,人物不多,乐队不大,舞美装置不复杂,是适合地县剧团移植演出的。即使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戏,也可以有普及版、通俗版。移植演出文华奖剧目,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措施,文华奖的获奖者们应以自己的戏被更多的基层剧团移植演出为荣。基层剧团通过移植演出文华奖剧目,既丰富了自己的上演剧目,又提高了自己的艺术品位,何乐而不为!
为了普及文华奖剧目,还要重视对民间职业剧团的管理和引导。我国现有各级政府直接管的剧团二千六百多个,其中部、省、地直接管的约八百六十个,县管的一千七百多个,约有四百个县没有剧团。这些县和广大老、少、边、穷地区主要是看民间职业剧团演出。据了解,全国民间职业剧团共有五千多个。它们有的是社会团体办的,有的是企业办的,有的是集股办的,还有个人办的,但都以演出为职业。它们不靠政府拨款,主要靠演出收入养自己,它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演出队伍,占着广大基层特别是农村演出市场,为农民演出,靠农村养着。但是这些民间职业剧团演的剧目却大部分是陈旧的,即所谓“老演老戏,老戏老演”。如果这些剧团每年都能演几个新戏,特别是能演一两个文华奖的戏,既提高了剧团的水平和声誉,又满足了群众看新戏的渴望,也把文华奖剧目普及到了基层,还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不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吗?我以为县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移植普及优秀剧目,其意义并不小于派大剧团送戏下乡。
文华奖经过8年进取, 经过全国文化行政部门和全体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已经站住了脚,但如何站得稳,站得牢固,站得潇洒,还需要再花心血和汗水,使文华奖本身也成为一尊光采照人的形象。
(本文原有9节,限于篇幅,选用了其中的5节,特此说明)
标签:文华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