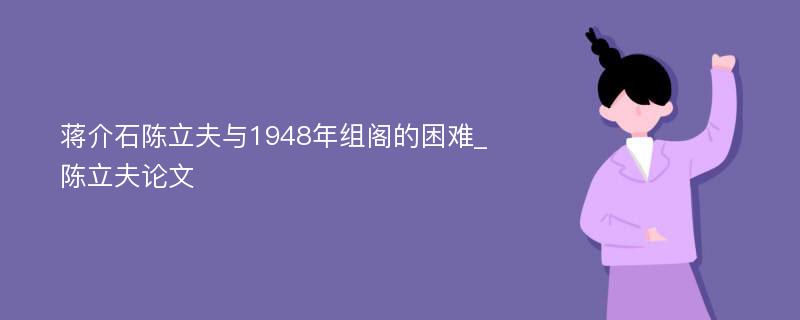
蒋介石、陈立夫与1948年行宪组阁的困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局论文,蒋介石论文,陈立夫论文,年行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8年3月29日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各派系围绕副总统的选举,展开激烈的争夺,最终于4月30日由李宗仁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尽管蒋介石自我辩称:“如余不应选,则竞选副总统者必先竞选总统,而毫不谦让,是则余之目的不仅不能达成,而且党与国更乱,而人民之痛苦,亦不知伊于胡底”,①但现实却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被国大选举极度激化,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国大落幕之后,国民党内各派系在立法院副院长选举及行政院院长组阁问题上,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蒋介石更曾因“立法与行政二院及党务问题内部纠纷,意见不一”,担忧“本党实有崩溃之虞矣”。②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不仅注重从国民党派系政治的方面进行解读,更侧重从国民政府行宪后立法院权力与角色变化的角度展开分析,③可问题是,蒋介石、陈立夫、张群等核心人物如何运作内幕政治,彼此矛盾与冲突若何?蒋介石如何因应立法院的权力制衡?仍旧无从得知。因此,笔者试图重新勾勒出1948年5月立法院选举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的前因后果,重点展现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矛盾冲突以及蒋介石对立法院的认知及反应,进而凸显宪政体制在国民政府派系政治异化下所面临的困境。 一、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矛盾的演变 自1928年10月陈果夫接替蒋介石出任组织部长到1948年7月前后的20年间,主要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轮流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重心,加以陈氏兄弟与蒋关系密切,因此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一般人也以他们当组织部长时,所属的各省市党部、特种党部人员列为CC系”。④CC系作为拥蒋派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支撑蒋介石成功的重要基石,又是导致蒋介石及国民党最终溃败的恶性肿瘤”。⑤尤其是随着CC系势力的不断发展,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即便蒋介石也难以掌控,逐渐开始对二陈产生不满,至1947年4月爆发的中央政治学校风潮,更令蒋陈矛盾急速升温。 中央政治学校作为国民党党办学校,长期由陈果夫、陈立夫主事。1947年4月21日,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段锡朋因病请假,教育部令蒋经国代理政校教育长,陈果夫、陈立夫却暗地组织该校师生罢课,反对蒋经国到校任职。“学生知道这个消息后,纷纷议论起来,形式上表现了这些毛孩子真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居然对太子不大礼貌,七嘴八舌开起会来,决定并贴出了下列的几条欢迎标语:1、欢迎蒋宋美龄做中央政治学校校长;2、欢迎蒋经国的老婆做看护长;3、欢迎蒋经国做总务科长;4、欢迎蒋纬国做军事队长;5、实行学校家庭化。蒋经国知道情形后,就不能去了”。⑥此事让蒋介石颇感意外,“余以为此乃于党于校最有益之事,不料教育部命令发表以后,反对标语与行动突势爆发,其势汹涌,其理由为经国年轻无学,反对培植封建势力,其他甚至牵涉我家庭”,蒋介石感到事件必然与二陈相关,“向来校中教育长应果夫之干涉,不得其人,以致无人负责,校中每况愈下,共产党员组织深入校中,而老教职员与共匪恐经国负责,彻底解除其势力、肃清其党员,以致反对抵抗,视为其生死关头,可知本党腐败与黑暗之一般,痛心益极。惟此事只可以共匪故意捣乱,更又抓到我父子关系,毁损荣誉,视之不以为意”,“此乃果夫、立夫应负其责”。⑦4月22日,蒋介石令陈立夫负责政校风潮的解决,陈立夫却告知蒋“政校反对经国到校,仍甚激烈”,无从消弭。蒋介石表示“余对此惟有痛心,自恨干部无能,用人不当,致为反动盘居,自入污潭,乃决心辞去校长名义,并令经国亦自动辞职,不使反动派乘机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也”。⑧最终,政校风潮以蒋介石、蒋经国的退让而告结束,但蒋介石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不满却不断累积,“对于政校之近状与果、立之无能,以致党务、校务无法改革,不胜忧愤”,“余再不愿掩护若辈,以害党国也”。⑨ 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时有矛盾,但促使二者矛盾激化的事件却是1948年5月的立法院副院长的选举。国大副总统选举期间,陈立夫主掌的中组部难以统驭党内代表,就连陈果夫也感叹“人心日坏,信义不讲,个人权利之争,锱铢必较,为国家、为民族,则置之脑后,如此中国,安得不乱?”⑩最终蒋介石属意的孙科落选,党内陈立夫意见颇大,如4月29日马超俊夫人见到陈立夫,“很生气的对他说:恭喜你,恭喜你的组织部没有组织。”(11)1948年5月1日,陈立夫向蒋介石引咎辞职:“大半年来,办理党团合并、党员总登记及国大立委选举指导诸项工作,在个人虽已竭其忠诚,心力交瘁,终以障碍重重,均未能达成理想结果,即以中央所订之国大与立委之选举指导办法而论,事前考虑确有未臻完善之处,施行之时又未能严守原则,各方步调亦未见配合得宜,因之演成错综复杂纠纷迭起之局。立夫虽未负主持选举指导之责,然身为选举指导委员之一,又为组织部长,自不能辞其咎。惟有恳求准辞本兼各职,以赎衍尤”。(12)陈立夫随即辞去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这次的副总统选举,没有发生组织力量,使他(陈立夫)从组织部座上掉下来,他开始走下坡路”。(13) 陈立夫在国大总统选举之前,“有力方面且有默契,以他出任行宪后的立法院院长”,但“天有不测风云,副总统落选以后,孙哲生的出处问题,自然还是以立法院长一席较为相宜”。(14)事实上,“除了立法院院长以外,实在没有更适当的地位安置他。这样蒋介石就只得支持他仍任立法院院长”,辞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就不得不退而竞选副院长”。(15)行宪后的立法院早已今非昔比,“这个立法院是依宪选举的,性质不同于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立法院。依宪法的精神,这个立法院实是一般民主国家的众议院,它是代表人民行使立法大权的。据宪法所规定,立法院的权力是很大的。行政院是责任内阁,行政院长要对立法院负责,所以立法院对政府的制衡作用是很大的”。(16)陈立夫对竞选位高权重的立法院副院长跃跃欲试,然而“在地方上有些CC做得过火了,未顾虑到各方面人才的运用,大家埋怨CC的重要因素,是在重庆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选举前的提名,现在各地方的巨头进了立法院,都来反CC了”。(17)围绕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选举,“现在院长似乎不成问题,一致推孙,副的却已成为争夺之的”,(18)国民党各派系就立法院副院长的人选展开激烈争夺,就如王宠惠预感的那样:“立法院开会恐怕要比国大代表还多纠纷”。(19) 立法院是政治的大舞台,“当时什么俱乐部、什么聚餐会、什么座谈会、什么社的组织很多,一句话都是在拉关系,想造成自己的势力”。(20)立法委员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组织部陈部长(立夫)等所领导之同志”;第二类是“有主张之党员(不属于陈部长者)、团员、参政员及桂籍之立委”;第三类是“中立性之社会贤达及游离之党员(此类占立委全额半数以上)”。其中陈立夫CC系领导的立委“原有其悠久组织系统,近来萧铮、赖琏等又组织所谓革新俱乐部于文化会堂,约有会员一百余人”,而三青团籍立委则组织新政俱乐部,“其核心人物为黄宇人等,亦为反对组织部之集团”。同时,吴铁城成立自由座谈会,“为言论比较激烈份子所组织,以团员及老立委为基本干部,其核心人物为倪文亚、涂公遂、邓鸿业、刘治平、王培仁、祁志厚、钟天心(刘不同亦有关系,但未参加)等,约有七八十人之多,以吴秘书长铁城主持为号召,现正吸收贤达参加”;桂系李宗仁组织立委,“以改革政治为号召,活动甚力,不惜以金钱广收各立委参加,党员及团员如李世军、范予遂、彭昭贤等均已先后参加,约共有六七十人”。此外还有王俊组织的益世俱乐部,“为中立性而稳健之集团,无甚力量”;王普涵等组织的联合座谈会,“内部份子似比较复杂,意见不易集中,其中以参政员立委比较中立持重,团员立委已先后退出”,但其影响力较为有限。(21) 团派众多立委表示:“假如立夫先生再当选立法院副院长,CC的势力将更膨胀,各地青年团同志所遭受的压迫也就没有解除的可能”,黄宇人更是认为“假如立夫先生当选立法院副院长,中统人员自必将以各种身份渗入立法院各种委员会,如此一来,立法委员的一言一动,都在他们监视之下,必将更对我们一班不满现状的人,故作种种歪曲的报道,引起蒋校长对我们的憎恨”。故而团派立委主张在选举立法院副院长时给予陈立夫以打击,最好使其落选。(22)黄宇人“利用机会联络了所有反对CC系的立委们,如新中学会的童冠贤,民联的于振瀛、陈建晨,改组派的武和轩,朱家骅系的甘家馨,以及吴铁城系的张潜华等,企图公开拒绝陈立夫为副院长候选人”。吴铁城不仅同意张潜华与团派立委合作,并示意“他个人今后要在这部分人中起些作用”,吴所领导自由座谈会“基本上都是些反CC系的立委”。(23)当时在立法委员内部“反统制、反独裁、反陈立夫,要求改革,要求进步,便是最有力的口号”。(24) 为了避免副总统竞选的风波再度重演,5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推定孙哲生和陈立夫做将来立法院的正副院长竞选的候选人,并且命令所有立法委员的国民党员,必须一致服从命令”。(25)5月7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常务委员举行谈话会,蒋又提出孙科和陈立夫为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问题。“此一问题,本来已经中常会无异议通过,蒋校长又征询众意,自是因为知道有很多人正在酝酿反对立夫先生,想藉此镇压”。“CC和与青年团有关的中常委都有多人发言,前者一致支持立夫先生,后者则持反对意见”。(26)谈话会上,“反对立夫者十分之七以上”,最终与会各委员迫于蒋的压力,通过“立夫为立法院之副”。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乱象,令蒋感到“党内纠纷已极,应积极改正领导办法,以资恢复向心力也”。(27) 参加谈话会的团派中央常委如刘健群等会后态度大变,表示“他们在蒋校长官邸起立,并不是赞成立夫先生,而只是对蒋校长表示尊敬”,“决定不论蒋校长的意旨如何,都要反对立夫先生”。5月15日,反对陈立夫的各立法委员于南京安乐厅举行集会,他们“反对党的控制,他们在该院决定不承认党提名的候选人”,试图“集中力量击败陈,将陈视为政治机器和反动力量的象征”,(28)最终决定联合推举傅斯年与陈立夫展开竞选。他们认为傅斯年是学术界中人,以他为行宪后的首届立法院副院长,“不但可以证明我们反对立夫先生并非是党内的派系之争,而且可使国外对立法院有一种新的观感”,并且傅斯年“正在美国医治高血压,CC不可能利用蒋校长向他施压力,迫其中途退出竞选”。(29)蒋介石得知此事后,5月11日感慨道:“青年团旧干部对党部二陈之不满,演成极端反对态度,表示立法院副院长之选举仍不能服从常会之决议。若辈诚不惜毁灭本党历史,以泄其私愤,因之倍增痛苦”。(30)5月13日更是在日记中大骂团派立委“尤以青年团干部阳奉阴违,道义与精神婉劝丧失,殊所不料也。处境之忤逆,无以复加矣。加之物价继涨不已,无法阻遏,经济与党务皆有崩溃之象”。(31)蒋介石此时对陈立夫当选仍旧抱支持态度。 面对团派立委等反陈联盟的挑战,虽然CC系立委有140至160人之多,“占据立法院内第一大派系”,但是“CC的势力日渐削弱与没落”亦是不争的事实。(32)如5月8日陈立夫拜访徐永昌,表示希望晋籍立委予以支持,徐明告其“晋立委恐三分之一,晋方无法控制之”。(33)陈立夫在反对派压力之下,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确保选举成功:“一面由陈立夫亲自出马,分别拜访参加安乐厅集会而有政治影响的立委,并举行盛大酒会招待CC系立委以及与CC系合作的孙科系立委,表示继续竞选的决心。一面由潘公展出面联络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用公开信的方式抨击来抨击安乐厅意见书的错误”。(34)对于即将到来的立法院副院长竞选,双方均摩拳擦掌,蓄势以待。1948年5月16日,就在立法院投票选举正副院长的前一日,“南京有两家晚报刊载胡适给某立委的一封信,说傅氏早已表示不图当立委,劝某某立委打消选其做副院长”,尽管该信是“有关方面非正式发表的”。(35)该立委汪少伦更是在17日公开声明“未接胡适信,更没有和他谈到这件事”。(36)事实上,就如段麟所言,这封信“无论有无,都是少数人利用校长(胡适)的姓名,做政治足球来打击对方”。(37)然而,“很多与傅斯年不大熟识的人,看了胡适的电以后,便信以为真,也就不愿意选一个连立委都不想做的人而开罪立夫先生了”。(38) 5月17日,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揭晓,孙科以550余票的大多数当选立法院院长,陈立夫340余票,以出席人数过半票数当选副院长。尽管蒋在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纠纷中倾向支持陈立夫,但在立法院选举投票当日,蒋介石则态度暧昧,不愿意在CC系和团派等之间的纷争中直接表明立场。陈立夫虽然当选,但面临的挑战与危机亦不容置疑,故而在5月21日面见蒋介石时,“一反常态,并明言其干部怪他太服从总裁,过分使其所部毫无出路”,明言对于行宪后行政院长的人选,不能按照蒋的意思令CC系立委支持张群,蒋介石直骂陈立夫“变态之快,殊为一生最大之教训也”。(39)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矛盾由立法院副院长选举一事引发,迅即在行宪后首任行政院长人选问题上趋于恶化,“CC既然是立法院最大派系,竟不听命中央,这是蒋与陈立夫关系恶化的开始”。(40) 二、行政院院长提名背后的较量 1948年4月国大总统选举完成后,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训政时期的行政院须立即解散,由总统向立法院提名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重新组阁。因此,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张群于1948年4月21日致电蒋中正,请求辞去行政院长职务。(41)一时之间,行政院院长的人选成为蒋介石考虑的首要问题。5月2日,蒋介石正式召见张群,“商议行政院长事,劝其继续担任,彼坚决拒绝”。蒋对张群的态度颇为不满,认为“其语意神态渐现骄矜轻侮之心”,决定另选他人。(42)而此时何应钦以中国派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从美国归来,迅即被认为将是行政院院长的重要人选。5月2日,蒋介石又“约见蔚文,嘱其转商敬之(何应钦),征求其行政院长可否担任也”。(43) 何应钦对于蒋请其组阁一事,暂时接受了行政院长的职位,并与来自各阶层的组织协商,以便较好的提出他的计划和内阁。以后几天里,他希望见到委员长,如果委员长同意他提出的内阁和改革计划,将予以公布。(44)然而,蒋介石随即又拒绝了何应钦要求的改革,(45)他仍旧希望张群能够组阁,“最近虽有请敬之先生出任之意,惟仍未放弃要他蝉联的计划。主席为此事颇伤脑筋”。(46)5月7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常委举行座谈会,除确定以陈立夫为立法院副院长外,还讨论了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蒋校长先提出张群、何应钦两人,说想就他们之中选择一人为行政院长,要大家表示意见,久之,无人应声”,“田昆山低声说出何应钦的名字,蒋校长又说:他要负责军事。言外之意即是要大家赞成张群为行政院长”,(47)“最后仍以岳军为行政院长”。(48)张群在获得蒋和中常委的明确支持后,不再半推半就,“党这方面已经一致的表示对他的支持,无法再事推辞,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并指示陈克文准备五百亿元的特别机密费,以应付组阁各项事宜。(49) 对于蝉联行政院长,张群并非毫无后顾之忧,“再做下去,最困难的是对付立法院这一批委员,人家说我是政学系,其实我一向不搞党这一套,毫无组织,不容易应付”。(50)缘何立委成了张群组阁的最大担忧?这又与国民政府宪政实施后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根据1947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根据下列规定须对立法院负责:“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二、立法院对于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之。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议,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三、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于该决议送达行政院十日内,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51)立法院俨然成为西方国家之议会,尽管此后蒋介石颁布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据此“总统有紧急处分权,就给今后的行政院大开方便之门,立法院的权力已大大削弱”,(52)但不可否认的是立法院的政治地位较之前有了极大的提升。而此时诸多立法委员“对于将来行政院长人选同意案的提出,都存有一种心理,要求将被同意的人提出他的政策,并且要知道他组阁的人事配备”,(53)试图利用立法委员的权力干预行政院的组阁,博取各种政治利益。蒋介石对之极为不满,“近日立法委员中之党员……对行政院长人事亦要求过问干涉”,哀呼“党纪法纪皆荡然无存,内心忧伤,不知所止”。(54)5月15日,蒋介石一度曾有自任行政院院长,以便熄灭任命纠纷的念头,“朝醒后,深虑总统应否就职,或如愿仍退任行政院长,而让位于德邻,再三考虑,决定退让,起床后向天父祷告,究竟应否就职,无论进退皆恳求天父明示,后指点示进,不予辞总统,故决不辞”。(55) 尽管5月7日蒋介石通过召开中常委座谈会的形式暂时达成了张群出任行政院长的党内共识,但在宪政体制下,蒋介石若要顺利行使权力,必须能够在国民党内拥有绝对权威,掌控大多数立法委员,实现对立法院的有效控制。(56)然而蒋与陈立夫的矛盾因立法院副院长选举一事趋于激化,陈立夫领导的CC系围绕行政院院长的任命问题,与蒋介石展开了全面较量,蒋介石的政治权威面临严重挑战。 CC系作为立法委员内部第一大派系,在行政院院长人选的问题上态度极为明确,反对张群、支持何应钦,究其缘由当然与政治权力的争夺密切相关。CC系反对张群组阁,除蒋陈矛盾之外,张群在行政院阁员的任命上不愿意向CC系妥协与让步亦是主因。张群反对CC系立委挟权自重,“宪法很明白的规定,行政院副院长和各部会首长是院长自由选择的。至于政策的宣布,他认为未同意之前不能向立法院宣布,否则有运动同意的嫌疑”。(57)而CC系虽然反对张群,“但却抬不出一个像样的人来,假如何氏能够组阁的话,大部分阁员的位置,是可以由他们一手包办的”。(58)5月18日,在陈立夫领导的CC系立委的策动下,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长同意权之条,又在其议事规则上,附加用人与政策报告质询等条文”,造成“使行政院长无人敢允任此职”的局面。(59) 5月18日,张群闻讯后,意识到“在这局面之下,无法干下去”,(60)当日即向蒋介石提交辞呈:“本月八日暨十五日先后奉谕敦迫,经长时商榷考虑之结果,新阁人事政策均难一当,加以日来观察舆情,考验事实,立法院中集团对峙之局已成,继则势难两可。偏至则理有未安,其结果不独不能获得行政与司法之合理制衡、推行宪政,且将进退失据,应付道交马川,致政局日形动摇,纠纷日趋剧烈,此素性所不屑,亦良知所不许。群非敢避劳怨,亦不恤牺牲,只以国家在此动荡转捩之交,行政院之成败关系国家永久之前途,若明知不可,而眛然尝试,是自误误国,咎戾弥深,关于行宪时期首任行政院长之人选,务恳另行考虑,群此志已决,无论如何敦迫,皆不敢承,短期内拟辞京返籍,省母养疴”。(61)当日,蒋介石并未知悉立法院通过的各项条文,对张群再次坚辞行政院院长颇为不满,“回属忽见岳军,坚不愿新政府行政院长,此种行态实非意料所及,且出人情之常。以彼提辞职时,我已属敬之准备组阁,彼又愿继续组阁,故转请敬之辞让,而今日即于组织新政府之前夕,彼又突然坚辞,仍令人不堪设想也”。(62)5月19日,蒋明白事情原委后,斥责党内立委“在平时受本党组织统制之苦闷,以今日民主宪政之口号下,揭露其极端反动,而且反常失却理性如若狂之行态,此为梦想所不及。党员如此,更增厌心,而且顿崩厌世之念,心理悲惨,环境险恶,诚有不知所止之感”,召集孙科等人“商立院党员谈话会之程序,交换同意权条文之意见”,可惜最后“仍无结果”。(63)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宣布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然而此时蒋却毫无欣喜之感,“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悽惨未有如今日之甚”,因为“按照欧洲各国常情,新阁应在一两天之内组织完成,假如在时局特别动荡的时候,新阁甚至希望能在数小时之内组成,使国家的神经中枢不致因政潮的波动而中断太久,俾可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64)内定的行政院长坚辞不就,组阁之事遥遥无期,即便蒋转而倾向于何应钦,何也不愿出任,“朝课默祷,约见立夫、略三、道藩商讨敬之行政院长问题,彼亦不愿担任也”,蒋表示“余则忍耐,总想设法行政院长能使之早日通过也”。(65)当日下午,立法院召开第二次大会讨论有关同意权的议事规则,共有甲乙丙丁四个方案,其中甲案为总统向立法院提名行政院长,须将各部长名单一并提出;乙案规定必要时得请所提名之行政院长说明其施政方针;丙案仅要求总统向立法院提出行政院院长人选;丁案则是总统直接任命行政院院长,不需向立法院提名。会议之前蒋介石“宴请立法委员于国防部,作了一篇很不客气的演讲”。(66)蒋介石批评“这次国民大会和立法院一部分同志的表现,无异自相残杀,自速灭亡!”要求党内立委在讨论制定立法院议事规则时,“关于同意权的行使各条,拟有甲、乙、丙、丁四案,在没有决定采用那一案以前,各位似应加以郑重的考虑,我认为如果采用甲乙两案中之任何一案,都与宪法的精神不相符合,而且事实上如需行政院长事前向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和用人意见,谁也不愿意出来担任行政院长。我今天以个人的资格向各位说明,关于行政院长的人选,各位在院外尽可向我提出意见。我可以尊重各位的意见,正式向立法院提出”,蒋表示“我觉得各位在同意权方面,不必在文字上斤斤较量,要知道不成文宪法的养成,才是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67)“如果这样的条文竟然通过,总统我也不干了”。然而蒋的此番居高临下的讲话,“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发生更坏的反应”,“开会的时候,会场情绪非常激昂,结果竟通过了总统认为违宪的条文”。(68)“纵有江一平等致力采用丙案,而经过热烈讨论,终以三百零六票通过乙案(到场五百零五人)”。(69)乙案的通过使得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威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就职的第一天,立法院便直接给总统这样的一个无情的打击,将来的发展如何,谁能料得及呢?”(70) 立法院通过乙案之后,“行政院院长的人选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第一,是蒋总统因此生了气,不肯另行提出人选来。第二是张岳军和何敬之两人都因此坚决不肯干,岳军先生并且于今晨飞赴重庆,表示决心。”(71)5月21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不料陈立夫一反常态,明言CC系成员认为陈立夫之前唯蒋命是从,使得CC系政治势力日趋低落,尤其蒋出游太湖更是暗示不支持其竞选立法院副院长,因此向蒋表示“他要求其所部赞成张群为行政院长,势已不能”。蒋介石听后,一怒之下竟欲辞职下野,“余乃告其辞职下野之决心,余本为爱护前方剿共官兵与全体党员,所以不忍坚辞总统候选人,今你中坚干部既如此心理,我已无可依恋矣”。(72)然而陈立夫在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上,并未因蒋的下野示威而有所让步。21日,在中央党部召集党内立法委员开会,就行政院院长举行假投票,颇有挟立委投票权逼蒋就范的意味,“结果何敬之得二百五十余票,张岳军约九十余票,吴铁城得八十余票”,何应钦成为行政院院长的首选。(73)蒋介石在得知假投票结果后,“自觉愤激过甚,神经几失常态”,认为陈立夫此举是逼其就范,“彼对余亦弄手段,以假投票方式来压迫胁制,使余不能不顺从其意,提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藉此以排除其政敌张群,殊为可痛”。(74)蒋陈矛盾开始不断升级,“蒋先生大恨陈立夫办党无效果,一意嫉妒,名为对政学系,实不啻害党国事也”。至于蒋愤而提出下野一事,党内干部均表反对,“蒋先生无论下野成不成,但声张出去,必至影响军事”。(75)事实上,蒋并非真打算下野,因此在宋美龄、蒋经国等众亲信劝说下,22日遂即打消辞职念头,“妻与子皆劝余相忍为国,无论如何,此次必须再加以更大努力,忍辱负重也。否则前方官兵制心必动摇,后方经济必崩溃,将予共匪灭亡民国之机会矣”。(76) 5月22日,蒋介石召见立法院院长孙科,商谈行政院长问题,仍“未得结果”,(77)就如立法委员陈克文担心的那样:“总统虽就了任,因为没有行政院长,无人副署,不能发布命令,不能组织政府。无政府状态已经三日,再拖延下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乱子。立法院停会已两天,等候总统把行政院院长的人选提出来。总统却因为立法院通过了他不愿意的议事规则,生了气,不肯提出人选。这僵持的局面,如何打开?宪政政府一开首便遇如此困难,前途实在可虑”。(78)23日,蒋介石经仔细考虑后,决意不让何应钦组阁,“立夫、道藩等借预测投票为名,以敬之为工具,而驱除岳军,其用心之恶劣,好弄手段,欺蒙党魁,于公于私皆不当,乃以实情明告敬之,故余决不强其所难”。(79)蒋令顾祝同向何应钦转达此意,“下午何敬之来述蒋先生迩来无论直接间接曾约其出长行政院,顷间顾墨三来略言蒋先生拟请其考虑云云,并述立委派别多难于应付”。(80)同时,蒋开始考虑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另举翁文灏为新行政院长”。当晚蒋召集孙科,表明其最终决定,“约哲生等商谈行政院长事,决提翁也”。(81) 提名翁文灏一事并非蒋介石突发奇想,早在5月2日蒋就已电召翁由平回京,“兹有要事待商,请即日返京为盼”,(82)表明蒋事先已有所考虑与准备。而蒋认为翁“向少系派关系”,(83)“是个学者,过去对经建多所努力,廉洁自好”,(84)在CC系立法委员与总统争执的僵持局面下,倒不失为双方均能接受的选择。5月24日,蒋“朝课后,即约本党老者征询行政院长拟提请翁文灏之意见,彼等皆甚赞成,乃到中央党部纪念周后开临时常会,提名翁为行政院长,讨论一小时,表决通过。常会以立法院中之党员对中央决议每持反抗态度,如常会决议后恐不能在立法院通过为虑,故有主张不用决议方式,而先开立法院党员大会通过后,再由党会决议。余以为此乃不成体统,中央自弃经纲不可也,仍由常会决议,一面召集立院党员会议,要求其赞成也。下午二时召集立院党员会议,余亲自出席说明”,(85)蒋向党内立委坦诚“张、何两人坚辞不干,中央常会已经决定另行推荐翁文灏同志,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个人的困难和时局的严重,予以一致的支持”。为保证提名翁获得通过,蒋态度较20日的训话缓和得多,“蒋总裁今日说话的态度和口气非常的诚恳和平,没有丝毫命令的意思,出席的党员也就因此大受感动,一反前几日那种反抗的精神”。(86)最终,党内立委“全场一致接受”,并未按照乙案要求行事,“乃开立法院会议,审查结果甚为顺利,通过即交付大会表决,以六分之五以上票数同意当选也”。(87) 翁文灏获得立法院投票通过,成为国民政府立宪后首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如释重负,“于是新政府第一之难关通过,此为一星期以来惟一之难事,幸得解决矣”。(88)尽管蒋介石25日向翁文灏保证赋予全权,“彼恐余不能以全权赋予组阁,余即告以全权赋彼,余有所见亦必开诚明告也”,(89)但外界认为翁氏组阁,“阁员人选并不是翁院长个人能够自由决定的。民二十四,蒋做行政院长,翁做秘书长;现在蒋先生做了总统,翁做了行政院长,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变动而已”,(90)尤其是翁文灏组阁后,面临立法院的质询与责难,更是举步维艰,“翁将发现他本人处于不愉快的地位,在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委员长和难以对付的立法院之间,他将无可奈何”。(91) 三、蒋介石控制立法院的企图受挫 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院长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立法院CC系立委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新的冲突仍旧不断出现。5月25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陈对此前违逆蒋之旨意、令CC系立委借假投票逼蒋就范,“毫不反省其重大错误”,蒋认为陈“好弄小手段,仍一意怪人不是,可痛”。26日,蒋介石召开党内宣传汇报,“对党务不满,因之斥责立夫之过错,毫不留情”,事后蒋担心过于斥责陈立夫,可能造成团派干部趁势打击CC系,“其中有反对立夫之青年团员,亦在其内,闻之必对立夫更加不利,党内纠纷必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92)CC系立委仍旧我行我素,对翁文灏组阁并不予以配合,5月27日,翁文灏向蒋汇报组阁进展,“立法委员保荐部长与彼此攻讦,几乎不遑应接”。(93)5月31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翁文灏报告行政院阁员名单,CC系立委程天放表示反对,认为“旧阁员太多,恐难社会所希望”,只是在蒋表态后,方得以通过,“蒋先生谓国防、财政、粮食、资委会四部门皆重要机构,何谓太少”。(94)随后,翁文灏向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更成为CC系立委发泄不满的对象。 为避免翁文灏向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过程中遭遇困难,6月7日,蒋介石提前召集党内立委举行谈话会,“介绍行政院长翁文灏在未向立法院提出报告之前,先向本党籍立法委员说明行政措施,并交换意见”。(95)翁文灏报告完毕,“出席的党员纷纷发表意见,差不多都是表示不满意的”。蒋当时“没有表示意见,只说:翁院长的施政方针原定明日出席立法院报告,各同志既然有这许多意见,可分别以书面送交翁院长参考。翁院长出席立法院的报告日期也可改迟两三天”。(96)自6月11日起,翁文灏内阁成员开始向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翁氏“报告完毕,引起极热烈的质询和批评。送发言条子要求发言的达一百五十人左右。大部分发言的立法委员都表示不满意,不是说过于空洞,便说没有重点,又有说这和政府过去敷衍参政会的官样文章毫无两样的”。(97)6月12日,蒋介石得知“立法院委员上午对翁院长施政方案报告多加责难,其质询且越出范围,失态不敬,令行政院各部会长气愤难受,尤以组织部所属一派赖琏、萧铮之态度更为恶劣,闻之痛愤”,(98)当即召见陈果夫,“斥责其所培植之干部,在立法院出反动言行,徒贻反对者所快,为共匪造机会,使我党自趋灭亡”。同时,为减少立法院的阻扰,蒋选择联合团派立委对抗CC系,蒋下午召见团派立委刘健群等,请其支持翁文灏内阁,当晚又与翁“研究对立法院不规行态之办法”。(99) 新内阁成员面临立法院连日质询,“有些阁员的确忍耐不住,露出引退的意思”。(100)6月13日,翁文灏、王云五“皆表示辞职,以不堪立法委员之污辱也”。当日,蒋介石为此“召见彦棻、扩情指示立法院委员对行政院施政报告无礼无法之不规态势,应加纠正与停止质询之办法。下午召见道藩、布雷以及健群等,皆为立法院问题”。(101)6月14日,立法院就行政院院长施政方针进行投票表决,在蒋的干预与运作下,有惊无险,得以通过。但立法院动辄挟质询权压迫政府之事仍旧时有发生。6月24日,立法院要求“检讨河南军事失利与追究责任”,蒋认为立法院此举“无理取闹,不胜愤懑。乃去电责备河南立法委员之不知其不法与党员之不负责,而徒责军队与政府,实为本党党员无道德、无纪律、无廉耻之表现”。(102)面对立法院愈发难以控制的局面,蒋介石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立法院之职权与态度,总应设法根本解决也”。(103) 事实上,早在翁文灏通过立法院投票初始,蒋已对控制立法院之事有所思考。6月1日,蒋拟定的六月份大事,其中之一即为立法委员之组织与联系人选。(104)6月4日,蒋介石“研究组织立法委员与旧青年团籍立法委员之形势,决定使中立份子组成一派”,实则决定扶持团派立委,以便和CC系对抗。当日“下午召见各省市旧青年团主任干事三十余人”,蒋一反往日斥责团派立委的态度,对之极为赞许,“此辈精神与能力皆比党部主任委员优强,而立夫等组织部皆拒之于门外,可叹”。(105)6月16日,蒋介石再度召集立委谈话,“同时应约前往的共十三人,都是立法委员。以派别来说,除了两陈系统之外,各方面的分子都有”。蒋仍旧不满立委的言行,“米价每石已涨至九百八十万元,经济情形已至最险恶之境地。立法委员除在其院内,对政府无端攻讦,作不堪入耳之言。此外其余如刘不同、黄宇人皆对新闻记者公开诋毁余个人,并诬辱本党。此辈身为党员,而且皆为黄埔学生,由党培植留学者,今竟反噬,违背至此,不仅为共匪张目,而且为外国利用,使本党自取灭亡之途。如不有对上帝之信心,与本身人格之自信,则早自杀,以了一生矣”。告知党内各派系立委,“目前最重要的须把我们的党加以改革,党的改革最好先从立法院内的党员做起,请大家切实研究改革的方法”。(106) 鉴于立法院的纷乱情形,1948年6月,翁文灏向蒋建议组织党团进行控制,侧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因翁文灏为学者型官员,故而应加强与各派立委的联系,“一般同志希望李秘书长惟果能代表行政院,不时保持直接联系”。其次,依靠团派立委的力量,逐步控制立法院,“立委倪文亚、张光涛同志等均向职面称,倘由张道藩、郑彦棻二同志负责联系,或疏通意见,乃南辕北辙之办法。倪等说郑同志在团方向不受欢迎,已无发言资格,更谈不上信任问题。例如郑向同志说应向东,一般同志必反向西。这几天有若干同志本不准备说话,郑去劝了,有四五同志立刻说,本来不想发言,郑叫我们不说话,我们今天偏偏要发言,骂一顿给他听听。一般同志认为联系工作以年青而色彩稍淡者,如谷正鼎、楼桐荪、宋述樵、陈傅生等担任为宜”。此外,给立委较高的物质待遇,以便收买人心,“立法委员多来自各地,对首都地方情形多不甚熟悉,平日苦无游休之所,应由中央拨款密为组织俱乐部,设备食宿、书报、弈棋等部门,廉价招待立法委员参加消遣,以资联系”。(107) 然而立法院并未因此而易于掌控,7月20日,蒋介石仍旧在日记中感叹“立法院之纷乱与行政院之推诿、不负责任,殊为可痛”。(108)1948年12月,孙科、陈立夫辞去立法院正副院长,CC系与团派立委再度围绕正副院长展开纷争,蒋介石控制立法院的努力未有任何实效。待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汲取教训,重新改造国民党,“来台湾后的CC,有意归顺中央者,一一被中央以挖墙脚方式拉走;不愿归顺者则备受打压。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CC呈现出相对的弱势,与权力核心渐行渐远”。(109)立法院的纷嚣亦不再呈现。 1948年4月国大总统选举之后,国民党党内各派系围绕立法院副院长与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展开激烈争夺,首先团派、朱家骅系、桂系等针对陈立夫竞选立法院副院长,置国民党中央决议于不顾,组成反CC系联盟,推举傅斯年与陈展开竞争,最终CC系险胜,但陈立夫认为蒋并未给其有力支持,进而导致蒋与陈立夫领导的CC系矛盾激化,双方在行政院院长提名问题上展开激烈较量。蒋介石支持政学系张群蝉联行政院院长,作为立法院第一大派的CC系则挟质询权与同意权以自重,推举何应钦出任,并制造假投票,逼迫蒋介石就范,蒋无奈之下,选择各派系均能接受的翁文灏出掌内阁。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后,CC系立委在翁向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的过程中,多有责难,使得翁氏内阁面临巨大危机,但在蒋的干预下化险为夷。正因如此,蒋开始考虑加强立法院的控制,不仅要求行政院各部会加强与立法院的联系,并选择倚重团派立委对抗CC系,亦通过物质享受笼络立委,但蒋的努力极为有限,立法院的乱象一直延续至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通过对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前后事件的梳理,我们或可清晰地窥见国民党政府宪政实施的本质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首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民主宪政的实施同样如此,需要有客观的政治、社会环境作为基础,方能实现国家政治体制的现代转型。国民政府1947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宣布实施宪政,然而国民党内部派系纷繁复杂,宪政民主体制在国民党派系政治的作用下,迅速异化为各派系争权夺利的工具,宪法赋予立法院的质询权与同意权,反却成为CC系与蒋介石就行政院院长提名展开较量的制度保障。就如立法委员陈克文的感慨:“在民主的潮流下,大家仿佛认为一个委员会里面有几个固定的召集人是违反民主的,再加上一些嫉妒和互不相信的心理,在民主这名义之下,拼命反对设置固定召集人。他们对于各委员会将来的实际工作如何进行,似乎不加重视。经过这一场喧嚣,愈可以看出,我们对于议会政治实在幼稚得很,大家都缺乏经验,应该加意学习”。(110)而国民党内的各派系,因民主竞选的刺激,日趋组织化与公开化,宪政体制甚至成为加速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与混乱的催化剂,蒋介石就曾对之不无忧虑,“今日极为民主制度危国忧也”。(111) 其次,CC系作为附属于蒋介石的次生派系,曾为建立、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与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CC系组织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对之的控制日趋困难,尤其是围绕政治权力的分配,CC系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累积,待至行宪后首任内阁的任命,CC系依靠宪法赋予立法院的权力,向蒋介石的权威公开挑战,尽管最终CC系提名何应钦组阁未能实现,但至少可表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与反对。正是因为陈立夫领导的CC系公然违逆蒋的旨意,造成行政院院长任命问题上,CC系与蒋对峙的僵局,CC系此后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逐渐边缘化,陈立夫也不得不被迫出国,远离权力的核心。 此外,蒋介石迫于美国及国内的政治压力,宣布召开国大、实行宪政,然其并非拥有现代民主思想的政治领袖,仍旧是威权式的独裁者。因此,当立法院成为宪政体制下制约总统与行政院权力的重要机构时,蒋介石明显缺乏耐心,急欲实现对立法院的控制,就如李宗仁对蒋的比喻:“现在的总统好比一匹野马,自由自在惯的,一旦加上缰绳,配上鞍镫,并且坐上一个人,这匹马自然不肯往前跑,并且不免发怒了”。而行宪后首任行政院院长的难产,固然由于CC系立委的发难,但蒋不顾党内众议,坚持己见,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立法委员陈克文自述“朋友见面都把这事做谈话的中心,仿佛异口同声,一致非难蒋总统的态度,以为不够民主,只要他老人家念头一转,不坚持成见,改变作风,这问题立即可以解决”。(112)蒋介石忽视党内成员意见表达的诉求,丧失的却是其政治权威。 注释: ①秦孝仪编纂《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册,1948年4月3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3432页。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抄录自胡佛研究所,下文不再分别注明。 ③代表性研究论著包括:刘维开:《1940年代的吴铁城》,《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易青:《“行宪”后的立法院》,《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张皓:《蒋介石与CC系在〈中华民国宪法〉下的权力之争》,《历史档案》2008年第2期;张皓:《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与国民党派系权力之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1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④刘凤翰等:《梁肃戎先生访谈录》,“国史馆”1995年版,第73—74页。 ⑤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⑥康泽:《党团合并前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一个侧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总14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⑦《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21日。 ⑧《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22日。 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24、26日。 ⑩《陈果夫先生日记摘录》1948年4月20日,徐詠平:《陈果夫传》,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948页。 (11)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4月29日,第1085页。 (12)《陈立夫呈蒋中正准辞组织部长及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典藏号:002-020400-00041-023。 (13)《陈立夫出国侧闻》,《新闻杂志》1948年第1卷第5期,第5页。 (14)《陈立夫空战傅斯年》,《新闻》1948年第2卷第5期,第10页。 (15)毛翼虎:《在国民党立法院内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总13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16)《社评:立法院集会了》,天津《大公报》1948年5月11日,第2版。 (17)陆宝千:《黄通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273页。 (18)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9日,第1091页。 (19)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3日,第1087页。 (20)毛翼虎:《在国民党立法院内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总138辑),第65页。 (21)《翁文灏报告立法委员对于政治主张之分析及其动态》,“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典藏号:002-080101-00015-013。 (22)黄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册,吴与记者报社1982年版,第68页。 (23)张潜华:《国民党行宪立法初期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总138辑),第52页。 (24)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13日,第1094—1095页。 (25)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3日,第1087页。 (26)黄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册,第71页。 (2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7日。 (28)"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8,U.S.of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 of Unite States,1948,Volume Ⅶ,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8,p.239. (29)黄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册,第74—75页。 (3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11日。 (3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13日。 (32)《新立法院内的各派系》,《新闻》1948年第2卷第5期,第16页。 (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8年5月8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64页。 (34)张潜华:《国民党行宪立法初期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总138辑),第53页。 (35)《胡适的一封信劝勿举傅斯年》,天津《大公报》1948年5月17日,第2版。 (36)《傅斯年竞选余波》,天津《大公报》1948年5月18日,第2版。 (37)《段麟致胡适》1948年5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980年版,第398页。 (38)黄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册,第77页。 (3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1日。 (40)刘凤翰等:《梁肃戎先生访谈录》,第76页。 (41)《张群呈蒋中正行宪后行政院宜另行考虑人选》,“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典藏号:002-020400-00010-093。 (4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日。 (4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日。 (44)"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6,FRUS 1948 Volume Ⅶ,The Far East:China,p.223. (45)"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7,FRUS 1948 Volume Ⅶ,The Far East:China,p.225. (46)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6日,第1089页。 (47)黄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册,第69-70页。 (4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7日。 (49)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8日,第1090-1091页。1948年4月物价指数为377 642倍,500亿法币约为1936年币值的132 000元。 (50)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6日,第1089页。 (51)《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18页。 (52)《社评:立法院集会了》,天津《大公报》1948年5月11日,第2版。 (53)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10日,第1092页。 (5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14日。 (55)《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15日。 (56)易青:《“行宪”后的立法院》,《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第123页。 (57)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10日,第1092页。 (58)《翁内阁组成的前因与后果》,《新路周刊》1948年第1卷第4期,第16页。 (5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19日。 (60)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18日,第1097—1098页。 (61)《张群呈蒋中正辞行政院院长职务》,“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典藏号:002-020400-00010-106。 (6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18日。 (6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19日。 (64)储安平:《评翁文灏内阁》,《观察》1948年第4卷第15期,第3页。 (65)《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0日。 (66)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0日,第1098—1099页。 (67)《立委同志应发扬党性尊重宪法》1948年5月20日,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84年版,第464-469页。 (68)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0日,第1098—1099页。 (6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8年5月21日,第67—68页。 (70)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0日,第1098—1099页。 (71)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1日,第1099—1100页。 (7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1日。 (73)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1日,第1099—1100页。 (7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1日。 (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8年5月22日,第68页。 (7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2日。 (7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2日。 (78)《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2日,第1100页。 (7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3日。 (8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8年5月23日,第69页。 (8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3日。 (82)《蒋中正电翁文灏即日返京商要事》,“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典藏号:002-070200-00024-016。 (83)翁文灏:《回顾往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84)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4日,第1101页。 (85)《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4日。 (86)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4日,第1101页。 (8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4日。 (8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4日。 (8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5日。 (90)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8日,第1103—1104页。 (91)"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24,FRUS 1948 Volume Ⅶ,The Far East:China,p.256. (9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5、26日。 (9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7日。 (9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8年5月31日,第71—72页。 (95)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5册,1948年6月7日,“国史馆”2013年版,第80—81页。 (96)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6月7日,第1109—1110页。 (97)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6月11日,第1111—1112页。 (9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6月12日。 (9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5册,1948年6月12日,第133—135页。 (100)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6月15日,第1112页。 (10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6月13日。 (10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5册,1948年6月25日,第261页。 (10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6月14日。 (10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5册,1948年6月1日,第19页。 (10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5册,1948年6月4日,第52—53页。 (106)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6月16日,第1113页;《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5册,1948年6月16日,第181—182页。 (107)《翁文灏报告立法委员对于政治主张之分析及其动态》,“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典藏号:002-080101-00015-013。 (10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7月20日。 (109)刘凤翰等:《梁肃戎先生访谈录》,第88—89页。 (110)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8日,第1103—1104页。 (11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7日。 (112)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8年5月22日、23日,第1100—1101页。标签:陈立夫论文; 张群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海时事论文; 行政院长论文; 何应钦论文; 立委论文; cc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