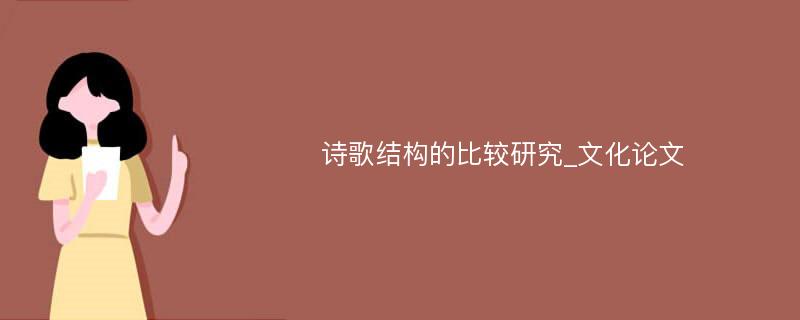
诗意结构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意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是一种“言”(即“话语”),甚至就是作为始源性语言的那种“言”。“诗言志”一说告诉我们:诗这种“言”发自我们的“志”,“志”,即“志意”、“怀抱”、“回忆”之类的思虑,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志”与“意”没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拿涵义较广的“意”作为诗在我们头脑中酝酿的起点比较合适。任何形态的“意”都是思维的产物,也就是说都已经从感性认识的基础提升到知性以至于理性认识的水准,所不同的只是:有些“意”是直觉到的,大部分的“意”则是在已有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过程而产生的。诗意是直觉意义与逻辑意义的结合物,离开前者则非诗,排斥后者则难以成言,前者便无以寄托。清代诗学名家王士禛与其门人郎廷槐的答问中已经扼要地说明了其间关系:“志非言不形,言非诗不彰”。[①]这就是说志、言、诗三者既有同一性,又有依次递进的差别:不成言的“志”是心中的混沌一片,言而非诗,则只是传达单方面的逻辑意义的日常话语,因此不象诗那么感人。显然,从这里引伸开来,我们就可以将诗作为人类从认识上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情感或娱乐作用包含在其中,而不是孤立的或与认识并列的;而且,“意”在这种诗性认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一、“以意为主”和“修辞为要”
在各类文体或“话语”中提倡“以意为主”,在中国渊远流长。《孟子·万章》上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批评上如此重视志意,那么,写作的要旨理所当然是“意义”的创造或表达了。《庄子·天道》中说得更明白:“语之所贵者,意也”。西晋陆机(261—303)在他的文学批评专著《文赋》的序中明确地以物、意、文三者的关系作为衡文的标准。他写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比最早出现于《周易·系辞上》的“言不尽意”一说有所发展。《文赋》正文每涉文体结构均以意与辞两者并重,尤其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其中“情”即指诗中之“意”,因为中国古典诗以抒情的短篇为主;而“绮靡”则指辞的富丽纷繁,是因“情”而发的。《文赋》后面又写道:“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等,从正反各个方面显示情思与言辞密不可分的主从关系。
后来,《后汉书》的著者范晔(398—445)在《文赋》的基础上更显豁地提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侄书》)。到了南朝齐梁时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刘勰那里,他便不仅继承前人的论说,阐明“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文心雕龙·体性》)等情理之意主宰言文的原理,而且在开宗明义的《原道》篇中已将文意提高到“道”的高度来认识,写道:“道沿圣(人)以垂文,圣(人)因文而明道……《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里将文辞的力量完全从属于作者的“真理性的认识”(“道”),一方面使“意”的潜在的人文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开了文学理念化和教诲主义的弊端。
从“以意为主”发展到“道之文”(即“文以载道”),在逻辑上顺理成章,但实践中往往低估了艺术性的“文”(现称“文学”),尤其诗,在文体上的特殊要求。“意”以至于“道”在应用文和理论著作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在诗歌领域中,意与辞,诗性意义与诗体形式,必须更加完好地结合在一起;诗人最初模糊的意念往往只是在落实到某些语句或韵调之时才生发开来,如果混同于一般逻辑思维中的概念,诗的创造性想象活动便要受到抑制。但是,诗的想象活动首选的目标是细致入微地观照生活之真,因为只有真中才有美,诗人的愿望也只有在想象之真中才能得以满足。如果反其道而行,循美以求真,有时便难免撷取其花叶而遗弃其根茎,复古派或唯美派的艺术家往往就步入这一歧途。既然诗意以求真为第一目标,某些流派的诗人在艺术领域中更加偏向于哲理的探求,或者更多从真情实事入手,这些仅仅属于艺术风格和趣味问题,应该得到读者的同情和理解。南宋诗评家严羽过苛批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沧浪诗话·诗辩》),实有偏颇;后来明代人盲目推崇和模拟盛唐诗风,产生不少“有词无意之诗”,就是一大教训。清人吴乔(1611—?)对此作过十分公允的评价:“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②]
在我国的古典诗领域一般还是“以意为主”的观念比较流行。例如,清初大诗人学者王夫之(1619—1692)就写道:“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所谓“无意之诗”,他指的是“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原注),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还指用下述方法写出来的诗:“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事,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③]由此看来,与“以意为主”分庭抗礼的诗派也大有人在,而且可以远溯至“绮丽不足珍”的两晋南北朝的许多诗文。[④]凡是“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或者只做些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的诗人所看重的是空泛或藻饰的语词,而不在乎“意”之轻重深浅、新旧正误,其诗通篇下来必然如同没有统帅的乌合之众,所以称之为“无意之诗”并不为过。
无意之诗以“修辞为要”,如清初有人问当时的著名诗人王士禛(1634—1711):“萧亭先生论诗,修辞为要,辞佳而意自在其中,未达其旨”?王答道:“以意为主,以辞辅之,不可先辞后意”。[⑤]自从明代初,中期一些诗人学者提倡学习盛唐诗以后,约有二百来年的时间里,中国古典诗处于低谷,其主要特点就是许多诗人刻意模拟唐诗中的比兴手法,如吴乔所指摘的:“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⑥]清代不少诗家注意到这个问题,除了王夫之,王士禛,吴乔等清初论者着力倡说“以意为主”外,清代中期的赵翼(1727—1814)强调诗要创新,要切题,不仅“兴会”要超绝,还要“肌理”亲切、逼真,[⑦]清代后期的何绍基(1799—1873),祝周颐,王国维等则从诗人的人品、学养方面着眼,认为写好诗词的先决条件是要有“真性情”。归根结柢,他们都把发现或培养诗意作为登入诗歌殿堂的基石。有些诗评家象刘熙载(1813—1881)那样,仍将“志”作为诗所擅长表达的一种“意”,并指出在诗歌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此有忽视的趋向。例如,刘在《诗概》中写道“古人因志而有诗,后人先去作诗,却推究到诗不可以徒作,因将志入里来,已是倒做了,况无与志者乎”![⑧]此处的“志”显然就是“意”。
以上简略地浏览了“以意为主”和“修辞为要”两种不同的诗歌创作原则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具体表现。其中的“意”既可以看作为由“志”、“情”、“理”等意识内容衍生出来的“作意”,也可以认为是上述意识内容的总称,都起着联系客观存在(“物”)和艺术作品(“文”)二者的中介作用;而“辞”则是作品的外观形式,包括语句及其修饰方式,它们既可以有“意”来主导和贯穿其中,也可以是无“意”或少“意”的纯表现形式,所谓“浮词”、“游词”等均可指后面这种形式的语句。但是,“修辞为要”并非都是漫无意旨的文字游戏,我国古典诗人孜孜以求的“兴趣”、“格调”、“神韵”、“性灵”等诗性,虽说一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终究还是经过语言文字巧妙地传达给读者的。王士禛精辟地归纳了我国古典诗上述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沂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⑨]据此可知,那些倡导“兴会”之道的诗人一般与执着于由学问而来的“根柢”者无缘,如同主张“修辞为要”的人便疏远“以意为主”一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王士禛本人既倾向于“神韵”之类的“兴会”,又不赞成“修辞为要”,那么“神韵”究竟凭什么表现出来呢?这也不难,他所谓的“神韵”就是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那种“清远”的诗歌风格。(《池北偶谈》)它讲究自然、真切、不过份藻饰的韵致,应该说是非同一般的修辞方式;至于其所主之“意”(自我性灵或恬淡的人生态度)与一般立足于现实和历史(包括书本知识),重视逻辑关系的那种“以意为主”的路线相去甚远,说明诗中别有“他意”,也就是常说的“言外之意”。
象王士禛一流着力强调诗中“言外之意”的中国古典诗人和诗评家与西方近现代倾向于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派人有些相似,所不同的是后者一般比较公开地承认自己倾心于“语言的魅力”。例如,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1871—1945)认定:“严格地称为‘诗’的东西,其要点是使用语言作为手段”。他又将“纯诗”看成是“对于由语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⑩]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1914—1953)也说:“开始之时,我之所以要写诗,是因为爱上了言词”;“随着阅读范围(当然不限于诗)的不断扩大,我对言词的真正生命的热爱也与日俱增,终于明白了:我必须永远与言词生活在一起或者生活在其中。事实上,我只能是言词的写作者,此外便什么也不是”。[11]因此,以语言研究为主体的诗学在本世纪的西方比比皆是。就是以文类学为主体的西方传统诗学(亚里士多德首开其例),发展到现代,也不主张抒情诗“以意为主”。例如,瑞士苏黎士大学已故诗学教授埃米尔·施泰格尔(1908—1987)认为抒情诗是“话语的音乐”和“话语的意义”的统一体,“然而,如果有人更多地任凭音乐的直接作用摆布,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诗人早已悄悄准备好让音乐成份占据某种优先地位。他偶尔偏离针对意识的语言的规则和习惯去讨好语调和韵”。[12]接下来,施泰格尔表示不赞成歌德与埃克曼谈话(1825年1月18日)中所说的:“一篇诗的真正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或动机),而人们却不考虑这一点;无数的诗篇没有任何母题(或动机),只靠情感和铿锵的诗句来反映一种存在。那些半瓶醋的诗歌爱好者往往以为,只要学会了做诗的技巧,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他们错了”。他更加不满于歌德如下的论断:一首诗歌只有通过散文的释义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生命力何在。于是,他用歌德的一首名诗《对月》来反驳歌德的上述见解,认为百余年来人们对这首诗的情境,甚至写作的对象,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仍然喜爱它。现选取《对月》一诗的开头五节来看情况究竟如何:
你又将朦胧的银辉
倾泻在林间溪谷,
你又将我的心魂
从够劳的身躯勾出;
你那柔和的光波
洒遍我庭园的内外,
一如好友的青睐,
时时怜顾我的劳作。
昔日的悲欢苦乐,
还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徘徊于忧喜之间,
在寂寥中频频回首。
流吧,流吧,可爱的小溪!
我再也找不到慰藉,
找不到嬉闹和热吻,
那段挚情就这样流逝。
但我曾经拥有过
至为珍贵的瑰宝!
纵使人生满是苦恼,
也决不会将它埋没!
这首诗写于1777~1787年之间,是歌德从“狂飙突进”的年代向“古典主义”过渡的时期里完成的。这时期他应聘在魏玛公国任职,过着繁忙而平凡的生活,静夜对景遐思,不能不勾起对青少年时代如梦如幻的爱情和友谊——性质上难以明辨的一种怀旧的诗意——的憧憬,兼含着对已逝的青春欢乐的眷恋和对眼前孤寂情景的惆怅。这是西方一首典型的“浪漫诗”,具有明显的“作意”或主题:厌倦散文式的现实生活,向往诗情画意的过去和未来;至于那位他为之魂牵梦系的“好友”是男是女,并不重要。施泰格尔想把这首诗归入“无意之作”,理由不足。作为一首“浪漫诗”,它颇受音乐性的“旋律”的支配,倾向于通过反复的吟咏以尽其意,但决非要以“话语的音乐”掩盖“话语的意义”。此诗后面四节的主要作用便是如此,由于译诗很难传达原诗的音乐性,所以这里略而不录。
无论哪一种风格的诗,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它的音乐性可以比诗意更重要;应该认为前者从属于后者,否则便要将诗等同于流行歌曲中的词句。歌德的《对月》诗意显豁,而且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呈现出来,不仅兼有同类抒情散文的真挚、亲切的本色,更重要的是包含着只有诗的形式才能容纳的简洁而深邃的韵致。这些都很容易使中国读者联想起李白的许多咏月的诗篇,如:“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把酒问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等。李白是歌德所崇敬的外国诗人,但他写《对月》时是否已对李白有所了解,尚待考证。不管怎样,歌德在西方可以说是较早能够欣赏月亮之美的少数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在上引的那天谈话中,歌德还主张采取这样的创作态度:“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根据是书本还是生活,那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13]他如果在中国,无疑会属意于知识的“根柢”,但包括《对月》在内的许多歌德的诗篇仍不乏“兴会”;同时,他又反对让诗美的价值天平偏向于“情感文词和诗的格律”。[14]根据这位伟大的德国诗人的创作经验可知,“根柢”与“兴会”并非如王士禛所言:“率不可得兼”;在真正的诗人那里,情况恰好相反:这两者一般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根柢”自有创意,“兴会”便是这种创意通过恰当的文词、格律和情采而生发和外现,否则不是故弄玄虚就是生拼硬凑,堕入单纯的“修辞为要”的彀中。艺术性的创意即诗意,这是历代有成就的诗人进入创作状态时首先考虑的东西,或者说正是这种东西才使他们进入了创作状态,这是“以意为主”最起码的涵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以不排除诗歌创作中“修辞为要”的意义,因为启发诗人“灵感”的创意,不等于作品完成后所蕴含的全部诗意,这里还要经历诗人斟酌辞句以构造意象和意境的过程。而且,作品中的诗意一般并非呈现为单一状态的。“多样性统一”的艺术原理,可以在“诗意”这一艺术细胞中得到最集中、突出的显示。究竟完整的诗意是如何结构而成的?这是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内、外意”说和“构架——肌质”说
诗中之“意”,不全等于诗人的“作意”或写作动机。无为而作,只求语句绚丽、巧妙或声韵调协、响亮,理所当然无“意”;即便有感而发,如果不熟悉一般的诗法,也可能将真意淹没在汹涌的语流之中,结果还是无“意”;以辞害意,也不是罕见之事,宋代诗评家蔡启在《蔡宽夫诗话》中指出过:“诗语大忌用工太过,盖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意”即意义,扩大而言可以包括诗或其它文字结构的“主题”或“内容”等,美国“新批评派”领袖兰色姆就说:“诗里表现出来的‘意义’就等于绘画里表现出来的实物,诗的韵律就等于绘画里的纯抽象形式”。[15]这与上述的陆机《文赋》序中关于物、意、文三者关系的看法很一致。兰色姆自命为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所以坚持现实主义的诗学观;如果他倾向于柏拉图,便要认为诗中的“意义”就是“理念”。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诗的这种“意义的结构”具有怎样独特的构造原理?在唐、五代文人徐寅的《雅道机要》中早已载有:“内外之意,诗之最密也。苟失其辙,则如人之去足,如车去轮,何以行之哉”?宋代诗人梅圣俞(1002—1060)进一步提出:“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意含蓄,方入诗格”。[16]一般人将此解释为我国古典诗中“托物寓意”的手法:“内、外意”即比喻(一般为“借喻”)或象征(一般为不出现“本体”的“暗征”)中的“喻旨”和“喻体”或象征意义(“本体”)和象征物(“征体”);“含蓄”则是诗中任何意义结构的基本原则,广义地说就是无论何种寓意手法都不要太露斧凿之痕,最好如同行云流水般自然,就象没有什么内、外意之分一样。但一般的写诗或读诗的人往往狭隘地理解“含蓄”二字,喜欢绚烂、峥嵘或故弄玄虚,忽略了梅圣俞论诗的主旨:“平淡”。[17]所以,当时就有一些论者(包括黄庭坚)不满“内、外意”之说,认为这样“穿凿”会使人误以为诗中都是“隐语”,“物物皆有所托”,结果只注意“发兴”而弃掉“大旨”。[18]由于梅圣俞的诗论不够系统和详细,至今人们对“内、外意”的确切涵义以及风格上“平淡”与“含蓄”的关系,仍缺乏较全面、彻底的研究。其实,本世纪西方诸多现代主义诗学已开始注意到诗意的这种结构特点。例如,上面提及的兰色姆就提出:“一首诗有一个逻辑的构架(Structure),有它各部的肌质(Texture)”。他还说:“如果一个批评家,在诗的肌质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等于在以诗而论的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只是把诗作为散文而加以论断了”。[19]兰色姆的这一见解似乎得到黑格尔著作的启发,因为他提到黑格尔往往在艺术品中看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种内容,并认为批评的中心问题就是辨明这两种内容的关系。兰色姆认为诗的逻辑构架不能与科学文体的严密性相比,前者只起负载肌质的作用;而作为局部细节的肌质,则与构架分立,彼此关系不十分密切;因此,散文只有一种价值,其枝节要起辅助主体的作用,而诗则有多种价值,肌质的总价值要比构架大。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说与梅圣俞的“内、外意”说都是独家之言,有待于辨析并归纳成为有普遍意义的诗论。
我们稍加深入探讨便知,梅圣俞的“内、外意”不限于比喻或象征的两造,一切诗语都不可少“内、外意”:字面上有逻辑关系的内容是“外意”,即“构架”,表现或传达诗中涉及的物象或含蕴着概念的表象,并非都是“喻体”或“征体”;除了字面上的意义之外的联想、歧义、讽喻以及其它各种“言外之意”,都可以称为“内意”。显然,越是含蕴丰富、深刻的诗,“内意”就越比“外意”重要。然而,“内意”产生于“外意”,离不开“外意”的携带,因此剖析两者之间关系便成为分析和评价诗歌艺术的关键。
我们还可以用美国“新批评”派中其它论者的有关看法来印证梅圣俞的“内、外意”的真义。诗人批评家艾伦·退特认为好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具有“张力”;这一科学词汇是取语言学上词的“外延”和“内涵”的同义词“外展”(extension)和“内包”(intention),截去它们的前缀之后剩下共同的词根tension(张力)而来的。退特比他的老师兰色姆更进一步看到:“一首诗突出的性质就是它的整体效果,而这整体就是意义构造的产物,考察和评价这个整体构造正是批评家的任务”。[20]他还说:“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21]从西文构词法上所得到这一启发,有助于消弭“整体论”与“内、外意”或“构架、肌质分立论”的争端,因为退特在注意诗的“整体构造”的同时,并不放弃以前采用的“诗的总体思想分离法”,而且,作为整体意义的“张力”就是由“内、外意”构成的。后来“新批评”派中还有人提出“反讽”和“悖论”的诗学观,[22]与上不同的只是将“内、外意”对立起来,即所谓的“反话正说”和“正话反说”。结构主义诗学的注意中心不在于抒情诗,而在于叙事文学,但不少重要的诗学观都与“新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只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后者更前进一步:对好诗的“有机整体性”的强调;对诗的文类特征(如韵律、分行排列等)的重视;对读者的参与作用的考虑……但“一般的结构主义者”就象美国接近这一流派的文论家卡勒所概括的那样:“都追随雅可布森的诗学路子,并把‘二元对立’看作为人类思维过程中基本的操作法则,意义便由此而产生,如同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二元对立这一基本逻辑是所有思考最起码的共同标准’”。[23]将“内、外意”等视为“二元对立”的意义结构,也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后者并不专指诗而言。其实,在各种现代批评流派出现之前,西方已有诗学家注意到诗意的复杂结构。例如,英国新黑格尔主义重要代表布拉德雷便认为,诗的题目与该诗本身对立,而且,诗的意义似乎在于“企图表现超越它本身以外的某种东西”,“含有无限暗示的气氛”。[24]布拉德雷的“题目无关”说与兰色姆的“构架无关”说接近,实际上“题目”与“构架”都涉及诗的大意或“外意”;在“诗本身”,他又强调那种不能用言辞以及音乐和色采来表现的、“无限暗示”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是“内意中的内意”。
我国古代持类似见解的也不只是徐寅、梅圣俞等一、二人而已。元代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记入几乎与梅圣俞的“金针诗格”雷同的一条“诗法”,即:“诗有内外意……方妙”。[25]可见持此说者后继不绝。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在诗论《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另有如下见解:“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26]王夫之比梅圣俞描述得详细,将“意”与“势”的关系说得很透彻:“势”在“意”之中,如果只有“意”而不知“取势”,就只能得到表象化或概念化的“画龙”,而得不到活灵活现的“真龙”,即只有“形似”而无“神似”。显然,这里的“意”与“势”相当于梅圣俞的“外意”和“内意”。至于分别或单独地论说过“内、外意”中一种的诗评家及有关的“诗话”,唐代以来便屡屡出现。著名的“金针格”便说:“炼句不如炼字,炼字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以声律为窍,物象为骨,意格为髓”。[27]有人问王士禛:“意何以炼”?王士禛答道:“炼意或谓安顿章法,惨淡经营处耳”。[28]显然,王士禛对“意”的理解,与王夫之相差无几,同时接近于美国兰色姆所谓的逻辑性的“构架”;它建基于学问的“根柢”上,因此要依赖于智性的“惨淡经营”。王士禛对于“炼意”,即如何实施“以意为主”,说得比较具体;但在“炼句”和“炼字”,即“以辞辅之”上,不如他的内兄兼诗友张实居(萧亭)了解得多。萧亭回答郎廷槐的“句法”问题时,借用宋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中一段话的大意加以发挥:“诗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此所谓句法也。以气韵清高深渺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故宁律不谐,而不得使句弱;宁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语俗”。[29]王士禛力倡“神韵”,但仅以“清远”一格概言之,而没有将它与“安顿章法”和讲求“句法”相联系,所以容易流于虚空。
以上的分析可以说明:我国古典诗论中的“意”或“外意”,大体上指诗的篇章结构或题材中的逻辑关系,即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构架”;而“势”或“内意”,主要反映在诗的句法上,即美国学者兰色姆所谓的“肌质”。不过,中国古典文论用语一般不很规范,常因各人的习惯和认识的不同而略有更易,“意”在多数情况下可以表示“外意”,但在某些场合亦可代替“内意”或“势”,这时往往作“会意”之“意”解。例如,明代识见非同一般的诗评家都穆(南濠)谈到好诗必具禅悟时,举出龚圣任的一首论诗的诗:“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30]这首诗深刻地说明:即使在句法范围内可以凭显意识安排的语辞,也只有传达逻辑性的“此意”的把握,而“内意”只能在很好地表达“外意”的过程中来“兴会”,无需特地重新结构。上面将内、外意分别放在章法和句法中来探求,只是大致而言可以这么做,不能绝对化地理解为:内意与章法毫不相关,或者句法一定能出内意而不出外意。至于“格”和“韵”,除指诗体形式,作“诗格”、“诗韵”用外,还分别指“品格”和“风神”,[31]与句法关系密切;“气”在我国哲学思想中涵义极广,但作为诗学名词,除兼含“品格”、“风神”之意外,还常单独或与“势”连用,指充斥于字里行间的直觉性的“笔意”,落笔时起着细腻的引导作用,如宋代苏辙所言:“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32]其兄苏轼将此说得更妙;“……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33]我们不妨将“初无定质”的云水这一比喻与“气”相通。总之,“格”、“韵”、“气”等诗学范畴都与“内意”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即作为文理和作者的气质体现于辞句中;它们与表示逻辑关系的“外意”不是毫无干连,只是这方面的关系不太密切,因为就诗歌的本体——抒情诗——而言,它无需着重于说明或描述,否则便要限制其暗示性的“内意”的扩展。
三、“肌理”说与“直陈诗”
我国最早研讨西方美学的著名诗评家是王国维(1877—1927)。在他之前,比较精于古典诗学艺术理论与鉴赏的学者要算翁方纲(1733—1818)。翁除有专论批评“格调”、“神韵”以及“性灵”诸诗派的偏向之外,还独树“诗法”的旗帜,“肌理”说便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肌理”原义为“肌肤的结构纹理”,与兰色姆的“肌质”(texture)同义,但在诗学中的用法不尽相同。上面已提到赵翼《论诗》中将“兴会”与“肌理”对峙(见注[⑦]),似乎“肌理”更多关涉于外意。翁方纲则将“肌理”看作诗法“穷形尽变”的地方;“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以至于“佳句法如何”,均属于这种“尽变”之理。他又说:“格调、神韵皆无可着手也。予故不得不近而指之曰:‘肌理’。少陵曰:‘肌理细腻骨肉匀’,此盖系骨与肉之间,而审于人与天之合征乎”?(《仿同学一首为乐山别》)可见他的“肌理”以作品实际和实践理性为基础,既包括整体结构的“条理”,也包括细部组织的“密理”。他还一再申说:“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延晖阁集序》);“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其实肌理亦即神韵也”(《神韵论上》)。
这种“肌理”说与上述西方的有机整体论有相似之处,在注意诗意结构中粗细相形,虚实互见之时,已将“内、外意”或“构架——肌质”的考虑包括在内了。翁方纲与西方的形式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并不特别留意于诗意结构的形式,而只专注于这种结构之“理”;他的诗法就是以这种“理”为基础,它来自古人,来自学识。因此,翁方纲根据《周易》指出:“‘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经也”(《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他还比同时代人更精辟地评析了宋诗的价值:“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
如同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诗学一样,翁方纲的“肌理”说也存在着指导思想保守、具体方法不详以及创新的实践较少等历史局限。尽管如此,他秉承清代中期鼎盛的“朴学”精神,力排众议地倡导诗歌领域中的理、法研究,对于发扬以杜甫和后来的宋诗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风作过重大的贡献。然而,他的同时代文论家姚鼐在肯定“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这一基本法则的同时,又委婉地对他的诗法提出如下的批评或补充:“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衔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彩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气”的作用,这里毋需细说;至于诗意结构到底有无“定法”却很值得探究。
前人的成功实践成为不容否认的艺术之法的基础。但是,艺术又是不断创新的活动,因此其法也在不断完善,永无“定法”可言。上一节论及的诗意的“内外”或“构架——肌质”之分,就不是定法:内、外意在反讽或悖论结构中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一般相辅相成的;其联系的紧密程度也不等,个别近于“有机整体”,或有“分寸”不差的“肌理”,大部份则是松散、随机的联系,听凭读者想象的牵引;内、外意之一缺如者亦不少见,“直陈诗”大半如此。
直陈诗(poetry of statement)亦称赋体诗,即不采用比、兴手法、仅靠述说(“赋”)方式的一种诗体。它在古典诗和浪漫诗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佳作也不少。例如,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云云,头两句就倾倒后代许多诗客;全诗的及时行乐主题虽已陈旧,但这两佳句仍熠熠生辉,成为猜不破的人生大谜。其实无需猜,它们字面上的“外意”也就是内涵之意,其特殊价值在于辞句间已形成反讽或“二元对立”的结构,不必再深挖构架内填充的肌质,因为构架在这里也就是肌质。
匈牙利裴多菲的“爱情,自由,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一诗更是突出的例子。殷夫把它译成一首五言绝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死,两者皆可抛”,至今依然风靡全国。然而,它的诗意结构却极为单纯,可以说是毫无掩饰的直白,“内意”完全裸露着。其魅力全在于它的诗意结构与现实的价值观适成强烈的对比,使我们身在平凡之中却有超凡的追求。但是,不少直陈诗给人一览无余的感觉,或者只是一连串铿锵的声响,找不到什么“内意”,只有字面上扶浅的“外意”。由此可知,好的直陈诗可以省略“外意”,即将外意消融于现实之中,却不能没有“内意”。
简而言之,诗意既然来自诗人之“志”,或来自诗人所感之“物”,结构诗意时理所当然要“以意为主”,并以适当的“辞”来表意。“意”与“辞”在诗中应是一致的,并非两个组成部分。由于客观和主观世界都是繁复多变的,而求“真”又是诗人的天职,所以真正的诗意必然是多层次的完整结构,只是其形式随具体情景而变换,难以在此尽述。
注释:
①《诗问四种》,[清]王士禛等著,周维德笺注,齐鲁书社、1985年,155页。另见《清诗话》,丁福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142页。
②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补遣》,见于上注《诗问四种》,第222页。亦见于《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72页。
③《清诗话》,丁福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第8页。
④王夫之最远只提到“齐、梁绮语”,但李白的《古风》中有“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之句。
⑤同注③,第151;“萧亭先生”即张实居,是王士禛的内兄,有《萧亭诗选》四卷。
⑥同注②。
⑦赵翼《论诗》中有“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古疏后渐密,不切者为陈”和“是知兴会超,亦贵肌理亲”等诗句。见嘉庆寿考堂本《瓯北集》卷四十六。
⑧《艺概》,[清]刘熙载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0页。
⑨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渔洋文》,见于《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65页。
⑩保罗·瓦雷里:《纯诗》,丰华赡译,载于《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11狄兰·托马斯:《关于诗艺的札记》,《20世纪的诗与诗论》(英文),G.Geddes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588—589页。
12埃米尔·施塔格尔(F.Staiger):《诗学的基本概念》(1946),胡其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
13《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14同前注,第54页。
15J.C.兰色姆(Ransom):《纯属思考推理的文学批评》(1941),《“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06—107页。
16《诗人玉屑》,[宋]魏庆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第197页。此记载见于该书卷九“托物”条目中,据称梅尧臣撰有《续金针诗格》言此,一般径称之“金针诗格”。
17同注16,第218页。梅诗中有“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等句。
18同注16,第198页。
19同注15,第97,98页。
20艾伦·退特(Allen Tate):《诗的张力》(1937),《“新批评”文集》(见注15),第109页。
21同前注,第117页。
22克林思·布鲁克斯(C.Brooks):《悖论语言》(1947)和《反讽——一种结构原则》(1949)二文,见于《“新批评”文集》(注15),第313—350页。
23J.卡勒(Culler):《结构主义诗学》(英文),伦敦,1975年,第15页。雅可布森认为诗的特点是:经常采用比喻、象征、对偶、排句等“两造”串联的句法,将一些意义接近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列维—斯特劳斯的原话见于《今日的图腾主义》(法文),第130页。
24A.C.布拉德雷(Bradley):《为诗而诗》(1901),见于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05~110页。
25《历代诗话》,[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737页。
26同注③。
27同注16,第172页。唐代何人创“金针格”待考。宋代范温《潜溪诗眼》:“世俗所谓乐天《金针集》,殊鄙浅,然其中有可取者,‘炼句不如炼意’,非老于文学不能道此。又云‘炼字不如炼句’,则未安也”。据此还难以断定白居易创过“金针格”。但他力倡诗必有为而作,“系于意,而不系于文”。(《新乐府》序)
28同注③,第158页。亦见于《诗问四种》(注①),第95页。
29同注①,第56页。《珊瑚钩诗话》:“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见于《历代诗话》。(注25,第455页。
30都穆:《南濠诗话》,见于《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1234页。
31王士禛答某人问格与韵之别:“格谓品格,韵谓风神。”见注①,第87页和注③第154页。
32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11页。
33苏轼:《答谢民师书》,《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3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