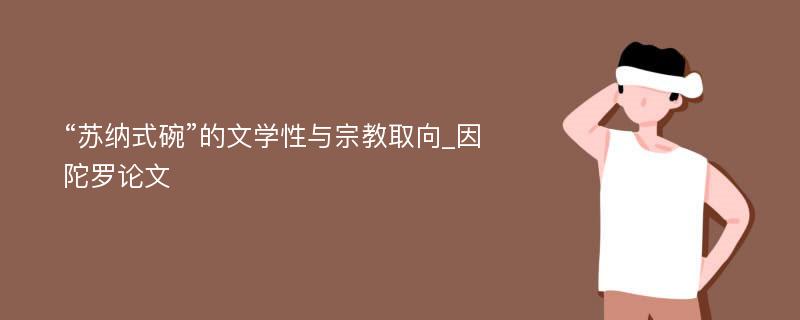
《苏那式钵》的文学性与宗教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文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8—0050—08
中国儒家论述文学与思想的关系时,提出过“文以载道”的命题。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义也。道德,实也。”① 印度古代文学宗教性极强,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的文学。佛教盛行时期的印度文学如此。大乘者大车也,小乘者小车也,都不是虚车,而是车身负载教义,车轮滚滚向前。大乘小乘都是用来传教的。吠陀时期的文学,更是如此。在吠陀时期,基本不存在非宗教性的文学创作。笔者以为,古代的印度文学基本上可以用“文以传教”这一命题来概括。这在吠陀时期的印度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婆罗门教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为宗教服务的。印度梵文文学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苏那式钵》的故事就是一部文学性与宗教性水乳交融的典范之作。由于《苏那式钵》的宗教性是通过文学性而展现出来的,因此它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通过对《苏那式钵》文学性的仔细分析,并连带对当时的印度社会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这一印度文学名著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其宗教学的意义。具体地深入地阐明作品的宗教学意义,而不是笼统地用宗教性去硬套一切作品,应该是我们当代学人研究印度古代文学最基本的态度。
在古代印度,存在过用活人来祭祀的风俗。许多古代印度文献中有这方面的记载。其中,以吠陀文献《爱他罗氏梵书》(Aitareya Brahmana)中关于苏那式钵(Sunahsephas)的记载,较为完整。根据中国学者的习惯,《爱他罗氏梵书》简称《他氏梵书》。魏庆征编《古代印度神话》一书录有苏那式钵的故事。尽管该书已经有所删节,篇幅仍然很长。为着研究的方便,笔者采用《爱他罗氏梵书》的原话,试将苏那式钵的故事缩写如下。本来,故事中穿插着大量的诗歌,有的具有吟咏生发的性质,有的具有总括上文的性质,还有的具有美化文章的性质,宛如一簇簇鲜花点缀在葱绿的草原上,不得不忍痛割爱,予以省略。在缩写的过程中,根据梵文的基本知识,改动了个别字句。为了文脉贯通,添加的少数字句置于方括号中,同时对标点符号也作了一些调整。
诃哩湿旃陀罗,甘蔗族王的后裔,无嗣。他虽有百妻,却无一为他生子。两婆罗门——婆哩婆陀和那罗陀,居于诃哩湿旃陀罗那里。一次,他向那罗陀询问如何得子。那罗陀说道:“你去求助于神王伐楼那!你许诺:如生一子,则以此子向他献祭。”诃哩湿旃陀罗应允;他来到伐楼那面前,说道:“请让我得一子吧,我将以他向你献祭。”伐楼那答道:“就这样吧!”
诃哩湿旃陀罗果然得一子,名叫卢酼多;伐楼那对诃哩湿旃陀罗说道:“你已得一子,以他向我献祭吧!”诃哩湿旃陀罗答道:“献祭的动物,出生十日后才适合作为牺牲。我的儿子满了十日,我再以他向你献祭。”伐楼那答道:“就这样吧。”卢酼多已满十日,伐楼那对诃哩湿旃陀罗说道:“你的儿子已满十日,以他向我献祭吧!”诃哩湿旃陀罗答道:“献祭的动物,长出牙齿才适合作为牺牲。等我的儿子长出牙齿,我再以他向你献祭。”伐楼那答道:“就这样吧!”卢酼多已长出牙齿,伐楼那对诃哩湿旃陀罗说道:“你的儿子已长出牙齿,以他向我献祭吧!”诃哩湿旃陀罗答道:“献祭的动物,只有掉牙之时,才适合作为牺牲。等我的儿子掉牙之时,我再以他向你献祭。”伐楼那答道:“就这样吧!”卢酼多已掉牙齿,伐楼那对诃哩湿旃陀罗说道:“你的儿子已掉牙齿,以他向我献祭吧!”诃哩湿旃陀罗答道:“献祭的动物,当它再长出牙齿时,才适合作为牺牲。等我的儿子再长出牙齿,我以他向你献祭。”伐楼那答道:“就这样吧!”卢酼多又长出牙齿,伐楼那对诃哩湿旃陀罗说道:“你的儿子又长出牙齿,以他向我献祭吧!”诃哩湿旃陀罗答道:“刹帝利只有当他可使用兵器时,始可作为献祭的牺牲。我的儿子一旦会使用兵器,我便以他向你献祭。”伐楼那答道:“就这样吧!”卢酼多已会使用兵器,伐楼那对诃哩湿旃陀罗说道:“你的儿子已会使用兵器,以他向我献祭吧!”诃哩湿旃陀罗答道:“好吧!”他又对卢酼多说:“我的孩子,这便是将你赐予我者。现在,我应将你作为牺牲向他献祭。”卢酼多答道:“不行!”他拿起弓,逃入森林。他在森林中呆了一年。
这时,伐楼那抓住诃哩湿旃陀罗(甘蔗族王的后裔),后者因患水肿而腹胀。获悉这一切,卢酼多从森林返回家乡,行至一村。因陀罗化为凡人,同他相遇,说道:“游荡吧!”因陀罗是游荡者的襄助者。卢酰多重复他的话:“游荡吧!——婆罗门告诉我说。”他又在森林中呆了一年。当他从森林返回家乡,行至一村,因陀罗化为凡人,同他相遇,说:“游荡吧!”[于是卢酼多继续游荡]卢酼多重复他的话:“游荡吧!——婆罗门告诉我说。”他又在森林中呆了一年。当他从森林返回家乡,行至一村,因陀罗化为凡人,同他相遇,说:“游荡吧!”[于是卢酼多继续游荡]卢酼多重复他的话:“游荡吧!——婆罗门告诉我说。”他又在森林中呆了一年。当他从森林返回家乡,行至一村,因陀罗化为凡人,同他相遇,说:“游荡吧!”[于是卢酼多继续游荡]卢酼多重复他的话:“游荡吧!——婆罗门告诉我说。”他又在森林中呆了一年。当他从森林返回家乡,行至一村,因陀罗化为凡人,同他相遇,说:“游荡吧!”[于是卢酼多继续游荡]“游荡吧!——婆罗门告诉我说。”——卢酼多重复他的话,又在森林中栖居了一年。他在森林中遇仙人阿阇迦利陀;他是苏耶婆娑的后裔,正为饥饿所折磨。阿阇迦利陀有三子:苏那普乔、苏那式钵和苏诺兰古罗。卢酼多对阿阇迦利陀说道:“仙人,我给你一百头牛,倘若你让给我一个儿子,以代我赎回生命。”“只是不能让他!”——阿阇迦利陀说完,将长子拉到身边。“也不能让他!”——阿阇迦利陀指着最小的儿子说道。他们商定让次子苏那式钵去赎命。卢酼多交给阿阇迦利陀一百头牛,便与苏那式钵离森林返回家乡。他来到诃哩湿旃陀罗面前,说道:“噢,父亲!我想以此人赎回我的生命。”于是,诃哩湿旃陀罗来见神王伐楼那,说道:“这便是我向你献祭的人。”伐楼那答道:“好的。婆罗门确比刹帝利好。”伐楼那命诃哩湿旃陀罗举行王祭:在为王者敷油之日,以苏那式钵代替牺牲,作为献祭之牺牲。
举行此献祭之时,众友仙人为祭官,家摩大格尼为阿陀婆哩尤,婆私吒为婆罗门,阿雅西耶为优陀迦陀哩,尚未找到宣示将其身缚于祭柱者。这时,阿阇迦利陀说道:“再给我一百头牛,我去捆缚他。”他又得到了一百头牛,允诺将其子缚于祭柱上。人们将苏那式钵引来,捆缚起来,向他念诵咒语,在他周围燃起圣火,却未找到宣示将其刺杀者。这时,阿阇迦利陀说道:“你再给我一百头牛;于是,我去刺杀他。”他又得到一百头牛,磨刀霍霍,走上前来。这时,苏那式钵心中暗想:“唉呀!我好像不是人,——他们要杀死我。我要求诸神救助!”他首先向诸神中的生主吁求,念诵诗句。生主答道:“在众神中,阿耆尼与世人最近。向他吁求救助吧!”于是,苏那式钵向阿耆尼吁求,念诵诗句。阿耆尼答道:“沙维陀利是一切举措的主宰。向他吁求救助吧!”于是,苏那式钵向沙维陀利吁求,念诵诗句。沙维陀利答道:“你是被捆缚献祭给王者伐楼那。你向他吁求救助吧!”于是,苏那式钵向王者伐楼那吁求,念诵诗句。伐楼那对他说道:“阿耆尼是众神中首屈一指者和最慈惠者。你对他赞颂,我们共同使你得到解脱。”于是,苏那式钵以诗句对他赞颂。火神阿耆尼对他说道:“向诸神赞颂吧。我们将使你获得解脱。”于是,苏那式钵以诗句赞颁诸神。诸神对他说道:“因陀罗是诸神中最强有力者、最勇敢无畏者、至强至大者,他是最好的襄助者。对他赞颂吧,我们将使你获得解脱。”于是,苏那式钵以诗句对因陀罗赞颂。因陀罗听了苏那式钵的赞颂,异常欢悦,遂赠以金车。苏那式钵既得金车,又诵一颂诗句。因陀罗对他说道:“现在你颂扬双马童吧,我们使你获得解脱。”于是,苏那式钵以诗句对双马重赞扬。双马童对他说道:“现在你颂扬乌莎斯吧,我们使你获得解脱。”于是,苏那式钵以诗句颂扬马莎斯。苏那式钵就这样不停地念诵诗句,其束缚逐渐减少,诃哩湿旃陀罗的腹部也逐渐缩小。当他念诵完最后一颂诗句,其束缚无影无踪,诃哩湿旃陀罗也已痊愈。祭司们告诉苏那式钵:“现在,你自己应完成今天的献祭。”于是,苏那式钵着手进行压榨苏摩汁的仪式,压榨完毕,亦念诵诗句。嗣后,苏那式钵将苏摩汁注入硕大木桶,又念诵诗句。嗣后,当诃哩湿旃陀罗触及苏那式钵,犹如捐输者所为,苏那式钵则举行献祭,并念诵诗句。嗣后,苏那式钵为诃哩湿旃陀罗(捐输者)完成洁净仪式,并念诵诗句。继而,苏那式钵将捐输者引到火旁,并念诵诗句。苏那式钵既完成献祭,跪在众友仙人面前。
这时,阿阇迦利陀对众友仙人说:“仙人,将儿子还给我吧!”众友仙人答道:“不。众神已将他赐给我。”于是,苏那式钵便成为众友仙人之子,又称神赐者。②
《苏那式钵》的故事,其缘起是求神得子。由于梵书产生在人类文明史的早期,其中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当突出,为了获得儿子,诃哩湿旃陀罗(Harishichandra)向一位名叫那罗陀(Narada)的婆罗门发问,吟诗一颂。那罗陀以诗十颂作答,这一段长达十颂的诗歌在论及生育的原理时采取的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那罗陀答诗第四颂:“与其妻结合的丈夫,/以精液入于母腹,/在其体获得另一生命,/怀至十月则降生。”[1](P.85) 人受胎而生,占有物理的生命个体,这不是典型的唯物主义生育观吗?然而,在远古时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相距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种情形,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我是在当前现实中意识到我的实在性的;于是自我意识就很顺当地发现它自己是物质,——灵魂是物质性的,观念是外界感觉印象在脑子这个内部器官中所引起的运动和变化。”[2](P.216)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人们意欲完成某一件困难的工作,往往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因此一个人受到了帮助,心中大多会念念不忘助力来之不易。处境困难的早期人类,容易对处于类似境况的他人发生怜悯。一旦受惠于人,亦油然而生回报恩人的念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问题,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知恩图报这一朴素的思维方式。时代发展至今日,在边远贫穷的山区,知恩图报的风习依然比较浓郁,就是这个道理。在《苏那式钵》的缘起部分,知恩图报这一朴素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反映。从亚洲各国宗教发生的历史看,知恩图报这一思维方式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因果报应这一思维模式。如所周知,知恩图报是婆罗门教、佛教和印度教等宗教的突出特征。那么,一般的知恩图报和宗教性的知恩图报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区别如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知恩图报,回报的对象是人,而在宗教性的知恩图报,回报的对象是神。在宗教氛围浓郁的社会里,有的时候受到恩惠的一方明明知道他应该回报于人,可是他依然会联想到神,从而将报答的对象转移到神的身上。宗教性的知恩图报,发展到后来,就是还愿。还愿是直至今日还盛行于民间的宗教性的知恩图报方式。人们在寺庙里对佛许下心愿,待到心愿实现之后就到寺庙里礼佛赞佛。因此,从缘起部分看,《苏那式钵》的宗教性是十分突出的。缘起中所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在获得儿子之后如何还愿的问题。然而,《苏那式钵》所讲的还愿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是受到神恩的一方提出来的,而是由婆罗门那罗陀提出来的。在古代印度,五趣之极,称为天;人而有神德者,称为仙。那罗陀,字面意思为“以辩胜人者”。具体说来,“那罗陀是著名的天仙之一,亦即神化了的圣人或神圣的贤人。他是梵天以意念所生的十子之一,据说他是从梵天的大腿里跳出来的。他被描述为一个信使,他把信息从诸神传给人们,反之亦然。而且他非常喜欢挑起诸神和人们之间的争端。因此,他有个绰号叫爱吵架者。据说他是笛子或琵琶的发明者。他也是一部以其名字命名的法典之作者。”③ 从宗教功能的层面看,这位那罗陀相当于基督教里的祭司(priest)。由于诃哩湿旃陀罗的还愿不是出于本心,因还愿而引起的痛楚就特别惨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吠陀时期的印度人看来,在人世间的各项工程中再也没有比造化人类更为困难和伟大的了。造化人类的工程,不仅困难和伟大,而且还神秘。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看,吠陀文献中所讲的造化人类这一工程与基督教的婚姻神学颇多相似之处,但亦不尽然。自有人类以来,非婚生的孩子不知有多少。有的夫妻恩爱呢喃一生,到头来却膝下无子。不少夫妇身强力壮,可就是没有子嗣。有的夫妇聪明透顶,可就是子女其笨如牛。这一切都暗示古人:造化人类的最后依据毕竟还是神。因而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人们容易相信神灵。于是,我们看到,诃哩湿旃陀罗为了求得一子,便去向神王伐楼那(Varuna)求助。所助既巨,回报必巨。根据伐楼那的吩咐,渴望求得儿子的诃哩湿旃陀罗的回报必须是:如得一子,便以此子向伐楼那献祭。人们不禁要问:求得儿子又将儿子献祭,岂不是白白求子一场吗?答曰:非然也。如果没有子嗣,那么作为父亲者,其人生将不完满。有了儿子,为父者之人生,倒是完满了,不过尚不丰盈。有了儿子,又将儿子献祭于神,为人父者其人生才丰盈,为人子者其人生才伟大。笃信神灵的古代印度人就是这么想的。然而,无论成就父亲的丰盈人生,还是成就儿子的伟大人生,都必须以牺牲父子亲情为代价。而父子亲情这一代价,则是人世间最为惨痛的。
《苏那式钵》的故事,其情节蜿蜒曲折,委婉动人。从发展的脉络上看,故事情节由两根链条组成,他们门好比铁甲车两边的履带,驱动着《苏那式钵》这一辆重型铁甲车缓缓前进。每一根链条各有相互衔接的五个环节。于是,十个环节就构成了《苏那式钵》的主干故事,它包括五次推迟献祭和五次长期游荡。
先看五次推迟献祭。父亲诃哩湿旃陀罗答应获得一个儿子之后就将之献祭,可是,儿子卢醢多(Rohita)出生之后,他却五次推托献祭。为了推迟献祭,父亲不得不挖空心思寻找理由。一般认为,梵书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成书。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释迦牟尼传教,其弟子承传其学说,这是原始佛教时期。我们看到,梵书的成书时间与原始佛教的存在时间有一部分是叠合的。此外,原始佛教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的思潮中诞生的。因此,原始佛教关于人生阶段的理解,也就必然与梵书的相关内容多所吻合。这就为我们借用原始佛教关于人生阶段的理解来理解苏那式钵的年龄阶段提供了可能。关于人生的各个阶段,佛教有六入(sadayatana)之说,本指六种感觉器官的形成。由于各种感觉器官的形成有先有后,后来也就用它们来指代人生的各个阶段了。兹将苏那式钵的年龄阶段与六入对照如下。一,初生儿满十日,眼睛睁开了,耳朵在动,鼻孔在呼吸,身体有感觉,心灵与身体首次相结合,属于“识”(vijnana)的阶段。二,长出乳牙,一至二岁,其间六入已经有所活动,以触为盛,婴儿开始接触外界事物,属于“触”(sparsha)的阶段。三,掉落牙齿,六七岁,此时生命个体有意识地感受外界的各种现象,属于“受”(vedana)的阶段。从这个阶段开始,生命个体进入自我创造时期。四,长出恒牙,大约发生在十四、十五岁以后,这时人知道避苦求乐了,女孩情窦初开,男孩初恋亦多半发生在此时,属于“爱”(trisna)的阶段。五,此后个体的生命逐渐成熟,主动地执取所爱的对象,属于“取”(upadana)的阶段。六,此后个体的生命占有欲逐渐增强,功名心趋重,名缰利锁驱使人们去拥有一切,属于“有”(bhava)的阶段。此后个体的生命渐渐进入老境,体力会逐渐减弱,思辩能力则维持到死去之前,人越来越富于智慧,不过,再往后就会老死了。在《苏那式钵》的缘起部分结束时,主人公已经学会了使用兵器,大约处于“取”和“有”这两个阶段之间。这时的苏那式钵,英武伟岸,这不仅使我们想起《薄伽梵歌》(Bhagavadgita)11:5所描述的那位美男子:“薄伽梵说:/帕尔特哟!请看!/我的形象变化万千,/种类殊多,奇妙动人,/形态不一,五彩斑斓。”[3](P.128) 血气方刚的卢醢多本来应当在这时将自己献身于神的,可是他还没有这种认识。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认为土地和一切出产均为神的恩赐,故应将首先成熟的粮食和果实奉献给上帝。这就叫做“初熟的果实(first fruits)”。《耶利米书》2:3写道:“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初熟的果子。”[4](P.1193) 根据大量道教化的民间传说的有关记载,历代奉献给神明或大王的也大多是童男童女。这是因为童男童女真气未散。与处于其他阶段的人相比,童男童女作为献祭品,更能体现出奉献者的虔诚。从性质上说,童男童女与初熟的果实更相近。在《苏那式钵》中,父亲诃哩湿旃陀罗挖空心思找出来的各种理由其实都是非常笨拙的,颇有些耍赖的意味。其实,他在使用种种理由拖延时间,好让儿子长大成人。为什么呢?年轻力壮的儿子一旦会使用兵器,就是一员猛将,就能够捍卫自己的生命,从而躲过“献祭”这一劫难。每一次诃哩湿旃陀罗都有不同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统统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父亲对儿子的深厚的爱,其核心是珍视生命。
再看五次游荡。儿子本来只想游荡一年之后就奔赴献祭,可是在因陀罗的劝说之下他却五次推迟献祭。五次推迟献祭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其核心体现了作为献祭主体的人即卢酼多之宗教性的渐进上升,并不断升华,一步步逼近最高的境界。本来,卢醢多是因为不愿意作为献祭的牺牲,才逃到森林里去的。卢醢多在森林里一共居住了六年。第一年,是卢酼多逃避当牺牲而躲避到森林里去的一年。在这一年的林居生活中,卢酼多直接与大自然相处。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中,他心中亦有所思,因而其道德水准有一定的提高。可以认为,这一年的林居生活也就是一种修行。尽管如此,这一年的修行却是不自觉的修行。之后,卢酼多在因陀罗(Indra)大神化身而成的凡人的劝诫之下,继续在森林中游荡。卢酼多这五年林居生活的实质,乃是一种自觉的修行。因为卢醢多乃是在因陀罗的劝诫之下而营林居生活的。劝诫,其本质就是精神指导。比如在基督宗教的早期,宗教领袖对民众的精神指导就是以劝诫的方式进行的。《圣经》中记录了许许多多的劝诫,其中最著名的是摩西十诫(Ten Commandments)。具体说来,五次游荡的原因如下。第一次,卢酼多继续游荡,长达一年之久,其目的是追求洁净的身体状态。第二次,卢酼多继续游荡,长达一年之久,其目的是追求种种幸福的境界。境界,就其实质而论,乃是具有一定高度的精神状态。第三次,卢酼多继续游荡,同样长达一年之久。不过,一年的时间,相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简直是太短了。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卢酼多居然在思想上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时期。④ 第四次,卢酼多继续游荡,长达一年之久。这一次卢酼多的追求更加具有宏伟的意识,他渴望与宇宙契合,以便以自身的蜜亦即修行得来的美好果实来与宇宙的美好实存状态相互印证。第五次,卢醢多继续游荡,时间依然长达一年之久。关于这一次游荡的具体内容,故事没有说。其实,亦不需要说。显然,卢醢多第五次游荡,追求的就是最崇高的宗教理想了,他心甘情愿地为宗教献身。卢酼多在森林中游荡六年,成为后来兴起的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的一种预表(typological representation)。⑤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因陀罗而不是别的什么神来劝诫苏那式钵游荡呢?原因在于,因陀罗大神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人们游荡。《苏那式钵》中穿插的诗篇唱道:“修苦行者的幸福多种多样,/仙人这样对我们说,卢酼多。/生活在世人中是可悲的,/因陀罗是游荡者的襄助者。”[1](P.88)这四行诗,出于《梨俱吠陀》(Rigveda),金克木在《梵语文学史》中译作:“不劳累的人没有幸福,/罗西多啊!我们听说过。/住在人群中的人有大祸。/流浪人的朋友是因陀罗。”[5](P.87) 那么,人们不禁要追问,因陀罗为什么要帮助人们游荡呢?因陀罗为什么做流浪人的朋友呢?原来,游荡并不是指好逸恶劳到处闲逛,而是古代印度人重要的人生体验。婆罗门教有四行期(ashrams,the four stages of life)之说,⑥ 它规定了教徒修行与生活的四重历程。一是梵行期(brahamacarin,student of Veda),又称学生期、梵志期,儿童成长到一定年龄,须离家从师,学习吠陀,熟悉祭祀仪式。二是家住期(grihastha,householder),此时期以经营世俗生活为主要任务,比如结婚、就业等。三是林栖期(vanaprastha,anchorite),年事渐长,就要弃家隐居森林,修养身心,为灵魂解脱做准备。四是遁世期(samnyasin,abandoner of all worldly concerns),舍弃一切财富,云游四方,乞食为主,严守五戒,置生死于度外,以期获得最后的解脱。前面谈到,作为父亲的诃哩湿旃陀罗第一次推托将自己的儿子卢酼多献祭时,说要等到孩子满十日才能用来献祭。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初生儿至少满十日才能命名。《摩奴法典》(Manava-Dharma Sastra)2:30规定:“小儿生后第十天或第十二天,或者,在一个吉利的太阴日,在吉祥的时刻,在吉星高照下,父亲应举行,或父亲不在时,应让人举行命名典礼。”[6](P.29) 后来,卢酼多经历了长出乳牙、长出恒牙、学会使用兵器等阶段。这时候应该是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了。这与《摩奴法典》的规定是吻合的。至于梵行期的具体时间,一般是8岁就师,此后学习12年。因此,到梵行期结束的时候,一般为20岁。处于梵行期内的青少年,称为梵志生。在梵行期内,梵志生主要学习吠陀经典,也兼习各种本领,以期获得一定的生活技能。因此,卢酼多还学习了使用兵器。这时,卢醢多已经20岁了,这是他开始去游荡时的年龄。这既是故事的叙述,也合乎《摩奴法典》的规定。不过,还留下了一个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卢酼多去游荡,究竟具有什么性质?笔者认为,卢酼多的游荡,其基本性质是行乞,但是卢酼多的行乞还兼具一些林栖期和遁世期的特点。本来,按照《摩奴法典》的规定,行乞属于梵志生的生活内容,主要目的在于了解现实社会、运用所学的本领和认识民生的疾苦,颇类似于今日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一个婆罗门教信徒在林栖期和遁世期内的生活内容。你看,那些“梵志生要携带满意的手杖,在面向太阳,从左及右,绕火一周后,按照规定去行乞。”[6](P.31) 从时间上看,卢酼多的游荡,发生在梵行期结束之后。从地点上看,卢酼多的行乞,大多在森林之中进行,不过他也不时来到村庄即城乡的结合部。由于卢酼多主要在森林里游荡,因此其游荡兼具林栖期的性质。同时,卢酼多在游荡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婆罗门教信徒所应有的完整的人生经历,所吃的苦头与一个虔诚的遁世者一样多,而其思想的体验则比一般的遁世者更加丰满,因此其游荡兼具遁世期的性质。这里,还留下了一个难题,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那就是,大神因陀罗为什么要化身为凡人来对卢酼多进行劝诫?笔者认为,因为卢酼多的宗教理念是在林中栖居的六年中逐步建立的。在卢酼多建立其宗教理念的六年中,在卢酼多思想最后升华的那一刹那之前,卢酼多始终还是一个凡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另一个凡人对于作为凡人的卢酼多进行劝诫,卢酼多才会信从。否则,他要么会因为害怕而放弃林居生活即修行,要么会因为拒绝接受劝诫而导致已有的修行前功尽弃。
《苏那式钵》的故事,其高潮是献祭,而这一高潮是通过主人公的人物置换而实现的。《苏那式钵》故事用了许多笔墨来描写卢酼多,但是,走向祭坛的那个人却不是卢酼多,而是苏那式钵。在故事中,苏那式钵是卢酼多的替身,他勇敢地走向了祭坛。这不禁使人纳闷:那些描述卢酼多的大量篇幅不是白费了么?其实不然。在这里,为增强故事的艺术感动力,文学的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主人公的人物置换。值得注意的是,卢酼多属于刹帝利种姓,而苏那式钵属于婆罗门种姓。这对于理解婆罗门教的祭祀万能是一个关节点。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从苏那式钵的身上我们处处感到卢酼多的影子。稍微不注意,就会把苏那式钵与卢酼多相混淆。而受众心理中的混淆,正是《苏那式钵》这个故事的艺术奥妙之所在。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分不清耶稣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而《圣经》的作意,就是要叫你分不清。一般说来,宗教的说教,时间长了容易使人疲乏。艺术的魅力可以使受众兴趣盎然。既然苏那式钵是卢酼多的替身,那么二者之间势必得有相似之处,否则就无法充当替身了。在日常生活之中,充当替身的人必须是外形相似。在宗教生活之中,则更看重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一致。故事告诉我们,罗酼多一共在森林里游荡了六年。根据上面对梵行期的分析,可以推断出卢醢多结束林栖生活时的年龄。当卢酼多结束游荡的时候,他大约26岁左右。既然苏那式钵充当卢酼多的替身,则苏那式钵的年龄也在26岁左右。然而,一个26岁左右的人尚未经历四行期的全过程。将一个尚未经历人生四行期的人之个体奉献给神,从内在的精神的层面上说,显然是不够完满的。这是因为,伟大的神不是妖怪,他并不贪吃嫩肉。古代印度之所以存在以人为祭品的祭祀仪俗,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祭祀而昭示人性与神性之间具有完美结合之可能。这样看来,理应将一个完成了四行期的人之个体奉献给神。不过,这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完成了四行期的人,由于他已然垂垂老矣,其外形便绝然不美。你看,“家长看到自己皮皱发苍,子孙绕膝时,要退隐山林间。”已经皮皱发苍了才退隐山林间去过林栖期和遁世期的生活,又在那两个时期中生活若干年,其形体岂不是更加不美么?因此,我们从历史记载中所了解到的古希腊古罗马的祭仪,以及我们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祭仪,都是由年轻美貌的男女充当牺牲的。这样做的理由亦是十分明白,祭神必悦神,可谓一条基本的献祭规律。被实际用来献祭的苏那式钵,其人生经历如何,故事中语焉不详。不过,由于苏那式钵是卢酼多的替身,而这次献祭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可以明了,苏那式钵在形体和精神方面必然与卢酼多并无二致。换句话说,苏那式钵是卢酼多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替身。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从灵性的层面上说,苏那式钵是一个经历了完整的四行期的人。也就是说,苏那式钵就是置换卢酼多的那个活生生的存在。为了让这种置换发生得令人可信,故事做了一些必要的铺垫。这些铺垫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牛换取人的人生命。一是诸兄弟折其中而取之。以牛换人命,主要的效果是突出人祭的重大和庄严。三兄弟折其中。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印度在奴隶社会时期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前者甚有趣味,后者反映出中国的影响。兹分说如下。
古代印度是一个祭祀繁多的社会。祭祀的仪式分为三类:家庭祭、供养祭和苏摩祭。三者之中,苏摩祭的规模最大,凡是家庭祭和供养祭之外的大型祭仪都属于苏摩祭(somayajna)。之所以称为苏摩祭,乃是因为,在举行祭祀的时候要使用苏摩酒。苏摩(soma)是一种蔓草。采取苏摩的茎杆加以压榨,可得到黄色的汁液,再加上牛奶和面粉等加以发酵,便可以得到苏摩酒。苏摩酒气味芬芳,具有强烈的兴奋作用,饮用后使人勇气倍增,并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吠陀文献把它描述得神乎其神。这是古代印度大型祭祀必用苏摩酒的理由。苏摩祭分为八种,分别用于不同的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大事的场合。(1)向火神举行的祭祀,称为阿耆尼湿头摹(Agnistoma)。(2)国王为求战争胜利而举行的祭祀,成为力饮祭(Vajapeya)。(3)为新国王即位而举行的祭祀,称为即位礼祭(Rajasuya)。(4)向生主(Prajapati)和因陀罗大神举行的祭祀,称为马祭(Ashvamecha)。此祭用马作牺牲,耗费巨大,不轻易举行。举行马祭可以使国王成为王中之王,类似于中国战国时代七雄中某一国君主得以称霸于其他诸侯时而举行的盛大祭典。(5)为建立祭坛而举行的祭祀,称为火坛祭(Agnicayana)。(6)为欢送婆罗门教僧侣出家而举行的祭祀,称为全祭(Sarvamedha)。(7)奉乳祭(Pravargya),这是一种附属的祭仪。(8)人祭(Purusamedha),又叫人祀。该祭祀的仪式类似于马祭而更为盛大庄严,以活人为牺牲,仅在为祈求获得马祭所不能达到的更大欲望时才举行。须知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诃哩湿旃陀罗为了保存自己儿子的生命,想出了寻找替身的办法。最终,苏那式钵充当了卢酼多的替身。这一替身乃是用三百头牛的代价换来的。《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孔颖达疏:“《司马法》:‘六尺为步,百步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7](P.683) 这是关于我国春秋时鲁国交纳军赋的记载,每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也就是说,144个男劳动力耕种12800亩地,每年交一匹戎马三头牛的军赋。当然,对于这种制度,其他典籍也有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而且春秋时的地积单位和现在相差较大,尽管如此,这也说明了饲养一匹马或一头牛十分不容易。牛和马一样,同是大牲畜。然而在印度,牛和马还有所不同,牛是神圣的动物。倘若某农家未将牛拴好,牛闯入街市,到处乱踩,随便拉屎,横冲直撞,没有哪一个人敢于吆喝那头牛,只好等它在街市上玩够了之后,自己返回牧场。印度报刊常有这样的报道。按照《苏那式钵》故事的叙述,三百头牛才换了一条人命,这主要是说明人的生命极其宝贵。印度文学有喜欢搬弄数字的特点,在吠陀时期未必是三百头牛换一条人命,《苏那式钵》的记述有所夸张,尽管如此,在突出人祭的盛大和庄严方面,这样的记述起到了增强艺术效果的作用。
古代印度是一个宗法制度严格的社会,和许多东方国家一样,其宗法制度集中地反映在财产的继承权上。印度土地肥沃,气候温暖,解决遮身果腹问题较为容易。但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印度次大陆的各个族群,其生殖率一般都比较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结交了一些留学生中的印度朋友,也经常阅读英文的印度报刊。印象深刻的有两篇报道,一是说加尔各答的房价为世界最高,一是说印度的人口增长很快,到2013年将超过中国的人口。从这两篇报道的口吻来看,印度人对此甚为乐观,并不担心人口爆炸问题。从吠陀文献的记载看,古代印度人基本上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子女多就带来一个如何分配遗产的问题。《摩奴法典》第九卷第103条至第219条对子女的财产继承权作了详尽的规定,并阐述了理由。有些东方国家实行长子继承权。比如,从前的日本就是如此,长子可能是大富翁,末子可能是穷光蛋。有的国家则偏重于把财产留给末子。我国西南地区有句俗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皇长子是皇权的继承人,幺儿则担负着给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不过,从理论上说在古代中国严格地实行长子继承权的只有皇帝一家。而普遍地注重末子继承权的则有亿万斯家。换句话说,在古代中国,虽然弟兄分家时各位弟兄都能够得到一份家产,但是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大部分遗产还是留给了末子的。一般说来,已经分家出去单独过活的兄长们大都不会与小弟弟争遗产,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么多年来毕竟是小弟弟在为父母养老送终。吠陀时期的印度在遗产的继承权上偏重于长子。从理论上说,长子有权取得一切遗产。根据就是《摩奴法典》9:106的记载:“长子出生时,甚至在还没有接受净法之前,男子就已经变为父亲而清偿了对祖先的欠债,所以长子应该取得一切。”[6](P.220) 婆罗门教认为,大梵是人类的生主,任何人一出生到世间,就已经欠了大梵的债,因此人的一生应该潜心修行,以期偿付欠债。《摩奴法典》9:107接着说:“人由于长子出生,得以清偿其欠债,获得永生,故长子为完成义务而生;贤者认为,其他诸子系生于爱情。”[6](P.221) 借用基督教伦理学的术语来说,这种看法的着眼点在于如何消除原罪。《摩奴法典》9:109写道:“长子有德无德,可致家庭盛衰;在这世界上长子是最可尊敬的;长子不为善人所慢待。”[6](P.221) 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从家族的总体利益着想的。它说明了吠陀时期的印度实际上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不过,在古代印度财产继承权方面其他诸子依然可以继承到一定的份额,《摩奴法典》9:112规定:“长兄应该先取得遗产的二十分之一,并一切动产中最好的动产;二兄取得其一半或四十分之一,最小的取得其四分之一或八十分之一。”[6](P.221) 此外,根据诸子出身来源的不同,比如,为第几位妻子所生,妻子的种姓如何等,还有种种极为繁复的规定。要而言之,就是长子获得遗产的最大头,而其余诸子也能分得少量的遗产。有了这种认识基础,回头再看《苏那式钵》故事的记述,就会看得明晰一些。贫病交加中的婆罗门阿阇迦利陀(Ajigartha)对待三个儿子的态度耐人寻味,显然与《摩奴法典》的规定不符。面对一百头牛的巨大财产,作为父亲的阿阇迦利陀对长子和末子同等重视,将次子苏那式钵交出去做替身。而且,这是召开家庭会议作出的决定,你看,“他们商定让次子苏那式钵去赎命。”不用长子苏那普乔去赎命,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吠陀时期的印度基本上实行长子继承权。然而,做父亲的不让末子苏诺兰古罗去赎命,就使人纳闷了。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不让末子去赎命,实际上是中国式的末子遗产继承权,即“百姓爱幺儿”,在梵书中的反映。或许有人认为:你联系太远了吧!有证据么?吠陀时期哪里有中国人到印度去嘛?思齐曰:有的,而且人数还不少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第五章《印度古代文明》第二节《吠陀时代对思想文化和宗教的贡献》:“《摩诃婆罗多》是两大史诗中较长和较早的一部,比《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之和的七倍还长。一个关于俱卢国王皇家两个支派相互斗争的很一般的故事,情节却复杂零乱,充满了令人兴奋和诡异的插曲。它包含了一个罕见的一妻多夫制的例子(一位公主答应嫁给四位贵族武士兄弟,他们在一次新娘争夺战中赢得了她的芳心),也包括一个在一次骰子赌博中一掷失去王国的例子。一场真实的战斗在约公元前1400年发生于德里附近,这给故事带来了高潮。据说从希腊、中国和全印各地来的国王加入了战斗,战斗持续了18天,所有参战者均阵亡。”[8](P.162) 对于不擅长历史记载的印度人来说,两大史诗就是他们的历史典籍。常识告诉我们,中国的任何国王都不会只身前往遥远的国度,更不用说千万里之外的印度了,他也不会单枪匹马去参战。结论只能是这样:曾经有一位中国的国王率领了一支大军去参加过俱卢大战。这就是《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透露给我们的历史信息。
苏那式钵的献祭是故事的高潮。这高潮并非一次推到顶端,而是随着苏那式钵对神的祈祷和赞颂而逐渐推向顶端的。这高潮本身也呈现出回环往复的态势,它让人的思绪跌宕起伏。跟随着对神的赞颂,苏那式钵一次又一次地去体会那深邃的宗教感情。在与神的交往中,苏那式钵一次又一次洗涤凡俗的心思,一次又一次地契合于神的本真。苏那式钵一共九次向神祈祷和礼赞。这时,神终于显示大能了,将苏那式钵捆绑于祭柱的那条绳索终于松动了。他脱身开来,圆满地完成了献祭,却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而且,他的父亲诃哩湿旃陀罗的鼓腹病也痊愈了。这病可是肝硬化腹水的绝症呀,现在居然全好啦!由于故事中穿插了大量的颂诗,从速度上说,故事的高潮来得较为缓慢,犹如一头雄壮的大象在森林中缓步前行,它一会儿抬起左前足,一会儿抬起右前足,时而昂起长长的鼻子仰天长啸一声嗡莽,时而甩甩尾巴拂起一阵风采。尽管如此,故事的高潮毕竟在推进,它显示出印度宗教故事特有的深厚底蕴,凸现了人的虔诚,颂扬了神的大能。原来,人和神的关系是互为营养的。诚如《薄伽梵歌》3:10—11所唱:“万物主之造人兮,/原与牺牲俱周。/始谓滋藩此所由兮,/牺牲遂汝之所求。神以兹歆飨兮,/将供汝之馔;/人神相互为养兮,/距汝臻乎至善。”
《苏那式钵》的故事,其指归是祭祀万能。在故事的末尾,还有讲述人的一则特别的申明。就故事的叙述而言,这申明是多余的话,然而对于故事的宗教指归而言,它却是十分必要的:“这便是有关苏那式钵的故事;其中包括《梨俱吠陀》的约一百节诗句;由祭官在举行敷油礼后向国王念诵。”这与欧洲各国寓言结尾的道德教训(moral)十分相似,因此可以认为,《苏那式钵》这一故事处于寓言向小说发展的过渡期中。《苏那式钵》这一故事,其情节远比寓言复杂,其人物远比寓言众多,有人,有神,还有半人半神的仙人,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画面,也远比寓言来得广阔,然而它依然拖着一条道德教训的尾巴。
收稿日期:2007—03—07
注释:
① 宋·周敦颐《周子通书》卷二八。
② 文本依据为魏庆征编《古代印度神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联合出版,第84—106页。为了贯通文脉,不得不添加的话用方括号表明。
③ Narada is the name of a celebrated Devarishi(deified saint or divine sage).He is one of the ten mind-born sons of Brahama,being supposed to have sprung from his thigh.He is represented as a messenger from the gods to men and vice versa,and as being Very fond of promoting discords among gods and men;hence his epithet of Kalipriya.He is said to have been the inventor of the lute or Vina.He is also the author of a code of laws which goes by his name.——Vaman Shivram Apte,The Student'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70)285.
④ 它们是克哩陀时期(Krita-yuga,纯真世、圆满世,此时世界一片圆满美好)、陀哩陀时期(Treta-yuga,三一世、三分世,此时善与恶为三比一)、托娑波罗时期(Dvapara-yuga,二一世、对分世,此时善与恶对半)和迦梨时期(Kali-yuga,斗争世,此时世界充满邪恶),大致相当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公元前八世纪左右)所说的黄金时期(Colden Age)、白银时期(silver Age)、青铜时期(Brazen Age)和黑铁时期(Iron Age)。婆罗门教的一世(yuga),相当于大梵天的一个白昼,即人间的四十三亿二千万年。从梵文的构词法上说,krita、treat、dvapara和kali的含义分别为骰子上标有四点、三点、两点和一点的那一面,作为词素分别指四、三、二、一倍,则这四个时期的长度分别为四十三亿二千万年乘以四、三、二、一。由于古代印度人喜欢搬弄数字,关于这四个时期的长度,尚有其他种种说法。
⑤ 释尊也在一座森林中游荡六年。游荡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苦行,他每天只食一麻一麦,形体枯瘦,身心衰竭,始终未能成道。不过,释尊游荡六年之后,没有选择将自身献祭的作法,而是选择了创立新教来教化众生的更为积极的人生道路。
⑥ 梵文ashram,意思是阶段、时期(stage,period),单数。统称四行期时,人们仿照英文的语法构成其复数形式,用ashrams表示四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