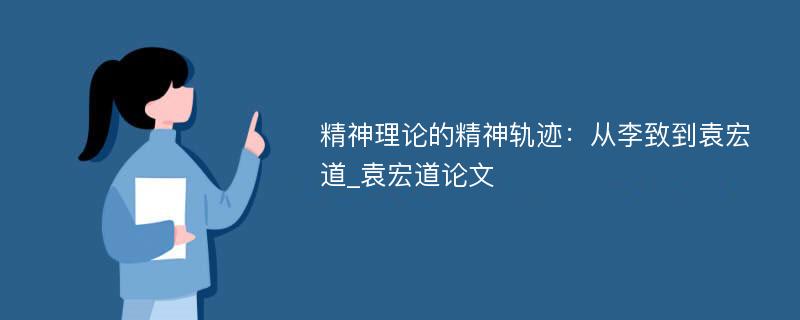
性灵说的精神轨迹:从李贽到袁宏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轨迹论文,精神论文,李贽论文,袁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性灵说的提出
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虽然为同胞兄弟,但性情与处世态度却差异很大。对此,三弟袁中道如是说:“当是时,伯修(袁宗道)与先生(袁宏道),虽于千古不传之秘,符同水乳,而于应世之迹,微有不同。伯修则谓居人间,当敛其锋锷,与世抑杨,万石周慎,为安亲保身之道。而先生则谓凤凰不与凡鸟争巢,麒麟不共凡马伏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意见各不同如此。”[1](P756)宗宏两兄之间如此不同,使他们在常人看来立于共同的文学立场上,实际却主张着不同的文学原则:两人都反对剽窃模拟、虚伪浮弱的文风,但宗道以道学为旨归,而宏道却以反道学的个人性情为旨归。
宏道成为公安派的执旗人、性灵论的倡导者,与李贽的影响直接相关。袁氏三兄弟均对李贽的思想、学问敬重有加,而且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其影响,但是宏道与李贽思想性情的契合最深。1591年(万历十九年)春夏之际,宏道只身前往湖北麻城龙湖拜访李贽,而宗道、中道首次拜见李贽,则是在三年之后(万历二十二年),三兄弟结伴前往龙湖拜见李贽。中道记述,李贽曾对人说“伯(宗道)也稳实,仲(宏道)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于入微一路,则谆谆望之先生(宏道),盖谓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2](P756)由此可见李贽对宏道的特别器重和心契。结识李贽、从学其下,是宏道学问思想转折的关键一步。中道说:“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3](P756)
应当说,受李贽思想的熏陶和砥砺,是宏道突破宗道所奉守的道学文学观的一个必要契机。李贽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不仅突破传统道学的束缚,实际上也突破了阳明心学的“圣学”情结。阳明思想的要义,自然是解放程朱道学的繁琐义理缠缚,但其主旨仍然是归宗为孔孟圣教的“天下为公”的天理。李贽却借阳明的心性解放之途,达成自我生命的解放,寻求个人心性的快乐自在,即他之所谓“自私自利”之学。李贽式的人生理想,落实为文艺,就是突破一切规范体制的自由表现和自由体验,这即他的“童心说”和“化工说”的主旨。李贽的《焚书》初版于1590年(万历十八年)。1595年,作吴县令的袁宏道致信李贽说:“作吴令亦颇简易,但无奈奔走何耳……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4](P221)这证明,在1596年前,宏道不仅阅读了《焚书》,而且与之精神契合极深,奉之为朝夕诵读的经典。因此,1596年,宏道以《叙小修诗》等文为代表,发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5](P187)的性灵论主张时,我们就不奇怪宏道与李贽之间所表现的几乎是一气同声的契合。①
袁宏道倡导性灵论,是以晚明文艺思想解放为大背景的:李贽在文化精神的层面为他提供了基础支撑性的思想资源,而汤显祖所代表的唯情论文学思潮,则在文艺创作的层面给予他重要支持。当时的明代文坛,一方面为王世贞、李攀龙把持,拟古复古之风笼罩文坛,积弱成疾;另一方面则是唐顺中、汤显祖和徐渭诸人主张情感至上、为情作文的反叛之声。袁宏道的性灵论,实是反拟古、求真情的文学思潮的集大成之声。清人钱谦益说:“中郎(宏道)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致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6](P2527)宏道之说有如此影响力,既有他思想敏锐、言词犀利之功,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性灵论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之声。
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性灵”一词,早在六朝时,已被用于文学批评,钟嵘、刘勰、颜之推都使用过。钟嵘说:“晋步兵阮籍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7](P3)他突出了“性灵”实为诗人自我的情感所本源,而且指出“性灵”所发的诗歌特征是“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此说,是与他主性情的诗歌本体观一直的。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8](P1)与钟氏之说相比,颜之推所谓“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9](P20),并刘勰所谓“综述性灵,敷写器象”[10](P346)等说,还未直击诗歌之本,因此清人刘熙载称钟嵘之说“为以性灵论诗者所本”[11](P43),是有道理的。
至于明代,将“性灵”引用于诗文评说,则更为普遍。前后七子的领袖李梦阳、王世贞都有相关论说。王世贞说“诗以陶写性灵、抒纪志事而已”[12](P1811),单从字面而言,就很接近性灵说了。但是,可以归之于公安派名下的性灵说,与此前涉及“性灵”概念的文论之不同,是必须由袁宏道的论说主张来表示的。宏道倡导性灵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自然是写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的《叙小修诗》一文。
[《叙小修诗》之一]弟少也慧,十岁余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余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13](P187—188)
这是《叙小修诗》的第一段。这一段叙述袁中道的文学经历和生活情态。中道以少年聪慧发蒙,开始也不过步趋先贤,但待其识见增长而至于自我觉悟的时候,不仅喜读老庄一派“非圣之书”,而且“的然以豪杰自命”,表现出对世俗亲情伦常的背弃,卓然独行而寄情于天下山水。正是这个特立独行的出世豪杰形象,成为宏道性灵论的代言人。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宏道在此提出性灵论的宗旨是独特自由的自我表现,它的要义是在形式上不受规范约束,在内容上是自我真情表现。宏道好友,性灵论的支持者江盈科在《敝箧集叙》中转述宏道话说:“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蝼蚁蜂虿皆足寄兴,不必《关雎》、《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是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而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之为沾沾
自我表现可以是澎湃激越的,也可以是婉约低徊的,但是,宏道借评中道诗,推崇“如水东注,令人夺魂”的直露式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宏道特别赞赏中道诗歌的“疵处”而轻其“佳处”,认为其“佳处”没有摆脱“粉饰蹈袭”的习气,而“疵处”却“多本色独造语”。推崇“本色独造语”,就是推崇真我和个性表现,性灵论的宗旨就在于此。
李贽以“童心说”立意,其一,童心就是真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其二,好文章必须是真心之作,有真心就有好文章,“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15](P91—92)。李贽童心说的立意,正是宏道性灵论思想所源。
宏道倡导“独抒性灵”的“本色独造语”,是针对晚明“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的文坛风气而发的。宏道认为,剽窃模拟造成了“共为一诗”的局面,作诗实为做“诗家奴仆”[16](P695—696)。在1596—1600年间,他修书撰文的主题内容,就是抨击这种“共为一诗”之风。在写于1597年的长信《张幼于》中,宏道对模仿蹈袭再次作了尖锐痛斥,用词非常犀利。他说:
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17](P501—502)
在此信中,宏道直言自己作诗“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对于循规蹈矩、步趋模拟之徒是一个颠覆性的态度。对于世人对秦汉唐宋诗文的尊卑褒贬,他亦颠倒而言。他的目的就是要倡导“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的立个性、写真情的文风。因为对剽窃模拟、“共为一诗”的深恶,他立言不惮矫枉过正,竟然以“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这样的语词斥责批评对象。
在《张幼于》这封信中,宏道特别拒绝张氏以“似唐诗”选取其诗。宏道指出,在自己的诗作中,“似唐诗”非“自有之诗”,而“非唐诗”才是“自得意之诗”。他说:
公谓仆诗亦似唐人,此言极是。然要之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唐诗,安得不谓中郎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近日湖上诸作,尤觉秽杂,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昨已为长洲公觅去发刊。然仆逆知幼于之一抹到底,决无一句入眼也。何也?真不似唐也。不似唐,是干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复谓之诗哉?[18](P502)
在这段话中,宏道很明确地将反对模拟的目的落实到自我确立:世人以唐诗为榜样,求“似唐诗”,他反其道而行之,求“非唐诗”,并认为只有在“非唐诗”中,才可求自得意,才能成就自我之诗。
三、“不法为法,不古为古”
性灵论的主旨是主张自由任性的自我表现,为达此目的,就必须破除拟古派所设置的唯古是崇、步趋模拟的立场。宏道说:
[《叙小修诗》之二]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抄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19](P188)
前后七子的文学旗帜是尚古非今,与之相反对,则是去古推今。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20](P92)这是当时最激烈大胆的反复古言论。宏道批评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使用的武器也从李贽所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之主张演化出来。在“真心出至文”的立论下,李贽将原本不为文学正统所认可的俚俗文艺推崇为“天下至文”,而且转而菲薄圣典《六经》;宏道的论说,则以“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立论,同样否定“古胜今弱”,也同样推崇民间“无闻无识真人所作”的俚俗文艺,嘉奖其妙处在于不模拟剽窃,“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宏道此说发出的是对人生自然情感欲望的肯定,将之作为文艺的主题内容,特别明确地发出文艺世俗化的呼声。就此而言,虽然两人都关注并吸取民间俚俗文艺的素朴自然之意,但是,李贽的立场仍然还是在一个“士夫”的“精神建构”上,而宏道则表达着“士夫”精神并追求世俗欲望情感的意志。
1596年,在写作《叙小修诗》的同年,宏道写了《诸大家时文序》等文,阐述“时变文变”,“文必从古而今”的文学演变观。在《诸大家时文序》中,宏道指出:“以后视今,今犹古也”,古今之分,是延续转变的。他批评拟袭古文词作文的做法,认为如此导致了“所谓古文者,至今日而蔽极”的文坛状态。他说:
优于汉谓之文,不文矣;奴于唐谓之诗,不诗矣。取宋、元诸公之余沫而润色之,谓之词曲诸家,不词曲诸家矣。大约愈古愈近,愈似愈赝,天地间真文澌灭殆尽。独博士家言,犹有可取。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才之所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二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子之伸其独往者,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为文不类古,至摈斥之,不见齿于词林。嗟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
宏道认为模拟古词作文,“愈古愈近,愈似愈赝,天地间真文澌灭殆尽”;他推崇时文,“体无沿袭,其词必极才之所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比之于“古文”(拟古之文),“时文”的长处就在于依时顺变,“手眼各出,机轴亦异”,即成为随心任情的真实表现。
“求真”,是宏道反拟古复古的意旨所在。在《丘长儒》(1596年)一信中,他说:
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果儿,反不如一张白纸,诗灯一派,扫土而尽矣。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22](P285)
“真”是个人才气性情的独特存在,它不仅不能求同于古人,而且也不能混同于古人。“贵真”,就是推崇表现自我的个性真实。《诗经》、汉魏诗歌、选体(源自萧统《文选》)诗歌、唐代诗歌、宋代诗歌,是历史递进的。宏道认为,从情感气势而言,诗作从古而今确有一个递减之势;但从状写奇妙而言,诗作却是今优于古。“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自然不可尊古卑今。在1597年的《江进之》一信中,宏道提出“夫物始繁者终必简,始晦者终必明,始乱者终必整,始艰者终必流丽痛快”的论说,以此为准则,诗文发展,从古至今,后代优于前代。“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23](P515—516)
“求真”,要表现“真我面目”,则不能“有法”(拘于格套),而是要“无法”(不拘格套),信心任口而作。在1597年《小陶论书》一文中,宏道提出“古人无法,不可学”的论说:
小陶与一友人论书。陶曰:“公书却带俗气,当从二王入门。”友人曰:“是也。然二王安得俗?”陶曰:“不然。凡学诗者从盛唐入,其流必为白雪楼;学书者从二王入,其流必为停云馆。盖二王妙处,无畦径可入,学者摹之不得,必至圆熟媚软。公看苏、黄诸君,何曾一笔效古人,然精神跃出,与二王并可不朽。昔人有向鲁直道子瞻书但无古法者,鲁直曰:‘古人复何法哉?’此言得诗文三昧,不独字学。”余闻之失笑曰:“如公言,奚独诗文?禅宗儒旨,一以贯之矣。”[24](P472—473)
在《答张东阿》(1599年)信中,宏道说:“唐人妙处,正在无法耳。如六朝、汉、魏者,唐人既以为不必法,沈、宋、李、杜者,唐之人虽慕之,亦决不肯法,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25](P753)在宏道看来,古人的妙处,就在于求真,不步趋模拟,不循规蹈矩,即无法而行。因此,他认为,学古人,唯一可学的就是其“无法”。在《叙竹林集》(1599年)中,宏道说:
往与伯修过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画苑诸名家,如文征仲、唐伯虎、沈石田軰,颇有古人笔意不?”玄宰曰:“近代高手,无一笔不肖古人者。夫无不肖,即无肖也,谓之无画可也。”余闻之悚然曰:“是见道语也。”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像,不师先辈。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是故减灶背水之法,迹而败,未若反而胜也。夫反所以迹也。今之作者,见人一语肖物,目为新诗,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嗟夫!是犹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谓之蔡中郎,岂不悖哉!……不法为法,不古为古。[26](P700—701)
董其昌(玄宰)所谓“无不肖,即无肖”,是指习画者临摹古人,从笔画上模拟古人,仅得其笔画形式(“无不肖”),而失其精神气韵——“无肖”。绘画的旨归是以形得神,无神,即“无画”。宏道对董说作发挥,在“人—物”、“道—心”、“万象—先辈”三重两极对立中,明确主张以“物”、“心”和“万象”为师。宏道的选择,是要排斥他人(人)、学问(道)和古人(先辈)的障碍,让自我以无拘束的心灵直接与现实万象打交道。宏道提出学习古人,不能从形式、字句着手——袭其迹,而要得其精神真谛——反所以迹。唐人能创作不朽于世的唐诗,其“真法”就是唐人自作唐人,即“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不法为法,不古为古”,在宏道看来,“法”与“古”的至理均在于自我与自然的直接交流以及相应的真情表现。
宏道写于1600年的《雪涛阁集序》,当是他关于“时异文变”思想的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在该文中,他说: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等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辩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驺子,皆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27](P709—710)
宏道在这里以屈原创作的《离骚》体裁为中心,论述了诗歌体裁、风格必然顺时而变的规律。“《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宏道承认《诗经》中的《雅》与《骚》之间有情感上的相近性,但又认为《雅》的体式不足以表达屈原的情感,因此屈原创作《骚》体裁。应当注意的是,宏道一方面看到苏、李述别诗及《古诗十九首》对《骚》体的改变,另一方面又肯定它们对《骚》的精神继承性,认为必须称为“真《骚》”。这说明,宏道主张诗文顺时而变,反对因袭古人,但并不反对和否定从古而今的传承关系。进而言之,宏道论及从古而今,诗由虚而实、文由实而虚的演变,并得出古人之法变化无穷,不可概括。在对文学历史演变规律认知的基础上,宏道指出复古主义的症结在于:字比句拟、拘于格套,致使作者对外与生动的现实人生隔绝,对内屈抑才情心意,从而不得不终结于模拟附和,文学创新之力衰竭。
在古今、新旧之争中,宏道并不一味厚今薄古、喜新厌旧。他对于古今新旧,只持一个标准去衡量,即是否出于性灵之作。江盈科《敝箧集叙》记述说,袁宏道曾告之:
唐人之诗,无论工不工,第取而读之,其色鲜妍,如旦晚脱笔研者。今人之诗即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饤饾,才离笔研,已似旧诗矣。夫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盖新者见嗜,旧者见厌,物之恒理。唯诗亦然,新则人争嗜之,旧则人争厌之。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拟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由斯以观,诗期于自性灵出尔,又何必唐,何必初与成之为沾沾哉! [28](P1685)
四、“情至之语,自能感人”
性灵论的精神原则,正面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张扬,反面主张打破因循格套、模拟仿袭,因此,它在创作手法上则主张任性纵情、直率激烈。袁宏道说:
[《叙小修诗》之三]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
宏道的描述,将中道表现为一个不受世俗规范束缚而又情感丰富、任情恣性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必然是才情过人,而命途坎坷。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一个潦倒无能的弱者,但恰是其积贫累病,而胸郁极愁,不可不发之于诗。宏道为中道诗歌失于直露伤怨作辩护,认为“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宏道此论,无论从意旨还是从文字来看,都与李贽《焚书·杂说》中所论相近。李贽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30](P91)
两相比较,宏道之论,对李贽思想的接受认同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仅接受了李贽的直抒胸臆的主张,而且也把李贽所推崇的愤懑激烈的狂者文学作为最真实、最个性的文学加以推崇。与李贽每每标举“豪杰异人”、“大才狂汉”、“出格丈夫”,并自认“其心狂痴,其行率易”一样,宏道也以“颠狂”为文人士夫之至尊品格。他说:
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张无尽诗曰“盘山会里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颠”是也。化虽颠去,实古佛也。求之玄,有周颠焉,高帝所礼敬者也。玄门尤多,他如蓝采和、张三丰、王害风之类皆是。求之儒,有米颠焉,米颠拜石,呼为丈人,与蔡京书,书中画一船,其颠尤可笑。然临终掌曰:“众香国里来,众香国里去。”此其云来,岂草草者?不肖恨幼于不颠狂耳,若实颠狂,将北面而事之,岂直与幼于为友哉
这段话写于1597年《张幼于》信中。在推崇一干历史狂士之后,宏道发出“不肖恨幼于不颠狂耳,若实颠狂,将北面而事之,岂直与幼于为友哉?”这就是,不仅他自认为颠狂之士,更要求他人亦作颠狂,方可与为友。值得注意的是,在早一年(1596年)撰写的《识张幼于箴铭后》中,宏道还承认古今士人中,既有如司马相如、东方朔、蔡邕、阮籍一样的放达人,又有拘谨恭敬备至的“慎密人”。“两种若冰炭不相人,吾辈宜何居?袁子曰:两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今若强放达者而为慎密,强慎密者而为放达,续凫项,断鹤颈,不亦大可叹哉!”[32](P193)据其“率性而行,是谓真人”之论,在此文中宏道是认同“淳谦周密,恂恂规矩”,即非放达、非颠狂的性情的。而一年之后,对于同一个“张幼于”,宏道却要违其淳谦的天性、“强求”其颠狂。
被袁宏道推崇为明代第一的文人是旷世奇人徐渭。在《徐文长传》中,袁宏道将他在1597年从友人陶望龄家中偶然读到徐渭作品时的情景,描写为一次“惊跃”的人生奇遇,深恨“何相识之晚”。他用近于“文学”传奇的笔调向读者描述徐渭形象: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在宏道的笔下,徐渭俨然成为一个天生的文学英雄,其天才盖世、卓尔不群、慷慨激烈,成为其终生不渝的特质。这显然不是徐渭的本来面貌。徐渭从一个怀才不遇的普通文人,锻炼成为一个绝世破俗的文化英雄,是历半生百死千难的人生磨难的结果。②徐渭于1593年病逝,宏道在其逝后四年发现他,而1599年宏道撰写此传时,徐氏已逝六年。宏道对徐渭的理想化书写,当然不是一个文人对另一个已故文人的浪漫想象或普通敬意所使然,而是借徐渭其人,再塑性灵论代言人的理想形象。而这时,离《叙小修诗》的1596年已过五个年头。由此足见,宏道坚持性灵,以恃才傲物、任性纵情的狂士文人为文学英豪的理念仍没有改变。
注释:
①关于李贽与袁宏道的思想关系,参见何天杰:《李贽与三袁关系考论》,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春之卷)。
②参见肖鹰:《“旷世奇人”徐渭精神演变再考》,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2);肖鹰:《祢衡:老年徐渭的少年情怀》,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3)。
标签:袁宏道论文; 诗歌论文; 李贽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叙小修诗论文; 唐诗论文; 焚书论文; 古诗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