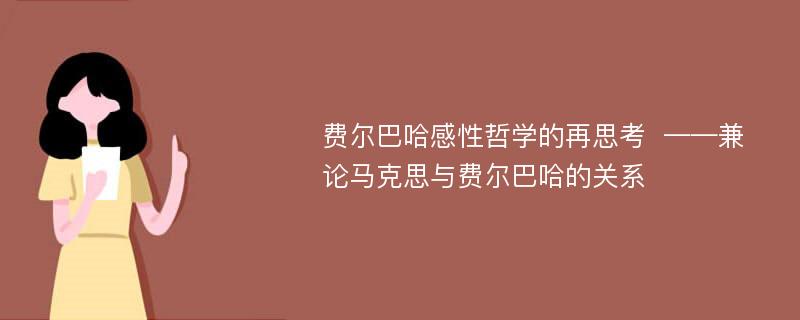
【摘要】费尔巴哈感性哲学革命从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改革与颠覆开始,坚持“感性第一性”原则,希望通过“感性”与“感性直观”回归感性的生活世界。但这一革命很少受到学界严肃而认真的对待,“感性第一性”原则及“感性直观”的积极意义为“感性活动”所遮蔽。实际上,马克思的感性革命就是将他的“感性第一性”原则扩充、发展为“感性活动”即实践原则。此外,作为感性哲学出发点的“人”也不是抽象的“一般人”,而是感性个体,不过费尔巴哈对其历史内容没有进行具体的阐释,马克思则在感性与历史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关键词】感性;感性直观;思辨哲学;感性活动;现实的人
费尔巴哈虽自称其哲学为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但其哲学诞生以来却很少受到学界严肃而认真的对待。一是学界一旦需要陈述他的哲学,可能会说他是黑格尔之子,马克思之父,但对于他自身的哲学却缺乏比较细致的研究;二是学界关于他的研究常停留于一些抽象的断言上,特别是习惯于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个结论出发去解读他的思想;三是学界关于他的研究常集中于他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颠倒,但对于他从“感性”去理解“存在”关注不够。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他的感性哲学对以往哲学的艰难理论突破和对新哲学的富有创见的建构晦暗不明,比如罗素就认为费尔巴哈哲学除了恢复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权威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供世人称道的成就。
一、政治革命与哲学革命
费尔巴哈是于19世纪30年代末以哲学家身份登上德国历史舞台的,他认为当时的德国既需进行政治革命,也需进行哲学革命,但后者比前者更为迫切和关键。
第一,德国发动政治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没有参加1848年革命,费尔巴哈在生前死后遭受到了很多批评,他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的序言曾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过辩解,也在该书第一讲中再次提及到了他所受到的批评。费尔巴哈的时代是德国政治无比黑暗的时代,一切官职的升迁都必须通过政治上的奴颜婢膝或者宗教上的欺蒙拐骗才可以得到,费尔巴哈曾努力地表述了当时德国社会的公民要求和政治要求,他敌视一切以专制君主的权力为转移的封建国家,主张国家应根据人们的意志和愿望而存在,君主权力无限是极不道德的。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德国政治革命的时机还未成熟,“按照我的学说,空间与时间是一切存在与本质、一切思维与活动、一切繁荣与胜利的基本条件。革命之所以落到如此可耻的和如此无成效的结局,并不是因为议会还缺乏虔诚……而是因为这次革命没有任何地点感和时间感”[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02页。 。而且,即使政治革命获得了成功,假若没有哲学革命的成功,政治革命的意义也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在决定性意义上摆脱了思辨哲学之理性魅影和宗教迷信之上帝魅影后,才能在决定性意义上否认政治的奇迹,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末日审判才会到来。因此,他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中鼓励大家先做政治上的唯物主义者。
第二,近代思辨哲学在黑格尔这里发展到了顶峰,基督教作为国教是统治德国的重要力量之一。在费尔巴哈看来,思辨哲学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把客观本质主观化,即把自然的、人的本质看作是非自然、非人的东西。基督教以想象的对象为现实的对象,黑格尔思辨哲学也不过是理性化的神学,当我们进行思维时,本应以思维的感性前提为对象,但实际上却把思维独立出去使之成为一个绝对无条件的本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可以在神学的天国里再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也可以在神圣的逻辑学的天国里再现”[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 。正因为思辨哲学与基督教乃是一丘之貉,即都是由纯粹的、思辨的、抽象的“存在”演绎出经验的、现实的、原始的“存在”,因而理性和上帝都应成为哲学革命的对象,他也因此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和宗教思潮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对此,瓦特夫斯基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费尔巴哈早期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他的宗教批判的前提和基础,但发展到后来,他对宗教的批判就成了他批判思辨哲学的方法论上的实质性基础。[注]W. Wartfsky, Feuerb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7.
因而,积极开展哲学革命成了费尔巴哈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他一生都致力于将哲学从抽象精神和上帝那里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以使我们能对世界、自然和人本身具有正常的观念。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而其意义也许还要经过好几个世纪才能真正显露出来,同时他还说到,哲学革命只是整个革命的一部分,哲学革命之后还有很多事要做,他一个人没办法完成,只能留待后来者了。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主要包括一般健康教育及呼吸机通气治疗的常规护理等。研究组接受针对性护理,具体为:①向家属讲解有关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的病因病机、治疗方法及并发症等,争取家属的信任与配合;②抬高床头15°~30°,以避免新生儿食物反流与误吸的发生,做好气道护理,及时清除气道分泌物,保证起到通畅,定期为新生儿翻身,防止褥疮;③每天评估新生儿的口腔状况,预防口腔感染,遵医嘱使用质子泵抑制剂、H2受体抑制剂,预防消化道溃疡;④认真评估新生儿的镇静程度,遵医嘱合理使用镇静剂,实施程序化镇静。
费尔巴哈认为哲学的出发点不是上帝,也不是精神,而是感性的自然和人,“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页。 。费尔巴哈曾说他的新哲学不同于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费希特所主张的自我,亦不是谢林的绝对同一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抽象的、仅仅被思想的或被想象的原则,而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将黑格尔哲学的思维、理念和理性在先的原则颠倒过来,突出存在、现实与感性的中心地位,确定“感性第一性”原则并以之对抗思辨哲学可以说是费尔巴哈哲学革命最重要的努力,“我不能承认感性的东西是从精神的东西派生出来,同样我也不能承认自然界是从神派生出来;因为没有感性的东西或在感性的东西以外,精神的东西便什么也不是;精神不过是感官的升华、感官的精粹罢了。”[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87页。 于是,费尔巴哈“把哲学的开端确立为具体的‘感性存在’,公开声明自己的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用‘感性’对抗黑格尔抽象的理性,开始了对终极存在进行追求和探索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颠覆,将哲学的视角从单纯的理性思辨转向对于感性世界的理论关照,开启了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新路向”[注]张云阁:《马克思思维方式论——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可见,颠倒的不仅仅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是以往哲学之非感性和超感性原则,“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既不是费尔巴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亦不是他以后哲学要研究的中心问题”[注]胡海波、韩秋红:《试谈外国学者对费尔巴哈哲学功绩的历史评价》,《外国问题研究》1990年第3期。 。
二、“感性第一性”原则的确立
因此,尽管马克思提出了“感性活动”与费尔巴哈“感性直观”针锋相对,但以此之故,完全否认或者忽视“感性直观”的积极意义是有问题的。不过对于费尔巴哈力图通过所谓的“生命直观”去揭示语言、思想之对象的本质秘密,并把不同的感性事实联结为一个互相有所联系的“思维中的直观”,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解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彼此之间的真正联系只有在建构世界和自身的感性活动中才能成为可能。
情感表达和民族声乐联系非常紧密,二者相互依存,互不分割。声乐演唱是情感表达的载体,而情感则为声乐演唱注入活力,使其内核更加饱满,作品更具感染力,非常容易打动人。
再举一例验证:L与F导联夹反接,余不变(图4)。重新作图形成新的Einthoven三角,与正常连接形成的Einthoven三角(图3)比对。比对结果表明,Ⅰ、Ⅱ导联互换位置,aVL与aVF导联互换位置,Ⅲ导联P-QRS波为正常连接Ⅲ导联波形图的镜像改变。
“感性直观”是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又一重要概念,学界以往认为它指的是对认识的机械反映,但通过深耕费尔巴哈文本,笔者发现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它强调感觉是认识的起点,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并生成人的感觉内容。费尔巴认为既然哲学是关于现实存在物的知识,那么,哲学的最高规律和任务就必须按照现实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和理解它们。笛卡尔曾认为在思想、在怀疑的我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费尔巴哈却认为它仍是可怀疑的,只有“感觉是人的第一个可信赖的东西,是人打开世界同时又是自己向世界开放的窗户,既是科学的导师和鼻祖,也是一切怀疑和争论的审判者”[注]董兴杰、才华:《费尔巴哈论基督教》,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坚持从抽象到具体,不过是将抽象概念加以现实化而已。第二,感性直观是辨别事物真假的唯一标准,真理性与现实性、感性的意义等同。与自绝于感官的思辨哲学不同,费尔巴哈认为“只有那种直接通过自身而确证的,直接为自己作辩护的,直接根据自身而肯定自己,绝对无可怀疑,绝对明确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神圣的。但是只有感性的事物才是绝对明确的”[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0页。 。当众人直观不一致的时候,多数人直观所肯定的一致意见便是真理,这一主张也曾为他招来许多批评。实际上,费尔巴哈想强调的只不过是类的真理性,他认为只有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才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我所以确知有在我以外的其他事物的存在,乃是由于我确知有在我以外的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一个人所见到的东西,我是怀疑的,别人也见到的东西,才是确实的”[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3页。 。第三,要实现对感性世界的把握,感性直观必须与思维结合,“哲学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维和直观,因为思维是头脑所需要的,直观感觉是心情所需要的。思维是学派和体系的原则,直观是生活的原则”[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1页。 。由此可知,思维充当学派和体系的原则,直观充当感性生活的原则,当且仅当二者有效结合,才能实现对感性事物的真正认知。其中,感性直观又是最根本的,因此,费尔巴哈一方面强调我们必须以感性的东西为最可靠、最明晰的东西,并从它出发过渡到复杂的、抽象的对象去,另一方面又强调思维必须在直观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认识,“既然只有为思维所规定的直观,才是真正的直观;反过来说:也只有为直观所扩大所启发的思维,才是真实的现实界的思维”[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9页。 。这与康德所强调的直观与思维的统一,有着某种一致性,也有着某种不一致性。直观和思维在现实意义上的真正结合,使费尔巴哈感性哲学既克服了18世纪唯物主义片面夸大感觉的作用,也克服了康德、黑格尔哲学片面夸大思维的作用。从对“感性直观”的强调出发,费尔巴哈认为当我们去探索生命之谜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求助的不是神,而是要勇敢地走向感性生活,后来马克思将“感性第一性”原则扩充、发展为“感性活动”即实践原则,使得费尔巴哈所开创的感性革命得以向纵深推进。
至于费尔巴哈视域中的“人”,在1828年他写作博士论文时期,他还认为理性才是人的本质,且是不朽的,而个体则并不是不朽的。但随着他思想的第二次转变,他通过感性直观对事物的“一般本质”采取了唯名论态度,认为“绝对精神”、“上帝”、“人”等只不过是抽象空洞的集体名词,这些标志一般的词只不过是主观的一种存在,是语言的一种方便表达,“因此德国人,虽然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但只在语言上如此,而不是实际上如此,只在思想上如此,而不是在感性上如此,也只是在精神上如此,而不是在肉体上如此,总而言之,一切都是纸面上的,而不是现实的”[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47页。 。因此,我们不能到处用省略的方法以概念代替直观,语言表达的不是事物本身,实际事物也不可能全部而只能以片段的方式反映在思维中,因而个别存在物具有不可言说性,“我之所以存在,决不是靠语言的或逻辑的食粮——自在的食粮——而永远只是靠这种食粮——依靠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9页。 ,但个别存在物的不可言说性也使得有人拿语言作证据去证明感性个体存在的不可能性。
打开网络和手机,一个个标题令人触目惊心:《被手机毁掉的下一代》《被抖音毁掉的中国年轻人》《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被直播毁掉的中国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是“标题党”耸人听闻吗?至少不全是。在青岛海边,年轻的妈妈专注于手机屏幕的方寸世界,身边两个年幼的双胞胎孩子被海水卷走,而她竟浑然不知。众人全力搜寻,最后找到了一个孩子的尸身。
三、感性直观、感性活动与现实的人
自费尔巴哈哲学诞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他的哲学是肤浅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或直观的唯物主义。他们或认为他的“感性直观”只是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因而尽管他提出了“感性第一性”原则来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同一,但实现的只不过是感性直观的消极同一。或认为他从抽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出发是片面的感觉主义,不理解人和社会的本质,因此,“从恢复唯物主义哲学的权威、否定意识的先验性质来看,费尔巴哈的哲学离现实更近了;从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来看,费尔巴哈却比黑格尔离现实更远了,变得更为抽象”[注]刘海江、萧诗美:《异化思想的辩证演绎: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可以说,以上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马克思对其哲学评价的影响,于是比较之下因马克思哲学独特的影响而认定他的哲学是肤浅的、狭隘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哲学两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因为这两个文本预示着它的正式确立,但学界也恰恰是依据这两文本认定费尔巴哈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或者直观的唯物主义,它跟马克思的新哲学有着质的区别。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而不是从“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批判他从抽象的生物学意义去谈“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直观性”继续展开严厉批判,认为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出发,其直观和感觉的主体是抽象的“一般人”,“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这里涉及到对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费尔巴哈“感性直观”是否只是旧物主义对认识的机械反映?二是费尔巴哈视域中的“人”是否只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历史中的个人?
费尔巴哈一生的思想轨迹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神学转向理性,此时他尊黑格尔为精神上的再生之父,但他从未成为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推崇与对它的质疑始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信奉黑格尔哲学之后不久,他就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逻辑产生质疑,并开始认真思考思维和存在、逻辑和自然的关系问题。黑格尔主张逻辑独立于自然和历史之外且可以无条件地过渡到自然和历史,费尔巴哈却认为只能是从自然过渡到逻辑,纯粹的逻辑就如童贞的处女一样,不可能产生出自然。因而,黑格尔从逻辑出发只不过是表明了思维与自身的同一,它永远不能超出自身并达到现实的感性世界,“黑格尔哲学的最大秘密和主要错误就在于颠倒了主语和谓语、存在与思维、现实与理念、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因而,克服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关键就在于将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恢复感性对于思维的基础性地位”[注]郗戈:《“感性世界”的重构与〈资本论〉的世界观》,《哲学动态》2016年第3期。 。
再生水项目提供的是替代水源,且一次投入资金额较大,可行的再生水项目方案必须在实施效果、财务状况、环境影响等方面较之常规供水、调水和海水淡化等更具优势。首先,规划必须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在各种供水相互竞争的格局下,全面比较,谨慎估算,充分利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对再生水的支持,寻找再生水项目的细分市场,确定供给和需求数量、需求群体、用途等。其次,进一步分析融资条件、收费标准,保障财务可持续并具有价格竞争力。再次,在水源获取、处理程度、多水质或者单一水质处理、技术工艺、产量、输水方式、储存方式、管网布局等多个环节进行比较,逐步完成最优方案的规划设计。
费尔巴哈哲学革命是从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改革与颠覆开始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抗衡,但由于长期以来对理性及理性批判所取得的成就的推崇,理性主义逐渐战胜了经验主义,并在黑格尔这里发展到了顶点,新的开端似乎不可避免,“如何克服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虚假性问题就成了哲学思想史上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可由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整个近代知识论哲学所开展的以颠倒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为目的的‘感性复兴运动’来加以证明”[注]王国坛:《马克思对传统感性思想的超越与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可见,“感性”是费尔巴哈哲学中非常关键的概念,在他看来,感性就是指现实性,即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它从本质上来说是理性、精神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精神的属性,而且感性即现实世界是人通过感觉可以直观的。通过对“感性第一性”原则的强调,他使得哲学从没有生机与生气的精神世界转向到了生动活泼的现实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感性决不是与某一哲学的某一方面发生矛盾,而是与整个理性主义传统发生全面的矛盾。“如果说,在费尔巴哈那里,黑格尔哲学乃意味着整个近代哲学的完成,意味着一般哲学—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实现,意味着柏拉图主义传统之奥秘的最终暴露,那么,‘感性’同‘绝对精神’的对立就不止是这一新原则同黑格尔哲学的对立,而是它同整个近代哲学,同一般哲学—形而上学,同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对立。”[注]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1页。 但学界恰恰只留意到费尔巴哈对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颠倒,而没有留意到费尔巴哈所肯定的存在不是抽象的物质,而是具体的感性世界及生活本身,这导致我们对费尔巴哈哲学革命及感性哲学之重要意义缺乏真正的理解。使哲学回归生活的确是德国古典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向,费尔巴哈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研究哲学的方法时说过:“我的思想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种解释事物的方式。”[注]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通信和遗著》,1847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35页。转引自胡海波、韩秋红:《试谈外国学者对费尔巴哈哲学功绩的历史评价》,《外国问题研究》1990年第3期。
施蒂纳曾认为费尔巴哈视域中的“人”是凌驾于个人即“唯一者”之上的一般人,他甚至认为费尔巴哈尽管以对人的敬畏取代了对神的敬畏,但充其量仍不过是基督教的最后变形,甚至是一种很糟糕的变形,它不仅没有让我们摆脱精神,反而使得我们更进一步靠近精神了,马克思后来转向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是受到了施蒂纳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施特劳斯的“实体”,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唯一者”,费尔巴哈的“类”和“人”,都同属于“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他更是严厉批判了费尔巴哈虽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没有将其理解为“感性的活动”,即没有从人广泛的社会联系去考察人及人生活的历史条件,因而,费尔巴哈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在于,费尔巴哈视域中的人并不是纯粹的“一般人”,相反,它是感性的个体。费尔巴哈是通过感觉主义或者唯物主义来强调感性个体的独特地位的,“感觉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同一的。然而,它肯定人并不是为了天职……也不是为了黑格尔逻辑的理念……不是的!它肯定人是出于纯粹的感觉主义的爱的欲望和对生活的眷念。理性或者那种脱离感觉并且否认感觉的真实性的哲学,不仅不能从自身认识个性,而且把个性当作自己的自然敌人而拼命加以仇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学说都证实了这一点。只有借助感觉我才知道,在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些生物,另一些人;我是一个与他们不同的个别的生物,正如他们也与我不同一样”[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8页。 。这些彼此不同的独特个体具有“不可分割性、统一性、完整性、无限性;我从头到脚,从第一个原子到最后一个原子,彻头彻尾是单个的实体”[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8页。 。所以,对于人来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般的人,只是作为某个绝对被规定的人而已,人的个性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不能被翻译和模仿的。“我恰恰和你同样地感觉着、希望着、思维着,但我思维并不是用你的或一般的理性,而是用我自己的、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头脑中的理性。我希望着,但也同样不是用你的意志和一般的意志来希望,而是用我自己的、在这里借助于这些肌肉来付诸实行的意志来希望;我也和你一样因为一些正在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过的不公正的现象而感到痛苦,但是我不是用某种一般人的心境来感觉,而是用自己的心境——正如在我的血管中的血液是我自己的、个人的血液一样——来感觉。”[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9页。 总之,费尔巴哈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必然的、必不可少的,都受着感性、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感性个体是可以直观的也是可以用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绝对真理,类也并不意味着抽象,它只不过意味着还有存在于我之外的其他个体。
正确在于,诚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费尔巴哈虽强调哲学应从现实的感性个体出发,但他对感性个体的现实内容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历史性解读与揭示,从而导致学界认为他所谈的仍只不过是抽象的人而已。费尔巴哈自己曾说,由于时间精力有限,这一工作他留给后来者去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正如他所希望的,对这一现实的内容进行了具体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这一现实的人既不是离群索居之人,也不是处于固定不变状态之人,而是处于一定现实历史条件之下且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中的个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72页。 。从“现实的人”的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以对历史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得出了历史发展的三要素的结论,即历史发展过程是由三种生产形式推动的: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为满足新出现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也称物的再生产过程;人自身的生产,即家庭关系。
实际上,除强调人是感性个体外,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也已经具备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比如他在对神学的批评中就谈到了生活上的恶、烦恼和痛苦具有必然性,并认为消除这些恶、烦恼和痛苦不能依靠所谓的上帝,而只能是“实践上的非信仰,这种本能上的无神论和利己主义”[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70页。 。这里所提到的利己主义不是生物学上的利己主义,而是已经包含了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利己主义,它既是一切祸患之原因,也是一切良善之原因,农业、商业、艺术和科学等都因它而起并得到发展,据此,董晋骞认为“费尔巴哈已经接触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实质”[注]董晋骞:《费尔巴哈哲学的现代哲学性质及其唯物史观萌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费尔巴哈认为当时德国财产为少数人占有,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新时代一定是大多数人能维护他们的合法利己主义并反对特殊阶级的不合法利己主义的时代,创造历史的也一定是合法利己主义受到压迫的大多数贫民。
四、结 语
可见费尔巴哈感性哲学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及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并为马克思哲学的诞生创造了很好的思想条件。如果说以往哲学以抽象的思辨和幻想的上帝为本体,致力于防止感性观念污染抽象概念,并在与感觉的矛盾、对立中进行思想,那么费尔巴哈新哲学则致力于以感性存在和感性直观的事物为本体,是在与感性直观和睦、协调的状态中进行思想的。感性哲学革命预示着新的哲学时代的来临,回归现实生活与鲜活生命是这一新哲学的重要表征,先有生活才有哲学,而不是先有哲学才有生活,“以前对我来说生活的目的是思维,而现在生活对我则是思维的目的”[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50页。 。所以,费尔巴哈坚信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真正的哲学家不仅必须认识事物,而且必须感受事物,他不仅从直观开始,而且还要回到直观,并且当哲学完成之时也就是哲学消灭之时,而当哲学消灭之时,也就是全人类成全之时。“我的第一个愿望是使哲学成为全人类的事。但谁若一旦走上这个道路,谁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应该把人看成自己的事情,而哲学本身,却应该被否弃。因为只有当它不再是哲学时,它才成为全人类的事。”[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50页。 从这个角度讲,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确对旧哲学进行了艰难理论突破,希望哲学能重新扎根在现实基础之上。
长庆石化公司信息门户自2003年建设应用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门户系统深入应用,为更好地适应集团公司信息化从集中建设向集成应用发展需要,门户升级工作必不可少。在其升级过程中,新老技术的更替成为此次门户升级的关键。
所以,费尔巴哈感性哲学革命是成功的,理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但正如学者罗萨·苏亚雷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概念的批判与变革》(Ludwig Feuerbach's Critiqu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hilosophy)一文中所提到的,费尔巴哈哲学尽管导致了哲学的一次非常有趣的转变,但其重要性和意义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因此,罗萨·苏亚雷斯认为我们需要对费尔巴哈哲学重新展开认真的探讨,并通过这一探讨使哲学回到感性和具体的现实本身。[注]Cláudia Dalla Rosa Soares, “Ludwig Feuerbach’s Critiqu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hilosophy”, Revista Portuguesa de Filosofia, T. 72, Fasc.2/3, / Perception and Concept, 2016, p. 460.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2-0023-06
作者简介:谢翾,湖南新邵人,(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642)华南农业大学讲师。
(责任编辑 巳 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