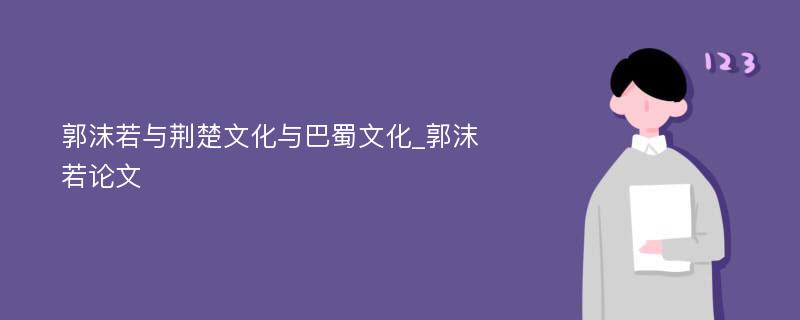
郭沫若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文化论文,巴蜀论文,荆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597(2000)04—0056—03
马克思说:人创造了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了人。人与自然、文化之间相互创造和被创造以其显在的事实表明,在一个自然文化圈内形成的某种地域文化生存形态,以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不自觉中规囿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程式,使生存于其中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具有特定价值观念的文化心理结构。作家艺术家较之一般人,其个性气质与其所在地域的民族文化背景有着更为直接深刻的联系。郭沫若的思想性格、个性气质,以及审美创造便浸润着他的故乡——南中国那块充满神奇浪漫土地的历史文化传统。
文化背景: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
中华文化是一体多元交叉发展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并孕育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源头——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包括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包括向上游的巴蜀文化、向下游的吴越文化)。中原文化以儒学标榜,儒在钟鼎,注重人与社会的协调,滋生伦理规范和内省模式;荆楚文化以道学著称,道在山林,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因而北有孔子儒学及其所编朴实无华的《诗经》,南有老庄及屈原奇幻瑰丽的《楚辞》,南北交相辉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内山川、土壤、气候、大致相同的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以至文化心态形成该地域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和塑造着这一区域的文学风格,也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郭沫若的故乡是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巴蜀。远古时蜀与楚,从文化上说是同一类型。巴蜀奇丽的山川,也酝酿了神话和巫风,在这一背景上演唱着热烈婉转的歌谣,舞踊着激情迸发的诸神,助长了巴蜀文化的浪漫主义气质。巴蜀和荆楚的交流渗透融合源远流长。秦统一天下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不仅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也在与周邻地区的文化不断地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融合中发展壮大。在这种融合中,巴蜀与荆楚,巴与楚,荆与楚及各地域文化并未失去其明显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在数千年的互相交流渗透的历史进程中,从文化上说是同一类型的巴蜀荆楚文化圈,其文化共同性仍是很鲜明的,即道文化因素和浪漫色彩。及至郭沫若诞生的年代,巴楚之地虽一定程度的儒学化了,但在山青水秀的乐山,道文化仍具有活力。
少年时代:对巴楚文化个性的感悟和认同
郭沫若青少年时代的家族文化背景和早年生活氛围、文化教育及故乡的民俗风情,给予他较多道家文化的影响。
首先,就郭沫若的家族文化背景和早年生活氛围而言,郭沫若出生在川南有“海棠香园”之称的嘉州。“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蜀地山川毓秀钟灵,峨嵋山、凌云山、高标山、沫水、若水、泯江……山连着山,水连着水。郭沫若从小就在故乡充满诗情画意的山山水水中熏陶着,传承着崇尚自然的情趣。四川“绝好的山河”曾经给历史上许多文学家以丰富的滋养;同样,峨嵋、凌云、泯江、大渡等名山大川的宏伟气魄和博大精神对于郭沫若的陶冶及其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形成,也有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郭沫若祖籍福建宁化县,其家族清朝末年入蜀,从事被儒家视为“末流”的商业。祖上“由两个麻布起家,长途贩运,逐渐殷实”,父亲“奔走于铜、雅、府三河之间,酿酒、榨油、卖鸦片烟, 兑换银钱”[1]。商业经济生产方式培养人的开拓精神和强烈个性, 郭家的商贾文化氛围也培养了他耽于幻想、追新求异、自由浪漫、奔放不羁的个性特征。
其次,从民俗文化的角度考察,侠义精神是嘉州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郭沫若称他的故乡“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郭沫若的祖父、父母不仅有游侠之风,而且还有那样不幸的遭遇和可赞的事迹。郭沫若儿时记忆深刻的不是文人学士,农夫贫妇,而是“土匪”,他对出身沙湾的大渡河土匪头领的爱乡心和义气颇有几分欣赏和佩服,这些都影响和塑造着他的豪爽叛逆的性格和游侠之风。家族血缘背景中的道文化因素与商贾文化所蕴含的耽于幻想、追新求异的特征,构成郭沫若早年生活氛围中与巴楚文化联系的内在根基,而较少纲常名教的束缚。
再次,从文化教育和思想倾向上看,郭沫若二三岁时就接受了母亲“诗教的第一课”。在“绥山馆”发蒙读书,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塾师沈先生以《千家诗》、《诗品》、《唐诗三百首》等古诗作教材,结合当地的自然景物教郭沫若读诗、对对子[2]。陶渊明、王维、李白、 孟浩然、柳宗元等著名诗人对大自然的生动描绘,给幼年沫若以莫大的兴会。郭沫若从小又接受了较多的道家文化的影响,在乐山求学期间表现出某种倜傥不羁,愤世嫉俗的道家风范。郭沫若十三、四岁时开始研读《庄子》,他不仅喜欢其汪洋姿肆的文辞,而且也迷恋过庄子的思想。同时他向往苏轼、崇拜王阳明、景仰屈原。在以风骚并重,即“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中国抒情传统的两大精神原型中,郭沫若更认同了《楚辞》缘情的秉性,对巴楚文化个性的感悟和认同,在不为主体觉察的无意渗透和诱导中,追寻巴楚文化的浪漫色彩,形成郭沫若对大自然执着的偏爱,热烈奔放的气质,狂放不羁,反抗叛逆的个性。
实践场景:创作和审美取向上的隐性传承
生长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郭沫若继承了老庄那种破坏偶像、崇拜自然、尊重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在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二级形态结构中也逐渐认同了孔子务实的品格和人文精神。东渡日本求学后,其由庄子引发的泛神论基因导引到王阳明、歌德、斯宾诺莎并改造、整合成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在一系列整合中,他身上的传统文化中的巴楚文化因子不断升华,并不断消解着传统文化的影响。
郭沫若的创作尽管受时代精神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但究其审美取向,巴楚文化的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故乡的历史文化养育了郭沫若,并内化到其人格和性格之中,隐性传承在他的创作和审美取向上。
第一,郭沫若的作品体现了崇尚自然,独抒性灵,主观外向的特点,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精神。
郭沫若少年时代就有《晨发嘉州返乡舟中赋此》等许多歌咏家乡自然山水的佳作,抒发少年沫若的浪漫心性。当他跨出家门,足迹遍及海内外时,他以诗人的卓越天赋,赞颂大自然的伟力,洋溢着追求光明与解放的热情。他早年的《怪石题群虎》、《与成仿吾同游原林园》和五四时期的《雪朝》、《日出》、《太阳礼赞》、《光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海舟中望日出》和后期的《蜀道奇》、《黄山之歌》、《金字塔》等,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在大自然面前所产生的狂喜、惊讶、感慨、思考、幻想。
郭沫若对自然的礼赞与崇尚大自然原始活力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是相通的,荆楚——巴蜀文化因子赋与郭沫若诗歌一种内在生命力。郭沫若作品中太阳、月亮等主要意象,贯穿着楚文化光明崇拜的原型,寓意深刻,它象征着青春、生命、力量,象征着自由、和谐、宁静,积淀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第二,郭沫若的作品中处处表现出大胆反抗叛逆的个性解放精神和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
《女神》中“摆脱一切羁绊”的抒情主人公,冲决一切藩篱,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并借凤凰涅磐的古老神话所创造的意象表现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和反叛。他热情赞颂古今中外一切反抗旧世界的匪徒,并向一切叛逆者连道27个“晨安”。在历史剧中,他借屈原之口呼唤风、雷、电,烧毁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这种大胆反抗的叛逆精神无不深受着楚文化代表人物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篇》)“汪洋姿肆以适己,秕糠皆可为尧舜”以及庄子的行为所表现的反权威、反偶像崇拜的思想的侵润,承传着巴蜀作家李白、苏轼等不拘礼法、张扬个性的传统,洋溢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郭沫若笔下的“偶像的破坏者”、“天狗”涌动着时代的新潮,骚动不安。他“飞奔”、“狂叫”、“燃烧”、甚至爆炸自我,吞食日、月、星辰和全宇宙的那种疯狂的自我扩张和自我实现,与屈原《离骚》、《天问》淋漓尽致表现“自我”的梦想、追求、身世、遭遇何其相似。屈原的“自我”所表现的意识不是“个体”意识,而是蕴含了极其深切的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同样,郭沫若的“自我”也不仅仅是“小我”,不仅仅是一己的个性解放,而是在强烈的“自我”情感的抒发中,蕴含了我们民族上下求索,追求光明,渴望新生的情愫。
第三,郭沫若的作品有着巨大的的气魄,奇幻的意象,充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激情。
在表现手法上,郭沫若的诗承继楚辞诗人的艺术思维方式,以诗人式的直观想象气质,在神话幻想中遨游,在历史传说中追忆,以狂幻的激情,创造出许多奇幻的意象:“涅磐的凤凰”、吞食日月的“天狗”、“棠棣之花”、不断地努力飞扬、向上的“雄壮的飞鹰”、“环天的火云”、“赤的游龙、赤的狮子、赤的鲸鱼、赤的象、 赤的犀”、 “Apollo的前驱”,还有雪朝、光海、霁月、风、雷、电等等,既颇具有时代特征和现代意识,又与楚文化奇幻的想象一脉相承;那浓烈的浪漫主义激情无疑是楚——巴文化潜质受现代文化意识的导引升华,在郭沫若作品中的显现。
第四,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对巴楚文化传统的自觉追寻。
抗战时期,他以“百史注我”的浪漫诗情创作了《屈原》等六部战国史剧,从中挖掘民族振兴的力量。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典型激励着郭沫若,他不为史实所囿,以浪漫不羁的想象“一任感情的驱使塑造人物”,设置场景。婵娟、如姬等,无不是诗化之人、情化之人,莫不“积淀和秘传”着楚文化崇尚女性的传统,承续着楚辞中“芳草美人”的象征意向,郭沫若用诗化的手法塑造的屈原更是作者全部理想的化身。屈原上下求索,虽九死而其犹未悔,把一腔的冤屈和愤恨同咆哮的风、雷、电合为一体,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第五,郭沫若的作品还有意无意间使用了巴楚民俗和方言。
《女神·新月》受蜀地儿歌《月儿走》、《月光》的启示。《凤凰涅磐》中凤凰和鸣也是从大渡河畔船夫号子得到启示,那“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则直接运用了蜀地方言。历史剧中出现的中原一带的自然民俗也留下楚文化的印痕。《棠棣之花》对濮阳民俗的渲染,是从湘楚一带“极为公开而自由”的“男女性爱生活”情景移植而来。(马茂元选注《楚辞选》)《虎符》中的“中秋赏桂”则是楚地蜀地的风习。《高渐离》中击筑伴唱,男女合声,也出自于《九歌》中的场面,而《屈原》则直接取材于楚国故都的生活,浸透着浓厚的楚地风情。
以上探究和阐释可见,郭沫若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取向与故乡历史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联系,荆楚——巴蜀文化赋与郭沫若浪漫主义的文化特质,并显现在他的创作和审美取向上。诚然,作家的文化个性,思想特质和审美取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着多方面的文化影响,特别是郭沫若这样的作家更处在一个多元复合的世界文化结构中。如果过分强调外来文化影响,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保持自身文化民族性、地域性,则有失偏颇;反之,我们也不能将传统文化的影响夸大到失当的地步,诚如黑格尔所言:“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3]这个精当的论断,毫无疑问,同样也适用于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