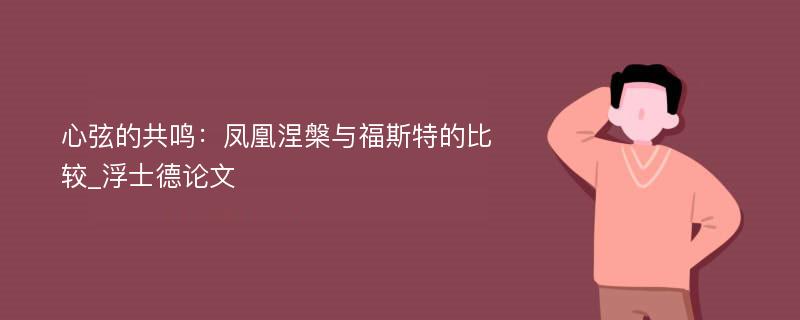
心弦的共鸣——试比较《凤凰涅槃》与《浮士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浮士德论文,凤凰论文,心弦论文,共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6月13日,周扬专程到医院去看望重病中的郭沫若,望着这位中国文坛的泰斗、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老人,周扬忍不住对他说了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1]
周扬将郭老比做中国的歌德,并非偶然。周扬清楚知道郭老的一生,深刻了解他的为人与事业。是的,郭老与歌德一样,是一位终生不懈奋斗的战士,是一位活动领域广、活动时间长,成绩卓著的文化巨人与社会活动家。而且,郭沫若与歌德,虽然国籍不同,生活的时代又相距百余年,但是,歌德的作品,早在中国五四时期,就悄然拨动了青年郭沫若的心弦,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
1914年初,22岁的郭沫若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10年的留学之旅。在日本,郭沫若学的是医科,但一直酷爱文学,尤其是诗歌,他从未忘情于吟诗作词。不过,此时的郭沫若,已不再拘泥于旧体诗词的写作,而开始了新诗的探索历程。郭沫若留日时,正是日本近代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日本作家除了创作出一大批作品外,还大量翻译介绍了欧美作家及印度作家(主要是泰戈尔)的作品,出版了一批外语原著,郭沫若由此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日本医学属德国系统,为完成学业,郭沫若除了必须具备熟练的日语外,其德语成绩也相当不错,这为他直接阅读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提供了极大方便。郭沫若接触外国作家,据他自己回忆,最先是泰戈尔,其次是海涅,再后就是惠特曼、歌德等人了[2]。这些文坛先行者们都对郭沫若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其中影响较大而历时较长的,恐怕非歌德莫属了。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启迪,更主要的还在于精神气质的沟通。
郭沫若是在1915年正式开始“认识”歌德的,并很快成为歌德的崇拜者。1919年,郭沫若着手翻译《浮士德》,1921年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后者曾是解放前再版次数最多的外国小说,在读者中引起过强烈反响。郭沫若心仪歌德,首先当然是时代原因。他曾在《〈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中写道:
“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像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进运动,同是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因为有这样的相同,所以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
其实,能引起郭沫若心弦共鸣,并不仅仅是时代的因素和类同的社会矛盾,更重要的还在于歌德的人生态度、哲学观点与郭沫若十分沟通。郭沫若曾在《〈峩默·伽亚谟百零一首〉导言中》极力称赞歌德:
“灵不偏枯,肉不凌辱,犹如一只帆船,既已解缆出航,便努力撑持到底,犹如一团星火,既已达到燃点,便尽性猛烈燎原。”
这几句话道出了郭沫若欣赏、崇敬歌德的真正原因。郭沫若赞赏歌德执着现实、关注人生、自强不息、终生奋斗的精神,这与他自己的性格与追求非常合拍,也是歌德能引起他心弦共鸣的重要原因。
郭沫若与歌德心弦的共鸣,在郭沫若翻译歌德的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郭沫若的译作,倾注了译者满腔的热忱和丰富的感情,有些段落、字句,甚至可以看作是译者本人的情感渲泄。此外,郭沫若本人的新诗创作,如著名的《凤凰涅槃》,在精神气质上就与歌德的《浮士德》有不少相通之处,充分表现了两位大诗人心意相通。应当说明的是,如果仅就两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具体内容及篇幅而论,《凤凰涅槃》当然不能与《浮士德》相提并论。《浮士德》长达12,111行,是歌德惨淡经营60年,耗费毕生心血的作品,其内容庞杂,艺术地总结了西方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叶300年间思想探索的历程,表现了歌德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辩证思想。《凤凰涅槃》仅248行,是郭沫若诗情灵感在一天内的结晶。但这并不影响《凤凰涅槃》在中国诗坛上的崇高地位,更不能否认它与《浮士德》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首先,两部作品的创作动机有其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本着对人类命运,民族出路的思考与关心而选择了民间传说作为艺术载体。歌德从小熟悉浮士德的传说,令他激动不已的,不是浮士德与魔鬼签约,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人间享受的传奇故事,而是浮士德一生永不满足的奋斗与追求。歌德认为这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民族必须具备的品格。然而,当时歌德身处的德国,“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媚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3]。歌德虽然也常对这种庸俗习气妥协、迁就,但从总体上看,他对这种卑鄙俗气深恶痛绝,渴望冲破其束缚。镕铸了歌德思想、情感、体验的浮士德形象,就是他力图为德国人树立的生活榜样。在歌德眼里,人必须像浮士德一样,“投入时代的激流”、“追逐事变的旋转”、“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4]。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郭沫若创作《凤凰涅槃》时,虽然还只是个20多岁的留学生,但五四狂飙式的爱国运动,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扉,他与不少留学生一起,组织社团,编写诗文,与国内学生运动遥相呼应。身在异国他乡,郭沫若深切地感受到作为“弱国子民”的屈辱与悲哀,因而对当时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更加痛心疾首,对造成国家分裂、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他感到5,000年的文明,“一切都已去了”[5]。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萦绕在爱国学生们脑中的严峻话题。郭沫若尽管诅咒现实,但他深信中国决不会沉沦,经过血与火洗礼而诞生的新中国,一定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基于对祖国热切的期望与坚定的信念,他选择了古老的阿拉伯传说“凤凰自焚而后生”的题材,创作了新诗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凤凰涅槃》。郭沫若明确指出,这首诗“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6],点明了他创作这首诗的本意。
郭沫若与歌德心弦的共鸣,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他对《浮士德》思想精华的深刻领会上,因此,渗透于《浮士德》中的批判精神、进取精神,在《凤凰涅槃》中也有鲜明的表现。
在五光十色的人类社会中,真善美与假恶丑常常混杂一起,而假恶丑又是人类前进的绊脚石,人类若想到达一个完美的世界,就必须批判、否定、清除一切来自外部的和存在于自身的弊端,尽管这种批判、否定的过程有时很痛苦、很艰难。在《浮士德》中,歌德就揭示了这种痛苦的批判过程。在浮士德的五次探索中,每前进一步,他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都要不断与外界的、自身的问题作斗争。浮士德所处的外部环境是黑暗的:死气沉沉、窒息生机的中世纪书斋,追求玩乐、醉生梦死的来比锡小酒店,鄙陋庸俗、保守沉闷的德国市民社会,政治腐败、危机四伏的封建朝廷,“海盗、走私、战斗”三位一体的资本主义,……总之,“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7]。浮士德生在这样的时代,其追求处处要受到制约和影响,如果他不能清醒地看到其中的危害,不批判、否定它们,甚至同流合污,他就会走向毁灭。《浮士德》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你先得把这个世界打破,另一个世界才会产生”。诗剧中的批判锋芒,不但直逼封建社会,而且还谴责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另一方面,诗剧还描写了浮士德不但要与丑恶的现实斗争,更要不断否定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摒弃自己的错误道路,不断地超越自我、战胜自我。浮士德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在我的心中啊,|盘据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之中,|以固执的官能贴紧凡尘;|一个则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先人的灵魂。
浮士德的前进道路,也是他“两种精神”不断搏斗的过程。诗剧中,浮士德先后否定了脱离实际的知识追求,否定了在“个人小世界”里的官能享受与狭隘的爱情追求,否定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妥协道路,否定了向后看,从古代艺术美中寻求改造现实丑恶的幻想。正是有了这一系列的自我否定与批判,他最终才会在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公众事业中找到人生真谛。
《凤凰涅槃》虽然篇幅短小,但诗中显示出来的批判精神却相当强烈。值得注意的是,《凤凰涅槃》显示出来的批判方向与《浮士德》相似,也是两方面的。它既批判“身外的一切”(丑恶现实),也否定“身内的一切”(自我)。在“凤歌”中,郭沫若以“天向”方式,用激越、悲怆的声调诅咒现实世界是一座“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控诉“生在这样一个阴秽的世界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他质问,如此丑恶的世界,“你到底为什么存在?”郭沫若的这些诗句,饱含着对现实的彻底否定精神。在如泣如诉的“凰歌”中,作者又勇敢地暴露了古老中华自身存在的弱点。古老中华曾经“新鲜”、“甘美”、“光华”、“欢爱”,然而,随着岁月流逝,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而今剩下的只有“悲哀”、“烦恼”、“寂寥”、“衰败”。在这些诗句里包含着中国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包含着一个作为曾是泱泱大国的子民而今面对沦落衰败的祖国而生发出的悲哀。郭沫若认识到,而今中华所拥有的,是500年的眼泪也“洗不净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焰,荡不尽的羞辱”。既然自身的活力已失,既然“死期已到”,那就毫不犹豫地“去了,去了”吧,只有如此,才能重获“新鲜”、“华美”、“净朗”、“芬芳”的新生命。在这里,郭沫若与歌德一样,表现了辩证否定的思想:没有对旧事物、旧思想的彻底否定与批判,就决不会有新事物、新思想的诞生与成长。可以说,尽管“凤歌”、“凰歌”只有短短百余行,其批判精神仍力透字里行间。
《浮士德》思想精华中最核心的是那种永不满足、不断探索、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精神。诗剧中,浮士德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魔鬼靡非斯特用尽一切手段:感官刺激、纯情少女、宫庭权力、古典美人等等,都不能使浮士德停止追求的步伐,喊一声“你真美呀,请你暂停”,这是因为浮士德深知“只要我一旦躺在逍遥榻上偷安,那我的一切便已算完”。为此,他发誓:|我要投入时代的激流!|我要追逐事变的旋转!|让苦痛与欢乐,|失败与成功,|尽量互相轮换,|只有自强不息,|才算得个堂堂男子汉。
浮士德坚信:|人要立定脚跟,向四周环顾!|这世界对于有为者并非默然无语。|他何必向那永恒之中驰骛?|凡是认识到的东西就不妨把握。|就这样把尘世光阴度过,|纵有妖魔出现,也不改变道路。|在前进中会遇到痛苦和幸福,|可是他呀!随时随刻都不满足。
歌德极为赞赏浮士德的乐观进取精神,所以,在诗剧的结尾处,当浮士德的灵魂即将为魔鬼所有时,歌德特意让天使们高唱着“不断努力进取者,吾人均能拯救之”,与魔鬼展开了争夺浮士德灵魂的战斗,并最终将浮士德的灵魂接上天庭,使其获得永生。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时,特别强调这点,他说浮士德灵魂获救的秘密就藏在这些诗句里,他说:“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帝永恒之爱的拯救。”[8]
歌德总结的历史经验至今都有启迪意义,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中的社会,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不断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社会。因此,人类的追求永无止境。
《凤凰涅槃》当然不可能像《浮士德》那样,周全详尽地展示主人公追求探索的历程。但是,洋溢于全诗的乐观进取精神仍然相当突出。凤凰不畏“群鸟”的流言、嘲笑、诬蔑、攻击,以死赴难,勇于牺牲,不是因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求得新生。果然,在熊熊的烈火中,“光明更生了”,“宇宙更生了”、“凤凰更生了”,新生的凤凰与这个新世界更加“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热诚”、“挚爱”、“欢乐”、“和谐”、“生动”、“自由”、“雄浑”、“悠久”。在“凤凰更生歌”中,郭沫若连用了15 个诗段来欢呼新生活、新中国的诞生。这些流畅、欢快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光明、对未来的执着追求、深情呼唤和坚定信念。
《凤凰涅槃》与《浮士德》都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中充满丰富的想象、强烈的感情。此外,在题材选择与艺术手段上,二者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题材上都取自于民间传说。《浮士德》取材于德国中世纪时期江湖术士浮士德的传奇故事,而《凤凰涅槃》一开篇,作者便明确交待了本诗的题材来源:“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斯’(phoenix),满五百岁后,采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
西方的浮士德与东方的凤凰,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在这两个故事中,有着一种内在联系,那就是它们都暗含着一种对生命本体的辩证认识,体现一种肯定——否定——肯定的发展规律。浮士德肉体消失了,灵魂却获得拯救;衰老的凤凰自焚了,更富生命力的鲜美异常的年轻凤凰更生了。可以说,两位作者都发掘出了原题材中最富象征意义、最有价值的部分。
对比手法,是两部作品中采用的基本艺术手段。《浮士德》中处处存在着对比,小至场景,大到人物关系。诗剧中,阴暗潮湿的书斋与阳光明媚的郊外,个人“小世界”与社会“大世界”,现实与历史,现实与神话处处形成反差。从人物关系上看,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善与恶,肯定与否定的对比;浮士德与他的学生瓦格纳,是运动与静止的对比;浮士德与玛甘泪,是不断追求与安于现状,躁动与宁静的对比;浮士德与海伦,是现实与历史的对比。就是人物自身,也时刻处在矛盾发展的对比中。在浮士德的胸中,始终进行着“两种精神”的激烈搏斗。至于魔鬼靡非斯特,本是“罪孽、毁灭等一切,简单说,这个恶字便是我的本质”,然而,又正是这个靡非斯特,成为浮士德追求“善”不可缺少的推动者,他主观上想引诱浮士德堕落,然而客观上却促进了浮士德不断克服自身弱点,不断从错误中摸索正途。所以,靡非斯特不得不承认自己“常常想的是恶而常常作的善”。歌德广泛采用对比手法,是源于他辩证的哲学思想。
《凤凰涅槃》从整体上看就是以对比手法为基础。自焚前的凤凰与更生后的凤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前者沉重、衰老,后者欢快、年轻,充满自信,体现了新旧交替,新生事物必然取代陈旧事物的趋势与规律。诗中的凤凰与群鸟也形成鲜明对比,群鸟的庸俗、自私、卑劣、目光短浅、落井下石更反衬出凤凰的崇高、伟大、光明磊落、不同凡响。
《凤凰涅槃》与《浮士德》的相通,正是郭沫若与歌德的心弦产生共鸣的结果。但是,《凤凰涅槃》并不是对《浮士德》的简单模仿,它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带有强烈的郭氏特点,是中国五四时期的必然产物。《浮士德》的创作历经60年,它凝聚着歌德的政治思想、哲学观点与审美情趣,包含着歌德对历史、现实、人生、宇宙的哲理思考,整个作品充满了思辩色彩。同时,《浮士德》的创作年代毕竟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当时的德国还处于政治分裂,经济滞后的状态,封建势力与小市民习气还颇为强大,这使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胜于英法两国。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歌德不能不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经常处在矛盾之中,这正如恩格斯所精辟评论的一样:
“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9]
《浮士德》中就鲜明表现了歌德的这种思想矛盾,歌德肯定积极的进取精神,肯定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但这些更多局限在精神探索领域,歌德甚至不像雨果,对社会革命还有高昂热情。歌德也洞悉封建社会的腐败、黑暗,渴望根除,但却反对用革命手段。他对推翻波旁王朝帝制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不但态度冷淡,甚至攻击它是一场“政治骚乱”[10]。因此,他笔下的浮士德,历经数次探索,最后是在统治者的恩赐下,才在改造大自然中找到人生的真谛与归宿。诚然,人类通过改造大自然来建造乐园的想法并无不对之处,然而,当全社会还处于严重的阶级压迫之下,当绝大多数劳动者连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的时候,改造自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可见,《浮士德》尽管是一部伟大作品,但其中社会改良成分与个人道德完善的特点是不可否认的。
反观《凤凰涅槃》,其最突出的,恐怕就是那种彻底否定旧事物、旧思想、旧我的革命精神,郭沫若不要那种渐进的社会改良,他渴望突变的革命运动,他希望尽快燃起一把熊熊大火,把旧世界烧个干净,把旧世界中的人,包括他自己也烧毁后再重塑一代新人。1920年1月18日,也就是《凤凰涅槃》创作的前两天,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就写道:
“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静的灰里生出个‘我’来。”
《凤凰涅槃》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与郭沫若所处的时代、与郭沫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息息相关。“五四”前后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是中国人民觉醒的时期。任何一个具有爱国良知的中国人,在张牙舞爪、意欲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在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军阀政府面前都别无选择,郭沫若也不例外。他没有犹豫,没有彷徨,而是高举起匕首投枪般的笔,奋力地刺向旧中国、旧世界,以迎接新中国、新世界的诞生。
注释:
[1]《悲痛的怀念》,载《人民日报》,1978年6月18日。
[2]《郭沫若诗作谈,关于〈女神〉〈星空〉》,载《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
[3]恩格斯《德国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3页。
[4]凡《浮士德》诗剧中的引文,均见董问樵译《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
[5]凡《凤凰涅槃》中的引文,均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
[6]郭沫若《创造十年》,载《沫若文集》第7卷,第64页。
[7]恩格斯《德国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3页。
[8]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44、222页。
[9]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页。
[10]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44、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