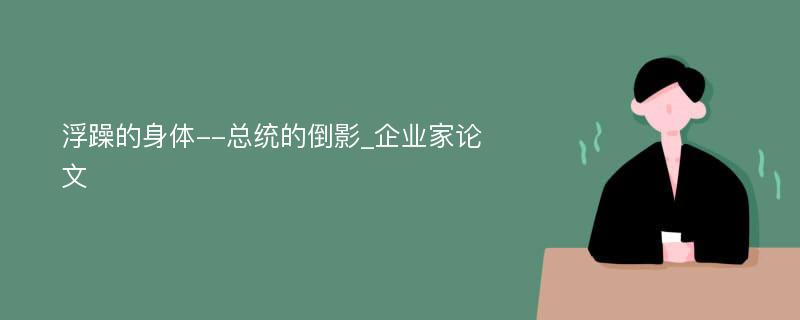
掸去身上的浮躁——总裁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浮躁论文,总裁论文,身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春夏之交,北京的书店中静悄悄地出现了一本并不华丽的书:《总裁的检讨》,但它不论在企业界,还是在学术界,均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是当年曾在国内叱咤风云的百龙矿泉壶“壶主”孙寅贵的自白;因为这是一次检讨,一次在成败的剧烈震荡后勇敢而深刻的真诚检讨,一次从哲学的高度审视自己乃至一代经营者的冷静反思;因为它记录了在我国企业界罕见的能从失败中重新崛起的历程。面对在兵败矿泉壶之后,又能连续4年在塑钢产业独占鳌头的骄人业绩,孙寅贵的体会经营者不可不读,不可不想。
想一想管理者该干什么?
“什么是管理?管理者该干什么”?孙寅贵在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我们很多经理、厂长可能从来就没有深想过的问题。
他在一次对下属的批评当中指出:“真正的管理者,他的职责应该是研究政策、建立制度。一个劳动模范式的管理者决不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
其实,“事必躬亲”和“以身作则”是两回事,“管理者”并不应成为“拼命三郎”,而真正的“则”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想清楚。典型的案例在《三国演义》中就有,诸葛亮绝顶聪明,却为什么六出祁山一无所获反命丧五丈原,而屡战屡败的司马懿却为什么笑到了最后?因为司马懿抓住了管理的真谛:管理者最需要的并不是自己去拼杀,而是建立起井然有序、行之有效的制度,让它自己顺畅地运转。而连军士的灶坑如何去挖都要过问的诸葛亮则在“事必躬亲”中拖垮了自己、耽误了事业。他死之后,流尽了泪水的蜀军上下忽然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工作都不会,因为自己以前从没机会去做,丞相全包了。没有制度,光靠聪明与激情,是害己更害人的。
所以,孙寅贵在轻松中不乏中肯地谈道:“越是上层,弄明白自己到底该干什么就越是重要。我觉得如果一个热爱自己企业的老板能使自己轻松起来,乃至有些无事可做,那这个企业倒会很有希望”。
百龙精神:在“如果缺了我……”中实现自我
孙寅贵指出:“光靠制度也不行,制度有它管不到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管理就需要信仰。具体到我,就是要塑造好百龙的精神、百龙的企业文化”。
百龙的文化是“强调自我的文化”。孙寅贵有一个很生动的阐释:“我鼓励所有员工都来‘叫板’,在共同的‘叫板’中求得相对公平的价值。百龙有一个理念就是:‘争做缺不了的能人’,大家都要问一个:‘如果缺了我……’。如果企业缺了你将蒙受损失,你就可以得到和损失相称的回报;如果缺了你会蒙受重大损失,当然就会得到与重大损失相应的回报;如果缺了你企业会完蛋,那你就坐到我董事长的位子上来,我乖乖坐到一边去,因为企业没了,我连一边都坐不到。相反,如果缺了你无所谓,甚至变得更好,那你就赶紧另谋发展吧。这样命运与回报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只会担心跟不上企业的需要”。
将人的价值与缺少之后的损失相联系是颇有道理的,不要总自以为是地叫喊:“缺了谁都一样”,因为往往在失去之后,原先存在的事物对于我们的价值才会得以显现或被我们感悟。好的制度和文化,应该使个人的价值与企业的发展成为统一、互动的关系。然而我们以前却总是抓住农民头脑中的“大饼意识”不放,好像集体就是个大饼,一提个人价值就是在分大饼,是在分割集体利益,总是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其实当我们无节制地要求和赞美“奉献”、抹杀个人的价值和合理的回报时,孙寅贵指出:“这恰恰有一个大的缺陷:它破坏了社会应有的秩序,破坏了价值规律,滋生了大批的懒人。所以百龙追求的是公平的价值,而不是单一‘奉献’。”
真正维系职工与企业的,不是感情,而是彼此的需要
百龙的另一文化特征就是崇尚“理性”。百龙要建立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信仰。孙寅贵认为:“企业与员工之间就是一种技术关系,是人与企业之间彼此需要,从而构成了一种稳定的关系,不存在谁感激谁,也不是单纯的感情,而是事业在维系着感情。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饭碗都在这个企业里,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饭碗一样爱护我们的企业”。在多年前,就有人提倡“感情投资”,孙寅贵坚决反对:“投资是什么?投资是要有回报的,那么‘感情投资’的本质不就是‘用感情来换钱’吗?这种‘感情’是装给别人看的,并不是发自内心的需要,这不是‘愚民’又是什么?这是在玷污‘感情’这两个字。从文化上讲,我们欢迎职工对企业进行‘感情投入’,而不是‘投资’,我明确对职工说:‘投入’是不讲回报的”。
看透我们的浮躁,溯清根源,然后果敢地掸掉
“掸去身上的浮躁,擦去脸上的伪善,抹去内心的狂傲,静静地寻求这一切的根源”。这是孙寅贵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也是我们企业界急需要做而很多人并没有做甚至没有意识到要做的根本大事。
对于“浮躁”,这个代表了我们一代民营企业经营者的总体特征,孙寅贵以自身的渗痛教训体会得太深了:“总过分地依赖机会和‘点子’去谋求发展,依赖感情去管理企业,依赖小聪明去应付危机,然后又固执地一错再错”。
是机会?还是事业?
我们那么多很好的产品乃至企业为什么都那么短命?孙寅贵认为:“完全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把它当成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事业来做”。是的,在浮躁的心态下,企业文化、产品创新、人才战略等一切本应成为内在根本的东西在我们手中已完全成了对外欺骗的装点、吹嘘炒作的手段,脚踏实地变成了哗众取宠,而在“本末倒置”之下又焉会有“长命百岁”之理?
是撕杀?还是建设?
此外,过于热衷于用打仗的思路去指导我们办企业也是浮躁的表现。包括百龙在内的不少民营企业,过去都曾慷慨激昂地把“××战役”作为开拓市场的口号,于是“××大战”也频频见诸报端,而史玉柱甚至在企业内建立了“八大军区”。然而“战争思维”注定就是“短视”的,因为将军在乎的永远是近期的战果,他不会考虑战争带来的长远影响;“战争思维”追求的就是“你死我活”,它既无法理解“竞争中的合作”,也不会明白要“培育共同的市场”。战争是毁灭,经商是创造。虽然历史上战争与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用战争的思路去指导和平中的行为肯定是走不通的。孙寅贵在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反思后,提出了“建设”的思路:“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企业”?那么“浮躁”的根源又在哪里?
孙寅贵认为:胆量+诱惑+机会=浮躁“一举成名”之后就是“昙花一现”
“一个时代造就了一批具有共同时代特征的人。第一批民营企业业主的前身就是个体户,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和对世界理解的深度都非常有限,他们的素质所拥有的就仅仅是勇气和胆量;而像比尔·盖茨这样一代成名的样板又在不停地诱导他们;同时,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社会的市场空缺又相当的大,带来的机会又相当的多,使得一举成名、一夜暴富成为可能;这种时候,必然会产生浮躁。
“而结局也是必然的,那就是‘昙花一现’。因为今天的市场已不是昨天的市场,今天的消费者已不是昨天的消费者,今天的媒体也不是昨天的媒体,只有自己,还是昨天的自己,这必然就要完蛋”。
浮躁的路可能很宽,但它却是非常短的死路
孙寅贵接着谈道:“应该说这批人的素质限制了自己很难再提高,同时他们又在自我腐蚀。
“在立竿见影的炒作声中,你面前的路确实显得很宽,但如果你以为‘糖+水+广告=利润’就是直通罗马的阳光大道而一路冲杀过去,你会发现路突然断了,想再回头,回路也没了,完了。百龙矿泉壶就是走上了一条死路。本来矿泉壶可以补钙,治失眠,是个好产品,可说过了头就坏了:有的厂家子虚乌有地说他的壶还能治癌,眼看消费者都去治癌了,你又得说我的壶可以长寿兼美容,后天又有人说他的壶连艾滋病都治!自吹自擂吹不动了,就开始互相揭短。到最后消费者由‘不知信谁’变成了‘谁也不信’,整个产业也就完了。当时是重视眼前忽视长远,重视宣传忽视建设,将市场竞争发展成了恶性商战。可以说矿泉壶大战的各方都缺少市场大局观念,都忽略了市场的脆弱性而不惜以重创既有市场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局部利益,结果在‘打破’对手时,也‘打破’了市场和市场中的自己”。
最重要的是选好你下一级领导,然后施之以鹭鸶政策和目标管理
折戟矿泉壶后,孙寅贵现在掌管着十几个下级企业,并且在国内塑钢产业居遥遥领先的地位。他认为“管理企业,第一靠领导人,第二靠领导人,第三还是靠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该有理想、有道德。在我认真地检讨自己如何做人后,我觉得总经理除了要懂专业、有经验、会管理之外,又加了很重要的一条:‘人品好’。
“选好后,如果经过考核他胜任这个位子,接着就要实行鹭鸶政策。你要从他创造的利润中给他适当的提成,但过高的待遇会导致短期行为。百龙的待遇不算很高,但目前并未发生人才流失,就在于人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还有精神、自我实现和社会地位。熟悉而又得心应手的工作环境同样会吸引住人才。
“在你与他之间还要形成一种制度。在我组建‘青岛百龙’时,赋予了它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的体制:不从百龙现有企业调派一兵一卒,以目标式管理体系体现双方关系,由董事会制定年度任务,以量化形式明确总经理的职责目标,尤其是持续发展阶梯目标。实际就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我对青岛百龙的总经理宋桂忠说:‘我只管你一个人’。而总经理只管副总和要害部门的正职干部,同样以责任目标和量化指标作为考评标准”。
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策的企业有的是,可我们不少“浴血奋战”惯了的主管并不能真正做到。大权旁落带来的失落和对下属出错的愤怒使得他们在“放了收,收了又放”的怪圈中转个不停、精疲力尽。对此,孙寅贵自有说法:“人要耐得住寂寞才算得上成熟,因为只有在寂寞中才能冷静,在寂寞中才能清醒地看明周围的一切。特别是管理大企业,如果不能跨越这一步,就很难再提高”。
真正彻底地去执行既定的制度
让孙寅贵感到庆幸的是,这些以前可能只是说给别人听到,现在他能以认真的态度做到了。确实,我们中国人并不缺智慧和谋划的能力,缺的是执行到底的决心和韧劲;而执行不力在于我们“不认真、不细致”。钱钟书先生曾讥讽我们中国万事总是“制定得严”,而“解释得宽”,只是“富于弹性的坚定”而已。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痼疾。
绰绰有余的“小聪明”,使我们总想“投机取巧”、“一劳永逸”,而我们却总是缺少“持之以恒”、“返朴归真”的“大智慧”。每当我们讲“灵活”时,总能找出各种理由并大叫“下不为例”,同时嘲笑“照章办事”为“教条”。殊不知,让这一次次的小小的“灵活”积习成性的结局便是:我们经常处于“无原则”的状态,实在令人汗颜。就“认真”这方面,日本企业远比我们要强,而且似乎只是这方面比我们强,但却带来了天壤之别。
用“不信任”来确立“制度意识”
百龙及其它企业的大量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决不能“因‘信任’而放弃‘制度’”。“信任”是不稳定的,而“制度”是长久的。我们过去总将制度作为“权宜之计”,作为出现问题后的解决办法,而没有看到制度的确立与执行正是为了避免问题的发生,因而经常出现制度随问题表现的强弱而存亡的奇怪现象。因此,反思之后的孙寅贵主张要有意识地制造“不信任”以让下属习惯于制度的存在与制约。
以真正的企业家的标准来衡量下级
“什么人才算是真正的企业家”?一度也曾飘飘然的百龙总裁冷静地问道,“真正的企业家,应是能够领导企业走上持续发展,并在行业及区域内使企业具有相当影响的人”。显然就此看来,我们现在的企业主管恐怕没有几个配享受“企业家”这个称号的。孙寅贵的想法是以企业家的标准来衡量下属,使百龙成为培养企业家的摇篮。
“我们为明天和后天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影响我们今天的利益。如果你过多地考查他今天的业绩,他可能就会忽略或不得不放弃明天的利益。所以我们不能仅仅考查下属的今天,还要考查他为企业明天的利益所做的贡献和铺垫”。
我愿意以巨大的代价来换取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
孙寅贵谈到了他与其他老板很不同的一点:“百龙的人都知道他们可以不听我的,可以和我争执。为了使下属获得认识上的提高,我可以不在乎我的尊严。我为了教育一个有前途的人,有时会牺牲很大的代价,用很痛苦的教训来博得他思想意识上的转变。所以要培养真正过硬的企业家,决不是送去读读什么MBA那么容易的,‘学费’是相当高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曾经投资5500万去做电池,颗粒无收。也就是说,要培养出我这样一个人、我现在这样的心态和认识,‘学费’可能要上亿!“所以说他们为什么不走,就在于我给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的机会,在我‘看到’的情况下,我仍允许他们交一二百万的‘学费’”。
这些话实在震撼人心。孙寅贵的气魄确实令人佩服,比起当年百龙以人才招聘为幌子进行宣传“造势”,如今的他对“人才”的理解显然已真诚、深刻得多。同时,我们也真正体会到了“人才的价值”到底有多高!得来实在不易。真正的企业家决不仅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在多年的实践中经历了无数坎坷、无数摔打“炼”出来的。企业家是我们社会一笔巨大的财富,当他们终于可以用自己毕生心血换来的能力为社会作出贡献、为社会的明天积累经验时,我们应当尊敬他们,爱护他们。
在销售上,我不做压指标的蠢事
孙寅贵在销售管理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百龙规定:销售部门以完成头一年销量的85%作为下一年的销售指标。对这一似乎不合常理的措施,孙寅贵谈道:“我们社会中存在一个问题:有不少部门除了自己不努力寻找客户外,还把客户往外推。为什么呢?就是怕上面层层加码。这样我累死也没个头,也落不着好,索性自己留有余地。可这样,积极性又从何而来呢?既耽误自己也耽误企业。我们中国总喜欢以指标压人,总一厢情愿地以为指标一压就出来了,实际这很蠢。这将导致两个后果:底下或是一开始就直接对抗,或是造假蒙你。业绩应是诱导出来的,而不是压出来的。
走“多元化”是不合算的,我会慎之又慎
孙寅贵以前也尝试过“多元化”,但自己也承认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资金,乃至是百龙最大的浪费。而近年来,国内企业盛行“多元化”,但多半是乘兴杀去,败兴逃回,甚至从此垮掉。对此,孙寅贵认为原由是他们对“多元化”不求甚解。
“‘多元化’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世界上最大的企业GE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它的成功在于它每决定进入一个行业就要确立一个前提:你能保证进入该行业的前三名,否则就不干。
我们有的企业在一个行业还没干好,就想分散它在第一个行业的风险,其实它在原行业继续发展的优势比开辟第二战场的优势更大,成就更大。结果我们产生误解,最后风险没分散,精力财力倒分散了,哪个也没弄好。而我们,光‘青岛百龙’就已经连续4年在塑钢行业产销量居全国第一。可当了4年‘老大’,我都没想过我可以走第二个行业,以后也轻易不走。做自己最熟悉的事情是最容易出成效的,而贸然走‘多元化’是件不合算的事”。
中国的血缘文化将很难造就成功的家族企业
在西方,家族企业是很常见的企业形式,也不乏发展成跨国大公司的,而百龙从来就不是家族企业,但孙寅贵还是通过自身的经历看到了笼罩在中国家族企业头上的阴云。
孙寅贵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同样的企业形式的前景却完全不同,西方的亲情是松散的,乃至是短暂的,而我们中国这种紧密的血缘亲情关系是不可能用制度来代替的。你永远不会看到他们之间有制度。因为制度,就意味着彼此的不信任;而人情的价值恰恰就是信任,当信任没有时,一切也就都没有了。没有制度,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对资本对分工对贡献都没有明确的认定与衡量,所以我们的企业不容易搞大,反而容易走向分裂。
“相比之下,由血缘维系的特殊关系更需要加以约束,尤其是当他们面临诱惑的时候”。孙寅贵语重心长地说。
没有“股份制”照样可以成功
对于“股份制”,孙寅贵明确表示没有这个打算。他认为我们应从哲学的角度去看,世上万物都是“双刃剑”,“股份制”也有利有弊,不是一“股”就灵。而世界上很成功发大财而不搞“股份制”的企业也有,所以它不是唯一的路。况且,“股份制”有一个问题,正如《编辑部的故事》中李冬宝所言:“你说没民主吧,没我们说话的份;有了民主吧,又谁都不服谁”。事实上,因为“股份制”而毁掉一个企业的例子也有。
标签:企业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