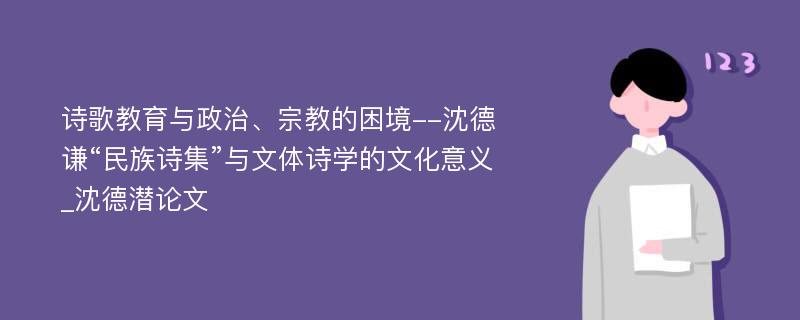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政教论文,格调论文,意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0)05-0082-06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而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这一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沈德潜之遭遇,表明了诗教与政教的微妙关系,在乾隆时期具有典型意义。沈德潜先后参加十余次乡试,都以失败告终。直至乾隆三年,66岁的沈德潜方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沈德潜在庶吉士散馆考试考场上见到了前来巡视的乾隆帝,乾隆帝称沈德潜为“江南老名士”。三日后,沈德潜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了与乾隆帝的诗歌唱和。直至退休之后,乾隆帝对沈德潜仍恩遇有加。沈德潜作为文人所受之旷世恩典,作为盛世文治精神之象征,受到当时文人的艳羡。[1](卷3)然而当退休后的沈德潜将自己所编选《国朝诗别裁集》呈献给乾隆帝,请乾隆帝为之作序时,一切顿然改变。乾隆帝不仅在删改重刻的《钦定国朝诗别裁集》序言中对沈德潜加以训斥,甚至在沈德潜去世后下令追夺其阶衔,罢祠削谥,平毁墓碑。据乾隆帝在《钦定国朝诗别裁集》的序言中所说,其对沈德潜之痛恨,是因为沈德潜违背了其素昔所主张的诗教。实际上,乾隆帝和沈德潜之矛盾在于诗教和政教之矛盾。沈德潜坚信其所编选的诗集,所张扬的“格调”,所倡导的“雅正”审美理想,皆为对风雅诗教的最好阐释。沈德潜欲超越政治而谈诗,然文学终无法脱离政治,诗教实与政教紧密关联。沈德潜诗学中潜在之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亦正是此矛盾引起乾隆帝之怒。
一、“因诗存人”:《国朝诗别裁集》的编选原则与沈德潜对诗教之理解
正如乾隆帝所云,其与沈德潜之交往,“以诗始,以诗终”。沈德潜于乾隆十年开始编选《国朝诗别裁集》,乾隆二十三年完成,乾隆二十四年刊刻,共收九百九十三人诗四千九十九首,凡三十六卷。乾隆二十五年又加增删,前后历时达十六年之久。修订后的《国朝诗别裁集》于乾隆二十六年刊刻。乾隆二十六年十月,沈德潜至京城为太后祝寿,将《国朝诗别裁集》献于乾隆帝。乾隆帝阅后,指出选钱谦益、钱名世之诗,称慎郡王之名等几处失误,下令南书房删改重刻。[2](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南书房删改重刻本即《钦定国朝诗别裁集》,18名“贰臣”诗人和屈大均之诗篇全被删除,前附《御制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序》云:“沈德潜选国朝人诗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潜老矣,且以诗文受特达之知,所请宜无不允。因进其书而粗观之,列前茅者则钱谦益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问,既求朕序,则千秋之公论系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存焉。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昧缔构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在德潜则尤不可。且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义。今所选,非其素昔言诗之道也。岂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门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无达大义具巨眼人捉刀所为,德潜不及细检乎?此书出,则德潜一生读书之名坏,朕方为德潜惜之,何能阿所好而为之序!又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选,而慎郡王则朕之叔父也,虽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国家典制,平时朕尚不忍名之,德潜本朝臣子,岂宜直书其名?至于世次前后倒置者,益不可枚举。因命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俾重锓版以行于世,所以栽培成就德潜也。所以终从德潜之请而为之序也。乾隆二十有六年岁在仲冬月御笔。”[3]
乾隆所列沈德潜编选之失误中,最为突出的是钱谦益、钱名世的入选。钱名世在雍正朝即被定为所谓的名教罪人,而引乾隆之关注者尤为钱谦益。乾隆在三十四年所发敕谕中称钱谦益为“有才无行之人”,下令将其所作之《初学集》、《有学集》一律禁毁。[4](836)在敕谕中乾隆特别提到了沈德潜:“若沈德潜,向曾以钱谦益诗,选列《国朝诗别裁集》首,经朕于序文内申明大义,令其撤去。但既谬加奖许,必于钱谦益之诗,多所珍惜。或其门人弟子狃于锢习,尚欲奉为瓣香,妄以沈德潜齿宿爵尊,谓可隐为庇护,怂恿存留,亦未可定。果尔,岂沈德潜不知恩重,不复望朕为之庆百岁耶?”[4](卷84)乾隆所谓“谬加奖许”指沈德潜将钱谦益列为卷首,选其诗32首,数量上仅次于王渔洋,沈德潜在小传中评云:“尚书天资过人,学殖鸿博。论诗称扬乐天、东坡、放翁诸公。而明代如李、何、王、李,概挥斥之,余如二袁、钟、谭,在不足比数之列。一时帖耳推服,百年以后,流风余韵,犹足詟人也。生平著述,大约轻经籍而重内典,弃正史而取稗官,金银铜铁,不妨合为一炉。至六十以后,颓然自放矣。向尊之者,几谓上掩古人;而近日薄之者,又谓澌灭唐风,贬之太甚,均非公论。”[5](P1)对于钱谦益之诗,乾隆以为有违世道人心,而沈德潜则评云:“兹录其推激气节,感慨兴亡,多有关风教者,余靡曼噍杀之音略焉。见《初学》、《有学》二集中,有焯然可传者也。”[5](P1)除钱谦益外,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所收身仕两朝、大节有亏之诗人还有吴伟业、龚鼎孳等。沈德潜评吴伟业云:“故国之思,时时流露。《遣闷》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不意而今至于此。’读者每哀其志。”[5](P17)沈德潜又将因悖逆而在雍正朝被戮尸袅示的遗民诗人屈大均之诗选入,且评云:“翁山天分绝人,而又奔走塞垣,交结宇内奇士,故发而为诗,随所感触,自有不可一世之概,欲觅一磊落怪伟之人对之,艺林诸公竟罕其匹。”[5](P299)
沈德潜之所以将这些被朝廷贬斥的诗人收入诗选且置于前列,并非故意违背朝廷之意旨,也并非如乾隆所指斥的违背了素昔所主张的诗教,在沈德潜看来,这些所谓的“贰臣”特别是遗民诗人的家国之思、身世感慨,正是温柔敦厚诗教之体现,恰可教时人忠孝之理,于太平之世,对满清统治之巩固有利而无害。而乾隆对汉文人之芥蒂,其对儒家诗教理解之肤浅,使他对沈德潜之所为殊为不解而大为恼怒,终于酿成一实际上之文字狱。
沈德潜之所以如此编选,还因为他想超越社会政治而专论诗。在《明诗别裁集》的序言中,沈德潜提出“因诗存人,不因人存诗”[6]。在《国朝诗别裁集》的凡例中,沈德潜论选诗之原则云:“国朝选本诗,或尊重名位,或藉为交游结纳,不专论诗也。陈检讨《筐衍集》,较诸本为善,然只及康熙癸丑,以下闭如。兹补癸丑后八十余年诗,而名位、交游之念,不扰于中,此差可自信者。”[7]不以人存诗,自然也就不因人而废诗,沈德潜引以自豪的正是《国朝诗别裁集》不涉政治,为一纯粹的诗选,之所以将满清宗室成员之诗置于卷三十而非首卷,之所以称乾隆帝叔父慎君王之名允禧,亦本此编纂之原则。沈德潜本以为乾隆自命风雅,而又与其有诗文唱和,乾隆当对其所选诗赞赏有加,而实则乾隆写诗作文本为政事之余事,于关键之时,当然首先注意于政治。沈德潜之遭遇,为文学附丽于政治的另一种解读。《国朝诗别裁集》事发后,乾隆帝下令查禁钱谦益之诗集,谕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密查沈德潜是否收藏有《初学集》《有学集》。在沈德潜死后九年,乾隆得知沈德潜为一柱楼诗案之主犯徐述夔作传,勃然大怒,下令追夺其阶衔,罢祠削谥,平毁墓碑。
二、“性情”与“忠孝”:沈德潜的格调说对温柔敦厚诗教的阐释
乾隆帝指斥沈德潜选诗违背了“素昔言诗之道”。所谓“素昔言诗之道”即指此前沈德潜反复阐扬的温柔敦厚之诗教。沈德潜中进士第前,编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著有《说诗晬语》,其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忠君爱国被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康熙五十六年,沈德潜为编选的《唐诗别裁集》作序云:“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8]而所谓本原指兴观群怨,指事父事君。完成于康熙五十八年的《古诗源》序文中称此选“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9]。完成于雍正九年的《说诗晬语》开篇第一条即标明论诗之主旨:“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10]《国朝诗别裁集》之凡例第一句亦云:“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7]其于《答竹溪诸诗人》中云:“诗教阅古今,温厚归一般。诗何尝愚人,诗人自愚耳。”这正是德潜和归愚的命意所在。沈德潜将“温柔敦厚”之诗教作为“仰溯《风》《雅》”以尊诗道之要义。其《说诗晬语》之开首云:“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10]其选编诗集,一以“温柔敦厚”为宗旨,如其于《唐诗别裁集》中评骆宾王之《帝京篇》“非诗之正声”,因其没有按照诗教之要求“敷陈主德”,而对于一己之湮滞表示了过分的哀伤。[8](卷5)而《离骚》之所以被尊为“《诗》之苗裔”,亦因为《离骚》虽“有诧傺噫郁之音,无和平广大之响”,但其思想之内核,仍为忠君忧国。其诗歌创作,虽有对现实之揭示,如《刈麦行》《汉将行》《制府来》《挽船夫》等等,但其宗旨正如唐朝新乐府运动,为补救时弊而作,基本上贯彻了“主文而谲谏”之诗教。
所以沈德潜所张扬之格调,与明朝前后七子之“格调”名同而实异。格调之说,始于明代,前后七子主张在格律声调上摹仿盛唐诗歌,李东阳于《怀麓堂诗话》中解释说.“眼主格,耳主声”,“格”指“格律”,“调”则指“声调”,皆指外在之形式。[11]沈德潜之格调说显然受明代七子之启发,他认为诗之“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诗歌的意蕴风格可以通过格律声调体现出来。但与明代七子的“格调”比起来,沈德潜的格调说对诗之内在作了强调,如果没有内在的性情之表达,仅仅是格律声调的摹仿不可能形成有格调之诗,而性情之表达则要以“温柔敦厚”为极则。沈德潜以对古诗格调的摹仿作为入门之要诀,将不学古之诗称为野体,这一点与明代前后七子同;沈德潜推尊盛唐,将盛唐之诗作为学习之样本,亦与明代前后七子同。他主张拟古而通变,积久用力,充养既久,变化自生,方可换却凡骨,明代前后七子亦作过类似的表述。但与明代前后七子不同的是,沈德潜强调经由盛唐而仰溯《风》、《雅》:“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衎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10](P186)其批评前后七子之失云:“有明之初,承宋、元遗习,自李献吉以唐诗振天下,靡然从风,前后七子互相羽翼,彬彬称盛。然其敝也,株守太过,冠裳土偶,学者咎之。由乎守唐而不能上穷其源,故分门立户,得从而为之辞。”[9](《古诗源序》)其评宗唐之风云:“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今夫观水者,至观海止矣,然由海而溯之,近于海为九河,其上为洚水、为孟津,又其上由积石以至昆仑之源。《记》曰:‘祭川者先河后海。’重其源也。唐以前之诗,昆仑以降之水也。汉京魏氏,去风雅未远,无异辞矣。即齐、梁之绮缛,陈、隋之轻艳,风标品格未必不逊于唐,然缘此遂谓非唐诗所由出,将四海之水,非孟津以下所由注,有是理哉?”[9](《古诗源序》)
沈德潜所倡导的格调理论,虽然在其诗论著作《说诗晬语》中有所论述,但更主要的是通过其所编选的诗文总集体现出来。其43至45岁期间(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六年)即编辑了二十卷本的《唐诗别裁集》,选录诗歌1920余首;47岁时(康熙五十八年)又编选了《古诗源》十四卷,收录唐前古诗700余首。乾隆四年,67岁的沈德潜和友人一起编选了十二卷本的《明诗别裁集》,收录明朝诗歌1010余首。乾隆十二年,75岁的沈德潜选评杜甫诗歌为《杜诗偶评》,不久又与友人一起编辑了三十卷本的《唐宋八大家古文》。到乾隆二十五年,88岁的沈德潜编辑完成《清诗别裁集》三十二卷,收录清前期诗歌3952首,至此沈德潜完成了上自远古下至其所生活的清朝的诗歌编选的系统工程,亦以诗为史,完成了重建诗统的努力。
虽然乾隆在其为《清诗别裁集》所作的措辞严厉的序言中对沈德潜没能遵照其所宣扬的宗旨,但沈德潜坚信其所编选的诗集,为其诗歌思想之最好的体现。其倡导回归风雅之目的,主要为在诗道渐趋沉沦的时代,再一次将政教与诗歌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提高诗之地位。其于《说诗晬语》之开篇即云:“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诗道沦落之主要原因,正在于对诗教的放弃:“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月,弄花草,游历燕轩之具,而诗教远矣。”[10]其编选《古诗源》,是为古体诗之创作提供范本,“汉京魏氏,去风雅未远”,学习古诗应以汉魏为宗。至于近体诗,则应该以盛唐为宗,盛唐诗歌在汉魏基础上加以通变,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明清诗歌经由汉唐回归风雅。至于宋元之诗,既无体制之创新,又流于卑靡,偏离温柔敦厚之精神,这也是沈德潜独独不选宋元之诗,而以明诗续唐诗之原因。其对唐诗之推崇,与其以格调说为核心的诗歌理论有关,亦受早年学诗经历之影响,其自称“于束发后,即喜抄唐人诗集”[8](《唐诗别裁集序》),但更主要的是其有意识的选择。于顺治、康熙之际竞尚宋诗的时代,沈德潜高举唐诗之旗帜,直至晚年其编选《清诗别裁集》时仍然坚持认为:“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愚未尝贬斥宋诗,而趋向旧在唐诗。故所选风调音节,俱近唐贤,从所尚也。”[5](《凡例》)
沈德潜之所以推尊盛唐之诗,是因为盛唐之诗既格力雄壮,又气象雄浑,符合他的审美标准。而杜甫之诗正体现出沉雄浑厚之风格。沈德潜认为,杜甫以其才气和笔力之塑造阔大之意象,形成笼盖宇宙之气势,从而产生感人之力量。乾隆十二年,沈德潜编成《杜诗偶评》四卷,他在《序》中称:“录诗三百余篇,皆聚精会神,可续《风》、《雅》者。”成于《杜诗偶评》后16年的《唐诗别裁集》二十卷,所选诗亦以杜诗为最多,共计231首,比李白之诗多130余首。沈德潜于《唐诗别裁集凡例》中说:“是集以李杜为宗,玄圃夜光,五湖原泉,汇集卷内,别于诸家选本。”书以“别裁”为名,即出自杜甫之句“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沈德潜表明《唐诗别裁集》之编选是为补王士禛《唐贤三昧集》之偏:“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咸酸外矣。而于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韩语意定《唐诗别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12]成于雍正九年的《说诗晬语》论《诗经》到明清时诗歌226条中,论及杜甫之诗者即达44条。
沈德潜将杜甫之诗视为他所倡导的格调之诗的典范。诗之宗旨须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而杜甫之诗为国爱君,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契,“生平种种抱负,无不流露于楮墨中”[12](《凡例》)。“圣人言诗自兴观群怨,归本于事父事君。少陵身际乱离,负薪拾橡,而忠爱之意惓惓不忘,得圣人之旨矣。”[8](卷2)这正是杜诗之深厚处,沈德潜甚至将杜甫之诗比作周公之礼乐,“后世莫能拟议”[8](卷2)。杜甫身际困穷而心忧天下,致君尧舜,再淳风俗之志至死不改,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才识,所以才有第一等真诗。
沈德潜显然对杜甫诗中的忠君爱国之旨作了过多的强调。《唐诗别裁集》评杜甫:“一饭未尝忘君,其忠孝与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可以寻常诗人例之。”[8](卷6)之所以如此,或与其身份地位有关,乾隆对他恩遇有加,而乾隆帝倡温柔敦厚之诗教,沈德潜当然理解乾隆所谓温柔敦厚之指向。忠君爱国之情可发露无隐,而感时伤世之情则须含蓄婉转,沈德潜评杜甫之《新婚别》云:“与‘东山’、‘零雨’之诗并读,时之盛衰可知矣。‘君今往死地’以下,层层转换,皆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国风之旨。”[13](卷1)即使是讽刺之诗,只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旨,只要有补世道人心,亦合乎温柔敦厚之旨:“《巷伯》恶恶,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尝留一余地?然想其用意,正欲激发其羞恶之本心,使之同归于善,则仍是温柔和平之旨也。”[10](卷上)
沈德潜承认性情为温柔敦厚之内核,有了性情,即使是议论亦可成诗:“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伦父面目耳。”[10](卷下)“诗之真者在性情”,[14](《归愚文钞余集》卷3《南园唱和诗序》)有不得不言之隐,发抒为文字,方有真诗:“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隐,借有韵语以传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远嫁’,或慷慨吐臆,或沉结含凄,长歌短言,俱成绝调。若胸无感触,漫尔抒词,纵辨风华,枵然无有。”[10](卷上)杜甫诗之沉雄浑厚,即源于其情感之深挚。
三、“雅正”:沈德潜的审美理想及其对王士祯神韵诗学的补充
沈德潜之审美理想曰“雅正”,曰“中正和平”,而达“雅正”之途径,曰审宗旨、观体裁、讽音节、辨神韵,沈德潜于《唐诗别裁集序》中云:“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8]于《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云:“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于《七子诗选序》中云:“子惟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揽其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14](《归愚文钞余集》卷2《七子诗选序》)沈德潜所强调的诗歌宗旨,即儒家诗教所强调的性情,他反复强调:“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诗必原本性情。”“诗贵性情。”[10](卷上)
无论是温柔敦厚还是沉雄浑厚,皆须体现于文字,都要落实于体裁和章法,此亦为其强调“观体裁”、“讽音节”之原因。其论诗法云:“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不同体裁有不同的作法,如其论七言律诗云:“贵属对稳,贵遣事切,贵捶字老,贵结响高,而总归于血脉动荡,首尾浑成。后人只于全篇中争一联警拔,取青妃白,有句无章,所以去古日远。”[10](卷上)明代七子和沈德潜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杜甫之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杜甫之诗有法可循。杜诗之章法音律自然与其内涵紧密融合,而后代诗人即使无法达到杜诗之深广,然如摹得其格调,亦不失为诗。如沈德潜总结杜甫五言古诗之章法云:“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10](卷上)在具体的起承转合处,更可看出杜甫诗法之精妙:“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姪王冰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某人,而下倒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墉。’此其法也。《丽人行》篇中‘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10](卷上)
至于“辨神韵”,显然受王士祯神韵诗学之启发。和王渔洋一样,沈德潜对唐代司空图所描述的“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与道俱往,著手成春”的自然之境甚为欣赏,他认为明代前后七子复古之失即在于陈陈相因而失自然之趣。自然为诗之极则,自然方有神韵。沈德潜认为,性情、气骨、才思三者具备而归于自然,发而为诗,自然“或如巨壑崇岩,龙虎变化;或如寒潭削壁,冰雪峥嵘。”性情为诗之本原,而气骨表现为风格,才思流为神韵:“风格者,本乎气骨者也;神韵者,流于才思之余、虚与委蛇而莫寻其迹者也。”[14](《归愚文钞余集》卷2《七子诗选序》)
然沈德潜所云之神韵,又与王士祯之神韵说有所不同,而与温柔敦厚之诗教相通,与儒家诗学之比兴说又紧密相关。神韵也就是“含蕴无穷”,也就是“语近情遥,含吐不露”,“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10](卷下),也就是“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9](卷12)。其于《施觉庵考功诗序》中论诗云:“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后代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纵放”,致使“忠厚之道衰”。好的诗歌应该是“和顺以发情,微婉以讽事,比兴以定则”[14](《归愚文钞》卷11《施觉庵考功诗序》)。《说诗晬语》开篇云:“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有深情,而又以比兴发之,方能有神韵,若如邵雍之诗那样直头说尽,则兴会全无。[5](《凡例》)
实际上,在王士祯之后,沈德潜有意识以格调补神韵说之不足,更明确地与政治靠拢,有意识地融入主流文化。作为对神韵诗学的补充,沈德潜选唐诗首先推崇盛唐诗歌特别是李白、杜甫,将崇高作为其美学追求。在表现手法上,强调理、事、情的统一。其论理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陶渊明‘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圣人表章六经,二语足以尽之;杜少陵‘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天地化育万物,二语足以形之。邵康节诗,直头说尽,有何兴会。至明儒‘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真使人笑来也。”[8](《唐诗别裁集序》)
沈德潜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坚守的儒家诗教竟然与政治发生冲突。他将忠孝视为温柔浑厚之内核,又以温柔敦厚作为作诗、选诗之标准,而乾隆帝却认为其《清诗别裁集》之编选恰恰违背了温柔敦厚之旨:“且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意。今之所选,非其宿昔言诗之道也,岂其老而耄荒?”[15](卷19)沈德潜一生之遭际,是文学在政治主导的社会中的边缘地位的最好阐释。
虽然清代前期的帝王大都爱好文学而倡导风雅,如康熙帝命儒臣辑《历代诗余》、校勘《词谱》而倡“雅正”,雍正帝在上谕中提倡“清真雅正”,乾隆帝亲自“厘正诗体,崇尚雅淳”,但他们对风雅的理解显然更多的是从政治出发。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儒理治世来进行文化整合,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使儒家诗学的复兴最后成为政治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虽然如王夫之所说:“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然在世俗政权统治下,道统往往屈服于政统,风雅诗教由此而发生异化。清代前中期的文学发展历程,说明了影响文学发展的“灵心”、“世运”、“学问”三要素中,世运的影响有时更为重要。文学的发展固然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但外因的作用有时更为直接、有力。清代前中期文学在政治社会中的另类生存,也说明了文学独立自主发展的艰难。
标签:沈德潜论文; 唐诗别裁集论文; 唐诗论文; 乾隆论文; 杜甫论文; 说诗晬语论文; 古诗源论文; 钱谦益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