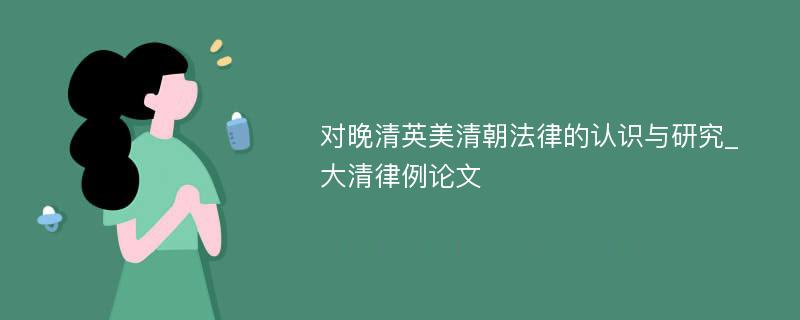
晚清英美对《大清律例》的认识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例论文,晚清论文,英美论文,大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11)03-0124-06
马戛尔尼访华前,中英贸易虽已在中国南部沿海有所发展,但英国人对中国法律还所知甚少。马戛尔尼出发前,曾试图找一位谙熟中国法律的随从,但未能如愿,他感慨道:“使团能否成功取决于对中国法律、风俗和中国人性格等知识的了解。我害怕是因为,由曾到过中国的搬运工及其他曾在广州居住过的人那里,我得知,极少有西方人考察过中国城市1公里之外的情况,极少曾经有人单独居住在中国城市,而且没有人具备掌握这门语言的好奇心和勤奋。”[1]因此,在访华过程中,马戛尔尼使团注意搜集、记录有关中国法律的知识和见闻。副团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Ceorge Leonard Staunton)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参赞约翰·巴罗(John Barrow)所著的《我看乾隆盛世》都涉及中国法律。约翰·巴罗对《大清律例》评价较高,他说:“为便利臣民使用,在其语言所允许的范围内,中国人用最通俗的文字出版了《大清律例》……这部中国法著作文字清晰,结构严谨,完全可以与布莱克斯顿的《英国法释义》相媲美。”[2]这是英国人较早对《大清律例》的评价,可以说从马戛尔尼访华开始,西方开始关注中国法典。
一
马戛尔尼使团中斯当东的儿子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当时只有12岁,由于年少好学,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汉语对话。当使团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时,小斯当东用汉语请安,乾隆龙颜大悦,并赐其礼物,而小斯当东学马戛尔尼的样子单膝跪地领赏。此场景被使团的画师记录下来。这也成为小斯当东再次来到中国并与清政府打交道的资本。小斯当东回英国后继续接受教育,并获得法学学位,后受聘于东印度公司,长期在广州一带活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翻译《大清律例》。小斯当东曾参与涉英案件审理,维护英商利益。1807年2月,英国商船海王星号上的水手在广州与当地村民斗殴,3天后,一名受伤的村民去世。中国政府扣押海王星号英船,并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英国人辩称此次斗殴为双方混斗,凶手实难查明。后中英双方妥协,中国政府同意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派人员参与审判,英国人则交出当时参与斗殴的水手。斯当东参与整个交涉过程,并于4月份参加审判,为英国水手辩护。当时中国政府认定水手希恩可能是正犯,但是没有确切证据,最终中国政府妥协,判希恩“罚款抵罪”。东印度公司认为这是对华斗争的一次胜利,小斯当东也因此获得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的奖励。据载“托马斯·斯当东爵士由于他在希恩事件中的卓越贡献,董事部曾给予奖励(1808年2月26日训令),授予商馆翻译职位,年薪500镑,另外又加以大班工资。”[3]海王星号事件刺激斯当东尽快完成《大清律例》的翻译①。但“由于准备前言和附录花去了大量时间,这一卷直到1810年3月才得以出版。”[4]45不过小斯当东仅翻译了《大清律例》中的“律”,而对“例”则极少涉及,而且,虽然在前言中他称赞中国法律严密,但又认为中国法律在罪责等方面非常落后。
小斯当东的《大清律例》为西方人认识和研究中国法律创造了条件。《中国丛报》上研究中国法律的文章多参考斯当东的译本。此书出版后便获得广泛好评,1810年8月《爱丁堡评论》发表专文评论此书,“尽管英国与中国之间重大的商业联系已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著作是近来第一本将汉语原著译成英文的著作,这相当了不起……这给我们提供的,不是由于景慕者或者诋毁者带有偏见的梗概,而是原始的真实法规。旅行者带有感情色彩和充满想象的描述,使得我们不能客观评价中国法律……然而,我们有众多理由相信,在我们眼前的这本书翻译的完全正确和精确,而且翻译者的如此真诚而沉着的判断使得他有资格让人信任。托马斯·斯当东,在一篇相当长而又简练、谦逊、充满才智的前言中让我们有更多的期待,他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制度一般特征的有趣梗概。”[4]47-48另一份英国著名期刊《评论》(Critical Review)则指出,“我们对中国法典翻译者的感激之情丝毫也不会因我们持有的对中国的厌恶而减弱。”[4]46鸦片战争后,英国占领香港,英译本《大清律例》便获得实际用处。当时香港保留了中国传统法律,这本书成为香港英人法官审理华人案件的依据[4]47。斯当东对此也颇为满意,他自己评鉴道:“这本书使我在35年后沾沾自喜于自己在我们的东方学术中拥有了令人尊敬的席位。”[4]50
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并不是出于研究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英商在华利益。斯当东对中国刑法的了解,使他成为推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谋求在华利益的重要力量。在1840年英国一次议会辩论中,斯当东曾言:“显然,驱逐出中国是中国法律提供的唯一补救措施……我想,我们没有必要为这种暴行要求补偿,在敌对状态下诉诸于补偿只会导致拒绝。我们在整个东方的高姿态主要是基于公共观点的道德力量。如果我们屈从于中国实施的这种暴行和商业恶化,而不进行任何澄清的努力,那么离印度到来这一天的时间也不远了。”[5]这为推动发动战争和战后英国主张在华治外法权提供了重要舆论支持。
二
从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开始,直到1899年E.阿拉巴德②出版其名著《关于中国刑法和同类性质论题的评注》之前,一直未有专门研究中国法律的英文著作出版。阿拉巴德曾遗憾地说:“然而,事实上,自从小斯当东开始才出现了中国法律梗概,但是他已出版的巨著已经落后于时代。法律的某些部分确实不时出现——主要深藏在杂志之中,但是没有展现完整细节——不管多么模糊。”[6]正如阿拉巴德所言,从1810年斯当东出版英文版《大清律例》一直到19世纪末,英美对《大清律例》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当时的英文期刊中。
1833年的《中国丛报》刊登了一篇对《大清律例》的书评,作者认为《大清律例》是中国的根本法,它有多种版本,但都是经过大清皇帝批准后刊印发行。文章认为,中国当前正在施行的法典并非是斯当东翻译的那一部《大清律例》,新的法典较斯当东的版本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7]10。此篇书评重点介绍《大清律例》中关于刑法的内容。作者首先描述了刑罚,认为《大清律例》对“杖刑”有严格规定,“10~50板是4~20岁的人所受的惩罚,50~100板是对20~40岁人所受的惩罚”[7]12。其次,作者认为,“中国众多的刑罚以及统治者许多的言论和行为,似乎仅是威胁或恐吓性的”。[7]13他还认为中国法律具有等级性,因此在刑罚方面也有区别,他说指出“有八个特权阶级……不接受审判,除非叛国罪。”[7]14而且“当政府官员犯罪时,他的上级需要向皇帝报告,由皇帝指导和批准审讯。”[7]15作者也指出《大清律例》对天象家、技师、音乐家和妇、老、幼、弱者有相应赦免条款。最后,这篇书评较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涉外法律,斯当东曾言“一般来论,所有服从帝国政府管辖的外国人,一旦在中国犯罪,将会按照当地法律审判和判刑,而一些详细规定则要参考理藩院关于蒙古族的规定。”[7]17书评作者对中国引用针对蒙古的法律处理涉及英国人的案件颇为不满,认为这损害了大英帝国的荣誉,他说:“当外国人不幸卷入案件,若屈从中国的法律即是抛弃帝国的尊严。”[7]18
除介绍评价斯当东翻译的《大清律例》外,一些英美人士开始利用此译著研究中国刑法。1834年《中国丛报》上刊登一篇介绍中国杀人案的文章,并介绍了《大清律例》中关于“六杀”的规定,作者认为,《大清律例》关于杀人案的一些规定,彰显了中国法律的不公平性。他论述道:“即使对杀人案件的判决,中国法律也要取决于犯人所处的等级。一个杀死仆人的主人不同于一个杀死主人的仆人所受的惩罚。即使在自卫杀人的案件中,判决也取决于杀人者的等级。中国法学家把各种因素融合到法律最后判决中,这的确让人费解。例如,一个很普通的案件,如果一个妇人反抗一个男人的暴力侵犯,并将其杀死,这是正义的杀人,属于自卫。但是如果这个男人是其应当尊敬和孝敬的公公,那么她就被判以死刑。”[8]39
另外,当时一些汉学著作也涉及到对《大清律例》的评论。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在《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一书中花费较多笔墨介绍了中国法律,他虽然同意斯当东在其译著《大清律例》中对中国法律的评价,但是认为斯当东忽视了这部刑法典三个明显的缺陷。首先,这部法典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强制执行一些混乱的职责,而这些职责留给道德要远比留给成文法好……实际上,这些强制的义务损害了人们的向善之心。我们则是把慈善的规定放在《济贫法》[9]219中。中国这种强制性的义务甚至要延续到对方生命结束之后,如中国刑法规定,不定期祭祀祖先的人将会受到刑法的惩罚。”[9]224中国刑法的另一个缺点是,关注一些非常琐碎细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实际中并不会发生作用。“考虑每一种可能性,反而不能区别对待案件,这与欧洲相反”[9]224。第三个缺点是这部法典的一些规定表现出政府的极端恐惧,不仅仅表现在法典上,也表现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具体执行上,如法律规定外国人不得进入中国内地,而对违反者的严厉惩罚也说明了这一点。德庇时认为“没有什么比这部法律更能向我们展现专制与民主的区别了。”[9]224他还依据《大清律例》批判了当时西方人心目中认为中国刑罚残酷的普遍观点,“在谈及中国法律规定的刑罚时,我们认为中国刑罚滥用、残酷,这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刑法对刑罚有严格规定,严刑逼供在适用范围和强度上也都有其严格要求。虽然中国的严刑逼供非常多,并可能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严刑逼供。”[9]227他认为“总体上看,中国优于亚洲其他国家,包括在政府管理和法律的普及方面,这使法律更加广为人知,更平等地进行管理,当然,这也是在施加野蛮惩罚的陪同下。”[9]238
鸦片战争前,英美人士主要关注《大清律例》中关于刑法的规定,而且多数是对它的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外国水手、商人经常与沿海中国人发生冲突,产生大量涉外案件,来华的英美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法律,以在交涉中维护本国利益。美国学者基顿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一书中就曾说,《中国丛报》刊登批评中国法律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在涉及英国人的案件中能够抵制中国法律,以维护在华外国人的利益。”[10]
三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大量从事贸易、传教活动的西方人来到中国,西方人与国人之间的商贸交往更加频繁。与此相适应,英美学者逐渐关注《大清律例》中有关民事案件的规定。另外,英美在中国已获得领事裁判权,因此,批评中国刑法的兴趣也不断降低,逐渐更加客观地研究中国刑法,注重刑法中的各种原则性、制度性的规定。
1889年,J.M.詹姆斯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关于《大清律例》的部分翻译,主要是针对民事案件的“律”、“例”规定,虽仅是节选,但补充了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的不足,丰富了西方对中国法律的认识。对民事案件的刑事处罚,詹姆斯认为“似乎,在实际中,没有可依循的统一法律,多由与古老习俗一致的类推方式做出案子裁决。”[11]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大清律例》关于私偕官物、擅食田园瓜果等的处罚规定,甚至详细介绍了将物品或牲畜委托给他人受损时的各种规定:受委托者个人原因导致受损情况下,受委托者本身需承担责任,但是因火、水、偷或牲畜生病等原因则免责;火灾情况下,如果当铺本身起火,需赔偿委托物价值的58%,若从邻居家火苗蔓延,则赔偿委托物价值的20%。不按照政府规定,双方私办,将受杖刑并没收物品。詹姆斯还介绍了中国一些涉外规定,如住旅馆需登记,旅馆需将登记上报,不允许购买外国人进贡的违禁品,若掮客进行欺诈交易、伪造重量及拖欠外国人费用将受到流放的惩罚等。
另外,这一时期的英美学者不再集中批判《大清律例》,而是注重介绍和研究其中原则性的制度,如1882年《中国评论》上《中国法律中的保辜制度》一文介绍了《大清律例》中的保辜制度。作者论述到“根据《大清律例》,在暴力伤害他人四肢或身体,或者导致他人骨折,不管伤势是由手、脚或他物造成,保辜期限为50天。”[12]286“假使受害人在保辜期限失效后死亡,犯罪不应是谋杀,而应在有关攻击导致受伤的条文下审理。”[12]287
1874年《中国评论》上的《中国法律的掌管执行》一文对《大清律例》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作者认为中国刑法典的根基是父母和子女关系,他认为“在《大清律例》中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构成了这部法典的基础”[13]233。文章还回顾了中国刑法典的发展历史,指出中国古典著作是中国法律的发源之地,其起源是“萧何将经书分成9章”,而且“据说这比基督纪元早了200年”[13]231。作者认为,在魏、晋时期,中国还没有固定的书面法律,成文法律只可追溯至唐朝,“明朝通过增补或删减的方式发展和扩充了这些法律,而且这些法律是从特定用法中推断而来。当前王朝也只是通过增补或者删减而轻微修改已存在的法律。因此,清朝法律并不是那么古老”[13]233。虽然,此文作者认为中国成文法最早形成于唐代的认识是谬误,但其追溯中国成文法典的历史,则是对西方流行的古代中国无法典观点的直接批驳。另外,作者也批驳了西方认为中国法律是专制主义工具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存在法律,这与西方世界流行于大多数人中的观点相违背。这暗示了存在某种文明,并将中国从野蛮和凶猛的国家中除名。在有法律的地方,尤其是有书面法典的地方,法典在某种程度上已规范了其法律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典使社会装备了一副盾牌,一方面保护生命和财产免受无政府和暴力的侵害,一方面也设置了抵挡暴政和压制的栅栏。”[13]232作者认为,欧洲法律中也存在错误和暴虐,不能因为中国法律存在严酷的刑罚就完全否定中国法律。此外,文章还介绍了《大清律例》中的多项法律制度,如保释、审讯、上诉等。
随着西方汉学发展和英美学者研究中国法律的深入,1899年阿拉巴德出版了《关于中国刑法和同类性质论题的评注》一书,此书是阿拉巴德在其父阿查理遗作的基础上完成。阿查理对中国哲学和法律颇有研究,也是当时英国著名的汉学家,而阿拉巴德不仅在英国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而且还曾在中国海关供职,比较了解中国法律,并且,此书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又得到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协助。因此,此书被当时英国汉学界视为研究中国法律的权威之作、典范之作。与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不同,阿拉巴德在《关于中国刑法和同类性质论题的评注》中对《大清律例》的“律”和“例”都进行了翻译和研究,同时详细介绍和研究了中国家族法、民事法及习俗法,因此,此书成为当时研究中国法律的集大成之作。阿拉巴德认为需要区分《大清律例》和“刑法”,指出过去所认为中国刑法存在于《大清律例》之中的认识是狭隘的理解,事实上,中国刑法涵盖的内容非常全面和庞大,中国刑法有无所不包的重要性。另外,他提出中国刑法不是仅仅包含在《大清律例》中,也可在判例中找到。他说:“中国法律,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体系的,但是很难说是集中的。我是指,例如在法典中,所有涉及的考虑因素,如任何特定犯罪,不是依据所述罪名判刑,而是出现在多维度的关联之中。”[6]此书出版不久,一篇评论认为,阿拉巴德的《关于中国刑法和同类性质论题的评注》一书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在研究《大清律例》时需要区分“律”与“例”,而且这本书使“我们了解到中国法律的运行状况和发展”[15]148。当然,《关于中国刑法和同类性质论题的评注》中也存在错误之处,如弄错朝代顺序等。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汉学的发展,当时英美学者逐渐倾向于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政治制度和法律习俗。适应这种时代潮流,1906年,阿拉巴德出版了《中国法和诉讼复审程序略记》一书。在此书中,他为中国传统法律进行辩护。他认为看问题要透过事物的表面,抓住事物的特性和内在本质,过去单纯研究中国刑法本身的研究方法并不可取,中国有其特殊的一面,中国文化调节中国法律的运行,因此要研究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法律,这才是研究中国法律的正确途径。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刑律进行了修正,保证了中国法律的公正,中国法律中“满含令人敬佩的原则”,因此,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法,是一种“良法”[14]16,而且这一法律适合于中国国情,并不需要按西方标准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更需提及的是,阿拉巴德反对用西方标准衡量中国法律,他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像能说一口流利的语言,却长了一只猴子的脸。”[14]75他甚至反对用西方的法律术语解读中国法律,他认为“将外国法律术语运用到中国法律中非常危险”,并以其自身经历解释到,“几年前我也曾这样做,要恰当的翻译中国法律必须从其源头忠诚地翻译,而且不应该以其他任何方式改编,除非它的本土方式。什么是故杀?是谋杀吗?不是。它是六个明确类别中的之一,这些类别是法律分辨最坏犯罪与其他犯罪的标准,什么是违制?什么是挟制?他们是其本身,……我只在这篇文章中使用诸如盗窃和其他英美法特殊行话,尽管中国法律行话,如果有的话,更加独特。但是,当适用于比较大的问题时,术语对比以及术语的用法有其特定的位置。”[14]76对此现代评论家给予积极评价,如在《近来关于中国法律的研究》一文中,作者塞勒斯.H.培可(Cyrus H.Peake)就非常赞赏阿拉巴德反对用西方法律术语解读中国法律的做法,认为阿拉巴德开创了研究中国法律的新路径[16]128-138。
阿拉巴德的观点反映出西方学术潮流由“现代性”转向“反思现代性”,并由此承认中华文明本身的合理性。但是到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近代民主思想已在中国传播,传统儒家思想逐渐式微,新的生产关系不断涌现,正是从中国现实来看,《大清律例》已经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
四
从1810年斯当东出版英文版《大清律例》到20世纪初期,英美学者对中国法律进行了近百年研究。这一时期英美人士主动研究中国法典,积极了解中国法律制度,但毋庸置疑,不论是含有恶意的批判或较客观的评断亦或如阿拉巴德般为中国法律辩护,都是带着功利性的目的,即主要是为来华的英美商人、传教士服务,以维护他们的利益。
由于鸦片战争之前,中外之间经常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生涉及外国人的刑事案件,因此,这时英美人士主要关注《大清律例》中关于刑事案件的规定。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条约的签订,西方不仅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而且还获准在华设通商口岸,开矿设厂,建教堂传教。与此相应,外国来华人士与中国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断增加,因此需要熟悉关于中国民事买卖关系、土地典押关系等法律规定,英美学者研究《大清律例》中关于民事关系的规定就成为重中之重。不过,由于西方已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英美人士对《大清律例》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了,但是仍然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先。如1874年《中国评论》上刊登的《中国法律的执行实施》一文认为,《大清律例》中含有民主因素,是严明的法律,但在文章最后,作者却说:“中国法典体现了美好的理念和道德,但令人悲伤的是,当将其付诸实践时,却缺少这些理念和道德,只有低劣的民族道德音调……中国法律执行实施的特点严重影响了治外法权问题或者与外国势力订立条约中内容。”[13]243因此,断言在中国实行类似于基督教的法律之前,各国应该不放弃对华治外法权,“否则一旦本民族的基督徒受到迫害,我们该怎么办?”[13]24419世纪末20初,中国国内改革声音的加大,中国修改法律逐渐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时,英美汉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成为当时的学术潮流。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术发展趋势下,英美学者公开为中国法律辩护,其中包括对《大清律例》的评价。阿拉巴德更是直接反对当时中国变法修律,认为《大清律例》适应中国社会和国情,中国不应该按照西方的标准变革法律。
在百年研究中,晚清英美对《大清律例》的认识和研究不断发展,从最初的注重研究刑事案件到比较全面的研究包括民事案件在内的各种原则和规定;从最初的批评到相对客观的评价。可以说,这其中也折射出近代中外关系的变化及西方思想从“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转向。
收稿日期:2011-01-18
注释:
①根据东印度公司的史料,“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已随同波郎返回广州任职,而部楼顿则乘第一批船队返回英伦,被证明为体质衰弱及总的健康状况不良。托马斯·斯当东爵士由于他在希恩事件中的卓越贡献,董事部曾给予奖励(1808年2月26日训令),授予商馆翻译职位,年薪500镑,另外又加以大班工资;但由于他离开中国,所以工资只能从他回任之日起享有。”(参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三卷:130页),而根据小斯当东的回忆录小斯当东1803-1807年呆在澳门,而后“在回家的旅途船上我完成了这项工作。”(George Thomas Staunton.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the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London:Printed by O.Barclay,Casae St.Leicester Sri,1856:44.)由此可知,斯当东是在中国处理完案件回国的船上完成了《大清律例》的翻译工作,而不是一些著作中所言的1810年。
②阿拉巴德(Ernest Alabaster,又译E.阿拉巴斯特),1872年生,他是英国驻广州领事阿查理(Chaloner Alabaster)的儿子,英国四大律师学院内殿律师学院(Inner Temple)大律师,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ambridge Christ's College),1889年来到中国,20世纪初任职中国海关,曾担任梧州税务司。其在汉学方面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中国货币史和中国法律方面,1899年出版在其父遗著基础上修订完成《关于中国刑法和同类性质论题的评注》(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Chinese Criminal Law and Cognate Topics,1899.)一书,奠定了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回国,1936年发表《帝国官员的法律汇编》(Dips into an Imperial Law Officer's Compendium,Monumenta Serica,Ⅱ:426-436.)一文。
标签:大清律例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法律翻译论文; 中国法律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法律论文; 阿拉巴论文; 中国丛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