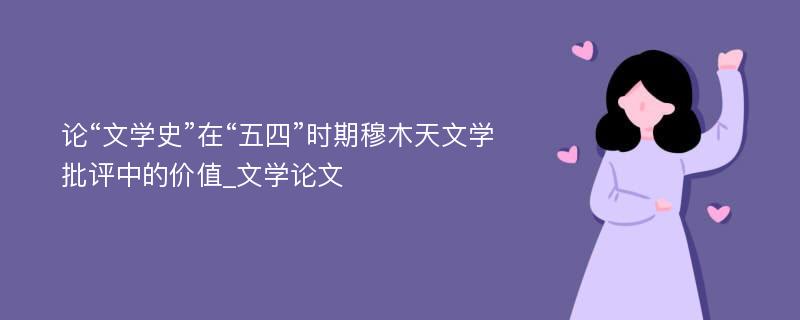
论穆木天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史”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文学史论文,价值论文,论穆木天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既有的新文学描述的质疑中重新认识穆木天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史”价值。文学革命倡导中的“意识形态”泛化,导致新文学初始期非文学之流弊,这在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有突出的表现。穆木天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切中这一弊害,虽在当时未产生影响,但因其“合理性”,在尔后的新文学发展中得到历史的回应。文章通过穆木天的个案分析,建构新的“文学史”观。
去年在吉林师院召开的一次关于“文学史论”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学者提出:“文学史无法还原历史,文学史也无须还原历史”。这颇引起一番争论。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认为“文学史”确实无法还原历史,但“文学史”应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于是,我提出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
这里所说的文学史,有两种虽相关却又不同的内容:一是指从过程到结果的具有实证意义的文学史;一是指在实证性文学史基础上产生的主客观统一的富有思辨意义的“文学史”(这里加引号以区别前者)。
提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似可作这样的理解:文学史上那么多作家,大浪淘沙,经由时间的筛选与沉淀,最终会有几个能进入“文学史”?不必为此大惊小怪。但中国新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确使一些不该失踪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失踪了。穆木天就是一个。
说穆木天在“文学史”上失踪,其实也不尽然。首先,穆木天曾经引人注目地存在于文学史上。1918年,他就发表过鼓吹新思潮的文章。留学日本,他列名于创造社发起人之一。1925年,他在《语丝》上与名声昭著的钱玄同进行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论战。次年,他学成回国,指名道姓地批评提倡“作诗如作文”的胡适,“把中国诗坛害得断子绝孙”!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与冯乃超、王独清在刚创办的《创造月刊》上,有宣言、有作品地“发难”于诗坛,为人瞩目,引出不少评论,有“创造社三诗人”之称,他留下了当时颇受好评的第一部诗集《旅心》。1931年初他到上海,加入“左联”,担任《北斗》编委和“创委会”诗歌组负责人。翌年9月,他与同人发起并组织了“中国诗歌会”,后又创办了会刊《新诗歌》,写出著名的发刊词《我们要唱新的诗歌》,创作了第二部诗集《流亡者之歌》。抗战爆发后,他在武汉当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会刊《抗战文艺》的编委,创办了诗歌刊物《时调》和《五月》。到大西南他仍然力主抗战诗歌活动,并出版了最后一部诗集《新的旅途》。穆木天如上这些文学活动,在当今各类“文学史”著作中得到程度不同的描述,树立了一个紧随时代前进的诗人形象。
但是,我仍然认为穆木天在“文学史”上失踪了。正像不能撇开鲁迅称之为他的“哲学”的《野草》,而仅仅着眼于《呐喊》、《彷徨》来描述他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一样;对于穆木天,舍弃了他的文学批评,他在“文学史”上的存在,失其魂而剩其壳,说其有而实为无。所以如此,是因为:一、穆木天曾经多次说过他不具备诗人的素质,他的三部诗集,即使是被称为“上乘”的前期诗作,也佳作甚少,难说不被今后的“文学史”淘洗掉;二、穆木天曾反复强调自己有抽象思维的天分,他留下的在篇幅和文字量上要远远超过诗歌的文学批评,是一座并未得到真正开发的“矿藏”,仅从近年来引起研究者关注的他的诗论来看,其价值和意义就明显超过他的诗歌创作;三、更重要的是,文学史进程中的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这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
在我看来,从实证意义的文学史到思辨意义的“文学史”,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是文学演进过程中的文学批评。作为从“结果”追溯“过程”的“文学史”所面对的,首先是以“作品”为核心的文学现象,这构成文学史本体的“第一真实”,而文学演讲过程中的文学批评,以其特有的与“第一真实”的亲合性与涵盖性以及对“第一真实”的导向性与超越性,则体现了文学史本体的“第二真实”,后者较之前者,就其所引发的“过程”对“结果”的颠覆,对于在实证基础上产生的富有思辨性的“文学史”,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我所关注的是1926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经过近十年紧张地奔波,渐呈“告结”,在诸多从不同理论背景出发的文学批评使之孕育着多种发展可能的机运中,穆木天以《创造月刊》为阵地,发表的《谭诗》、《写实文学论》、《法国文学的特质》、《维尼及其诗歌》、《维勒得拉克》[①]等一组有内在联系而自成体系的理论批评文章。
走进穆木天批评理论框架理解其精神实质并非易事。我以为可先读一本书和一篇文章,这就是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版)和王晓明发表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上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朱学勤认为,在中国从清末君子上书光绪,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连贯其间的一条政治文化思路的源头之一,即是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释放出的“意识形态”泛化,这在王晓明的文章对《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倡导并统制新文学的非文学的动机与方式的剖示中得到印证。陈独秀的那篇引爆“文学革命”的檄文,开篇即引荐欧洲(法兰西)政治革命的激进范例,从他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到茅盾著名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贯穿这一新文学批评主流话语中心思路的是实证主义一元进化观。“实证”以求社会对文学的决定意义,“一元进化”则以欧洲主要是法国文学中激进的一脉为本,要求新文学向更切合“意识形态”泛化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发展。这虽然有助于新文学摆脱传统的束缚,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五四时代,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学本体失落而审美意识薄弱的致命弊害。恰如王晓明的那篇文章所说:“在现代中国,对文学艺术独特性的领悟,恐怕是知识分子从进化论和决定论崇拜那里逃脱的唯一出口,一旦错过了这个出口,就难免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穆木天正是当时从这个“唯一出口”中“逃脱”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他的文学批评的要害正在这里。
穆木天的文学批评是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他的《法国文学的特质》一文所针对的就是依据“一偏的进化论”和“从泰纳得来的实证的影响”,“认定‘社会的’是法文学的特质”,“最足代表的是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与十九世纪的写实文学”的“独断的批评”。他认为法国文学存在着“外的”与“内的”两个层面,表现为“社会的”与“心理的”两条脉络。他通过对这两条脉络不间断的“离”、“合”过程的考察,得出了“不仅古典派、写实派是法文学的嫡派,浪漫派象征派的文学亦是法文学的正流”的结论。穆木天为浪漫派、象征派正名,提出对法国文学全方位的参照,就是从“文学艺术独特性”出发,矫正新文学批评主流话语忽略文学本体建设的偏失。
一般认为,穆木天1926年的文学批评主要借鉴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穆木天在东京帝大法国文学部毕业的学士论文,选择的是法国象征主义鼎盛期地位“隐微”(罗大冈语)的年轻诗人萨曼,论文所得出的结论是:萨曼“是一位在象征主义时期保持了安德烈·舍尼埃的传统,并且为新古典主义流派作了准备的作家”[②]。这里存在着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与认同。穆木天早在“五四”前夕的随笔中就表露出这种依恋传统的“古典主义”情绪,对取法法国大革命而颇显激进的文学革命倡导甚不以为然。死于法国大革命断头台的安德烈·舍尼埃是一位极端崇尚希腊罗马古风的古典主义的贵族诗人,他的诗歌启示了19世纪前期整整一代浪漫派诗人。勃兰兑斯说:“舍尼埃影响的第一位作家”就是贵族浪漫派诗人“阿尔夫莱·德·维尼”。穆木天说:“我非常爱维尼的思想”,“我读了诗人维尼的诗集”《命运集》,“好像是决定了我的作诗人的运命了”[③]。近年来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泛化而产生的类似中国“文革”的文化浩劫的批判,提出正是那些精神贵族在这场浩劫中是文化精品的真正的继承者与保护者。穆木天与维尼的精神联系,在客观上起到了对文学革命倡导中的“意识形态”泛化所产生的新文学非文学之弊的防范与抵御作用。
穆木天在《维尼及其诗歌》一文中认为,维尼青年时代作为狂热的保王党人,为动乱岁月中的波旁王室效命,1935年后,蜇居乡间私邸,褪去外在的政治色彩,在以贵族精神特有的极强的“艺术意识”和“爱美家的态度”构筑的“象牙之塔”中的诗歌创作,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内在地获得了艺术的升华,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体现了对文学的真正理解。但是,文学革命将文学的贵族精神与平民精神截然对立起来,在新文学平民化倡导中看重的是“平民”而非“文学”。穆木天追根溯源,在《法国文学的特质》中进一步指出:法国文学的本质是高卢精神与拉丁精神的不调和,二者的区别:前者体现的是追求外部社会功利的平民精神,而后者则体现了注重内在诗性境界的贵族精神;认为,正是高卢人受到拉丁精神的“洗礼”,两种精神结合遂“开后来数百年的文华”,造就了“伟大的文学”。显然,穆木天对文学的贵族(拉丁)精神的倚重,所针对的就是新文学平民化发展中,文学在根底上应该有的贵族精神的剥蚀。
这样,穆木天将他的文学批评建立在对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的严格区分与界定上:一方面,他在《谭诗》中提出“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让诗回到诗那里去,对“纯粹诗歌”进行形式建构,以矫正五四白话新诗的非诗化流弊;另一方面,在《写实文学论》中,他提出“写实”与“写真”的区别,认为“写实”产生于作家的“内意识”(创作主体),“写实文学”是“内意识的结晶”,以滤除左拉的自然主义对新文学创作的淫染。穆木天从“文体”到“创作”对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的严格区分与界定,绝不是遗忘或舍弃文学的现实性品格。在《谭诗》与《写实文学论》中,文学从追求外部社会功利的非文学表现,回到文学本体建构,而由作家创作主体的“内生命”中积淀、蕴蓄的丰富的社会历史与现实人生体验,内在地与时代相统一。穆木天进一步提出文学的“哲学”意义,即文学根底上的贵族精神所决定的文学的形而上的本质特征,认为文学在面对现实的同时,还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的品格,蕴含着根源于人的本性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哲学”。
穆木天从艺术审美领域唤起人们对文学的重新认识,使新文学向文学本体回归,并对新文学发展的内容、形式及创作,做了更切近文学内在品格与规律的理论建设。他的文学批评对于正孕育着多种发展可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新文学发展汲取了穆木天提供的有益因素,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但实际情况却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穆木天1926年的文学批评迅速成为过眼烟云,不仅文学史上再无人提起,而且在迄今所有的“文学史”著作中无一描述,甚至为尚不多见的现代文学批评史、思潮史著作悬置在外。这有穆木天自身的原因,对此,我曾做过这样的说明——
穆木天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出现“恰逢其时”,而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他的理论又“生不逢时”,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寂寞的。急速推进的时代,呼唤着文学的应和。尽管他避开大革命策源地广州,到古都北京去持续他的思考,最终也耐不住透骨的寂寞与孤独。面对故土在军阀势力蹂躏下的破败,帝国主义日甚一日的掠夺,激发着他的时代责任感。当在日本的诗友已经先行“自我否定”,投身于时代大潮中,他发出了“还是不要脸地在那里高蹈”的自责,把自己精心构筑的并未舍弃“时代”的理论视为“异端”,打碎后重新组装的“理论”,倒真的成为他曾经激烈批评过的“异端”。人们不能不追问个中缘由。这有他的理论欠完善,尤其是建构理论的思维方式未能从根本上突破他所处时代的局限等根源。但直接原因是,他的理论是把文学从时代政治中“隔”出来,按照文学自身特征在建构中内在地与时代相统一,这样,隔,即在外部与时代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是理论确立的前提;当时代政治要求文学以其外部社会功能的极度膨胀相配合,当多灾多难的民族对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有力冲击,他对这种“距离”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距离”一经消失,理论自然瓦解。这是以牺牲文学内在品格与规律为代价的理论“自赎”的悲剧。[④]
穆木天在思维方式上突破了主导新文学发展的实证主义一元进化观,他的文学批评充满生机与活力;但他并未从根本上逾越在新文学中有着更深根基和更大能量的绝对主义两极对立观——如在旧与新、中与西、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等问题上,非此即彼,“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新文学先驱者作为“历史中间物”,他们的这种思想方式又深植于传统之中——受儒、道思想影响的传统文人的存在方式,或“儒雅”或“风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理智与情感上都偏于“传统”的穆木天,受新文学风气所染,在深层意识中自然很难逾越他所处的时代的这一思维水准——他在与钱玄同的“欧化的中国”说的辩论中,就一定程度地表现出“传统主义”的偏执[⑤];他对法国文学中的高卢精神与拉丁精神的特点的两极对立式的描述(包括他对诗与散文的绝对化的分界),并将法国文学的本质归结为二者的不调和。这种思维方式的惯性作用,当他一旦将自己的批评理论视为“异端”,自然走向另一个“异端”。穆木天“转向”后的文学批评虽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却失去了他的“根本”,如他在1935年出版的《法国文学史》的“卷头语”中所说:“所谓拉丁精神与高卢精神之不调和即是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调和的历史。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的总合是社会的表现,而(且)是当时的阶级的不调和的反映。”他的批评个性自然消融于从法国文学参照迅速转向俄苏理论背景的新文学批评主流话语中,“转向”后的穆木天在“文学史”上的失踪自是必然。
但是,穆木天1926年的文学批评,并未随他的“转向”而失去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因为他批评的现象,在新文学发展中始终存在——诸如,文学追求外部社会功利,致使内在品格与规律的丧失;文学满足于现实感,停滞于现实意义,而缺乏超越现实的追求,等等。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合理的,并非就一定持续性存在。
本文作者对穆木天在“文学史”上不应失去的踪迹的追寻,也并非对他情有独钟。穆木天1926年的文学批评的“瞬间显现”所蕴含的有生命力的因素,并未“转瞬即逝”。抗战爆发后,一些新文学作家经过对30年代对峙的两大文学派别的反思,开始找到真正的“自己”,穆木天1926年的文学批评得到了历史的回响。“中国新诗派”中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不仅在对外参照方面,借鉴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而与穆木天的法国文学取向中的浪漫派、象征派相渊源;而且在诗歌理论建构上,以坚持文学的独立品格为前提去感应时代,也与穆木天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胡风抗战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更为深刻地再现了穆木天的“文学史”价值。请看我在对穆木天《维尼及其诗歌》一文的分析——
文章把维尼作为体现法国文学本质的高卢精神与拉丁精神不调和的代表:一方面,维尼追求“外生活的光荣”,“是一个贪欲的恶魔”,他有权力的欲望,要作拿破仑作将军,他象“摩西”那样要“救世济民”(《摩西》),他象“爱洛亚”那样要拯救“堕落的天使”(《爱洛亚》),他想作“斯泰洛”那样的“爱社会”的诗人;另一方面,维尼又有“内生活的神秘”,他是一个“纯洁的圣者”,“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是一个哲人”。这样,“内生活”与“外生活”的矛盾,“灵的世界与肉的世界的不调和”,贯穿了维尼的一生。但是,“维尼的艺术意识是最深的”,所以,外生活“一切的幻灭,一切的失败,越发使他作了内面的人”。在这由“外”到“内”的转换过程中,穆木天充分展示了维尼内心深处的“争战”与“苦斗”,以说明由“外”到“内”的艰难,内在“艺术意识”征服“外生活”的艰难。在这一过程中,维尼从“深尝人生”到“懂透人生”,实现了内在的自我,成就了他的艺术。穆木天通过对维尼一生创作的剖析,提出文学创作需要作者的创作主体的自省与自强,揭示了在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与现实人生的相生相克的结合过程,其间的“争战”与“苦斗”,反映了创作主体驾驭现实人生使之成为艺术的血肉的艰难。显然,穆木天从艺术意识的主导作用出发,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⑥]
从中不难看到胡风的文学批评的“理论雏形”。在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上,胡风与穆木天的联系,显然还有更丰富的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上已成的“结果”——持续性存在的主流趋向,视为文学发展的唯一选择,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对其“合理性”不容有任何怀疑。这是穆木天1926年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史”上失踪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根源。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旧序里反复强调,采取什么思维形式、研究方法对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文学史研究应该从实证层面上升到思辨层面,在对“持续性存在的文学主流趋向”的反思中,不断地发现并正视那些与其相悖的,仅仅断续性存在的,甚至是瞬间显现、转瞬即逝的文学现象,发掘其蕴含着的必将为文学史证明是更富有生命力的合理因素;从而认识到,“文学史”描述虽无意更改但也绝不局限于已然的历史事实,而要在最大程度上还原文学的多元矛盾运动过程,并将矛盾运动过程中的每一矛盾侧面,包括那些并未能转化或者未能完全转化为文学实体的矛盾侧面,放到文学历史演进的最终形态中,充分揭示其所具有的正面或负面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找到包括穆木天在内的“失踪者”,确立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位置。
注释:
①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1、4、5、6、7、8、9、10期。
②《阿尔贝·萨曼的诗歌》(原文为法文,载日本大正15年3月1日《东亚之光》21卷3号),吴岳添译,载《吉林师院学报》1994年第3、4期。
③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载《现代》第4卷,第4期。
④ ⑥陈方竞:《论穆木天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即刊。
⑤穆木天:《寄启明》,载《语丝》第34期。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穆木天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法国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