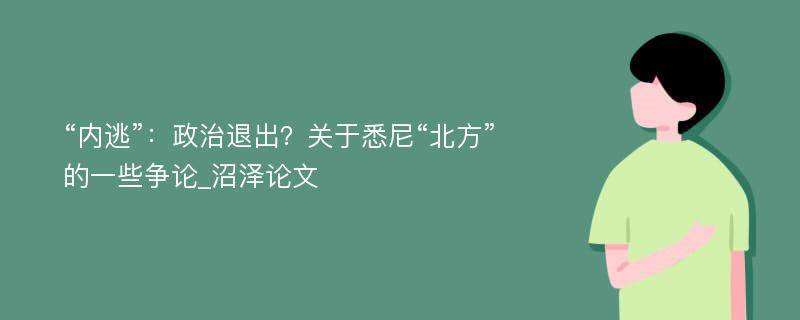
“内心的逃亡者”:政治退缩?——关于希尼《北方》的一些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逃亡者论文,内心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5)08-0151-05 当代英语诗坛执牛耳者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的第四本诗集《北方》(1975)一经出版,即广受各方好评:“《北方》在英语媒介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大多数评论家很高兴北爱尔兰终于在诗歌中有了他们认为适当的表达了”。[1]例如海伦·范德勒(Helen Vendler)就称赞道:“(在1968至1975年间)没有其它作品可以像《北方》那样,用强有力的象征形式和紧促富有想象性的语言唤起那个时期对个体所能产生的所有绝望和毁灭感”。[2]然而,在对希尼此起彼伏的褒奖声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声音。德斯蒙德·芬内尔(Desmond Fennell)一方面既肯定希尼是一个好诗人,并将希尼传奇式的受捧称之为“希尼现象”,[3]但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希尼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他的北爱尔兰出身。[4]芬内尔认为希尼信奉北爱尔兰天主教“无论你说什么,什么都不要说”(Whatever you say,say nothing)的信条,指摘希尼政治上的缄默不语:“简而言之,他的诗歌——像绝大多数好但不入流的诗歌一样——词枯意穷,言之无物”。[5]无独有偶,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McLiam Wilson)声称“任何实际上有读过希尼作品的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体上看,他遗漏那些不诗意的东西,那些真实的暴乱”。[6]同样,奥恩·哈里斯(Eoghan Harris)亦批评希尼对当代北爱尔现状说得很少,指出希尼的诗歌“实际上陷入过去(的泥沼里)”。[7] 那么,希尼的成功仅是出于地缘出身的眷顾吗?他真的是一个逃避政治现实的诗人吗? 首先,从表面上看希尼的北爱尔兰文人身份似乎是他得以登堂入室的关键因素。芬内尔分析道:“对于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爱尔兰或英国诗人,最好的成名方法是(他/她)来自北爱尔兰以及在伦敦出版(作品)”。[8]希尼显然恰好符合这两个条件。他出生于北爱尔兰摩斯巴恩一个世代务农的天主教家庭,从小接受的是英国传统的正规教育,其出版商是伦敦知名的费伯出版社,因此,他在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大动乱白热化阶段所推出的《北方》能“获得一个巨大的市场销量并使得希尼成为英国顶尖诗人”[9]似乎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在北爱尔兰动荡不安的政治语境里,人们期待希尼的《北方》应该能对当时的动乱有所体现。[10]然而,《北方》作为希尼一本饱受争议的诗集,一方面既取得了可观的市场销售额,另一方面却倍受诟病:“人人都急切地期待《北方》成为一部伟大的著作,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不是如此,尽管它是被视为一本好作品来加以对待的……”。[11]其次,对于“政治退缩”的指责,希尼本人的经历也遭遇了同样的困扰。在北爱尔兰处于战乱频繁的1972年,他携家南迁爱尔兰共和国之举曾引起舆论界的哗然,甚至被视为一种叛逃:“在这种情形下,希尼此举被有些人视作背叛北爱尔兰天主教群体以及因此在他心中引起不安甚至是内疚就不足为怪了”。[12]的确,希尼在诗歌《暴露》(Exposure)中曾透露过他南迁所伴随的政治意味的忧虑与不安:“我既非拘留犯,也不是密探;/一个内心的逃亡者,头发长长/若有所思”(希尼:425)。①希尼把自己定义为“内心的逃亡者”(inner émigré),怀疑自己是否会错过“终生一遇的奇迹,/彗星正在使玫瑰的脉跳动”(425),即错失与北爱尔兰患难与共的机会。 那么,情形果真如此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回顾当时北爱尔兰的政治语境。 北爱尔兰集体暴力冲突的直接起因,是60年代末在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等地的北爱尔兰天主教社群举行的民权示威活动,示威的参与者要求享有同新教居民相同的政治权利、就业环境和社会福利。这些要求是对北爱尔兰地方当局长期以来施行的种族区别政策及其现实后果的挑战和反抗……英国政府的强力介入,并没有起到维护秩序、消除暴力冲突的效果,反而激起了北爱尔兰冲突双方的强烈反弹,暴力冲突愈演愈烈。1972年1月30日,从伦敦德里出发的未经英军批准的天主教和平示威,遭到英军的枪击,共有13位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士遭到枪杀,另有12人受伤。这便是北爱尔兰历史上著名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间,恐怖和暴力冲突持续不断,超过了三千六百多人的生命在冲突中丧失,其中两千多人为手无寸铁的平民。[13] 还原了北爱冲突的历史现场,不难发现北爱尔兰事实上成了一个“国家压迫、准军事暴力和教派仇外的严酷战场”。[14]而希尼的《北方》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语境中诞生的。《北方》是“北爱诗人中第一部受到广泛关注的、以1968年之后的冲突为题材的诗集。然而,这部诗集的成功之处不是因为诗人选择了当时备受关注的北爱冲突,而是由于诗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融合中表达了他的困惑与追求”。[15]不可否认,希尼的声名鹊起的确与其醒目的北爱尔兰出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希尼的性格随和、内敛寡言等人格品质亦为他传奇性地位的奠定加分不少”。[16]但这些决不是他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尽管他致力于倡导爱尔兰语和推进爱尔兰传统,但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北爱尔兰诗人身份而)成为(英)美国人的‘珍奇式人物’(a curiosity)”。[17]希尼在接受贝岭采访时曾坦露心迹:“我承认,我承受的压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压力,但我不把政治作为我的写作题材,我想用某种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的形式,来履行我的责任”。[18] 鉴于此,希尼在《北方》中是怎样对那暴力冲突不断的北爱环境做出反应以履行他作为一名诗人对世界的职责呢? 希尼本人对《北方》曾做出如下评价:“我确信到《北方》为止,这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一本书;它用某种方式成长起来并发展下去”。[19]在《北方》中,希尼致力于“从只是简单地获取令人满意的语言图像转变为寻找适宜我们困境的意象和象征”,[20]而他找寻到的“意象和象征”,便是从沼泽底下挖掘出土的远古尸体。 沼泽地(更确切地说是泥炭沼)是北爱尔兰独特的地貌。早在希尼的第二本诗集《进入黑暗之门》(1969)的《沼泽地》一诗中,希尼就注意到了这种特殊的地形: 我们没有大草原/可以在晚上一片一片地切除大太阳——/这里的任何地方眼睛都要向/侵蚀到眼前的地平线让步,//被引进独眼巨人眼睛似的/山中小湖。我们无遮拦的国土/是一片沼泽,在太阳落下和升起之间/不断结着硬壳。/……我们的垦荒者们不断在这里开掘/向内向下。//他们开掘的每一层/似乎都曾有人住过。/沼泽地的凹处可能是大西洋水渗出的地方。/潮湿的中心深沉无底。(37-38) 泥炭沼具有“奇特的魔力以保存落入其中的任何物品。(沼泽里)充满了爱尔兰过往的遗迹,包括尸体(通常是那些被杀害或以其它方式遇害的人)。这种自然地象将土地与人民以及希尼自己过去像大多数靠挖泥炭维生的农村家庭联系在了一起”。[21]对希尼而言,这些沼泽尸体“因暴丧生,却永久地以一种恐怖的死亡姿态保留下来……是爱尔兰动荡过去和现在的完美意象,也是暴力历史在现今的存续的绝好象征”。[22]沼泽“潮湿的中心深沉无底”,正如北爱尔兰错综复杂的历史那样显得深沉而厚重。希尼下定决心从这幽深无底的沼泽中展开挖掘。“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我将用它挖掘”(8)—希尼在他的第一本诗集里的《挖掘》中曾发出这样的宣言。“‘挖掘’……意味着诗歌穿透重重历史的障蔽而返源的行为”。[23]希尼选择挖掘出深埋沼泽地下的历史暴力,以一种巧妙而深刻的方式传递出他对北爱尔兰所经历的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浪费和精神浪费”(426)命运的思考。 《格拉伯男尸》就是《北方》沼泽系列诗中一首典型的暴力考古诗歌。“他手腕的纹理/像炭化的橡木,/他脚跟的球形//像一个玄武岩的蛋。/他的脚背萎缩/像天鹅的脚一样冰冷/像潮湿沼泽里的树根。/他的双股是小山脊/是一个隆起的贝壳,/他的脊椎是条鳝鱼/被拘禁在闪光的泥中”(87-88)。希尼在诗歌中对这具尸体外貌进行了细致而又不动声色的观察与描述,仿佛是在欣赏一件刚出土的精美艺术品。对于这种远古暴力,希尼似乎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从他的字里行间,读者却隐隐约约可以听得到希尼的同情、迷茫,甚至是些许无奈:“他好像是从柏油模中/铸出,躺在/一个泥炭枕头上/似乎在流着//自身黑河的泪”(87)。希尼这种置身事外的超然与冷静,反而更深刻地映衬出诗人对这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暴力所作出的回应:“他被吊在天平上/一边是美一边是暴行:/一边是垂死的高卢人/过于精密的罗盘//镶嵌在他的盾牌上,一边是有实际重量的/被蒙上头的受害人/被砍死后,抛入泥炭田”(89)。希尼在诗的结尾将两组反差鲜明的意象并置,使诗歌内涵被赋予了极大的张力:一组是美与暴行,另一组是以高卢人为代表的艺术和以格拉伯男尸为代表的现实。在这架历史的天平上,希尼虽然没有明言,但他的“受害者”一词实际上已经让读者听到了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他把天平倾向于处于弱势的暴力牺牲品的一方。如果我们联系希尼自身的处境,或许希尼对北爱尔兰家乡政治暴力冲突的态度就会变得更加明晰了。他在1972年移居爱尔兰共和国之举以及在这之后的到世界各地漂泊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观察格拉伯男尸方式的呼应——与家乡北爱尔兰保持距离使得他能得以获取更好的视角审视发生在北爱尔兰的政治暴力冲突。正如艾尔默·安德鲁所评价的:“正是从力量角斗场之外才能最好地理解各种(参与斗争的)力量模式,而不是只能默默地承受(来自这些力量的压迫)”。[24]梅格·泰勒(Meg Tyler)亦评论道,“希尼选择从一个相对远的距离来测听政治历史的做法是真实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他是一个诗人,他利用丰厚的历史遗产积淀,从中汲取养分以找到理解现状的一条出路。[25]希尼“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422),即他不愿意将诗歌作为政治喉舌,失去其应有的艺术创作独立性,然而在“外部世界真实的冲击”(422)下,在北爱尔兰苦难深重的历史境遇里,他又不失一名诗人对历史、社会的关怀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他的教养和经历给了他富有说服力的理由去感受到其中一方弱于另一方,他的诗歌必须对此有所体现”。[26] 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希尼挖掘出的沼泽诗在北爱尔兰赤裸裸的暴力现实面前究竟有何意义?对此,希尼曾经思考过“诗歌以及总体上(所有)想象性艺术的一个大悖论:在残酷的历史屠杀面前,它们实际上毫无用处”。[27]换句话说,诗歌能做的很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功效为零——没有一首诗曾阻挡过一辆坦克”,[28]这似乎与奥登的至理名言“诗歌不能使任何事发生”异旨同趣,然而,希尼同时亦声称:“在另一个意义上,诗歌(的力量)又是无限的”。[29]体现在《北方》收录的诗中便是希尼使用的沼泽意象具有独具匠心的巨大力量。借用罗纳德·舒哈德(Ronald Schuchard)的话说,希尼的沼泽系列诗中采取的超验诗学“不是逃避(诗人)对国家(生存)状况的同情,而是把情感转变为一种象征符号”,[30]通过这种客观对应物来迂回巧妙地表达出他对北爱尔兰暴力无奈和抵抗并存的情感体验。在历史与现实暴乱之间,希尼看到了“文明暴行”的循环,“在社会历史冲突中,对于无辜者的杀戮始终存在着,虽然地点、理由和名目可能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3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希尼甚至突破了对于北爱尔兰历史文化思考的局限,而具有更宏大的人文情怀”。[32] 希尼的作品如今已进入欧美各大学的教材,被学界纳入经典的行列。希尼能最终于1995年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能被学术界奉为圭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作品本身卓越的艺术成就:“希尼之所以蜚声文坛,或许有种种外在因素,或许得益于经典化过程中诸多环节和机缘,但归根结底,是其诗作本身的经典性使然,是作品内在的审美维度使然”。[33]正如他的诺贝尔颁奖词所揭示的那样,希尼的作品“具有抒情诗般的优美和伦理的深度,使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和活生生的往事得以升华”。[34]正如他把自己定义为“内心的流亡者”——一个身居爱尔兰共和国,却始终心系北爱尔兰故土的艺术家一样,希尼在《北方》中表面上看似回避北爱现实暴力,却绝不是所谓的“政治退缩”。虽然希尼在《北方》中没有直接谈论北爱现实语境中的冲突,但他却以沼泽尸的挖掘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角,搭建了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透过这种历史暴力的艺术回溯,希尼得以在广袤的层面上运用一种迂回的策略,以更冷静客观的笔触观察、书写和反思人类文明史上的暴力循环,从而致力于为更好地洞悉现在提供一种诗歌的纠正功能。 ①本文所引用的希尼诗文,除特别标示外,均引自《希尼诗文集》,希尼著,吴德安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此后仅在括号内标出所引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