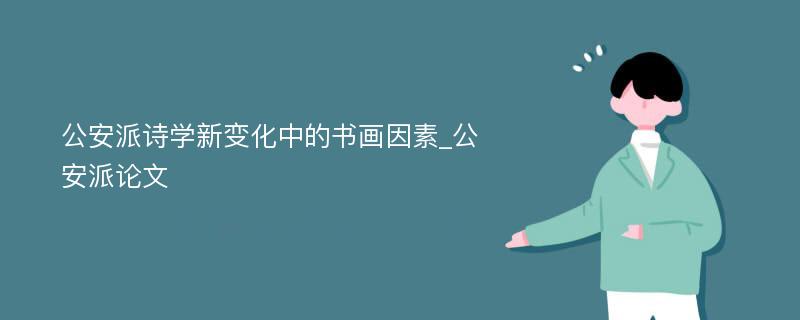
公安派诗学新变中的书画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书画论文,因素论文,公安论文,新变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矫正前后七子的复古流弊,明代公安三袁的诗文创作“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形成了风靡一时的诗学风尚。这样的诗学除了受到师法渊源、道释思想与阳明心学这些因素的影响外,与其他因素之间也存在联系,研究者对此尚未予以关注①。袁宏道有诗云:“尝闻工书人,见书长一倍。每读少陵诗,辄欲洗肝肺。”②又云:“谭诗宗岛瘦,运笔想怀颠。”③诗书并举与互融,似乎可以窥见他们的诗学与书画艺术有着微妙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求新求变的诗学意趣或多借用于书画艺术,并形成一种诗学批评方式和一定的诗学履践。进而言之,这不仅仅和他们对徐渭的推崇以及与董其昌的交游有关,更和其放浪形骸、求趣觅真的追求有着紧密的关联。如袁宏道《答人》云:“走不能书,而有书癖;不能诗,而有诗肠。”④《和萃芳馆主人鲁印山韵》诗曰:“上马揖来无别语,米家曾乞载书航。”⑤取意于黄庭坚《戏赠米元章》:“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任渊注:“崇宁间,元章为江淮发运,揭牌于行舸之上曰‘米家书画船’。”⑥后来“米家船”借喻对书画的喜爱。因此,在公安派前后两期的思想变化过程中,他们求新变于书画艺术的诗学旨趣贯穿始终,并形成一种诗书画诸艺术之间的融会贯通。 一 诗学中的取法书画观念 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学主张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由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在《敝箧集》和《锦帆集》中予以实践的。江盈科《敝箧集引》谓:“世之称诗者必曰唐,称唐诗者必曰初曰盛。唯中即不然,曰: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天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⑦《锦帆集序》说:“君诗词暨杂著载在兹编者,大端机自己出,思从底抽,摭景眼前,运精象外,取而读之,言言字字,无不欲飞。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觉者。”⑧这一学说通过他们对徐渭的发现与表彰得到进一步确定,取得书画诸艺的呼应和观照,从而上升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精神。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月,袁宏道与陶望龄得徐渭诗,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⑨。看似狂放的行为却显示了发现徐渭的欣喜。陶望龄说:“袁宏道中郎者来会稽,于望龄斋中见所刻初集,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闻者骇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谭乎!”⑩他们之所以如此激赏徐渭的诗歌,在于徐渭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具有“眼空千古,独立一时”的独特艺术风格,在复古思想笼罩一时之际,显示了表现自我和张扬主体的诗歌艺术追求。袁宏道在《冯侍郎座主》中说:“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11)又《答梅客生开府》记载梅子所言:“今代知诗者,徐渭稍不愧古人,空同才虽高,然未免为工部奴仆,北地而后,皆重儓也。公然侈为大言,一倡百和,恬不知丑。”(12)徐渭的“尽翻窠臼,自出手眼”和“不愧古人”的特征,正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学纲领的完美典范。需要注意的是,徐渭的诗歌多为题画论书之作,显示了与书画相似的审美品格。徐渭亦擅长行书与草书,袁宏道也同时称赞其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中年学画,则次之,“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实际上注意到了徐渭奇崛的主体精神在艺术之间的贯通。袁宏道的好友梅生说:“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而袁宏道本人则对此予以赞同,并补充道:“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13)更可以坐实这一点的是,袁宏道在《答徐见可太府》中说:“于鳞有远体,元美有远韵;然以摹拟损其骨,辟则王之学华。会稽徐文长稍自振脱,而体格位置,小似羊欣书,仁公何得遂奄有之?”(14)李攀龙和王世贞是后七子的中坚力量,袁宏道认为他们因模拟而有损其诗歌艺术成就,故将之比作王献之模写《华山碑》。而徐渭摆脱了复古模拟的弊端却“小似羊欣书”,按史称羊欣学王献之书,以至于“买王得羊,不失所望”,达到了相近的艺术成就。张怀瑾《书断》谓:“师资大令,时亦众矣,非无云尘之远,如亲承妙首,入于室者,唯独此公,亦犹颜回之与夫子,有步骤之近。”(15)但袁昂《古今书评》论羊欣书说:“羊欣书如大家婢女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16)故羊欣与王献之的书法终究是神情风韵有所不同。袁宏道将徐渭诗与羊欣书相比拟,看似指摘其诗歌的局部缺憾之处,实际上却能突出他突破复古自成一家的独创特征。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推崇徐渭时不吝溢美之词,称“徐文长,今之李杜也”(17)。有意彰显徐渭高标气格、痛快淋漓的艺术精神,从而反对如同书法临摹一般的复古一派。同时也体现了公安派借用书画理论展开诗学观念的批评路径。 正因为如此,公安派在其诗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会借引书画艺术,他们的诗学生成与其交往书画大家有着紧密的关联,以至书画艺术家的思想表述和艺术实践都深刻地影响了公安派的诗学思想。袁宏道与董其昌为至交之谊,他们之间谈玄析理,恣情山水,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与董其昌书道:“何日得把臂挥麈,共探玄旨耶?”同年又作书云:“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18)其情谊相尚,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袁宏道更是对董其昌推崇备至,将其与唐宋大家王维、苏东坡比配,他在《答董玄宰太史》中说:“不佞尝叹世无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骚雅,书苑画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苏玉局(轼),而摩诘无临池之誉,坡公染翰仅能为枯竹巉石。不佞将班足下于王、苏之间,世当以为知言也。”不仅着意于其诗书画兼擅的文艺才能,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誉。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认为董其昌的“兼才”正是清除复古诗学流毒的关键,他进一步申说:“楚中文体日弊,务为雕镂,神情都失,赖宗匠力挽其颓。”(19)为什么袁宏道如此看重董其昌于诗书画上的兼才并能呢?这是因为书画艺术对公安派的诗学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引导启发作用。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在《叙竹林集》里明确提到了董其昌对自己的影响: 往与伯修过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画苑诸名家,如文征仲、唐伯虎、沈石田辈,颇有古人笔意不?”玄宰曰:“近代高手,无一笔不肖古人者。夫无不肖,即无肖也,谓之无画可也。”余闻之悚然曰:“是见道语也!”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是故减灶背水之法,迹而败,未若反而胜也。夫反所以迹也。今之作者,见人一语肖物,目为新诗,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规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嗟夫!是犹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谓之蔡中郎,岂不悖哉?(20) 这是公安派一篇言辞颇为激烈的反对复古模拟的诗学檄文,由董其昌的画论导引,遍称文徵明、唐寅、徐熙诸位画坛名家,其取意于画学思想,可以说确凿无疑。值得注意的是,师法对象的选择是画学史上恒久的命题。唐代张璪的《历代名画记》首先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21)的主张,范宽承其绪云:“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22)明王履在《画概序》中则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23)董其昌进一步言:“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24)由此可知袁宏道诗论“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之渊源所自。袁中道的题画诗也表现了与之相似的看法,其《西山图》云:“爽气果然佳,终朝看不足。何如貌此山,岚雾指中出。”(25)即谓不师古而强调师法自然的重要性。明代画学思想中重天然的新鲜因素,正是公安派所看重的地方,而“以不法为法,不古为古”的诗学主张的提出,则意味着师法对象的转移最终契合了公安派通变求新的文艺观。袁宏道在《诸大家诗文序》中说:“夫沈之画,祝之字,今也;然有伪为吴兴之笔,永和之书者,不敢与之论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也;然有伪为古钟鼎及哥、柴等窑者,不得与之论轻重矣。何则?贵其真也。今之所谓可传者,大抵皆假骨董赝法帖类也。彼圣人贤者,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以彼较此,孰传而孰不可传也哉?”(26)便含有重视当下即是真艺术,学习古代即是伪作品的求新求变思想。在《小陶论书》中,袁宏道记陶望龄之弟陶奭龄与友人论书,陶曰:“公书却带俗气,当从二王入门。”友人对曰:“是也。然二王安得俗?”陶曰:“不然。凡学诗者从盛唐入,其流必为白雪楼;学书者从二王入,其流必为停云馆。盖二王妙处,无畦径可入,学者摹之不得,必至圆熟媚软。公看苏、黄诸君,何曾一笔效古人,然精神跃出,与二王并可不朽。昔人有向鲁直道子瞻书但无古法者,鲁直曰:‘古人复何法哉?’此言得诗文三昧,不独字学。”(27)“白雪楼”借指李攀龙,“停云馆”借指文徵明,二人各于诗书方面为一时复古大家,这里所谓“二王妙处”是讲“无法自得”,在古人面前凸显自我精神面貌的书学真谛。因此由书论到“诗文三昧”,其实是讲反对模拟,求变于自我,与袁宏道“以不法为法,不古为古”的诗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袁宗道亦持类似的看法,认为:“模拟文字,正如书画赝本,绝难行世。”(28)他在《顾仲方画山水歌》里说:“吾观仲方画,不从诸家入,亦复不从十指出,直是一片豪性侠气结为块垒,以酒浇之不能止。忽尔进散落缣素,偶然浓淡分山水。”(29)另外,与公安三袁交往颇深,往往被引为一派的江盈科、汤宾尹亦从绘画书法中求得新变的诗文观。江盈科《求真》云:“善论诗者,问其诗之真不真,不问其诗之唐不唐,盛不盛。盖能为真诗,则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不能外。……盖凡为诗者。或因事,或缘情,或咏物写景,自有一段当描当画见前境界,最要阐发玲珑,令人读之,耳目俱新。譬如写真传神者,不论其人面好面丑,黑白胖瘦,斜正光麻,只还他写的酷像……何也?写真而逼真也。”(30)汤宾尹《徐见可鸠兹集序》谓:“吾尝以此论书论文,法无外者。世人每见人书,不省美恶,辄问某帖某帖,见人诗文,缪相推拟,曰若也周秦,若也汉魏六朝,若唐若宋。於乎!周秦之与唐宋,其代既已往矣,帝自为统,人自为氏,则胡不曰若明诗明文,而反借于异代?”(31)同样是将书画与诗并论。 诗学取法于书画,已经成为公安一派的约定共识。总之,公安派诗论由“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师心说,到“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的取法自然说,以及“代有升降,而法不相延”的变通思想,这些前期核心性诗学观念的形成受到书画艺术的启发和影响,展现了一种新的诗学批评视野。 二 诗歌风格的书画境界 在诗学观念受到书画理论影响的同时,书画境界对公安派诗学风格的形成也有所启发。公安派的诗学风格往往被批评者斥为“俗陋”“入于俳谐”“戏谑嘲笑,间杂俚语”,是对白居易、苏轼诗风的继承,虽说稍有偏激之嫌,不过整体看没有太大的疑问。但是,如果我们要做进一步细致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诗风实际上包含有自然和平淡两部分。其中信口信手的自然诗风鼎盛于前期,后期亦多有继承,一般被认作公安派的标志诗风。但随着袁宏道思想的变化,特别是袁中道的主盟,不加修饰的平淡诗风得到有意的凸显。上述公安派诗风的形成与其对诗书画艺术融合的追求有着一定关系。这是因为,自然与平淡都是庄禅的境界,更是以此境界为根基的书画品格。公安派诗风均是以此为基石生发的。 自然的风格在性灵思想那里源自于对趣的追求。趣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术语,到了有明一代,更是掀起了有关诗趣的文艺主张,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即有“诗以趣为主”(32)的著名论断;但袁宏道等人所追求的诗趣则带有很强的书画特质,意在强调趣于诗书画不同艺术体裁之间的融会贯通。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认为:趣产生于人的自然本性,是真性情的表达,所谓“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如果主体有所欲心,即便是对书画艺术的涉猎也仅仅是趣之皮毛而已,“何关神情”(33)?与之相似,江盈科也认为:“若系真诗,虽不尽佳,亦必有趣。”(34)可见,真趣是公安一派的共同主张。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把趣分成了三个品级:上乘、无品与下品。就这三品而言,上乘的“婴儿”与“赤子”在现实中不可求,而无品中的山林之人和下品中的酒肉、声妓之徒在袁宏道看来则可以达到,这便促使趣在现实祛伪过程中对不合常规、脱尘脱俗特质的着意彰显,具有了书画逸品“不拘常法”的特点。故袁宏道称趣又作“异人之趣”讲,其《纪梦为心光书册》云:“枝山书法,为当代第一,文彩风流,辉映一世,至其一诙一笑,有晋人风。骚坛之士,传为口实,米颠而后,一人而已。余尝论古人,如东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苏子瞻辈,皆实实知道,而画苑书法,下至薄技能之人妙者。若其资非近道,技与神卒不相遇。夫画如吴如顾,书如王如旭辈,岂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远。同者既不能相远,则其远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异乎人者矣,是以谓之异人也。”(35)这些书画大家一般都被公认为逸品的典范,袁宏道所强调的诗书画文艺创作要达到与天道合一的真趣境界则又暗合逸品“得之自然”这一层含义。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就以二米为例说:“画家以神品为宗极,又有以逸品加于神品之上者,曰失于自然而后神也。……士大夫当穷工极妍,师友造化,能为摩诘而后为王洽之泼墨,能为营丘而后为二米之云山。”(《画禅室随笔校注》,第137~138页)进而言之,公安派强调诗趣的书画特质,实际上是更多着眼于书画的庄禅境界,这是诗书画神理相通的理论基石。袁宏道对庄子独有心契,非常向往老庄境界中的散木状态。他在为周生题跋《清秘图》时说:“不才之木,得子而才,故知匠石不能尽木之用。嗟夫,岂独木哉?世有拙士,支离龙钟,不堪事务。头若齑杵,不中巾冠;面若灰盆,口若破盂,不工媚笑;腰挺且直,足劲而短,不善曲折,此亦天下之至不才也。而一入山林,经至人之绳削,则为龙为象,为云为鹄,林壑遇而成辉,松桂荫而生色,奇姿异质,不可名状,是亦生物之类也矣。”(36)至人对散木的挖掘来源于庄学理论,实际上只有以“无用之用”的眼光看待畸人拙士,才是对天道真正的体悟。所以说袁宏道笔下的散木又何尝不具有逸品风格呢?袁宗道则有题画咏竹诗云:“风竿不满尺,以饶千丈势。高僧礼诵余,味此萧萧趣。”(37)亦强调以庄禅玄心,即虚静状态观竹才能体味到其蕴含的“萧萧趣”。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路,公安派又将趣称为“天趣”,更能体现趣的本体内涵。袁宗道《答陶石篑》云:“坡公自黄州以后,文机一变,天趣横生,此岂应酬心肠、格套口角所能仿佛者乎?”(38)屠隆《论元画》云:“评者谓士大夫画,世独尚之,盖士气画者,乃士林中能作隶家,画品全法气韵生动,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39)文人画自王维始就强调“迥出天工,笔意纵横,参乎造化”,用天眼胸次表现自然景物。这也就是说,艺术家只有在天趣的观照下,才能创作出符合自然法则的尚真艺术。故此,袁宏道在《识雪照澄卷末》中独拈深谙文人画趣的苏轼时云:“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儿弄丸,横心所出,腕无不受者。公尝评道子画,谓如以灯取影,横见侧出,逆来顺往,各相乘除。余谓公文亦然。其至者如晴空鸟迹,如水面风痕,有天地来,一人而已。”(40)又《长卿内子无如氏绣佛及诸人物行楷精绝诗以记之》云:“白描设色种种工,活夺龙眠与松雪。横见侧出灯取影,有意无意鸿没灭。”(41)均出自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以画喻诗说。与袁宏道交往颇深的汤显祖在《合奇序》中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不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象宛然。”(42)则是对袁宏道取意苏轼思想的进一步补充。可以说,公安派对具有自然风格诗歌的追求正是在老庄境界下、诗画融合基石上展开的。 淡则表现为通过对色彩修饰的摒弃、达到自然天成的艺术效果,被公安派推崇为“真性灵”。所谓“醉后书颠如长史,老来诗淡类斜川”(43),袁宏道后期对此多有阐发,他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说:“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惟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惟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44)顾恺之与吴道子是青绿着色法描绘人物与山水的代表,通过对他们的否定,袁宏道所谓“淡之至”指的是水墨渲染法的艺术效果。他的《为杨粉暑题小像》诗云:“高人气韵不在似,如写寒松与花卉。宽眉廓额信手涂,疏淡只似铺山水。”(45)以及《刘常侍水轩》诗云:“墨光浓淡里,山水赵吴兴。”(46)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袁中道有着与其兄相似的看法,更是这一话题的主要阐释者。他反复用绘素来比拟诗歌,例如在《程晋侯诗序》中说:“诗文之道,绘素两者耳。三代而上,素即是绘;三代而后,绘素相参。盖至六朝,而绘极矣。颜延之十八为绘,十二为素。谢灵运十六为绘,十四为素。夫真能即素成绘者,其惟陶靖节乎?非素也,绘之极也。”(47)又《于少府诗序》云:“诗之为道,绘素已耳,三代而上,绘即是素;三代而下,以绘参素。至六朝,绘极矣,而陶以素救之。近日文藻日繁,所少者非绘也,素也。”(48)推崇以素为质的诗歌,并将其演化为诗史认识。故此他极其反对金碧辉煌的大青绿画法,而倾向于水墨画法,并进而及于诗文。其《马远之碧云篇序》云:“夫画家重逸品,如郭忠恕之天外澹澹数峰是也。世眼不知,乃重许道宁辈金碧山水,不亦谬乎?吾观远之之文……比之忠恕之画,气类自同。今欲取合世眼,降格作宁辈浓腻之笔,吾固知远之不为。”(49)如同袁宏道所谓的“真性灵”一样,袁中道也认为淡是“从肺腑中流出”。故此公安派所谓诗学中平淡的风格何尝不是对绘画水墨渲染法的崇尚与继承,从而赋予了诗歌一种笔墨氤氲的艺术风格呢?总之,自然平淡的诗歌风格与书画的真趣、淡色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公安派从前期到后期在诗学风格上的创新所在。 三 诗歌创作中的书画技巧 除了受到书画理论和书画境界的影响而显现为诗歌外在审美追求与形态的转变外,公安派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597~1608)期间还力求从书画的笔墨技巧入手,寻求内在诗艺的开拓创新,这恰巧和诗学理论、诗学风格受书画艺术熏染的时间段相吻合,正是其激变期的关键环节。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论述宋诗鄙陋时指出了一种拟古的现象,师法陶渊明的陈渊“一眼望出去都是六七百年前所歌咏的情景”,他的“心眼给陶潜限制的很偏狭”(50)。公安派摆脱复古的束缚,投入到山水的怀抱中,但是他们满眼望见的多是书画的景致,常以有形的笔墨写出无声的诗歌。这种取法于书画艺术的创作实践贯穿于公安派前后两期,从共时性的维度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画面空间感的凸显,分布于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1598~1608)之间的诗作。公安三袁很少有对绘画作品进行直接题咏的题画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山水景物看作纸上图画的现实幻化,从而赋予诗歌很强的画面空间感。如袁宏道《王丞相邀饮阳和楼》:“十丈朱旗照水殷,家家箫鼓乐江山。千峰如画供杯酒,不道清时是等闲。”(51)《丁未初度泊池阳,自寿,兼忆李安人》:“溪头微雪点疏松,睡起开窗对远峰。谁写画图来寿汝,谢家江上九芙蓉。”(52)《舟中逢周行可》:“君是滕元发,长舠破浪来。入群瞻岳岳,顾水影髟髟。黄石曾窥奥,稠林每乱才。通侯画地取,筠管亦何哉?”(53)《灯下观菊花影,同社中诸友赋》:“墙颓生画意,蛇断晤颠书。离即成三昧,超超实起余。”(54)如是等等。写实景如同写画景,咏诗歌好像在绘图形。山水之外,他们亦有对花草绘画式的传写,如袁宏道《赋得朱华冒绿池》:“曾见云锦光明地,花采虽繁无生气。又见杨妃出浴图,未离宫粉香奁意。花意高洁水清冷,色态两绝非浓腻。坐看风晓月斜时,柳妥烟沉天欲醉。不放玻璃光潋滟,高窗低箔如茜染。”(55)《小竹林腊梅盛开,兼呈主人》:“顿绝水沉粗,幽香袭一湖。瘦枝梅韵格,鲜蕊桂肌肤。月下高真梦,烟中静女图。”(56)以及袁中道《冬日湖上》:“委练重桥接,烟云画不成。”(57)总之,诗无形而成象于吟咏之间,具有了造型艺术的立体特征。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诗歌图画的选取往往落入前人经典的窠臼,拓展了诗歌用典的范围与方式。如袁宏道《十二月十八日至蕲阳,舍舟从兴国走咸宁,道出金牛镇,山路如刀脊,飞雪侵肤,舆人艰窘几不能步。然千峰微雪,或如鸦鵛,或如积琼,亦行役之一快也。道中随事口占,遂得十六绝句》(其十二):“峰峰雪点缀,曲曲水苍寒。却似曾经眼,王维画上看。”(58)《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赋》:“湖光摇碧柳拖黄,青带何妨尚缟装。似与夭桃添粉泽,聊同飞絮关轻扬。……拟写烂蕉深雪里,怕人误作辋川庄。”(59)又袁中道《赠鲁印山》:“秋来浓月上高梧……竹里辛夷浑在眼,不须重画辋川图。”(60)乃借用王维《雪里芭蕉》《辋川图》等画作。又如《食笋,时方正月》(其六):“苦将墨派染龙孙,只写萧萧个字繁。寄与湖州文与可,袜材争似买盘飧。”《竹香》(其二):“削尽秾华是此君,碧栏银沼醉氤氲。全凭出格幽微韵,体出无声太古文。定里只消风引月,梦来惟觉水依云。袜材写尽湖州派,清冷知他闻不闻。”,(61)乃借用文与可画竹法。再如袁宏道《刘常侍水轩》(其一):“入室翠层层,秋容分外澄。花分西内种,树古北朝僧。……墨光浓淡里,山水赵吴兴。”(62)则借用赵吴兴画法。这种引画理入诗歌的行为使诗歌具有了新鲜形象的画面感,同时也必然造成诗歌描写技法上的转变,在公安一派那里表现为赋予诗法以绘画的笔墨技巧。 第二,笔墨技巧的运用,散见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1597~1607)间的作品。绘画中的笔墨技巧主要体现在,通过笔与墨的变换配合,用水墨渲染法来展现所描摹的对象,其所用的墨分为浓、淡、干、湿、黑、白六彩,所用的笔又分为筋、肉、骨、气四势。分别用来进行图画的施色与造型。公安派的诗法便蕴含了这样的笔墨技法,从而赋予了性灵诗学一种崭新的特质。我们先说墨,绘画之墨可以通过干枯浓淡来区分阴阳远近,饶自然总结墨法道:“墨者远淡近浓,逾远逾淡,不易之论也。”(63)公安派的诗歌便多用墨法来塑造景物的远近。袁宏道的《集平山堂用平山字为韵,偕游者方干、两谢生也》诗云:“斜桥与废水,淡墨有无山。”(64)《柳浪馆》诗云:“凿窗每欲当流水,咏物长如画远山。”(65)又《集元定行记斋记再赋得原字》诗云:“幽弦清入涧,淡墨远成村。”(66)袁中道的《江午》:“山色本宜远,坐来玩山色。水生却宜近,两耳声瑟瑟。……远山能磨墨,何必入法工。”(67)又《艳歌》:“霄台可扶杖,远山可磨墨。”(68)袁宗道亦有此类写法,其《斋中独坐》:“云根披远画,竹韵谱新琴。”(69)诗歌中写山云与村庄的方法,如同画家用墨之浓淡以区分远近,饶有山水画的趣味。此外,他们还善于运用浓墨来写云。袁宏道《夏日刘元定邀同顾升伯、沈仲润、李长卿、丘长孺集城西荷亭是日热甚得暴雨乃解》谓:“黑云蟠墨湿崔嵬,雨头未展风脚回。羊角直上旋飞灰,鸣阶稀点大如杯。”(70)袁中道《偶过侯师之园逢唐君平》云:“云生千嶂墨,风到万人喧。”(71)墨湿而浓,赋予了诗歌笔下乌云立体的空间效果。我们再说笔,画笔的运用在公安派诗法里主要表现为通过位置的经营获得飞动的气势,达到所谓“气韵生动”的画学效果。其实袁宏道审美日常化的生活中已经刻意体现出了这点,他的《五宜称》中讲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72)。空间的营造中凸显出灵活生动而不呆板的美学特质。我们且看其在诗法中是如何实践的。其描写泉水滞涩,曰:“一片青石棱,方长六大字。何人妄刻画,减却飞扬势。泉久淤泥多,叶老枪旗坠。纵有陆龟蒙,亦无茶可试。”(73)画学中所说的泉包括“湍而漱”的“涌泉”与“水石泼而仰沸”的“喷泉”(74)两种,皆具有流动喷薄之势,故饶自然论“绘宗十二忌”就有“水无源流”条:“画泉必于山峡中流出……平溪小涧,必见水口。寒滩浅濑,必见跳波,乃活水也。间有画一折山,便画一派泉,如架上悬巾,绝为可笑。”(75)袁宏道所称的“刻画”即是指缺少“飞仰势”,是死水而非活水也,正与绘画所要求的一一契合,可见其写水完全是从画论视角出发着笔的。 第三,逸笔草草的传神技法,集中于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1600~1604)的诗作。上述以笔墨技巧贯注于诗法的行为更多地是着眼于诗画技法上的融合,使诗歌具有绘画图物写貌的高超能力。这突出体现为袁宏道等人赋予诗歌一种由书画品第中的逸格向书画笔墨技巧中的逸笔升华,并最终具有文人墨戏的特点。袁宏道《服卿访余柳浪不遇,俟我沙头,既归,服卿再至,遂用韵赠之》:“逸格临杯见,新思入路微。云山心总在,未与宿根违。”(76)《梅花》:“瘦枝逸格总天真,不属东风旖旎尘。尚有腊梅不佞幸,可无修竹作同人。花前乍许孙登啸,座上唯容靖节巾。”(77)对隐逸的强调都突出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的逸格要求。但是逸格不仅仅体现在对高蹈绝尘艺术风格的追求,从“笔简形具”的角度来说,更是强调一种倪瓒与徐渭式的“逸笔草草”技法的掌握,要求诗歌具有绘画略形传神的特质,所谓“咏物写生同一肖,不貌而工神已足”(78),这便上升到画论形神之辨的高度。形神之辨是历代绘画理论中的惯常话题,自从宋代开始,对形神不同的偏重便成为了文人画与匠人画之间的重要区别。苏轼即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的著名论断,便是标榜重神弃形的文人画主张。袁宏道继承文人画传统,亦持这种看法:“画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亲而近俗,工意者远而近雅。”(79)而这几乎成为了公安三袁的共识,袁宏道在《题潘稚恭小像》诗中说:“当年曾见虎头真,长短浓纤各有神。”(80)袁宗道的《顾仲方画山水歌》诗云:“俗眼赏鉴皆如此,不重真骨重形似。”(81)袁中道《作字》亦云:“我字不入法,聊恣一时戏。……作诗惟伫兴,作字亦任意。未当强心为,虽拙大有致。”(82)那么他们是如何在诗法中贯彻绘画的工神技巧的呢?袁宏道的《看梅》诗云:“自剥青苔自扫尘,仙径沉缕对幽人。不须更画维摩诘,恰有梅花为传神。”(83)便是运用了简略物象寥寥数笔的文人墨戏法。而与欧阳修《盘车图》所谓“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84)同一意趣。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公安派诗学不仅仅是反拨明代复古诗学流弊的结果,更是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诗学发展中崭新的变化,书画艺术往往就是容易被忽略掉的那一环。可以说,书画艺术确认和冲击了公安派的核心性诗学观念,影响了他们诗学风格的形成与变化,更赋予了诗歌创作一种新的书写技巧。明代诗歌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最为薄弱的环节。钱锺书先生便给宋元明清的诗歌排了个座次:“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宋诗选注》,第10页)这其实代表了一般研究者对明诗的成见:明诗与宋诗、清诗自不敢攀,就是在“元诗浅”面前也低人一等。但相反的是,明代人却自我感觉良好地夸口说:“明风启而制作大备。”(85)其正是着眼于明诗在历时积累方面的成就,即所谓:“明不致工于作,而致工于述,不求多于专门,而求多于具体,所以度越元、宋,苞综汉、唐也。”(《诗薮》,第1页)明诗的这点成就却为研究者所忽视,更不用说从共时维度考虑,求新变于书画的公安派诗歌显示出了明诗的一种别体风貌,可谓是继宋诗在唐诗高峰开拓后的又一次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们研究明代诗歌史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道释思想与阳明心学对公安派的影响偏重于人格心态的形成与人生观的塑造,并由此过渡到诗学观念,故多是间接推导而非直接类比。即使明确如“诗理入禅参”“将禅比诗不争多,色里胶青水中味”“每与诗外旨,悟得句中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五《又次前韵》,中册,第837页;卷一二《西林庵为从石上人题》,上册,第127页;卷九《潘庚生馆同诸公得钱字》,上册,第385页)的说法,也是倾向于人生境界与哲理意蕴,同时涉及一些诗学审美风格的问题。相比较而言,师法渊源对公安派诗学风格和技法的影响就更为直接明显。钱谦益说:“(袁中道)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66页)袁宏道《赠王以明纳赀归小竹林》:“销心白傅诗,遣老白公偈。”(《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六,中册,第662页)从中均可看出,虽说公安派诗学是很多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的文学现象,但与上述因素相比,书画艺术与其诗学的关系同属审美范畴而较为明确和直接,且包含了诗学观念、境界与创作三方面以及出位之思的文艺现象,也更为全面与独特。总之,可以帮助我们对公安派诗学作进一步挖掘。 ②《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二《夜坐读少陵诗偶成》,中册,第1049页。 ③《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二《送蕴璞之通州》,中册,第535页。 ④《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答人》,上册,第225页。 ⑤《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九《和萃芳馆主人鲁印山韵》,中册,第942页。 ⑥黄庭坚著,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卷一六《戏赠米元章》,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册,第563~564页。 ⑦江盈科《江盈科集·雪涛阁集》卷八《敝箧集引》,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册,第275页。 ⑧《江盈科集·雪涛阁集》卷八《锦帆集序》,第2册,第277页。 ⑨《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九《徐文长传》,中册,第715页。 ⑩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册,第1341页。 (11)《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冯侍郎座主》,中册,第769~770页。 (12)《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答梅客生开府》,中册,第734页。 (13)《徐文长传》,《徐渭集》,第4册,第1344页。 (14)《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二《答徐见可太府》,下册,第1248页。 (15)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页。 (16)袁昂《古今书评》,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册,第390页。 (17)《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孙司礼》,中册,第746页。 (18)《袁宏道集笺校》卷六《董思白》,上册,第273、289页。 (19)《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二《答董玄宰太史》,下册,第1266~1267页。 (20)《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叙竹林集》,中册,第700~701页。 (21)张璪《历代名画记》,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22)范宽《宣和画谱》卷一一,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2册,第361页。 (23)王履《华山图序》,《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707页。 (24)董其昌著,屠友祥校注《画禅室随笔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95页。 (25)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八《西山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416页。 (26)《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诸大家诗文序》,上册,第185页。 (27)《袁宏道集笺校》卷一〇《小陶论书》,上册,第472页。 (28)袁宗道著,钱伯诚标点《白苏斋类集》卷一六《答陶石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页。 (29)《白苏斋类集》卷一《顾仲方画山水歌》,第5页。 (30)《江盈科集·雪涛阁四小书》,第2册,第700页。 (31)汤宾尹《睡庵稿》卷一《徐见可鸠兹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3册,第23页。 (32)《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一《西京稿序》,下册,第1485页。 (33)《袁宏道集笺校》卷一〇《叙陈正甫〈会心集〉》,上册,第463页。 (34)《江盈科集·雪涛阁四小书》卷四,第2册,第705页。 (35)《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一《纪梦为心光书册》,下册,第1223页。 (36)《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识周生清秘图》,上册,第196页。 (37)《白苏斋类集》卷六《题双寺画竹》,第77页。 (38)《白苏斋类集》卷一六《答陶石篑》,第234页。 (39)屠隆《画笺》,《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第122页。 (40)《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一《识雪照澄卷末》,下册,第1219页。 (41)《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五《长卿内子无如氏绣佛及诸人物行楷精绝诗以记之》,下册,第1313页。 (42)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卷三二《合奇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1077页。 (43)《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七《又赠朗哉,仍用前韵》,下册,第1383页。 (44)《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五《叙呙氏家绳集》,中册,第1103页。 (45)《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三《为杨粉暑题小像》,中册,第575页。 (46)《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四《刘常侍水轩》,中册,第607页。 (47)《珂雪斋集》卷一〇《程晋侯诗序》,上册,第470页。 (48)《珂雪斋集》卷一〇《于少府诗序》,上册,第471页。 (49)《珂雪斋集》卷一〇《马远之碧云篇序》,上册,第482页。 (50)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页。 (51)《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七《王丞相邀饮阳和楼》,下册,第1384页。 (52)《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六《丁未初度泊池阳,自寿,兼忆李安人》,下册,第1364页。 (53)《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五《舟中逢周行可》,中册,第856页。 (54)《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二《灯下观菊花影,同社中诸友赋》,中册,第1029页。 (55)《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六《赋得朱华冒绿池》,下册,第1338~1339页。 (56)《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一《小竹林腊梅盛开,兼呈主人》,中册,第974页。 (57)《珂雪斋集》卷一《冬日湖上》,上册,第37页。 (58)《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六《十二月十八日至蕲阳,舍舟从兴国走咸宁,道出金牛镇,山路如刀脊,飞雪侵肤,舆人艰窘几不能步。然千峰微雪,或如鸦鵛,或如积琼,亦行役之一快也。道中随事口占,遂得十六绝句》(其十二),下册,第1368页。 (59)《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三《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赋》,中册,第1062页。 (60)《珂雪斋集》卷三《赠鲁印山》,上册,第138页。 (61)《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七《食笋,时方正月》,中册,第902页;卷三〇《竹香》,中册,第988页。 (62)《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四《刘常侍水轩》,中册,第607页。 (63)饶自然《绘宗十二忌》,《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695页。 (64)《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六《集平山堂用平山字为韵,偕游者方干、两谢生也》,下册,1361页。 (65)《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五《柳浪馆》,中册,第842页。 (66)《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五《集元定行记斋记再赋得原字》,下册,第1328页。 (67)《珂雪斋集》卷二《江午》,上册,第72页。 (68)《珂雪斋集》卷二《艳歌》,上册,第85页。 (69)《白苏斋类集》卷四《斋中独坐》,第33页。 (70)《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五《夏日刘元定邀同顾升伯、沈仲润、李长卿、丘长孺集城西荷亭是日热甚得暴雨乃解》,下册,第1334页。 (71)《珂雪斋集》卷三《偶过侯师之园逢唐君平》,上册,第93页。 (72)《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四《五宜称》,中册,第822页。 (73)《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二《白乳泉》,中册,第524页。 (74)韩纯《山水纯全集》,《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665页。 (75)饶自然《绘宗十二忌》,《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696页。 (76)《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一《服卿访余柳浪不遇,俟我沙头,既归,服卿再至,遂用韵赠之》,中册,第1023页。 (77)《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二《梅花》,中册,第1055页。 (78)《袁宏道集笺校》卷三〇《看梅,用前韵》,中册,第977页。 (79)《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二《风林纤月落》,中册,第1040页。 (80)《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二《题潘稚恭小像》,中册,第550页。 (81)《白苏斋类集》卷一《顾仲方画山水歌》,第3页。 (82)《珂雪斋集》卷三《作字》,上册,第106页。 (83)《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五《看梅》,中册,第832页。 (84)欧阳修著,李逵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盘车图》,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册,第99页。 (85)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标签:公安派论文; 袁宏道论文; 董其昌论文; 徐渭论文; 诗歌论文; 书法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书画论文; 袁中道论文; 复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