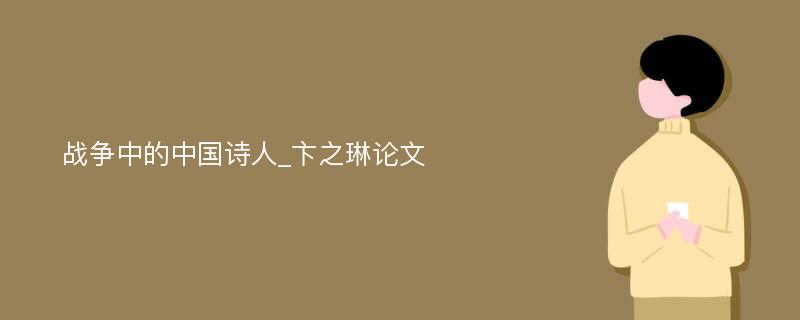
一个中国诗人在战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中国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像一个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
从热闹中出来闻自己的足音。
——卞之琳:《归》①
对于认识卞之琳的人来说,世上最奇怪的事莫过于看见他——我们过去习惯称作好孩子的人——在战时出现。他身材短小瘦弱,看起来弱不禁风,一副厚厚的眼镜后面闪动着浅灰色的眼睛,他的声音微弱,表情迷茫,让你有置身九霄云外之感。他的整个外表和本质及其诗中的幻想情调,会一同造就如下印象:他一定是世上最不堪这场战争的狂暴风云一击的。可是,他就这么出现了,以战时诗人的身份出现了,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战时诗人,完全无愧于这个名号。不过,也不要认为战时诗人就一定是以笔为枪去战斗,言辞轰轰如发射子弹一般。想象一下吧,狂暴的海水侵蚀着巨大的礁石,一只白鸽就在海水中经受着冲刷。白鸽最容易受到狂暴海水的伤害,可是它依然以最为从容的姿态振动它那雪白的翅膀,不因喷溅的浪花而受挫。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一个诗人就该像这样。
不过,也别再弄错。卞之琳并非隐逸诗人,根本不是。相反,他是最早前往中国西北的人之一,并在那里加入了游击队。他书写这场战争,整个被这场战争激发起来了。
也许这么说是合理的:在过去的十二年,每个年轻的中国诗人都不得不成为一个战士,并不一定是成为政治或革命中的战士,而是为了他自己的个性而战。战前,因为政治和精神的混乱,也因为腐败和狂热的信仰,一个诗人同时还不得不成为自己的守护天使,总是提心吊胆以免跌倒。今天,所有的伤痛、商业化的风气(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以及战时“服从的需要”都并不一定使得中国的美好大地成为诗的沃土。还必须加上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白话对于这些诗人战士来说,是一件正当的然而用起来仍不够顺手的武器。一个诗人若不能成功地创造出独特技术,那就没有希望赢得他的战斗。卞之琳就属于那少有的几个坚强面对这些困难的人。他从未因这些困难而失去自我,相反,他克服了所有困难,每次都有进步,自我更为丰富同时又保持不变。
在我编选的那本《中国现代诗选》(与哈罗德·阿克顿合作译为英文,1936年出版)中,有关卞之琳的自传文字如下所述:
卞之琳,1910年生于江苏省。1929年进入国立北京大学学习欧洲文学,1933年毕业。读本科期间,他对波德莱尔和法国象征派很有兴趣,主要是就技巧而言。……他的语言才能令他能以流利的白话表达自我。他的风格以极为直白、具有自然节奏和有效使用口语而著称。
天才是个用起来非常模糊的词。就卞之琳而言,我们可以说,正是他熟练掌握的独特技巧,天生的诗感以及独立的个性才使得他成为一个杰出的诗人。
卞之琳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关注到它了。下面这首诗写于北平陷落前的一年,表明了日本人占领的满洲地区那些“长城外的旷野”是如何已经不祥地打动了他的诗之想象:
长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
可是我们却一声不响,
走着,走着……
走了多少年了,
这些影子,这些长影子?
前进又前进,又前进又前进,
到了旷野上,开出长城去吗?
仿佛有马号,是一大队骑兵
在前进,面对着一大轮朝阳,
朝阳是每个人的红脸,马蹄
扬起了金尘,十丈高,二十丈——
什么也没有,我依然在街边,
也不见旧日的老人,两三个
黄衣兵站在一个大门前,
(这是司令部?当年的什么府?)
他们像墓碑直立在那里……②
不过,卞之琳的诗中并无政治口号。他认为中日战争是强加在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头上的,反过来中国人民也会对其做出勇敢的回应。不过,他从未拥有其他中国作家那种可以称为“无产阶级对抗性”的情绪。不管怎么说,他不是那种在一个宏伟远景的世界中迷失自我的诗人。他坚守着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下面这首《断章》就很能说明问题,它暗示了诗人的隐秘观点: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③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已是五年前了。他去了游击区,走了很远很广的路,如同一个灰色的小点匆忙穿行于崇山峻岭,在危险的浪潮中航行,如同风暴中一片飘飞的叶子!他一定是随着团队行走。不过他不像任何其他的人和事。他一直都是那个叫做卞之琳的诗人,不同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一切。他加入那个艰难旅程并非出于想要战斗或是前往“青年圣地”朝圣的汹涌激情。他虚弱得连枝枪都扛不动。他的“组织能力”几乎为零。站起来做演讲,从未有过的事!他很清楚,战争中他只有用他的诗才能做出最好的贡献。因此,他寻找着诗,坚守着自己的诗意视角,就在他置身的这个地方,最为凶险的战斗在打响,社会重建工作也依靠着发挥到极限的人类智慧在展开。他寻找诗,他也在这里找到了诗,正如他无论去何处都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所寻找到的。
就像一个灵巧的画家,可以在任何画布上作画但总能施以自己最具特性的美妙笔触,他的写作也是如此。他所写的每首诗都是有关战争的,每一首都充满了亲切的同情,雅致的幽默,温和的笑声,这些就构成了这场战争中中国人这一方最为微妙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状态,这些也只有卞之琳这样的诗人能够看清并充分地加以表现。他是以自己天生的诗人魅力和敏锐感受来写作,非常好地运用了中国口语的自然节奏。没有哪一首诗带有激情澎湃的色彩,甚至都没有任何对于爱国情感的抽象表达。他的这本小册子让人联想到契诃夫那本具有启示意义的《札记》,这位俄国大师在这本书里写道:“我相信单个的人,我在散居各处的个体——无论他们属于知识阶层或是农民——身上看到了拯救,他们是强大的尽管为数很少。”卞之琳写的也都是个人,中国那些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的男男女女。他从游击区出来时完成了一个集子,二十首诗,长短不一,标题包括《给一位刺车的女子》(为了阻止一个年轻人临敌逃跑),《给随便哪一位神枪手》,《给一位夺马的勇士》,《给实行空舍清野的农民》,《给卖笑的献金者》等等。这个战时的诗集1940年在昆明出版,是一个小册,名为《慰劳信集》。
几乎不可能将这些诗令人满意地翻译成英文。不过,由于下面的翻译主要是为了展示卞之琳独特的诗感和他独有的描写战时主题的方式,所以我使用的是一种直白的“洋泾浜英语”,接近于中国的口语。原诗中的语言节奏和自然韵律很大程度上也就不得不牺牲掉了。下面就是《给随便哪一位神枪手》的第一节:
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后,
你看见的,如果你回过头来,
胡子动起来,老人们笑了,
酒窝深起来,孩子们笑了,
牙齿亮起来,妇女们笑了。④
《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真实地表现了中国工人活干得很好并且热爱这个工作。最后的一个字“干”,这个字曾用在Rey Scott的中国电影《苦干》中,它的意思是“努力奋斗”:
母亲给孩子铺床总要铺得平,
哪一个不爱护自家的小鸽儿,小鹰?
我们的飞机也需要平滑的场子,
让它们息下来舒服,飞出去得劲。
……
我们有儿女在华北,有兄妹在四川,
有亲戚在江浙,有朋友在黑龙江,在云南
空中的路程是短的,捎几个字去罢:
“你好吗?我好,大家好。放心吧。干!”
更为典型的诗是《给实行空舍清野的农民》:
家禽家畜都不会埋怨
重新过穴居的生活。
谁说忘记了一张小板凳?
也罢,让累了的敌人坐坐罢,
空着肚子,干着嘴唇皮,
对着砖块封了的门窗,
对着石头堵住了的井口,
想想人,想想家,想想樱花。
下面这句是严峻的,揭示了从长期的苦难中所学会的简单的民间智慧:
忧虑是多余了就是快慰⑤
卞之琳非凡的“诗意想象”和他“远取譬”的能力赋予这些书写普通主题的诗以灿烂的魅力。下面这两行只是一个例子:
夜摸的时机熟透了,
像苹果快要离枝。⑥
这本诗集中最重要的诗之一是献给蒋介石的,标题很简单,《给委员长》。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人对于中国人民意味着很多事情,这是西方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中国人支持他并非因为他代表了任何政治体制——因为严格说来也并没有——而仅仅因为他们知道不能没有他。他们崇敬他是出于那种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的对于家庭的忠诚。今天的中国人最害怕的不是任何政治变动,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而是委员长的过世。也许这听起来像是毫无必要的忧虑,因为他本人身体状况还很好,不过,这些年的艰难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衰老的印记,只会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激起温柔的感激和悲伤之情。郭沫若,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和小说家,据称他曾经被蒋介石驱逐到海外,他在战时的1937年回到了中国。在与蒋介石会谈后,他写道:“我感觉委员长的手。很温暖。如此温暖而有力。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两颊红润。当时我对自己说,‘中国仍旧有着伟大的未来’。”正是这种真正的“家庭”忠诚,人际之间的这种深厚感情,超越了所有政治冲突和个人仇怨,使得中国在他的领导下有力地团结起来。卞之琳这首诗,是他在游击区时写的,代表了中国的这一颗心:
给委员长
你老了!朝生暮死的画刊
如何拱出了你一副霜容!
忧患者看了不禁要感叹,
像顿惊岁晚于一树丹枫。
难怪啊,你是辛苦的顶点,
五千载传统,四万万意向
找了你当喷泉。你活了一年
就不止圆缺了十二个月亮。
你一对眼睛却照旧奕奕,
夜半开窗无愧于北极星。
“以不变应万变”又上了报页,
你用得好呵!你坚持到底
也就在历史上嵌稳了自己。
卞之琳如今在四川的一所大学教书。他离开中国西北的游击区的原因经常引人猜测。有人说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有人说是因为那里的“舆论氛围”仍旧遵循着激进路线,使得“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根本就是个谬论,另外有些人则会说四川和延安一样,都很适合他。所有这些也许是真的——或者没有一个是完全真实的。即使现在有人告诉我,卞之琳正在南极,和企鹅们在一起,或是寄居在高加索,我都不会太惊讶。因为他从不属于任何地方。他总是一个人,但从不孤独——从不,因为他的缪斯女神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满是“强大的个体”和奇妙的变迁。就在那副厚厚的眼镜后面,他一直是观察整个宇宙的“天文学家”,他清楚地听到他“自己的脚步声”。
(原载《亚洲》(Asia)1942年8月号)
注释:
① 诗句原文据《鱼目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从注释2起均为译者注。
② 《西长安街》,诗句原文据《三秋草》,上海新月书店,1933年版。
③ 诗句原文据《鱼目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
④ 诗句原文据《慰劳信集》,昆明:明日社出版部,1940年版。以下所引该集诗句皆同。
⑤ 此句出自《给地方武装的新战士》。
⑥ 此句出自《给一位特务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