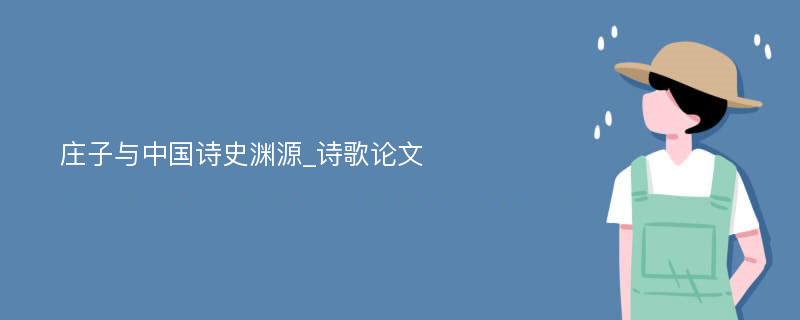
《庄子》与中国诗史之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庄子论文,中国论文,之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考察了《庄子》与中国诗史的关系,文章认为:《庄子》的审美情感开拓了诗的疆域;庄子创造了丰富的意象、全新的意境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庄子》的艺术精神超越了同类文化典籍,足以与《诗三百》、《楚辞》鼎足而三;以《庄子》为中心形成了道家诗学体系;《庄子》在塑造中国古代诗人心态,建构诗人人格模式,规范诗歌创作流向诸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庄子》是中国诗史之一源。
关键词 诗史之源 神美情感 诗学体系
何谓“诗史之源”?本文认为,可称为诗史之源的文本,当具备下列因素:一,该文本形成于民族文化的发韧期。在中国,即是先秦时代;二,必须是诗歌总集或是具备诗歌艺术特质的文化典籍。如果是后者,它必须具备同类文化典籍所缺乏的艺术特质,而其艺术特质能够填补诗歌总集艺术建构方面的空白;三,以它为中心,形成了一种美学诗学体系;四,此文本不是一个静态的标本,它能够以顽强的生命力与巨大的渗透力引领后世诗人心态的走向,规范后世诗歌艺术精神的流程。以下的讨论即据此展开。
一
虽然《庄子》中有一些语句整饬而又押韵的章节,《大宗师》、《人间世》、《知北游》中皆有诗意盎然的直接标明为“诗”与“歌”的段落,然而,从整体上看,《庄子》毕竟是间有韵语的散文。如果诗必须要有整齐的句式、和谐的韵语,那么,《庄子》不是诗。幸而,这只是诗的表层形式。诗,还有诗的深层形式,还有诗之魂。
“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1]若无真情灌注的诗,纵然精工,终如纸花,缺乏生气。《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一部《庄子》处处充溢着这种精诚之情。
韦勒克、沃伦说过:“历史上确曾有过哲学与诗之间真正合作的情形,但这种合作只有在既是诗人又是思想家的人那里才可以找到。”[2]在中国诗史上庄子是第一位将哲学诗化的哲人。作为哲人,庄子对自己建构的哲学体系充满了深情。对其哲学最高范畴“道”的描述、对其理想人格“真人”、“神人”、“圣人”的描绘,无不倾注了宗教般的热忱。在他的笔下,“神人”们“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大宗师》)此神人真人是宇宙的精华、天地的英灵。从形体到精神莫不符合美的标准、诗的神韵。庄子并不因倾心于形而上的“道”而遗忘了人间世。所谓诗人就是关注人生,热爱生命,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人。庄子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诗人。他说:
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徐无鬼》)
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比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山木》)
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则阳》)。一个无情之人,难以有如此细腻的情感领悟,难以有这种心灵的悸动。只有眷恋人生、珍视生命的诗人才能将远离家园、远离亲人、漂泊无依的悲哀感和盘托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是庄子体认到生命短促而又无可奈何的哀叹。惠子,是庄子的论敌,又是他的挚友。他们曾共同游乐、相互争执、甚至势不两立……随着惠子的去世,这一切都成为永久的回忆,留给庄子的是无尽的哀伤: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殷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殷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石匠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
这是诗人的伤逝,这是哲人之间的友谊。真情厚谊,感人肺腑。钟向知音,人亟称之;庄惠之交,世所罕言。真正的友谊,不仅在于理解,其实启迪友人的灵感,撞击友人思想的火花,尤为重要,尤为难得。也许,这样要求太过苛刻,因为庄惠之交,千载而下,惟此一度。解牛之庖丁、承蜩之佝偻、斫轮之轮扁、运斤成风之匠石……因了《庄子》的缘故,进入了文学的殿堂。是的,《孟子》中亦有揠苗助长的宋人(《公孙丑上》)、乞幡之齐人(《离娄上》),《韩非子》中亦有酤酒之宋人(《外储说右上》)、鬻盾矛之楚人(《难一》)等等,也写到了下层人物,但后者多是被嘲笑的对象或者只具有工具价值。不似庄子用真情肯定他们的品质、赞赏他们的技艺。《庄子》之情,弥漫人寰,也弥漫自然。从天体的运行、四季的推移到鱼之乐、蛙之惊、螳螂之怒……庄子无不作了细致地观察。庄子把自己的身心安置于自然之中:或与友人漫步濠上,观赏鱼游之乐;或与弟子穿越山林,讨论材与不材;或垂钓河畔,思悟人生至理……他说:“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焉!”(《知北游》)至此,大自然已成为诗人完整的审美对象,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浑然如一。
庄子立足于自然的尚情论以及他对人间世、对自然、对其哲学境界的深情,犹如一阵春风,吹入被儒家道德说教所笼罩的诗坛,这是一场诗界的革命。因之,古人云:庄子是“最近情的人”(林云铭:《庄子因》卷一),是“最深情的人”(方以智:《药地炮庄·庄子论略》)。闻一多先生云:“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诚哉,斯言!
情感并不等于诗,只有运用一定的艺术形式(如意象,意境,格律……)将情感予以艺术的再现,才能形成诗。贯通整个中国诗史而看,意象的创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意境的类型上,庄子除了创造了许多社会意象、心理意象外,着力创造了一批具有象征性的自然意象。譬如《齐物论》中栩栩然飞翔的“蝴蝶”、万窍怒号的“大块噫气”等等,此处的蝴蝶与风,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蝴蝶和气象学意义上的风,而是诗的蝴蝶,诗的风,只能用审美心态去体味去把捉。庄子笔下的动物植物无不浸透了诗的色彩,从不同的角度象征着庄子的哲学范畴。这些意象作为一种意象原型被长期沿用。仅“蝴蝶”意象就被诗人化用为:庄周化蝶,庄周梦蝶,庄周蝴蝶,蝴蝶庄周,蝶化庄生,栩栩蘧蘧,蘧蘧栩栩,梦蘧蘧,蘧蘧梦,蝶蘧蘧,蝴蝶梦,梦蝴蝶,蝶梦,梦蝶,化蝴蝶,化蝶,蝶化,蝶与周,蝶为周,周为蝶,漆园蝶,南华蝶,庄蝶,庄生蝶,庄叟蝶,枕蝶,蝶入梦,庄周梦,庄叟梦,庄梦,梦栩栩……。庄子意象的主要特征是采用夸张性变形性意象。写大时则曰:“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逍遥游》)“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外物》)写小时则曰:“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角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写肢体的变形则曰:“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肋。”(《人间世》)王国维云:“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其实,即使在南人中,庄子亦是独一无二的。其文“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宣颖:《南华经解·庄解小言》),创造出一系列丰富而鲜明的意象。是故,有人誉庄子为“第一位创造意象的大师”,[3]不是没有根据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将意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我对峙;无我之境以物观物,物我两忘。庄子哲学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之境,又可称为“吾ˉ我”之境。“我”指偏执的我,斤斤计较于一己得失的我,蔽于成见同于流俗的我,物与我相互对立的我。只有消解这样的“我∷椰才能进入“天地与我并啥,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澄明境界。从美学诗学的角度看,这是审美的境界,是诗化的境界。它既是诗论史上“无我之境”理论的发源地,又是诗歌史上“无我之境”的首次呈现。同时,“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具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是庄子。”[4]
庄子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庄子中,既有昆仑神话系统的产品,也有蓬莱神话系统的产品。……如果说,它借助昆仑神话表现出从现实社会超脱到天国、自然之中的观念行为,呈现出磅礴雄伟的气势;那么,它借助蓬莱神话则表现出‘逃遁’心灵、静心养气的观念行为,呈现出淡漠超然的气势。这两种风格分别成为古典浪漫主义全部作品的风格基础。”[5]甚至,有人认为屈赋中并没有真正的浪漫主义,代表中国浪漫主义审美理想的真正源头的只有《庄子》。[6]是不是可以作这种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至少可以肯定《庄子》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源头之一。
概之,《庄子》的情感溢出了伦理道德的堤坝,为诗歌创造开辟出新的天地;庄子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意象意境,开创了浪漫主义风格。从本质上看,庄子是一位“天生的诗人”,《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
二
《庄子》的艺术精神和艺术价值远远高出于同类文化典籍。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和法家认为审美与艺术不具有直接的功利作用,从而漠视忽视艺术的价值。此处略而不论。对中国艺术精神发生根本性影响的只有儒道两家。孔子作为塑造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巨人,同时亦具备诗人气质,其“吾与点也”的潇洒情怀即为明证。不过,他更多的关注于社会伦理道理规范,更多的投身于平治天下的事业。因而,与其说他重视诗歌,不如说他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他明确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诗歌只具有“兴”“观”“群”“怨”四种社会作用,他还规定了“思无邪”、“中庸”等审美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他的诗学理论从属于他的社会人生哲学体系。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孟子和提出了“诗以言志”的荀子,继承了孔子诗学精神,对文艺社会功用的强调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原始儒家的不懈努力,使中国诗歌从先秦时代开始,便与国计民生、政治教化紧密绾结。从文学的角度看,《孟子》亦具备较强的艺术性。孟子讲究知言养气,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其人充满了浩然之气,孟子其文亦充满了浩然之气。而且,孟子亦善于借助譬喻说理。与《庄子》相较,《孟子》的气势更充足,结构更完整,条理更清楚,说理更充分,逻辑性更强。也就是说,正因为如此,《孟子》更接近典型的议论文。
《周易》的封爻辞是上古时代最早见之于文字的歌谣,其中个别歌谣已具备优美的韵律,但它们还达不到“诗”的标准,最多只能算是一些不成熟的诗。倒是其中一些概念(如“神”“意”“象”等),因在客观上与审美思维和艺术精神相通,对诗学史有一定影响。
老子是道家的始祖,他的哲学体系以“道”为最高范畴,他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直接启迪了庄子思想,同时,《老子》一书文采斐然,有比兴手法、有形象描绘、有强烈的情感,并且,其句式、韵律更接近于诗歌形式,被人称之为“长篇哲理诗”。然而,从思想体系上看,《老子》思想属于社会政治学说,他依据“反者道之动”(《老子·三章》)的原理,设计出“无为无不为”的以反谋正之术。难怪《汉书·艺文志》称其为“君人南面之术”。汉初以黄老之术并称,不是偶然的。而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境界,“庄子思想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7]从艺术手法上看,“《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之妙,得于《诗》”(吴世尚:《庄子解》)。《易》之“象”并非诗歌的意象,而是由“—”“_”两爻叠加组合的符号。《老子》的“象”亦是比较抽象的。虽然,《老子》中有“车辐”、“户牖”等具体物象,有“犹之,若畏四邻”(《三十一章》)等新颖的喻体,不过,与《庄子》丰富的意象清晰的意境相较,《老子》尚停留在简单的比附阶段。二者虽不能说有霄壤云泥之隔,却分明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
概之,在先秦文化典籍中,《庄子》具有同类文化典籍所不具备的诗歌艺术特质。
三
《诗》、《骚》是诗歌总集,但它们决不单纯是诗歌总集,可以说以它们为核心凝成了中国诗学史上的两大重要的体系:儒家诗学体系和楚骚诗学体系。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当忽略:诗学史上还有另一种重要体系——道家诗学体系,《庄子》则是道家诗学体系的核心,它具有《诗三百》和《楚辞》无法替代的诗史价值。
《诗三百》与《庄子》、《楚辞》的区别甚为明显。一是产生时代不同。据考证《诗三百》中最晚的一篇是《陈风·株林》,它形成于公元前600年或前599年。而屈原则诞生于前340年,相差二百余年。庄子生平难考,学界认为他大约与孟子同时,略早于屈原。这一推论当是基本可信的。二是文化背景不同。《诗三百》基本属于北方的中原文化系统,而《庄子》《楚辞》主要反映的是南方荆楚文化系统的特色。三是作者的哲学素养不同。英国学者柯勒律治说:“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伟大的诗人。”先秦时代,只有庄子和屈原可以称为伟大的诗人。四是庄屈之“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上天入地,神游八极,情思飘逸的浪漫主义特色。《庄子》中的意境前已指陈。仅就屈原作品中的诗境而言,其诗中有苍梧、县圃、白水、阆风、昆仑、西极、流沙、赤水、不周等神奇之地,有羲和、望舒、飞廉、丰隆、雷师、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等神人。他将遥远的上古神话传说、虚幻神秘的楚地巫风以及诗人超群出众的想象力揉合起来,建构成一幅幅浪漫神奇的艺术画卷。他所选择的意象、组接的意境源于现实合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神奇而不怪诞,夸张而不变形,迷离而不恐怖。这种对个体心灵情感世界细致深刻的描绘,对超现实世界的神奇的勾勒,在《诗三百》中是找不到的。《诗三百》则是典型的现实型文学。现实型文学即是以侧重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通读《诗三百》不难发现它以日常人生为写作素材,以人间世为抒情对象。在这里有社会政治秩序之乱与治,有国计民生之利与病,有社会风气之好与坏,有君臣朋僚的往来,有双亲妻子的聚离散合,有男女间的痴恋与绝情,有孤儿弃妇的哀吟,有山川景物建筑工艺的描摹……。诗人所歌咏所展现的是有哭有笑、有声有色的人间生活,其中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在依依杨柳间行进的士卒,在故国宗庙宫室之遗址抒发黍离之悲的大夫,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露”的秋天追寻理想的士人,在桃花盛开的季节走向新生活的少女……时隔千载之后,今天读来,依旧清晰,依旧亲切。五是作品篇幅的长度不同。《楚辞》多是长篇巨制,《天问》三百七十多句,二千五百多字;《离骚》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屈原博大精深的思想、上天入地的神思、忠而被谤的怨怼,非借助宏篇巨制难以抒发。但这种鸿文长篇在中国诗史上所占比例很小,中国古代诗歌大都是数十句甚至八句四句的篇幅短小之作。这一传统无疑始于《诗三百》。《诗三百》的语言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颂”诗中只有个别篇章以杂言为主,“风”诗中杂言化倾向较为明显。
庄屈同是晚周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自其同者而言之,“二子皆才高而善怨者,或至于死,或迫于无所有之乡,随其所遇而变耳。故二子所著之书,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其宏逸变幻,亦有相类。”(陈子龙:《谭子庄骚二学序》)自其异者而言之,则“庄骚实二,不可以并”(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原始儒家讲究修齐治平,与屈原同。屈原继承了儒家忧国忧民的情怀,自觉承担起历史的重荷,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然孔孟荀皆以天下之士自许,并不独钟情于故国。屈原在接受原始儒学基本思想的同时,“受命不迁”,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向故国,自愿与故国共存同亡。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一种新形态的文化的精神。为了这种文化精神他甚至选择了放弃生存。当屈子在汨罗江畔举身赴水之时,中国诗史上崛起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伟人。他的精神、他的情操、他的人格与日月共存!屈子之情充塞八极、弥漫寰宇。他为战乱漫延,民不聊生而悲:“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他为楚国君王而悲:“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为自己的理想无由实现而悲:“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与悲相对,屈原还喷吐了自己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产生了怨怼之情。他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反复无常的楚君:“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其次,他怨恨精心培养的人才的变节:“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他尤愤恨奸佞党人的嫉贤妒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屈原对人民、对故国的爱与对君主的怨对奸邪小人的恨是同一情感的一体两面。与屈子那殉道的精神和献身的热忱不同,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他淡泊功名,志在山林,趣入皋壤,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性的解放,庄子的人格是一种独立型人格,他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一方面坚守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批判社会现实,同虚伪的礼教作不妥协的斗争。庄子的人格境界对后世士——诗人之人格建构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个“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一个“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时”(《缮性》)。尽管同样值得敬之重之,却分属两种情操类型、两种人格模式。此其一也;
屈子“这种激情的倾诉,表现了一个自我生命存在的历炼与挣扎;因此,自我性的突显,可以说是《楚辞》文学的特征。”[8]这与《庄子》的追求恰恰相反。故《楚辞》多“有我之境”,《庄子》多“无我之境”。此其二也;
《诗三百》中的比兴是自由随意的,到了屈原时代,他将比兴固定化,并形成了一个比兴系列,如此则更能突显比兴的审美作用,使比兴走向深入,走向系统化。屈原扩大、深化了《诗三百》比兴意象,“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文选·张衡〈四愁诗〉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比兴结构,而庄子意象却更为庞杂奇诡不拘一格,没有固定的格式。此其三也;
屈子虽然上游天庭,下穷九泉,他的心却始终不曾忘怀故国,忘怀民众。其诗歌意象属于政治伦理之载体。这与儒家诗教有扣合之处,而与庄子将审美情感倾注于永恒的自然大异其趣。故清代学者刘熙载认为:“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艺概·诗概》)。此其四也。
庄屈分野,判若鸿沟。
显然,《庄子》自有其独特的诗史价值。不是《诗三百》和《楚辞》所能替代的。先秦时代《诗》、《庄》、《骚》相继崛起,如同三条粗大的根系,共同支撑起中国诗史的参天大树。
四
无论共时性的考察还是历时性的探究,都不难发现,中国诗史的肌体内始终流淌着《庄子》的血液。
两汉是一个诗思消歇的时代。汉代儒士采用断章取义的诠释法,先变《诗三百》为“经”,继而,又变《离骚》为“经”,扼杀了《诗三百》和《楚辞》的生命力,把它们制作成僵硬而贫血的政治标本,至于《庄子》则被他们久久的遗忘了。直到汉末魏初才有了根本的转变。汉魏之际《诗》、《骚》、《庄》的诗史位置得以确立,并呈现三源合一流的趋势。其中,《庄子》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一到魏晋间,庄子的声势突然浩大起来,……庄子突然占据了那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9]由于庄子思想和艺术精神的博大无涯,魏晋诗人对《庄子》的认同体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为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
《古诗十九首》以其“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陈绎曾《诗谱》)突破了《毛诗序》“诗言志”的藩篱,大胆的将朋友阔绝,男女相思,叹老嗟卑、知音难遇,逐臣失意之情写人诗中。稍后,建安诗人进一步开拓了“真情”、“至情”的范畴,使诗歌与人类情感紧密扣合;在特殊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代诗人,其人生追求往往与政治、社会、仕途、功名联系在一起,限于主客观因素,个人的期望常常会遭到挫折,或者完全落空。有时不仅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甚至会有性命之忧。一代天才曹子建就是这样,他后期生活,名为藩王,实同囚徒。理想的失落,生命的变幻莫测,使他自觉地投靠《庄子》,沉浸于《庄子》的士大夫人格境界以消解生命的悲剧意识。庄子思想与中国失意士人的全方位结合,当始于此。此后,庄子思想便成为历代失意、潦倒之士的精神避难所。正始时期,阮籍、嵇康以老庄为师,用自然对抗名教,在王弼何晏正始玄学之外别开竹林玄学一途。嵇康“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逍遥,阮籍“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的悲怆,与庄子精神遥相呼应。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诗人继承了庄子批评黑暗现实,冲决封建礼教罗网,向往精神自由境界的思想和行为;晋宋玄言诗,“诗必柱下之指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直接将老庄义理用韵语排列。玄言诗之衰亡与《庄子》的兴盛,雄辩地说明:诗之所以为诗,在于诗之魂,不在于诗的外层形式;晋宋之际陶渊明因时局险恶,壮志难酬,毅然挂冠归去,隐居浔阳,躬耕垄亩。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纯真人格,“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之情,“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怡然自得,无不与庄子的思想境界和艺术精神妙合无垠。稍后,谢灵运在青云失路后,寄情山水,写出了大批山水诗。庄子之后,将自然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行观照,进而创立田园诗派山水诗派,是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功绩。从此,湖光山色、林泉籁韵作为新的美感范畴全面进入了诗史领域。如此,庄子终于一步一层占领了中古诗坛。徐复观先生说:“在庄子以后的文学家,其思想、情调,能不沾溉于庄子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属于陶渊明这一系统的诗人中,更为明显。”[10]诚如斯言,即以伟大诗人李白、苏轼而言,古人早已指明:“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刘熙载:《艺概·诗概》)太白东坡二人豪放旷达的性格,傲岸不羁的人格,浪漫神奇的艺术境界与《庄子》密不可分,因二人气质经历、处世方式的不同,其诗文又各具特色。大体说来,太白更多地接受了庄子“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的天真”,而东坡则更多地继承了庄子“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11]天真者多沉溺于幻境,多自信自负,多放浪形骸,多奔放之激情,故常常放声歌唱:“大鹏一日随风起,扶遥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怅惘者则多忧患意识,多理性的思索,多人生无常的慨叹,故时时咏叹:“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迁居临皋亭》);“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过滩》);“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郁孤台》)……,在艺术表现方面,太白喜欢用纯朴天真的诗情、夸张变形的意象,袒露强烈的主观情感,“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东坡则在飘逸洒脱、自然流传的同时,擅长于细致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如导师说天上妙谛,如飞天仙人下视尘界”(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显然,二人从精神、人格到创作个性、诗歌风格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庄子思想境界、艺术特质的熏陶。从对魏晋诗坛和陶李苏三大诗人的析论中,可以看出庄子艺术精神渗透于一部中国古代诗史。而以上论述尚未包括《庄子》对中国古代文论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当《诗三百》成为历史的绝唱,当《楚辞》的魔笛尚未奏响,诗歌那寂寞的天宇突然间响彻了天籁之声,这就是《庄子》。《庄子》的审美情感开拓了诗的疆域;庄子创造了丰富的意象、全新的意境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庄子》的艺术精神超越了同类文化典籍,足以与《诗三百》、《楚辞》鼎足而三;以《庄子》为中心形成了道家诗学体系;《庄子》在塑造中国古代诗人心态,建构诗人人格模式,规范诗歌创作流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下发展。”[12]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庄子》是中国诗史的三大源头之一,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注释:
[1]《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庄子》(以下简称《古典新义》),三联书店,1982年,第282页。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第119页。
[3]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10页。
[4]《古典新义》,第289页。
[5]张碧波、雷啸林:《试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诸问题》,《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
[6]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第312页。
[7]《古典新义》,第208页。
[8]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篇·意象的流变》,三联书店,1992年,第33页。
[9]《古典新义》,第279页。
[10]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11]《古典新义》,第281页。
[12]郭沫若:《今昔蒲剑》,海燕书店,1949年,第288页。
标签:诗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庄子论文; 文化论文; 老子论文; 读书论文; 离骚论文; 屈原论文; 孟子论文; 楚辞论文; 国学论文; 知北游论文; 古诗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