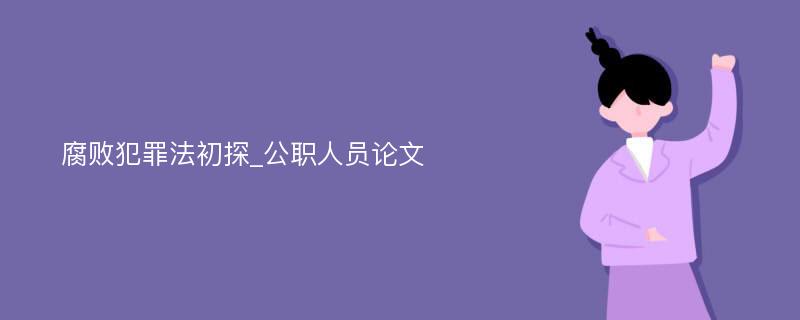
贪污犯罪规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由于这种犯罪在犯罪主体上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特定性,在犯罪属性上具有以权谋钱的滥权性,在犯罪心理上具有求无厌足的贪婪性,在犯罪对象上具有损害国家物质基础的公益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这一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中外历史事实说明:轻者,表现为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腐蚀公职人员队伍,损害国家机关声誉,败坏社会风尚,诱发各种犯罪。重者,表现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结构式腐败,甚至导致整个政权肌体的腐朽堕落,亡党亡国。所以,贪污犯罪是弄权谋利的政治腐败现象的重要表现之一。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国家公职人员要追求物质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中大多数人能把自己的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少数人则会走上铤而走险,践踏法律,贪婪无度的犯罪道路。更由于贪污犯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无本万利”的获利行为,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刺激性。所以,贪污犯罪就成了历代统治者禁而不绝的痼疾。
贪污犯罪虽然是难治的“痼疾”,但它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探索这个历史时期中贪污犯罪的规律,对于预防与惩治贪污犯罪,促进廉政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
起伏规律,也称升降规律。贪污与其他犯罪一样,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呈现时起时伏、时主时低的规律。
(一)贪污犯罪起伏演绎的梗概
从新中国成立46年来的反贪史看,大体上是一个马鞍型的起伏态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为贪污犯罪的一个高峰期。建国之初,由于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公职人员中,留用了大批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其中一些腐朽贪婪恶习深的人,便利用新政权刚刚摧毁旧法统、新法规尚不健全的时机,与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相勾结,大肆进行侵吞、盗窃公共财产的贪污活动。有鉴于此,我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4 月2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反贪污为主要内容的“三反”、“五反”斗争,严惩了数以万计的贪污分子,枪毙了象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那样极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犯,击退了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取得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
1957年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贪污犯罪的低谷期。这个时期是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全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公职人员清廉从政风尚良好,刑事犯罪明显下降,贪污犯罪的发案率极低,没有大的起伏,一般年份的发案仅有二、三千件。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属于非正常状态,没有可供分析的可靠资料,故不列入研究范围。
1976年至1994年,是贪污呈波浪式上升期。这十多年来,是我国深入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变动、大发展时期,各种犯罪亦呈上升态势(改革前年发案率一般是3—5件/万人,个别年份6件/万人; 而现在一般是5—7件/万人,高的年份达8—9件/万人),其中贪污分子钻新旧体制转换的法律不完备的空子,大肆进行侵吞、盗窃、骗取、私分公共财产的活动。这个时期的贪污犯罪与过去的贪污犯罪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一是犯罪总量呈波浪式的上升趋势,平均年侦破贪污案件均为1万件以上,多的年份达2万件以上,较之我国过去的低犯罪率相比,已是成倍的增长;而个案的贪污数额,较之过去更是数倍、数十倍的增长。海口市一银行会计贪污案,数额竟达3344万元。二是贪污手段呈多样化、智能化趋势。有的地方统计,贪污手段多达40余种。利用电脑贪污,从无到有,现在已不罕见。特别是一些公职人员钻法律的空档,走政策的边缘,制造模糊性行为,混水摸鱼,猖狂侵吞公共财产的事件突出。三是犯罪对象呈复杂化趋势。经济体制改革前,公共财产存在形式单一,侵犯行为易于认定。改革后的各种经济联合体、承包体、中外合资、合作体的财产公私交织,界限难分,性质难定。四是犯罪主体呈广泛化趋势。过去的贪污分子多为直接管钱管物部门的人员,而现在则波及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员;过去贪污分子多为管钱管物中有经验的中、老年人员,而现在则多是中青年,甚至有参加工作仅二、三月就贪污数万元的胆大妄为的青年;过去贪污分子多为掌管财物的一般工作人员,而现在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的领导干部也不少。
(二)起伏规律的诱因与抗制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看,贪污是一种非法图利的行为。一个公职人员是否要铤而走险去贪污,至少取决于下述四个要素:一是贪污可能获益与受损的预期比例;二是贪污得逞条件的多少;三是贪污后可能被揭露的概率;四是惩罚的严厉程序。这就是说,凡是诱发贪污犯罪的因素强、犯罪条件好、被揭露的概率小,贪污犯罪就会活跃起来,反之,贪污活动则会有所收敛。由此可见,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最终取决于贪污犯罪的诱发因素与对贪污犯罪控制因素的强弱对比。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强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上升态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与控制贪污的因素势均力敌时,贪污犯罪就会呈现平缓而无大起大落的态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弱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现下降态势。
当前,我国还处在诱发贪污的因素强于控制贪污的因素的时期,故贪污犯罪仍呈现波浪式的上升态势。
贪污诱发力增强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物俗充分解放,“一切向钱看”观念普及人心,加之社会分配不公,诱发和刺激了利用职权贪财的动机;
其二,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经济运作机制与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与玩忽职守普遍,“小金库”林立,真空和漏洞随处可寻,利用权利攫取财物的机遇增多;
其三,执法水平、侦查装备、办案经费不能适应与贪污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犯罪成本少而得逞率高,破案率低而“风险小”,强化了这种“无本万利”的贪污犯罪的吸引力。
贪污控制力减弱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立法滞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联合、承包、租赁、金融、证券、竞争等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型侵吞公共财物的行为,又缺乏法律规范,界限模糊,性质难定,客观上放纵了贪污蔓延;
其二,政治思想工作虚化,一些公职人员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失去了精神抗体,追求“高消费热”、“攀富热”,成了“无官不贪”意识的俘虏;
其三,社会综合治理不落实,“唱功好,做功差”,没有把政治、经济、监督、惩罚等各方面的抗制贪污的措施形成合力,预防犯罪的疏漏太多,失控面太大。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基于上述两种因素力量对比而出现的贪污发案率较高(相对于过去的低发案率而言)的态势;这是合符事物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原理认为,一种运行模式向另一种运行模式迁跃的社会转型期,必定有一个“磨合”过程。只有“磨”才能“合”。磨合是在动态中进行的,“磨”的过程会有一定的“振荡”和“痛苦”,要付出一定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贪污发案率低,并不能证明体制就好,经济发展就快,贪污发案率相对较高,并不能证明体制不好,经济发展会慢。我国改革,开放前贪污犯罪少,而经济发展缓慢,而现在却相反,这就是一个历史见证。作者在这里并不是主张贪污越多越好,而是说明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并不是政治、经济体制是否优越的表现,而仅是诱发贪污犯罪与控制贪污犯罪两极因素的循环的态势,不断强化控制贪污犯罪因素,削弱诱发贪污犯罪因素,按照两极循环服从优势的规律,就能达到预防与减少贪污犯罪的目的。所以,降低贪污犯罪率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综合治理,减少贪污发生的条件,使欲行贪污者在获益率极低、受损率极高的现实面前怯步。
二、贪污犯罪的辐射规律
贪污犯罪,自古有之。贪污发生的地区和部位,则是相对的。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贪污辐射规律,是指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这个特定时期贪污犯罪走向的轨迹。
(一)贪污犯罪的部门辐射规律
所谓部门辐射规律,就是指贪污活动在不同系统、行业中的运行轨迹。我国司法部长肖扬在研究贪污贿赂犯罪的部门流向规律时指出:大致是“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社会服务性事来部门→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行政性公司→经济监督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与党委机关”。〔1〕
近十多年来,我国贪污犯罪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其“源头”始于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的公务人员受“物质诱因”的影响最为直接,利用职权攫取公共财物的机遇最多,加之,在新旧体制转换中,经济秩序不很稳定,对生产经营部门监督机制相对弱化。故在80年代初期,这些部门的经理、厂长、会计、出纳、采购、销售、供应人员中贪污犯罪突出,成为贪污犯罪的“重灾区”。紧接着,贪污“风潮”波及的是与生产、经营部门密切相关联的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逐步走上了有偿服务,讲究经济效益的轨道,作为社会的利益主体之一的服务部门,便受到生产、经营部门相同的“物质诱因”的刺激,成为继生产、经营部门之后的贪污犯罪的多发部位。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在某些方面具有严重“短缺型”的特点。而管理这些短缺的生产资料和其它生产要素的部门,便成了需求者的“上帝”,为竞争“紧缺物资”、“短线产品”和生产要素而各显神通、不择手段,甚至金钱、美女都给“霸主”献上,在监督不严,防范不力的情况下,这些部门必然会滋生更多的贪污犯罪分子。
接下来贪污辐射对象便是对生产、经营和服务性事业单位的活动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经济监督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然后再逐渐渗透到司法机关和党委机关。贪污犯罪为什么要辐射到执法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这是社会分配不公和部门比较利益均衡化的必然结果。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收益丰厚,而另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收益低微,无论这种收益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只要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就必然会导致相互攀比,并千方百计向追求利益均衡化的趋向发展。要实现利益均衡化,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人权、物权、财权、司法权去捞钱,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恶性膨胀。这些部门贪污犯罪的蔓延,便是采取非法手段妄图实现利益均衡化的一种表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司法权。司法权的行使,是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颁布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为依据的,所以,司法权是最具有代表国家意义的神圣权利。但是,近年来贪污犯罪无孔不入,某些司法机关公职人员手中的司法权的商品化,已经使这一神圣的国家权力蒙受了玷污。这标志着腐败现象已经辐射到了很深的层次。
党委机关是领导机关,既是距离“物质诱因”最远、可供利用贪污的条件最少的系统,又是抵御腐蚀“免疫力”最强、监督机制比较完备的部门。但是,近年来在追究物质利益“大潮”的袭击下,在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刺激下,利用手中的管理指挥权而捞钱者已不乏其人,甚至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也有“湿脚者”。这个最后一道防线的被突破,也是贪污“辐射线”向纵深渗透的结果。
(二)贪污犯罪的地域辐射规律
所谓地域辐射规律,就是贪污犯罪发生地区的运行轨迹。肖扬部长在研究犯罪的地域运行轨迹时说:“开始是较多、较早地出现于沿海地区,继而向内地移动,最后连一些边远地区也呈现出犯罪人数多、犯罪数额大、犯罪手段狡诈诡秘的趋势。通常,在沿海地区新出现的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经过一定时期会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出现。”〔2〕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这是由于沿海地区交通方便和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所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首先是从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在广东省推行,然后逐渐发展到整个沿海地区,再逐步向内地和边远地区辐射。
我国经过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墨守成规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如何指导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新的经济秩序和法制应如何建立?商品经济消极因素的影响如何预防与控制?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逐步探索。
沿海地区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猛异常,推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众口一辞的。与此同时,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愿望强烈,贪污犯罪的“物质诱因”和“精神诱因”增多,么职人员利用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真空与漏洞进行贪污犯罪的也就相应增加。这与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地辐射一样,贪污犯罪也就像瘟疫一样,由沿海向内地和边远山区辐射。
贪污的地域辐射,总的特点是无不打上市场经济的烙印,其具体表现为:
一是贪污发案率和贪污数额的幅射。80年代初,沿海地区的贪污犯罪发案率比内地高,更大大地超过边远地区,而后内地则迅速增加,最后连一些边远地区、甚至穷困地区的贪污犯罪也愈来愈多;前几年贪污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特大案件,一般都发生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而现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贪污案也屡见不鲜,甚至一个乡镇企业、一个村也发生几万、几十万的特大贪污案。
二是贪污部位的辐射。贪污的部位取决于经济机制的规范程度和对经济的控制与监督程序。传统的贪污犯罪,多发在管线、管物的部位,而现在则主要是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经济热点领域辐射。改革、开放中,新的经济领域拓展到哪里,贪污分子的触角便伸向哪里。如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高科技市场的不断兴起,由于这些市场资金投向集中,利润丰厚,惹人眼红。有的钻政府职能转变的空子,或者利用经商办企业的机会直接控制这些经济热点领域获利,把权力直接商品化;或者通过提供咨询、沟通信息、索线搭桥以及祝贺剪彩等形式获利,把权力间接商品化。
三是贪污主体的辐射。贪污主体辐射内容,主要表现是:改革、开放之后,公有财产存在形式的复杂化、多样化,相应地使贪污犯罪主体多元化;传统的单个的小量侵吞、盗窃、骗取公共财产的贪污行为,已为现代贪婪性、冒险性极大的贪污分子所不取,故目前内外勾结、上下串通、跨单位、跨地区、跨国界的呈现蜘蛛网状的群体犯罪大量增加;法人和其他组织,打着“为公”、“为集体”、“为单位”利益的旗号,利用职权敲、卡、勒、诈公共财物,到处私设“小金库”,化公为私,集体私分。
四是贪污手段的辐射。改革、开放后的贪污手段与传统贪污手段相比,突出的特点是更加隐蔽化和智能化。通常在沿海地区新出现的新的贪污手段,经过一个不长的时期就必然会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出现。
三、贪污犯罪的黑数规律
犯罪黑数,亦称“犯罪隐蔽数”,“犯罪暗数”、“犯罪潜伏数”,其基本含义都是指实际已经发生,但在正式的犯罪统计中没有反映出来的犯罪数字。
原西德的孔德·凯塞尔,在研究“犯罪的隐蔽数字”时说:“从很早以前开始,科学家就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官方已知的犯罪情况与实际的犯罪相符合的程序究竟如何?”即“已经暴露出来的犯罪和未暴露出来的犯罪之间的关系”。他在测算70年代西德的犯罪隐蔽数字时指出:“西德每年犯罪数量应当在400万件左右这个范围内”, 而“每年警察局只揭露出120万嫌疑者,其中38万人被判刑”, “已经登记的盗窃犯罪和盗窃犯罪的比例已从1∶2发展到1∶5。〔3〕美国米切尔I·凡茨尔在研究美国“犯罪的测量”问题时说:“也许被我们查明的犯罪活动最多只占整个犯罪活动的50%,而这些查明的案件中,也可能仅有一半被正式报告到警察局”。〔4 〕我们虽然无法考证他们所论证的黑数的大小是否科学,但至少说明犯罪黑数是一个客观存在。
根据一些国家学者总结的经验,犯罪黑数的规律是:黑数程度的高低与人们感觉到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成反比。社会危害性越明显的犯罪,犯罪黑数越低;社会危害性越不明显的犯罪,犯罪黑数越高。原苏联B·K茨维尔布利说:“一般说,潜伏程度越低,这类犯罪的社会危险程度就越高。如杀人罪和重伤罪,潜伏性的指数几乎等于零,而对于某些类型的渎职罪,根据抽样数据,潜伏指数则达7%~53%”。〔5〕
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贪污犯罪的黑数规律,就是指的检察机关对贪污案件的侦破数与实际发生的贪污案件数量之间差距的情况与特点。
我国的贪污犯罪是否存在黑数?回答是肯定的。这个黑数与实际侦破数的比例有多大,目前尚没有精确的数据可供推算。但“黑数较大”这种看法,是可以取得共识的。
贪污犯罪之所以存在“黑数较大”,是由于本罪具有下述一些特点决定的。
(一)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易显露。贪污犯罪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单位内部实施的,其侵犯的对象又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公共财产,一般不是以公民个人利益为直接侵害对象。因此,别人既不容易了解贪污者的职务内幕,又不容易与之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故不易被察觉和揭露。而杀人、放火、抢劫等犯罪,是以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为侵害对象的,受害者与犯罪者利益冲突激烈,要求惩处的积极性高,相对来说“黑数”就会大大降低。
(二)贪污手段智能化的隐蔽性强。公职人员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中的漏洞,因此,在作案前,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并有充分的条件采取规避法律的犯罪措施,故一般人是难以察觉的;利用电脑、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作案,增加了破案难度。广州市西化路农行储蓄所电脑记帐员蔡×,利用电脑假造帐户和存折,贪污54万元;四川省外汇管理局兰×用破译电脑秘码方法,一次便贪得58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
(三)贪污主体特定性的“保护功能”。贪污犯罪主体是一种特定身份犯,是将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主体的特定性带来了贪污分子的“自我保护”功能。犯罪前它是打着“公平”、“合法”执行职务的身份进行,理所当然的不易受到阻碍;犯罪中它实施的是以权谋利、将公权暗化为私权,理所当然的可以骗取领导和同行的支持;犯罪后它可以利用职权地位所形成的影响,公开或秘密地对抗司法机关的侦破活动,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进行开脱,增加司法追诉难度,促使“黑数”增大。
(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某些贪污犯罪的产生与某些地方的“土政策”,与某些部门的“搞活措施”有关,与某些领导的支持纵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贪污犯罪一旦被揭发,就会暴露出单位在管理、监督方面存在的漏洞,影响到单位及其领导者的声誉,同时,还要出车、出人、出钱支持办案,反而造成额外负担。故一般不愿举报,用党纪政纪代之。万一东窗事发,一些党政领导人总是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予以保护,因而也增加了“黑数”。
(五)模糊性行为对贪污的放纵。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贪污行为中,也有一些是属于模糊性行为。贪污犯罪是特殊主体侵犯公共财产。在经济市场下,改变了过去公有财产的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一的格局,而出现了各种对公有财产的租赁、承包、公私联营,中外合作、合营等形式。这些利益主体中特定公职人员的界定,公私财产性质的界定,都具有一定程序的模糊性,对其中某些公职人员侵吞、盗窃、骗取了这些经济体中的财物,是贪污还是一般侵占就难以界定,按“就低不就高”原则,一般不宜按贪污论处,就其实质而言,其中就有的属贪污的“黑数”。
(六)知情人有顾虑不愿举报。保障贪污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的制度不完备,有的举报人害怕被打击报复,担心触犯权势难逃掣肘。对贪污犯罪知情不举,包庇纵容,不愿作证或不敢作证,为“黑数”的扩大提供了社会条件。
(七)办案能力不适应办案工作的需要。要减少贪污犯罪的“黑数”,关键因素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追诉能力。从我国目前的实际出发,需要继续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有素质高、作风正、业务过硬的反贪队伍;二是要有物质保障,包括充足的办案经费和先进的办案设施;三是要完善监督防范体系,适应同隐蔽很深的贪污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减少贪污“黑数”,逐渐实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理想,唯一的出路是强化包括反贪队伍在内的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注释:
〔1〕(见《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2年创刊号第2页)。
〔2〕(见1992《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创刊号第2页)。
〔3〕(西德)孔德·塞尔著《犯罪学》,1983 年西北政法学院译版,第137、139、143页。
〔4〕(美)米切尔·茨尔著《犯罪及其矫正》,1981 年北京心理学会译版,第27页。
〔5〕(苏)B·K茨维布利等主编《犯罪学》,1986 年群众出版社版,第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