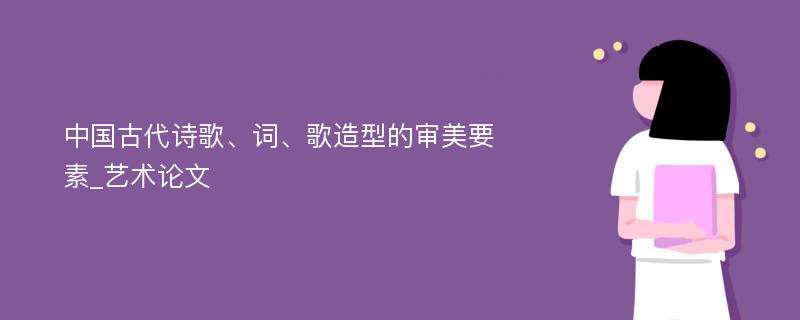
中国古诗、词、曲中的造型审美元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诗论文,中国论文,元素论文,曲中论文,造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诗和画两个艺术类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如诗如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表述,还有画上的题诗、诗配画等。更能深刻反映这个传统的,是中国画中的浓厚诗意和诗词描述的强烈画面感。如无名氏纨扇形的画《出水芙蓉》:新荷在夏日静静初放,饱满的花瓣层层绽开,点点花蕊,无限清香,淡红色的花在绿叶铺衬下妩媚动人,清新、淡雅、自然,真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诗意何其浓郁。再如《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暮秋傍晚的景物,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在字里行间凸现,无不一一入画,在给人萧瑟凄凉的情感冲撞之时予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画作为视觉艺术,传达一种情感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由抽象文字组成的古诗、词、曲,让人产生视觉形象的冲击与如画的美感呢?因为,在古诗、词、曲中深藏着造型艺术美的诸多要素,这些要素在诗与画中架起了互通的桥梁。
在造型艺术中,艺术家常强调力象美,即反映人类本质力量的情态,如向上、奋发、积极、富于理想、永不停止等。而这种力象美在古诗、词、曲中比比皆是。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的诗句:“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读其诗,我们能被诗中描绘的画面所展现出的力象美深深震撼。雪海、莽莽黄沙、斗大的石头在干涸的河床中随风乱滚的险恶景象,金山烟尘飞动、马毛雪汗蒸腾的强烈动感,使人如身处其中,可感、可触、可观,真如境、像俱佳的画作。这些物象因素整合形成的盛大征战场面,充分体现了力象美中的单纯性与真实性特征。正是这些单纯与真实的画面,使得读者思想情感产生共鸣。可以说,岑参的这首诗中所展示的画面的力象美足以撼人心魄,振奋精神。
李白的《蜀道难》中有这样的诗句:“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清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透过“百步九折”、“萦”、“连峰”、“枯松倒挂”、“砯崖转石”等动态鲜明、形象逼真、极具力象美魅力与冲击的字眼,我们真真切切看到了具有生动画面效果的奇险而壮美的山川风貌,体验了作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造型艺术美的诸要素中,意境美是常见而又关键的致美元素之一,而这恰恰也是中国传统诗、词、曲的审美要求。“意境不是形象,是由形态诱发出来的,即诱使观赏者通过联想或想象进入某种境界,产生‘无形的象,无声的音’。”(宗白华《美学散步》)《深山藏古寺》画中,画家不直接画出寺庙,而是画出郁郁葱葱的山林中的一缕炊烟或深山溪畔一担水的和尚,以此来体现一个“深”字和一个“藏”字,让观者产生无尽的联想,进入深山、幽谷、古寺的意境。
古诗、词、曲也常注意通过象的组合形态,“诱发”意境美。王维的《山居秋暝》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中所描绘的山乡傍晚的秋色,初歇的新雨、苍松间穿行的明月、青石上清亮明净的泉水、翠竹中的浣衣女、素净雅致的青莲以及悠然自得的渔舟,“诱发”出山水画般的意境。
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是这样写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涧边幽草、深树黄鹂、春雨、野渡舟横等景物,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寂寞、幽深的春景。其描绘的景物与王维不同,但它们的组合,同样也“诱发”出一种意境,让我们在春景中也有一丝寂寞、一份恬淡与悠闲。这种意境,同样有画面的境界与很好的视觉效果。
其实,在传统的诗、词、曲中,文字构成的画面感极为突出,或细致入微、或宏大壮美,但其形象营构的意境,令许多画作都难以相比。孟浩然《宿建德江》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让人恍若独立黄昏,遥看远天低树;俯身清江,相伴浏水明月。这完全就是画中佳作,展开的,是一幅空旷安静,清净而带有淡淡乡愁的画面。再看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诗中,残阳铺水,半江碧透,半江殷红——这是色彩鲜明、气势壮美的画页;如珠之露、如弓之月——这是细致入微的形象刻画,照此描摹下来,就是一幅形、色、意境俱佳的画作。诗、词、曲的这种画面感,也许是作者的有意营构,也许是无心之得,但无论如何,诗、词、曲的这种绘画效果,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效果,“诱发”了诗、词、曲的美好意境,而这种效果转到绘画中,也同样能“诱发”美好的意境。
相传古代考试中就常用古诗意境为考题让考生入画。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有善解题意者,则取一近景,画舟子在船尾入睡,横置竹笛于身。这么处理,以画人来强调“无人”,出于常人的意想。可见古诗、词、曲中的意境美是可以为绘画创作提供广阔的表现空间的。
在造型艺术中常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也许我们不懂作者在表达什么意思,我们无法体会作者所营造的意境,但我们却会被作品本身的形式美与结构美打动。造型中的美是在变化和统一的矛盾中寻求既不单调又不混乱的某种紧张而调和的世界。在形式与结构中,通常讲究对称与均衡,对比与均衡,对比与调和,节奏和韵律,比例和尺度。分析古诗、词、曲的优秀作品,我们发现其作者大都有潜在的美术天分,当然也有些人本身就是书画家,如苏轼,他的《枯木怪石图》就是以苍老遒劲之笔抒发个人意识的代表作。在宋代文人学士中,把绘画作为个人爱好的还大有人在,因此,在古诗词中随处可见形式美、结构美就不足为怪了。刘禹锡在《望洞庭》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翠小,白银盘里一青螺。”作者把湖光和月光放在一起,形成天上地下对称之势,而湖光、月光相辉映形成了调和的色彩,青绿的君山远景在广阔似玉盘的湖面上,仿佛一颗青螺。这种构思布局充分体现了物象之间的大小,远近的对比,青山与银湖在色调上又统一、调和在清新、素雅这一基调上,生动而逼真地描绘秋月照耀下的洞庭景色,境界开阔,色调淡雅,是一幅优美的洞庭秋月图。
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用模糊的夜色以及江枫的暗影对明亮的月色以及霜露的寒冷青辉,再配以跳动的渔火使沉寂的夜景多了一丝温暖与妙不可言的生命感;正当夜幕沉沉,昏昏欲睡,万象归于静默之时,寺院的钟声飘入港口的客船,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画面。画中有远景、有近景,有明暗相辉映、有动静相结合,整首诗展现的画面充满了节奏和韵律感的审美情趣,构图匀称,设色和谐,耐人寻味。再看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寥寥几笔,一左一右,一黄一苍,典型地运用对称均衡的手法展示人物形象,又富于节奏和韵律。
中国传统的造型艺术特别强调手段过程本身的美,这就是造型艺术另一致美元素——表现技巧的美。“在文人画家看来,绘画的美不仅在于描绘自然,而且在于或更在于描画本身的线条、色彩亦即所谓笔墨本身。笔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表现对象(景物)的相对独立的美。它不仅是种形式美、结构美,而且在这形式结构中能传达出人的种种主观精神境界、‘气韵’、‘兴味’。”(李泽厚《美的历程》)。在表现技巧美的过程中,人们讲究精确和完善,即“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古诗、词、曲提供了可供造型艺术家展现技巧美的广阔空间,这些作品中的很多字句都是经过作家精推细敲、反复玩味得来的,所描述的事物特征恰到好处。鲜于必仁《普天乐·平沙落雁》中的描写具有典型性:“潮平远水宽,天阔孤帆瘦。”此句入画,其中一个“瘦”字便精确传神地表现出水波宽远,天高帆小的视觉美感,可谓妙笔。刘秉忠在《干荷叶·有感》(二首)其一有这样的句子:“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对比其二中的句子“干荷叶,色无多,不耐风霜锉。贴秋波,倒枝柯……”我们不难发现,同样是描写干荷叶的枯黄,在程度上却有很大的区别,一个“色苍苍”,一个“色无多”,一个“减了清香,越添黄”,一个“贴秋波,倒枝柯”,这样的描述为画家在表现技法上的用色造型提供了生动、形象、准确甚至是精确的信息,使画面更具技巧美。
机敏和巧妙是技巧美的另一动人之处。机敏和巧妙分不开,所谓巧妙,是指方法或技术灵活高明,超乎寻常又恰如其分。中国的艺术历来是讲究巧思的,传统的手工艺品又一向以“工巧”为美。颜真卿谈书法有言:“欲书先予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稳,成意外全体,含有异势,是之谓巧”。可见其提到的“异势”就是用独特的手法表现独特的美。在古诗词曲中,我们能获取很多机敏和巧妙的提示。再说《普天乐·平沙落雁》,其中有:“山光凝暮,江影涵秋”的语句。这种在山光里凝聚着暮色,在澄江中倒映着秋景的表现手法运用于绘画中可谓绝妙;又如欧阳修《蝶恋花》中的词句:“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其中一个“横”字动态地描写出风雨的狂猛,“横雨”入画,其表现手法何止一个“妙”字了得。而其《采桑子》中的:“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水平船静,沙禽“惊”、“掠”,动、静相衬的美生动成趣,妙在其中。
在古诗、词、曲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特有的审美意识及审美技巧,为我们艺术创作积累审美经验。中国人观察事物不是用焦点透视,更不是只看事物的一面,而是求“全”的空间意识,其中“动点透视”就是典型特征之一,观察者总喜欢移动观察点,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消除了观察认识的片面性,从而能够冲破表象,还物以真实。古诗《一望二三里》中写道:“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诗中从全局写到局部,观察点从远到近,描写也是从远景、中景描述,到贴近处的细节刻画,虚虚实实,让读者在不同层面感受到山野乡村的祥和、宁静,似一幅兼工带写的山水画。王维《桃园行》的“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亦展示了远景与近景的“动点透视”的观察方式。
此外,“以小观大”是求“全”的审美意识另一手法,即透过一个小的部分,反映整体特征。在古诗、词、曲中,我们经常能感受到这一审美意识的魅力所在,徐再思《水仙子·夜雨》中描述:“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就是透过梧桐树叶的枯黄飘零,传达秋的信息,通过残败的芭蕉树叶抒发心中的忧愁;再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亦是通过一枝小小的红杏传达整个春天生机勃勃的信息,集中而含蓄,充分展示了“以小见大”表现手法的魅力。
中国人的审美理解,不是就形论形,而是突出一个“悟”字,利用形态的意义扩大形态的场,这就是思悟的象外追求。其典型的表现手法就是“借物抒情”,其明显特征为:以感物为基础,以抒情为先导,感物生情,托物以抒情,使人与物融合。这一审美特点在古代绘画与诗、词、曲中屡见不鲜,郑板桥就利用画竹抒发“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气概。梅、兰、竹、菊的自然特性成为诸多画家和作家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载体。张谓在《早梅》中写道:“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明看写寒梅早开,实则写自己的争春精神,催人向上。诗中用“白玉条”突出梅花的高洁,利用梅花与白雪的形象牵引互换,达到视觉一体化的效果,表现手法亦幻亦真,为造型艺术家提供了绝妙的创意思路。再看元稹的《菊花》:“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一句“此花开尽更无花”,既含有对菊花经霜后凋的品质的称赞,也引出了一个普遍的人生哲理,那就是艰难险阻,却挡不住理想之花的盛开。
古诗、词、曲中常借用自然物的属性,抒发情感、营造意境。前文提到的《秋思》,用“枯藤”、“老树”、“昏鸦”、“西风”、“瘦马”、“夕阳”等暮秋景物,烘托出萧瑟、凄凉的气氛,表达出羁旅中彷徨与悲怆之情。在古诗、词、曲中常有象征意义的物象描写,如“残菊”、“残阳”表现失意,“老树”、“孤帆”表示落魄;“黄菊”、“红叶”象征傲岸品格,冲天沙鸥代表挣脱世俗;“圆月”代表圆满、团圆,“残月”、“破荷”引申破败等,此类约定俗成的象征物不胜枚举。
元曲《梧叶儿·嘲谎人》中写道:“东村里鸡生凤,南庄上马变牛,六月里裹皮裘。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瓮来大的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诗中看似荒诞嘲讽的句子,若反其道而用之,也能启发造型艺术新的理念,即敢想别人不敢想,把不存在、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变为全新的形象。此为创造的最高境界,亦为造型艺术个性化的魅力所在。
唐诗、宋词、元曲,历来被文人骚客所吟诵把玩。其实,古诗、词、曲也是造型艺术家的资源,其造型艺术的审美元素,将在形式、内涵等多方面、多层次为造型艺术家提供取之不尽的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