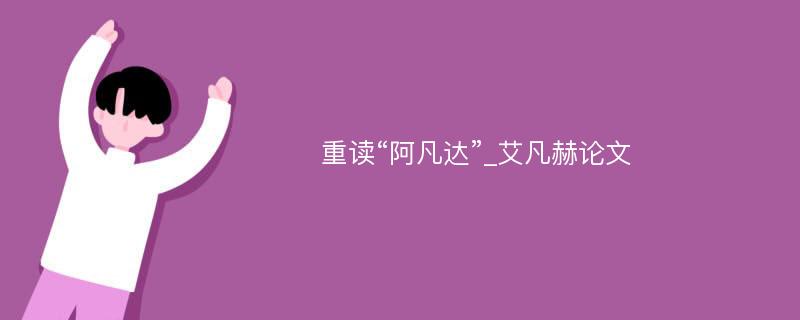
重读《艾凡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各特于1820年出版的小说《艾凡赫》在其创作体系中是一部颇具“突兀感”的作品。众所周知,自他于1814年完成《威弗莱》以后,其后出版的多部小说,如《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1815)、《我的主人的故事》(Tales Of My Landlord,1816)、《罗布·罗依》(Rob Roy,1817)、《惊婚记》(The Bride Of Lammermoor,1819)与《蒙特罗斯传奇》(A Legend Of Montrose,1819)都无一例外地以17、18世纪的苏格兰作为小说创作的背景与主题,而《艾凡赫》却一反常态,摒弃了其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笔法,变身为一部颇具瑰丽想象力的“中世纪浪漫传奇”。继《艾凡赫》之后,司各特下一部发表于1820年的小说《修道院》(The Monastery)又将背景转换回了读者所熟悉的苏格兰,这样一来更显出了《艾凡赫》在其整个作品体系中的特殊性。那么,促使司各特创作风格与主题突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一疑问在司各特研究领域中成了人们一直热衷讨论,而至今也未有定论的一桩悬疑公案。 针对这一谜题,近年来诸多学者试图以“文学外部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在其创作时期的政治历史事件中挖掘促成司各特撰写这部作品的直接动因。如格拉哈姆·约翰·塔洛克(Graham John Tulloch)通过对比分析司各特在《艾凡赫》与《空想家》(The Visionary)两本书中的相同署名而推断,促使司各特写作《艾凡赫》的重要动因是当时的彼得卢广场大屠杀事件,①而司各特在《艾凡赫》中描写的阶级矛盾是当时社会现实矛盾的生动写照。②类似地,S.J.怀特(Simon J.White)则通过小说中罗宾汉为代表的绿林强人的自由农身份解析,指出《艾凡赫》与英国1817年6月爆发的彭特里奇起义(Pentridge Rising)有着直接联系。③ 本文关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条学理脉络而提出的。笔者认为,《艾凡赫》与司各特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密切关系,有现实所指和现实意义,但具体观点却与关注社会阶级矛盾的学者有所不同。本文提出,《艾凡赫》是一部关于王权的小说。 一、王权之殇:从一棵橡树说开 在《艾凡赫》中,有一个看似普通的意象,细数起来在全文中却出现了十八次之多,且这一意象总与狮心王理查如影相随,那就是“橡树”。小说中,为了营救被囚禁在弗朗·德·别夫城堡内的罗文娜等人,狮心王理查率领由绿林人与农奴组成的“联军”将大本营建立在“一株庄严的大橡树下”,④在发给敌方的战书中,也刻意强调是签署于“大橡树下之集合地”(224页)。战斗取得胜利之后,罗宾汉呼吁,“把战利品带到哈特希尔牧场橡树下”(303页)。当狮心王理查遭受贼人偷袭时,他“背靠着一棵橡树作为屏障,挥动宝剑抵住贼徒的攻击”(407页)。其后在狮心王理查公开国王的真实身份之后,众人向他叩拜效忠,也是在一棵橡树之下发生的。由此可见,“橡树”这一意象与狮心王理查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王权之间有紧密的关系。 作为一种高大雄伟、生机勃勃的树木,橡树自古希腊起便有着“树木之王”(King of Trees)的美誉。亚瑟·伯纳德·库克(Arthur Bernard Cook)在《宙斯、朱庇特与橡树》(Zeus,Jupiter and the Oak)中指出,古希腊神话中存在着一种“橡树崇拜”(oak-cult)的现象,主神宙斯在希腊古城多多那(Dodona)正是通过“一棵神圣的橡树”来传递神谕的。而著名的“维也纳青铜雕像”(Vienna Bronze)也将宙斯塑造成一个头戴橡树叶做成的皇冠的王者形象。⑤弗雷泽在《金枝》中进一步提出,最初的国王同时身兼巫师与祭司的三重身份。国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崇拜,是因为他本身就被当作神灵看待,能够控制天气,为他的臣民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年,而希腊神话中宙斯正是一个具有强大的司雷行雨能力的主神。由于原始社会中的“橡树崇拜”情结,人们普遍认为与宙斯密切关联的橡树是具有神性的。因此,“古代希腊遍布橡树的山区小君候们……自称是宙斯的化身”。⑥ 橡树对于近代英国人而言,更被赋予了君主之保护神的特殊意义。传说中,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英王查理二世在伍斯特战役中败给议会军领袖克伦威尔,在逃亡途中,正是一棵空心的老橡树帮助他摆脱了敌军的追杀,这也才成就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那棵救命的老橡树后来也被赐予了“皇家橡树”(Royal Oak)的封号。司各特于1826年创作的历史小说《皇家猎宫》(Woodstock)就是以查理二世的遭遇为背景写成,而且他在小说中也特意描写道,“在那快乐的英格兰的密林中,矗立着一株具有庞大躯干的树中之王”,⑦并借杰丝琳之口介绍:“这就是‘国王的橡树’。”⑧由此可见,司各特对于橡树及其蕴含的王权之义有着清楚的认识,那么他在《艾凡赫》中反复多次使用并强化橡树这一意象,绝非偶然之举,其中隐含力挺王权并试图为其谋求合法性的深意。 19世纪初,坊间曾流传一则秘闻,传言英王乔治三世受到了橡树的诅咒。先是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他在利特尔公园(Little Park)里下令砍倒了一棵名为赫恩的橡树(Herne's Oak),⑨后又有传闻,说他在1788年时曾神情恍惚地将一棵橡树当作普鲁士国王,并上前与其握手交谈,之后便犯了精神疾病。⑩这一传说影响极广,多部专门研究英国王室史的著作都提及了这个原因,如露丝·宾尼(Ruth Binney)的《皇室惊奇异事录》(Amazing & Extraordinary Facts Royal Family Life)与A.R.拉什顿(Alan R.Rushton)的《皇家症候:欧洲统治家族的遗传疾病》(Royal Maladies:Inherited Diseases in the Ruling Houses of Europe)。然而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多年前就愤怒地指出,这个故事最初来源于一本1789年出版的粗制滥造的小册子,纯属胡编乱造,其目的就是为了诋毁乔治三世的名誉,造成他是一个“又疯又坏”的国王形象。(11) 如前文所述,橡树因蕴含神性而成为世俗王权合法性的象征,隐隐含有“君权神授”之意。虽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一古老的说法再也不能成为国王合法统治的理由,但人们依然愿意相信君主拥有某种神性力量。如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人头落地的那一刻,“许多看客……用手帕去蘸查理一世的鲜血,他们认为这血可以愈合伤口,治疗疾病”。(12)又如安妮女王曾经在1714年触摸过二百多个病人,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君主的触摸(King's touch)可以驱赶恶魔,祛除病痛。(13)而这个有关橡树导致国王疯癫的离奇故事的本质是欲将“神”与“王”对立起来,从而剥夺了国王身上的最后一点神圣的力量源泉,进而使人们质疑王权合法性的基础。 司各特之所以在小说中反复强调橡树这一意象,以及它与王权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针对当时这一谣言的“反叙事”,体现了他竭力维护王权的意愿。这一努力的背后,是英国王权在历史上面临的真正危机。埃德蒙·伯克在18世纪末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政治檄文《现状令人不满之原因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他在文中写道:“王权,作为一种近乎业已腐烂至死亡的特权,又死灰复燃,且有变本加厉之势。”(14)他所批评的,正是乔治三世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利用皇室特权中的任命权(powers of patronage)来任命和革除内阁大臣这一事实。他一手提拔并力挺的首相诺斯软弱无能且不善军事,对失去美洲殖民地负有重大责任,乔治四世因此成了众矢之的,以伯克为代表的诸多反对者开始在法理上论述其行为不当之处,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条就是滥用王权,按自己的意愿在内阁中安插亲信,企图颠覆宪法,体现了“王在法上”的傲慢。在这种猛烈的质疑与追问下,乔治四世“于1820年去世时,这种特权(指任命权)也迅速消失了”。(15) 由此可见,《艾凡赫》1820年正式出版时,英国君王已然大权旁落,颓废之势无可挽回了。如果说乔治三世为人刚愎自用,但尚有些雄韬大略的话,那么他的继承人,被司各特戏谑地称为“我的胖朋友”的乔治四世,则胸无大志、好色贪吃而彻底沦为了街头小报调侃讥讽的对象。如英国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就经常讽刺其大腹便便的丑陋形象,并在漫画旁的注释中称其为“生活在消化不良恐惧中的酒色之徒”。(16)乔治四世虽然爱好艺术与音乐,被冠以“英格兰第一绅士”的美誉,但也因为对这些个人爱好投入过多而让王室陷入债台高筑的窘境,即使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国家财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依然保持着穷极奢侈的生活习惯,1820年其加冕典礼的支出达到了243,000英镑的天价费用,(17)因而为人诟病。 现实生活中,司各特与乔治四世私交甚好。1815年,当时尚为摄政王的乔治四世邀请司各特共进晚宴,席间曾向“小说《威弗莱》的作者”敬酒。1820年,即《艾凡赫》正式出版那一年,摄政王正式登基成为乔治四世,并于同年封司各特为次男爵(Baronet),系他即位以来所封的第一个爵位。1822年,乔治四世首次到访苏格兰,全程活动均为司各特安排,包括他本人穿着的、能够激起苏格兰人情感认同的特色服饰,均出自司各特的精心谋划。 众所周知,英国议会本就划分为主张限制王权、提升议会权力的辉格党,以及主张维护君主特权、代表贵族利益的托利党。就司各特本人的政治立场与社会观点而言,他显然属于后者:他曾在《幻想》这部政治檄文小册子中对“激进改革与普选权”冷嘲热讽,在《论骑士精神》(On Chivalry)中扼腕叹息贵族精神的陨灭,在《威弗莱》、《蒙特罗斯传奇》、《皇家猎宫》等多部小说中对保皇党人流露出深刻同情与理解,他也曾力排众议,迎娶了逃亡到英国的法国保皇党人家庭出身的玛格丽特。 鉴于司各特与王室的密切关系及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并考虑到《艾凡赫》的出版与乔治四世正式即位发生在同一年的“巧合”,我们有理由推断,《艾凡赫》极有可能是司各特为力挺乔治四世而著的一部小说,它所针对的是19世纪初英国王权在内忧外患之下威信与实权每况愈下的状况,以及暗流涌动的民族分裂危机,它所表达的乃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王权之于民族国家团结与繁荣所能起到的重要凝聚作用。司各特在小说中塑造的狮心王理查的完美形象,与历史上那个“为了金钱可卖掉伦敦”的贪婪暴虐的君主大不相同,对其形象的“改编”富有现实意义。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中世纪复兴(medieval revival)的潮流之中,各个领域都存在“中世纪崇拜”的思想倾向,而中世纪王权观对于英国近现代君主以及国家的权力观念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世纪末期,王权逐渐汇聚了各种分散的权力,所以,它是现代国家权力的生长点与直接前身”,(18)在这一情势下,借中世纪王权来“借古讽今”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选择。 二、从“君权神授”到“人民同意”:中世纪王权合法性来源之变 如前文所述,这部小说可被视为一部“国王复仇记”,讲述的是狮心王理查如何击败意图谋反的弟弟约翰及其追随者,在绿林英雄以及忠于自己的骑士的协助下,最终夺回王位的故事。然而,如果我们认真思量这一问题,却会产生疑问:为什么理查才是“真命天子”?如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的那样,“合法继承的君王具有较少的理由与较少的必要去激怒他的臣民,所以他之较能得人爱戴,乃是自然之事。”(19)那么,理查的王权合法性基础何在?对于这一基础的深入叩问,又会引出涉及中世纪王权观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相关考察对理解司各特的创作主旨及小说的现实意义至关重要。 在小说中,对理查的王位虎视眈眈,图谋取而代之的正是他的亲弟弟约翰亲王。约翰不顾及手足之情以及哥哥理查平日对他的种种恩惠,勾结理查的死敌法兰西国王菲利浦,费尽心机地怂恿奥地利大公延长其兄长的羁押期。与此同时,在国内他又利用土地财物为诱饵来收买扩充党羽,意图篡权。然而,除去约翰亲王令人鄙夷的品性不论,就当时长子继承王位(Primogeniture)的习俗而言,约翰的做法也不符合法理。司各特在小说的注释中特意注明:亨利二世有子五人,理查是次子,第三子是乔佛瑞,第四子是约翰(58页)。这意味着即使理查不幸罹难,合法的继承者也是乔佛瑞,而非约翰。这种长幼有序的王权继承制度,在中世纪只是以日耳曼习惯法的形式流传下来,直到查理四世《黄金诏书》第25章中才出现完整的、清晰的表述: 自此至将来任何时候,诸卓越而宏大之选侯领地……其土地、辖区、附庸及属于彼等之任何事物,俱不许割裂、分开,或在任何情形下被分裂,而应永保完整。长子应为彼等之继承人,除非长子为心智失常之人,或白痴,或有任何其他缺陷不能君临人民者,否则一切统治权与领地均应属于彼一人。如有上述情况,长子不能继承……应由次子继承,或由死者之长弟或其他在俗戚属继承,但必须为父系之直系后嗣。(20) 以上内容表述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基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国土不可分割”之观念。关于这一点,中世纪早期曾经有过惨痛的前车之鉴,查理大帝将国土均分给他的三个儿子罗退耳、查理、路易,以至分崩离析后的法兰克帝国再也难见昔日的庞大与辉煌。比这一史实更为闻名的,当数同样以中世纪为背景的《李尔王》,在莎翁笔下,老国王的悲剧亦自他决定将国土馈赠与他的三个女儿那一刻便已注定,因为“李尔王在三分国土的同时也‘解剖’了王权”。(21) 由此可见,在以土地采邑制度为基本经济形态的中世纪,作为王权之基础的国土不可均分,而应该由长子继承,是中世纪王权观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王权在政治结构相当分散的不稳定状况下,能够持续地在某一家族内以一种无争议的合法继承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一思想体现了中世纪王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即基于血缘关系进行王位继承的“正统主义”。其核心观念来自古代日耳曼部落,认为领袖所在的家族是神意的选择,因此其权力在凡间有着毋庸置疑的合法性。约翰亲王欲谋害自己的亲兄弟取而代之,破坏了前述思想中的血缘伦理思想,必然不得人心,遭人唾弃。相比较而言,理查则十分重视亲情。在小说的结尾,虽然他毫不留情地处死了追随其弟弟的诸多叛党,但是“独有约翰亲王,他虽是阴谋的主持人,却获得了好脾气的哥哥的饶恕,什么罪名也没有加到他身上”(455页)。 然而,基于血缘关系的日耳曼部落传统并不能构成中世纪王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将国家财富视为王室家族的私产,因而缺乏“公共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它不得不向基督教屈服,通过后者“君权神授”的理念来弥补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的不足。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王权的公共性,因为“基督教要求王权服务于作为上帝子民的全体基督徒,因此其对象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2) 另一方面,中世纪王权在依附于基督教来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的同时,也沦为了后者的附庸。在《旧约全书》中,先知撒母尔用涂油礼的形式来肯定大卫的王权之合法性。而1066年征服了英伦三岛的威廉也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共同为其加冕,方才获得了合法的英王身份。教会法学家认为教皇拥有“完全的权力”(plentitudo potestatis,英文为fullness of power)和“绝对的权力”(potestas absoluta,英文为absolute power)。王权在庞大的宗教共同体中只是一个行使世俗权力的部门罢了,必须经过教会的授权方具有合法性。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所提倡的“整体主义观”与“普世之治”(regimen universal)将全世界视为一个庞大的宗教共同体,将所有人都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抹杀了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界限。然而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独立、自足、自主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开始萌芽,国王作为国家民族团结一致与凝聚力的代表,必然有着对抗基督教的强烈意识。爆发于11世纪末期的“叙任权之争”(the investiture contest),以及1215年《大宪章》(Magna Carta)的签署,便反映了两者间在长期此消彼长的争斗之中所形成的矛盾而又共生的关系。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理查王在小说中对基督教表现出的令人费解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在小说开头,理查王之所以身陷囹圄,正是因为听从教皇的派遣,率领十字军东征讨伐异教徒的结果。另一方面,理查王却对基督教会表现出了极大的对立与敌视态度,如他对圣殿骑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傲慢的圣殿骑士,你是拒绝不了的。你抬头看看,你看那塔楼上飘扬的已经不是你们圣殿的旌旗而是英格兰皇家的旗帜了!”(451页)又如小说中著名的对瑞贝卡的“神意审判”,更是无情地讥讽了所谓教会法律的荒谬性,与理查王父亲亨利二世着手推动的陪审团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孰优孰劣,立见高下。 著名的中世纪思想史学家厄尔曼提出,中世纪王权之合法性共有两个来源:一是“自上而下”的“神权理论”,二是与其相对的“自下而上”的“民权理论”。(23)亨利四世提出“王权二重性”,将“俗世”与“精神”区分开来之后,王权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与神祗无关的自主性基础,从而摆脱教权的管辖与控制。借着古罗马共和精神与古希腊城邦精神的复兴潮流,“人民同意”这一观念愈加深入人心,“民权说”从而逐渐占据上风,王权合法性也找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人民性因素。 在司各特的笔下,理查王之所以能够最终取胜,除了忠于他的贵族与骑士,以罗宾汉、脱克和尚为代表的绿林强人,以及葛尔兹、汪巴等农奴的支持亦至关重要。这种支持意味着对王权合法性的授权,而这又是通过理查王刻意强化其王权的“公共性”而实现的。首先,理查王的思想中流露出“国王、王权、国家”的三位一体观念,其内在逻辑是试图将“爱国”与“爱君”等同起来,从而使人们的爱国热情全部投射在他个人身上。小说中多次出现这一观点,如塞德里克认为“爱国与爱君是一回事”;神箭手洛克斯雷诚挚的爱国宣言“我的手是一个真实的英国人的手”(331页),也为其爱君埋下了伏笔;理查本人亦声称,“你可以看出现在和我在一起的都是忠于英国的人民。”(414页)此外,“公共善”是其实现王权公共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理查曾口头修改森林法,允许其酒肉朋友脱克和尚在自己的森林中打猎,虽有不成体统之嫌,但也充分体现了愿与民众共享国家资源的意愿。他为营救罗文娜、塞德利克、犹太人父女不顾自身安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体现了“为公共善服务的责任是对所有中世纪统治者的基本要求……统治者就是为公共善服务的工具”(24)这一理念。最后,“祛魅”(disenchantment)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做法。这一说法来自于马克斯·韦伯,意为西方国家在从宗教神权社会到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对于神圣体所赋予的霸权权威的消解。就《艾凡赫》而言,它指王权摆脱了笼罩在头上的神祗光芒,凸显出与“下源性”权力连通的具体方式与意义。在小说中,理查王之所以受到底层人民爱戴,是因为司各特生动地刻画了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肚子饿时喝酒吃鹿肉,高兴时唱歌吟诗,兴起时也会和他人斗气,等等。如果用中世纪基督教义中的“君之两体”(the King's Two Bodies)的观念进行衡量的话,司各特笔下的国王并非是神圣的“政治体”(Body Politic),而是与其他常人一样“服从激情与死亡”(25)的“自然体”(body nature)。 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国王,让民众觉得真实、接地气,自然会赢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这就清除了中世纪王权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障碍,即由封建社会的土地采邑与分封制度所带来的王权权力断层问题。在中世纪,贵族的土地来自于国王的分封,然后贵族再将所分得的土地向手下更小的封臣进行分配,以换取财物与兵力。这样的经济制度看似稳定,但对国王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封建誓约的不可传递性严格将王权限制在国王与其直接封臣之间,没有资格直达次级封臣,更难直达每一个臣民”。(26)这也印证了中世纪那个非常有名的说法——“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理查强化王权公共性的这几种方式赢得了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王权藉此穿透了由封建经济结构造成的重重权力屏障,与普通人民形成联盟,直接向民众发令,由贵族掌控的地方割据权力逐渐被瓦解,君主从而拥有了更具实质性与广泛性的权力。在中世纪历史上,正是随着王权之合法性由“上源”向“下源”的逐渐过渡,中世纪末期以君主为权力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才逐渐形成,绝对君主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也开始萌芽。 三、王权、民族、自由:《艾凡赫》中王权观的现实意义 与中世纪中后期类似,英国在19世纪早期也面临着王权合法性向基于“人民同意”的“下源性”逐渐过渡的局面。司各特卒于1832年,恰恰那一年英国通过了议会改革的法案,议会从此变为代议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参与国家管理,而后来的第二次议会改革又使得工人阶级与下层群众获得了选举权,“集体统治”的序幕以一种渐进但坚定的方式徐徐拉开了。从这一角度而言,司各特在小说中流露的“主权在民”的中世纪王权观具有前瞻性意义,他所塑造的理查王形象具有难能可贵的面对人民的“公共性”,这也正是现实中的君主所欠缺而饱受人民抨击的。从这一角度来说,《艾凡赫》这部小说因富有隽永的劝诫意义而呈现出英国16世纪“君主宝鑑”(mirror-for-prince)的意味。如16世纪最后十年中莎士比亚创作的十部有关君主的历史剧(如《约翰王》、《亨利八世》、《理查三世》等),剧中所批评的社会与宗教问题便成为了“当下女王时代与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借镜”。(27)意为将文学作品作为一面镜子,可映照出完美的君主形象,现实中的君主应效仿典范,为人民树立良好的榜样。正如17世纪英格兰王宫新斯多葛主义政治学所提倡的那样,“君主主要做美德典范和表率,用谦让、忍耐等美德教育臣民”。(28)《旧唐书·魏征传》中所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29)有着类似的内涵。 司各特在小说中塑造的狮心王理查这一形象,实际上是经过浪漫化与美化的,综合了乔治三世与乔治四世两人现实特质的化身。他既有统一国土的雄心和号令诸侯的霸气,也在伤感地演奏竖琴并咏唱撒克逊民谣时展现出自己过人的才情。更为重要的是,他象征着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能够使国土上各个冲突的民族与阶级摒弃前嫌,紧紧地团结一起。如在小说中,理查拒绝接受撒克逊贵族赛德利克对他“安茹的理查”这一带有法国意味的称呼,而自称“英格兰的理查”,因为“我最恳切的关怀……我最热烈的愿望,就是看到英格兰的儿子们互相团结起来”(428页),彰显了强大的王权之于民族团结与统一的重要性。正是在其强大王权的统摄之下,撒克逊民族与诺曼民族方才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 如果我们认同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观点,将民族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那么理查王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君主,能够将所有认可其功勋,分享其荣光的英国人都纳入到一个庞大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中,这对于建构团结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在现实中,君主也起着类似的意识形态纽带作用。正是在乔治三世治下,大不列颠王国与爱尔兰合并为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而乔治四世也在正式加冕后于1821年与1822年紧锣密鼓地出访爱尔兰与苏格兰,个中深意不言而喻。 在民族融合这个问题上,司各特一向是主“和”的一派。他在包括《修墓老人》、《沼地新娘》、《中洛辛郡的心脏》、《古董家》、《雷德冈脱利特》在内的多部小说中,都流露出强烈的民族统一意识。D.K.格里菲斯(Dale K.Griffith)认为,司各特出于“商业的繁荣”、“政府的节制”与“宗教的自由”三方面的考虑,极力拥护英格兰与苏格兰建立联合王国。(30)继1707年联合法案之后,英国在1801年又吞并爱尔兰占据了整个大不列颠群岛,从而初步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设。然而,这种地域上的统一并没有彻底解决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当时爱尔兰与苏格兰频频爆发的、由激进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动乱便是这种深刻的内部矛盾的表征。D.马昆德(D.Marquand)指出,当时的英国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欧陆国家的特征,“它是由英国君主在不同时期获得的、以不同方式治理的一些岛屿……其居民享有法律规定的公民权,但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是君主的臣民,乐于拥有祖先们从以往的君主那里获得的‘自由’”。(31) 马昆德的观点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相对于基于法律的“公民身份”而言,在大不列颠人们更倾向于认同在君王权威之下的“臣民身份”,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王权在维系国土完整性与民族统一性方面发挥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这些臣民在崇敬、崇拜国王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于“自由”的珍视。这一论调与前文所引述的洛克的观点不谋而合。“自由”这一词语的背后,是英国近代形成并逐渐成熟的自由主义思想。19世纪初英国王权衰落的原因,表面上看,品行上有诸多缺陷的君主个体难辞其咎,但实质上危机却是由早已暗流涌动、蓄势待发的自由主义思潮所引发的。 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以来,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学说一直建立在以妥协与保守为根本特征的自由主义之上。英国思想家们在不断推进、完善这一理论的时候,“王权”作为“自由”的对立面往往饱受攻击。如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的理性主义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法理基础,斯宾诺莎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指出君主制国王往往因私欲而不守约,因此不可信赖;而洛克的理性自由主义精神则天生与拥有绝对管制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格格不入,因此他不仅反对“庸君”,也反对“贤君”,理由是绝对权力就会导致绝对腐败,君主制必然带来暴政。其后,法国启蒙主义思潮催生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以及卢梭将国王降低为“人民的委托人”的观念。以上思想中所包含的社会契约思想与自然法思想成了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王的有力的理论武器,无论是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还是托马斯·杰弗逊负责起草的《独立宣言》,都怒斥英王凌驾于法律与民权之上,并由此得出结论:“这样一个国王,他的所有行为都呈现出暴君的特征,不配统治我们自由的人民。”(32)同时,随着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人头落地,诸多欧洲国家的君主都开始变得谦虚与谨慎,所谓“开明专制”的政治气候开始出现,国王时刻提醒自己,“同地位最为低微的臣民一样,自己也是人……他仅仅是国家的第一公仆”。(33) 这种摧朽拉枯的激进式自由主义思潮与19世纪初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后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对于主张审慎渐进与温和改革的司各特而言,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很可能会成为分裂尚不牢固的大不列颠帝国的潜在威胁。事实上,当时在大不列颠群岛爆发的种种民族主义骚乱都是以“自由”为口号的。这就是为什么司各特在小说开篇便强调了“民族”与“自由”这两个要素:撒克逊人与诺曼人之间“血统还没有融合起来”(3页),存在着“巨大的民族差别……始终保持着一条分界线”(4页),并顺势道出了两者间的重要矛盾,就是诺曼人的法令与撒克逊人“自由的精神格格不入……而一个英格兰人心目中最高贵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独立自由”(2页)。 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发端于英国近现代,但追求自由的精神却早在中世纪便出现萌芽。在中世纪历史上,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贤人会议”,还是约翰王1215年被迫签署的《大宪章》,都体现了人民限制绝对王权的强烈愿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王权越大,人们享有的自由越少”,因而王权总是被置于人民自由的对立面。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绝非如此简单。司各特在小说中屡屡发问,“自由”到底是什么?身为“自由农”的罗宾汉等绿林人以打劫为生,看似无拘无束,却只能昼伏夜出以躲避追剿。农奴汪巴在主人被俘之后,自由本已是唾手可得之物,他却迷茫地喃喃自语:“常听人说自由是多么幸福;我现在是得到自由了……我拿它作什么用呢?”(171页)由此可见,所谓“自由”有其哲学意义上的内在矛盾,即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任何个体所拥有的部分自由都只存在于某种默认的契约之中,并通过所放弃的另一部分自由交换得来。在小说中,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英格兰普通民众,本可自行其是,不必受封建主驱使,然而出自对于安定生活的渴望,他们自愿放弃自由,“找一个附近的土皇帝做自己的靠山”(2页),并通过与贵族签订契约以换取庇护。欧洲中世纪早期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有些相似,诸侯分立混战,百姓则遭受池鱼之殃,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他们的保护者有了野心,轻举妄动一下,他们都得分担一部分风险”(2页)。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终结群雄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一个使大家都慑服的共同的、集中的国家权力化身。只有当作为“利维坦”的狮心王理查现身,与民众直接立约,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有安全感的自由。从这一点来看,司各特的思想受苏格兰启蒙时期休谟等人的思想影响颇深,将其描述为保守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似乎更加公允,它对前文提及的激进式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一种含蓄的回拨力量。 司各特并非政治思想家,如果说他有一套成熟的、系统的王权理论,未免言过其实。然而,他以一种轻松愉悦地讲述故事的方式,巧妙地将“王权”、“自由”、“民族”这几个当时重要的政治议题穿插在小说中,潜移默化地强化了王权之于后两个议题的重要意义。司各特对于这三者之间关系的阐释,是他对于19世纪初期王权理论的独特贡献:一方面明确了王权自中世纪以来的合法性来源之嬗变,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王权之于民族国家形成、保障国家内部人民自由的强大意识形态功能。然而,尽管司各特在小说中对王权不吝惜溢美之词,但他并不认为强大的王权可以永世长存,正如小说所述,由于理查王在位不久就中道崩殂,他向民众许诺的种种善意诺言未能兑现。可见,基于国王个人魅力的王权正义性是无法延续的,自然个体的死亡便动摇了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公民的福利不能由个人意志决定,最终还是要依靠健全的、成熟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才能得以实现。正如亨廷顿在谈论政治现代化的权威合理化时提到的那样,“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他任何责任。”(34)因此,司各特塑造的这一完美国王形象,不应简单地理解为阿谀奉承或粉饰太平,作家欲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劝诫之意,缅怀之情及美好之愿望。在充盈的情感流露背后,我们也可窥见作者对基于个人权威的专制王权必将逐渐衰落的理性判断。由于王权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重要成分,因而这一思想倾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休谟、弗格森等人提出的“进步的历史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注释: ①司各特在1819年曾针对当时爆发的彼得卢广场大屠杀事件(Peterloo massacre)发表了系列社论文章,收录在一本名叫《空想家》(The Visionary)的小册子里,署名为L.T.,紧接其后出版的《艾凡赫》则是以Laurence Templeton为化名出版。显然,这两个名字有隐含的一致性。 ②Graham John Tulloch,"Writing 'by advice':Ivanhoe and The Three Perils of Man",in Studies in Hogg and His World,15(2004),pp.32-52. ③Simon J.White,"Ivanhoe.Robin Hood and the Pentridge Rising",in 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3(2009),pp.209-224. ④司各特:《艾凡赫》,刘尊棋、章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227页。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⑤Arthur Bernard Cook,"Zeus,Jupiter and the Oak",in The Classical Review,3(1903),pp.174-186. ⑥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241页。 ⑦Walter Scott,The Works of Sir Walter Scott:Woodstock(London:Houghton Mifflin,1913),p.44. ⑧Walter Scott,The Works of Sir Walter Scott:Woodstock,p.44. ⑨Roger Howell,"Reviewed Work:King George III:America's Last Monarch by John Brooke",in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3(1975),pp.503-505. ⑩Karcn Stollznow,Language Myths,Mysteries and Magic(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208. (11)Roger Howell,"Reviewed Work:King George III:America's Last Monarch by John Brooke",pp.503-505. (12)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君主制的历史》,荣予、方力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135页。 (13)Peter Martin,Samuel Johnson:A Biography(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3. (14)Paul Langfor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London:Clarendon Press,1981),p.258. (15)罗伯茨:《英国史》(下),潘兴明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159页。 (16)哈维:《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韩敏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176页。 (17)《英国与世界:1714-1830年》,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版,60页。 (18)李筠:《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的中世纪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5页。 (19)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惠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4页。 (20)《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法学教材编辑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285页。 (21)冯伟:《李尔王与早期现代英国的王权思想》,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32-42页。 (22)李筠:《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的中世纪起源》,18页。 (23)沃尔特·厄尔曼:《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夏洞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8-9页。 (24)李筠:《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的中世纪起源》,208页。 (25)丛日云、庞金友:《中西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91页。 (26)李筠:《乌尔比安格言的创造性利用罗马法复兴对现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影响》,载《学海》2012年第2期,74-81页。 (27)胡程:《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莎士比亚历史剧阐释的宗教之维》,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16-20页。 (28)陶久胜:《英国巴洛克时期的宫廷政治:新斯多葛主义下的〈白魔〉》,载《外语教学》2015年第6期,75-79页。 (29)高坊清:《历代经典谏文通览》,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版,257页。 (30)Dale K.Griffith,Scott's Fiction and the Union of 1707(New York:University of Nevada,Las Vegas,1996),p.iii. (31)D.Marquand,The Unprincipled Society(London:Fontana,1988),p.152. (32)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杨颖玥、张尧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472页。 (33)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君主制的历史》,荣予、方力维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102页。 (34)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