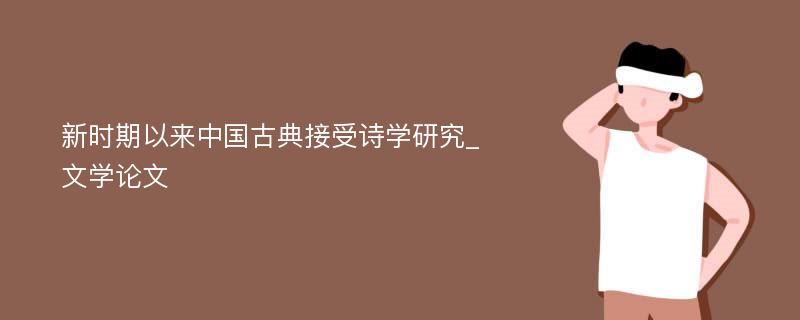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6-0057-05
古典接受诗学研究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它与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一起,成为了近年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两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世纪交替的特定历史时期,一同起到了拓展古典文学研究格局,丰富古典文学研究路径的作用。本文拟对新时期以来的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的研究略作回顾。
一、新时期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应该说,二十世纪以来,古典接受诗学的研究并不始于新时期。早在四十年代,钱钟书《谈艺录》中“陶渊明诗显晦”一节,就从历时视野对陶诗的流传、接受情况予以了粗略的考察,其构架已具诗学接受的雏形。进入新时期,一些研究者在对古代作家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阐释,这实际上已开始了对古典诗人诗作的接受研究。1980年,罗宗强出版《李杜论略》[1]列有“李杜优劣论”一章,他通过抓取“抑李扬杜”和“抑杜扬李”这两种在文学接受史上互为对立的论评取向,对一千二百余年间的李杜之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比照分析,为后人对李杜的更深入把握拉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流变线索,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先导。
1982年,程千帆在《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他通过选择唐诗中经典名篇《春江花月夜》的接受作为考察对象,向人们展示出了文学接受过程中所存在的极为复杂的情形与错综变化的时代特征。程文在开头部分中指出:“在文坛上,作家的穷通及作品的显晦不能排斥偶然性因素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的甚至具有决定性。但在一般情况下,穷通显晦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因而是可根据这些条件加以解释的。探索一下这种变化的发展,对文学史丰富复杂面貌形成过程的认识,不无益处。”该文立足于文献,结合社会文化思潮、诗学趣尚的变化,得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结论。它成为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1983年,张隆溪又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了《诗无达诂》一文,对接受美学的理论内涵较早予以了阐发,对我国古典文论中所含蕴的接受美学思想也有所论及。这为新时期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开展较早提供了理论准备。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接受美学理论不断被翻译、介绍进来。与此相应,古典接受诗学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一些知名学者也涉足于此,如周勋初、萧华荣、潘啸龙、蔡镇楚、袁行霈、龙协涛、莫砺锋、张可礼、金元浦、钟振振等。他们或以自己的理论阐释,或以对具体接受个案的考察,身体力行地推动了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向前发展。由此,古典接受诗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并逐渐形成了几种较为稳定的研究路径:1、对诗学接受所进行的理论性探讨;2、对古典诗人接受的个案化考察;3、对具体诗歌作品接受的研究;4、对古典诗歌范式和诗学观念接受的考察。进入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进一步从拓展古典文学研究路径、深化古典文学研究层次的认识高度撰文,不余遗力地提倡从接受美学的视点来研究古典文学,如朱立元《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陈长荣《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等。他们努力从学科渗透与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论,这对推动九十年代以后的古典接受诗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新时期以来的古典接受诗学研究中,有几位中青年学者的研究特别值得提及。陈文忠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将文学接受作为其研究的着力点之一,发表了《柳宗元〈江雪〉接受史研究》、《从阐释史看〈饮酒·其五〉的诗学意义》等一系列论文。1996年,他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一文,对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意义、基础、环节、开展其研究的思路及具体操作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自觉的接受史意识对经典作品进行接受史研究,不仅能深化对艺术作品、诗学理论和审美规律的认识,而且开拓了一个具有无限潜力和魅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又提出:“‘诗歌接受史研究’的完整过程包括两个基本环节:其一,文献学意义上接受史料的系统整理;其二,批评学意义上接受历程的现代理论阐释。”他还对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开展予以了界分:即“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认为此三方面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三条主线。该文名为“刍议”,实对促进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学科化,具有重要的意义。1998年,他又将相关成果加以汇集,推出了专著《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2],既从宏观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对诗学接受予以了学理性探讨,又在自身理论框架内对一些经典接受个案进行了具体考察。该书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领域的首部论著。邓新华从九十年代初以来,从考察我国古典文论中的“品味”艺术接受方式入手,进入到对古典接受诗学理论与历史发展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品味”论与接受美学的异同观》、《“品味”的艺术接受方式与传统文化》等系列论文。2000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接受诗学》[3]一书,“这部著作以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从现代学术的视野,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历史流变和各种观点作了梳理和阐释,把中国早己存在的接受诗学思想做了充分而深刻的研讨,从而把它系统化、逻辑化”(王先霈序语),为“建构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接受诗学”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与邓著出版几乎同时,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又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4]一书,该书以35万字的篇幅,立足于对不同时期、不同样式文学接受的研究,对先秦至清代的文学接受历程、面貌、特征予以了详细的勾划,视野甚为开阔。其“绪论”部分则从宏观上对文学接受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从理论上进行了界定和阐述。该书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古典文学接受研究,促进文学接受研究的不断成熟,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文学接受研究中,勒成专著的还有樊宝英、辛刚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接受》,尚永亮的《庄骚传播史综论》等。限于篇幅,我们不作过多述及。
二、新时期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维面展开
1.古典接受诗学的理论性探讨
中国古典诗学中蕴含哪些接受诗学的理论内涵,与西方接受美学的异同何在?这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探讨的首要论题。继张隆溪发表《诗无达诂》一文后,不少学者对此予以了探讨。如董运庭《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殷杰、樊宝英《中国诗论的接受意蕴》,龙协涛《中西读解理论的历史嬗变与特点》,紫地《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接受论》,普慧《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解释学思想》,金元浦《空白与未定性:中国诗学的内在精蕴》,韦志成《中国阅读理论的祖碑——“以意逆志”辨》,刘月新《“出入”说——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樊宝英《论中国古典诗论的“误读”接受》,钟振振《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等。上述论文,触论到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的理论内涵、历史发展、话语特征、接受方式等一系列论题,对深入发掘古文论中的接受美学意蕴,张扬古典接受诗学的民族特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对诗歌接受方式的考察上,董运庭、邓新华、龙协涛、韦志成、陈文忠等人是做出了自己努力的。他们立足于民族独特的思维特征、接受习惯,在对中西文学接受的比较中予以立论,不断拓展和完善了对古典诗学接受方式的研究。如董运庭《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5]一文,通过比较“玩味”与接受美学对作品存在、作者与读者能动作用三个方面的不同认识,见出了深具中华民族思维特征的“玩味”艺术接受方式的优势在于:“对作品存在的认识:‘玩味’说强调被‘玩’者自身之味”;“对作者的认识:‘玩味’说强调‘诗品’出于‘人品’”;“对读者能动作用的认识:‘玩味’说强调鉴赏中的再创造”。该文立足比较,是新时期以来较早的对文学接受方式进行考察的成果之一。又如,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一书,花费了三分之一多的篇幅,详细地对我国古典接受诗学中的“玩味”、“品评”、“释义”三种接受方式予以考察,分析它们作为不同的艺术接受方式所含蕴的理论内涵、文化成因、艺术定位准则、其诗性言说方式、相互间的联系与本质差异,并将上述三种艺术接受方式分别与西方接受美学、印象式批评及阐释理论予以比较,为较好地认识我国古典诗学接受方式提供了参照。
2.古典诗人接受研究
对古典诗人接受的个案化考察,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研究者们就一些在文学历史上或广有争议的,或具有典范性的,或具有转捩意义的诗人,围绕其文学地位的起伏,读者接受侧重点的不同,历代诗论家们对其的各异阐释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棘园《东坡论杜述评》,韩钟文《朱熹论陶渊明》,朱易安《明人李杜比较研究浅说》,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陈新璋《从接受美学看苏轼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吴兆路《陶渊明的文学地位是如何逐步确立的》,邬国平《从接受文学批评角度看陶渊明》,李剑锋《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杨合林《陶渊明在东晋南北朝的被读解》等。笔者近年来也致力于对古典诗人接受的考察,发表了《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宋代诗话批评视野中的韩愈论》、《明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李贺论》等相关论文,力图对唐宋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接受一一进行考察,拟最终汇集成《唐宋诗人接受的个案化考察》(暂名)一书。
从八十年代初以来对古典诗人接受研究的开展来看,目前是存在明显欠缺的,突出地表现为研究对象的范围过窄,主要集中于几个在文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性但接受又明显存在起伏变化的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杜甫等,而以对陶渊明的接受研究为最多。因此,未来的古典诗人接受研究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要进一步将研究对象扩展开来。当然,也还需将接受的探讨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使接受研究与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想思潮的研究能更好地互融而互相发明。从已有古典诗人接受研究成果的研究路径来看,大致体现为如下几方面:(1)由点到线,以点串线,选择文学史上某人对前代某诗人的接受进行考察;(2)由面到线,线面交合,选择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对某诗人的接受予以研究,或作纵向细部梳理,或作横向不同维面的考察;(3)专注于对接受线索的清理,通观性地考察某诗人在后代接受的独特历程。上述几种研究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丰富、深化了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文学演变、发展历史的把握。
3.古典诗歌接受研究
拈取在文学历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具体诗作,或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诗歌创作、诗歌观念及某种具体诗体的接受加以考察,这也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着力开掘的领域。自1982年程千帆发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引领这一研究方向以来,古典诗歌接受的研究逐渐得到展开。八十年代中期,齐治平出版了《唐宋诗之争概述》[6]一书,他在着力从文学批评思潮演变发展的角度勾划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历史流变的同时,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千余年对唐宋诗作为两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诗型及诗歌创作观念接受的历史线索。齐书虽篇幅短小,但对于古典诗歌接受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之后,伴随古典文学接受研究中对小说作品接受研究和辞赋作品接受研究的率先开展,出现了不少对诗歌及诗学论题接受进行研究的成果。如吴祁仁《从唐代的〈金陵五题〉到清代的〈金陵怀古〉——对宋代“融化”“隐括”及其影响的思考》,萧华荣《补〈诗〉,删〈诗〉,评〈诗〉——〈诗经〉接受史上的三个“异端”》,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春怨〉阐释史新说》,申洁玲《诗经阐释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型》,张可礼《〈诗经〉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影响》,高曼霞《接受过程中的〈湘君〉、〈湘夫人〉》,邓劲夫《两千年来对〈诗经〉的若干误解》,陈桥生《论王公贵人对南朝乐府民歌的接受》,高洪奎、刘加夫《李贺歌诗的接受史研究——中唐至五代》,李正春《论六朝诗歌的传播与接受》。上述研究成果,体现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归纳起来,有以下特点:(1)通观性或断代性地考察诗歌或诗歌观念在后代接受的具体情形或不同侧重;(2)将文学历史上具有直接内在传承关系的不同诗作联系考察,钩连其演变,探究其成因及所含的审美意蕴;(3)对历史时期的某种诗体的接受整体地进行考察。以萧华荣《补〈诗〉,删〈诗〉,评〈诗〉——〈诗经〉接受史上的三个“异端”》[7]一文为例,作者选择西晋夏侯湛、束皙补写《诗经》、南宋王柏删改《诗经》和晚明钟惺等人评点《诗经》三个在正统经学家眼光看来为“异端”的接受史实予以剖析,勾划出了《诗经》由经学接受向文学接受缓慢演进的历史轨迹,将历史上“逐步撩开披到《诗三百》身上的神圣袈裟而还其文学面目的过程”阐述得极为清晰而独到。立足文献,以小见大,以点串线,是此文的最大特色。它为后来的古典诗歌接受研究作出了榜样。
在古典诗歌接受的研究中,立足于具体诗作的显晦,或某一诗学论争,反观中国古典诗学审美观念的嬗变及不同历史时期诗学的精神特征,也成为其研究的取向之一。这方面论文不多,却具有将接受研究与诗学观念、思潮流变的研究互融互渗的显著特征,因而特此提及。如周勋初《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流变》,钟涛《从陶诗显晦看中国古代诗歌审美观念的走向》,萧华荣《试论汉宋〈诗经〉学的根本分歧》等。以周勋初《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流变》[8]为例,他抓住唐人七言律诗推何作品为第一的论题,对严羽推崔颢《黄鹤楼》为第一,何景明、薛蕙推沈佺期《古意》为第一,胡应麟、潘德舆以杜甫《登高》为第一分别展开分析,使我们对不同历史期的文学审美有了极为细致的认识。
总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作为一个正在生长中的古典文学分支学科,已走过了其孕育阶段,这无论从学科理论基础的建构,还是具体研究成果的出现来看,都可得到证明。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古典接受诗学研究的范围还过窄,研究的方法也比较单一,对学科发展的系统规划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收稿日期:2002-06-23
标签: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诗经论文; 接受美学论文; 古典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