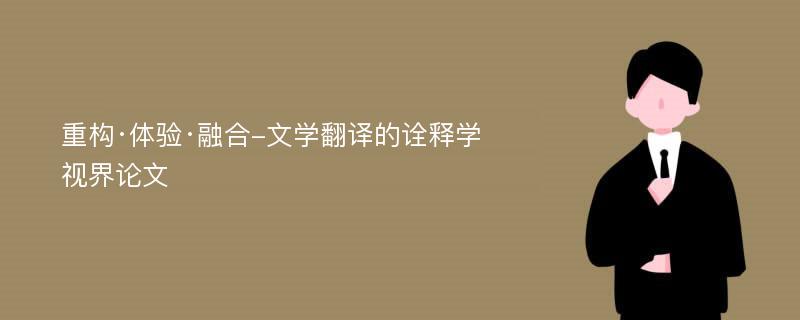
重构·体验·融合
——文学翻译的诠释学视界
李嘉辰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法学系,天津)
摘 要: 文学翻译的诠释学视界一方面能让人们更好的认识到文学翻译的性质、标准以及诠释的复杂过程。而就文学翻译的发展历程方面来看,施莱尔马赫的重构理论主要强调翻译需对原作予以客观再现;而狄尔泰则主张翻译需借助移情的方式来激发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情感共鸣。至于伽达默尔的理论则是基于了效果历史与视觉融合的原则,其认为,文学翻译需在全是作品的历史性同时启发译者通过对话创造出译语文本。
关键词: 文学翻译;诠释学;视界
近年来,翻译界讨论热度最高的话题主要集中在翻译的主体性、翻译理解以及诠释的合理性及有效性之上。当然,也正是基于以上论述,尤其是哲学诠释学代表伽达默尔所提出的历史性、世界融合以及效果历史的论述,更是加深了我们对翻译的认知,进而使得相关的研究思路及视野亦得到了极大的拓宽。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上来看,无论国内外,其在针对诠释学于文学翻译中的研究仍旧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且研究深度亦有待提升,对此,本文将通过对诠释学重要范式的研究,即基于重构、体验、视觉融合于文学翻译中的现实意义展开探讨。而纵观此前的著名论点,诸如由施莱尔马赫的重构理论主要强调翻译需对原作予以客观再现;而狄尔泰则主张翻译需借助移情的方式来激发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情感共鸣上来看,两者均未能摆脱传统西方科学主义的论调,直至伽达默尔提出效果历史意识与视觉融合,方确立了诠释着自身的历史。继而使得文化翻译能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文学翻译者的分析以及文学翻译的性质,继而逐步了解到诠释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某批原材料为φ12mm、材质为YL82B的热轧盘条,在拉拔加工过程中,发生断裂现象,图1中左侧断口从盘条周边到心部逐渐凸起,形似笔尖,右侧为与之匹配断口,呈漏斗状,这是断裂起始于截面心部,并逐渐沿周边向外扩展的一种特殊断裂方式。经了解,拉拔工艺为:热轧盘条→机械去皮→拉拔。分别在原材料及断裂样品上取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及金相试样进行检验分析,以期查明其断裂原因。
一 强调重构,立足于作者的视角
诠释学于西方可谓历史极其悠久。而传统的诠释学主要是围绕着《圣经》以及法律方面的解释。且在狄尔泰之前,诠释学仅仅只有一种方法,那便是理解与解释科学,至于文本则通常被认定为作者表达自身思想以及表现自身生活的一种方法。然而,鉴于时间距离与时间环境等变化,使得译者往往无法体会到词义的变化,进而也无法真正获取到作者的个性心理,以致种种隔膜的产生。对此,为确保理解的正确性,则必然要促使译者回返到讲话者与听话者这种原始的关系之上,如此方能让译者摆脱自身境遇及观点的束缚,继而帮助自身从历史与偏见中解放出来。当然,无论这呢啊有关弄的创造或重构,其均需基于作者原本的思想。对此,施莱尔马赫方提出了两种重构的方式与途径,其分别为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主要具有字面、外在以及客观性的特征,而后者则是基于人的心理层面,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的。
文学翻译是一种理解和诠释。为避免文学翻译反而让读者对作者的思想产生误解,则译者除了要认真研读作者的原因外,更需Udine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历史背景以及主体意义等诸多方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此方能确保自身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亦能准确表达出原作者所欲表达的思想情感。对此,郁达夫曾基于文学翻译的“信、达、雅”三大原则而进一步提出了“学、思、得”三字,其所强调的重点译者本身需具备一定的内在素质。就论点所表达的观念而言,其与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认为:译者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之前,应首先了解原作者的精神。虽然,因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存在着遥远的时间间隔,故要想领会原作者精神无疑难以加上,但我们仍不可就此放弃,而是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
就文学艺术本身而言,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当属语言,而语言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形象性。因此,要想让文学语言所传达的意义于译者头脑中构成直观化的艺术形象,则文学作品本身除了要在语言方面能让译者感知到作品的构成表象,又能切实唤起译者的‘想象’。简言之,即语言的形象性亦将囊括在抽象的语义注重。对此,当我们诠释原著时,应首先解读原文语言的语义,如此方能就原文的语言形成某种艺术形象,进而基于语言的对应再将一言塑造的形象抛开,方能真正领会到原作者的文学创作精神。否则,一切离开了形象塑造的语言均无异于空中楼阁。当然,鉴于文学翻译,其终归属于语言转化活动的一种,故若仅是依靠文艺学的方法,则必然无法避免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虽然,以体验为前提能帮助译者更好的理解作者内心及精神,但仍旧由诸多问题值得深思,诸如该方法能可真正解决精神科学的问题?体验能否促进文本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同一性?以及体验能否做到翻译的绝对忠实等。而正是基于以上问题的存在,方使得人们认为,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其最大的问题便是忽略了人生命的本来意义。
总之,基于共享型生活服务平台的社区价值共创,除产生了直接价值外,社区主体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和信任度增加,彼此间建立起更强烈的情感联系,同时社会资本增加,也对顾客忠诚度产生了积极正面影响,这些因素均促使社区整体和谐度提升。
二 深入体验,引发译者的情感共鸣
狄尔泰所说的“体验”,其特指生命体验,是一种与生命活动关联极为密切的经历。当然,也正是基于该体验与生命活动之间的密切关联,方使得该体验具有了内在、能动、主体、个体等多重性质。至于体验作品,最主要的体验对象便是要感受对象的形象、性格、清洁与技巧。作为作家的精神产物。文学作品绝不仅仅是要被分析或归纳,更重要的还是要让读者通过阅读来感知其中的精神及内涵。然而,当下的文学翻译,其劣迹往往仅是译者的再体验、再经历,具有主体性、创造性与过程性,既是一种注入了译者生命意识的经历,又是一种被激活了的译者的经历,是译者心灵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一种张力场。在体验中,译者主要通过想象、移情、神思、感悟等多种心理活动的交融、撞击,激活已有经历,并产生新的经历。经历此过程,虽是让译者有了新的经历,却无法让译者因此而获得更多的感知。以此,针对文学作品的体验过程,需译者融入自我的意境,以达到无我两忘的境界,如此方能促使译者的认知得到进一步升华,继而逐步理解对人的生命意义。正如杨苡在谈及《呼啸山庄》定名时所说,“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此间语言便是作者抓住了突然窜出的灵感,于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编写出了“呼啸山庄”四字。
作为传统诠释学的代表,狄尔泰的毕生目标便是要为精神科学奠定理论基础。其认为无论自然或精神科学,两者均是真正的科学。至于两者之间的差距,则自然科学是以事实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从事物的外部去探讨其可实证性与可认知性。至于精神科学则是加工精神与生命等具有一定客观性的事物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又具体事物的内部着手去探讨世界的精神生命。除此之外,诠释学最重要的两大概念便在于“说明”与“理解。而说明通常是将个别实例放到一般规律之上,而“理解”则是要基于译者本身的体验,继而以移情的方式进入他人的内在生命,从而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由此可见,狄尔泰所强调的“体验”,正完美诠释出了精神与自然科学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从诠释学的角度上看,因评论者个体的视域及评判的尺度不同,故即便是对同一事物进行评判,其最终的评判结果也将因评判标准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与此同时,鉴于价值本身亦是一个相对概念,且同一事物的价值也将因评估者所秉持的评判标准不同而有所差异。也正因此,方使得如今的翻译界衍生出了诸多不用的学派,如在我国便有“科学派”与“艺术派”之分,而在俄罗斯则是以“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为主。
本文基于光储电站的微电网系统,研究了离网情况下无电动汽车和有电动汽车接入时的电压质量问题。以母线电压为控制对象,提出了闲置的电动汽车参与调制的控制策略,并设置了4个算例,通过仿真验证了电动汽车在改善母线电压质量上的作用。结论如下:
三 深化视界融合,与译者深入对话
文学作品饱含作者对生命的体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因诠释的往往是基于自身当下的历史条件在进行文学作品的的翻译。因而使得其所翻译的做学作品往往具有历史事件性以及特殊性,故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伽达默尔方会提出理解的历史性应是相互理解。因文本所展现的视界必然是原作者自己的视野,而译者的视界则是基于具体的时代氛围所形成,故鉴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将引起时间间距与历史情境的变化。故伽达默尔方主张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去理解,如此方鞥呢让译者与原作者均“穿越到”同样的视界中,继而让双方均能更好的了解彼此的内心精神。
9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网”等全文收录,作者稿酬已一次付清,如不同意文章上网,请来函声明。
由此可见,理解应是两者对话统一与融合而非是由文本或译者某一方面来决定。就文学翻译而言,任何翻译均不能脱离文本单独进行。反之则是要耐心“倾听”作品本身所欲表述的任何思想。当然,在此过程中,译者还需融入自身丰富的生活经验与阅历,并认真理解为何每一次理解原作时均会产生不一样的体验及感受,围绕切实抓住每一次理解作品时的不同感受,方能从中获取更深的感悟。至于译者的每一次理解,其本质均是以此前所理解的文本世界相交融。而正是因两次理解所交融的具体感受均有不同,故使得作品也蕴含了更加丰富的意义。诸如由我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先生所翻译的歌德作品《浮士德》。两者虽有将近30年的年代之隔,但郭沫若先生翻译其第一部作品时却感到较为轻松,其原因便在于《浮士德》中包含的内容,其与我国的“五四”时代极为相似,而少年歌德的情感亦与郭沫若情感极为接近。但第二部歌德晚年所学,而郭沫若先生则先后经历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与抗日战争这段黑暗的时期,这使得两者情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也使得先生在翻译此部作品时变得苦难重重。由此可见,译者并不像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要求的那样,必须抛弃自己的视界而置身于作者的视界。否则,译者将丧失时间距离带来的好处以及自己理解文本的基点。相反,理解乍一开始,译者的视界就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视界。
伽达默尔针对德语“自身置入”一词的分析,其认为“自身置入”并非是要丢弃自身,而是要将自身置于观察之外;正如理解一部文学作品,虽是要基于历史的视界,但也并非是指译者需将自身完全置于该历史情境中,而是要具有相当的世界以将自身的思想与理解带入到相应的过程之中,如此方是真正的自我置入。且但凡存在真正翻译之处均不能抛弃原本的语言,而是要将译者自身的语言融入其中,如此翻耕在丰富译者本身的一言同时融合此前所不具备的意义。对此,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亦认为,其风格与老舍的风格极为接近,故在翻译的同时,他也习惯于借助老舍的语言风格。而这样的风格也将因译者的不同而最终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总之,就施莱尔马赫的心理重构论与狄尔泰的移情体验观而言,两者虽有极大的区别,但也有一定的共通点,那便是两者均强调译者需在翻译某一部文学作品时,将自身想象为作者的第二个“我”或另一个人格,以设身处地地重构他人经验,进而准确把握原作者的真正意图。至于两者最大的区别则在于对礼节历史性的认知,诸如伽达默尔对理解的主体则更为关注,其认为无论是译者或是原作者,双方均是理解的主体,而文学翻译本身既是一门“倾听”的艺术,又是译者参与“应答”的艺术,故两者之间无论身份或地位均是平等的,如此方能真正揭示出文本的真理。除此之外,鉴于翻译的本身并非独白,而是与原作者之间的有效对话,故双方均应对彼此“人格”给予高度尊重,若双方任何一方均过于执着于自我,则真理的大门也将越闭越紧。反之,当译者不再强调自我而是追随原作者的感受时,其与真理之间的距离也将越来越近,继而实现双方的共识与共融。
参考文献
[1] 刘树英, 任晓霏. 哲学诠释学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运用-《京华烟云》两个汉译本的对比[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 10(5):162-164.
[2] 崔东琦.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5):98-99.
[3] 陈丽.“人性”与“存真”——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视界中梁实秋的译莎活动[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02):90-93.
[4] 马铁威.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古诗翻译的多元化[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7(6X):194-194.
本文引用格式: 李嘉辰 .重构·体验·融合——文学翻译的诠释学视界[J]. 教育现代化,2019,6(49):164-166.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49.055
作者简介: 李嘉辰,男,本科学历,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法学系,研究方向: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标签:文学翻译论文; 诠释学论文; 视界论文;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法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