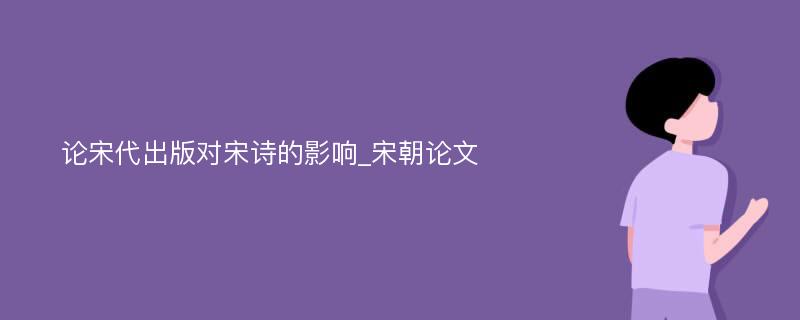
浅论宋代出版对宋诗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08)02-0085-05
有宋一代,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雕版印刷风行,出版业发达。
雕版印刷的技术至迟到隋唐之际就已出现①,但因为来自拓石等民间工艺,应用上也多局限于佛教经文等的拓印传播,主流文化领域一直未能接纳它。直到五代时期,后唐宰相冯道主持用雕版印刷了儒家经典《九经》,这一技术才开始真正服务于主流文化。宋代出版业也因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出版业的繁荣对宋代的社会文化影响巨大,本文仅拟就出版业对宋诗(主要是宋代律诗)的影响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 出版繁荣带来整个社会欣赏力水平的提升
近代实验美学对音乐的研究证明,“乐调的生熟往往能影响欣赏程度的深浅。但是欣赏力愈强者愈不易受生熟差别的影响,欣赏力愈弱者愈苦陌生的新音乐不易欣赏”②。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文学,也尤能说明宋人对宋诗的态度。读者的欣赏力愈强,对于文学形式中的新变,则愈不会感到陌生不可理解,反而会在稍事琢磨后更能体会到审美快感,反之,欣赏力愈弱,则愈对新形式无法把握,也就很难产生审美体验。欣赏力的高低显然能影响到欣赏者对于艺术形式的接受态度。
欣赏力的强弱有一定的个人资质与悟性成分,但更多地还是来自后天艺术经验的熏陶。对于诗歌来讲,阅读面越广,读的诗越多,对诗的知识了解得越广泛,则欣赏力水平也会相应的越高。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就会发现,宋代出版业的繁荣无疑成为宋世欣赏力水平提高的重要物质基础。
首先,宋代凡出版业兴盛的地方,都会是文化兴盛的地方。如江浙、福建均为宋代出版中心,这两地随之成为文化发达地区,在江浙地区,“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③。唐宋时期随着北方士人大量南迁,江南成为才俊集中之地,再加之发达的出版业,江浙文化之盛势成必然。再看福建,“宋代刻书之盛,首推闽中”④。“福建本几遍天下”⑤。福建在唐代时文化水平并不突出,然而到宋代,发达的刻书业却使这一地区成为了文化兴盛之地,到南宋后期甚至超过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浙次之,江西、东、湖南又次之”⑥。
其次,大量诗文总集、别集的刊刻为宋代整个社会文学欣赏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唐人文集多在宋人手中变成了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宋人自著诗文集约有1500种,当时多镂板刊行。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学总集《文选》在宋世刻本风行,公私均见刻印,监本、郡斋本、坊刻本齐备,宋人对《文选》也非常熟悉,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这种诗文出版的热潮对于整个社会文学欣赏水平的提高自不待言,仅以儿童读物为例即可见其影响。宋代出版的儿童读物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史知识和文字审美要求。后世知名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和《百家姓》均出自宋人之手。《三字经》中集合了大量文史典故,使宋人自小即能掌握一般性的文史知识。再看吕本中著《童蒙训》,这是宋人家塾中教小孩子的课本,其书不但提倡诗文必以苏黄为法⑦,而且在文字写作中提倡委婉典丽的表达方式:
“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不说作赋,而说雕虫;不说寄书,而说烹鲤;不说疾病,而云沉绵。“椒颂添讽味,禁火卜欢娱”,不说岁节,但云椒颂;不说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⑧。
这实际就是宋代律诗中常见的“言体不言用”的创作方法。可以想见,宋人自小即在这种文化熏陶下长大,能写出而且欣赏此类诗作也就理所当然。也即是说,我们今天看到后备感艰涩的诗作在宋人眼里很可能正是他们从小就学着做的,而在后世读者眼中最为困难的用典问题在宋代好读书的士人那里也许正是乐趣所在。因此,宋代律诗重用典、重学识等的诗体特点与其身处的文化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诗话类著作的出版成为社会欣赏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宋代诗论较之唐代呈现出极为繁荣之势。宋诗话是宋代诗学理论的代表,从其发展可以看出宋人对诗歌的欣赏与评论是日趋深入的。从形式上看,宋代诗话由早期的分散存在发展到出现《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大型综合性的诗话总集;从作者队伍看,由早期的欧阳修等文坛名流扩展到一般士人,“诗之有话,白赵宋始,几于家置一书”⑨;再从理论形态上看,由早期《六一诗话》的随笔闲谈式发展到《沧浪诗话》那样系统的理论模式。宋人诗话多镂板以行,达100卷之多的北宋诗话汇编《诗话总龟》在南宋初年即已刻印于福建,而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100卷亦有浙江刻本。这种专门针对诗歌当世评论的分散或结集出版,说明宋人诗歌的鉴赏评论与诗歌创作已经结合得十分密切。而这类撰著在社会上的出版与普及不仅会成为宋人阅读创作诗歌时的指南,诗话中的诗学意识与诗法诗病分析也同样会影响及诗作的语言形式。
2 有意识地刻书作注使宋代律诗的审美要求深入人心
2.1 出版诗集注本树立了律诗的摹仿标准
律诗的摹仿标准今人多推重杜甫,认为杜诗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天下诗人写作的楷模,这完全是一厢情愿,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杜诗为标准并非起自唐,而是立于宋。有唐一代,杜甫的影响其实很小,罗根泽早就指出这一点,他引日本人山田钝的《文笔眼心抄序》中的话:“大师(遍照金刚)入唐也,在贞元元和之际,而此编所论,专为四六骈俪,其言不及杜少陵韩昌黎何也?盖少陵变诗格,昌黎唱古文,久而后行,当时言之者少,故殷璠编河岳英灵集,选有唐名家诗,而不收少陵,韦穀著才调集,自存阅李杜集,而不录杜诗,时好之所存,亦可知焉。”⑩ 很显然,杜诗并不入当时唐诗的主流,因此唐代知名的诗作选集如《河岳英灵集》《才调集》都没有收录。真正将杜诗立为标准而且大规模摹仿的是宋人。
有宋一代,诗坛推重杜诗,叶适《徐斯远文集序》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11) 。清代吴之振《宋诗钞》亦言“宋诗大半从少陵分支”(12)。这种推崇一部分固然来自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当世名人的鼓吹与倡导,另一部分则要归功于刻本的推动与传播。我们可以通过杜甫、黄庭坚的诗歌集子在宋世的传播情况得知大概。
先看杜诗,宋代初期,刻书较少,宋初书籍主要还是以抄本的方式流通。北宋名臣韩琦说“少时家贫,学书无纸,时印板书绝少,文字皆是手写。”南宋文学家洪迈也指出“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13)。宋初曾巩所作文章“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14),可见新作还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刻书始盛于真宗、仁宗朝。杜诗的大面积流传即是自仁宗朝后期开始的。宋人编集并校注杜诗,其主要目的就是有意识地广泛传播杜甫诗作。杜甫诗集定本的最早镂版是在嘉祐年间,王琪守吴郡时,在姑苏刻了家藏的《杜工部集》二十卷,印了一万本,士人争买(15)。尽管王琪有一定的经济目的,是为了补上修建厅堂所借公家的钱,但他在后记中也说将杜集镂于版是为了“庶广其传”(16),即是有意识地要让杜诗广为流传。到南宋,郭知达有感于当时市面上流行假托苏东坡所写的《杜诗故事》,混淆了杜诗的真面目,于是出资刊行《九家集注杜诗》,“大书锓版,置之郡斋,以公其传”(17),目的是为了让真正的杜诗广为流传,有以正视听之意。
宋人不仅整理杜诗以广其传,还通过各种注本来有意识地普及杜诗。为杜诗作注始自宋人,注本都是刻本,注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面向社会公众传播,以达到提倡杜诗和普及杜诗的目的。南宋蔡梦弼编《草堂诗笺》时,在跋文中称自己“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重复参校,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其岁月之先后,以为定本。于本文各句之下,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之反切,方举作诗之义以释之,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从出。离为若干卷,目曰《草堂诗菚》。尝参以蜀石碑及诸儒定本,各因其实以条纪之。凡诸家义训皆采录集中,而旧德硕儒间有一二说者,亦两存之,以俟博识之抉择”(18)。蔡梦弼先搜集了足够多的杜诗集子,然后互相参校,编为定本,字音、字义、用事都参考相关资料作了详细讲解,不同解释也加以存录,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阅读起来更方便。“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览,口诵心惟,不劳思索而昭然义见,更无纤毫凝滞,如亲聆少陵之声欬而熟睹其眉宇,岂不快哉”(19)。可想而知,这种着眼于读者阅读需求、质量上乘的注本必定会赢得较广的读者群。今传宋人注杜诗之作有:赵次公《杜诗先后解》,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黄希原《黄氏补注杜诗》,黄鹤(黄希原之子)《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鲁訔编、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20)。有宋一代,以杜诗注本为最多,至有“千家注”之说。南宋董居谊为黄希原《黄氏补注杜诗》作序说:“近世锓板注以集名者毋虑二百家”(21)。此序作于南宋宝庆二年,是为南宋中叶,则董所说近世,恐怕以南宋可能性为大,一百多年间就有二百多家注杜诗的集子雕版印行,可见杜诗在宋世流传之广。北宋中叶以后,“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蔡宽夫诗话》)(22)。这种景况与宋人有意识地推广杜诗之举是分不开的。
宋人以注本的形式整理杜诗,除了有推广之意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通过在注本中讲解杜诗,为学习杜诗树立标准。在宋代的杜诗注本中,大都十分侧重对杜诗艺术手法的讲解。较早的赵次公注本在注释中即首创“句法义例”,从艺术特点的角度讲解杜诗句法,以后注本大都沿袭这种传统。这种对杜诗艺术手法的重视对于摹仿与创新都极有益处。另外,杜甫生平的考证、年谱的编订到宋代已基本成型。南宋蔡梦弼在《草堂诗跋外》还专门编选了《草堂诗话》二卷,专论杜甫诗歌,全书对杜诗的渊源、家学、修辞、用典、交游等均有记述,并且间以作者的按语,这已经是专题性的研究了。至此,杜诗有集、有注、有生平考证与艺术研究,围绕一个诗人进行如此全面透彻的评析,宋以前从未有过。宋世有如此多的人争相去编集、刻印、注解和推广杜诗,爱好固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更大原因恐怕还在于对一种诗作规范的有意提倡,对一种诗歌审美风尚的自觉标举,而刻本的便捷就为这种提倡提供了最佳载体和最大可能性。
再看黄庭坚的诗集。宋代黄庭坚的诗文集版本众多,出版地域涉及四川、江西、福建和浙江,其注本不下10家,还有为数不少的总集本或合刻本,如《江西诗派》《苏门六君子集》《四学士文集》《黄陈诗集注》等。而且黄庭坚的诗文集刻本大都带有推介、研究的浓厚色彩。黄庭坚的文集定本《豫章集》由其外甥洪炎在南宋初年编集刊刻,洪炎在编集的时候,只选了黄庭坚壮年之后的作品,而于少时之作一无所取,因为他认为要选取精粹之作。这已含有十分明确的编辑意识和指向性了。十多年后,黄庭坚的后人又从各种资料中搜集整理,编成黄庭坚《年谱》三十卷。显然是为研究学习之用。黄庭坚在世之时即有人为他的诗作做注。最有名的注本是四川人任渊所做,而任渊在黄庭坚到四川时曾亲自登门执弟子礼,后闲暇时便取黄庭坚、陈师道二家诗进行注释,可见其注在黄庭坚在世时即已在进行,南宋时任渊注本刻于四川。后又有史容的注本,也刻于四川,其注本后又重刊。这样,黄庭坚的诗文集在宋代即已呈现出完整的面貌,既有可资学习参考的注本,又有可深入研究的《年谱》,还有去取标准不同的各种选本,通过这些刻本,宋人就完全可以对黄庭坚进行系统性的摹仿与学习了。另外,任渊也为江西诗派的另一领袖陈师道的诗作了注,《后山诗注》在宋代也有数种刻本。
我们注意到,与杜诗之注不同,这是当代人为当代人做的注,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苏轼。宋世苏轼的诗文注就有“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百家注”等诸多名目,足见影响之大。而宋人学诗尊杜、尊苏黄,蔚为风气,注本之力不可小视。
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到南宋时,士人多把当世诗作为创作学习的标准,南宋胡仔云“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23)。足见南宋时的士人多直接学习江西派,不再上溯到杜甫。这与江西派诗人诗集刻本的大量流传有直接关系。
2.2 以诗派为名结集流通使律诗的语言特征得到突出
江西诗派在宋代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成为中国诗学史上第一个正式宗派,也与刻本有极密切的关系。北宋末年吕本中把效法黄庭坚的诗人25人罗列在一起,作了《江西诗社宗派图》加以推介,其序云“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无余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原流皆出豫章也”(24)。从此之后,江西诗派之名得以确立。南宋时程叔达编《江西宗派诗集》115卷,曾巩的族侄曾纮编《江西续宗派诗集》2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江西诗派》137卷,《续集》13卷。可见当世即有这一诗派的三四种版本的集子流传,而且卷数众多。清代朱彝尊曾指出“终宋之世,诗集流传于今惟江西最盛”(25)。清代看到的宋人诗集还以江西诗派的为最多,可见当时江西诗派的流传之广。
宋代的律诗写作尽管有杨万里、陆游、永嘉四灵、江湖诗派等不同于江西诗派的风格,但一个总体特点是,他们都与江西诗派有着割不断的关系。杨万里始终佩服黄庭坚与陈师道,所以尽管在诗歌形式上尽量多用俗语,但钱钟书说他骨子里还是江西诗派重用典的底子,俗语也要挑来头大的用。陆游对诗作的要求是“律令合时方贴妥,工夫深处却平夷”(《追忆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而且在诗中也善用典故和精致的对偶,同样承袭着江西诗派的作风。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推尊晚唐的目的即是为了反对江西诗派。可以说,江西诗风是整个宋代诗坛特别是律诗领域中的一株长青树,几乎没有人能不受它的影响,而正是不断出版的江西诗派的诗集刻本使得江西诗风真正深入人心。
宋末另一著名诗派江湖诗派的声名也是与出版业息息相关。南宋末年,杭州书商陈起为江湖诗人刻印诗集,他采用丛刊的形式,随得随刻,一家一家地出版,后总名为《江湖集》(2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曾著录此书:“《江湖集》九卷,临安书坊所刻本,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士之不能自暴白于世者,或赖此以有传。”(27) 江湖诗派的定型实赖陈起结集刊刻之力,“由于陈起刊刻《江湖集》,使得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诗坛上站了起来,由过去散漫的聚合,一变而为集团性的行动,从而大大扩展了诗派的社会影响。”(28)
这种以诗派为中心的结集出版,其特点是挑选审美倾向创作风格类似的作者汇编为集,如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所云:“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29) 江西诗派的成员并不都是江西人,名之为江西更多地是从他们诗作的审美风格上着眼,即“以味不以形”。这种根据相似诗作风格统一结集的行为本身不但使一种诗歌流派的面貌清晰起来,而且借刻本之力,其诗派所含蕴的审美倾向与艺术风格很快就可以在社会上普及开来。程叔达在江西刊刻115卷《江西宗派集》的目的是“兴发西山章江之秀,激扬江西人物之美,鼓动骚人国风之盛”(30)。也明显是为了张扬一种风习,倡导一种审美风尚。陈起之所以刊刻《江湖诗集》原因在于他是晚唐诗的忠实爱好者,他的书铺就出版了很多晚唐人的诗集,因此,《江湖诗集》的刊刻本身包含着他对晚唐诗风的钟爱与推重。而这种刊刻也确实起到了引领一时风气的作用。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说陈起刊刻的《江湖集》“书一刊出,即引起很大反响。时人写诗赞云:‘雕残沈谢陶居首,披剥韦陈杜不卑。谁把中兴后收拾?自应江左久参差’”(31)。总起来看,这种有意识地多卷本结集出版不但有利于突出诗派的整体审美风貌,而且非常有利于普及诗派的审美观念。
从总体上看,宋代发达的出版业创造了一种好读书重学识的社会风尚,也为宋人诗歌语言经验的积累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从而为宋代律诗语言形式中用典之风、学识之风的盛行提供了阅读经验积累的物质条件。同时,宋人可以借助出版之力引导和提倡一种诗作标准和审美风格,并使之能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宋代律诗语言风貌的形成即得力于杜甫、黄庭坚诗作的编集整理与注释,更得力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刻与流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把宋代的刻本出版当作宋代律诗资以形成其自身特色的强大的媒介保证。
(收稿日期:2007-11-20)
注释:
① 陈静.从唐代拓石看雕版印刷的产生[J].中国文化月刊(台湾),2001(257):63-78
② 朱光潜.文艺心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310
③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史部·编年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④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9:39
⑤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子部·杂说类·杂家之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⑥ 吴潜.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许国公奏议·卷二[M]//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29
⑦ 童蒙训·四库提要[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子部·儒家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⑧(22)(23) [宋]胡仔.渔隐丛话[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集部·诗文评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前集卷12,前集卷22,前集卷49
⑨ [清]息翁.兰从诗话序[M]//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64
⑩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3
(11) [宋]叶适.水心集(卷12)[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2) [清]吴之振.宋诗钞(卷64)[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集部·总集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3)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43
(14)(20) 冯钦善.中国古代文献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541,519
(15)(16)(17)(18)(19)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42,2242,2248,2249,2249
(21) 黄希原.补注杜诗·原序[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4) [宋]赵彦衛.云麓漫抄(卷14)[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5) [清]朱彝尊.竹斋诗集[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集部·别集类·竹斋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6) 四库全书·江湖后集提要[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集部·总集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7)[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428
(28)(31)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5:24,23
(29)(30) [宋]王霆震.古文集成(卷4)[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集部·总集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标签:宋朝论文; 诗歌论文; 黄庭坚论文; 江西诗派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杜甫论文; 南宋论文; 江湖集论文; 文渊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