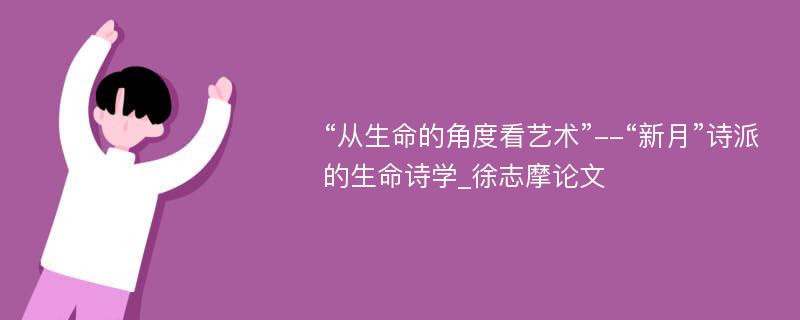
“以生命的眼光看艺术”——“新月”诗派的生命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命论文,诗学论文,新月论文,眼光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是实现生命的”,“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新月”诗人都有这种近似的生命哲学,都坚守这种以生命为本位的生命美学观。“新月”前期的徐志摩、后期的林徽因坚持这种生命美学观。这种生命美学观贯穿于他们诗歌创作的始终。他们以“生命的眼光看艺术”,以艺术的眼光审视生命,创造了中国现代新诗的新的艺术高度。这种美学观迥异于新文学创建与发展时的其他诗学观念。同他们的文学审美论思想在那个时代被遮蔽一样,现代文学史上,“新月”的生命美学观也被现代文学启蒙与民族救亡的伟大的时代主题所遮蔽。
一 《新月的态度》:“新月”生命诗学观的诗意表述
郭沫若认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同郭沫若一样,“新月”诗人也在诗与生命之间确认了一种内在联系:将诗歌当作是对生命的“审美”,从生命视角来看取文学及其价值。徐志摩讲,“文学是实现生命的”,“诗是写人们的情绪的感受和发生”。艺术紧密的联系着生命:“我们的生命存在确实太可怜了。人生的贫乏必然导致艺术的贫乏。”(注:徐志摩《艺术与人生》,《徐志摩全集·散文卷(上)》,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87、89页。)“诗人中最好的榜样:我最爱中国的李白,外国的雪莱。他们的生平经历就是一首极好的长诗。”(注:《徐志摩全集》第8卷,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461页。)梁实秋讲“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 亦止于人性”(注:梁实秋《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第122页。);朱湘说“诗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常新的:它便是人性”(注:朱湘《北海记游》,《朱湘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饶孟侃讲人生是诗的原料之一。闻一多认为“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注:闻一多《爱国与诗》,《晨报·诗镌》1号,1926年。)。“至于诗这东西,不当专门以油头粉面,娇声媚态去逢迎人,它是应该有点骨格的,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注:闻一多《邓以蛰〈诗与历史〉识》,《诗镌》第2号,1926年。)1928年,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对这种内在联系作了富有诗意的表述:“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他那无限的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望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则生命的努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吧,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吧,我们想象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新月”诗人在诗与生命之间确认的这种内在联系,受西方生命哲学的启迪,并依据于这样一个逻辑前提:诗歌与生命之间存在一种同源同构关系——“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本源,文学是生命的反映。这个前提的确立使“新月”诗人找到了话语的立足点。站在这个话语制高点上,在五四“人的文学”观念影响下,“新月”诗人高举五四“启蒙”的大纛,追求个性的解放与个性的自由,把人性奉为信条,把艺术奉为宗教,在诗歌创作中表达着自己,诠释着自己,阐释他们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在“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以后,“新月”诗人又把“启蒙”的重心转移到了对个体生命和个体内心世界的关注上,接受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在生命与艺术间构造他们的“醇正”与“尊严”,从而构筑了他们的生命诗学观。
按生命哲学的理论,世界现实根本上来说是生命。生命哲学从生命角度对世界本质的思考与诠释,启发了渴求新的人生观的“新月”诗人的灵感:既然生命是世界的本源,又是本体,那么,把“最高的努力的目标”和“生命本体”相联系的“新月”诗人就必然看重生命了。他们信奉“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象”。据此,“新月”诗人的创作相当一致地表现出了下述两个特点:用生命意识来观照世间一切,表现出对生命的执着思考与探索;诗学批评基本遵循人性的标准。
“生命”一词是“新月”诗人最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在他们的语汇中,生命是一切之源,尤其是诗(与艺术)的源泉。生命被赋予相当于本体的意义。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艺术活动,目的就是生命启蒙,人生的启蒙,重新恢复生命原本的意义。因为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无所谓善恶可言,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正如西方的基督教文明里,对生命做了许多道德与伦理的评价,把许多正常合理的生命冲动视为罪恶,严重的遏制与践踏着生命,摧残着人性。反封建、反礼教,倡导科学、文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其中就包含新的生命的启蒙。“新月”诗人,尤其是像徐志摩这样的诗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艺术活动就是生命启蒙,人生的启蒙,恢复生命原本的意义。这样一来,“新月”诗人的生命的启蒙便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通过标举“性灵”而申述生命的诗歌观念,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在新的文化制高点上对生命进行了新的审美。
郭沫若在《生命的文学》一文里说:“文学与生命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注:王锦厚等《郭沫若佚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文学愈有生命,愈真,愈善,愈美。”郭沫若的这个观点同五四“人的文学”的观念相一致,强调了文学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新月”诗人“文学是实现生命的”观点颇类郭沫若,比郭沫若更为理性的是,“新月”诗人从生命、人生、人性等诸生命体系确认文学及其文学的价值系统,构建了他们有关文学的新设想,在诸多关于文学观念的探索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并在此前提下对诗美的本质进行了新的体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诗学观念,由此影响下的创作将必定是新的模样。由于这种生命诗学观是在五四人性解放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这种背景下那种解放了的人性的生命惊喜和欢畅、生命的追求与理想、时间体验与人生体验、自由与幻美追求、自我裂变与精神突围的展示的诗歌就显得格外的清新,格外的有力量,也格外的具有“深意”。
“新月”的生命诗歌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初以“文学是实现生命的”或者“文学的本质是生命”来表述,30年代左右以“人性论”来表述。“新月”诗派活动十多年,根本上坚守的就是这样一种诗歌观。徐志摩1922年在清华所作的演讲《艺术与人生》、1928年写的《新月的态度》和陈梦家1931年所写的《新月诗选·序言》中,都宣告过这种观念;“新月”诗派的诗,从《诗镌》、《新月》到《诗刊》到《新月诗选》,无不辉映着生命的光辉。今天阅读“新月”的诗,如果抛开他们的生命诗学思想,恐怕也还是不能真正作出理想的诠释,如徐诗“并无深意但清新可爱”,闻一多的诗“只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自我夸说”。因而,某种程度上来说,从徐志摩《“新月”的态度》的艺术生命观出发,也许我们会理解“新月”诗歌的真谛。
二 “以生命的眼光看艺术”:生命诗学观的哲学依据
“诗者,吟咏性情也。”从严羽的这种认识到袁枚的“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抒怀抱”,再到郭沫若的诗的本质专在抒情,中国诗学一直给我们提供着丰富的生命信息:诗人生命的理想、志趣、怀抱、他们的生命形式、存在状态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全在诗中。“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袁枚《随园诗话·答何水部》)“新月”诗人继承了中国诗学的这个传统,发展了这个传统。他们认为文学是实现生命的,并将生命理解成一个整体,并在现代的生命意识高度将“性情”、“性灵”、“情感”赋予了生命的价值内涵。徐志摩一再强调诗歌的“生命气魄”,闻一多强调“人类生活的经验”、“境遇”,梁实秋标举“普遍固定永恒的人性”,都从不同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吟咏性情”的诗学观念。
就思想与美学角度来说,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人本主义和18世纪以来欧洲文学的浪漫主义对“新月”诗人的生命诗学观的形成有直接的催生作用。“新月”诗人受浪漫主义影响,又在“新人文主义”的思想下进行着深刻的艺术与生命的反思,渐次树立了他们颇有新意的生命诗学观念。如徐志摩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充满着生命意识的绘画、丹浓雪乌(邓南遮)的文学创作和“翡冷翠”(佛罗伦萨)的陶醉,闻一多对文艺复兴及其西洋绘画的人文主题的专心,表明了这种影响的直接。又如,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重要主题——对情爱与女性的歌颂,对生命的颂扬,也成了“新月”诗人诗歌的一个恒常主题。
欧洲浪漫主义诗人把情感、意志、心灵、灵魂当作生命的体现,“新月”诗人也如此看待。华兹华斯认为,诗歌的特质在于表现情感,激情是诗歌的灵魂,好诗都是澎湃激情的自然倾泻,这被“新月”诗人所共同信奉。华兹华斯还说一切好诗的共同点就是合情合理(注:刘庆璋《欧洲文学理论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这颇合梁实秋的“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古典主义”的文学理想,又被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等“新月”领袖在诗歌创作的鼎盛期所遵循。
就哲学层面上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生命哲学的兴起和流行应该是“新月”生命诗学观形成的最为深刻的原因。这种哲学“把揭示人的生命的性质和意义作为全部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进而推及人的存在及其全部认识和实践,特别是人的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再由人的生命和存在推及人的历史与文化,以至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换言之,由对生命的揭示而推及对整个世界的揭示”(注: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19页、125页、126页。)。他们认为哲学所探索的不是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而是内在于并激荡着整个世界的生命。他们把生命看作是主体对自己存在的体验、领悟,也就是心灵的内在冲动、活动和过程;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看作是具有活力、或者说具有能动性、创造力的生命存在。柏格森运用变化和整体联系的观点说明生命现象,为生命哲学提供了完整的理论形态。他的《创造进化论》认为,世界现实根本上来说是生命,它们如同火焰的腾起与扩展,具有无限的活力。狄尔泰是历史—文化生命哲学的代表。他的视野中的生命,大体上是指人的生活体验,即作为反思主体的人内在的体验和领悟到的生命,它包含了主动的参与的动态意义。他把精神科学看成是对生命的解释,认为人文科学只能以对生命的体验、表达和理解为基础:“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量性的东西才有可能,……那么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注: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19页、125页、126页。)“生命以及对生命的体验是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的生生不息、永远流动的源泉;从生命出发,理解渗透着不断更新的深度,只有在对生命和社会的反映里,各种精神科学才获得其最高意义,而且是不断增长着的意义。”(注: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19页、125页、126页。)齐美尔则畅言自我意识、“个人规律”与人格,从内部的立场来观察生命:“内在性,我们只能把它称为是生命。”“生命本身,……靠它的迫切感、它的超越力量,它的变化和区别,生命给予全部运动动力。”(注:李健鸣译、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08页、46页。)按费迪南·费尔曼的分类,生命哲学的近代历史有两个时期:与浪漫主义相近的18世纪和19世纪交替的生命哲学和1900年左右的生命哲学。他认为,正是后者为本世纪精神发展奠定了基础。“什么是浪漫主义?每种艺术,每种哲学,都可以看作服务于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的药剂和辅助手段,它们始终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前提的。然而,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过剩的痛苦者,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另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静谧的海洋,自我解脱,或者迷醉,痉挛,麻痹,疯狂。”(注:周国平译《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12月1版,第253页。)像尼采这样的生命哲学家观照艺术——浪漫主义艺术,看中的就是其生命基础。
西方生命哲学缘起的背景是什么呢?一般的结论是这样的: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人们对启蒙思想家所赞许的理性和国家的理想业已破灭,加之传统形而上学以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形式出现的各种认识论上的局限充分暴露,黑格尔学派解体,于是,哲学上的转向之风暴起,人的自由、价值、生命、历史和文化等问题代替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成了哲学家们最关切的问题,生命力代替物质和精神本质成了全部哲学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新月”诗人接受生命哲学的背景与此极为相似。先是,他们高举五四启蒙的大旗,进行科学、民主以及人的启蒙,随着五四的落潮,民主政治理想的破灭,和人生理想的幻灭,以及社会价值的失范,接着,他们便退居内心,在生命的审视中力图找到一种最低的道德底线与价值底线。这种情况下,浪漫主义的生命观和生命哲学便给了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这种从对生命意义的揭示出发来探讨精神生活、文化、历史和价值问题的理论,成了“新月”诗人最为心仪的理论。为了解释艺术,便必须从生命出发,从生命出发,便能真正理解艺术,理解诗。徐志摩的创作与批评的缘起,大体遵循了这个理路。他的诗歌创作的灵感是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激发的,他评诗的标准也是这种生命意识。他的那篇《济慈的夜莺歌》展示了这种倾向,拿生命哲学的标准评衡一首诗歌:“‘生’是有限的,生的幸福也是有限的,——诗,声名与美是我们活着时的最高的理想,但都不及死,因为死是无限的,解化的,与无尽流的精神相投契的,死才是生命的最高的蜜酒,……比生命更深奥更博大的死,那就是永生。懂得了他的生死的概念我们再来解释他的诗。”(注:《徐志摩全集》第3卷,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75页。)因此,对于诗人来说,发现和表达人的这种性质、意义及深层存在的哲学的方式就是诗了。徐志摩“文学是实现生命的”是这个结论的最好注解。
生命哲学给“新月”诗人的影响还在于,生命哲学确立的以人为世界本原和哲学研究核心的思想,为他们的生命诗学观提供了新的价值尺度,为他们诗歌的主题确立了新的意义深度。徐志摩说:“爱虽然最不严肃,却是万物中最有意义的。”“人的精神在一个文化统一体中,在生活潜能最大限度的一致表现中,享有实现自我的幸福机会,这种生活是丰富、热烈、生动和自觉的。”(注:徐志摩《艺术与人生》,《徐志摩全集·散文卷(上)》,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87、89页。)爱最有意义,“自我”表现的诗歌最有价值。徐志摩和“新月”诗人从尼采等生命哲学家那里,从生命哲学处为他们的生命诗学观找到了内在依据。
尼采说他的《悲剧的诞生》是一次“以生命的眼光看艺术”的尝试:“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德国哲学家费迪南·费尔曼说尼采“把艺术看成是生命的表达——生命的眼光必然是有远见的——就使美学经验变成了某种‘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同时也是‘有意思的东西’,在这种有意思的东西中,个人的生活以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注:李健鸣译、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08页、46页。)。“新月”诗人的生命诗学观,是生命与人性的凝思,也是以生命的眼光看艺术,它的理论渊源就是佩特等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者、唯美主义者的浪漫主义生命观和尼采等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诗学观正如费迪南·费尔曼所说,把美学经验变成了某种“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同时也是“有意思的东西”。“新月”生命诗学观的深刻的艺术的、美学的、哲学的渊源盖在于此。
三 生命之在的沉思:“新月”诗歌生命内涵与生命意识
依据“新月”诗人的这种生命诗学观及其渊源关系,我们可以对“新月”诗歌作出一种新的诠释,即“新月”诗歌并非是通常所说的那种虽清新可读却了无深意之作,也并非仅仅是浪漫诗人的自我夸说之作,在生命及其存在意义上,它显示着独特的价值。具体说来,诗歌创作,就是“新月”诗人生命的展示与审视,对生命的沉思与审美。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人命关天”的思想,突出的是生命价值之巨大,意义之至深。这是从人道关怀审视生命的结论。事实是,当我们从人道主义角度审视生命,对生命审美,世上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包括我们自身的生命,会叫你产生奇特的冲动与感动,这种冲动与感动的书写便是诗。“新月”诗人,那群高尚的人道主义者,生命哲学给他们的灵感,传统文化的生命情怀给他们的诱发,他们的诗也便由此而生:“夏娃:‘亚当,我见亮光了!/好一个美妙天地!/赶快睁开你的眼皮,你我准备见面礼。’/亚当:‘你的疯话我不信,/哪有眼皮会睁开——/咳,真奇怪,果真两眼/有些发痒酸齑齑,/夏娃,夏娃,真稀奇,/果然是光亮天地!’/夏娃:‘不成,慢点儿过来,/你我原来是裸体!/不好了,快躲起来,/那边来的是上帝。’”(注:《徐志摩全集·诗集·人种由来》,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徐志摩认为,生命的觉醒和艺术的觉醒是共时的, 爱意识的觉醒是生命意识觉醒的前提:“‘爱窍’不通,哪能懂得生命,‘美窍’不通,哪能懂得艺术,‘知识窍’不通,哪能认识真理,灵窍不通,哪能望见上帝。”“通过爱和宣泄自己的情感和精力,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充实而自由的男人和女人。”(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再来跑一次野马——致孙伏园》,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234页。)徐志摩的《情死》,就是对“充实而自由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命最真实的审视:因为爱,生命才相互发现,相互实现。又如《雪花的快乐》,分明就展示了新个性那颗灵动的心,对美欢喜的情状和灵魂的惊栗:把艺术看做是生命的实现,美的发现,独特生命力的发现,表现的是那新个性“欢喜的心和灵魂的觉醒”。“新月”诗人中,闻一多的《红烛》、朱湘的《夏天》等浪漫主义诗歌,大多如徐志摩创作,主题是爱与生命的启蒙,以及发现新个性的惊异。
凡是浪漫派的文人,主观的色彩是少不了的,也极为推崇内心的情感。他们一般不满现实的世界,都市的烦嚣,人生的痛苦,他们要找一个生活的满意途径,唯有向一己的内心去寻求。他们用神奇的想象,去开掘内心的秘府,因此,他们的作品,多是心血造成的琴瑟,人们读了立刻会领会到生命的可贵和现实的无穷。“新月”诗人的作品就是如此,留恋“主观”、尊捧一掬“内心的情感”,以个体生命的观照为出发点,表现一个个觉醒灵魂的生命实现和生命自觉,以及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任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融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抒情主人公浪漫,飘逸,洒脱,诗歌展示的是个体生命的惊喜与欢畅。朱湘的《雨景》,尊捧一掬“内心的情感”,展示的是个体生命内心的丰富与自持:“我所喜爱的雨景也多着呀:/春雨春夜时窗前的淅沥;/急雨点打上蕉叶的声音;雾一般拂着人脸的雨丝;/从雷电中泼下来的雷雨—/但将雨似的天我最爱了。/它虽然是灰色的却透明;/它蕴着一种无声的期待。并且从云气中,不知那里,/飘来了一声清脆的鸟啼。”诗是一个觉醒灵魂的自我欣赏。
“新月”诗人重视“既美好又可怕的灵魂的现实”的表现,这使他们生命诗学的内容具有了某种内在的深度。人类超越的精神,情爱本能的理性,灵与肉的冲突,灵魂里善恶的较量,“新月”诗人诗歌能多方面得到展示。一方面,他们那令人惊异的美的艺术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和人类灵魂所能表现的最深切最崇高的感情。《猛虎集》、《死水》、《石门集》、《花一般的罪恶》及《新月诗选》的部分诗作,展示的正是这种内容。另一方面,《情死》、《爱的灵感》、《末日》、《你指着太阳起誓》,展示生命那种矛盾着的状态,探索了人类情感的矛盾品质。这使他们的诗歌更有意义,更具现代性,而《蛇》、《女人》,尤其是《女人》一诗,把生命中具有的那种矛盾的状态展示得淋漓尽致:“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你用温润的平声干脆的仄声/来捆缚住我的一字一句。/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
“新月”诗派生命诗学观的内容还包括把生活和艺术联系起来,在文学旨趣上与生活旨趣上求其相同相谐,在艺术中追求生活的理想,或者说在文学中实现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生活。徐志摩说:“关心人生才能关心艺术,……只要努力追求艺术的激情,就会认识美和人生的价值。……然后,应把生活本身作为一件艺术品,或一个艺术问题”,“生活是件艺术品”(注:徐志摩《艺术与人生》,《徐志摩全集·散文卷(上)》,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87、89页。)。徐志摩、闻一多等“新月”派诗人崇尚的“艺术人生”的主张对后来的“京派”作家影响极大,就是在当时,也表现了“他们试图在侧重思想启蒙的文学观和侧重情感宣泄的文学观之间作某些调和,以期达到在对传统和西方双向冲撞下的新文学走向的恰当把握”(注:杜卫《走出审美城》,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的努力。
既然把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对生活的把玩、欣赏,一种绅士风情、一种生活情调也便有了深长的意义。徐志摩《石虎胡同七号》、闻一多《闻一多先生的书桌》等诗歌,审视自己的生活,表现一种闲适的情调。另外,“风花雪月”的吟咏,在“新月”诗人,也便是他们生活方式的追求。如像《再别康桥》,诗人面对政治理想的破灭、爱情人生的坎坷,所具有的那份耐心,那种品味:“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表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人生无奈的一种洒脱情怀。不是撕心裂肺,那样太失风度,不是颓废、放纵,那样太乏涵养,不是勇烈、刚劲,那样太矫情,而是洒脱的面对。这就是所谓“艺术人生”,是“新月”诗人的艺术与人生,一种“小资情调”的人生。“新月”诗人生命的风范在此,“新月”诗派诗歌的独特魅力也在此。
徐志摩“文学是实现生命的”诗学观还包括对生命的“静观”与“直观”,在“静观”中体会生命的刹那间的意义。他认为感觉的本身而非感受的果实才是目的,强调人的经验的本身,而不是它的结果或目的。所谓“经验的本身”又指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个体内心的生命体验。如他的诗歌作品《沙扬娜拉》、《山中》,包括《偶然》,都是这种观念的结晶。其它如陈梦家的《生命》,在“静观”的体验中体验着生命的渺小、随意及不关痛痒。《迟疑》则表现对爱情的“刹那”体验。“新月”诗歌到后期,生命中的这种体验越来越多地被关注。像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尽管是“一句爱的赞颂”,却无疑是对一种生命的“静观”与颂扬:“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白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由此诗我们可以联想到席慕蓉那首名诗《一颗开花的树》:“让你如何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颗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的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的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好多时候,我们认为席慕蓉的诗歌是爱情诗。其实,这首诗表达的是对青春与生命的珍惜之情,与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有相同的旨趣:诗,是对生命的审美。
存在主义美学也是一种生命诗学。同哲学上的生命哲学必然走向存在主义一样,后期“新月”诗人的诗作,如陈梦家的《一朵野花》,方令孺的《诗一首》,就闪耀着存在主义美学的光辉。“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香火的热,/长河一道的水流。/看,那山岗上一匹小犊,/临着白的世界;/不要说它愚碌,它只默然/严守着它的静穆”。诗有种对个体生命的自尊与庄严的深刻的审视与“静观”,以及对存在的独有领悟。对林徽因而言,她更多关注生命、灵魂的沉静状态和生命的极终思索:“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美丽的想象。”(《深夜里听到乐声》)这是一种典型的存在之思。像陈梦家的《雁子》:“我爱秋天的雁子/终夜不知疲倦:/(像是嘱咐,像是答应)/一边叫,一边飞远。/从来不问他的歌,/留在那片云上?/只管唱过,只管飞扬,/黑的天,轻的翅膀。/我愿是只秋天的雁子,/一切都是忘记—/当我提起,当我想到:/不是恨,不是欢喜。”对自我生命方式的选择与个体生命内在价值的持守,使诗歌显得特有个性。越到后期,“新月”诗人诗歌创作的生命意识日益浓厚,命运感更强。方令孺、林徽因和陈梦家等的诗,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与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相比,后期“新月”诗人的创作少了些激情,却多了些存在之思,以纪弦等现代派诗人的美学观念权衡,这应该是新诗艺术的进步。
四 另一种声音:“新月”生命诗学观的诗学意义
“新月”诗派的生命诗学观有很现实的诗学意义。作为一种在生命哲学影响下形成的诗学观念,它强调从生命出发的艺术本体观,侧重的是人的情感的表现,人性的挖掘,心灵的展示,个体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探寻,以及生命及其存在命运的思考。这与生命哲学家关注的问题相一致。柏格森认为,哲学应该在我们的感觉与意识之内去寻求事物的实在性,从生命内部,从时间里去把握生命。纯粹绵延(时间)只有在自我意识中凭直觉才能把握它。时间是生命的本质。人文科学只能以对生命的体验、表达与理解为基础。“新月”诗歌对这类“实在性”的把握往往内在而直接:“我当年初临生命的消息,/梦觉似的骤感恋爱之庄严;/生命的觉悟是爱之成年,/我今又因死而感生与恋之涯沿。……我泪洒向风中遥送,/问何时能勘破生死之门?”(徐志摩《哀曼殊斐尔》)这显然是时间的追问,生命本质的追问。我们千百年来的优秀诗、抒发性灵的诗无不是在阐释着这种生命的哲学,“新月”诗歌更典型。持这种哲学的“新月”诗人的诗歌叫我们记着自己是活生生的生命,记着艺术或诗永远写的是生命和它的体验,这是“新月”的独特所在,也是“新月”生命诗学观的根本内涵与意义所在。把诗与生命分开这是诗的不幸。现代诗歌曲折发展的历程,它的经验与教训时时回应着“新月”诗人的那种思考与探索,即使今日的新潮诗,探索的起点仍然是生命,坚持的也是这种以生命为本位的生命美学观。
生命诗学观既是在艺术本源意义上对诗的一次确认,又是新文学不同艺术观念中极有生命力的一个声音。与流行的黑格尔的艺术是理想的表现,丹纳的艺术是社会的表现,佛洛伊德的以性为基础的心理分析,马克思的唯物论的反映论艺术观相比较,生命诗学观也是一种富于生命力的诗学观念。艺术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的艺术行为,是艺术家个体对生命活力的独有感知并首创展示的行为,艺术真正本体的源泉是生命。生命是一种存在的动态性过程。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家竭力展示个体对生命存在的独有体悟和审美直觉过程本身,并延展和延长个体的体悟和审美直觉过程,以便于观者对其真正的认知与观照把握。所以,艺术家要勤勉于对事物生命过程的洞察、体悟,用艺术家独具慧眼的艺术捕捉力,去发掘展示、传达生命过程意义中的点点滴滴的闪光点,以艺术首创的表达方式满足人们对艺术精神文化的渴求愿望。封孝伦教授说:“‘生命’确实对审美研究有着巨大的潜力,抓住了生命,也就抓住了美的真正内涵。”(注:封孝伦《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中国当代美学本质核心内容的嬗变》,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11期。)“人类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最深刻的内在动力受生命活力的有机驱遣。人类的艺术行为,就是艺术家个体对生命的独有感知并首创展示的行为。所以,艺术真正的本体源泉是生命。”(注:杨义《楚辞诗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一文,就以生命的超功利性和创造性驳斥了13种流行的“文艺观”,结尾宣告的就是这种诗学观的响亮声音,一种迥异于当下所有诗歌观念的声音。
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普遍的事实是,“新月”诗人对生命诗学观的坚守,在某重程度上是包含着对现实的拒绝态度的,至少包含对当时流行的描述这个世界的方式的“阶级论”(现实主义)话语的拒绝。今天我们回顾《“新月”的态度》一文发表的语境,当能更清楚地知道“新月”生命诗学观在当时的特殊意义。
生命诗学观是我们确认以“人本”为出发点的艺术题材、主题的作品的价值与意义的重要艺术依据。克罗齐说,不论在什么时候,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从他的内心里面,反射出整个的世界,能了解生命,就知道了诗歌,了解了宇宙。这里判定问题的依据正是这种生命观念。有学者指出,胡适何以能开拓“新红学”领域?无非是他“从清人的诗话、杂传、方志钩沉探微,以证明这部伟大的小说中包含有曹雪芹的生命体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其中包含曹雪芹对宇宙、人生的无限感悟,包含他对生命透彻体悟和那种“人生如梦”的感喟,而不仅仅是它揭示了一个王朝崩溃的规律。后者主要应该是社会学的问题。个体(人类)的生命体验,同永恒普遍的人性一样,它如同柏格森的“绵延”,是生命的本质。曹雪芹借《红楼梦》故事对命运无常感的慨叹,正是生命本质的追问啊!又如,为什么我们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美?杜甫《秋兴八首》沉郁深邃?就因为它们包含了深刻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和生命的悲剧力量。“新月”诗人的生命诗学观告诉我们,“文学是实现生命的”,实际上说诗是生命的象征。这为我们创作与鉴赏诗歌提供的启示是,创作应该永远关注生命这个艺术之源,欣赏应该把玩这个象征的生命意蕴。
从鉴赏角度讲,鉴赏者所以阅读这类作品能获得美感,是因为他作为主体的生命意识的充盈。一个老年人行走在黄昏的路上,想到自身的生命时,会倍感“夕阳无限好”的美妙。一个中年人悠闲独居时,想到生命,会不禁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切而陶醉。像《雪花的快乐》,就是一个生命的象征,包含丰富的生命意蕴。诗歌充满了少年般的天真,神话般的秀美,一种温柔、纯洁、执着、快乐的情调,叫读者想起了青春的好梦。从这个生命的故事里面,你将发现自由的可贵,追求的价值。从艺术品作为对象讲,是因为它以人的情感、人的体验、生存智慧和感觉经验为内容,这和有生命意识的鉴赏者在审美意义上感觉经验的复合,灵犀相通,经验印证,从而就产生了灵魂的欣悦和理智的满足。艺术史和审美的理论证明,“新月”诗派的生命诗学观念体现的正是这种思想,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一种实现生命的诗学及其诗学实践,当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来体认与把握。如果拘于一种道统“工具”论、庸俗社会历史诗学观,或者将一切都置于内容形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去衡定,除此之外便不知道有何种标准可以权衡一首诗的崇高价值和审美魅力,那他永远也看不清一首诗的生命所在。这也从逆向说明了,“新月”诗人的生命诗学观的意义当如此观。实际上,我们可能也正是在这种诗学观的基点上,才能接近“新月”诗歌和“新月”诗人,以及那些我们能感受其动人的艺术魅力却说它没有“深意”的无数精美的文学艺术作品。
生命、人性与美,从某方面说,是永恒的,也是神秘的。也许在不无偏狭的“新月”生命诗学观中,我们将能看到他们诗美的真谛。
标签:徐志摩论文; 闻一多论文; 诗歌论文; 生命哲学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艺术与人生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文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读书论文; 人性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