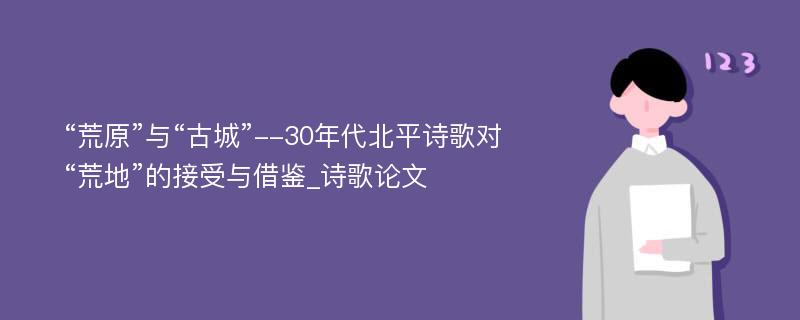
“荒原”与“古城”——30年代北平诗坛对《荒原》的接受和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原论文,北平论文,诗坛论文,古城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划时代杰作。30年代,中国诗坛遭遇“《荒原》冲击波”(注:参阅孙玉石:《现代诗歌中的现代主义》,《西方文艺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297—2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初绽现代主义艺术花蕾。其中,北平现代主义诗人群成绩斐然,他们不仅在《荒原》的译介上有突出贡献,而且还在《荒原》精神的启发下,集中创造出一系列独具民族色彩和历史意识的“古城”意象。
一
中国诗坛是在20年代初开始注意艾略特的,不过,那时还未将他与《荒原》以及整个现代主义诗潮联系在一起(注:参阅孙玉石:《现代诗歌中的现代主义》,《西方文艺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297—2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928年,徐志摩为他的诗作《西窗》加上一个副标题——“仿T.S.艾略特”,但在卞之琳这样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看来,他模仿得“却一点也不像”(注: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人与诗:忆旧说新》第39页。)。真正模仿得神形兼备的是孙大雨发表于1931年的《自己的写照》,只可惜又模仿得太像,几乎没了个性。1933年,《新月》杂志第4卷第6期在介绍美国利威斯的《英诗的平衡》一书时,援引了原著者对艾略特和《荒原》的介绍,特别明确地阐述了《荒原》已成为英诗“一个新的开始,树立了新的平衡”(注:荪波:《利威斯的三本书》,《新月》第4卷第6期(1933年3月1日)。)。比这篇文章稍早,在《新月》第4卷第3期上,叶公超在撰写介绍文章《施望尼评论四十周年》时也提到艾略特,说他是“现代知名的英美作家”之一,是“诗人与批评家”。叶公超当时身在北平,是清华的教师,通过他对艾略特有所了解这一情况可以推知,北平现代派诗坛已有人开始接近艾略特及其作品了。当然,上海的诗人对艾略特和《荒原》的译介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正是在上海诗人领袖戴望舒的约请下,北平女诗人赵萝蕤才最终译出了这首伟大作品。但由于本文讨论的是北平诗人对《荒原》的接受,所以重点在于专门理清北平诗坛这方面的工作。
就目前所见的报刊而言,北平地区最早对《荒原》的介绍是从大学校园内开始的。1933年10月,《清华周刊》第40卷第1 期上发表了一篇由文心翻译的文章《隐晦与传达》(Obscurity and Communication ),作者是John.Sparrow。文中这样谈到《荒原》:“的确, 就全体说,《荒地》(The Wasted Land)是比较更难的诗, 正如它之更可理解一样。我们听说,那里面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可解的,有小心的象征在里面穿过,并且富有知识上的用典(intellectual refrence), 像一切饱学有创作力喜用省文的诗人的作品一样,解释这些东西是困难的。”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只着意于《荒原》的隐晦问题,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相比之下,一年以后发表在《清华周刊》第42卷第6 期上的默棠翻译的R.D.Charques的《论现代诗》一文就要具体全面得多了。这篇文章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最全面的评介《荒原》的译文。他不仅介绍了一些具体情况,提供了一定的解读路径,而且论及了《荒原》的主旨和对其他诗人的影响。作者说:
与诗的想象底传统背景相对, 爱略特( Eliot )君底《荒地》(The Wasted Land)在11年前出版时颇震惊一时。 在现在这时候我们对这首名诗还来说什么呢?现在要拿来当做一个题目讨论的还不是爱略特君底诗底内在价值,而是他对于别的诗人及现代一般诗的影响。关于《荒地》,我们见着各个注释者对于这诗有着各不相同的解释,对于这诗说的什么或爱略特君写这诗的艺术的动机是什么也没有一致的意见,而爱略特君本人似乎提示这诗底主要的文学的影响应求之于拉福格(Jules Laforgue)底诗与后起衣里沙白时代作家的散文与韵文中。这诗充满了文学的典故与文学的假借,而且在它四百行诗后边还有七页注释来把读者勉强从爱略特君底渊博底迷惑中引导出来。诗中整段的引用外国语至六种之多,中有一种为梵文。在某一意义《荒地》既不是晦涩的也不是难懂的诗——至少在现时看来已不如最初那样晦涩与难懂——不过它底含义却不定。诗底整个显然比各部分加在一块更大,而疑难处也正在爱略特底诗的体系。此外,本诗包含有许多行的华美的意象,不过其中哪些是诗人自己的,哪些是从别的作家借用来的,除过量的博览之士外,这对于大家倒是一个问题。
爱略特君对他同时代人的巨大的影响是不成问题的。这里并不想来对这影响试作一个公正的评判,更不想来探究他心灵底深邃与复杂。……现在试放开《荒地》来看他另一首比较简单的诗,也许可以因而抓住他对于诗的概念的一个主要点。……这里明白地表现出来的是爱略特君底对于庸俗Vulgarity的畏惧。……庸俗就是《荒地》诗中的流氓, 恶魔,而常与过去的虚构的荣华相对比。……
也许是看到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对中国读者的切实帮助,一位名叫马骥的译者又不约而同地将之重译了一遍,发表在1935年1 月《诗与批评》第46期上(注:从文字上看不是同一篇译文。),改题目为《英国现代诗歌》,使更多的读者从中获益。
作为译介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的重要阵地的《诗与批评》, 在1934年7月的第28、29 期上曾连载宏告翻译的瑞恰慈的《哀略特底诗》一文:
如果要用几个字来标明哀略特君底技巧底特点,我们可以称他的诗为“观念底音乐”(Music of ideas)。观念有各种各样:抽象的与具体的,一般的与特殊的;像音乐家的phases,它们底排列不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而是要使加于我们的效果能合成一个情感与态度协调的整体,或者能产生意志底特殊解放。这些观念期待你的反应,并不期待你的思索或寻译。这自然是许多诗歌中一再应用的一个方法,而且只是诗歌底一般方式中的一种之重用与专用而已,哀略特君后起更难懂的作品便是有意和几乎专一地引用这一方法。……《荒土》……纯粹是“观念底音乐”,已经全然不装作有一条联想的线索了。
一味指斥和荒凉只是他底诗底表面而已。有些人以为他仅只把读者引到“荒土”就不管了,在他最后的一篇诗中他自认不能致此济世的水。我们的答复是:有些读者在他的诗中不仅是比任何处所更明白更完全的自己的苦况(一代人全部的苦况)底实现,而且由于那个实现所发放的这种力量,得到一个济世热情的返临。
瑞恰慈对艾略特的了解和评价比其他人或可更加深入贴切,他不仅指出了“观念的音乐”这一重要方法,而且还说明了《荒原》反映“一代人全部的苦况”的现实主题,进一步启发读者去发现和体味艾略特在诗中隐藏的“济世热情”。瑞恰慈是艾略特在理论上的同盟者和颇能会意其作品的分析者,他1929年至1930年曾在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一年,卞之琳等诗人都曾听过他的课,很显然,瑞恰慈的北平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平诗坛对《荒原》的引进工作。
另外,在《清华周刊》第43卷第9期上的《T.S. 厄了忒的诗论》和第43卷第11期上的《战后英国文学》,以及在《诗与批评》第36期和第53期上分别刊登的曹葆华翻译的《论隐晦》和《现代诗歌底趋势》等文章中也都提到了《荒原》和艾略特的深远影响,并都做出了准确到位的分析和评价。从这些材料已可以看出,北平诗坛对《荒原》的译介已经涉及到其艺术特征、思想内容,及其对其他诗人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对北平诗人来说,《荒原》无论从方法上还是精神上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同时,全世界都承认的《荒原》的“晦涩”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困扰着北平的读者。他们希望找到理解这首长诗的钥匙,希望追寻作者的思路,这种渴求的表现,就是他们对外国评论文章的有选择的翻译。
在逐步的接近和了解中,很多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艾略特的诗“尤其是以《荒原》为代表作品,与他对于诗的主张确是一致的”,“所以要想了解他的诗,我们首先要明白他对于诗的主张。”(注:叶公超:《爱略特的诗》,《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1934年4月)。 )因此,译介艾略特的文学理论的工作与译介《荒原》同步开展起来。
《诗与批评》上刊登的艾略特的译文共有5篇:《诗与宣传》、 《批评中的实验》、《批评底功能》、《完美的批评家》、《论诗》。其中《论诗》一篇分别在第39期由曹葆华和第74期上署名灵风的译者翻译了两遍。事实上,这篇《论诗》就是艾略特最著名的理论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早在1934年5月已由卞之琳译出, 以《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为题发表在了由叶公超主编的《学文》创刊号上。在短短的时间内3次刊登同一篇文章, 这不仅说明了北平诗坛对这篇文章的重视,更说明了他们对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有着相当准确的认识。
完成于1934年但直到1937年方才出版的曹葆华译文集《现代诗论》中,也收入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底功能》和《批评中的实验》3篇。 曹葆华在自序中这样说:“爱略特和梵乐希的诗论与他们的创作是分不开的,仿佛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就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诗。”“爱略特那篇文章特别使我们心感,就因为代替译者说了许多应该向国内的读者说的话。对于近代批评的本源、现况,和今后的趋向,他都深刻地剖析过了。这是可议论一篇当作本书引论读的文章。”(注:曹葆华:《现代诗论序》,《诗与批评》第33期(1934年8月23 日)。)
在对作品和理论的双重研读中,北平诗坛上出现了自己解读《荒原》的声音。1934年,叶公超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爱略特的诗》一文,是目前发现的这类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涉及对《荒原》主题的理解和对艾略特诗歌技巧的分析。
关于《荒原》的主题,叶公超说:“‘等候着雨’可以说是他《荒原》前最serious的思想,也就是《荒原》本身的题目。 ”“《荒原》是他成熟的伟作,这时他已彻底地看穿了自己,同时也领悟到人类的苦痛,简单地说,他已得着相当的题目了,这题目就是‘死’与‘复活’”。叶公超注意到,“《荒原》是大战后欧洲全部荒芜的景象”,而艾略特不仅仅是揭示这种荒芜,更重要的是,他表达出自己的“悔悟自责”和追求的幻灭。在此基础上,叶公超准确地发掘了艾略特的“现代”性:“这些诗的后面却都闪着一副庄严沉默的面孔,它给我们的印象不像个冷讥热嘲的俏皮青年,更不像个倨傲轻世的古典者,乃是一个受着现代社会的酷刑的、清醒的、虔诚的自白者。”“他是一位现代的形而上学派的诗人”。
在诗歌技巧方面,叶公超的见解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高度。他看到了艾略特在语言方面的“刺激性”和“膨胀的知觉”,注意到了他对隐喻(metaphor)和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应用, 认识到《荒原》是艾略特“诗中最伟大的试验”,“他的诗其实已打破了文学习惯上所谓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区别”,是现代主义的发端。因此,叶公超准确地说:“爱略特的诗学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他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注:曹葆华:《现代诗论序》,《诗与批评》第34期(1934年9月3日)。)。叶公超是中国最早引进并完整阐释《荒原》的人,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卞之琳就曾说过: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的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注: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水星》(合订本)第3页。)。
对艾略特的文学理论和诗歌的译介工作积累了三四年后,全文翻译《荒原》的条件渐渐成熟。中国诗坛和翻译界终于等到这样一个契机,出现了一个连艾略特本人都曾亲自对她表示了真挚谢意的功臣——赵萝蕤。
赵萝蕤“初对于艾略特的诗发生了好奇的兴趣”约在1934年,她“在仔细研读之余,无意中便试译了《荒原》的第一节。这次的试译约在1935年5月间。”但随后, “因为那种未研读之先所有的好奇心已渐渐淡灭,而对于艾略特的诗的看法又有了一点改变”,翻译的工作又停了下来。1936年底,上海新诗社听说了她曾译过一节《荒原》,就主动与她联系,希望她完成译文,交给他们出版。于是,赵萝蕤“便在年底这月内将其余的各节也译了出来”,并将“平时留记的各种可参考可注释的材料整理一下,随同艾式的注释编译在一起”寄出付印(注: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我的读书生涯》第7页。)。1937 年夏天,《荒原》的译本出版,一共印行简装300本,豪华50本。 《荒原》中译本的出现无疑是中国诗坛上的一件大事。虽然此前很多诗人已接触过原文,但全文翻译才是引进《荒原》的工作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因此,赵萝蕤的译本一出现,立刻有评论称:“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荒原’中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注: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我的读书生涯》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面对如此“冗长艰难而晦涩的怪诗”(注: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我的读书生涯》第7页。), 赵萝蕤仅凭好奇是不能完成翻译工作的,打动她的是艾略特的全新诗歌观念和深刻的精神内容,而这一点,也正是《荒原》打动所有中国诗人的地方。赵萝蕤发现,“艾略特的诗和他以前写诗的人不同,而和他接近得最近的前人和若干同时的人尤其不同。他所用的语言的节律、风格的技巧、所表现的内容都和别人不同。”她看到了艾略特的“恳切、透彻、热烈与诚实”,也深刻理解到艾略特所表达的现代人特有的“荒原求水的焦渴”,看到“欧战以后,人类遭受如此大劫之后”,只有艾略特“将其中隐痛深创作如此恳切热烈而透彻的一次倾吐”。另外,赵萝蕤自己作为一个诗人,也敏锐地感受到艾略特在技巧上带来的冲击,她看到他的用典的客观性和综合性造成的诗歌佳境,也看到其“由紧张的对衬而达到的非常尖锐的讽刺的意义”,因此赵萝蕤说:“往往我们感觉到内容的晦涩,其实只是未能了解诗人他自己的独特的有个性的记述。一件特殊的经验必有一特殊的表现方法,一个性灵聪慧、天资超绝的诗人往往有他特殊的表现。”“所以艾略特的晦涩并不足以使我们畏惧他,贬降他的价值,同样亦不必因他的晦涩,因好诡秘造作而崇拜他”,赵萝蕤要求中国的读者“经过虚心的研读与分析”,真正的了解,公正的评价。此外,赵萝蕤翻译《荒原》还有其现实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她发现“艾略特的处境和我们近数十年来新诗的处境颇有略同之处”,因此她希望《荒原》的全新观念也能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她“大大地感触到我们中国新诗的过去和将来的境遇和盼望。正如一个垂危的病夫在懊丧、懈怠、皮骨黄瘦、色情秽念趋于灭亡之时,看见了一个健壮英明而坚实的青年一样。”(注: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我的读书生涯》第18页。)因此她说:“我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作与不变不屈的信心。”(注: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我的读书生涯》第17页。)由此可以说,赵萝蕤们正是通过引进《荒原》表达出他们对新诗“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因为叶公超对赵萝蕤翻译《荒原》提供的重要帮助,也因为叶公超是北平诗坛上最权威的艾略特的研究者之一,所以,赵萝蕤请叶公超为她的译本作序,由此产生了一篇“真正不朽的”序言。在这篇序中,叶公超侧重讨论了艾略特的艺术技巧,并独树一帜地将艾略特的用典与中国宋诗中的“夺胎换骨”法相比,进一步扩大了对《荒原》理解的思路。最重要的是,叶公超在序中称艾略特的诗歌观念为“新传统的基础”,认为“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注:叶公超:《〈荒原〉序》,《荒原》上海新诗社1937年。)。他真正将《荒原》定位于新诗潮的经典地位,为寻找西方资源的中国诗人提供了一幅标志鲜明的“地图”。
二
1933年1月, 早在艾略特和《荒原》尚未大规模地在报刊上得到译介之前,北平的校园内诞生了一个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刊物,它的名字叫《牧野》。《牧野》由北大的李广田、邓广铭主编,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北平校园现代派诗人的代表“汉园三杰”——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
《牧野》创刊号的《题辞》中这样说:“我们常四顾茫然。如置身无边的荒野中,只听得狗在嗥,狼在叫,鬼在号啕,有时也可以听到几声人的呼喊,却每是在被狗群狼群和魔鬼的群所围困所吞噬着的时候,多么样的荒凉,多么样的凄惨啊!于是感到了孤立无援的惊悚。”他们“自己感觉到,能力是太有限了。作不出‘战士热烈的叫喊’,因而也作不出‘浊世的决堤的狂涛’。但这怵目惊心的惨剧又实在看不惯,有时便也忘了自身理论的微弱,感到兴奋,想要振作。”于是,他们创办了这个刊物,目的就在于“将各人在这人生的途程中所体验到感受到的一切,真正地表曝出来,无论是社会的一角的解剖,是自身的衷情的诉说,是被噬时的绝叫或反噬时的怒吼,都按期汇集起来,呈供大家。”这篇《题辞》清楚地表现出以“汉园三杰”为代表的北平现代主义诗人群体当时的普遍心态。他们与艾略特有着思想深层的默契。他们身处现代社会,却感到如同置身荒野,空虚而且孤独,清醒的批判和反思是他们最常有的思绪。他们有现实的抱负,渴望改变现状,但他们又深知自己作为思想者的无能为力,因此产生苦闷和矛盾,并将这些情绪以现代人的方式体现在诗歌作品中,从时间上说,我无法断定《牧野》的创办已经受到《荒原》的启发,而且在一共只有6期的刊物中, 他们也没有提及艾略特或《荒原》。因此,我不想妄下结论,说这“牧野”就是那“荒原”。但是通过比较确实可以看出的是:北平诗人在30年代初已经萌发了与“荒原”意识相通相近的思想和情感。正是这种共通为北平诗人接受艾略特和《荒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北平诗人遇到《荒原》后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赵萝蕤曾说:《荒原》的艺术方法和精神“几乎震撼了全世界”,“我们要了解现代诗,一定要了解艾略特的精神所指的路径,虽然有若干的批评家觉得他的创造生命已经过去(《荒原》序言亦说过),但他的影响已深入了许多新诗人的灵感中了。”(注: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我的读书生涯》第7页。)的确, 在北平现代派诗坛上,不少人都受到了艾略特和《荒原》的影响。卞之琳曾说过:“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注: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雕虫纪历》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方敬也在回忆曹葆华时说:“葆华逐渐爱上了法国象征派和英美现代派的诗,受到波德莱尔、韩波、庞德、T.S.艾略特等诗人的影响。”(注:方敬:《寄诗灵》, 《方敬选集》第760页。)最明确地说出这种影响的是何其芳,他说:“当我从一次出游回到这北方大城,天空在我眼里变了颜色,它再不能引起我想象一些辽远的温柔的东西。我垂下了翅膀。我发出一些‘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我读着T.S.爱里略忒。这古城也便是一片‘荒地’。”(注:何其芳:《论梦中道路》,《大公报·文艺》第182期(1936年7月19日)。)北平诗人有选择地吸收了《荒原》复杂错综的思想内容,在艾略特的启发下以一种新的、现代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传达出了他们对麻木人群的精神世界的批判,对民族生命力的渴望,对重建家园的憧憬,以及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他们有个性地接受着《荒原》的影响,淡化或摒弃了不符合民族心理的宗教虔诚和对情欲泛滥的谴责。本文无意将北平诗人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与《荒原》的影响一一对号,只希望发掘《荒原》影响下的北平诗人的新创造。而在众多方面的创造中,最具有高度和民族个性的,就是“古城”意象的塑造。这个意象是北平诗人将自身文化背景与现实体验融入对“荒原”意识的思考之后,再造的一个独具东方民族色彩,甚至说独具北平城市特色的整体意象。它以其民族色彩、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隐喻性质卓然突出于中国新诗意象群落,在意义和价值上不亚于波德莱尔的巴黎和艾略特的伦敦。它没有发达的工业文明的景观,但它突出了东方的历史文化色彩,丰富了世界城市现代主义诗歌的意象群落。这个“古城”的意象将与巴黎和伦敦一样,成为世界现代主义诗歌意象群中一个不可替代的经典。
“古城”与“古都”、“荒城”等意象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象群落。这类意象既与“荒原”精神相通,又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性格。“荒原”是抽象的,而“古城”具体真切;“荒原”是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而“古城”纯然脱胎于东方历史文化氛围。这就是说,“古城”意象并不是对“荒原”精神的机械模仿,而是一种带有民族性的创新。
北平诗人创造的“古城”意象既有现实的提炼,又有艺术的升华。一方面,北平的确是一个衰落的古都,这里没有上海那样“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奏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注: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第4卷第1号(1933年11月1日)。), 也没有闷热的“沙利文”(注:施蛰存:《夏日小景》。)和摩天楼上如“都会的满月”一样巨大的时钟(注:徐迟:《都会的满月》。)。现实的北平本来就是“风沙万里的荒原”(注:林庚:《长城》。),还有那些与气候一样寒冷干燥的人面人心,写古城的荒凉本来也算忠于现实。但另一方面,北平的诗人又超越了这个现实,为“古城”意象注入了深广的历史意识和现代人独特的情感内容,使“古城”不仅是北平本身,更因为浓缩了千年的民族历史而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深藏着对诗人对民族命运的反思和预言。
“古城”与“荒原”最表层的共同点就是自然环境的荒凉。这种外在的相似最先引起了诗人的共鸣。因此,诗人在描绘自然环境的作品中突出了最具北方特色的“风沙”,以此营造出干燥寒冷的荒凉境界。遮天蔽日的风沙使古城愈显沧桑破败,古城仿佛终将被现实和历史的黄土埋葬。“忽然狂风像狂浪卷来/满天的晴朗变成满天的黄沙/……/卷起我的窗帘子来:/看到底是黄昏了/还是一半天黄沙埋了这座巴比伦?”(注:何其芳《风沙日》。)“……这座城/是一只古老的大香炉/一炉千年的陈灰/飞,飞,飞,飞…”(注:卞之琳《风沙夜》。)“巴比伦”和“大香炉”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们象征着古城的古老死寂、了无生机。前者的终成废墟和后者的灰飞烟灭更象征着古老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命运。在这风沙里,诗人看到的只有被埋葬的历史和被渴死的生命,却看不到丝毫对未来的希望。风沙中“惨白的”、“晦涩而无光”的“日影”就像“20世纪的眼睛”(注:林庚:《风沙之日》。),它没有光芒、没有热情,预示着整个人类的悲剧命运。
并不是因为寒冷的风沙磨砺了诗人的感情,诗人就满腹牢骚,也不仅是风沙和寒冷才让诗人感到置身荒原,他们的苦闷更来自心灵的寂寞和焦渴。在风沙中,他们说:“我的墙壁更厚了/一层层风,一层层沙。”(注:何其芳:《病中》。)风沙的墙壁象征着诗人的心灵与社会的隔绝。所以,诗人表面上诅咒的是风沙,实际上诅咒的是社会气候的干冷压抑。他们从描绘自然环境的“荒”深入到揭露社会现实的“荒”。
苦闷的心情令北平现代派诗人更贴近和认同了艾略特笔下的现代“荒原”,也更唤起了他们清醒的现实批判精神。卞之琳的名句“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注:卞之琳:《春城》。)与《荒原》的首句“四月……荒地上/长着丁香”就有深刻的相似性:风筝和丁香是美丽的事物,但却发生于肮脏荒凉的垃圾堆和荒地上,对此诗人的心理是复杂的,他们有批判、有惋惜,甚至还对美超越丑寄予些许希望。实际上,这种心理也是艾略特和北平诗人批判精神的基调。他们不是单纯的绝望和诅咒,而是怀有虔诚的济世热情。
卞之琳曾经说过:“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指得出波特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启发。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注: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雕虫纪历》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这就是说,他吸取了两位诗人的共同点——对大城市的批判精神,并将之融入了自己对北平景物的描写和思考中。卞之琳的说法可以代表一大批北平现代派诗人,他们大多具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们用一系列作品共同勾画出荒凉冷漠、衰弱麻木的“古城”巨象,尤其描绘出了“古城”中丧失生命力的沉默民众的群像。他们的思想一方面受到艾略特关于人心“苦旱求雨”的启发,更多的则是承自“五四”的思想传统,是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最深切的体会和批判。身处“五四”的发祥地,北平诗人们依然沿袭着那光荣的思想传统,就像《牧野·题辞》中说的,他们深知自己无力掀起社会变革的巨浪,于是就用诗的方式揭开社会的一角,以现实的情怀和艺术的手法勾勒出一个古国的现代性荒芜。
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北平的现代派诗人与其他启蒙知识分子一样,首先指向沉默麻木的“国民性”:
白日土岗后蜿蜒出火车
许多人在铁道不远站着
当有一只鸟从头上飞过
许多人仰头望天
许多欺负人的事,使得
……
大人拍起桌子骂得更生气
四邻呆若木鸡
孩子撅着小嘴
站着
像一个哑叭的葫芦
摇也摇不响
——林庚《沉寞》
鲁迅笔下麻木不仁的“看客”形象出现在现代主义的诗歌作品里,显得那样朴素凝练。人们麻木沉默,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尊严,就连孩子也“像一个哑叭的葫芦”,从小就丧失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意识和能力。
麻木的人们无法领会自己的悲剧命运。更无法明白民族的苦难和危亡。也正因这种麻木性格的加重,理想的民族精神更快地接近了消亡:
有客从塞外归来,
说长城像一大队奔马
正当举颈怒号时变成石头了。
……
说是平地里一声雷响,
泰山:缠上云雾间的十八盘
也像是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
……
悲世界如此狭小又逃回
这古城。风又吹湖冰成水。
长夏里古柏树下
又有人围着桌子喝茶。
——何其芳《古城》
民族精神中昔日的刚烈英勇已经如受了魔法和诅咒的石头一样不再复活,而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泰山”也终于发出了“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塞外的胡沙和大漠风虽然能够越过长城这自然的屏障,但却永无办法唤醒古城的死寂,撕开人心麻木的外壳。诗人悲愤地看着麻木的人群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他们沉默空虚、昏昏噩噩的生活,哀叹“地壳早已僵死了”。在他强烈的批判背后,更流露出长久深沉的内心痛苦。
北平的现代派诗人并没有模仿西方诗人那样描写大城市中拥挤的人群,他们只是拣取北平街头常见的风景,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古城”中的自然和人物,但他们与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一样触及到了人类灵魂丧失的深刻主题。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很好地结合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想与古城北平的现实。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暴露和批判的层次上,还不足以体现出北平诗人的现代性品格。北平现代派诗人的先锋姿态就表现在他们对象征性、隐喻性内涵的大力深入和开拓上。他们将现实的批判意识与古城特有的历史纵深感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他们的批判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现实层面,具有了更加深广的象征意义和隐喻性质。“古城”的历史实际就是“古国”历史的缩影。诗人将“古城”意象加以扩展,纵向涵盖了千年的历史,横向象征着整个国家和民族。
在古城北平,有数不清的历史遗迹,故宫、煤山、长城、圆明园等都进入过诗人的作品。他们或象征英烈的忠魂,或象征怨女的幽情,或代表曾经辉煌的古代文明,或代表不堪回首的屈辱和沧桑。这些遗迹是古城中固有的,但又因诗人的艺术升华而象征了整个中华古国。在诸多意象中,石狮子是艺术效果最强最独特的一个,它就是整个民族历史的隐喻体。中国人向来以狮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古城”中的石狮子因其威武的过去与破败的现状间的巨大反差更深刻地象征了古国的现代遭遇和命运。在北平诗人的作品中,有的“石狮子流出眼泪”(注:何其芳:《夜景》。),有的则满腔“古国的忧愤”,“张着口没有泪”(注:曹葆华:《无题》。),更有曹葆华讲述了一个“石狮子眼里/流血的故事”(注:曹葆华:《无题》。)。石狮子流泪,流血的意象可谓惊心动魄,其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效果将全民族的悲剧命运与民族精神在苦难中的挣扎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血泪是全民族的千年血泪,古国的历史也就是一部血泪的历史。诗人以忧愤的石狮子象征着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寄托了他们深沉的思考和忧患。这种隐喻的运用实现了艾略特等人将“现代”与“传统”融于一诗的现代主义诗学追求。
自然环境干燥寒冷,历史环境衰败荒凉,而现实中的人又是那样沉默麻木,灵魂亦是一片荒芜,这一切都令诗人感到了巨大的寂寞和忧愤。这忧愤如此宏大,大过了“古城”的上空,大过了“古国”的疆土,一直指向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曹葆华在一首《无题》中这样咏叹:“唉,我也逃不出这古城/纵有两只不倦的翅膀/飞过大海,飞向长天……//还得跟着冷冷的影子/在荒街上同月亮竞走”。“古城”的意象在诗人的笔下得到了极度的拓展,它已不再是一个有形的城市,而成为一个无形的、巨大的隐喻体。它不仅象征着打破了地理概念和时间界限的“古国”,也象征着包括古国在内的整个人类历史,更象征着全人类都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北平诗人以“古城”寄托自己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反思和现代性焦虑,这与“荒原”精神的深层内涵完全一致。这“古城”其实也就是一片具有东方民族色彩和历史意识的现代“荒原”。
何其芳曾经说过:“假若这数载光阴过度在别的地方我不知我会结出何种果实”。是的,是古城北平将他们送到了诗神的身边,是“那无云的蓝天,那鸽笛,那在夕阳里闪耀着凋残的华丽的宫阙”(注:何其芳:《论梦中道路》, 《大公报·文艺》第182期(1936年7月19日)。)赋予了他们诗的灵感。但同时,是否可以这样反过来说:假若没有这些诗人的创作,“古城”北平也许永远只是一个历史地理的名称。没有他们,“古城”就不能被赋予那样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品格,也无法成为一个带有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的独特的诗歌意象。“古城”虽“古”,但其精神实质是极先锋、极现代的。它一方面深受“荒原”精神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中国诗人对“荒原”精神的民族性阐释和引申。可以说,“古城”意象是北平现代派诗人对“荒原”意象和精神的一次创新和超越。
标签:诗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赵萝蕤论文; 牧野论文; 论诗论文; 卞之琳论文; 叶公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