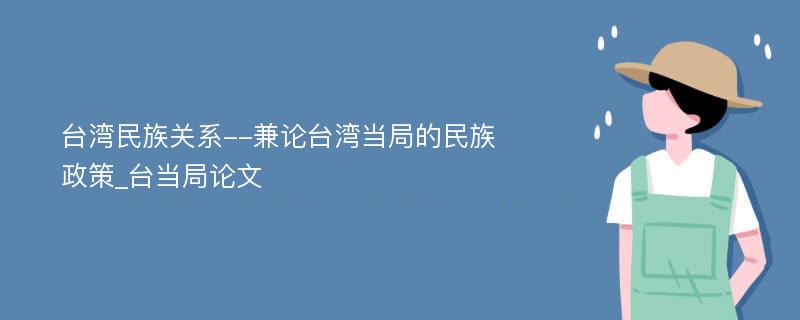
试论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兼评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民族政策论文,台湾当局论文,试论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D633.0(2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0)02—0007—06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无论是从其重要性还是从其复杂性来看,与祖国大陆相比,均有明显的差异。然而,近20年来,台湾岛内的民族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伴随着“原权运动”的发生,批评国民党当局民族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因此,研究岛内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地评价国民党当局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其所谓“山地政策”,对于全面认识台湾地区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现状,是不无裨益的。
一、台湾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的嬗变概况
台湾地区居民的民族构成虽不如祖国大陆那样复杂,但也是多民族的。居民中的绝大部分是在各历史时期从中国大陆迁入岛内的汉族,其次是台湾少数民族(注:台湾少数民族即大陆一般所说的高山族,台湾当局称其为“山地同胞”,而其自称“原住民”,笔者赞同中央民族大学许良国先生的观点,以“台湾少数民族”作为其统称。),再次是从中国大陆迁入的满、蒙、藏、回、维吾尔等族。据台湾“内政部”公布的数字,1990年台湾总人口2100万中汉族占98%以上,约2060万;“山地同胞”为33.8万,占1.65%;其他由大陆迁入的少数民族如蒙、藏、回、满、维吾尔、哈萨克等总数仅千余人[1]。
台湾少数民族被祖国大陆称为“高山族”,而台湾当局称其为“山地同胞”或“山地人民”,简称“山胞”。而历史上,自汉代开始,先后被称为“东夷”、“山夷”、“流球土人”、“东番”、“番”、“蕃”、“生蕃”、“熟蕃”。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称“高砂族”、“蕃族”、“蛮族”。1945年台湾光复后改称“高山族”,1947年国民政府又通令改“高山族”为“山地同胞”或“山地人民”[2]。
事实上,台湾少数民族并非单一民族。因此,用“高山族”或“山地同胞”以及“台湾原住民族”来称呼均不适当。1980年,台湾当局公布了《台湾省山胞身份确认法》,随即开展了“山胞”身份认定。结果,经官方确认的“山胞”分9族,即阿美、泰雅、排湾、布农、曹、 雅美、鲁凯、塞夏、卑南。1990年上述各族人口分别为:阿美族约12.8万,泰雅族为7.7万,排湾族6.1万,布农族3.6万,卑南族9千,曹族和鲁凯族各8千,赛夏族和雅美族各4千[1]。
台湾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岛山区,东部沿海纵谷平原及兰屿岛上,台湾当局将其居住地划为30个山地乡和25个平地乡,行政区划面积15850平方公里,占台湾全岛面积的44%[1]。除雅美族至今仍以渔猎为主外, 其他各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水稻、小米、玉米、番薯、芋头、高粱,家畜饲养和捕鱼是重要的副业。擅长竹藤编织、刺绣、贝雕等工艺。
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无定论。主要有土著说,西来说(中国大陆移民说)和南来说(南洋诸岛移民说)。笔者同意施联朱先生的观点,即台湾少数民族是多源的,最早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古越人的一支,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又有从东北琉球群岛和南方菲律宾,婆罗洲以及密克罗西亚诸群岛的居民,相互融合而成[3] (P170)。正因为如此,才使台湾少数民族在体质特征、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呈现出与大陆少数民族明显不同的特点。
在历史上,祖国大陆很早就同台湾有过联系。这种联系既有武力征伐攻掠,也有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民间交往。而每逢乱世,大陆沿海居民则移台避难。
三国时,吴主孙权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遣将军卫温、 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妢洲,欲俘其民以益众,”后因妢洲“所在绝远,卒不可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4]。妢洲是传说中秦始皇派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求蓬莱神山到达的地方,夷洲即台湾岛。
隋朝时,炀帝于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派虎贲中郎将陈棱发兵万人击台湾(当时称“流求”),“虏男女数千而归”。所掠之民,安置在福州之福卢山(注:均谓隋将陈棱掠流求五千户安置与福卢山,而大陆学者施联朱、张崇根经实地考察认为五千户系50户之误。)[5]。 唐朝贞观年间,马来群岛洪水泛滥,岛民“各驾竹筏避难,漂泊而至台湾”[6](P5)。东南亚诸岛马来人的侵入, 使台湾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隋唐以来,大陆东南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台湾,带去农耕、养殖技术,而两岸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日益密切。例如,隋将陈棱率军抵达台湾时,岛民“初见舡船,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7] 可见当时大陆商人赴台贸易是经常之事。宋元以后,大陆居民常去台湾北港、鸡笼互市。“当宋之时,华人已至北港贸易。”[8](P442 )而宋钱已在台湾流通, 成为两岸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 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为防止台湾土著居民(当时称“毗舍邪人”)滋扰,开始在澎湖建造军营,“遣将分屯”。说明南宋已在台湾地区派驻军队,开始屯田。这是中国大陆中央王朝控制台湾的开始。元朝时又正式设立了澎湖巡检司。
明末,台湾相继受倭寇、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略。1642年荷兰殖民者打败西班牙殖民者,独霸台湾达20年。台湾各族人民不断开展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武装斗争。1661—1662年郑成功率军驱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对台湾少数民族实施民族和睦政策,抚慰“土社”上层,开展军垦,减轻当地人民负担,不准滋扰“土民土社”,发放耕牛和铁农具,帮助发展农业生产,设立学堂,奖励“土民”学习汉文。这些政策深得民心,使台湾各族经济迅速发展。少数民族“亦知勤稼穑,务积蓄,比户殷富。”[9](P14)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攻灭郑氏,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隶福建省厦门道,府下设台湾、凤山、 诸罗3 县。 雍正六年(1728年)增设澎湖厅,次年又改台厦巡道为台湾道。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清朝统治者将台湾少数民族分为“生蕃”和“熟蕃”。对“熟蕃”(平地少数民族)实行开发和同化政策,推广农耕技术,大量种植水稻、甘蔗;而对“生蕃”(山地少数民族)则实行隔离政策,划定其聚居区域,设立界石,严禁“生蕃”下山和汉人上山。清朝统治台湾210多年,其间台湾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稻米、 蔗糖成为闽粤及全国各地不可缺少的珍品。大陆移民台湾的汉族人民也迅速增加,嘉庆、光绪年间,达二三百万人之多。台北、台中等都市也初具规模。
1895年,日本割占台湾,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达半个世纪。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少数民族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政策。一方面实行强迫归顺,收缴武器,武力镇压,并划定汉蕃界线,实行隔离统治;另一方面,也大力推动山区开发,强迫垦荒种田,种植鸦片、烟草,开发樟脑。文化上推行奴化同化政策,灌输“日台人共存共荣”,推行“皇民化运动”和“蕃童国语(日语)教育运动”。为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一起,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仅在1895—1915年间,就爆发了百余次反日暴动,1930年的雾社起义,更是台湾少数民族反抗殖民统治的光辉典范。
1945年台湾光复,1949年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台湾由国民党统治已达半个多世纪。
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具有同祖国大陆不同的典型特点:一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多源性,包括中国大陆古越人、土著居民、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二是与汉族人民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台湾,且光复以来岛内民族关系主要是少数民族同汉族(政权及人民)之间的关系;三是岛内民族关系深受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四是由于台湾相继遭受过西班牙、荷兰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使台湾的民族关系不能不留下殖民地的痕迹,如语言、服饰、宗教文化上的影响。
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评析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民国时期,其民族政策就是极为偏颇的,表现在:其一,讳言民族问题,称民族为“宗族”,只承认“五族共和”中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对国内众多的其他少数民族概不承认;将民族问题一概称做“边疆问题”,将自己的民族政策一概称做“边政”。例如,蒋介石1942年8月27日在西宁演讲时就声称:“我们中华民国, 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10](P1422)蒋介石认为,“解决边疆问题, 一是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即羁縻”。“既无实力可用,便不可不有相当之政策……予以为目前最适当之政策,莫若师苏俄‘联邦自由’之意,依‘五族共和’之精神,标明‘五族联邦’之政策”。何谓“五族联邦”?蒋介石说:“简言之,即采取允许边疆自治之放任政策。”[11](P193—195)其二,在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政策上, 实行重蒙藏两族,轻其他各族的政策。1928年设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央机构之一,专司蒙古、西藏问题。1947年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在国民大会的代表、立法院委员、监察院委员组成等方面,均有明文规定蒙古、西藏的名额,而未规定其他民族的名额;其第十一章“地方制度”也只明文规定蒙古和西藏的“地方自制制度应予以保障”。[12]甚至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优待政策,也只施于蒙藏两族。
1949年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在相当长时期内秉承了其在大陆时期的民族政策。蒙藏委员会随迁至台湾,至今仍是其“中央机构”之一,更为荒唐的是,孤立海上的台湾当局在相当长时期在台北设立“新疆省政府”,设立“西藏噶伦办事处”。由于海峡两岸在思想、政治、军事上的长期严重对立,国民党长期以反共为各项政策的出发点,以“光复大陆”为梦中的理想,故其民族政策亦属反共政策之一,亦服务于国民党当局反共的最高需要。
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大陆的蒙藏政策,一是对岛内少数民族的所谓“山地政策”。
蒙藏政策或称“边政”,始终是国民党台湾当局民族政策的重点,也是其长期反共宣传的一大方面。其要点有:(1 )不承认外蒙古(即今蒙古共和国)独立。1953年2月,国民党宣布废除1945年8月14日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宣布,1946年外蒙古公民投票导致的独立无效。台湾出版的中国地图至今包括外蒙古在内,并仍称其首都乌兰巴托为“库伦”。(2)挑拨大陆的民族关系, 诬蔑中共的民族政策。1950年3月和1952年7月开办对大陆的蒙古语和藏语广播。此举被台湾当局称为“对大陆边疆人民的心战之始”[13](P590—595)。 此后又创刊《中国边疆》杂志(后改为《中国边政》);还在政治大学内设边政学系(1955年)。成立边政研究所(1970年)。目的均为“培训边政人才,储备复国建边干部”[13](P590—595)。(3)与藏独势力相勾结。1959年西藏农奴主叛乱发生时,蒋介石在台湾发表《告西藏同胞书》,给达赖集团开出空头支票:“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地位……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13](P590—595)。 90年代以来,李登辉集团与达赖集团更加频繁接触,1995年达赖访问台湾,受到国民党当局规格最高的礼遇。
应该说,国民党台湾当局的蒙藏政策是极其荒唐的,又是纸上谈兵的“务虚政策”。蒙藏委员会迁台50年除了每年农历3月21 日祭祀成吉思汗,就是在孤悬的海岛上侈谈“动员组织边疆人民举行抗暴起义”,以及“光复大陆后的边疆建设”之类的呓语。说它是痴人说梦的政策亦不过分。其政策效果一如其对退伍老兵(又称“荣民”)发放分给大陆田地证书一样,连愚民的目的也难以达到,只能成为笑柄。
面对数十万台湾少数民族,国民党当局不愿正视,但又无法回避。为巩固其统治,乃制定了所谓“山地政策”,但仅作为其一项“地方政策”。1950年1月以“台湾省政府”名义颁布《山地施政要点》, 后相继颁布《促进山地行政建设计划大纲》(1953年12月颁布),《山地行政改进方案》(1963年9月颁布), 《现阶段扶植台湾省山地同胞政策纲要》(1966年月颁布)[14](P97—100)。
台湾当局的“山地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
(1)取消族名,建立统治体制。1947 年国民政府通令改“高山族”为“山地同胞”和“山地人民”,事实上取消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这是和其在大陆的民族政策一脉相承的。从50年代初开始,台湾当局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地”建立了乡、村两级基层政权。全省12个县设30个山地乡(乡公所)、162个村(村办公处);到1973年增至215个村(山地村196个、平地村19个),委任“山胞”担任乡长、村长。 县级政府主管“山地事务”的是民政局山地科,后又在其“省政府”内设山地科[14](P97—100)。
(2)推行山地“三大运动”。 “三大运动”为“山地人民生活改进运动”、“定耕农业运动”与“育苗造林运动”,1951年开始。其中,生活改进包括推行国语、改进衣着、饮食、居住、日常生活、改革风俗习惯6大内容;先以户为对象,后扩大到以村为对象[14](P97 —100)。定耕农业方面,规定每户除水田外,不得少于1甲(注:1甲等于0.97公顷)作为耕地,耕地多者由村乡县评定奖励。在山地开垦梯田,由官方补助经费。育苗造林方面,规定每户造林不得少于10公亩;每村不少于10公顷,苗圃不少于100m[2]。造林收益归造林者所有, 育苗造林经费和苗木由官方发放[14](P97—100)。上述“三大运动”至7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台湾当局称这一时期为“山地经济社会建设时期”。
(3)划定“山地保留地”,实行山地管制。 这是沿袭日据时代的做法。1948年颁布《山地保留地管理办法》,规定将山地保留地分为定住地、耕作地和牧畜兼其他产业增进地。1952年先在新竹县五峰乡大隘村试点,次年又在全省30个山地乡进行测量划地,至1969年完成。1966年至1970年实施了土地分配、造林地租用及开发利用山地保留地计划。山地管制主要是限制汉人出入山地,全省共划定了近30万公顷(山地保留地24万公顷、平地保留地5.7万公顷)[14](P97—100)。 将山地分为山地管制区、管理游览区和山地开放区3种,入山管制程度依次递减。
(4)某些优惠照顾性政策。1953 年公布《台湾省山地籍同胞免征租税原则》,规定对“山胞”暂免征收除印花税以外的各项租税。在教育方面,建立了24所“国中”、198所“国小”; “山地籍”学生升学加分优待,并免收书杂费。在职业训练方面,建立职业补习学校,培训木工、竹工、藤工、养蚕、驾驶、理发、建筑等技艺。[15](P250)
(5)“山胞”文化维护政策。1975 年台湾当局拟定了《维护山地固有文化教育实施计划》,但该计划并未实施。1986年,台湾“省政府”又制订了《山地发展与行政措施方案》,此后即开始实施。内容包括:①“加强辅导山胞生活计划”,分文化建设、生活改进、青少年辅导、经济发展等数十项计划。②“台湾山区文化园区建设”。包括设山地文化村;采集山地歌谣及培训山地歌舞人才;辅导举行“丰年祭”;研究山地织布、雕刻;山地文物收集保护及陈列。③“整理与建立山胞家谱”。④实施“新山村计划”[2]。
台湾当局民族政策总的来说是本末倒置的,其“蒙藏政策”既是纸上谈兵、痴人说梦的“务虚”,更是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策。其“山地政策”虽不无可取之处,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却因台湾当局及大财团利益驱动,使“山胞”的土地横被侵占,使一些冠冕堂皇的“政策”或束之高阁,或大打折扣。“山胞”生活“改进”几十年后,仍是台湾最贫困的群体。所以,广大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并不满意所谓“山地政策”。80年代兴起的“原权运动”便是对台湾当局“山地政策”的最好回答。
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的谬误之处在于:
第一,不尊重历史,亦不顾现实,始终将民族政策纳入其反共总政策体系之中。推行荒唐无稽的重大陆、轻岛内,重蒙藏、轻“山地”的错误政策。始终以“边政”代替民族问题,并长期对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妄加攻击,蒙藏委员会原本应在1949年寿终正寝,却“延年益寿”至90年代,早已引起台湾各方人士的批评。在90年代初台湾的“修宪”讨论中,不少人(包括一些“立委”、“国代”)纷纷要求取消,改设“少数民族委员会”[16](P1)。却被台湾当局顽固地加以拒绝。
第二,不承认台湾少数民族,将其称为“山地同胞”,故意抹杀民族间的区别,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在管理体制上,故意将“山地管理体制”定在“地方”级别,其“山地政策”亦仅属“地方政策”,其重要性无法与“中央”的蒙藏政策相提并论。事实上,台湾少数民族对自己的族名十分重视,他们拒不接受“山胞”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统称,“原住民”便是他们用来对抗官定称谓的自称。
第三,拒不实行民族自治。台湾当局虽在50年代初即宣称“自治”,但却是假的。在“山地”虽擢选了一部分“山地籍人士”担任村、乡两级基层负责人,并“考试”选拔了一些“山胞”进入“立法院”、“国民大会”,但并不能证明这是自治。因为,“山地行政体制”仍不过是台湾集权统治体系的一个很不起眼的部份,有关“山地各项事宜,概以行政命令行之”,“山胞”可以任村乡长和“立委”,却不能担任县市省长等职,更罔论进入“中央”!更有甚者,台湾当局还公开表示,所谓“宪法”关于“保障扶植边疆地区各民族自治及教育文化交通经济”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山胞”[1]。也就是说, 在台湾当局眼里,“山胞”并非应予保障扶植的“边疆民族”。这里,可以看出其“山地政策”的虚伪性。
第四,民族同化政策。台湾当局制定的“山地政策”,一开始即以同化为重要目标。在台湾当局公布的各种有关计划、方案里,“促使山地同胞逐步融入大社会”均是首要目标。“三大运动”中的“生活改进”政策,主要即汉化政策:推行国语、衣着整洁(中山装、西装)、吃饭用碗筷桌椅、居住汉化,改善祭祀,纠正婚姻陋习及防止早婚。台湾“教育部”1984年12月8日还明令禁止山地教会使用山地发音书刊。 台湾“户籍法”也规定:“山地”妇女嫁汉人,其“山胞”身份自然消失:而汉族妇女嫁“山胞”,其汉族身份不变[2]。此外, 将原来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名一律改为汉化地名,以及官方酝酿取消“山地特殊政策”,更是民族同化的同义语。
三、关于“原住民权利运动”
“原住民权利运动”简称“原权运动”。是80年代以来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不满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要求维护自己的民族权利而发动的政治运动。
1983年5月, 一批在台北就读的台湾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费创办油印刊物——《高山青》,抨击台湾当局对“山地”的歧视,并开始自称为“台湾原住民”。这是“原权运动”开展的标志。1984年12月,排湾族歌手胡德夫发起成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简称“原权会”,创办《山外山》杂志。一时影响颇大,许多台湾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原权会。1987年又成立了“台湾原住民领袖发展小组”,并创办著名的刊物——《山青论坛》和《原住民之声》。至此,原权运动走向高潮。
在此之前,一些台湾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主要是“立委”“国代”和学者)于70年代末成立“山地建设协会”,创办《山地文化》杂志。80年代中期又成立“山地同胞福利策进会”,主要由“山地籍民意代表”组织。他们与原权会观点完全相反,支持台湾当局的全部“山地政策”,认为“山地政策”对“山地人民”是德政和福音。反对原权运动对台湾当局的猛烈抨击。
但随着原权运动的声势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岛内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80年代末,上述两类台湾少数民族团体的政治主张渐趋合流。台湾少数民族上层接受了原权会的基本主张,而原权会也同意走上层路线。1987年,一批“山地籍议员”向台湾当局接连提出19项提案:阿美族“立委”蔡中涵亦于同年向台湾“行政院长”提出有史以来措词最为强烈的质询,从而一反原来为官方辩护的立场。作为原权运动主要阵地的《山青论坛》立即发表了向蔡“立委”致敬的公开信[17](P422)。
原权运动的目标在于争取“原住民”的权利,其主要内容包括:①在族称问题上,不满台湾当局官定的“山地同胞”,也不满原来的“高山族”名称,认为应统称为“台湾原住民族”或“原住民”,在此前提下再细分各族。为此,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原住民族群认同”运动。②在政治上,要求修改“宪法”,制定“法律”,保障“原住民”的政治权利;要求改革行政机构,改蒙藏委员会为“少数民族委员会”,提升“山地行政”的级别。③在经济上,要求归还被侵占的“山地保留地”,检讨和修改“山地”经济政策,改善“原住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④在思想文化上,要求尊重“原住民”的人格和习俗,号召“原住民”要族群自我认同,信奉同一宗教,推行讲母语,延续本族的传统习俗。
原权运动为何会在80年代的台湾兴起?笔者认为,这是台湾当局长期推行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的必然结果。《山青论坛》的一篇文章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原住民的权益一再被剥夺,‘抢我土地、逼我出海、迫我下海、推我入坑、挖我祖坟’便成为台湾原住民在20世纪的今天最真实的写照与最沉痛的呐喊;在最远的海洋中,最深的地底下,最高的鹰架上,及最无人性的妓院里,散落着一张张最质朴敦厚,最天真无邪的原住民同胞的脸……为了延续种族的生命而委曲求全。甚至,人之所以为人最起码的“尊严”,许多时候,对我们而言是“奢侈品”的代名词。在祖先所遗留的土地上,我们卑微地挣扎,受难了好多年头。每当我们遭受不公平,不正义的对待时,是多么渴望有人能为我们拨开层层的愁云而重见天日”[18]。
在台湾当局歧视性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台湾少数民族被公认为“弱势族群”,在社会生活中处在最低层。他们主要从事汉人一般不愿从事的脏、累和高危职业或低贱的职业,男子一般多从事远洋捕鱼、高层建筑、矿井作业、长途运输、码头搬运等职业,女子则大多被迫沦入卖淫及相关特殊服务行业。在新竹、花莲、高雄等地,山地籍妇女占了全部卖淫女的40%左右,其中许多少女沦为雏妓。雏妓每天要接待30—40个客人,没有休假,身患各种性病,境况十分悲惨[19](P212—232)。 在经济上,台湾少数民族的土地经常以各种理由被侵占。如1980年台湾当局以新建军港为名,诱骗取得兰屿土地,结果修的却是核废料场。又如屏东县玛家乡以修文化园区为名,无偿征用30余户“山胞”的土地及果园,每株芒果树年产值8000—20000元,却只赔偿400—800元, 导致这30多户“山地”农家完全破产[19] (P212 —232 )。 据统计, 仅1975—1987年间,完全失去土地的台湾少数民族就增加了15倍(从占总户数的1.2%猛增至34.3%)[19](P212—232)。在教育方面,台湾少数民族大专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仅为汉族的20%。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山胞”死亡率为汉族死亡率的2—3倍,婴儿死亡率为25倍。在高危工种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大多数是台湾少数民族工人[19] (P212 —232)。在文化上由于台湾当局推行汉化政策, 使少数民族文化逐渐消失,少数民族普遍有自卑感,不愿认同本民族文化。一些人担心,照此下去,“再过50年,原住民便要如平埔族一样永远消失”[19](P212—232)。
“原权运动”震撼了台湾社会,成为80—90年代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标志着台湾少数民族的觉醒,也标志着台湾当局民族政策的破产。在“原权运动”的推动下,“原住民”问题成为台湾各级人事事务关注的热点问题。台湾当局也不得不对此有所回应。如接待示威的“原权会”代表,对“原权运动”提出的问题,如“山地同胞”名称、蒙藏委员会的名称及权限、归还被侵占的山地保留地,以及修改宪法中有关民族政策条文……等等,均提交有关部门研究讨论。虽然最后均无果而终,但至少反映出“原权运动”对台湾当局的冲击。
“原权运动”在台湾仍处在方兴未艾的时期。前期“原权运动”未能取得满意成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台湾当局依然坚持其僵化的民族政策,不肯改弦易辙;二是以“原权会”为核心的台湾少数民族人士力量单薄,孤军奋战;加之他们以“台湾原住民”自居,有排斥其他民族之嫌,又容易被民进党的台独理论所利用、故岛内广大汉族居民对其持警惕态度。没有占人口总数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原权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四、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在台湾地区,祖国大陆人民同台湾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源远流长,并由此形成了台湾地区民族关系中不同于大陆的特点。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主要是岛内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是台湾地区有关各方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然而,台湾当局却舍本逐末,长期推行重大陆、轻岛内,重蒙藏、轻山地的错误僵化的民族政策,歧视和企图同化少数民族。致使台湾少数民族在各方面都沦为弱势族群,从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原权运动”。“原权运动”既是对台湾当局错误的民族政策提出的抗议和挑战,更是台湾少数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虽然因自身力量弱小而未能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却给台湾当局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岛内未来的民族关系增添了变数。
收稿日期:1999—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