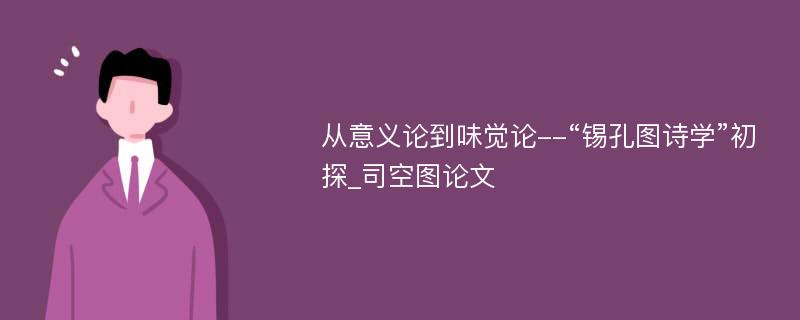
从意境论到品味论——司空图诗论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境论文,司空论文,诗论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唐末文人淡漠政治、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在直接造成诗歌创作由冷寂情思与淡泊境界走向浅俗平庸的同时,由于远离现实政治之纷扰,实际上又为诗人得以集中精力于艺术的涵味品鉴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之六诗云“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忧花阵被风欺。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正是对这种人生感受、心理动态乃至价值取向的极为简洁、明晰而生动的概括。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唐末文人亦往往能于平淡浅俗的体格中营造出一种可资品味的空间,宋人评薛能诗“天分有限,不逮诸公远矣,至合人意处,正如刍,时复咀嚼自佳”(《西清诗话》),包含在由“天分有限”而造成的大量平庸作品中的小部份“合人意处”却具有耐人咀嚼之佳味,实际上普遍符合唐末诗人的创作状况。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自举诗例云:
得于早春,则有“草嫩侵沙短,冰轻著雨销”,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得于山中,则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人”,又“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冰人”。得于江南,则有“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又“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得于塞下,则有“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得于丧乱,则有“骅骝思故第,鹦鹉失佳人”,又“鲸鲵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于道宫,则有“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幢幽”。得于夏景,则有“地凉清鹤梦,林静肃僧仪”。得于佛寺,则有“松日明金象,苔龛响木鱼”,又“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得于郊园,则有“远陂春旱渗,犹有水禽飞”。得于乐府,则有“晚妆留拜月,春季更生香”。得于寂寥,则有“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墨”。得于惬适,则有“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虽庶几不滨于浅涸,亦未废作者之讥诃也。又七言云“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又“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又“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又“殷勤元旦日,歌舞又明年”。皆不拘于一概也。这类作品,在司空图全部作品中虽为数甚少,但却显然代表着一种自觉追求的趋向,也就是他自己以之标榜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对此,宋人苏轼尝云“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又云“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独有承平之遗风”(《书黄子思诗集后》),由悲叹“当时不识其妙”,可见苏轼所持之赞许态度;由诗文高雅于“兵乱之间”,又正道出了唐末文人因逃避政治而得到艺术精味的结果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南宋人杨万里《读笠泽丛书》诗云“晚唐异味谁同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虽就陆龟蒙诗而发,然其明以“异味”概括整个晚唐诗,则又显然可见对那一时代性艺术走向的把握与理悟。
这种淡中求味的创作倾向,在映带着避世淡泊的社会思潮、士人心理因素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一种模铸新的艺术范型的自觉意识。再者,主要表现为前期余波遗绪的唐末诗坛,其本身又最大限度地承接容受着整个唐代诗史上的丰富创作经验与多种艺术渊源。这两大客观条件在唐末诗坛的交汇,也就为诗歌理论的深化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从而在创作实践衰微走势中呈现出理论成果丰硕的局面。在这方面,司空图的理论建树无疑是其最突出的标志。
二
在唐诗史上,司空图是最后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在其本人文学生涯中,主要成就亦显然在于诗歌理论方面。作为唐朝末期的诗论家,司空图对唐诗史各个阶段的重要诗人涉及颇多,在具体论述中带有对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创作特色与艺术经验加以总结概括的意味,如在其主要诗论文章《与王驾评诗书》、《与李生论诗书》、《题柳柳州集后》、《与极浦书》、《诗赋》等篇中,论及范围就包括张九龄、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大历十才子、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皇甫湜、贾岛、杨巨源、刘得仁、王驾等众多诗人,所论绝大部份无疑是极见精诣的。在总结前人丰富创作经验基础上,司空图进而将诗歌艺术表现的各种风格与意境特色概纳为二十四种类型,这集中体现于其著名的风格论专著《诗品》之中。以“品”论艺,在唐代之前大抵不出品等第优劣、叙渊源流变,司空图之《诗品》则略无品第叙源之义,除部份属表现方法外,大多皆指实某一风格类型,且不局限于某一派别或某一作家,既构成一种纯粹的理论形态,又显出相当广阔的宏观视界。每品之表达方式,大抵有二:一为摹神取象,以一境象之描述说明某一类诗风之特征,如论“典雅”云“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一为议论点悟,以抽象之语言辨明某一类诗风之特质,如论“雄浑”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正是这种既包容广泛又表述独特的理论形态,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被誉为“浑分两宜,至详且尽,增之不得,减之不得(杨迁芝《诗品浅解总论》),可见其生动性与准确性,另一方面又被称为“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赵执信《谈龙录》),可见其广泛性与启示性。
司空图固然试图在全面总结诗歌史丰富艺术经验基础上客观概括各种风格类型。但由于自身处在有意寻求避世环境与自觉追求淡泊诗境的时代风气之中,因而又显然可见其对冲淡一路诗风的偏爱。如“冲淡”云: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苒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借助高士精神风范的生动描绘,展示出一个理想化的艺术美境界。他如“高古”之“太华夜碧,人闻清钟”,“洗炼”之“空潭泻春,古镜照神”、“自然”之“幽人空山,过水采苹”、“疏野”之“筑室松下,脱帽看诗”、“清奇”之“神出古异,淡不可收”、“飘逸”之“缑山之鹤,华顶之云”、“旷达”之“花覆茅檐,疏雨相过”等与“冲淡”品格接近之类型,固与淡泊境界近似,即如“沉著”、“典雅”、“精神”、“缜密”、“实境”、“悲概”等与“冲淡”品格迥异之类型,也是“脱巾独步,时闻鸟声”、“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碧山人来,清酒满杯”,“水流花开,清露未晞”、“晴磵之曲,碧松之阴”、“萧萧落叶,漏雨苍苔”,实际上同样渗透着淡远的精神风范。正是因此,司空图最为推崇的是以“澄淡精致”的王维、韦应物诗为代表的淡远诗风。在《与王驾评诗书》中,他虽然说到“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但其充满热情的具体赞美则是“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沅之贯达”,同时贬斥元稹、白居易诗“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在《题柳柳州集后》又云“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深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对柳宗元诗更有相见恨晚之慨。联系这些态度鲜明的褒贬之语,无疑可以视为司空图自身价值取向与理论主张的重要佐证。
王、孟、韦、柳在唐诗史上既以“闲淡自得”、“温丽清深”的大体相类特点构成一个清淡诗风系统,又以“诗中有画”、“著壁成绘”、“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的艺术表现特点构成情景交融的最佳范式,因而成为试歌意境论建构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实践基础与理论依据。如殷璠标举“兴象”,即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为典例;戴叔伦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实际上也正是王维“诗中有画”,“在泉为珠,著壁成绘”之境界。因而,司空图以王、韦澄淡诗风为理想范式的诗歌理论,也自然与诗歌意境理论产生密切关联,如《与王驾评诗书》云:
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王生寓居其间,浸渍益久,五言所得,长
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其所倡导“思与境偕”,远接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之“神与物游”,近取皎然《诗式》“取境”之说,实则都是强调诗歌创作构思过程中的心物关系问题。就对作为诗境构成核心的心物关系的讨论而言,自王昌龄《诗格》、殷瑶《河岳英灵集》已肇其端,其后,随着创作实践中诗境构造的细密深化,大历、贞元以后,在戴叔伦、皎然、刘禹锡、白居易等众多诗人的自觉探索之中,诗歌意境理论已渐臻成熟。但是,此类论述无论是造境还是取境,实际上都属于对以情景交融为基本结构方式的诗境主要特征的定性认识与总体把握,,而对于诗境构成本身的多重性特点尚未能够深入探析。司空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显示出对其前辈的超越,其《与极浦书》云: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愚近作《虞乡县楼》及《柏梯》二篇,诚非平生所得者。然“宫路好禽声,轩车驻晚程”,即虞乡入境可见也。又“南楼山最秀,北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复生,亦当以著题见许。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试为我过一县城,少留寺阁,足知其不怍也,岂徒雪月之间哉。
司空图借“题纪之作”为例,说明既须“著题”,又不可徒摹“雪月”,所谓“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孙绰《兰亭诗序》),在景物描摹中必须注入作者的思想情感,才能达到“思与境偕”,也就是后世“意境”论者所标举的“意与境浑”、“意境融彻”的基本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司空图并不以此为止境,而是借“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之象喻,进而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概念,这就在刘禹锡“境生于象外”说的基础上更进一层,认识到诗境本身的多层次特点。其所云的第一个“象”,显指明晰可见的“著题”之境象,而第二个“象”,以其“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特点,则似乎为有赖于接受者审美联想而隐约呈显之境象,也就更具一种空灵缥缈之意味,这从司空图最为推崇的王维诗多有“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之类耐人寻味的虚无境象,似可得到较为具体的理解与印证。
三
正是基于这种多层次的诗境具有“岂容易可谈哉”的丰厚蕴含与虚玄意味,难以精确说明而仅能“味其深搜之致”(《题柳柳州集后》),司空图进而提出文学批评、艺术鉴赏的“品味”理论。其《与李生论诗书》云:
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之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停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举哉?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在以此为标准列举自己“得味于味外”(苏轼《书司空图诗》)之诗句后又云:
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
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司空图在这里明确提出两大问题,一是“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二是“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如果说前者是论诗之方法,那么后者则是论诗之内涵,而皆围绕“味”为核心。
本来,“味”为食物之味道,但因其中含有人的感觉功能因素,所以“味”的适用点也逐渐泛化开来。魏晋时代,“味”被用于艺术范畴,如阮籍《乐论》云“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其后,陆机《文赋》云“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又将“味”引入文论。以“味”论诗,则始自钟嵘《诗品》,其于《诗品序》中标举“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并由此在具体批评中建立、贯彻这一诗论“滋味”说。司空图以“味”论诗,显然受到钟嵘初建的“滋味”说的直接影响,而其论诗专著又明以“诗品”为题,也可见出与钟嵘《诗品》之间的渊源联系。不同的是,钟嵘《诗品》之“品”在于第高下、品优劣,司空图《诗品》之“品”则在于“辨于味”亦即品味,这就在以“味”论诗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品”的主观能动作用,使钟嵘的“滋味”说发展成为“品味”论。其《诗品》列述二十四品目,大要即在品辨各种类型诗风的不同之味。在确定“辨味”为论诗要旨之同时,司空图进而以“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为“味”之终极内涵。他以酸、咸为喻,醯虽酸、鹾虽咸,但仅有酸、咸而已,乏醇美之味,而只有“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才可得酸、咸之外的醇美之味,亦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苏轼在《书司空图诗》中尝言“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从苏轼的理解看,所谓“味外之旨”即味外之味。司空图最为推重的王、韦一路诗风,也正是以“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构成其艺术精髓。这样,在司空图艺术“品味”理论中,“象外之象”的审美联想与“味外之味”的品辨感受的叠合,便构成其诗学理想与艺术辩证法中的“全美”境界。
司空图的艺术品味理论,就其理想境界而言,固然远远超出了唐末诗人创作实践之范围,由对诗境的“全美”化要求以及其理论形态本身的虚玄化倾向,体现了以作为情景交融范式的淡远一路诗风为实践基础的特点,其理论本身则显示了作为初建于唐代中期的诗歌意境理论的伸展深化的性质。但是,由于淡中求味的创作倾向与审美情趣作为其理论生长点,唐末诗坛淡漠化人生态度与艺术追求,则显然是其最初的促发契机。因此,司空图艺术品味论的出现,究其根本,仍然可以视为与唐末文人避世生活、淡泊诗风大体保持同一走向中的理论产物。
四
就艺术表现特征及其所激发的诗学理想的实际走向看,如果说,唐初宫廷诗歌艺术的精致化特点,在随着诗坛中心的转移而走向社会,最终成为开元都城诗艺术构成的重要渊源,从而促使成熟于开元时代的以情景交融为主要标志的精雅诗境的生成,那么,唐末诗歌艺术的淡泊化特点,在诗人因有意识逃避世事而得到集中精力于艺术品鉴的条件下,则进而促生淡中品味的艺术趣味,使得诗学思想由对传统意境论的深化而走向“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那样的虚玄化。以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唐末诗论,就“一方面领导了后来的文品、赋品、词品等等的著作,一方面又领导了后人的意境、空灵等等诗论”(罗根译《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唐以后文学思想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宋人严羽论诗标举“盛唐”,却并未祖祧作为开天诗坛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的殷璠的“风骨”、“兴象”(《河岳英灵集》)之说,而是撷取司空图《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旨申论“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穷”(《沧浪诗话·诗辨》),将诗论引向禅悟之境。其后,清人王士禛进而据之编《唐贤三昧集》,正式标举色相俱空的“神韵”之说。尽管赵执信认为《诗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谈龙录》),纪昀亦云《诗品》“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王士禛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又取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语,以为诗家之极则,其实非图意也”(《四库全书总目》),对其偏取一格持批评态度,但在客观上恰恰标划出由司空图→严羽→王士禛构成的“神韵论”渊源与走向。由此也可以说明,唐末诗坛所呈现的唐诗审美的蜕变与诗学理想的转向,在主要表现为雄强风骨的衰靡与虚玄韵味的替兴的同时,实际上已经铸就了艺术“神韵论”的最初雏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