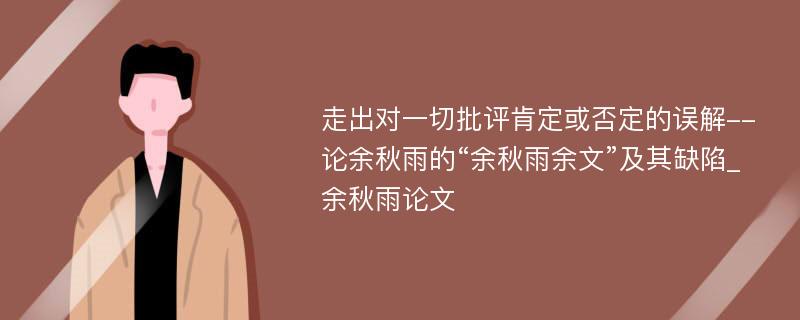
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再谈余秋雨散文的瑜与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秋雨论文,再谈论文,误区论文,散文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在文坛上下不胫而走,赢得了几乎是众口一辞的赞扬时,我曾写过《过于随意的历史读解》和《平心静气话秋雨》两篇文章,旨在强调应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待和评价秋雨先生的散文创作,特别是要清醒地看到和认识秋雨散文中掺杂的某些观念上的偏颇和尺度上的悖谬,而切不可不加分析地一味推崇褒扬,以致捧杀作家,同时误导读者。这两篇文章分别在《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4 期和《当代文坛》1995年第6期发表后, 我曾接到几位学者和评论家的信函与电话,表示同意拙文的思路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则相继于1995年第10期和1996年第2 期全文转载了上述二文。这庶几可以说明,拙文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当时曾有报刊约我再写一点有关秋雨散文评论的文章。然而,我却迟迟没有从命。之所以如此,倒不是我自觉在秋雨散文这个问题上已经无话可说,而完全是为了避免某种误会。要知道在时下听惯了颂歌的文坛上,一个批评家就某一位作家的创作连续发表毁誉参半的文章,是很容易被认为彼此间有“夙怨”的。我同秋雨先生素昧平生,甚至缘悭一见,以往撰文说些不同的意见,无非是出于书生的较真,又何必因一时的痛快而自招嫌疑呢?
然而,此时此刻,我终于决定拿起笔来,再谈秋雨散文创作这个老话题。这一则因为自前番论秋雨散文迄今已将近一载,时间距离已自然消解了产生误会的可能,而我在这个问题上又确有以往未曾说尽的意思要接着说: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缘故,这就是近来我有幸读了几篇同样是谈论秋雨散文的文章,它们特有的观点、尺度、思维方式乃至语言表达,使我关于秋雨散文的评价在原有思路之外,有了一些更为微观具体,也愈加深入辩证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无论从准确评价秋雨散文创作得失优劣的角度考虑,抑或就普遍增强文艺评论科学性的意义着眼,都有明白一叙的必要。
我于近期报刊读到的有关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主要有三篇,它们是王强的《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刊于《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1期;韩石山的《余秋雨散文的缺憾》, 刊于《北京青年报》1996年3月12日;程光炜的《疲惫的阅读》, 刊于《中华读书报》1996年3月27日。另有汤溢泽刊于《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的一篇,我未能读到全文,但从《作家报》上看到了题为《〈文化苦旅〉是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的较长的观点摘要。这几篇文章,一看标题就知道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批评余秋雨散文文本的,属于秋雨散文的否定派。按说在秋雨散文的评价上,我早就写过包含了诸多批评意见的文章,对于以上诸家所论,似乎应当引以为“同调”。然而,事实上,我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几篇文章的观点和说法。这是因为,当初我撰文指出秋雨散文的某些观念偏颇和尺度悖谬,是在充分肯定其成绩和贡献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一分为二的、旨在准确认识评价秋雨散文现象的审美考察,而上述几家所论,是单说秋雨散文的缺憾与弊端的,更确切一点说,是从整体和根本上否定秋雨散文的,而他们所指出的秋雨散文的症结,或者说否定秋雨散文的理由,从学理的角度看,明显存在着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与片面性,因此,其论述本身连同相应的结论,便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足够的说服力。为了把这一问题表述得更具体、更清晰一些,以下针对几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分别进行一点简要的辨析。
二
不妨先谈韩石山先生的文章。这篇只有1600字的短论,其结论为:“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入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而实际上用来说明、印证这种“缺憾”和“模式”的文本,却只有一篇《道士塔》。而这篇《道士塔》的主要毛病,在韩先生看来,又在于作家描绘历史细节时的“信口雌黄”,即“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自己亲眼见过似的”,以致于让人感到“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这样一种逻辑论证显然是极不严谨、颇多罅漏的。此外,我们且不说仅凭对一篇作品的分析就引申出作家整个散文创作的“缺憾”、“模式”,有没有管窥蠡测、以偏概全之嫌;也姑不论细节描写的生动逼真与创作“模式”之间有什么关系,不加分析地将它们扯在一起,强为因果,是否属于毫无道理的“拉郎配”?即使单看对《道士塔》本身的诟病,也根本经不起推敲。试想:散文一体固然有真实的要求,然而,无数成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这种真实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主体品格的规范,即散文作品必须承载作家真实的人生与情感体验;而并不绝对排斥作家在抒发真情实感的过程中,对某些艺术化了的客体场景和生活细节进行必要的整合、生发和渲染,更何况《道士塔》中的某些历史的钩沉。在这种早已失去了体验世界的依托与参照的艺术创造中,作家从史料出发,凭借合理的想象展开灵动的描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需的。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一篇《道士塔》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自己亲眼见过似的”,非但不是什么缺憾,相反是一种成功。至于它在文体上是像散文还是像小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大凡有创意的文学作品,常常善于打破既定的文体界限,而把多种文体的表现因素汇于一身,其结果并不妨碍自身的审美价值,而是成就了一种艺术的新鲜感与“陌生化”。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社戏》、《鸭的喜剧》等作品,已提供了为人赞赏的先例,石山先生又何必胶柱鼓瑟,不事变通呢?
再看程光炜先生的文章,尽管也只有区区千余字,但是却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整体性的判断:读余秋雨的散文让人感到精神很累。至于“累”的原因,作者归咎于秋雨为文的两大失误:一曰讲述历史时的教师姿态;二曰引征史料,传播史识时的缺乏节制与收敛。这样的责难乍一听来似有道理,但稍加分析,仍然难以自圆其说。首先,秋雨散文讲述历史确有不少居高临下的教师口吻。但是这种口吻在作家那里,与其说是知识人格的一种外化,不如说是为了达到吐纳古今,传经布道的目的而选择的一种叙述手段。它在接受效果上并不一定导致疲惫,这里关键看它是否做到了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君不见,作为古代小说“家数”之一的“讲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居高临下,全知全能的“教师爷”口吻,但由于它很讲究传达的技巧和艺术,所以,照样具有引人入胜的力量。具体到秋雨散文而言,它的叙事形态,包括语言、笔调、结构、场景、境界等等,都是极富才情和高度审美化了的,因而表现出很强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关于这一点,不少读者包括一些艺术要求很高的作家和评论家的阅读体验可作证明。由此看来,光炜先生在教师身份和阅读疲惫之间简单划等号,是不足为训的。其次,出于同读者一起淘洗历史、感知历史的目的,秋雨散文在构建艺术文体的过程中,的确引入了较多的正史、裨说、诗文、掌故、遗迹等等。此种引入虽然有时暴露出或辨别不慎,以讹传讹,或张冠李戴,郢书燕说的毛病(关于这一点,笔者《过于随意的历史读解》一文即有所涉及,可参阅),但就整体的叙述形态和阅读效果而言,毕竟称得上渊赡丰厚而又举重若轻,旁逸斜出而又水乳交融,不少青年读者正是通过这样的历史解读,知道了莫高窟与天一阁,懂得了毛笔文化与科举制度……而此种效果之所以取得,自然主要得力于作家征引历史资料、传播历史知识时的舒卷自如,万取一收,即一种从容自由地驾驭材料的功力。光炜先生无视这样的事实,在不提供任何文本实证的情况下,断言秋雨散文“太爱铺排历史常识”,缺少敏锐的适度感,用情不敛等等,便颇有几分无的放矢和言不及义之嫌,因而也就很难令人心悦诚服。
接下来再看汤溢泽的文章。在这篇专门批评《文化苦旅》的文字里,作者除留下了“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业余散文爱好者摆弄现代汉语的词藻而步入一条媚史之路”;“都是陈年白酒(如古代文化)与当今矿泉水、自来水(如优美的语句、感叹)掺和的产物”;“是一本单调的散文集子”、“是当今散文界典型衰败的标本”之类的基本评价外,还指出了《文化苦旅》走俏文坛的两种原因,即:80年代中后期的特殊文化氛围和由文化界哄抬及作家自我推销构成的商业性包装。坦率地说,上述观点,无论是基本评价抑或是原因探寻,都显得相当草率,相当随意,其中偏颇失当,信口开河之处,几乎一目了然。譬如:对于余秋雨,我并不同意某位评论家所作的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的极端性、夸饰性的定位,但是,汤文将其降至“业余散文爱好者”的水准和层次,是否又走上另一极端呢?要知道,秋雨先生作为作家的学养与才识,毕竟是大多数同行难望项背的;对于《文化苦旅》,我也不赞成有的论者故作惊人之语,把它说得尽善尽美,天衣无缝,俨然是前无古人的峰巅之作,然而,汤文将其断为“一本单调的散文集子”,“是当今散文界典型衰败的标本”,无疑属于另一种向度的哗众取宠之语,须看到《文化苦旅》在散文文体的拓展与更新上,毕竟有着属于自己的贡献。还有汤文把《文化苦旅》的走俏,归结为迎合了80年代中后期的特殊文化氛围,也许不无道理,只是作家从环境和读者的角度出发,做创作切入点的选择,原本是符合艺术规律的正常现象,论者又有什么理由借此来贬抑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呢?至于汤文说《文化苦旅》的畅行得益于文化界和作家自己的商业性包装,更属不负责任的妄断。这里,我们即使不在乎论者将“作品后记”、“作家简介”统统视为商业性策略与包装,已有无中生有、强词夺理之嫌,而只要想想“文化苦旅”散文系列自1988年在《收获》连载,到1992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再到1994年引起广泛注意,整整经历了六年的时间,即可发现,它的走俏与商业包装炒作的一般规律委实无涉,更何况一部《文化苦旅》先后再版七次,印数达20多万,这是以一次性消费为突出特征的商业行为无论如何难以达到的效果。
最后来看王强的《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这篇文字以空前激烈的语言对余秋雨的学术研究和散文创作,展开了严厉的批评直至彻底否定,其中不能说没有合理的因素,但从总体观点和文风上讲,却显得简单、武断、粗疏、生硬、贻人以浮夸、霸道之感。以下试举其在秋雨散文评价上暴露出的两点重要缺欠作为例证并稍加辨析:第一,王文全然否定秋雨散文的鼎新意义,而此种否定的依据是一个三段论:秋雨散文是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混合物;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是早已有之且过了时的情绪,因此,秋雨散文也谈不上什么新贡献。这样的逻辑推理实在包含了太多的破绽。我们完全可以反诘论者:你根据什么把秋雨散文划入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此种划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秋雨散文的实际?伪浪漫主义固然已为文坛所不取,但真诚的浪漫主义却永远是蓬勃生命的润滑剂,在物质每每挤压人性的今天,我们能说浪漫情怀已是明日黄花吗?退一步说,即便是秋雨散文打上了某种古已有之的创作思潮的印记,难道我们可以仅仅凭借这一点,便绝对否定它推陈出新的可能吗?答案无疑同论者的观点是相反的。第二,王文每每用“余秋雨身上毫无现代学术气息”,“缺乏最起码的学术理性”,“他根本不懂什么是人类学,更谈不上用现代人类学的方式研究地域文化”这类绝对化的语言作为自己的审美判断,但是能够支撑这种判断的例语分析却十分单薄,且常常喜欢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譬如,为了说明余秋雨“对西方文化的无知”,该文闭口不谈秋雨散文中随处可见的对西方文化的成功引述与评说,而单单抓住《阳关雪》写“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一句展开褒贬,认为艾略特《荒原》一诗的意象和坟堆毫不相干,进而断言余秋雨并未读过《荒原》一诗。然而,论者是否知道,艾略特的《荒原》虽然没有多少荒原的形象,但是却着重写到了死亡,诗的开头便有“在死亡的/土地上养育出丁香”这样的句子,这怎能说和坟堆毫不相干呢?还有,王文为了说明秋雨不懂地域文化研究,便选中《天涯故事》进行相当简单的归纳和相当随意的抽象,而将《上海人》、《江南小镇》、《西湖梦》这些成功地勾勒出特定地域文化风致的篇章一概置之不顾,此种失去了起码的科学性与严肃性的推论,自然是无法服人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韩石山等四位先生的批评文章,尽管立论大胆,颇具锋芒,但都未能真正触及到秋雨散文的症结所在,更不用说从根本上否定秋雨散文了;相反,它们因自身的粗疏草率而贻人以吹毛求疵、故作惊人之语之感。这时,我不禁想起西哲的名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第一次是正题,第二次是反题……当代文坛对秋雨散文的评价似乎也在遵循着这一规律:开始是毫无保留的赞扬,继而是七嘴八舌的批评,而无论是赞扬或批评,都缺乏一种客观的、公允的、辩证的精神,都流露出好便好得无懈可击,差便差得一无是处的绝对化倾向,都显示了我们批评的尚不成熟。现在,是我们应当由正题、反题走向合题,即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地打量、评价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时候了。
三
那么,在当代散文乃至文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下,秋雨散文作为颇有影响的一家,究竟有何种突出贡献,而又有哪些明显不足呢?关于前一个问题,我在《平心静气话秋雨》和《过于随意的历史读解》中,已有虽然简单、但却明白的概括,此处不赘。倒是一个问题,拙文两篇尽管花费了不少笔墨,但受特定的逻辑思路的限制,却没有把该说的话都说彻底,说清楚。以下笔者在原来所论的基础上,着重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在我看来,秋雨散文的缺陷并不在艺术形式上,相反,在这一视角上,作家的实际情况堪称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秋雨散文的根本弊端是精神的返祖、思想的陈旧和情感的落伍。说具体点,便是将一种比较典型的旧式文人的情感方式、心理结构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了文体叙述之中,以致造成了诸多篇章审美意向的倾斜。当然,所有这些返祖的、陈旧的、落伍的基因,都同一些相当现代的东西嫁接组合在一起,都拥有一种相当现代的文化姿态,因而,它不那么容易辨识,也不那么令人生厌。
第一,众所周知,余秋雨的散文作品,尤其是《文化苦旅》系列,常常叙写自然环境与风物,而每当这时,作家所极力推崇,一味激赏的是那种阴柔宁静的氛围与平和疏淡的画面。譬如,他这样写鸣沙山和月牙泉:“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惟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沙原隐泉》)。他这样看江南小镇:“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并认为:江南小镇“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生范式,在无形之中悄悄控制着遍及九州的志士仁人,使他们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梦中轻笑”(《江南小镇》)。显然,在作家笔下和心中,宁谧、平实、避世绝尘,已不仅仅是美到极致的自然形态,同时,它还是令人神往的生命境界。这便很有些封建文人仕途坎坷时常有的出世意味与隐逸色彩了。对于此种植根于千年封建文化的人生态度,我们固然无法否定其曾经有过的积极意义——譬如它使一些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因远离肮脏的权利之争而保持了高洁,但是,它出现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特别是出现在一些以建设当代精神文明为已任的中国作家身上,却不能不是一种悲剧。因为在这种隐逸与出世的背后,是精神的失语,责任的消解,守望的放弃,是社会精英意识的淡化乃至沉沦。
第二,正如许多论者所言,余秋雨的散文包含了较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便决定了其艺术叙述不得不经常进行历史与文化的透析与评价。而每当这时,作家对作为遗产的一切,虽然不乏站在时代高度的理性的批判,如《十万进士》指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历史的暗角》揭露了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小人”现象等等。但是,在感情上,他仿佛保留了太多的肯定和认同,因此其字里行间仍旧自觉或不自觉地流溢出一派或惋惜眷恋,或推重激赏,或毕恭毕敬的倾向。请读读《笔墨祭》吧!这篇溶知识性和史料性于一体的文字,在如数家珍的谈笔说墨中,将中国传统的毛笔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书法人格,表现得灵象飞动,意趣盎然,以致使读者几乎忘记了作家的“卒章显志”:传统的毛笔文化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青云谱随想》是写晚明画家朱耷的。该文一方面对朱耷生命激情的强悍呈现给予了热情赞美,另一方面却对现代艺术和现代受众表示了某种遗憾,这样一来,它留给人们的干脆就是一种有关传统的审美缅怀与仰视。还有《风雨天一阁》写宁波天一阁,《千年庭院》写湖南岳麓书院,《遥远的绝响》写魏晋人物,无不是相当投入地抒写着、体味着先贤的伟举与昨日的辉煌,有时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平心而论,这样的描写孤立起来看,并无太大的不妥,只是它一旦成为作家的感情和心理定势,便必然会影响其对历史文化所应持的批判鉴别的目光,特别是必然会影响其在扬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时代新文化的自觉性与彻底性。
第三,余秋雨的散文喜欢驻足于阔大的历史空间,发掘历史遗迹,评价历史事件,因此,也免不了要臧否历史人物。而在进行后一项工作时,作家似乎有一种并不怎么自觉的褒贬习惯,这就是总愿意将一种欣赏的目光,投注到那些清静无为的生命状态和逍遥空灵的人生范式上,如《狼山脚下》写遁入空门的骆宾王,《西湖梦》写隐居西湖的林和靖,《柳侯祠》写谪贬永州的柳宗元等等,均可作如是观。而在所有类似描写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自属《苏东坡突围》一文所写的苏东坡。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苏东坡兼有儒、释、道诸家思想。而这诸家思想又随着作家人生经历与环境的变幻而有隐显之别,大致来说,21岁考取进士,步入仕途时的苏东坡,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堪称儒家思想鼓舞下的“奋励有当世志”。后来经过宦海沉浮,新旧党争,特别是经过“乌台诗案”,40多岁被贬黄州的苏东坡,则更多归入了佛禅之门。此时,他深感“四十七年真一梦”,“此生念念随泡影”,所以,总是标举随遇而安,追求逍遥适意,寻觅自我解脱,归于乐观旷达。而《苏东坡突围》所极力推崇、张扬和肯定的,正是到黄州之后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苏东坡。应当承认,这样一种有关历史人物的亲近感自有它产生和存在的道理;它所亲近的历史人物特有的生命状态和人生范式,在封建社会里亦自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只是它频频出现在一位当代作家的笔下,便无形中浮现出人格崇尚的意味;而那种陶渊明式的弃嚣绝尘,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同健全的现代人格,毕竟相去甚远,因此,在今天的文化语境里,过多地称赞它和过高地估价它,都可能引发消极的、负面的因素,以致最终影响现代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第四,就秋雨散文的全部作品来看,后期的“山居笔记”系列较之前期的“文化苦旅”系列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思辨内容的增强和政论色彩的渐浓。正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山居笔记》系列的一些篇章,直接提出了若干模糊的社会基本矛盾,从本质上讲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例如《抱愧山西》主张保护社会经济的自然进程,而不赞成包括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在内的来自上层建筑的任何革命;《一个王朝的背影》认为,近代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引申出来的民族正统论风行的结果;《苏东坡突围》则干脆把苏东坡的命运悲剧归咎于中华民族的“酱缸文化”……凡此种种,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抑或就哲学的意义讲,都是很可以探讨与商榷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以往的二文中,已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析,本文为节省篇幅,就不再枝蔓了。
标签:余秋雨论文; 散文论文; 文化苦旅论文; 余秋雨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苏东坡突围论文; 荒原论文; 作家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