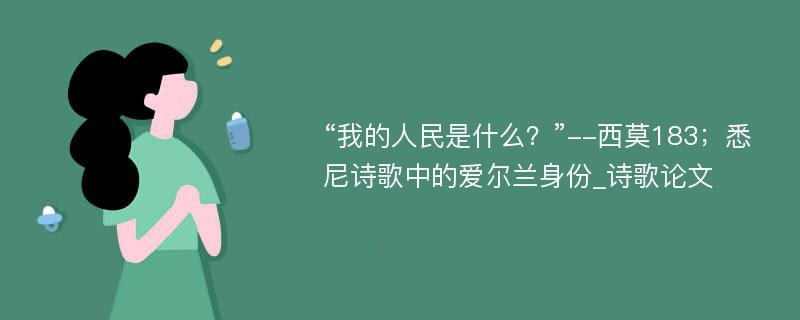
“什么是我的民族”——谢默斯#183;希尼诗歌中的爱尔兰身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尔兰论文,诗歌论文,身份论文,民族论文,谢默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莎士比亚笔下,爱尔兰人麦克默里斯就问过:“什么是我的民族?”①这个困惑延续至今,对民族身份的思考可以说构成了当代爱尔兰作家创作的重要部分,因为对“处于危机”的爱尔兰文化来说,“个体对肯定和特性的追求与群体定义自我的努力密切相连,至少相似”。②在当代爱尔兰作家中,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尤其被欧美读者认为表达了对爱尔兰身份的重要直觉,③国内很多研究者也提出了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杂合性,并将其与希尼的文学创作联系起来。④不过,希尼笔下的爱尔兰民族文化甚至“民族性”是否可以用某个词语来完全概括?此外,所谓爱尔兰的“民族性”是否是一个随着时代和环境而不断改变的意识形态建构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民族概念的历史性,但民族文化、民族性这些概念有时仍被赋予一种本质主义的内涵。⑤通过分析希尼不同阶段的诗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希尼的民族身份观的变化,也可以对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动态建构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矛盾中的三思
在创作初期,希尼赋予了他的出生地摩斯巴恩(Mossbawn)重要的时间和空间意义,把这个小农庄视为北爱身份的象征和立足点。他从词源上对Mossbawn进行了辨析:“Moss”是苏格兰词,“bawn”是英语,当地口语中的“bann”则是爱尔兰语“bán”的变化;在空间上,摩斯巴恩位于莫尤拉勋爵家那高墙环绕的庄园和班河西岸苔藓遍布的沼泽地之间,是17世纪来到北爱的英国殖民家族的领地,因此摩斯巴恩正介乎英国殖民地和爱尔兰特色地域之间。⑥这一多元时空特点使摩斯巴恩“隐喻着乌尔斯特文化的分裂”(Preoccupations:35),同时也隐喻着希尼自己生于北爱天主教家庭却接受英国文化教育这一分裂的文化身份。
但事实上,在后殖民时代,希尼这样的多元文化身份并不少见,也并非不能建立一种和谐的生存模式。使希尼将多元等同于分裂的,一是北爱新教统治者在教育、工作、居住等方面对天主教徒露骨的歧视和排挤以及1968年后北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暴力冲突的升级,二是70年代以对抗和斗争为主流的世界政治话语。在这样的情势下,和解往往被视为妥协,因此希尼在文章结尾称“我把个人的爱尔兰情感当作元音,把英语滋养的文学意识当做辅音”(Preoccupations:37)还是需要勇气的。英国媒体固然会欣赏这种文化融合的态度,希尼身边的天主教社会却可能视之为背叛。正如伊格尔顿深刻地指出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我们所谓的道德问题”⑦,希尼的这种非民族主义立场让他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深感道德上的愧疚。诗歌《苦路岛》(1984)中,一个被射杀的天主教徒的鬼魂突然出现在他身后,满面血污,这正是希尼内心深处受到的道德责备的外化;而他强烈的痛苦则在诗歌结尾处的忏悔中体现出来:“宽恕我这种漠不关心的生活——/宽恕我胆怯和瞻前顾后的介入。”⑧
不过,像当时很多北爱天主教徒一样,希尼并不总能保持非政治的立场,有时英国和北爱新教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反而使希尼的道德选择变得简单。1968年北爱冲突升级后,希尼曾写过好几首政治色彩非常鲜明的鼓动性诗歌,这些诗歌后来在1972年出版《在外过冬》时都因为政治宣传色彩太浓而被希尼自己删掉了。其中,《克雷格德龙骑兵》以反讽口吻颂扬英国皇家龙骑兵1798年屠杀数万爱尔兰起义者的行为,该诗的目的简单明确,就是激起北爱天主教徒的民族主义情绪;《恫吓》一诗更直接表达了对北爱新教徒庆祝威廉三世博因河胜利的憎恨,骂这些新教徒是“一窝蚂蚁”、“贫民窟的老鼠”,说他们的行为不过是“仲夏的疯狂”,是“搅动过去来品尝灰烬”。⑨此时希尼常用“我们”和“他们”来为北爱社会划分界线,用“我们”来表达一种明确的群体意识。虽然在《在外过冬》中这些“派系冲突和暴力”⑩情绪被删除或淡化了,但有些诗歌,比如《骨之梦》中掷向英格兰的骨头(11),仍然流露出高压政治所激发的民族仇恨。甚至直到1977年接受谢默斯·丹恩采访时,希尼依然将自己的立场简化为“我的团体是天主教的和民族主义的”(12)。
但是,希尼毕竟是一个诗人,他那诗人的历史意识时时超出他的民族主义道德吁求,要求他对自己的身份有更细致的辨查,而不是做出简单的选择。单纯的民族主义在他的诗中只是少数,大多数诗歌则描绘了问题的复杂内涵和他内心的复杂情绪。事实上,就如海伦·凡德勒指出的,这种“三思”(second thoughts)正是希尼诗歌的魅力所在,“使情绪化的态度得到智性的反思,前者则几乎总是滑入政治宣传的两极立场。”(13)当希尼说“与我们自己争辩的是诗歌”(Preoccupations:34)时,说的正是自己在民族身份和诗人身份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要求之间感到的矛盾、斗争和所做的再三斟酌。
二、寻根和无根
希尼从创作伊始就意识到了自己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而在当时本质主义和本原论的思潮下,他首先试图在枝枝蔓蔓中寻找自己民族的根,以此为自己的身份找到一个立足点。而且,通过寻找民族的本原和本质,他的艺术也能在北爱的现实冲突中找到一个介入点,从而使他多少可以解决生活的现实责任和艺术的超现实自由之间的矛盾。(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1964年写的《挖掘》视为自己诗歌创作的真正开始,称“第一次我觉得自己不仅仅在排列词语”(Preoccupations:41),吴德安称“此诗要挖掘的是他的血源,他的根和在成长后独立起来的自我”(15),正确指出了“挖掘”在希尼这里具有的寻找身份的重要意义。
在《挖掘》中,希尼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归入父亲挖掘马铃薯、祖父挖掘泥炭这一爱尔兰乡村生活传统之中,换句话说,希尼将乡村视为爱尔兰性的根基。事实上,从1966年的《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到2006年的《域与环》,田野、树林、牛群这些乡村意象始终在希尼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在诗集《电灯》(2001)中希尼甚至直接将自己的诗歌追溯到维吉尔的田园诗传统。显然,和叶芝等很多爱尔兰诗人一样,希尼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爱尔兰性与爱尔兰乡村生活联系在一起,乡村的摩斯巴恩也因此被希尼称作世界的“中心”(Preoccupations:17)。
几乎完全被英国排斥在工业革命之外的爱尔兰无疑是乡村的和自然的,但问题是,这并不是爱尔兰自己的选择。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在传统话语中,“作为自然的爱尔兰被与作为文明的英格兰对立”(16),与未开化、骚乱、毁灭联系在一起,与粗野、褊狭、刻薄画上等号,最终在大饥荒中被当做“不可控制的外部”(17)被英国文明抛弃。希尼笔下的爱尔兰虽然常常充满着田园的宁静和美丽,但把乡村和“自然”视为爱尔兰文化的核心,与其说回到了爱尔兰的根,不如说落入了英国殖民话语对爱尔兰的他者化想象。
诗集《北方》(1975)中的《泥沼女王》一诗正是希尼早期文化寻根观的集中体现。《北方》虽然出版在希尼移居爱尔兰共和国之后,但其中不少诗歌却是在1972年创作的,因此可以与《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进入黑暗之门》(1969)和《在外过冬》一起,视为处身北爱冲突之中的希尼对民族身份的直接感受,其中《泥沼女王》则被认为是整部诗集的“基石”。(18)
泥沼女王是一个公元10世纪左右的维京女子,尸体于1781年在贝尔法斯特南部的泥炭沼中被发现。北欧海盗时代虽然不及凯尔特时代久远,但将现代的北爱尔兰与铁器时代的丹麦联系在一起,已足以帮助希尼进入英国殖民历史之前的爱尔兰。不过,诗中更重要的是作为全诗核心的两个意象:泥沼和女王——自然和女性。然而,事实上,这两个被希尼用来象征爱尔兰民族特性的意象却正是传统英国殖民话语中爱尔兰的主要形象。
希尼一直把沼泽视为爱尔兰的“历史轴承”(North:33),在他看来,向沼泽深处的挖掘正是向爱尔兰之根的挖掘。诗中的沼泽位于“泥炭地表和庄园围墙之间”(North:32),正如摩斯巴恩位于班河沼泽和莫尤拉庄园之间;沼泽女王的身体塞满“野性的根”,写下的是“盲文”(North:32),就像希尼的祖先用铁锹在大地上写下非文字的文化。问题是,维京文化并不是爱尔兰文化沼泽的底,希尼的沼泽寻根之旅注定没有答案。希尼自己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沼泽“无底”(Preoccupations:35)、“潮湿的中心没有底”(19),或“它的根基/不定可变”(North:14)。在《北方》的第一章第一首《安提俄斯》中,希尼曾雄心勃勃地称只要立足大地就有无穷力量。有趣的是,就在同一章最后一首《赫拉克勒斯和安提俄斯》中,安提俄斯却只能在无奈的失根中接受死亡。这个巧妙的首尾安排正暗示了希尼自身的寻根之旅所面临的无奈的失败结局。
《泥沼女王》中的女性意象同样值得注意。将爱尔兰比喻为女性是希尼诗歌常用的手法,比如在《凯维山的婚约》中将北方新教徒描写成抢劫南方新娘的暴徒。事实上,用受难的女性和强暴她的男性来比喻爱尔兰和英国在爱尔兰文学中长期存在。爱尔兰有一种8世纪流行的盖尔语诗体“幻景诗”(Aisling),常常把爱尔兰描写为纯洁无助的女子,一次次被来自英国的男性侵略者强奸。(20)希尼也知道这一传统,并以《幻景诗》为题专门写过这个体裁。不过,更重要的是,像“自然”一样,他不仅借用这个传统隐喻,而且把它完全内化为了自己的思想,比如常把自己的创作描绘为女性的爱尔兰题材与男性的英国文学手法的结合(Preoccupations:34)。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这一话语传统中的女性形象不但是对爱尔兰的歪曲,也是对英国殖民话语的不自觉的接受。(21)希尼笔下无论女性的还是自然的爱尔兰都暴露了希尼的民族本原观所受到的英国殖民话语的影响。
希尼对摩斯巴恩的历史挖掘同样问题重重。首先,在词源上,希尼认为“bawn”是英语词,但这个词实际来自爱尔兰语的“badhún”(牛栏)。其次,在空间上,希尼用莫尤拉庄园代表盎格鲁-萨克森民族,但莫尤拉勋爵的曾祖母弗朗西斯·霍尔(22)来自爱尔兰中南部的蒂珀雷里郡,非常可能有爱尔兰血统。由此可见,作为希尼的身份中心的摩斯巴恩并不像他勾勒的那么时空清晰。事实上,希尼对爱尔兰性的历史挖掘常常陷入黑暗的泥沼,希尼的困境显示的正是通过历史挖掘来寻找身份的“返祖的传统主义”(23)的困境。
三、民族与个人
1972年英军枪杀13名天主教示威者,北爱形势急剧恶化。几个月后,希尼移居爱尔兰共和国威克劳郡的格兰莫尔。希尼的这一选择,有人欢呼为公开表明了他的爱尔兰立场,但也有不少北爱天主教徒认为他背叛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爱同胞。(24)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当年创作的《格兰莫尔十四行诗》中,希尼描写了自己在格兰莫尔宁静悠闲甚至略带放纵的田园生活,与北爱血腥恐怖的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希尼的“改换护照”其实同时包含着介入和逃避双重含义,这种模棱两可的含混态度在希尼的很多作品中也都存在,实际反映了希尼从创作伊始就面临的群体与个体的矛盾。
1972年应该是希尼生命中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尤为激化的一年,12年后希尼专门撰文描述当年他如何在暴力冲突中放弃了录制自己的诗歌,两年后他又再次宣读了这篇题为《尼禄、契诃夫的白兰地及一个来访者的趣事》的文章。希尼在这篇文章中把他的困境称为艺术与生活的矛盾,本质上,这是个体立场与民族立场的矛盾。如果他当时录制的是民族斗争的诗歌,他并不需要停止自己的艺术行为。在民族危难时,个人的精神追求与民族的政治诉求并不总是一致,当两者间的冲突加剧时,作为诗人的希尼也开始对民族责任进行反思。在早期,“什么是我的民族”这个问题对希尼来说重要的是“什么”,而现在,“民族”这个概念本身成了问题。希尼开始认识到“民族”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先定概念,而是“我的”。那么“我的民族”是由一个个像我一样有着不同要求的个体组成的,还是一个需要牺牲这些个体自我的“想象的共同体”?
希尼移居爱尔兰共和国之后的作品表明,他后来渐渐离开了民族立场,转向了个人。在《北方》中一些后期创作的诗歌里,希尼已经开始反思自己那“负有义务的忧伤”(North:73),怀疑自己为了什么而忧伤,“为了耳朵吗?为了民众吗?/为了那些背后的言辞吗?”(North:73)当他喊出“我是……/一个内心的流亡者”(North:73)的时候,已经预示了向个人世界的转移。接下来的诗集《野外工作》(1979)中的第一首《牡蛎》明确表达了对那些纠缠着自己的殖民历史的厌恶,就像布莱克·莫里森所描绘的,决心“不再受历史的摆布;他的思想将自由地飞向任何想去的地方,他将仅仅依靠诗的想象”(25)。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整部《野外工作》的结构。在前7首中,希尼的想象仍然无法完全离开北爱的屠杀和死亡,但第7首《横祸》中,个人对快乐的要求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出现在民族对复仇的要求之中。该诗描写英军射杀了13名天主教示威者之后,爱尔兰共和军实行宵禁准备报复,而诗歌的主人公不顾宵禁去酒吧喝酒,结果被自己人炸成碎片。主人公本应该服从“我们宗族的共谋”(26),却坚持对个人快乐的追求。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我”也没有从群体的立场出发指责主人公的行为,反而称“我和他一起品尝着自由”(27)。有的评论者称希尼这里的转变是“为他的诗歌找到了一个新的非政治的范式”(28)。
由此,《横祸》之后的诗歌从前期的“匿名性和考古学”转向了“描写处身普通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人”(29),其中创作于1972年的《格兰莫尔十四行诗》没有被收入更早的《北方》而放在这里,显然希尼此时才对这种个人取向有了足够的自信。有的评论者认为这里的自信受到美国诗人洛威尔的影响,因为“洛威尔作为有着自己独特私人生活的诗人和艺术家,拥有自信的自我意识”(30)。希尼这些个人化的诗歌大都描写乡村的田野、树木、向日葵,描写小动物和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描写与妻子做爱、听着音乐旅行、给妻子写情书,描写盛夏夜晚孩子们的吵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种平静到《丰收结》一诗得到总结也走向终结。“丰收结”正象征着这个阶段希尼所追求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创作。诗中我和妻子仍过着散步、垂钓这类安宁的乡间生活,妻子用稻草编结的丰收结正是从私人化的乡村生活中诞生的个人化的艺术作品。但是在最后一段,希尼用诗中唯一的斜体写道:“艺术的结局是平静。”(31)这里的平静并不是说希尼从矛盾中找到了出路,从后面用来形容丰收结的“脆弱”、“陷阱”等词语来看,希尼通过前面那些虽平静却无力的诗歌认识到,离开了历史和社会的艺术是脆弱的,最终只能落入死亡的陷阱。因此在随后的两首诗中,希尼再次回到了一战中阵亡的爱尔兰战士以及《神曲》中意大利人乌哥利诺恨入骨髓的复仇。《牡蛎》中试图驱逐的历史重新回来,《牡蛎》中呼喊的“动词、纯粹的动词”并不能为希尼提供坚强的支撑。显然,就如希尼后来深刻地认识到的,在爱尔兰,“个体对肯定和特性的追求与群体定义自我的努力密切相连,至少相似。”(32)
不过,这一认识仍未能帮助希尼找到最终的答案,直到《苦路岛》,希尼仍然痛苦于“是忠实于群体的历史经历,还是忠实于这个正在形成的自我”(33)。《苦路岛》组诗突出体现了这一冲突。《苦路岛》是爱尔兰一个著名的天主教苦修圣地,诗中描写的朝圣之旅也是希尼自己的精神之旅。在这条精神的旅途上,希尼最先遇到的是传说中在基督徒的诅咒下只能生活在树上的疯斯威尼。希尼一直从他认为的爱尔兰性中的自然野性出发,选择斯威尼作为爱尔兰民族的祖先。斯威尼在诗中代表着爱尔兰民族对其民族身份的要求,因此希尼的个人精神之旅从一开始就是与民族身份之旅重合在一起的。
诗人遇到的第二个人是《德格湖朝圣》的作者威廉·卡莱顿。卡莱顿原先是天主教徒,后来改信了新教。不过卡莱顿在诗中告诉“我”,当下的宗派冲突不过是伤口中的蛆,来世的生活会洗净一切。但是,诗人在随后两章遇到的几位神父让他认识到了来世的虚幻和宗教的无能,同时也认识到现实无法逃避。接下来的3章相继出现了4个在北爱冲突中被杀害的天主教徒的亡魂,他们一次次的责备使“我悔恨/我那未断奶的生活,这种生活使我能/在默许和不信任中梦游”(Station:80)。但是,像他之前的创作一样,希尼的精神之旅并未在民族主义立场中结束,随着诗歌的发展,希尼最终走向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海伦·凡德勒认为乔伊斯“使这位诗人从民族主义焦虑和宗族顾虑中解放出来”(34),的确,只有乔伊斯这样敢于在“市民”们的喧嚣中大胆回击民族主义道德压力(35)的人,只有乔伊斯这样敢于抛开动乱中的爱尔兰又在更高的意义上将自己与爱尔兰永远结合在一起的人,才能帮助希尼解决民族身份中群体道德和个人追求之间的矛盾。
四、爱尔兰语与英语
在《苦路岛》中,乔伊斯首先将希尼从语言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19世纪赫尔德、施莱格尔等人提出用语言来定义民族,这种“语言民族主义”(36)至今依然是欧洲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模式。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将爱尔兰语定为第一官方语言,在国民教育中大力推行爱尔兰语,也是这种“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物。
然而,有的时候,选择何种方言甚至外来语言作为本民族的语言,与其说是语言自然演变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权谋的产物。盖尔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19世纪的“青年爱尔兰”开始,被选为爱尔兰的民族语言,而那时,虽然痛苦却不得不承认,经过14世纪的“基尔肯尼法案”、1831年的“国民教育体系”以及1845-1849年的大饥荒,英语已经成为爱尔兰岛上绝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生命力来自以文学为主的文化著作,而爱尔兰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作品大部分是用英语写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语爱尔兰文学错时的繁荣尤其将英语深深烙印到爱尔兰文化之中。至于爱尔兰语文学,除了以口头形式保留的凯尔特神话和传说外,很少有在力度和厚度上足以承载起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把英语排斥为殖民者的语言等于对爱尔兰自身文化传统的排斥,同样是对历史的误读。
乔伊斯在创作之初也对自己使用英语这种“永远是得来的语言”感到“烦躁不安”,(37)希尼早期的诗歌也描写过对英语的反感和对爱尔兰民族语言的呼唤。《传统》一诗描写了“我们”爱尔兰人如何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当做自己的语言,其他民族却因此把爱尔兰视为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死去了的野蛮民族。(38)《羊毛生意》的叙述者哀叹自己只能说着外来的语言,就像“只能谈论苏格兰花呢,/僵硬的布料上是血一样的斑点”(39)。《新歌》描绘了爱尔兰西部语言中包含的对爱尔兰古老历史的回忆,并宣言“我们的语言之河必须/从埋头舔舐本土栖息地中抬起身/变成汪洋洪水”(40)。
但是,随着开始质疑本质主义民族观,随着认识到“如果处处皆无处,谁能证明某处比另一处更重要”(Station:35),希尼也开始对爱尔兰的民族语言进行反思。他注意到乔伊斯不仅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质疑英语,更在结尾处对这个质疑本身进行了反思。在该书结尾处的日记中乔伊斯谈到,他发现英国教导主任轻蔑地称为爱尔兰语的“通盘”一词实际是古英语词,换句话说,其实词语的民族性随着历史的演进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不同民族的词语早已相互融合。因此像英国教导主任那样强调词语的民族性,与其说是对历史的梳理,不如说是一种制造他者的文化霸权行为。于是,乔伊斯最后说:“不管这样还是那样,都见鬼去吧!”(41)然后,希尼借乔伊斯之口说出了他对只把爱尔兰语当作爱尔兰民族语言的反对:“谁还/在乎呢?英语/属于我们。/……人们贩卖的这个话题是一场骗局,/幼稚无知,就像你那乡村朝圣。”(Station:93)乔伊斯还向希尼建议,当人们把英语的领地越扩越大的时候,重要的是“按照你自己的频率/在这个东西上写上调号”(Station:94)。应该承认,诗中乔伊斯说的那些话现实中的乔伊斯并未说过,“写上调号”是希尼自己提出的化外来语为民族语言的办法。希尼认为,没有必要把英语视为英国的专有财产,它同样可以属于爱尔兰。只要爱尔兰人充满自信地以自己的方式使用英语,在英语上打上自己的印记,那么就像美国人成功地用英语塑造了独特的美国文化,爱尔兰人同样可以使人们对英语的想象不可避免地与对爱尔兰文化的接受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如果说莎士比亚用他的英语诗句使英格兰永远成为一个民族,(42)那么叶芝、乔伊斯等则用打上了爱尔兰烙印的英语,把全世界的读者带进了爱尔兰文化。
李成坚认为希尼主张一种由爱尔兰语和英语杂合而成的语言,但事实上,希尼虽然在创作中有时也插入爱尔兰语,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的绝大多数内容使用的都是英语,他甚至从未尝试根据政治平等的原则让作品中的爱尔兰语达到一定比例。他说自己追求的是一种“不那么二元,总之不那么拼合的词汇”(43)。虽然现在大多数爱尔兰人说的是英语,但希尼认为,正如隔墙听话,虽然听不见具体的内容,却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情感和情绪,爱尔兰人的英语中也依然包含着爱尔兰人“内心的、私密的主旋律”(44),能够把爱尔兰的情感、语调、感觉等等与英语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英语爱尔兰化。
帕特里克·卡文纳的诗歌带有鲜明的爱尔兰地域色彩,但主要用英语创作,有的评论者甚至批评他过多使用了英国十四行诗的格律,希尼却称他的诗歌“比叶芝提倡的多数东西更直接和更亲密地触及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Preoccupations:137)。希尼分析了卡文纳的《因尼斯基恩的路,7月之夜》一诗,指出其中的“blooming”(沮丧/茂盛)和“go by”(经过)虽然是英语,但实际上已经在标准的英语含义和表达方式之外,发展起了一种“因尼斯基恩英语”(Preoccupations:138)。因此,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那些人为地使用爱尔兰语来“制造”地域感的作家不同,卡文纳完全自然地使用当地爱尔兰人所用的英语,传递出爱尔兰的真实现实。那些爱尔兰语文学的“爱尔兰色彩”因为脱离爱尔兰现实而显得虚假,卡文纳的地域英语却自然而然地在英语上写上了爱尔兰“调号”(Station:94),将其变为爱尔兰人的英语。用希尼接受采访时的话说,“我们应该忠实于的,是我们自己在爱尔兰自然形成的说英语的方式”。(45)
五、重新想象
1981年后希尼开始定期在哈佛大学执教,1989年又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大西洋两岸和爱尔兰海两岸不断往来,这使希尼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国际化。同时,1994年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1999年北爱历史上成立第一个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组成的地方政府,其间虽然仍有恐怖事件,但整个局势趋向和解。此时的北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像希尼自己一样,都面临着如何使自己的民族身份适应这个新的政治环境的问题。在文化融合这一大的趋势下,固守文化的本原和差异固然不再可能,闭锁于个体的快乐和痛苦同样不大现实,另一方面,完全放弃个人的特性而接受一个杂合的后现代身份,同样会在趋同中丧失个人的价值和力量。虽然瑞典文学院称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诗歌艺术,但实际上与他的北爱身份不无关系。希尼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获奖致词《归功于诗》(1995)谈的依然是如何在北爱冲突中确立自己的诗人身份。有趣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希尼让自己的艺术之旅最终“走在空中”,并称是诗歌“使这一太空行走成为可能”。(46)
从创作伊始希尼就坚持把地理空间作为诗歌想象的“苗床”(Preoccupations:19),地域感也是希尼诗歌的重要特征,现在他却要离开大地,走向空中。希尼这里的变化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并不是要离开他的文化土壤,而是要“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样,他早期诗歌中的个人关注和自觉体验就在更广阔、更包容的视野下被重新想象和改变”(47)。事实上,希尼在《归功于诗》中仍然强调对本土因素的爱和信任,他后期的诗歌也依然描写身边带有爱尔兰乡村色彩的事物,甚至依然描写北爱的冲突和死亡。但是,就如他后期的诗集标题《幻视》(1991)和也可以直译为“灵魂水平面”的《酒精水准仪》(1996)显示的,此时希尼对他的文化环境的审视越来越离开物质的和政治的层面,转向一种精神的和本体论的视角。他所看的仍然是爱尔兰的社会和生活,但他看的角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希尼在《归功于诗》中挑选的北爱暴力事件典型体现了他的目光焦点的变化。一队工人被蒙面武装分子拦下,其中只有一个天主教徒,其余都是新教徒。蒙面分子让天主教徒站出来,但最后站出来的天主教徒并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被杀死,被杀的反而是他的新教工友。希尼此时在叙述中强调的不是最后的屠杀,而是天主教徒站出来时他的新教工友悄悄拉住他的手。不同的焦点使希尼对北爱冲突有了不同的理解,他开始看到,民族对立有时只是一些人的政治选择,是他们把社会划分为对立的群体,个体之间则存在着“生灵之间的同情和保护”(48)。希尼深悉后殖民时代少数群体的立场,(49)却大谈超民族的人道主义,在颁奖典礼上向全世界讲述着这个故事,这无疑受到他此时的世界公民身份的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希尼经历了数十年痛苦而复杂的社会动荡、身份追寻和艺术探索之后,对民族和身份的新的理解。
希尼后期经历了母亲和父亲的过世,父亲的去世尤其让他重新思考人的存在。他纪念父亲的组诗《四边形》显示,是父亲的死亡使他转而关注生存的精神层面。1984年母亲的去世只让他感到此世中出现了空洞,(50)3年后父亲的离去却被他描写为“从远处孤独地[向此世]遥望”(51),并把一则关于彼岸世界的中世纪传说作为《四边形》的开始。对精神层面的关注使希尼重新思考人的身份问题,并越来越强调身份作为主观构造物具有的想象性和可变性。之后的《酒精水准仪》通篇描写的也是从“灵魂水平面”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其中希尼描写了很多对立的事物,包括北爱冲突中截然相反的非暴力忍耐和暴力反抗。不过,正如理查德·梯林哈斯特所说的,这里希尼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应对民族冲突,而是“通过立足于我们认为的对立事物之间的平衡点,我们有可能认识到有时我们的眼光(vision)彻底欺骗了我们”(52)。
正是这个新的视角使希尼在《四边形》中称“一切都流动。甚至一个坚实的人”(53)。他也从同样的角度描写了爱尔兰传统文化。在《高背长椅》中,他描写了爱尔兰特有的一种可当床用的高背长椅,也描写了他躺在上面时爱尔兰的新教和天主教传统如潮水般从头上流过。但是希尼接下来写道:
……所有被给予的
总能被重新想象。
你就像那个守望者一样自由,
那个远眺的爱开玩笑的人高据于浓雾之上,
此时宣布他要下来了
真正的船已经被从他的脚下偷走。(54)
认识到文化已经无根,认识到身份和传统充满了时代的想象,并随时都可以被重新想象,希尼感到的反而是一种自由后的快乐。
在《酒精水准仪》中希尼再次提到了1979年一个天主教徒对他的指责:“他妈的,你什么时候/为我们写点儿东西?”(55)这样的指责在1984年的《苦路岛》中曾让希尼充满痛苦,祈求宽恕,但1996年的希尼则毫不迟疑地回答:“如果我写东西,/不管是什么,我将只为自己写。”(56)这里的“只为自己”与1972年《格兰莫尔十四行诗》中的逃避到乡村世界并不一样,希尼这里显示的是自由地将个人的、群体的、历史的等等各种题材放在同一水平面上的自信;而且,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他都将只用自己的灵魂来裁断。有趣的是,在这首诗的前面部分,希尼描写了他的父亲,也描写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飞来飞去,这些航行被他称为“起飞和离开。摆脱责任后的轰鸣”(57)。显然,他那“只为自己”的自信与父亲之死带来的精神顿悟以及他作为世界公民的新生活环境是密切相连的。
到这里,希尼终于完成了乔伊斯告诫他的“让别人去悲切忏悔。/放开手,飞起来,忘掉它”(Station:93)。他甚至借爱尔兰诗人麦克尼斯之口说,“我认为人或许有种族的血中音乐这类东西,但这,就像人的无意识一样,或许可以由它去自己照料自己。”(58)希尼的这种自我主义看法或许会让那些担心爱尔兰人取得群体认同的英国霸权力量暗喜,但至少就希尼个人来说,他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自信,这种内心的力量在乔伊斯看来正是爱尔兰民族所需要的。
在2006年的《域与环》中,希尼描写了一个退伍的“爱尔兰佬乔伊斯”,他把战争留在身后,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天堂。(59)当然,对于已经登上世界文坛顶峰的希尼来说,这完全是可能的,但对生活在北爱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来说,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冲突也许并未结束。不过,个人和民族,就像耶尔·塔米尔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中所说的那样,未必就不能找到一个完满的结合点,毕竟没有抽象的民族,只有“我的”民族。(60)
注释:
①William Shakespeare,The life of King Henry the Fifth,ed.W.J.Craig,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4,3.2.36.
②Seamus Heaney,The Redress of Poetry,London & Boston:Faber and Faber,1995,p.6.
③See David Llyod,"'Pap for the Dispossessed':Seamus Heaney and the Poetics of Identity",in Boundary 2,Vol.13,No.2/3(1985),p.320.
④如李成坚、邓红《杂合中建立第三空间——从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看谢默斯·希尼的<贝奥武甫>译本》,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7-31页。
⑤详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⑥See Seamus Heaney,Preoccupations:Selected Prose 1968-1978,London & Boston:Faber and Faber,1980,p.173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作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⑦Terry Eagleton,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Cork:Cork University Press,1998,p.315.
⑧Seamus Heaney,Station Island,London and Boston:Faber and Faber,1984,p.80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⑨Michael R.Molino,Questioning Tradition,Language and Myth: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Washington: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4,p.59.
⑩Michael R.Molino,Questioning Tradition,Language and Myth: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p.63.
(11)See Seamus Heaney,North,London and Boston:Faber and Faber,1975,p.27.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12)Seamus Deane,"Interview with Seamus Heaney",in Mark Patrick Hederman and Richard Kearney eds.,The Crane Bag Book of Irish Studies(1977-1981),Dublin:Blackwater,1982,p.62.
(13)Helen Vendler,Seamus Heane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
(14)希尼在1984年反思自己的选择时,就把这一矛盾视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首要矛盾。See Seamus Heaney,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London & Boston:Faber and Faber,1988,p.xi.
(15)希尼《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7页。其中“血源”疑为“血缘”。
(16)Terry Eagleton,"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in Stephen Regan ed.,The Eagleton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p.384.
(17)Terry Eagleton,"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p.387.
(18)Thomas Foster,Seamus Heaney,Boston:Twayne,1989,p.57.
(19)Seamus Heaney,Door into the Dark,London and Boston:Faber and Faber,1972,p.42.
(20)See Josep M.Armengol,"Gendering the Irish Land:Seamus Heaney's 'Act of Union'(1975)",in Atlantis Vol.23,No.1(2001),pp.7-26.
(21)See Patricia Coughlan,"Bog Queens':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Poetry of John Montague and Seamus Heaney',in David Cairns and Toni O'Brien Johnson eds.,Gender in Irish Writing,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1,pp.88-111.
(22)"The Peerage.com:A Genealogical Survey of the Qeerage of Britain as well as the Royal Families of Europe",http://thepeerage.com/p36550.htm#i365496希尼撰写《贝尔法斯特》一文时,莫尤拉勋爵即杰姆斯·奇切斯特·克拉克(James Chichester-Clark),吴德安在《希尼诗文集》中误译为两个人。
(23)Terry Eagleton,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p.313.
(24)See Blake Morrison,Seamus Heaney,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2,p.72.
(25)Blake Morrison,Seamus Heaney,p.75.
(26)Seamus Heaney,Field Work,New York:Faber and Faber,1979,p.23.
(27)Seamus Heaney,Field Work,p.24.
(28)George Cusack,"A Cold Eye Cast Inward:Seamus Heaney's Field Work",in New Hibernia Review,6:3(2002),p.53.
(29)Helen Vendler,Seamus Heaney,p.59.
(30)Floyd Collins,Seamus Heaney:The Crisis of Identity,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3,p.109.
(31)Seamus Heaney,Field Work,p.58.
(32)Seamus Heaney,The Redress of Poetry,p.6.
(33)Seamus Heaney,"Envies and Identifications:Dante and the Modern Poet",in Irish University Review 15,No.1.(1985),p.19.
(34)Helen Vendler,Seamus Heaney,p.97
(35)详见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2章。
(36)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37)See James 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London:Triad/Panther Books,1977,p.172.
(38)See Seamus Heaney,Wintering Out,London and Boston:Faber and Faber,1972,pp.31-32.
(39)Seamus Heaney,Wintering Out,p.37.
(40)Seamus Heaney,Wintering Out,p.33.
(41)James 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p.227.
(42)详见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何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43)Seamus Heaney,Crediting Poetry,Oldcastle:Gallery Press,1995,p.23.
(44)Frank Kinahan,"Artists on Art:An Interview with Seamus Heaney",in Critical Inquiry,8(3)(1982),p.414.
(45)Frank Kinahan,"Artists on Art:An Interview with Seamus Heaney",p.406.
(46)Seamus Heaney,Crediting Poetry,p.9此处的“走在空中”是个双关,也有“洋洋自得”的含义。
(47)Irene Gilsenan Nordin,"Seamus Heaney:From the Personal to the Universal",in Studia Neophilologica 72:2(2000),p.174.
(48)Seamus Heaney,Crediting Poetry,p.47.
(49)See Seamus Heaney,Crediting Poetry,pp.33-34.
(50)See Seamus Heaney,The Haw Lantern,London and Boston:Faber and Faber,1987,p.31
(51)Seamus Heaney,Seeing Things,London and Boston:Faber and Faber,1991,p.55.
(52)Richard Tillinghast,"Poems into Plowshares:The Spirit Level by Seamus Heaney",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1 July(1996),p.6.
(53)Seamus Heaney,Seeing Things,p.85.
(54)Seamus Heaney,Seeing Things,p.29.
(55)Seamus Heaney,The Spirit Level,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1996,p.29.
(56)Seamus Heaney,The Spirit Level,p.29.
(57)Seamus Heaney,The Spirit Level,p.27.
(58)Seamus Heaney,The Place of Writing,Atlanta:Scholars Press,1989,p.42.
(59)See Seamus Heaney,District and Circl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6,pp.8-10.
(60)详见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标签:诗歌论文; 希尼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乔伊斯论文; 北方论文; 英语论文; 爱尔兰人论文; 爱尔兰语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