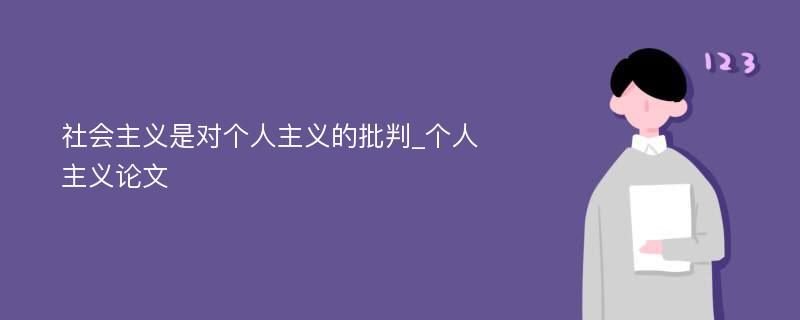
作为对个人主义批判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人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一词,在今天已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纷出的歧义,有时反而掩盖了它的本来意义。本文拟从考察“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入手,指出它作为“个人主义”批判的起源,并讨论这一起源的现代启示。
一
关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最早使用的问题,各有各的说法,概括起来,大致有这么几种:
第一,认为这个词的最早使用是在1753年,德国一个叫安塞尔姆·德辛的本尼迪克派(又译为本笃派)教士把承认具有社会性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socialiftate)。这是关于这一词使用的最早推断。
第二,认为这个词是意大利传教士贾科莫·朱利阿尼在1803年最早使用的。在他写的《驳斥社会主义》一书中,既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又使用了“社会主义者”一词。虽然,他以此来表达与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者相对立的概念,抨击18世纪盛行的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但是,在他那里,社会主义是指上帝安排的传统制度。
第三,认为“社会主义”这一词的最早使用是在英国,出现在1826年或1827年11月欧文主义者的《合作杂志》上,该杂志用“社会主义者”来指称信仰欧文合作学说的人。
第四,认为“社会主义”这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在1832年2月13日发行的圣西门派的机关报《环球》上,该学派的门徒戎西埃雷在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socialisme)这个词,他说:“我们不愿意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也不愿意为个人而牺牲社会主义。”
前两者与后来广泛流行的“社会主义”的含义显然不同。作为近代乃至现代意义上广泛使用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最初使用,明显地出现在英法两国后来被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并与他们的思想直接有关。《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说,“社会主义”一词的首先使用,“指的是法国傅立叶和圣西门,以及英国的欧文发挥的理论。”(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4卷,第45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家柯尔也说:“原先象这样冠以‘社会主义者’称号的流派主要有三个……: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以及在1841年正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的欧文主义者。”(注: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第9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英国人和法国人曾一度竞相争夺“社会主义”一词的发明权,事实上,关于最早创立这个词的时间和人物的各种考证,总是遭到怀疑,而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二词也不宜混淆。一般说来,“社会主义”一词最早由法国使用,而“社会主义者”一词则最早由英国使用。无论如何,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者”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都已广为流传、应用。这一点至关重要,英、法两国分别是当时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上发展最典型的国家,其社会问题的暴露也最为明显和严重,比如,阶级对立的日益加深、工人失业、小生产者的纷纷破产、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社会主义思潮由此诞生。可见,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和谐、不尽人意的现实而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对抗性思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英、法两国谁最先使用这个词并不重要。
社会主义,其针对的焦点是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者”一词并非从“社会主义”一词演变而来。“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由“社会的”一词派生而来的。“社会的”一词导源于拉丁文"socialis",其字根为"socius"(复数为socii),意为“伴侣”、“同志”、“社会中的人”。"socialis"意指“同伴的”、“同伙的”、“善于社交的”等,这个词到近代已演变成英文和法文的social,意为“社会的”。“社会的”与“个人的”相对立。因此在起源上,“无论从逻辑方面还是从社会学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的含义都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和个人主义的对照”。丹尼尔·贝尔写道,“到1840年时,‘社会主义’这个词在整个欧洲通常被用来表示这样一种学说:生产资料——资本、土地或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应该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掌握,并根据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来进行管理。”(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外国百科条目选择)》第165-166页,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柯尔认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实质上走的都是社会化道路”,“他们都把‘社会问题’看成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经济制度”,“坚决反对自然经济规律论”,“反对放任主义”,社会主义的最初使用“指的是以合作为基础、以大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的人类事务的集体管理制”。(注: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第9-10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935年,圣西门派学者皮·勒鲁写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是最早的一篇从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来阐述社会主义概念的文章,刊登在当时他和雷诺合编的《新百科全书》上。此后,“社会主义”一词作为“个人主义”的对立词得到了普及。
二
“个人主义”一词,原为法文"individualisme"。法国天主教复辟主义思想家德·梅斯特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在1820年,他说:“精神的这种深刻和惊人的分裂,所有学说的这种无穷破碎,政治新教变成了最极端的个人主义。”(注:转引自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词的英文形式"individualism"是1840年黎佛(H.Reeve)从法国政治评论家托克维尔1835年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翻译过来的。托克维尔用“个人主义”这个词来表示一种温和的利己主义,它使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的小圈子。
现在看来,至少从东方文化的背景下看来,“个人主义”一词明显地带有贬义的色彩。事实上,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个人主义最初是以一种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形式出现的。
至少到17世纪末以前,欧洲社会还是封建等级制,在这种以权力原则为基础、君权神授的制度下,神对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处于封建等级制的束缚之下,人没有自由,只是被视作团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庭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由。”(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4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从14世纪开始到16世纪达到高潮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而出现的一种反叛。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本主义作为旗帜和指导思想,竭力弘扬人的价值、地位和尊严。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的实质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者提出了“个人自由”、“个人幸福”,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目的”的口号,与欧洲中古时期限制个人自由,把个人纳入社会等级秩序的束缚之下截然不同。因此,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和观念被认为是判断近代史的一个重要标志。认为社会生活的目的就是满足个体的人的各种需要,这一思想成为近代乃至现代西方思想史发展的一条主要线索。
文艺复兴运动公开弘扬的这种个人主义的精神和观念首先在17世纪得到继承。被认为“政治理论的第一个真正近代的著作家”(罗素语)的霍布斯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所驱使,社会无非是帮助人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国家不过是私人安全的奴仆,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威只有在它们对单个的人的安全有所贡献时才是正确的。萨拜因指出,霍布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而“正是这种直截了当的个人主义使得霍布斯的哲学成为那个时代最富于革命性的理论”。(注: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526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作为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奠基人的洛克在讨论个人与国家、政府、社会的关系时,同样主张个人意志至上的个人主义。他以个人为本位来规范社会生活,视个人自由为一切公共权威、法律准则和道德评价的出发点。他提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的目的在于延续及保护人民的权利;人民不仅有道德和法律的权利,而且有道德和法律的义务去发动革命、推翻政府,因为在他看来,离开了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政治权力就失去了产生的意义。“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注:洛克:《政府论》下篇第7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注:洛克:《政府论》下篇第3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他的学说,如自然权利论、有限政府论、反抗暴君的权力论等,无不表达了这样的观念:政府与社会的存在都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构成了政府与社会权威的限度。洛克的思想,不仅成为后来法国大革命理论的一个主要基础,而且也成为美国革命理论的来源,无论是美国《独立宣言》还是宪法,都深受其影响。萨拜因指出:“洛克学说中为捍卫个人自由、个人同意以及自由获得并享有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抗争的思想在这两次革命中收到了充分的效益。”(注: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604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佛逊正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洛克等人思想的继承者。《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政府。”在杰佛逊看来,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才订立契约成立政府,政府的成立并不等于人们对于自己权利的放弃,而是让权利由于得到政府的保护而更加安全。因此,政府不过是人们用来实现他们的意志的一种方式而已。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控制最少的政府。他提出把人民自治作为代议民主制的基础以防止暴政的出现。而人民自治则要以个人为基础,国家应建立在“每一个贡献财力或人力以支持国家的成年人的民治”(注:《杰斐逊文选》第36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基础上。个人自治即个人凭借其单独意志自我决定、自我管理,其首要原则是个人的自由。自由就是在确定的界限内,按照权利平等的原则,依靠我的意志不受阻碍地行动。马克思称美国的《独立宣言》为“第一人权宣言”。它在后来成了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权宣言》的范本。
1789年,法国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的宣言》,简称《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原则。宣言指出,“对人权的无知、遗忘和忽视是造成公众灾难和政治腐败的唯一原因”(前言):“人生来即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第一条);“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二条):“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第十七条)。私有财产和自由的不可侵犯性是人权原则的核心内容。而自由这项人权,如马克思所指出,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权利”。“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而安全则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43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18世纪启蒙运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大革命和新兴的工业制度,曾经联合起来形成了圣西门的一个门徒在1826年称之为个人主义的学说。在这种学说中,社会是为了个人和追求个人自身的满足而存在的;天赋的权利是每一个人所固有的;政府不应调节社会的经济生活。”(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外国百科条目选择)》第166页,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个人主义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封建国家和教会的否定和批判,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
三
作为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个人主义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的思想和行动,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为资本主义文化及其工业文明奠定了主要精神内涵。因而,个人主义在历史上的合理性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同样无疑的是,就在个人主义思想兴起和发展的同时,对它进行批评和否定的思想也形成和发展起来。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个人主义的崛起,一方面使人成为精神的个体,这个个体在人格自由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发展也使得正常的秩序丧失了其应有的规范性。而黑格尔则告诫道,个人主义的发展将使得除个人以外的其他一切都变得虚无。概括地讲,对个人主义批评和否定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保守主义思想。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理论的保守主义思想,其形成直接与法国大革命相关。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不等同于个人的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某种文化的总体表现;人不能创造社会,社会是神意的创造和历史演化的产物。因此,使一个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的社会保持其延续性、稳定性和整体性是极其重要的。他们指责法国大革命破坏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个人主义的盛行。他们认为,革命后的社会是一个唯我主义的、每个人争相追逐自身利益而不顾他人的社会。被公认为是现代保守主义奠基人的伯克就指出,国家是社会发展稳定性的最高体现,“个人像浮光掠影,过往匆匆;而国家却是不变的和稳定的”。他崇尚国家,要求人们带着敬畏的心情去看待国家,他认为,法国革命由于高扬个人,把国家变成了“分解为若干基本原则之非社会的、不文明的、不相连属的混沌状态”,(注:柏克:《法国革命论》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898年版。)而对国家的稳定造成了危害。法国天主教思想家德·梅斯特最初使用“个人主义”一词也正是从对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角度而非正面意义上阐发的。在他看来,人类只是为了社会而存在,个人主义则会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他斥责当时的政治新教已变成了“最极端的个人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思想。就整个西欧而言,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一方面,工业社会初露曙光;另一方面,由之而来的社会矛盾、不协调现象也端倪初现:大量农民丧失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化、工厂中残酷的劳动纪律、剥削和被剥削、两极分化和对立,等等。正是源自于对这些现象的不满,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早期乌托邦思想家。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家们最早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他们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羊吃人”的社会(莫尔)、“人间地狱”(闵采尔)、“培养罪恶的学校”(康帕内拉)。他们试图通过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及私有制决裂的途径来寻找解决方案。虽然在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家们那里还没有出现“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这两个词汇的出现都是19世纪的事,但是,他们已经把私有制、利己主义等代表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主要观念和制度的批判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麦克弗森就把从霍布斯到洛克形成的个人主义称为“占有性个人主义”,意即对私有财产权利的辩护是个人主义的主题。因此,早期乌托邦思想家对私有制的批判,表明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而出现的。
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是19世纪初欧洲的三大社会主义思想家。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概念,最初就是用来形容这三大思想家及其门徒的思想和理论的。
圣西门直接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恩格斯称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圣西门所在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社会矛盾暴露得最为明显的时代,圣西门称之为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他认为,利己主义是造成社会种种罪恶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人类生来就是过社会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现有的政治学说和政策,使得一切思想的认同、集体的行动及协作都消失了,社会变成了一个彼此竞争的孤立个体的单纯的聚合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法国的革命“给我们帮了倒忙”(注:《圣西门选集》第1卷,第18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被人们认为可以解决社会自由问题的人权宣言,实际上只是公布了宣言而已。”(注:《圣西门选集》第1卷,第189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他宣布要用新的原则来重建社会,这一新的原则就是他的“工业社会”理论。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的竞争体制和无政府状态不同,圣西门设想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作者与伙伴的关系,“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这样的关系“应当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注:《圣西门选集》第1卷,第29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在生产方式上,联合体实行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一切工作都必须按协作的共同目的来行动,人们将联合起来去影响自然界。合作是工业的基础,而政府的重要功能就是协助人民组织合作社,提高人民福利。圣西门因而又把未来社会的制度称作为“协作制”,这很好地表达了他的针对性。
圣西门还认为,一个社会的团体纯粹靠经济力量的运行是不够的,又由于现代社会中个体利益高于整体利益的观念占主导地位,出现了道德、价值的社会真空。所以,未来社会需要有价值中心,即反对利己主义哲学的“新基督教”。圣西门去世后,他的门徒对他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在他们编辑的《圣西门学说释义》一书中,他们提出,对抗与协作是人类相互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对抗的减弱与协作的增强,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因而,协作制在二者消长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将促使社会从基层的协作社即家族,经过民族、城市、国家而发展为全世界的协作社会。
卢克斯认为,“个人主义”一词正是圣西门的门徒首先系统使用的。他们用“个人主义”来指称一种有害的和“消极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现代“批判”时代的罪恶。他们认为,现代“批判”时代的“混乱、无神论、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与“有序、宗教、联合和献身”的未来“有机”时代的图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卢克斯认为,由于圣西门主义的影响,在法国思想中,“个人主义”一词至今仍带有贬义,意味着强调个人就会有害社会的更高利益,意味着社会解体的原因。
圣西门之后的傅立叶对法国大革命也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法国1789年后制定的所有宪法“都是同样荒谬可笑的”(注:《傅立叶选集》第3卷,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他视法国大革命为一场由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造成因而也应由他们负责的社会大灾难。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及其现象作了尤为生动的揭示和淋漓尽致的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就是分散的、无政府状态的、到处是无限制的自由竟争、全然没有计划的社会,其生产不管是分散形式的还是集中形式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私利而进行生产。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只关心私利,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是对立的,每个人和别人、和社会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文明制度结构是个人反对大众的普遍战争。”(注:傅立叶选集》第3卷,第22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与个人利益至上导致的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傅立叶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不是以普遍的竞争而必须是以普遍的协作为基础的,他把它叫作和谐制度。在这个社会中,协作社是基层组织,整个社会是由无数个协作社组成的有机联合体,在联合体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都协调无间。
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直指这一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他指出,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三位一体的祸害。私有制使私有者变成了“无知的利己主义者”,使人们看不到个人幸福和他人幸福以及整个社会幸福的有机联系。欧文认为,组织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联盟的原则,而决不是“令人生厌的个人主义”。(注:转引自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他设想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社,即一种联合劳动和联合消费的组织。
在工人运动史上,欧文以开创合作社的实践而闻名。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制相区别,欧文试图通过当时的工会组织,由劳动者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按合作社原则来改组生产、组织生产。虽然,欧文的合作社运动以及几次组织公社的实验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些运动和实验,无不表达了他的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合作制的社会思想。日本学者伊藤诚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社会主义一词,“在当时欧文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运动中,表现了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倾向,主要以合作主义,一种改良主义为核心”。(注:伊滕诚:《现代社会主义问题》第1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版。)
四
从上可见,如同个人主义思想的出现,社会主义,无论从其思想起源还是从概念的最初使用上讲,都是批判地考察现实社会制度的结果。从个人主义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到社会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在认识、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演进过程。
从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而言,社会主义是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判然有别的。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它主张个人权利、个人利益必须有所限制、有所制约,反对个人至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连续性,就在于它同属于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锋芒所指即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名词,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标志,又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诸多设想,其中主要是人的个性全面发展,消灭城乡对立,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消灭阶级对立。这种关于社会的有机体概念,以及对自由人的“共同体”、“联合体”的追求,都表明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连续性。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6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因此,个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关系先于个人存在,并不仅仅是指社会关系构成个人存在的社会环境,而更是指社会关系构成了个人的特质。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这就好比有人这样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1-22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通过对个人的社会性的揭示,马克思才把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即个人重新驾驭由于私有制和异化而转化为物的力量的社会关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在今天,如果有的论者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攻势,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甚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注:这种在20世纪流行开来的做法,其始作俑者可追溯到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伯恩斯坦从区分“市民”与“资产者”(德文均写作Bürger)、“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德文均写作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中,得出了自由主义的社会理想,宣称社会主义运动是自由主义的传人——详见郁建兴、朱旭红:《社会主义价值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那么,也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个人主义批判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统统抹去了。在这方面,阿尔都塞说得好:“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被还原为任何人类学的内在主观性。”(注: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第86页,伦敦1970年版。)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被还原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的。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概念、“自由人的联合体”理想,应是我们今天批判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有力武器。
值得指出的是,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个人主义批判的意义,并不必然意味着排斥个人。有的论者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显、并于20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归咎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甚至在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划上等号。这种做法同样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毋庸置疑,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认为社会主义有国家主义的倾向,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有着诸多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但是,需要汲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恰恰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区分开来。勒鲁在他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曾经提出过防止极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警告,他说的要防止的极端之一就是过分夸大共同的原则,束缚人的自由;之二是过分夸大私人原则,发展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而马克思在批判个人自由主义的同时又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先于个人”,表达的是一个概念的范畴,并非具有时间的先后关系,它决非意味着存在一个外在于个人的“社会”实体。他说,在自由人的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说,一方面,社会关系先于个人,没有共同体,个人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真正的”)共同体意味着“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国家并不就是这种(“真正的”)共同体,恰恰相反,国家是一种“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在其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是“新的桎梏”。因此,对马克思而言,阶级消灭、国家消亡,是人的自由、解放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由此,从社会主义之作为对个人主义批判的起源,特别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形态——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决不能得出国家主义的结论。超越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从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具体概念出发,努力创设出新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为阶级消灭、国家消亡创造条件,最终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是我们的结论,也是我们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