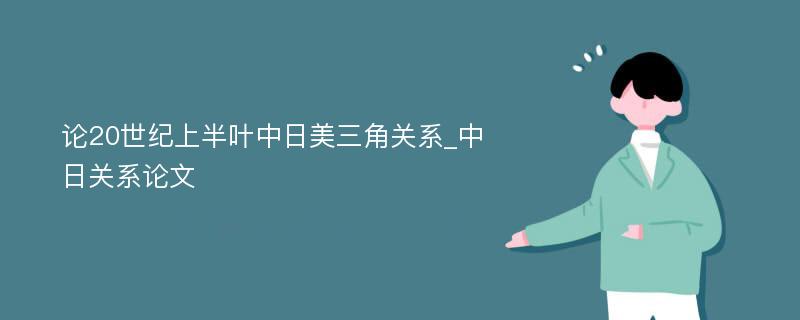
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美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前半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0)06—0015—06—0042—11
本文拟就20世纪初年至1945年间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史的若干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问题的缘起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在亚太地区,此前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已为中美日三角关系所取代。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研究,遂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现实性研究的著作可参考《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1],而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历史研究, 也引起史学界特别是中美关系史学者的重视(注:陶文钊在《中美关系史研究十年回顾》一文中提出:研究20世纪中美关系应更多了解中美日三角关系。[2 ](P306)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一书中简单勾画了二战前和二战中的美、日、中三角关系史。[3](P30—33)),还有些学者虽不使用中美日三角关系或不同意使用这个概念,,但也对20世纪的三国关系史进行了一些考察与回顾。[4][5]中国史学界的这种状况,既反映了学者们在近代中外关系史或国际关系史领域中的新追求,又与世界特别是美日两国的学术影响分不开。70年代以来,以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在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丹涅特(Tyler Dennett)、格里斯沃尔德(Alfred Whitney Griswold)为首构筑的美国与东亚史学体系提出批评的同时,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主导,对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进行了重新研究,并创建了新的学科体系。[6](P2—3)[7]其中,作为费正清弟子的入江昭(Akira Iriye),对于美中日三国关系史的研究最有成就, 并成为美国“综合几种国际关系史方法进行总体研究的先驱”。[8]日本政界早在70 年代初就提出建立日美中三角关系的问题(注:田中角荣在1972年7 月就任首相前称:“如果日美中三国成为等腰三角形,就能维护远东安全。”)[9](P76),进入90年代以来,又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10]因此,如何适应外交斗争的现实需要,并借鉴美日两国的学术研究,在中日、中美、日美双边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学术体系,应当成为我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以来,至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的30年间,由于日本与美国开战和战后依附美国,亚太地区已不存在中日美三角关系。如同对于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是否存在美中日三角关系的问题的争论[5][11](P204 )一样,1945年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中,亚太地区是否存在过中日美三角关系以及这个三角关系的发展过程及其体现的历史特点,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但由于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有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它作为一个知识门类是不成熟的[12](P2),又由于任何国家的学者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上也不可能摆脱本国国情的影响(注:例如:〔美〕泰勒·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研究19世纪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国的关系史,就表明他的“观点是站在华盛顿方面,而不是站在东京或北京方面的”(作者原序)。[13]),笔者仅从中国学人的角度,就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史发表一些个人见解。
二、20世纪初期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形成
判断中日美三国之间是否构成三角关系,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三国构成亚太地区的三极,并形成双边关系;二是三国双边关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三是三国关系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且影响到三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据此标准,可以认定:在近现代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关系格局中,中日美三角关系形成于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二十余年间。(注:前引时殷弘文,也对于“三角关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并由此认定从日俄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期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美日“三角关系”。[5])20 世纪初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既具备了形成的主客观因素,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运作,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中日美三角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
1.亚太地区外太平洋力量的衰落与开始退出 19世纪中叶以来,作为外太平洋力量的西方列强(注:此说参考何芳川著:《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开始以武力侵入亚太地区。它们在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旧国际秩序——“华夷秩序”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以英国为主导的列强独霸或共管的新秩序。这期间,横亘欧亚大陆的俄国,与领骚全球的海洋帝国——英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亚太地区西方列强的主要矛盾。伙同英国的法国与后起的德国,也分别加入其中,形成亚太地区外太平洋力量的“四强”。而作为内太平洋力量的美国,主要是与英法“分取杯羹”,并将对华利益“一体均沾”。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被粉碎,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明治维新之后又“脱亚入欧”,逐渐加入西方列强。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不但眼看着“华夷秩序”中的诸国被各个肢解而无能为力,其自身也被纳入西方列强的共管秩序之中,并不断遭受侵略、欺凌,最终被瓜分。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是19世纪列强共管秩序的最后一幕。而在19世纪末,日本尽管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但也被迫接受“三国干涉还辽”,其自身也被束缚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之下。美国虽然打败了西班牙并侵占了菲律宾,但与亚太地区的英、俄、法、德四强相比,仍居弱势。正在崛起的日美,尚不足以改变外太平洋力量主导亚太地区的局面,而中国也需周旋于英俄两大国之间。因此,直到19世纪末,亚太地区仍然不可能形成中日美三角关系。
但是,20世纪初期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改变了外太平洋力量主导亚太地区的局面。日本在英美的支持下,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沙皇俄国,从此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而已经成为太平洋国家的沙俄战败后,被迫以多次密约的形式,在亚太地区逐步向日本退让,并逐渐演化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日俄战争之后,由于英德矛盾上升为外太平洋力量之间的主要矛盾,亚太地区通过日本与英法俄美等国的协定,重新构筑了以英日同盟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但使德国彻底退出了亚太舞台,也使英法等国遭受了很大的削弱。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苏俄也逐步退出亚太地区。因此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外太平洋力量的衰落和开始退出亚太地区,客观上就为作为内太平洋力量的中日美三国形成亚太地区的新关系,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2.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崛起与争霸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和作为内太平洋力量的争霸,与上述外太平洋力量的衰落相伴而生。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加速了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步伐。《马关条约》则将这个惟一带着黄色面孔的帝国主义霸主,推向西方列强。而十年之后的日俄战争,又表明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正式加入亚太争霸的行列,成为英、法、德、俄、美之后的“六强”之一。1890年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注: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14](P145 )但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认为“1890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首位”。[15](P4)),迅速加入亚太争霸的行列。通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巴黎和约,美国占领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同时和稍后,又吞并了夏威夷,并与德国瓜分了萨摩亚群岛。这时,美国鉴于中国已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完毕,乃“采取一个新的途径,即用另一种方式去达到它的目标”,并由国务卿约翰·海于1899年9月6日和1900年7月2日,向列强发出了两个“门户开放”的照会。[16](P78、449—452)这项政策的发表表明, 美国已由长期以来跟在英国的炮舰后面“分取杯羹”的传统政策,转变为积极扩张在华权益的独立政策。[17](P228)从此,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争霸的主角之一。
20世纪初年,日本、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兴起,对于外太平洋力量主导的亚太地区旧国际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而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争霸斗争,也导致了建立以内太平洋力量为主导的亚太地区新国际秩序时期的到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天赐良机”,迅速参战,并初步实施了其亚太政策,其中以“二十一条”暴露了其独霸中国的企图。美国迟至1917年参战,1918年1月, 威尔逊总统公布了《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这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宣言书。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外太平洋力量在亚太地区趋于衰落并开始退出之日,就是日美登上争霸亚太舞台之时。
作为内太平洋力量主要强国的日美两国,在20世纪初期争霸亚太的矛盾的形成与展开,是中日美三角关系形成的一个重要主观因素。
3.半殖民地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变化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在20世纪初年,已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已从“瓜分主义”发展到“保全主义”,即使中国在媚外主义的满清政府统治之下维持着形式上的独立。[18](P108)此后,列强在“维持东亚之现状”主义下,建立了共管中国的东亚秩序:“各国在东亚之地位势力,其既确定者,曰谋保存,其未确定者,使之巩固。……利用中国之黑暗,以遂其蚕食鲸吞之野心。”[19](P14—15)
《辛丑条约》之后,已沦为“洋人朝廷”的满清政府,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高唱“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在20世纪初期进行了惟一的一次主动、自觉的“新政改革”。在对外关系方面,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外交措施,显示了作为半殖民地(而非殖民地)的中国政府,并非就是“彻底投降”帝国主义。[20]“庚子联军之祸以前,中国实无所谓外交”;在辛丑以后,“中国问题乃成为世界关系”,并“成为世界外交之烧点”,在“中国完全入于列强操纵时代”,现代外交亦由此开始建立。[21]这是清末十年半殖民地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新变化。
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沙俄的战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列强共管中国的秩序。俄国1905革命又揭开了帝国主义时代革命风暴的序幕,并引起了“亚洲的觉醒”。中国辛亥革命作为亚洲觉醒的发展顶点,推翻了满清王朝和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在华构筑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对外关系又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在北洋军阀统治初期,中国的国际环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爆发,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战期间,德奥两国战败衰落,俄国由于发生十月革命,退出帝国主义行列,英法等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只有日本与美国继续上升为强国,并展开了激烈争霸。这种环境,不能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同时,中国的参战,尽管收效甚微并为日本利用,但这也是作为半殖民地的大国向西方列强的第一次开战,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新兴的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也为最终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准备了基础。此外,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崛起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外交家,如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他们一直主持北京民国政府的外交事务,有的亦曾出任国务总理或摄行总统职权,对于中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发生了积极的作用。[22]
巴黎和会是中国半殖民地地位和对外关系发生新变化的重要标志。中国作为战胜国与会,得与主宰世界的列强共同商讨战后国际问题,这本身就是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改变。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和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这是中国“百余年外交大失败后,忽然大放光明,于各帝国主义层层压迫之下,竞突破其樊笼,展开外交之新局面,而造成吾国外交史上之新纪元”。[21]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之后,很快宣布与德国结束战争状态,并于1921年5月20日, 与德国签订了《中德协约》。[23](P370-372)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在此期间,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分别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以前沙俄政府历次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一切条约,两国建立平等、友好关系。[24](P14-20)苏俄对华宣言的精神,使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仅就第一次宣言,中国各团体各报纸均认为这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25]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对外关系发生的新变化,是20世纪初期形成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又一个重要主观因素。(注: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20年代以前)的中国外交特质,前引王正廷的见解比较乐观。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时期的中国外交,尚处于由“被强迫的外交”到“被动的外交”的转换时期,而达到“主动的外交”时期,尚有相当距离。[26])
总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外太平洋力量的衰落,中日美分别作为弱而大、小而强、强而大的三个大国,出现于亚太地区并构成该地区的“三极”,以及三国之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进而影响到与英俄等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中日美三角关系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二)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初步运作
20世纪初期,中日美三角关系在其形成过程中,也进行了初步的运作。兹举若干史例加以说明。
1.关于东北问题 甲午─日俄战争之后,被日本称为“满蒙”的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清末十年间对外关系的焦点。日本和俄国,先是斗争,继而又合作,企图瓜分并共同占领东北。而作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调停者”的美国,也借机深入东北,主要与日本发生了冲突。日本为与美国对抗,采取了联俄政策,美国为对抗日俄,在与日本谋求妥协、并签订《罗脱─高平协定》的同时,又一度与中国合作。[27]在上述背景下,晚清政府企图沿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采取了“联美制日”的方针,先有唐绍仪的赴美之行,后在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又与美国合作,对抗日俄。[28]
这样,在清末十年间,围绕中国东北问题,就形成了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第一个运作回合。在这个回合中,中日之间关于东北问题的斗争,无疑是这个三角关系的中心,而日美之间在东北问题上的分合,不但制约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程度,也影响了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向:当日美对抗加剧时,联美制日政策就可能见到一些实效;而当日美达成妥协时,这个政策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甚至无果而终。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对日关系上的成败,取决于日美关系的发展。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初次运作,奠定了此后的模式。
2.关于“二十一条”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表明了其参战的目的和独霸中国的野心,它不但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直接发生尖锐冲突,也关系到中国的存亡问题。这对于尚未参战、而保持中立的中美两国来说,再度带来合作的可能。急于称帝的袁世凯既不敢得罪日本,又不能全盘接受其要求,于是在中日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政策,而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际干涉上。1915年1月21日, 北京政府首先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透露了日本要求的主要内容。此后,顾维钧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迅速通报中日谈判情况,顾氏认为“根据世界的形势,惟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29](P123)美国政府接到芮恩施的报告后,1月25日, 威尔逊总统与国务院顾问豪斯、蓝辛在白宫讨论了中国的要求,豪斯提出了美国代表性的观点是:目前我们还不能为中国的门户开放问题同日本作战;当2月17日中国公布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后,美国国务院在远东问题上的三位决策人物白里安、卫理和蓝辛,都认为需要同日本达成某种“协议”,允许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扩张。[30](P103─106)因此,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希望美国方面予以支持,芮恩施也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出发,积极主张支援中国[31](P110),但美国政府既不愿因中国问题而卷入国际争端,也想借此调整美日关系,故在中日交涉上仅给予了中国极为有限的支持。
中国政府失望之余,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5月11 日,美国向中日两国发出同样的照会,称:“中日两国所订协议或条约,如果损害了美国在华条约和侨民的权利,妨害了中华民国政治和领土主权完整及众所周知的门户开放的国际政策,美国概不承认。”[ 32 ](P146)这是美国为维持在华门户开放政策,第一次声明采取“不承认主义”。5月1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全国公布了交涉经过,并发表宣言称:“如列强对于保持中国独立及领土完全暨保存现状与列强在中国工商业机会相等主义所订之各条约,因此次中国承认日本要求而受事实上修改之影响者,中国政府声明非中国所致也。”[33](P213)这就把中国被迫接受日本要求的责任推给主持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5月15 日美国政府又向中日两国发出了一个与前述“不承认主义”的原则相矛盾的照会:“正在谈判中的所有条款,凡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地位有所变更者,当然亦必须告知美国政府,使得美国能够分享基于最惠国待遇而自然增长的特权。”[32](P147)这个照会表明美国已很快从“不承认主义”原则后退下来,而企图与日本分赃了。5月25日, 中日达成“民四条约”,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基本得以满足。在上述交涉过程中,中日美三角关系再次运作,中国在日中、日美和美中双边关系中,成了最后的牺牲品。
3.关于中国参战问题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袁世凯政府时期已决定采取中立政策。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这场斗争又与日美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因而围绕中国参战问题,中日美三角关系又一次运作起来。
1917年2月3日,美国与德国绝交,并向中国等中立国发出通告,要求它们与美国采取同一行动。虽然美国驻华公使曾一度自作主张地积极活动,要求中国政府参战,但美国政府反对让中国参战,这个要求同黎元洪的愿望是一致的。日本本来反对中国参战,此时态度急转,积极支持中国参战,并与段祺瑞的愿望一致。因此,在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美国支持的黎元洪和日本支持的段祺瑞之间,斗争进一步激化,并导致了张勋复辟丑剧的上演。结果,“府院之争”以段祺瑞胜利告终。1917年8月14日,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对德国宣战。 在中国政府的参战问题上,日美两国已深深介于中国内政,并进一步激化了“府院之争”。而北洋军阀们为争夺国内统治权,也公开寻求日美的支持。这样,参战问题就成为中日美三角关系运作的一个典型史例。黎─美、段─日之间的不同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美两国的关系状况。日本在二十一条之后,继续扶持了段祺瑞政权,并开始了日皖的互相勾结。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始终占有优势地位;在三角关系上,日中关系决定并制约了日美、中美之间的关系。
围绕中国参战问题,日美冲突进一步加剧,但两国都不愿破裂关系。日本应美国之请,派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作为特使赴美,于9月6日─11月2日,与美国国务卿蓝辛,主要围绕中国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并于 11月2日互换照会,达成了《蓝辛─石井协定》, 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特殊权益”,而日本则同意不侵犯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34](P1─2)这是日美之间背着中国政府搞的秘密交易。11月9日, 北京政府对此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35](P107)这等于否认了上述日美协定。由于日本的胜利和美国的退让,皖系军阀主政期间,中日关系进一步密切,而中美关系一度退出舞台,中日美三角关系暂告结束。直到战后的巴黎和会期间,由于美国附合其他列强偏袒日本、压制中国,使中国民众一度兴起的对于美国及威尔逊总统的好感,再次跌入低谷。[36](P73-80 )中日关系的非常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冷却,最终导致了中日美三角关系的运作一度中断。
三、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发展
中日美三角关系形成并初步运作之后,在二三十年代,进入发展阶段。在40年代前半期,日美开战,中美结盟抗日,中日美三角关系走向破裂阶段。
(一)20年代华盛顿体系下的中日美三角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日美争霸和现代中国崛起的局面。虽然巴黎和会使中日美三角关系一度中断,但不久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又使这个关系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
巴黎和会和凡尔赛体系暂时调整并建立了欧洲新秩序之后,在亚太地区,美国联合英国,向独霸中国的日本展开了新的攻势,企图建立亚太地区的新秩序。1920年的直皖战争,日本卵翼下的皖系军阀的衰败和美英扶持下的直系军阀的兴起,就是新一轮日美竞争在中国的结局。美国在渐居优势的情况下,于1921年8月13日, 邀请日英法意和中国等九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解决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问题。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的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美英日法四国《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之条约》,列强实现了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均等,美国达到了拆散“日英同盟”的目的;通过英美日法、意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美国不但在太平洋上取得了与英国平等的海军优势,而且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通过与会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美国迫使各国明确接受并进一步确立了它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34](P736-772)会议期间, 在美英两国代表的参加下,中日两国还进行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1922年4月中日签署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中国收回山东, 但日本也保留若干权益。[23](P227-230 )这样就使一战期间的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之后基本解决。会议之后,美国以《蓝辛─石井协定》与“九国公约”原则不符为由,与日本进行谈判,于1923年4月14 日通过换文,正式取消此协定。[32](1923,Vol.1,P458)[37](P35-36)
华盛顿会议所签署的上述条约,构筑了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新秩序——华盛顿体系。它不但使日本随着“日英同盟”、“日美协定”的废止而在亚太地区陷入孤立地位,也以“九国公约”和“海军条约”限制了日本独霸中国、称霸亚太的野心,这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大胜利。又由于“九国公约”的签订和山东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因此,被称为“太平洋会议”的华盛顿会议,激起了中国对于太平洋问题的进一步参与,也使一度下滑的中美关系恢复起来。这样,中日美三角关系在华盛顿体系下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经过一次大战之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民虽然对于美国的好感有所增加,但对于中国的国际处境也有更深刻的认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 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就指出:“华盛顿会议中之主要问题——中国问题是在美国胁制之下解决的”,“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资本主义者的互竟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38](P39─40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新形势,也给华盛顿体系下的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在一战后的新一轮日美竞争中,由于军事、经济实力的差距和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日本居于劣势,日美关系从此被纳入美国主导下的华盛顿体系。20年代,日本政党政治兴起,尽管一度出现过田中义一的“积极外交”,但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主要以币原喜重郎外相主持,推行对于美、英等国的“协调外交”。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合作,标榜不干涉主义,并主要采取了经济手段。由于亚太地区的日美关系已由此前的“竞争中合作”发展到“合作中竞争”,中日美三角关系在20年代呈现了较为平稳发展的态势。
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后期,在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影响下,由于日本未干预第一次直奉战争,使直系战胜了奉系军阀,维持了统治。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因日本的干预而使奉系及冯玉祥国民军胜利,但此后的北京政府已很难由奉系一统天下,吴佩孚直系力量仍然存在并作为一股重要力量,形成共同对付南方革命势力的局面。直奉军阀势力的消长说明,北洋政府末期的中国政局,仍然是由美日共同主宰的。
北伐战争兴起后,南方革命势力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矛头直指美英日等国及其分别卵翼的直、奉军阀。但到大革命后期,由于美日两国采取了基本一致的对华政策即“怂蒋反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最后失败和蒋介石政权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建立(注:主要参考牛大勇的论文。[39]但沈予的观点与此对立,认为美、日对华政策不同。[40])。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日美关系仍是外交的重点。蒋介石的访日并向宋美龄求婚,就清楚地表明了两国对蒋介石的重要性的认识。南京政府为打开外交孤立局面、争取国际承认,不惜抛弃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忍辱妥协,迅速与美国解决了“宁案”。[41]后又与日本妥协,委曲求全地处理了“济案”。[42]并在“济案”之后,由日本转向与美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43]随后,国民政府在与列强的“改订新约”运动中,往往是先与美国谈判成功,然后迫使日本就范。到1930年,随着南京政府在中原大战后地位的稳固,与美日两国的关系也发展到稳定状态。
在整个20年代,中日美三角关系在华盛顿体系下的日美基本协调一致的状态中,获得了比较平稳的发展。
(二)华盛顿体系的逐步被打破与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破裂
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打破了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局面。维系这一局面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分别受到了德国和日本的冲击,直到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全面实施侵华和南进的亚太政策,逐步打破了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随着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进入逐步升级的冲突阶段和中国从局部到全面的抗日战争,30年代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进入又一个新的阶段。而以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为界,本阶段又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由“协调外交”迅速走向“自主外交”。[44]中国政府在事变期间,采取了不抵抗、不交涉的对日方针,而寄厚望于国际联盟和美国的干预。国联在“李顿调查团”之后,虽然通过了于日本不利的决议,但由于日本1933年3月退出国联, 从此它就失去了作用。而作为华盛顿体系的主导者和保证者的美国,因其“门户开放主义”与日本“大陆政策”的矛盾,在事变期间,开展了对日外交[45],并由史汀生国务卿再次宣布了美国的“不承认主义”原则,但它没有进一步采取足以制约日本的措施。在上述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在一二八事变后,改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同时开始探索“联美制日”的新途径。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就是在中国付出极大牺牲、而美国对日妥协的背景下,再次恢复运作的,在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处理和《上海协定》的签订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30年代中期,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一步步走向全面侵华。同时,在对外政策上推行“协和外交”,继续与欧美列强保持某种协调,并以亲善面孔对华。中国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下,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忍让妥协,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长期占据对外关系的主导地位。其间,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一度企图制造“联美制日”的格局,并在“棉麦借款”、《白银协定》等问题上,中国一再作出对美国的经济牺牲,换取了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和对日本华北事变的声明,但美国并未采取制日的实际行动。到了1935年之后,在中国政府转变到准备抗战为主、而日本已全面确立其亚太政策之时,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到1936年底,华盛顿、伦敦两个海军条约失效,日本完全脱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彻底走上了与此对立的“自主外交”路线。[46](P607)可以说,主要由于美国亚太政策的软弱和日本的不断扩张,七七事变以前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已变得相当脆弱,并为日本全面侵华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中国政府宣称这是“自卫抗战”,一度维持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并迟至1941年底才追随美国对日宣战。这期间,国民党政府在继续领导抗战的同时,即使在中日断交后,也不断通过密谈,企图实现对日妥协,同时又以更为迫切的心情,施展各种手段,力图操纵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日本从全面侵华到南进、从“东亚新秩序”到“大东亚新秩序”,独霸亚太的野心昭然若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欧洲形势和日德意同盟的影响下,美国对日政策渐趋对抗。三国之间双边关系的上述变化,进入了三角关系的最后阶段。
1937年11月,《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布鲁塞尔会议,日本拒绝与会,而英美等国又推行对日绥靖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华盛顿体系的彻底崩溃。中国政府此后将争取国际支持的主要对象逐步转向美国。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确立了“苦撑待变”方针,并于1938年9月任命胡适为驻美国大使,以促进美国援华制日。1940年6月又派宋子文赴美活动。而在对美交往中,国民政府又暗中与日本交涉“和平”,以要挟美国。[47](P548)由于国民政府的积极活动,加之美国对华政策的逐步改变,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中美关系已基本形成了战后才出现的格局,中日美三角关系亦获得充分发展,三国互动关系表现突出:三国之间的任何一个双边关系的发展,都会对其他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进而通过调整,又不断相互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外交谋略是相当成功的。1941年,日美之间进行近一年的谈判,两国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突出了中国的战略地位,亦成为中国政府借以实现中美结盟、打击日本的机会。日美开战前夕,中日美三角关系在最后阶段也发展到了高潮。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正式开始“大东亚战争”。8日,美国对日宣战。1942年1月1日, 以美英苏中四国为首的《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最后形成。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中美两国形成战时同盟、共同抗日,本世纪初期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中日美三角关系正式破裂。
战争期间,虽然中美之间在合作中存在着矛盾(例如史迪威事件),并导致了美国与中共延安政权之间的关系有所发展[48],一度形成了中日美“大三角”关系之后的国、共、美“小三角”关系,但美国又主要出于战后对苏的考虑,派赫尔利使华,扶蒋反共,从而继续维持了与重庆政权的战时同盟关系。日本在“大东亚战争”期间,为阻挠和破坏中美关系,也采取了对华新政策,加强对重庆政权的政治工作,企图实现蒋汪合流,日本军部还尝试对中共延安政权也进行“和平工作”[49],但在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太平洋战争期间,中日关系的崩溃,又是中日美三角关系破裂的前提和结果之一。
四、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特点
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受到世界形势、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以及三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
在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和美国分别崛起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强国,并参与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角逐,日美两国在对华关系上,虽然在东北问题上产生过冲突,但仍以合作为主,共同谋取在华权益。中国晚清政府开始酝酿实行“联美制日”的政策,但并无成效。因此,在这十多年间,中日美三角关系还处于正在形成中的萌芽状态。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均不如日美关系那样密切和深刻,但日美关系已开始成为调整三国关系的“杠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开始实施以独霸中国为主的亚太政策,美国虽然发表对于“二十一条”的不承认主义原则,并在一些对华问题上与日本有所冲突,但出于欧洲第一的对外战略需要,在亚太地区与日本仍以妥协、合作为主。中国北洋政府屡次试图“联美制日”,但终为日制,而段祺瑞皖系军阀政权则干脆投靠日本。这期间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已经显现出中日关系作为其“轴心”的特点。
华盛顿会议之后至九一八事变期间,亚太地区的主要争霸国家是日本和美国,而其争霸对象则主要是中国。中日美三角关系应当进入合理的运作阶段了。但由于日本在20年代主要以协调外交、基本奉行对于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的合作政策,从而形成了亚太地区“美主日从”的局面,而在对华问题上则是日美互相进退的局面。中国因军阀混战和不断的革命战争,使得更加软弱的中国政府,不可能积极跻身于“太平洋问题”有所作为,而仍是受制于日美的共同支配。因此,20年代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开始呈现出畸形的发展状态:中日关系的“轴心”作用削弱了,而日美关系却由“杠杆”演变为中美、中日关系的“轴心”。
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前夕的30年代,日本伴随着一系列的侵华战争,从东亚门罗主义的“天羽声明”到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直至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其亚太政策全面实施并逐步打破了华盛顿体系,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的矛盾以冲突与对抗为主。这就使得中日美三角关系应当也可能在20世纪初期的基础上,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即以日美关系这个“杠杆”来调整中日关系“轴心”,而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也始终在这方面努力开展了工作。但主要由于美国亚太政策的影响,中日美三角关系再次呈现出畸形的发展状态:日美关系的“杠杆”使用更加微乎其微,中日关系反而由“轴心”作用演变为“杠杆”作用,制约着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日美三角关系在开战前夕一度出现过较为正常的发展状态,但在日美开战、中美结盟之后即陷入破裂状态,这是此前中日美三角关系畸形发展状态的必然结局。
通过以上五个历史阶段的考察,20世纪前半期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它是由中日“轴心”和日美“杠杆”以及中美不平等关系而构成的“不等边三角形”。
20世纪前半期,中日美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即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分别构成了中日美三角关系的三个“边”。由于上述三“边”,在20世纪前半期始终未处于等距离的状态,中日美三角关系,也就呈现出“不等边三角形”的特点。在这三个“边”中,中日双边关系与日美双边关系,是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时远时近、时大时小的两个“边”,但不管怎样变动,这两个“边”的距离,均始终近于、小于中美双边关系。仅在太平洋战争的短暂期间,中美关系这一“边”的距离最近、最小,而中日、日美关系两个“边”距离最远、最大,但也不构成“等边三角形”的特点。
中日美三角关系之所以呈现“不等边三角形”的历史特点,除了亚太地区影响这个三角关系的外部因素之外,从内部构成机制来说,是由于中日、日美、中美这三个双边关系,在三角关系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而决定的。
中日双边关系构成的一“边”,是中日美三角关系的“轴心”。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及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近现代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是密切和复杂的,比较而言,中日关系更为密切和复杂。太平洋战争前40年,中日双边关系的距离也始终近于日美、中美关系。由于近现代日本奉行侵略扩张的对华政策,并不断掀起一次又一次的侵华高潮,因此,中日关系成为三角关系中最不稳定的“动因”,从而制约和影响了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与状态:每当日本侵华高潮期间,日美关系的冲突一面就加剧,双边距离即疏远,而中美关系就出现接近、寻求合作的特征;而当日本以亲善面孔或协调立场处理对华关系之时,日美之间的距离即接近,而中美之间则疏远。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变化发展,主要取决于中日关系这个“轴心”。
由于中日关系的上述状况和现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软弱,使得美国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既可以“左右逢源”、又经常“两头为难”。日美关系因此成为中日美三角关系中的“杠杆”,起到一种调节与平衡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日美关系冲突一面加剧时,中美之间的距离就接近,而中日之间则疏远;当日美关系合作一面为主导时,中美之间的距离即疏远,而中日之间就接近。由于存在着日美关系这个“杠杆”,在20世纪前半期,中日美三角关系的运作,一般是按照以下两种模式进行的:日本侵华、中日关系紧张→日美冲突为主→中美接近;日中“合作”→日美合作为主→中美疏远。但在太平洋战争以前的40年,由于日美两国始终寻求的是对抗中的合作,而中国的联美制日政策又难以见效,这就使日美关系这个“杠杆”,远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与平衡作用,而成为使中日美三角关系呈现“不等边三角形”的主要原因。
在中日美三角关系的互动过程中,美国是最后的最大“赢家”,而中国则始终是中日、日美、中美关系的最大“输家”。“以夷制夷”反演变为“以夷制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一个形象的写照。近现代中国的命运,常常要取决于东京或华盛顿的安排,则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就中美关系而言,即使是中国最终实现“联美制日”的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平等新约仍然也没有使中国摆脱附庸的地位,华盛顿体系崩溃后,中国不久又受制于美苏的雅尔塔体系。中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是中日美三角关系不可能呈现“等边三角形”的又一个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是中日美三角关系畸形发展的一个必然结局。正如有位中国学者总结历史教训时指出:“如果当时在东亚有一个强大的、足以促使中日美之间形成平衡的三角关系的中国,日美之间未必会发生太平洋战争。”[50]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又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才成为现实。历史的认识同样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学者们更不能因现实需要而健忘历史。
收稿日期:2000-07-20
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日开战论文; 中日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一战论文; 太平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