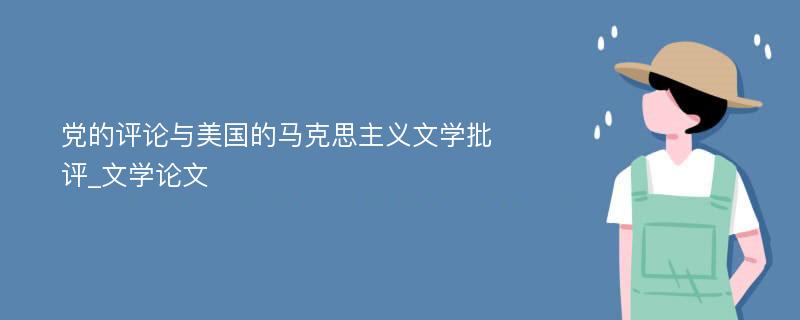
《党派评论》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党派论文,美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派评论》自创刊之日起,便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联系在一起,其创办者菲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与拉夫(Philip Rahv),长期负责编务工作,全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中。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杂志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潮流与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平台,从而吸引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最优秀的文学精英,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美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思想前提:摆脱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20年代末,俄裔犹太青年菲利浦斯和拉夫拒绝传统的犹太教,接受了具有国际主义诉求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选择正是当时青年人经由自由主义导向持异见的激进传统的具体体现。他们的文学批评也是在这样的知识路径中展开的,凭借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体察,他们及早认识到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弊端,进而走向了独立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路。 在文学批评起步时期,菲利浦斯与拉夫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与菲利浦斯在大学期间接受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是,拉夫早期对现代主义文学持批评态度,以附和高尔德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文艺。1932年,拉夫凭借《文学的阶级战争》一文,进入《新群众》的撰稿人行列。拉夫在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尚未成熟,与社会抗议文学完全不同。奠定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抗议文学属于资产阶级文化,而无产阶级文学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破除资产阶级的颓废审美时尚,坚持阶级对抗的不可调和性。① 在拉夫看来,资产阶级文学已经丧失了激发读者情感的作用,那么倡导一种适应时代的新的文学形式就势在必行。于是,他以辩证法阐发亚里士多德的怜悯与恐惧,提出“新净化说”。拉夫采用亚氏的悲剧定义,讨论现代主义文学,指责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缺乏故事的长度,未能构建出有机的整体,只是一些花里胡哨的形式技巧。通过对乔伊斯小说的品评,拉夫扩展到对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否定。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不过是作家神秘主体的内省冥想、幻觉的杂烩而已。他急欲以“新净化说”呼唤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 拉夫在1932年《致青年作家的一封公开信》中再次表露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鄙视态度,他说: 我们接受用资产阶级环境的染色,肢解我们自己,在为年迈无能的统治阶级服务中出卖我们的创造性,亦或我们将打起反叛的大旗,使我们自己带上唯一进步的阶级特征——那个朝气蓬勃、年轻的巨人正步入到战斗的竞技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增强我们的精神力量。② 拉夫借鉴布哈林在《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中的观点,把当下现代主义者的离群索居、利己主义、非道德性等,归咎为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拉夫认为文学形式与旨趣依赖于斗争中的阶级的戏剧性转变,而这种转变与综合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消亡有关,并渐次从群体扩展到个体的感觉当中。 接着,拉夫又运用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观点,指出2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极尽奢华,反映在文化上就是“纯粹的消费”,在文学上的表征则为现代主义。为了说明问题,拉夫把诺里斯与艾略特进行比较,指出俩人的创作反映了不同的时代本质:诺里斯小说中的人物是工业社会生活的主宰者,他们与自己的阶级一样年轻而富有活力,属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而艾略特在“消除自我”的创作方法指导下,听任艺术感受的摆布,致使人物丧失一切社会属性,沦为孤独的“自我”,最终折射出腐朽的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在拉夫看来,艾略特的摒弃自我的观点正是一种“纯粹消费”的非社会性心理的反映。 拉夫对现代派的批评,在《T.S.艾略特》一文中也表述得很清楚。拉夫把《荒原》贬损为艾略特颓废之象征,他指出:“艾略特在当AI写作作中已经发挥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从他近期在当代场中与所有反动的贫瘠的联系中着眼,人们无法不为此影响而悲叹。”③他全盘否定艾略特文学创作的积极性,认为其诗歌是对革命冲动的一种抑制。在拉夫看来,《灰星期三》是失败的,是艾略特创作的低谷。拉夫提醒读者注意,艾略特在诗歌中经常把自己比喻为“鹰”,很明显这只鹰将不再飞翔,因为诗人的贵族习性与苦行僧思想背离了人民的反抗和唯物主义繁兴的时代。④拉夫谴责艾略特诗歌中的神秘主义、个人主义含混绝望,把艾略特早期诗歌中的颠覆性冲动归咎为垂死的帝国主义文化。他再次以准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姿态解析现代主义文学,重申了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原则。由于拉夫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无法容忍那些桀骜不驯的同路人作家,所以,他贬损艾略特、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在拉夫看来,作家应该依照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需要进行创作,因为文学隶属于这个大系统。因而,拉夫无法容忍现代主义文学的颓废性,这些都是他后来指责斯大林主义者的。 在批评现代主义作家的同时,拉夫极力推崇威尔逊、阿尔文、希克斯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文章不断地刊登在《新群众》上,当即引起美共批评者马吉尔的关注。马吉尔赞同拉夫采用布哈林的时代文化划分的观点解释现代主义文学,但他并不欣赏拉夫过于严厉地批评现代主义文学。在马吉尔看来,拉夫未能体察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冲动,即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深远的反叛。马吉尔也不无忧虑地感到拉夫对同路人作家持宗派主义的偏见,未能体察到他们潜在的合作性。 菲利浦斯在1932年经常以华莱士·菲利浦斯的笔名发表文学评论文章。他最早发表的两篇评论为《古典文化》和《批评的范畴》;前者不过是一篇评述,后者显示了他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视阈中对形式的特别关注。在《古典文化》中,菲利浦斯运用“第三阶段”理论分析加塞特,他认为加塞特的《群众的造反》是在替帝国主义谢罪,而他本人不过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指出:“在《群众的造反》中,作者以自己大量混乱和诋毁的语言完成了大部分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支持。本来需要一部书批驳他所有的全部谬论和歪曲,但由于所有这些谬误都出于他的一以贯之的基本态度——为资本主义辩护和谴责革命运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了。”因此,“此书是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征兆,试图把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知识的反动力量收编进来”。⑤菲利浦斯在文章中不仅遵循党的路线,而且运用教条主义的修辞比喻,指责作者的观察是靠陈腐的理想主义支撑的,而此理想的反动性在于颠倒了马克思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论断。 《批评的范畴》涉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主要话题,即如何从印象式批评上升到考证层面。受到英国新批评派的理查兹(Ivor Richards)的启发,菲利浦斯开始探寻一种近似科学话语的批评范式。同时,他也受到现代主义的反实证主义影响,特别是接受了导师胡克的影响。在这些批评思想的合力作用下,菲利浦斯主张摆脱对绝对真理的依赖,探寻基于社会构成的客观性——既不依赖于个人的直接经验,也不倚于历史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他试图把个人行为的批评发展为一种集体的、有责任感的批评,即一种系统的批评范式。 菲利浦斯通过追踪亚里士多德、康德、休姆、涂尔干等人的理论,理清自己的批评思路。他首先扩展了休姆的否定范畴概念,他说: 范畴体现了理性对生活中的方法与思想的分类。在科学中它们是分析的支点,在理智者的态度和判断中,以及在这种独立的作为批评的领域里,范畴是根据正常生活(思想)不断变化的重点和关联的一些构成。就像一架离心机,第一个重点都环绕它的关联物展开。观念的历史是这些范畴的交互作用与相互结合之间的张力。⑥ 休姆提倡由特定的个体经验切入到涵盖广阔社会内容的理论中去,为的是呈现思想的历史流动性,而在这里菲利浦斯所关心的则是这些范畴的分割、限制和内在联系。菲利浦斯主张在主客体的交互作中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批评视为从敏感丰富的大脑到媒介的产物。从梳理休姆的理论切入,菲利浦斯试图在批评范畴与文学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个人与社会经验之间的某种协调。从这种意义上看,他所倡导的批评范式,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批评。他的兴趣是以传统方法进行知性的历史考辨,把历史与文本的联系理论化。所有这一切后来都衍生为《党派评论》的中心议题。也正是这些各不相干且又紧密联系的范畴,保证了文学批评来源的多样性,引导着菲利浦斯突破教条主义批评的思想束缚,而他也更愿意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灵活的分析方法。 1934年,菲利浦斯发表题为《感受力与现代诗歌》的文章,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阐发感受力。他认为,感受力体现了与行为主义、唯意志论相对立的主体性:感受力是认识与感性经验的融合,并需要对全部感性经验的形式进行体验,吸收那些全然不同的形式。比如,克兰的《桥》就具有一种机器般的感觉,而艾略特的《荒原》则传递出一种躁动不安、紧张无益的情感。菲利浦斯所关心的不是克兰与艾略特诗歌的政治属性,而是对其诗歌的感觉,即由资本主义和阶级冲突所造成的时代的主体性。如果历史为诗人们提供了相同的感觉,那么,一组诗歌就可以共享同一种感受力。正是凭借这种共同的“人文”感受,才使奥登、斯彭德、刘易斯、格雷戈里等诗人处在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的交汇处。菲利浦斯认为感受力是诗人的感觉冲动与寻找诗歌的特定形式的完美结合。⑦因此,感受力是文学创作中的一项重要参数,它既不能与教条主义者所强调的阶级意识相提并论,也无法等同于浪漫派所谓的感情深度,因为任何诗歌的特质都是其氛围与思想的影响与压缩,并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故而,对作品的感受决不能化减为单向度。他的感受力概念在个体与集体层面上保留着构成经验的要素,强调情感结构必须包括积极参与文化的感情、价值、氛围与判断。他坚持认为,集体生活的情感向度只是物质向度的一部分。菲利浦斯把感受力引入无产阶级文艺中,以此抑制教条主义批评。 很快,菲利浦斯的感受力也获得了拉夫的认同。自1934年起,他们都把感受力作为批评的主要议题,并从评论艾略特诗歌切入,探讨了许多重要的批评问题,诸如,政治内容的创造性吸收、形式的感觉的模式、关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等等。这表明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评论旨在匡正决定论和创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 二、批评精神:支持无产阶级文学 1934年初,拉夫和菲利浦斯在约翰·里德俱乐部的领导与资助下,创办了《党派评论》杂志。杂志支持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继续了《专题论丛》的办刊宗旨。⑧菲利浦斯与拉夫在《党派评论》创刊声明中说: 将刊登其成员的优秀创作,同时也刊登那些赞同约翰·里德俱乐部文学宗旨的非成员的优秀作品。虽然我们提出集中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但是我们将持守明确的观点——革命工人阶级的观点。通过我们特殊的文学媒介,我们将参与工人阶级和真诚知识分子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与种族压迫的斗争,参与到废除滋生这些邪恶和制度的斗争。保卫苏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⑨ 同时,他们又谈到了具体的文化事项,“我们不仅要与剥削阶级的颓废文化斗争,而且要与削弱斗志的自由主义斗争,因为这些自由主义有时通过阶级异化力量的压力渗透到我们的作家当中。我们决不会忘记维护我们自己内部的井然秩序。我们将抵制以狭隘思想、宗派理论和实践削弱我们文学的每种企图”⑩。显然,杂志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艺的读者作为刊物的主要受众,在理论上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当时美共所倡导的全部主张都被他们囊括在发刊词中。虽然党的事业跟杂志的文学宗旨相去甚远,但两位编辑心甘情愿地担负起党的现实重任。他们自觉接受党的主张——从整体上把资产阶级文化定位为颓废文化,同时也肩负着同进步作家残存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任务。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危害大于宗派主义,这充分反映了美共与共产国际的政治导向。当时《党派评论》的发行量超过了《大西洋月刊》,甚至比《新群众》影响还大。 《党派评论》侧重于文学评论,与同类的刊发原创性的无产阶级诗歌和小说的刊物(如《发电机》、《铁砧》)有所不同,它每期一半的版面用来刊登文学评论文章。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除了两位编辑之外,多为批评家。这些人都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即便有的人不是共产党员,也同党保持密切联系。 《党派评论》创刊后,菲利浦斯与拉夫的文学批评逐渐走向成熟,他们面临着反击教条主义批评的任务。他们继续品评艾略特的诗歌,以感受力为切入点,深入阐发诗歌所蕴含的辩证思想。同一时期,艾略特也在《一种诗剧的可能性》一文中,详尽阐发了文学形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特定的形式不仅是一种外形或节奏,而且是与特定内容密切相关的节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不仅是格律,而且是与其感情和思想方式紧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的东西。(11)艾略特又通过对但丁的阐发深化了论题。艾略特说,但丁之所以比其他诗人重要,就在于他成功地构建出自己的哲学体系(系统信仰),并以此透视世界。(12)在艾略特看来,但丁把客观的教义化为感觉,辩证地处理了主客问题。这样,结构就成了诗歌的每一部分所必需的要素。这正是艾略特所需要的信仰与诗歌内在结构的一种融合。艾略特的分析极大地启发了菲利浦斯与拉夫,他们感到中世纪末的宗教信仰与20世纪初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诗歌的影响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思想体系运用得当与否,就看能否在结构中嵌入感情,无产阶级诗人完全可以把政治信念化入作品的想象之中。他们从艾略特的文艺主张中找到了反对来自官方左翼批评的思想武器。尽管艾略特与他们所理解的感受力并不相同,但是,艾略特对感受力和客观对应物的论述,还是让他们认识到感受力可以重新打造无产阶级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菲利浦斯与拉夫在对艾略特的阐发中,集中展现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最富雄心的探寻,他们提出了诸多自己的批评主张。感受力成了他们批评的核心概念。当时关于形式与内容之争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难题之一,而菲利浦斯与拉夫在这场争论中拓展了感受力。对感受力的阐发,不仅让菲利浦斯与拉夫第一次在美国左翼文学中超越了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同时也使他们避开了形式主义,开启了纽约文人广阔的文化批评视阈。1934年,菲利浦斯与拉夫合写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学中的问题与透视》的文章。尽管他们在文章中把批评比喻为列宁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文艺中不可或缺的,但是,他们对文学问题的分析还是与官方观点相冲突,说明他们的批评已经开始逾越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指向即将来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新路径。 同年,拉夫在评论海明威的小说《胜者无所获》的文章中,明确谈到了远离阶级斗争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学自治,并欣然接受现代主义文学。他把商业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对照: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后者则是“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疏离、异议和颠覆。他称之为“否定的艺术”,即起到激发社会反叛的作用。对拉夫而言,文化决非同质的,现代主义文学也决不能理解为反革命意识形态的颓废的美学。(13)此后,拉夫一改早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否定态度,转而为它摇旗呐喊。 1935年,他们合写了题为《评论》的文章,在对福克纳的《圣所》的评论中深化了感受力。他们分析了“特定内容”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指出福克纳的小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关于南方的特殊内容的画卷,而这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人们看不出作家的立场是进步还是反动。这是因为“特定内容”就是个体感受力的产物。(14)当时许多左翼批评家都坚持优秀的作家应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以政治标准衡量作品的价值。菲利浦斯与拉夫在对福克纳的评论中提醒人们警惕此种做法。他们通过对文本力场与社会力场的解析,强调特殊内容与形式的无法分割,提倡在动态的语言与形式要素之间建立互动联系。所谓特殊内容包括观点(塑造人物性格的倾向性)、描写方式、情节结构等;而形式则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模式,同作家、作品的感受力联系在一起,它决定作品的成功与否。通过抑制文本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实现二者的互动,凸显各种中介因素的重要性,旨在维护文学的自主性。 1934年到1936年,菲利浦斯与拉夫不断调整批评话语,特别强调从审美与形式方面评价文学作品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此时期俩人合写了许多文章,他们在承载党的政治任务的前提下,维护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及拓展无产阶级的美学原则,甚至想重新勘定左翼文化的广阔界域。这样的批评策略在与斯大林主义发生冲突的同时,客观上加速了现代主义文学与政治激进主义的结合。他们声称《党派评论》正是为着无产阶级事业而倡导这种结合的,此时,一种初具美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呼之欲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时美共在文化领域推行其主张,但也不应过分夸大其实际影响。当时党的教义并没有强大到能够统领整个左翼的程度,不要忘记美共批评者马吉尔曾经批评拉夫的教条主义批评。事实上,当时各种独立的左翼文学刊物超出人们的想象,而《党派评论》的发刊词并没有说明杂志或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在流行的时尚中拥护特殊的政治立场,仅仅强调通过特殊的文学媒介发表左翼阵营中的优秀文学作品,使杂志参与政治斗争。这种说法很微妙,值得注意。由此,我们也联想到两位编辑非常关注那些“特殊的文学”。尽管在他们的文学批评愈发精妙与复杂之时,他们也倾力使杂志发挥党的喉舌作用,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文学观念裹挟着意识形态性,并不能保证他们必然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合拍,而且运动本身也为他们预留了巨大的话语空间。 三、应对论战:坚持批评理论的引导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中期,菲利浦斯与拉夫的几篇较重要的文章发表之后,引来了“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和“学院派作风”的指责。高尔德批评他们是“官僚主义”。为了驳斥对手,他们从阐发重要的美学范畴入手,探寻文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他们试图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厘清不同学派的思想本质。在他们看来,没有理论支撑的文学批评将沦为经验的观察、颠倒的唯美主义、政治理念的粗俗应用。(15)这样一来,围绕在《新群众》与《党派评论》周围的批评家及作家就逐渐分裂为两个阵营,但仅仅是萌芽。 以高尔德为代表的《新群众》周围的那些无产阶级文学的拥护者,坚持文学的政治性,不重视技巧,强调革命文学应该从工厂的严酷考验中诞生,实现约翰·里德俱乐部的“创作要与革命的政治携手共进”的宗旨,这些人均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对者。高尔德厌恶当代的精英主义作家,他称赞威廉斯的小说忠实地反映了原生态的工人生活,这是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楷模。(16)康洛伊在“第一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明确反对无产阶级作家在形式技巧方面的翻新出奇,认为那种晦涩的叙述和半隐秘的术语是大众所不懂的。(17)高尔德指责普鲁斯特是中产阶级的手淫大师,在他看来,没有新内容的新形式毫无价值,就像被虫子掏空了内瓤的胡桃壳。《新群众》所推崇的是辛克莱、德莱塞,甚至是战前那些典雅而缺乏革命生气的现实主义作家。(18) 尽管如此,《党派评论》与《新群众》并非水火不相容,在分歧中有联系。例如,布鲁克斯1937年聚集在《党派评论》的麾下,积极倡导现代主义文学,把乔伊斯、普鲁斯特与赫克斯利和德莱塞进行对比,指出正是这种新形式使作家与经验、感觉有了新的联系。他同时也为《新群众》撰稿,并与希克斯长斯保持了友谊。卡尔默担任过约翰·里德俱乐部全国主席,1936年他在《星期六述评》中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指责高尔德、弗里曼与年轻一代分裂了。但是,他一直与希克斯保持通信联系,不同的文艺观并未妨碍他们的私交。即便是在卡尔默出任《党派评论》编辑期间,他的许多极富争议的评论文章也发表在《新群众》上,并且长期负责美共的“国际出版社”的编务工作。 同为《新群众》旗手的弗里曼就力图改变左翼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倾向,他尝试用高雅文化教育群众,时常在工人集会上朗诵艾略特和庞德的诗歌。弗里曼认为《尤利西斯》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衰颓的绝妙的反映,“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是天才之作”(19)。希克斯也称赞普鲁斯特在人物心理描绘上的深度和非凡性,他认为形式从根本上可以脱离思想内容,敦促无产阶级作家大胆进行形式创新。(20)显然,《新群众》与《党派评论》两个阵营中的批评家是既互相对立又合作联系的。 1936年,这种既纷争又联系的平衡被打破了。《党派评论》与《新群众》的分歧越发明显,集中体现在“法雷尔之争”中。法雷尔出版《文学批评札记》率先对美国左翼文学阵营中的过度政治化、庸俗的机械决定论进行反思。法雷尔的书涉及三个问题:一,美共如果过多地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像组织工人罢工一样组织文学创作,就会使作家的创作屈从于政治,把很有前途的作家变成短命的新闻制造者;二,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不意味着作家也是斗争的工具,工具论是用政治实用主义取代艺术价值,产生了消极影响;三,早期美国左翼阵营把共产党等同于无产阶级、斯大林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苏联等同于社会主义,所以,美共领导人禁止作家发表批评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言论,致使左翼文学阵营内部严重缺乏民主气氛。法雷尔背后的主要支持者正是菲利浦斯和拉夫,这场争论不仅把纽约文人与高尔德等人的矛盾公开化,而且也预示着兴盛一时的美国左翼文学的退潮。 在菲利浦斯与拉夫看来,高尔德等人既缺少批评家的涵养,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新文学中探寻新的创作方法至关重要,这是批评家和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此意义上看,批评家的任务较之作家来说更为复杂。拉夫运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说法,指出左翼文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任意地把一个政党的文学装扮成一个阶级的文学。(21)他们呼唤一种艾略特式的批评与列宁的职业革命批评完美结合的先锋批评家,他们指出:“批评基本上是一种概念的分析,主要针对熟悉文学问题的读者。‘批评不是理性的激情,却是激情的理性’(马克思)。批评应该根据它的有效性、它的整体化的力量判定,而不是根据其热度或者易于接受它的读者的数量来判定。批评的转向是缓慢的……它最终以间接的形式抵达受众那里。”(22)这段话表明他们有意识地以建构新美学来推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1937年6月,在美共发起的“第二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菲利浦斯与拉夫彻底放弃幻想,与麦克唐纳、杜皮等人一道,公开挑战美共的文艺方针。他们在大会的讨论中把不同政见化入文学批评的话语中,大力推介托洛茨基,以此抑制党的文艺方针。到1937年10月,纽约文人与党的分歧越来越大,促使美共做出一项重大理论决定——与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二者已经没有对话的可能性了。 1937年底,他们脱离共产党自筹经费再办《党派评论》时,便立刻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他们在杂志上大张旗鼓地宣扬托洛茨基的文艺观点,刊登他的文章,进一步明确了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立场。由于得到了托洛茨基的肯定,纽约文人在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和推动现代主义方面获得了理论支撑,也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党派评论》复刊伊始,为了向公众表明与原刊物的承接关系,编辑部作出了再现工人阶级经验,吸收工人阶级读者的姿态,还开设了一个“穿越全国”的栏目,专门报道罢工、贫困等社会热点问题。拉夫认为丰富的无产阶级经验可以成为文学复兴的基础。不久,《党派评论》的编委们就公开转向,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放弃了他们早期承诺的保持同大众的联系,他们声言作为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革命阶级,可以替代大众。 独立后的《党派评论》卸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毫无顾忌地宣扬现代主义的激进美学。拉夫、菲利浦斯、麦克唐纳等人组成新编委会,他们热衷于欧洲的文化思想,贬损美国的自然主义文化传统,从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积极倡导现代主义文学。他们把早期对艾略特的评论中所升华出的感受力嵌进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中。1937年8月14日,《新群众》刊发了一篇题为《误贴标签的商品》的文章,声称公众被《党派评论》的编辑蒙蔽了。文章的作者把菲利浦斯与拉夫的言论与早期杂志的声明逐一进行对照,指出这些编辑毫不在意旧刊物的办刊宗旨,只是沿用原刊名而已,他们攻击共产党、“人民阵线”、美国作家联盟,推崇托洛茨基,参加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尽管他们未来的走向还不明朗,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新旧杂志之间没有任何联系。(23) 菲利浦斯与拉夫致信《新群众》,重申复刊后的《党派评论》秉承过去的办刊宗旨,使新旧杂志具有内在的连续性,从而确保了复刊后的《党派评论》延用原刊名。他们解释说,旧的《党派评论》从始至终也没有遵循相同的方针,而是边摸索边调整办刊方针与编辑队伍,而停刊与复刊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新群众》刊登了他们的来信,《工人日报》立刻登出《托洛茨基主义策划者的曝光》的文章加以反击。文章这样写道: 纽约的菲利浦·拉夫、弗雷德·杜皮作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已经被共产党开除,在去年的作家大会上,他们与一伙托洛茨基分子纠结在一起,并为他们投票,现在他们又联合其他知名的托洛茨基分子……阴谋策划玷辱过去的《党派评论》,并在这个名称下开办一份托洛茨基主义的文学杂志……他们现在希望在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风格中误导以前的《党派评论》的读者与支持者们订阅他们的托洛茨基杂志。他们占用这个刊名,他们允诺尊重旧的《党派评论》。他们的伪装在公众的眼光中是站不住脚的。(24) 《党派评论》的编辑们并不屈服来自美共的指责,批评共产党让文学隶属于政治,缺少雅量容纳异己,使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展为“真正的文化官僚”。孤立中的《党派评论》联合《日晷》、《小评论》、《猎犬与号角》等小杂志,大张旗鼓地宣扬现代主义的美学反叛,毫不妥协。 菲利浦斯与拉夫也在《政治十年中的文学》(1937)一文中,首次公开承认了这一转向,并且公开放弃他们过去提出的文学历史分期,即当代文学分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三个历史时期,而无产阶级文学是前两者的综合。(25)他们指出,30年代中期的无产阶级文学把人压缩成自身的一部分,不过是用文学的政治人替代非政治人,因而无法革新美国的文学意识。普通的无产阶级小说囿于实用主义模式,与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说没有区别,不过是用集体替代了个人。有鉴于此,他们才大力倡导现代主义文学用于激进政治,实现美学激进与政治激进的结合。 1939年,拉夫在《无产阶级文学:一种政治的剖析》中,再次重申了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否定。共产党让作家投身到无产阶级运动和“人民阵线”中,文学成了政治的急就章,“无产阶级文学是一个党派的文学改装为一个阶级的文学”(26)。在拉夫看来,共产党是运动的组织者、终极诉讼法庭,大大小小的左翼刊物都是共产党资助的,他们委派政治委员指导文学运动,规范其理论发展方向,并让作家在他们的控制中认识苏联——最高的权威。实事求是地看,拉夫的看法过分夸大了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操控。事实上,到了后期美共并不特别关注文学问题,而是关注重大政治问题。《党派评论》之所以能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存在,本身就说明美共允许一定程度的争论,尽管是在有限范围之内。 如此一来,《党派评论》就处在犹太裔、托洛茨基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三种张力中,同时又受到美共的打压。然而,杂志却绝处逢生,究其原因有几点:一,《党派评论》秉承思想自主与独立的理论追求,使它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超然于政治组织和运动之外,迫使他们从理论上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活力。二,杂志主力在革命的政治视阈中坚持文学独立性,“任何杂志……渴望在先锋文学上获得一席之地,思想倾向上都将是革命的”(27)。他们指出,尽管杂志担负着普遍意义上的革命,但是,文学也应该独立于宗派与政党之外。他们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它不再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理论或知识体系,也不是一套特殊的价值体系,而仅仅是一种分析与评价文学的方法。《党派评论》本身就是要呈现这一方法的灵活运用。正是这种综合的历史文化批评风格使杂志立于不败之地。三,纽约文人与《党派评论》在各种政治势力与文学的自由诉求之间不愿妥协与让步,他们既不承载斯大林主义,也不承载有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由此吸引了众多的自由知识分子,而这些人正是30年代中后期纽约呼声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杂志也因此而获得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力量,成为重要的非官方左翼喉舌,从而确保了杂志的知识权威性。综合起来看,以菲利浦斯和拉夫为代表的纽约文人,围绕着《党派评论》所展开的文学批评活动是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开始的,他们逐渐发展为官方左翼的最早批判者,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文学批评最终成为美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表述。 四、结语:构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自20世纪30年代起,菲利浦斯与拉夫以《党派评论》为阵地,通过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评论,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匡拘,开创了美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体说他们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如下特征。 一,从批评背景上看,菲利浦斯与拉夫是从自由主义文化导向持异见的美国激进文化的,因此,他们所开展的批评不过是一种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的文化批评。这种打上深刻自由主义思想烙印的批评,必然与官方左翼相龃龉。经过剧烈的思想碰撞之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所倡导的精英主义与无产阶级相互协调的观点,一方面拒斥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继续挖掘现代主义文学内蕴的反叛性,力求美学激进与政治激进相互贯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美国文化底色,为他们日后回归自由主义预留了一条后路。 二,从批评着眼点上看,菲利浦斯与拉夫都坚信无产阶级文学兴旺的可能性,但读者是关键,这使他们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批评家。当时威尔逊、考利、范德威克、门肯等人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主张着眼于传记和社会背景的分析;新批评的退特、兰色姆、布莱克默则侧重于文学文本形式技巧的分析。虽然新批评固守文本的做法在早期菲利浦斯与拉夫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到,但他们及时调整批评方向,把文本之外的经验、特定阶级的利益和读者等因素及时纳入批评视阈,从而摆脱了新批评的狭隘性。 三,从批评旨趣上看,菲利浦斯和拉夫高度重视艾略特的文艺观,但是,他们并不完全认同艾略特的精英主义,而是积极“教化”大众。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能够填平资产阶级文化鸿沟,让大众接近高雅文化;无产阶级的感受力可以打造高质量的劳动阶级的文艺作品。他们确信一种积极的个人感受力可以在一定范围的社会进程中汲取力量,并在新的视阈中变为现实,为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定基础。 四,从批评目标上看,菲利浦斯和拉夫竭力协调现代主义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关系。他们冒着从根本上扭曲无产阶级文学意图的危险,在左翼阵营中大力提倡借鉴现代主义艺术经验,他们把自己的批评努力视为正在为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文艺奠定基础。诚如美国学者高德贝克所言:“阶级斗争在真实与心理方面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便是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主题。资产阶级作家必然先批判后保守;无产阶级作家必然先破坏后建构。他是一位开拓者,开拓者必须具有创造性。”(28)当时菲利浦斯与拉夫敏锐地体察到无产阶级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内在精神的相似性。美国学者沃尔德也认为在整个30年代拉夫和菲利浦斯试图探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而此时共产国际和美共的追随者只会用简单的口号和斯大林主义的术语对革命作家和批评家进行指导。(29)然而,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他们难以实现这一愿望。不过,正是这种辩证的批评视野,以及与同时期其他批评派别的分道扬镳,才促使纽约文人形成自己独特的批评。 五,从历史角度看,纽约文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不仅使他们在摆脱庸俗决定论、反映论时,汲取到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资源,而且更让他们在阐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革命性的基础上,实践了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即扬弃了反映论,而注重过程,强调阐发力量、趋势和矛盾——这些因素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体现出一幅总体性的客观历史力量。换言之,菲利浦斯与拉夫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强调感受力、共鸣、独创,与同时期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联,这也为研究者留下了丰富的话语空间。 注释: ①Philip Rahv,"The Literary Class War",New Masses 8,2,August 1932. ②Philip Rahv,"An Open Letter to Young Writers",Rebel Poet 16,September,1932. ③Philip Rahv,"T.S.Eliot",Fantasy 2,3,Winter,1932. ④Ibid. ⑤Wallace Phelps,"Classical Culture",Communist 12,1,January 1933. ⑥Wallace Phelps,"Categories for Criticism",Symposium,1,January 1933. ⑦Wallace Phelps,"Sensibility and Modem Poetry",Dynamo 1,3,Summer 1934. ⑧刊物《专题论丛》(Symposium)从1930年到1933年发行,由伯纳姆(James Burnham)、莱特(Philip W.Wright)负责编辑。 ⑨Wallace Phelps and Philip Rahv,"Editorial Statement",Partisan Review 1,1,February-March 1934. ⑩Ibid. (11)T.S.Eliot,The Sacred Wood: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Methuen,1980,pp.63-64. (12)T.S.Eliot,The Sacred Wood: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Methuen,1980,pp.170-171. (13)Philip Rahv,"How the Waste Land Became A Flower Garden",Partisan Review 1,4,September-October 1934. (14)Wallace Phelps and Philip Rahv,"Criticism",Partisan Review 2,7,April-May 1935. (15)Wallace Phelps and Philip Rahv,"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Partisan Review 1,3,June-July 1934. (16)Michael Gold,"American Intellectual and Communism",Daily Worker,October 12,1923. (17)Jack Conroy,The Worker as Writer,American Writers' Congress,Henry Hart,ed.,Internatinal Publishers,1935,p.83. (18)Michael Gold,"Proletarian Realism",New Masses 6,September 1930. (19)Joseph Freeman,An American Testament:A Narrative and Romantics,Farrar and Rinehart,1963,p.636. (20)Granvill Hicks,"The Crisis in American Criticism",New Masses 9,Feb,1933. (21)Philip Rahv,"Proletarian Literature:A Political Autopsy",Southern Review 4,3,Winter 1939. (22)Wallace Phelps and Philip Rahv,"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Partisan Review 1,3,June-July 1934. (23)Falsely Labeled Goods,"Editorial",New Masses 24,12,September 14,1937. (24)Trotzkyist Schemers,"Exposed",Daily Worker,October 19,1937. (25)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Literature in A Political Decade",in New Letters in America,ed.,Eleanor Clark and Horace Gregory,Norton,1937,pp.174-175. (26)Philip Rahv,"Proletarian Literature:A Political Autopsy",Southern Review 4,3,Winter 1939. (27)"Editorial Statement",Partisan Review 4,1,December 1937. (28)Barbara Foley,Radical Representations:Politics and Form in U.S.Proletarian Fiction,1929-1941,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p.62-63. (29)Alan Wald,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ti-Stalinist Lef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p.79.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艾略特论文; 教条主义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