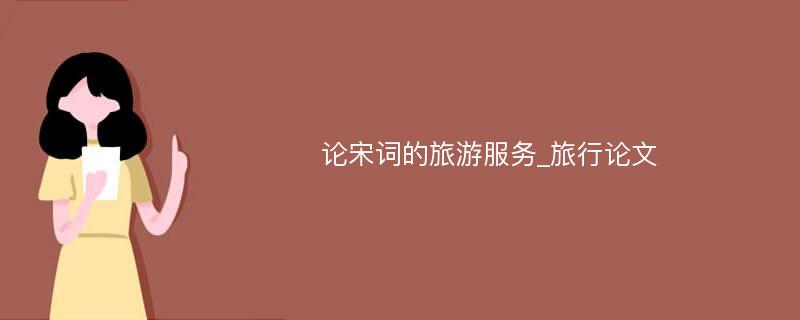
論宋詞的羈旅行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行论文,論宋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羈旅行役,是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傳統題材,但爲何在宋詞中這個題材内容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爲何在宋代,凡作詞的人大抵都寫作過涉及這個題材的作品?爲何作爲宋詞「新聲」而獨具創造性貢獻的柳永「尤工羈旅行役」?這其中有何玄秘?歷來人們只是議論到這個話題,或是僅對柳永的羈旅行役作品的寫作規律或成因做出論析探究。鮮有人對宋人在這個題材的偏愛上做出全面掃描和透視。本文試圖由歷時性和共時性的兩個視閾,將羈旅行役題材擺在縱横坐標軸上進行全方位文化觀照,以追索宋詞羈旅行役題材之所以爲宋人鍾愛的文學創作心理動因,以期從具體作品入手,重新審視宋型文化造成宋代文人行爲心理羣體無意識,並對文人創作傾向進行誘導,從而使宋代文人在創作題材選擇方面向羈旅行役主題偏移的事實。
詩歌寫羈旅行役,其淵源可以追溯到《詩三百》。其中《小雅·采薇》就是一篇典型的「羈旅行役」之作。在這首詩中,抒情主體寫了漂泊的原因「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也表示了自己意識到了身上的社會責任:「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但漂泊是辛苦和痛苦的:「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當然,像這首《采薇》,也具有「軍旅題材」的屬性,讀者可以品出其中家國意識與個體意識一致性的精神——這就是「玁狁」(敵人)的入侵,造成自己「靡室靡家」,而自己「載渴載饑」地奔波操勞,雖然「傷悲」,郤並無太大怨憤——這是由個體的生命價值與社會羣體共同價值的同一性所決定的。
爾後兩魏漢魏晉文人的「羈旅行役」之作,主旨有一些變化。如漢代無名氏的《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胡地多飈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悲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主要表述離家漂泊的痛苦。而其中「心思不能言」,正有許多不便明説和不願直説的傷痛與悲戚。當與那個時代世逢亂離、文人找不到出路、百姓漂流失所、許多人無國無家可依的社會現實有關。《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凜凜歲雲暮」[一]亦屬羈旅行役的篇什,其游子思鄉或戍客念遠的内容,增添了作品的感染力和人情味,是中國古代詩壇羈旅行役題材的代表作品。
唐代詩國的羈旅行役篇什,雖然算不上唐詩舞臺上的重頭戲,但也是人們經常吟詠的一個主題。(據初步統計,「羈旅」一詞在《全唐詩》中出現六十八次)唐詩中所涉及的此類題材,可以囊括前代同類題材吟詠範圍,並表現出唐代獨有的時代風貌。
如孟浩然《宿桐廬江寄廣陵舊游》:「山暝聞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游。還將兩行淚,遥寄海西頭。」李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除了表述漂泊的孤獨、寂寥外,還抒發了詩人對遠方朋友或借宿房東的友情或謝意——這與唐人普遍重視友誼與親情的時代風尚有關。當然,這類題材在唐詩中也以感時傷懷,自嘆身世者爲多。如杜甫《旅夜書懷》:「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久客》:「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横。」前者嘆老嗟卑,自傷飄零;後者於羈旅中有感於世態炎涼,表達對社會時局的憂慮和感傷。不過「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及「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數句,以及「王粲」、「賈生」的自況,已經涵融作者對個體存在的價值思考。戴叔倫《客中言懷》:「白髮照烏紗,逢人只自嗟。官閑如致仕,客久似無家。夜雨孤燈夢,春風幾度花。故園歸有日,詩酒老生涯。」也是在個體價值失落的嗟嘆中,想通過對「故園」舊夢的追尋,實現精神的超越。中晚唐以後,不僅羈旅行役題材的吟詠增多,其思想内容也往往由自嗟飄零而感時傷亂,但對個體「存在」與「價值」的思考,也往往嵌入其間。如張籍《羈旅行》:「遠客出門行路難,停車斂策在門端。荒城無人霜滿路,野火燒橋不得度。寒蟲入窟鳥歸巢,僮僕問我誰家去。行尋田頭暝未息,雙轂長轅礙荊棘。緣岡入澗投田家,主人舂米爲夜食。晨鷄喔喔茅屋傍,行人起掃車上霜。舊山已别行已遠,身計末成難復返。長安陌上相識稀,遥望天山白日晚。誰能聽我辛苦行,爲向君前歌一聲。」杜荀鶴《旅寓書事》:「日日驚身事,悽悽欲斷魂。時清不自立,髮白傍誰門。中路殘秋雨,空山一夜猿。公卿得見面,懷抱細難言。二刚者的「身計未成」「長安陌上相識稀」,後者的「時清不自立,髮白傍誰門」都是在羈旅中嘆息個體存在之價值的失落,但如何實現自我的超越,郤没有明確答案。杜儼的「書劍催人不暫閑,洛陽羈旅復秦關。容顏歲歲愁邊改,鄉國時時夢裏還。」[二]庶幾能代表唐代羈旅行役題材中關於唐人「存在」與「價值」的思考。讀書和習武,委實是唐代青年普泛的功課;成就功名事業,也只有這兩個途徑。讀書爲了進士及第從而進入仕途;學劍則爲了將來有機會去邊塞立功受封——「書劍催人」,是之謂也——這就是唐人的價值追求。無論追求能否實現,「洛陽」「秦關」的「羈旅」是無法逃避的人生命運;「容顏」的逐漸衰老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而對故鄉的思念,也只有托諸夢境了!這就是唐人在個人價值實現中的精神失落。這裏强調的作者的「失落」感,似乎有某種不可超越性。因爲它不是價值追求不到的憂悶和壓抑,而是一種終極關懷的失落。這正符合唐代知識分子在價值追求中比較在意於外部價值的實現這一時代文化價值選擇的特徵。當然,這一特徵在中晚唐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譬如李商隱通過無題詩對愛情的吟詠以求超越仕途失落的牢愁;杜牧採取自嘲的手段化解政治仕途價值失落的苦悶;温庭筠則通過放浪形骸、詩酒自娱以在傳統價值的頹然崩析中實現自我精神的超越……
宋詞中羈旅行役成爲很常見的題材[三],幾乎凡有詞作傳世的宋代詞人,都寫過以此爲題材的作品。其内容和吟詠主題與唐詩比較,則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以下將其分爲三種類型分論之:
(一)羈旅漂泊中對紅粉佳人的思念
在宋詞中,此項内容佔了羈旅行役作品相當大的比重。如北宋晏殊的木蘭花「绿楊芳草」、范仲淹的代表作蘇幕遮「碧雲天」、歐陽修的代表作踏莎行「候館梅殘」、柳永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等都屬此類題材的典範作品。下面看看李之儀的踏莎行:
一别芳容,五經寒暑。回文欲寄無鱗羽。多情猶自夢中來,向人粉淚流如雨。 夢破南窗,愁腸萬縷。那聽角動城頭鼓。人生彈指事成空,斷魂惆悵無尋處。
在人生漂泊的旅途,斷魂無根,萬事成空,唯一可以告慰心靈的,只有佳人的「芳容」和「粉淚」了。難怪秦觀在「霧失樓臺」後,有「砌成此恨無重數」[四] 的浩嘆;「亘古男兒一放翁」[五] 的陸游,在「淒涼又作它鄉客」時,也只得遥想佳人「料也應、紅淚伴秋霖,燈前滴」[六]了。再看看宋代不是很出名的詞人蔡伸的滿庭芳:
煙鎖長堤,雲横孤嶼,斷橋流水溶溶。憑闌凝望,遠目送征鴻。桃葉溪邊舊事,如春夢、回首無踪。難忘處,紫薇花下,清夜一尊同。 東城,携手地,尋芳選勝,賞遍珍叢。念紫簫聲闋,燕子樓空。好是盧郎未老,佳期在、端有相逢。重重恨,聊憑紅葉,和淚寄西風。
在羈旅漂泊中「目送征鴻」時,想到的即刻是「桃葉溪邊舊事」。這與唐人在漂泊中往往思念家鄉的心情大不一樣。究其原因,第一,宋人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即由唐人對外在的功名事業的關注而轉變爲内在的對個體存在以及生活質量的關注;第二,宋人關於生活質量高低與優劣的評價尺度發生了改變,他們比唐人更爲依戀家庭和妻妾。在宋人心目中,温暖、欣慰的家庭和可人、秀雅的如花美眷,是他們人生的歸依和漫漫苦旅中的重要伴侣,尤其在仕宦逆旅更是如此。如柳永歸朝歡:
别岸扁舟三兩隻。葭葦蕭蕭風淅淅。沙汀宿雁破煙飛,溪橋殘月和霜白。漸漸分曙色。路遥山遠多行役。往來人,隻輪雙槳,盡是利名客。 一望鄉關煙水隔。轉覺歸心生羽翼。愁雲恨雨兩牽縈,新春殘臘相催逼。歲華都瞬息。浪萍風梗誠何益。歸去來,玉樓深處,有個人相憶。
詞人在「路遥山遠」的「行役」中對「利名客」的鄙夷,最終導致對「浪萍風梗」漂泊價值的全盤否定;這種「歲華」「瞬息」而毫無益處的漂泊,實質上是詞人個體價值失落的一種表述方式。所以在「愁雲恨雨」的牽縈中,詞人「歸心」插上了翅膀,飛到「玉樓深處」,與那位「相憶」着自己的人相遇了——詞人在羈旅漂泊的失落中,終於在「玉樓」佳人那裏找到歸宿。第三,北宋黨禍、南宋異族入侵,給知識分子心靈投下灾難陰影;仕途險惡,命運難料,更讓他們無所適從,只有從温柔富貴之鄉去尋求心靈的栖息之地。如秦觀將身世之感打併入艷情、黄庭堅遷謫途中贈歌女陳湘之作等,便是北宋黨禍造成舊黨人物精神痛苦而結下的果實。蔣捷賀新郎《兵後寓吳》則是南宋異族入侵,在文人心靈投下灾難陰影的寫照:
深閣簾垂绣。記家人、軟語燈邊,笑渦紅透。萬叠城頭哀怨角,吹落霜花滿袖。影厮伴、東奔西走。望斷鄉關知何處,羨寒鴉、到著黄昏後。一點點,歸楊柳。
相看只有山如舊。嘆浮雲、本是無心,也成蒼狗。明日枯荷包冷飯,又過前頭小阜。趁未發、且嘗村酒。醉探枵囊毛錐在,問鄰翁、要寫牛經否。翁不應,但摇手。
詞人在後「兵後」東奔西避,「望斷鄉關」,看到的是寒鴉點點,浮雲變幻,山河依舊,人事蒼涼。縱經綸滿腹,可又有何用?連給農家寫「牛經」的請求也被拒絕。所以心靈唯一可以慰藉的,便是「記家人、軟語燈邊,笑渦紅透」了。词一開首便點明此意,正可凸現亂後詞人在人生絕望的價值失落中,僅能够憑借對家中紅顏眷屬的憶念而實現精神的超越。第四,宋代的庶民文化構型已經開始改變男權社會對女性成員的歧視與偏見,女性的社會成員資格正得到進一步的確認;在丈夫心目中,妻妾作爲人生伴侣的意識,已經成爲宋代多數知識分子的共識——這一點,尤其是唐代無法比擬的。第五,宋詞的繁榮,促使宋代社會歌兒舞女的人數朋增;歌兒舞女的妙喉美姿和淪落風塵的命運,又使得落魄士子將其引爲紅顏知己……如蔡伸唱道:
風卷龍沙,雲垂平野,晚來密雪交飛。坐看闌檻,瓊蕊遍寒枝。妝點蘭房景致,金鋪揜、簾幕低垂。紅爐畔,淺斟低唱,天色正相宜。 更闌,人半醉,香肌玉暖,寶髻雲欹。又何須高會,梁苑瑶池。堪笑子猷訪戴,清興盡、忍凍空回。仍休羨,漁人江上,披得一蓑歸。(滿庭芳)
詞人在這裏所强調的,在於對人的生存狀態之選擇。他認爲高官厚禄,聲名顯赫的富貴不必追求;爲士大夫盛贊不已、「乘興而游,興盡而返」的倜儻高士王子猷的行爲則十分可笑;清高孤傲,獨釣寒江的忘世漁翁,也不值得羨慕。他肯定的理想生活是:在「蘭房」中、「簾幕」下、「紅爐畔」,有「香肌玉暖,寶髻雲欹」的佳人「淺斟低唱」——直到「更闌」,還陪伴着「半醉」的自己度良宵。宋人這種心態,決定了他們在羈旅漂泊中對紅粉佳人的思念,自然成爲詞之寫作中進行題材選擇的一項主要内容。
(二)羈旅漂泊中的鄉關之思
鄉關之思,是中國古代詩歌最爲常見的題材。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關係密切。儒家文化,實質上是以國家爲本位、以宗法制家族爲基礎的社會文化構型——家國觀念,落到文化個體心靈小而化之,很大程度上就是家庭觀念——齊家、治國,對家庭的責任感和無窮的依戀,成爲恪守儒家教規的傳統中國人性格積澱中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如中秋佳節的團圓意識,春節闔家吃「團圆飯」等,這象征一年全家人幸福與欣慰的最隆重慶典,無不浸透了華夏子民對家庭的無條件依戀和牽掛的拳拳深情!這種深情厚愛,可以説已經昇華爲中國人的一種宗教情懷。這是其一。另外,道家文化的自然哲學觀念,將人們引向古樸淳厚的大自然。「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七]加上這位五柳先生在《桃花源記》中爲人們創造了一個小國寡民的出世烏托邦,中國古代讀書人便找到了回歸鄉土、歸隱田園的理論依據和實踐範型。中國人對故土的依戀,對家園的神往,就不僅僅是對家庭的一種責任感和一種依戀情懷,而且是一種生命的回歸意識,是人對個體生命的終極超越。這是其二。由於宋人的文化價值觀趨向多元和世俗,文化思考也變得深沈與執着,所以宋詞中此類羈旅漂泊中的鄉關之思在進行藝術的再現和表現時,也折射出鮮明的時代色彩。如陳德武望遠行:
城頭初鼓,天街上、漸漸行人聲悄。半窗風月,一枕新涼,睡熟不知天曉。最是家山千里,遠勞歸夢,待説離情難覺。覺來時,簾外數聲啼鳥。誰道。爲甚新來消瘦,底事懨懨煩惱。不是悲花,非干病酒,有個離腸難掃。悵望江南,天際白雲飛處,念我高堂人老。寸草心、朝夕怎寬懷抱。
作者的「離情」重在「念我高堂人老」,即是説,詞人「鄉關之思」的對象是家中老年父母。這在詞人惜餘春慢一種思情最長,萬叠江山,怎生遮斷。向北堂見了,忘憂萱草,此心方滿」一句中的意思是一樣,體現了宋人鄉關之思的一個特色——拳拳的赤子之情。儘管「孝」是儒家人倫規範中的一項主要内容,讀書人也將孝慈之心作爲人倫之本,但詩中直道這類「最長」「思情」的,確實不多,在唐詩中也少見。宋代庶民文化的多元價值選擇,體現在家族觀念方面,不像以往注重以宗法爲本位的祖宗崇拜,而是將對父母的孝心世俗化爲一種對個體精神失落後的超越情懷。也即是説,詞人是在人生失意的漂泊中,將父母作爲一種可以依傍的感情對象憧憬與向往,從而實現個體精神對象化的情感超越。另外如宋代特多壽詞,尤其爲父母慶贺壽辰的詞作很多,甚至大大超過宋以前這類題材的總和。可以從側面印證宋人羈旅行役作品爲何多詠嘆孝親的赤子之情這個基本事實。
所以,抒發鄉關之思的這類羈旅行役作品往往像孩子失去家長的關愛一樣,浸潤着人生的一種憂患,表現出深切的孤獨感、失落感、飄零感、迷茫感甚至絶望感。如晁端禮醉蓬萊:
乍酒醒孤館,夢斷幽窗,嫩涼天氣。瀟灑情懷,想鄉關迢遞。一枕清風,半簾殘月,是悶人滋味。南浦離多,東陽帶緩,新來憔悴。因念當時,亂花深徑,畫楫環溪,屢陪歡醉。踪迹飄流,頓相望千里。水遠山高,雁沈魚阻,奈信音難寄。吟社闌珊,酒徒零落,重尋無計。
上片寫羈旅飄零、客居他鄉時,遥「想鄉關」而感受到孤獨、鬱悶,遂體味到心靈的「憔悴」;下片憶念昔日的「歡醉」而「重尋無計」。在此種無可奈何的失落中,也只有通過填詞寫出内心的鬱悶,從而讓積鬱得以宣洩,以圖實現情感的超越。柳永則在「游宦」的「羈旅」中,遥望鄉關,恨不得立即「歸去」:
遠岸收殘雨。雨殘稍覺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靜,立雙雙鷗鷺。望幾點、漁燈隱映蒹葭浦。停畫橈、兩兩舟人語。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煙樹。 游宦成羈旅。短檣吟倚閑凝伫。萬水千山迷遠近,想鄉關何處。自别後、風亭月榭孤歡聚。剛斷腸、惹得離情苦。聽杜宇聲聲,勸人不如歸去。(安公子)
歸家的意念,往往與歸隱的念頭同時萌生。如秦觀石州慢《九日》:
深院蕭條,滿地蒼苔,一叢荒菊。含霜冷蕊,全無佳思,向人摇绿。客邊節序,草草付與清觴,孤吟只把羈懷觸。便擊碎歌壺,有誰知中曲。 凝目。鄉關何處,華髮緇塵,年來勞碌。契闊山中松徑,湖邊茅屋。沈思此景,幾度夢裏追尋,青楓路遠迷煙竹。待倩問麻姑,借秋風黄鵠。
所以,宋人的「羈懷」儘管發生的觸媒各異,但表現的情緒郤大致相似或相近。而最終歸結爲退隱出世的精神超越。
(三)羈旅漂泊中的出塵恬退之想
歸家之念的最終表現方式,必然是退隱林泉山野,實現遠離紅塵的、形與神的終極超越。這種陶淵明式的人性關懷,在宋代獲得了知識分子普遍的文化認同。考其原委,大致四端:1.宋代雖説仁宗務本禮道,重視儒學之教,但由真宗煽起至徽宗尚且熾熱的崇尚道教的熱潮,爲老莊之學的盛行大造聲威,也爲道家哲學的普及和道家精神的世俗化提供了上層權力的絶對支持;2.宋代庶族文化的構型,決定了國民的價值取向偏重於個體與家庭,對父母、妻子、兒女的依念與深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替代唐代如杜甫、李白等對於朝廷、皇上的至情深愛;3.北宋的新舊黨爭,在正直耿介的士子思想及生活、行爲中造成的精神打擊是深刻而久遠的。在近半個世紀中,時而新黨執政,時而舊黨掌權,無論哪一派在臺上,總有一派遭受打擊迫害。這部分文士,在政治的失意後,都萌發歸田退隱之想。哪怕某些人内心深處並不樂意退避,也不甘願蒙屈受辱,但面對殘酷的現實,也只得暫時用歸隱恬退的方式,來平衡自己的心態和逃避更慘烈的打擊迫害;4.北宋末的靖康之變,將宋朝分裂爲南北兩半,北宋的滅亡,造成宋代士大夫精神的震撼比新舊黨爭造成的心靈創傷來得更爲强烈和深刻。尤其是高宗朝,岳飛忠義父子及其他岳家將的被禍,以及主戰派接二連三的遭受迫害,使得很多士子「摇首出紅塵」[八],不願意再與投降主和的南宋統治者同流合污,從而走進漁村山野,去尋求靈魂對於大自然的回歸。隨着南宋朝廷對於蒙古族入侵的節節敗退,以致最終滅亡,這種文人習氣與創作風潮,到南宋末年愈演愈烈。所以,自北宋初到南宋末,歸隱恬退,是文人們經常吟唱的主題;在羈旅行役的題材中,這類詞作更是佔了較大比重。
如北宋初被人們稱爲「尤工於羈旅行役」[九]的柳永,在羈旅漂泊中,感嘆「走舟車向此,人人奔名競利」(定風波),「往來人,隻輪雙槳,盡是利名客」《歸朝歡》,因而決心「醉鄉歸處,須盡興,滿酌高吟。向此免、名繮利鎖,虚費光陰」(夏雲峯)。可説是北宋詞人這類題材寫作動機的一番表白。如李之儀的朝中措:
臘窮天際傍危欄。密雪舞初殘。表裏江山如畫,分明不似人間。 功名何在,文章漫與,空嘆流年。獨恨歸來已晚,半生孤負漁竿。
其中「功名何在,文章漫與,空嘆流年」的嘆息,正是一種個體價值失落後的精神迷惘,而要從這種迷惘中超越,又只有回到自己人生初始的出發點——那就是早年的疏樸淡泊的平民生活,在詩人的傳統抒情模式中,代表這種生活的象徵性符號,就是「田園」和「漁樵」——即「山中」和「漁竿」了。李氏在同詞牌題爲《樊良道中》的詞作中所謂「敗荷枯葦夕陽天。時節漸闌珊。獨泛扁舟歸去,老來不耐霜寒。 平生志氣,消磨盡也,留得蒼顏。寄語山中糜鹿,斷雲相次東還」則正是歸往「山中」的宣言。在同一個人的同調兩首詞作中,一處表示要「歸來」「漁竿」,一處表示要「東還」「山中」,表明作者退隱心情的迫切和執着。
到了南宋,羈旅行役題材中歸隱恬退的内容更是隨處可見。前期和中期,除了朱敦儒之外,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數陸游、辛棄疾兩位執着於儒家事業的忠貞耿介之士了。他們兩人均不屬那種嘯傲忘世的閑散人物,也不屬那種自甘淡泊的林下名士,但他們到了中晚年,每當人在旅途,就發出儒冠誤身、恨不早早「歸耕」的嘆息和牢骚。如陸游唱道:
山村水館參差路。感羈游、正似殘春風絮。掠地穿簾,知是竟歸何處。鏡裏新霜空白憫,問幾時、鸞臺鳘署。遲暮。漫憑高懷遠,書空獨語。自古。儒冠多誤。悔當年、早不扁舟歸去。醉下白蘋洲,看夕陽鷗鷺。菰菜鱸魚都棄了,只换得、青衫塵土。休顧。早收身江上,一蓑煙雨。(真珠簾)
在這裏,詞人的情感是激憤和悲愴的,他在宦途羈旅中體味到的這種「菰菜鱸魚都棄了,只换得、青衫塵土」的人生之失落感,的確難以用言辭予以表達。所以其中「自古。儒冠多誤。悔當年、早不扁舟歸去」的感喟,就不是一般的發牢騷,而是痛徹心脾地對現實生活的徹底否定和唾棄。「收身江上」,爲時已晚,悔不早早「扁舟歸去」——「竟歸何處」?詞人自己也迷惘。所以説,他們只不過是在人生的失落中,借歸隱和恬退,實現精神對現實的超越。
辛棄疾早歲便懷有逐鹿中原、掃蕩胡沙、收復北宋失地、「整頓乾坤」的少年壯志,年紀輕輕就起兵南歸。但南歸後,郤再也没有一展抱負的機會,反而數次罷黜,兩度閑居,每次賦閑十餘年。在這種難堪的際遇中生活,即便是鑽石寶刀也會生銹。所以詞人在孤淒的漫漫旅途,體味出了老莊哲學的深意和真味:
不向長安路上行。郤教山寺厭逢迎。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寧作我,豈其卿。
人間走遍郤歸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鷓鴣天《博山寺作》)
「從宋代詞史的發展脈絡尋繹,稼軒詞中這類頹放嘯傲的格調,是南渡後朱敦儒等詞作風格的繼響。比稼軒稍早出,以氣節名世的范成大、楊萬里等詩歌創作成就傑出,然而詞作亦常常表現出一種蕭散淡泊的出塵之趣,同樣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扭曲,在志節名士心靈上投下陰影。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互補機制的作用,在社會遭異族踐踏的大變動的擾攘時局中,人們有對惡勢力的抗爭,也有在抗爭中受朝廷權奸掣肘後的失落,有奮其智能爲民族而戰的豪情,也有正義和理想在冷酷現實的礁崖上粉碎後的傷心與頹唐。在豪傑之士的失落與頹唐中,往往潛在於文化積累中的老莊超脱達觀與佛學禪退的文化意識會露出頭角,爲緩和與化解鬱結於心的痛楚而蠕動於作者的意識之中,並形諸筆墨。這種文化性格的矛盾衝突,是中國傳統文化固有機制所決定的。中國文學史上各階段都有一批正直文人陷在這一文化性格的兩難處境中挣扎,未能獲得終極超脱。」[一○]
到了南宋末,隨着大宋趙氏皇權太陽的最終墜落,宋代士子的家國失落感像瘟疫一樣散漫開來,而這種超個體的價值失落的絶對值,遠遠大於以往的任何時期——這就是宋亡後演化成的所謂「遣民心態」。在這種心態狀況下的宋末知識分子羣落,具有一種更爲普泛而深切的隱遁意識——此時不再僅僅是對家山、漁樵的皈依之願望,而是一種失郤家園、無處栖遲的絶望——一種萬劫不復的、無枝可依的痛苦與彷徨。所以這個時期的羈旅行役之作,幾乎無一不浸透着皈依莊老,收身江湖,向慕山野林泉的强烈情緒。宋代文化的多元選擇,終於讓文人們在無路可走之時,尋找到一扇唯一的自我超越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