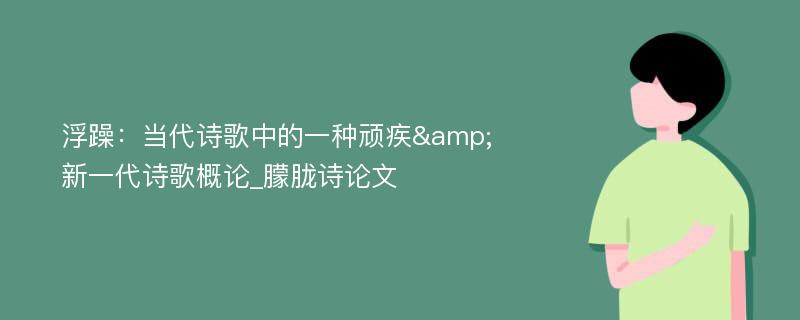
浮躁:当代诗坛的顽症——“新生代”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顽症论文,新生代论文,浮躁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需要英雄的时代造就不出自己时代的英雄,是时代的一种悲剧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需要史诗的时代,创作不出时代的史诗也是时代的一种悲剧。
为什么史诗的时代出不了史诗?我以为10年来在诗坛上有一个神秘的幽灵一直在徘徊着,时隐时现,这个幽灵不是别的,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浮躁情绪。这种浮躁情绪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无时不在。是当代诗坛难以制服的顽症。
浮躁表现之一:否定的极端化。当年朦胧诗派向传统诗扔下决斗的白手套时,那种与传统诗决裂所表现出的不驯服姿态,就曾给人以某种浮躁之感。近日闲来无事,顺手翻阅1991年8月在艾青诗歌国际研讨会上得到的周红兴同志赠阅的《艾青的跋涉》一书,书中对当年的那种“不驯服”,有过这样的披露:“终于/我们站起来对艾青说/你们的太阳已经过去/我们的太阳正在升起/你们这一代诗人代表不了一代诗人的我们……”,“你和你的诗歌正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死去,在一代人当中死去,我们要趁你还活着的时候把你的牧歌送进火葬场……”
……
“艾青,已是历史的陈迹。
老人,既然你这样颤巍巍的,你就别在我们中间挤了”。读者一定会看到,当笔者还没有把挑战者所有的言论一一引述下来的时候,那种挑战者对传统“不驯服”的姿态,那种躁动不安的骚动情绪,已经溢于言表了。
当然,这种以骂倒名人自己出名的人,或许根本就不着朦胧诗派的边际,或只是其中极个别分子,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历史的“陈迹”,就同“朦胧诗”本身也变成了历史的“陈迹”一样。尽管朦胧诗人们当时的呼喊代表着一代人的历史命运,代表着整整一代青年的追求、苦闷、彷徨和探索,是与时代合拍的、与人民共鸣的,只是在诗的手法上有些新探索,吸收了人们感到陌生的意象、象征、暗示等方法,有时甚至是直搬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而一时引起人们的轩然大波。现在有人把朦胧诗划为传统诗一列,正是基于朦胧诗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内容这点而言的。其实,当朦胧诗人们向传统诗扔下决斗的白手套时,当时就缺少必要的冷静,就没有认真地分析一下它们之间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起码是他们都承认诗的社会性,诗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其实,朦胧诗人们只不过是仅仅找到了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现方法,钻进了意象的迷宫,却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于是便高喊着代表了新诗发展的方向。
其实,就连表现方法,也并非完全是他们自己独特的发现。这点,笔者已经在《朦胧诗纵横谈》一书中,对艾青的《树》和舒婷的《致橡树》在意象构成上作了比较,说明了它们之间的承接关系,同时又引证了艾青的原话,借以说明朦胧诗派某些人,一方面想把艾青的诗送进“火葬场”,一方面还在“抄袭”他的作品,对他的诗进行“打砸抢”(详见《朦胧诗纵横谈》第159页)。这些都说明了当年的朦胧诗派,在宣布与传统诗决裂时,还没有看到自己与传统诗连接的脐带还没有剪断,从而多少显得有些不够冷静,有些浮躁了。
事隔几年,这种浮躁情绪又在诗坛上涌动着,奔腾着,这就是“新生代”对朦胧诗的挑战。
作为80年代初期以后诗坛主潮的朦胧诗,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他们的主将还都以自己的诗作显示着他们各自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朦胧诗已经开始渐次式微了。如果说一开始朦胧诗人们的呐喊,多少代表了大众的声音的话,那么到这时,他们当中的有的人,就开始以个人英雄主义悲剧主角出现了,远离了人民大众,走进了自己狭窄的小胡同。这情形很像“五四”运动初期,在反帝反封的旗帜下,一些人与人民大众是一路同行,但是当时代进一步向前发展时,他们便从人民大众的营垒中分离出来,走上了歧途。北岛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四人帮”的重压之下,他的声音某种程度上与人民的呼喊有一致的地方:“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但是,当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他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反抗,逐渐显得与人民大众的步伐不一致了,终于走向了歧路。
当浙江的程蔚东喊着要“Pass北岛”时,当他们喊着“北岛、舒婷的时代已Pass”时,80年代中期以后,新生代们已经向朦胧诗毫不客气地亮出了“手术刀”,这恐怕是当年的朦胧诗人们始料所不及的。当朦胧诗人们“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走入禁区/……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后来者”们竟纷纷打出了“Pass”他们的旗帜,而且这一次来得如此猛烈,是以群体展示的形式出现的。但不管“新生代”的口号喊得多响,旗帜举得多高,他们似乎都没有冷静地观测好自己的位置。其实,这只不过是新诗历史不断反复重临的起点,无论是“朦胧诗”,还是“新生代”,都仍然只是对中国新诗既有状态的不同程度的“整理”,是中国新诗相对阶段性蜕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新诗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在寻找着最佳的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
尽管如此,回过头看“Pass”的呼喊声,仍然显得有些急躁,有些操之过速,有些欠冷静。也无怪乎在这些呼喊声刚刚出口的时候,曾为新诗的“崛起”推波助澜的一位很知名的人物,就看出了有些操之过急,担心这种蜕变的“过速”。
为什么这种浮躁会再一次出现,这倒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否定的极端化,这恐怕和中国人一个时期以来“二值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关。要么全有,要么皆无。“A或非A”,像掷硬币一样,要么是正面,要么是背面,非此即彼。“二值逻辑”的思维定势一直笼罩着人们,这种无形的、庞大的、惯性很强的思维定势,长久以来,一直占据中国人传统思维的首要位置,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连高喊着“Pass北岛”们的新生代,也没能逃脱。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缺欠,必然带来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割断历史,割断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看不到人类的财富、尤其是精神财富生产过程中的连续性和承接性。片面的否定,否定的极端,正是缺少辩证思维的表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训练不足,是造成这种浮躁的根本原因。
浮躁表现之二:责任感的淡化。1991年8月在北京参加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有幸听到台湾老诗人钟鼎文先生的一席话:“什么是诗?”他说,“诗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美好事物的呼唤。清晨起床,在晨曦的薄雾中看到一位号手正在吹号,这就是诗。因为这位号手,用自己的心血变成了气力,再用气力发出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唤起了沉睡中的人们,实际上,这位号手是在用自己的精气血在召唤人们的醒来,这难道不是诗吗?”
尽管听者见仁见智,我还是从这一席话中听出了钟老先生仍然在呼唤诗的责任感。所以台湾诗界经过一番探索之后,现在也在回归,为人生的诗已经渐次成为主潮。
海峡对岸尚且如此,而我们这边有人还公然认为“诗就是诗”,宣称“诗歌从本质上就是诗歌:它是自足的实体,而不是我们借以感知其他实体的窗口,更不会带来荣耀”(《诗歌报》1988年7月6日第2版)。这声音其实我们是很熟悉的。有人不是说文学是什么,其实文学什么也不是,文学就是文学,是一个自足的实体吗?文学的存在,就如同地球自转那样自然得很,它不负载任何东西,是一种纯形式吗?这时,连西方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中的“意味”也没有了。甚至有人认为诗连情也不要抒了,“诗言志”、“诗主情”都是使诗有了负载物,是诗的异化。寄情、移情、抒情,都突现了诗的功利性,诗不是可以普渡众生的审美存在物。那么,诗是什么呢?诗只不过“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是不小心发出的声音”:“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也许你还喜欢大海/顶多是这样/你见过大海……”这首诗说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说,诗到这里,意义完全被消解了,诗什么也不是了,连意味都没有了。“你躲在房子里/你躲在城市里/你躲在冬天里/你躲在自己的黄皮肤里/你躲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地方……/画一座房子/画一个女人/画三个孩子/画一桌酒菜/画几个朋友/画上温暖的颜色/画上幸福的颜色/画上高高兴兴/画上心平气和/然后挂在墙上/然后看了又看/然后想了又想/然后上床睡觉”。在这里找不到实在的意义,前边已经说过,在这里意义已经被消解了,有的只是诗人心灵自由的存在物,是新生代们经常企盼着的那个时刻:“终于有一天,在一个稀有的时刻,当我们忘记了所有关于诗的理论,忘记了权威们对诗的要求,我们完全是浑然不觉地写下了一首诗的第一个句子,接着写下了其他的句子,这是诗!语言根本没有经过精心安排和设计,它们都是脱颖而出的,就像一杯水装满了要溢出来。”写诗,在新生代们看来,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没有任何目的的驱使和支配,如同原初状态人类的第一声呐喊,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在生命的深渊里,存在着一种实质性的东西,它是沉寂的、安静的、难言的。诗正是想表达这种东西。这样看来,新生AI写作诗还是有目的的,这目的不是别的,不是社会责任感的强化,而是自我存在意识的扩张,他们把写诗当成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在诗中追求一种生命意识。这点,正是下一节要讲到的。
浮躁表现之三:无根的生命意识。前边提到,在新生代那里,诗是生命的存在形式,是诗人自由心灵的外化,是诗人“内在生命的律动的本体体验”。人是诗最深刻的内容,诗是人最审美的形式。诗的生命化与生命的诗化同在,诗人心灵的自由与诗人的生命形式共存。写诗,就是为了显示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活动。写诗是“我们身心的血,我们的眼神,和惯用的手势”。在新生代们那里,“强烈的生命意识被他们顽固地摄入诗中,热情地、执拗地、浓厚地寻找生命、表现生命,到了虔诚的宗教徒般的地步。他们把诗作为生命的具体体现,作为生命价值的实现……好像没有诗,不写诗他们的生命就无法存在似的。”(《当代文艺探索》终刊号第5页),“超前意识”派宣称:“诗是纯粹的生命体验”,“诗的最高极限是生命的形式本身”。“情绪流”派也表白:“诗从属于生命过程,是生命内涵体验和深刻内省”。
“新生代”诗人们的这些主张,立刻得到了当时诗歌理论界的回应,形形色色的诗歌理论家们,在为其寻找依据。有的人进而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找:“新生代”们既然把写诗当成是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形式,当成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这不就和马克思主义走到一起了吗?因为在这些理论家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自我实现”(《当代文艺思潮》1980年第6期83页),进而认为“新时期诗歌理论的最大突破,就是对诗主体性的重新肯定,对诗人通过艺术创造达到自我实现的重新肯定,人的本性,或者人的最大追求,是人的自由发展,也是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我实现有多种形式,其中也包括诗的形式,它的实质,就是创造性的劳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自由发展,所谓共产主义,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那‘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也是诗的”。为了避免断章取义,这里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次全国新诗讨论会具有结论性纪要中的一段话,只要我们注意到加着重点部分,其中的意思就很明显了。结论是:人的本性,或者人的最大追求,是人的自由发展,也是人的自我实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抽象为这样一层意思之后,笔锋一转,既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自我实现,既然“新生代”们主张写诗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是生命价值的实现,那么,“不妨说马克思主义也是诗的”,而且是“新生代”们力主的那种诗。
结论就这样似是而非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问题出在哪里?抛开形式逻辑演绎中所犯的错误不谈,我想问题主要出现在对“人”的理解上。抽象地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发展”是不妥的。是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说过“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这与那种笼统地、抽象地谈“人的本性”是“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马克思这里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指的是“人的类特性”,而不是个别的“人的本性”。“人的类特性”是把作为主体的人相对于客体自然而言的。当我们把人的类特性看作是相对客体自然而存在时,就可以发现,人的这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乃是指人的改造客体的活动。换言之,这种自由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自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自由。这种自由,“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资本论》第1卷第201-202页)。恩格斯也说过:“自由是根据对自然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很明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所说的自由,是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而言,是人相对于自然而言的自由,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自由。而“新生代”及其理论家们所追求的那种自由,那种“人的自由发展”,那种“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显然不是相对于自然,不是相对于改造自然、认识自然的必然性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对于人的社会存在而言的。这显然是一种概念上的错位和偷换。
还有一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是以完成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为前提的,而“新生代”及其理论家们主张的仅仅是一种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仅仅是诗人主体自身的“自由发展”,与改造客体世界无涉,与诗人所生活、生存的世界又有何益?他人如何,且不去管,只求自我的伸展与扩张。不问外界的需求,只要自己坐在玻璃窗子里吃面包、喝牛奶,写诗,就行了。“该物体产于四川/81年起归北京保管/它长1.72米/宽0.43米/厚0.21米……根据规定第92条/该物体定名为阿吾。”看,这种自由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无论有什么样的悟性,付出多么大的耐心,从这里你都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看来,“新生代”及其理论家们企图在马克思那里找寻他们对生命意识迷恋的佐证,已经是徒劳无益了。“新生代”诗人们追寻的生命意识是无根的,这还表现在另一个问题上。
他们一方面把写诗当成生命形式的一部分,宣称“诗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诗的纯粹是生命的纯粹,是纯粹的生命……”;另一方面,他们更关心的是生命本体自身,更关心潜入到生命的深层中去窥探生命存在的奥秘,揭示生命的内涵与生命的构成。他们从人的生存本能出发,从人性的最基本层次出发,去充分体味生命所构成的种种部分,如爱、死、情、性等。正如黄力之同志指出的那样,谁把性行为写的淋漓尽致,充满山崩地陷的力度,惊世也骇俗,笼罩一切,谁的作品就被誉为“生命意识”的扛鼎之作(见《文艺报》1991年7月6日第3版)。在“新生代”诗人们那里,对生命的体验,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一些女诗人对性的赤裸、坦荡的描绘上:“待守闺中我们是名门淑女/悻悻地微笑/挖空心思/使自己变得多姿多彩/年轻,美貌/如火如荼/炮制很黑、很专心的圈套”,“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我在何处形成/夕阳落下/敲打黑暗/我们仍是痛苦的中心”。如果说翟永明的这首处处不离黑暗、黑色的诗,表达了女性特有的性苦闷的话,那么唐亚平的《黑色洞穴》一诗,便表现得更加赤裸和大胆了:“那只手瘦骨嶙峋/要把阳光聚于五指/在女人的乳房上烙下烧焦的指纹/在女人的洞穴里浇铸钟乳石/转手为乾/扭手为坤/……”而另一位曾经引起过不少争议的伊蕾已经不是羞答答的暗示,而是更为率直的呼喊了:“终于发现人类的秘密/为活着而活着/我甚至不生孩子……/我有无用之用……/谁来与我同居”(《独身女人的卧室》)。不可否认的是,在前几年性大潮泛滥的时候,对诗坛也是一种侵染,“新生代”们也没能幸免,尽管他们自己标榜着“纯诗”,标榜着生命的存在形式是诗。更有甚者是有的“新生代”勇士们写出了这样的句子:“我的生殖器硕大/摆来晃去/像北京车站那座巨钟的指针/为一声悠长而又肉感的鸣叫/我常常暗自得意”(《一头公驴对人的偏见》)。如此不堪入目到令人难以卒读的程度,据说是为了使诗“从贵族那里回到平民中去”。还有的“新生代”公民们以同样的粗鄙作过如此的描绘:“她的郛房友善地向男人致意/她的裙幅越荡越高/男人们在台阶上越走越低/一个个都是绝对的诗人。”这样的句子竟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对性压抑的血淋淋的反驳”,“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正宗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性与欲的对立在第三代笔下统一于生命之上”。在生命意识的大旗下面,“新生代”勇士们津津乐道于这些赤裸裸的性描写,不会给人们带来任何审美作用,只能是在呼唤人们从文明状态重新回到动物世界、回到原始森林中去。这样的诗句,这样的粗俗,这样的不堪入目,理论家们还为之吹捧,说什么是“情与欲的对立统一于生命之上”,而根本无视其审美价值,无视人们的接受心理,这就十分有力地说明了理论界对一种不好的创作倾向的盲从,从而也明显地暴露了诗歌理论评论界的浮躁。
“新生代”诗人们对生命意识的执著追求,不是偶然的现象,是与前几年在我们社会中一股普遍流传着的人本主义思潮密切相关。这种人本主义思潮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人的本能视为主体性内涵,当作世界存在的本体。但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化的观点看,对生命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原生状态作为生命的最高形式。就人的生命自然属性而言,生命体验虽然包含有动物性的本能骚动,但这远远不足以体现人的生命形式的全部丰富内涵。因为我们这里所谈的人,是进化意义上的人,不是停留在动物水平上的人。人的生命形式与动物的生命形式,是有区别的。这点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过论述:“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志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直接区别开来。”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人的社会性,恰恰是在这种社会结构关系中,人必须凭理智、理性来制约自己的本能冲动。这里同样涉及到对“自由”的理解。自由,在马克思那里,是相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是人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所达到的一种程度,这点前边已经说过。如果把这种自由硬不加分析地搬到社会结构的关系中,搬到人的社会性这里来,那显然也是与不约束自己的本能冲动一样,迟早会被排除社会结构之外的。
在“新生代”那里,把生命意识的本能冲动,原始生命的生存状态,作为诗的追求目标,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再一次遇到了红灯。
浮躁表现之四:艺术主张的杂乱无章。在“新生代”城头变换的数十面大王旗中,有一面旗帜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非非主义旗帜。他们的艺术主张的核心当数三个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这里的语言还原是焦点。非非主义认为,语言弥漫了一切,人类制造了足以取代和覆盖整个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语言,以至使人们一抬脚,便必然会陷入到语言的陷阱,语言与人的思维同在,人总是凭借语言进行思维、判断、推理的,借助语言进行交流沟通的,这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所有的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密不可分的,都有它早已为人所认可的字典意义,这种语言总是表现为一种文化语言,是人类长期文化的一种积淀。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语言,像网一样,约束着诗歌创作,以致使写诗的人,一动笔一使用语言,就落入到约定俗成的陷阱中去,从而也就带上了固有的文化意义。
在具有约定俗成的文化意义的语言陷阱面前,非非诗人们也许是读了一些拉康、德里达或者是福科等人的书,他们显得格外的焦虑,格外的急躁,于是他们试图返回到人类的史前状态中去,重新感觉世界,重新构筑不代表现有人类任何文化意义的语言世界,用这种感觉,用这种语言去写诗,彻底摆脱现有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互相一致的紧密封锁,摆脱这个符号化、语义化了的世界。据说,作了上述三个还原之后,“被文化之网膨胀起来的意识屏幕像孤帆一样远远离去,只剩下飘来飘去的直觉”了,只要靠这种超语义的直觉,便可以完成非非主义的诗作了。
这种理论的提出,一时间吓住了一些人,有人进而认为“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大陆诗坛的地基迅速下降了”,“根本改变了诗歌现状,引爆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革命来”。实际情况怎样呢?其实,这只不过是新潮诗歌理论的“乌托邦”,是食洋不化,吃了羊肉头上长出了羊角。正像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的一些人那样,身在地球上还要用自己的双手提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真正的超越文化,超越语言,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人类创造了文化,创造了语言,又生活在语言之中,受制于语言和文化。超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行为;超语言,也得使用语言。试问当非非主义者们提出要超越凝固的文化规范时,超越现有的语言藩篱时,他们不也同样在使用人类约定俗成的语言和文化吗?退一步讲,就是这种超越完成了,直觉体验是否就没有文化或达到了超文化的境地呢?恐怕仍然是一种文化,一种另外的文化,一种非非主义的文化罢了。因为直觉中仍然包含着、积淀着人类文化丰富的内涵。
其次,非非主义这种超语言理论的提出,也缺乏现实的依据。在诗歌创作中,远的不说,从朦胧诗开始,舒婷、顾城们的语言,就已经具备了“超”的意味,就已经远远不是那种约定俗成的、字典意义上的语言了。这点,笔者在《朦胧诗纵横谈》一书中早就作过详尽的分析,不妨再摘引一段:“在一首诗中,语言已经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原意,失去了字面上的意义,而赋予它新的生命。正像艾汉鲍姆所指出的:‘词语一进入诗歌,它们似乎就脱离了普通话语。它在四周的气氛具有新的意义’,雅各布森说,这是诗歌‘对普通语言的有组织的违反’………‘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这里的‘小巷’、‘钥匙’、‘墙’,早已经不是日常生活中普通的原来的意思了”。这时,“诗人创造了什么?”苏珊·朗格这样问,“诗人凭借词语创造了幻象,”“构思一首诗…其内核和胚胎我们仅能从词语中获得”(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第239页)。在朦胧诗人那里,实际上早已经构成了对语言常规格局的有意识的“违反”,早已开始具有“超”的意味了,而且他们基本上做到了恰到好处。这种“违反”、这种“超”,当时已有孙绍振等人给以明确指出,认为是一种“错位”、“超感”、“误差”等等,并认为正是这种“违反”、这种“超”,构筑了朦胧诗意象的迷宫和象征手段等等。人家都已经做到了的事,非非主义者们还要去做,而且似乎显得更彻底些,这显然是有些重复,有些添足,有些多余了。因为非非主义提出的超语言,并非新鲜事,在这以前的诗歌创作中,几乎是俯拾即是,他们只不过是想把这种“违反”、这种“超”推向极端而已。这里需要提醒的只有四个字:过犹不及。这时,人们不仅要问,非非主义诗歌及其理论,其新意到底何在?
浮躁表现之五:远离人群的“平民化”。很多人指出在“新生代”另一些诗作中,有一种“平民化”倾向,在具体作品中表现为一种反崇高、反优美、非英雄化、非意象化倾向等;在语言的使用上尽量追求口语化,不带任何暗示、象征意味,直接宣叙。“妙语的烟雾太浓重了/学究的枯枝太脆弱了”,在朦胧诗意象迷宫里行走得太累了,提倡一下诗的口语化,也是未尝不可的,也似乎给艰深晦涩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可是,“新生代”们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有更新的主张和表现。提倡口语化,就势必减少了对人自身灵魂和感情世界的深入,同时也减少了包括对人格化了的自然的沉思和领悟,是对那种能够展示人类命运的深层意识和灵魂骚动的大主题的表现,缺少必要的勇气和耐心。口语化很难使诗达到理性的审美深度,使诗具有一种崇高美。在“新生代”那里,一切英雄都不存在了,一切伟大的人物都被他们还原为普通人了:“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叼着雪茄/用鹅毛笔写字/字迹非常潦草/他太忙/满脸的大胡子/刮也不刮/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他写诗/燕妮读了他的诗/感动得哭了/而后便成为/全世界最多情的女人/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没有职业/到处流浪/西伯利亚的寒流/弄得他摇晃了一下/但很快就站稳了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穿行在欧洲人之间/显得很矮小/他指指点点/他拥有整个欧洲/乃至东方大陆。”在“新生代”诗人的笔下,马克思也是人,是人就要食人间烟火。这正是“新生代”反崇高诗作的一个典型例证。“新生代”诗人从追求诗的生命意识,到提倡诗的反语言,超语义,口语化,以至反崇高,这是一脉相承的。在稍后的一些时间里,当人们从一阵阵新潮的叫喊声中冷静下来的时候,就会理所当然地提出批评。
有人指出,不可否认反崇高有助于人对自己精神负面领域的深度掘进,在深入反思中,会更进一步认识自己,把人从神的位置上还原为普通人,把人从绝对理性禁锢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人的世俗相。但是这些在人的正面价值面前,又因失去自信而显得委琐渺小。特别是在中国,当一些人还不知道真正的崇高为何物时,极度膨胀地反崇高,究竟好不好,到底还能走多远?这种忧虑我以为是有道理的。“崇高乃人类赖以进化的重要精神支柱,这个支柱一旦倾圯,精神危机便会更加猖獗,有良知的诗人,应该以更持久的热情浇铸这一混凝工程。”(《艺术广角》1991年第5期第13页)这种对崇高的态度,我以为是难能可贵的,也愿意与“新生代”反崇高的勇士们共勉之:“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崇高,使他们的勇气、荣誉感、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昔日的光荣——复活起来。”(福克纳)
反崇高、平民化、口语化、写世俗人生,这样就难免使诗流于粗鄙、流于平庸:“你不愿向医生说明/自己是一位诗人/白色的门晃来晃去/像女人不甘寂寞的屁股/一回/你误入了女厕所/被一群白色屁股臭骂了一顿/那以后你就一直心神不定/躲避着什么”。据说,这样写正是为了“体现意象的优美度为粗鄙度所代替”,“以期逐步排斥意象本身的魅力”。但这样的“代替”到底是诗歌创作的进步呢?还是倒退?它能给人们带来的是审美愉悦呢?还是与此相反的东西?我想,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诗歌的审美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
浮躁表现之六:旗帜的辉煌与创作的疲软。吴开晋先生在《新时期诗潮论》一书中,实事求是地指出:“非非的理论建构,显得过于辉煌,而创作又显得那么疲弱、无力,这就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使人们对其终极目标不免产生怀疑”(吴开晋:《新时期诗潮论》第234页)。实际上,岂止是非非主义,那段时间里一股脑涌现出的数十个流派中,哪个流派没有一番堂而皇之的宣言?尽管他们的宣言互相矛盾,一方面标榜他们写诗什么也不为,一方面还要发宣言,说明他们写诗的目的;一方面反对诗是言志的,是主情的,一方面又高叫诗是排泄物;一方面宣称自己要做“平民诗人”,一方面虽然用口语、白话写诗,但人们仍然读不懂;一方面主张超语言、超文化,一方面还在使用着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化……总之,宣言是太多了,旗帜是太亮了,而有代表性的作品却又实在太少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煞是好看,关键是城里边没有兵,唱的是“空城计”。还是公刘同志说得好:“拿货色来!”“一首成功的小诗,胜过一打漂亮的宣言”。就边孙绍振都对“新生代”宣言的过猛,也表现出某种忧虑,指出“必然导致狭隘和肤浅”,而且“没有产生一个辉煌的代表”。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有独树一帜的才气,但却缺少那种指挥千军万马、继往开来的伟大气魄。终还是:“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新生代”宣言的过热,创作的过冷,使一些对“新生代”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那么,一时间到底有多少面旗帜铺天盖地般卷来呢?我手头正好有一份1986年9月3日的《深圳青年报》,节录下来,录以备考,他们是:
四川的“非非主义”、“整体主义”、“大学生诗派”、“流派外离心分子”、“四川五君子”、“自由魂”、“野生诗派”、“新传统主义”、“莽汉主义”、“群岩突破主义”、“新感觉派”、“新古典主义又一派”、“莫名其妙派”;江苏的“他们派”、“阐释主义”、“新口语派”、“日常主义”、“东方人”、“呼吸派”、“色彩派”、“南方派”、“超感觉派”、“新自然主义”;上海的“海上诗派”、“撒娇派”、“主观意象”、“情绪流”;北京的“情绪独白”、“生命形式”、“体验派”、“深度意象”;吉林的“迷宗诗派”、“八点钟诗派”、“特种兵”、“超低派”;浙江的“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咖啡夜”、“极端主义”;安徽的“世纪末”、“病房意识”;福建的“超越派”;广东的“现代女诗”;黑龙江的“男性独白”;湖南的“裂变诗派”;贵州的“生活方式派”;河南的“三角猫”;云南的“黄昏主义”等。
以上,从6个方面长短不齐地分析了“新生代”在向传统诗歌,尤其是首当其冲向朦胧诗冲击时,表现出来的某种浮躁情绪。其实,这种浮躁正是新诗发展的一种必然。正如中国新诗在朦胧诗之后,必然要出现“新生代”一样。这种诗歌艺术发展的“两极现象”,完全可以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找到佐证。比如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诗歌意象表现方法的成熟,还是诗歌形式格律上的严谨,都是不可企及的。到了宋代,要想突破已经很难。但是,艺术总应该是向前发展的,于是宋代的诗歌艺术就在另一个极端上去寻找,宋诗大量地摆脱了意象的表现方法,而近于“直说”,增加了诗的“理趣”色彩。当然,从思想上看,这与宋代程朱理学的发达有关,但在诗歌自身上看,却是对唐诗的一种突破,逐渐形成了宋词,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与唐诗并峙的一大高峰。
这点,很有点像“朦胧诗”与“新生代”的关系,朦胧诗大量意象的表现方法,使人总是在意象的迷宫中,脖子都有点酸了,于是到了“新生代”,他们开始提倡反意象、反变形、口语化。其实,这也是对“朦胧诗”高密度意象的反拨。
有人说自“五四”以后,中国新诗成熟周期是80年,现在正是新诗成熟的第三阶段;有人说1976年以后中国新诗运动正经历着“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新生代”的出现,正是由反题走向合题的开始。“新生代”是一个庞杂的诗歌现象,它实现了对传统诗歌美学的大冲击。从宏观上看上去,“新生代”在这冲击中,所显示出的种种浮躁,也是一种必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从中国诗歌发展总的趋势上看,这种“浮躁”,仅仅是“新生代向传统诗冲击过程中,自身准备不足的那一面,自己立足不稳的那一面,而这种冲击,自然也或多或少有其片面真理性的一面,起码是对中国新诗总体发展的一次整理,这当然不是本章的范围了,也许笔者有时间会撰文专述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