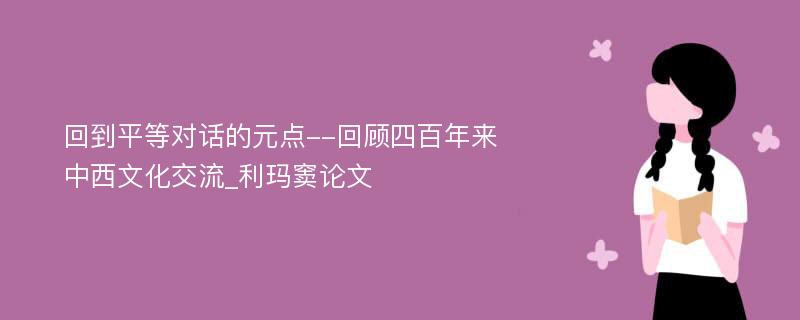
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对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交流论文,点上论文,中西论文,平等论文,四百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那一望无垠的大漠上的阵阵驼铃声连起了东方和西方,但直到世界近代化的曙光从碧蓝的大海升起,双方的交往才开始向思想和哲学的层次迈进。一个意大利人哥伦布身怀西班牙国王所写的“致大汗书”,肩负着寻找契丹的使命,带着他那到达香料堆积如山、白帆遮天蔽日的刺桐港的梦想,开始远航,从而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但阴差阳错,不知道大西洋上的哪股风把他的船吹到了古巴。哥伦布虽然没有到达中国,但东西双方宗教与哲学的交流乃至近代以来整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性人物还是由一个意大利人来完成的,这就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及他以后的来华耶稣会士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就是“西学东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掀开了新的一页。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继而又和明末大儒李之藻合著《浑盖通宪图说》。从此,对西方天文学的介绍一直是来华耶稣会士的重头戏,乃至明清间历局大部分为传教士所主持。历学和算学二者历来不可分,利玛窦和徐光启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阮元认为传教士所介绍的各种西学书中“当以《几何原本》为最”,梁启超也称这本书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利玛窦所绘制的《万国舆图》更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明清间先后被翻刻了12次之多,乃至万历皇帝也把这幅世界地图做成屏风,每日坐卧都要细细端看。表面上利玛窦所介绍的这些似乎都是纯科学的知识,其实这些科学知识蕴含着西方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学虽仍是中世纪的,但其理论对中国来说却完全是异质的,算学则把西方科学逻辑思维方法介绍到中国,而地学则是大航海以来西方新的世界观念的体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
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认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斯多葛、西塞罗等这些古希腊、罗马的大哲学家是在五四时介绍到中国的,其实不然。别的不说,仅亚里士多德的书明清时就有多部被译成中文。被称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认为西方哲学中的“落日加”即逻辑学位于首位,是“立诸学之根基”,傅泛际和李之藻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一部分译为中文,取名《名理探》,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则继而把他们未完成的后半部分整理出版,中文取名《穷理学》。这种逻辑思想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处于阳明心学衰落中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清风。
明清间,从利玛窦入华到乾嘉厉行禁教时为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这次西方文化的传播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此时士大夫阶层对西学的接受的态度。当时,尽管保守派并不少,并时时挑起争端,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学采取接受态度。利玛窦在明末时交游的士大夫有一百四十多名,几乎朝中的主要官员、各地主要公卿大夫都与其有来往。当时不少士大夫对于利玛窦等人介绍来的西学既不趋之若鹜,盲目随和,也不拒之门外,孤芳自赏,而是心态平稳,该做自我批评时就反躬自问,虚心学习,该承认自己传统时,也不夜郎自大,旁若无人。如徐光启在《同算算指》序中对中国算学失传做深刻反省,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实事”,而利先生的西学之根本优点在于“其言道、言理,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而只有学习西学才能把我们已丢失的黄帝、周公之算学继承下来。那时的读书人中既没有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也没有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如晚明名士冯应京所说:“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从容自如,大度气象一言尽之。
利玛窦和来华耶稣会士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中国文化传向西方,简称“中学西传”。由于利玛窦所确定的“合儒补儒”路线取得成功,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虽和中国文化时有冲突,但大体耶儒相通。这条路线的确定使传教士来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方块字,说中国话,用毛笔写中文书,这对后来的传教士产生重要影响。别的不说,仅利玛窦就有中文著作二十几部,这一点就是当今最大的汉学家也望尘莫及。
会说中国话,能读中文书,对中国文化就有了了解。于是一二百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要么写信,要么译书,要么著书,以各种西方文字把中国的书译成西文。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学西传上笔耕之勤,兴趣之广,成就之大,令世人惊叹!《论语》、《道德经》、《诗经》、《书经》、《礼经》、《孟子》、《中庸》、《大学》这些统统都有西文译本,而且不止一种语言的译本,甚至连《洗冤录》这样很专的中国最早的法医学著作都被他们翻译成西方语言。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开始,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如曾德昭的《中国通史》、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安文思的《中国新事》、卜弥格的《中国植物》、《中医脉诀》等。如果说在他们前期的汉学著作中转述性、介绍性内容较多,那么到后期他们的学术水平已达到很高的成就。像宋君荣的《中国天文史略》和《中国天文学纲要》两本书,通过考证《书经》中之日食、《诗经》中之日食、《春秋》中首见之日食来考察中国的纪年,其方法和今天中国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相差不多。
正是在利玛窦的“适应”政策之下,经过一二百年的努力,在西方的东方学中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汉学。汉学实为中西文化会通之产物,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难免有不实之处,他们中许多人就是“索隐派”的重要成员,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所做的重大贡献。
颇有趣味的是来华耶稣会士为了证明其“耶儒相合”路线的正确,争取欧洲对其在中国传教的支持,在他们的著作中护教成分较多,但这些文章和著作却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的著作不仅没有起到“护教”的作用,却反而被进步的思想家所利用。培尔高度赞扬中国的宽容精神,以抨击教会对异己思想的排斥;伏尔泰则高举起孔子的仁爱精神,批评西欧中世纪文化的落后性;中国哲学的自然理性成为莱布尼茨走出神学的主要依据。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文化接受中的“误读”实在是一个极有趣味的问题,但不论怎样误读,东方文化、中国精神,成为瓦解西欧中世纪城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被普通接受的结论。
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
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也个个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的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
那个时代的东西关系,尤其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与西方和南北美洲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西方面对一个国力比其还要强盛的大国,出于无奈,只能采取较为缓和、平等的政策。而来华的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宗旨,但面对比基督教文化悠久得多的中国文化,大多数传教士是震惊的,甚至是敬佩的。正是在向对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而遗憾的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乾嘉禁教之后,其间虽有嘉乾汉学之一搏,但终因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已成定局,这星星之火未成燎原之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始终还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打圈圈,会通之路没有打通。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因素,一个庞大的帝国终于衰败了。
1840年以后,中西关系彻底颠倒了,西洋人的战舰配备着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驶入了我们的海岸,用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大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晚清的大员们在南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平等的对话再不存在,中国再不是西方慕恋的对象。
19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是强者的世纪,是西方人凌欺、强暴东方人的世纪。晚清的败局刺激了每一个中国人,从此,“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成为中国的两面旗帜。而要达到这两条,只有学习西方。如梁启超所说:“参西法以救中国”,当“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毛泽东后来也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东西关系完全失衡了。在国家面临生存存亡之关头,人们似乎无别的路可走,这种局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五四。从此,在东西方关系上,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成为一个打不破的定式。
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做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的问题。
如果把20世纪的中国革命看做是晚清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延续,那么,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将渐渐淡去,西方的“霸权话语”也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在一定的意义上,今日东西方的思想对话又重新回到了公元1500~1800年这个起点上,这或许是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从客观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一时期也可以看作是今日世界的起点,是今日世界的胚胎。它包含着说明今日世界的一切因素。从这一丰富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对东西文化关系得出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任何民族都无法脱离这一进程,无论这种进程以“恶”的形式还是以“善”的形式表现出来,都无法拒绝。“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历史不可拒绝。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都不能再“独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在自己原有的封闭系统中发展。我们应当以当年康熙帝、徐光启、李之藻那种容纳百川的宏大心态对待西方文化,以一种平静的心态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徐光启说得好:“会通以求超胜。”一百多年来,我们总算有了可以喘息的机会,现在我们总算可以从更大更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以更深刻、更全面的方法来看这种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晚清以来的一百多年是特殊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最壮烈的时代,但那毕竟是一个东西方关系不正常的年代,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百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更重要的在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那时心态都是不正常的,在枪炮下的交往是扭曲的交往。在刀光火影中的评判带有极端性。只有到了今天,当我们在因特网上读美国图书馆的文献时,当中国近二十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并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家庭的重要一员时,一切历史的本质东西才开始清晰起来。以往焦虑的呐喊、病态的呻吟、无知的狂躁都成为过去。“化中西为古今”,此时才能对一百多年来形成的东方西方的定式给以重新考虑。我们仿佛又回到康熙时代,不!这是一个更为崭新伟大的时代。
第二,西方应该抛弃掉“霸权话语”。具有普世性的不仅是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同样具有普世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当然有它共同的话语、共同的价值。而这些标准的确有些是来自西方,但这并不能证明,西方文化可以取代一切。每一滴水都能折射出七色的阳光,每一个生命都有自身的尊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存在的依据,中国文化同样是人类普遍价值的源泉。近百年来西方的中国观是一个扭曲的中国观,他们忘记了“初恋”时对中国的钟情,昔日的“神”已变成了“鬼”。他们按照强权的西方话语编造了一个东方的故事。其实中国人既非“神”也非“鬼”。天同此道,人同此心,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梦想。大西洋,太平洋,潮水相连;阿尔卑斯山,唐古拉山,山山相连。世界万象,但殊途同归。自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四百年间,不仅是东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也是西方学习东方的过程。因此,西方应抛弃掉19世纪所确定的东方观、中国观,回到利玛窦所确立的路线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