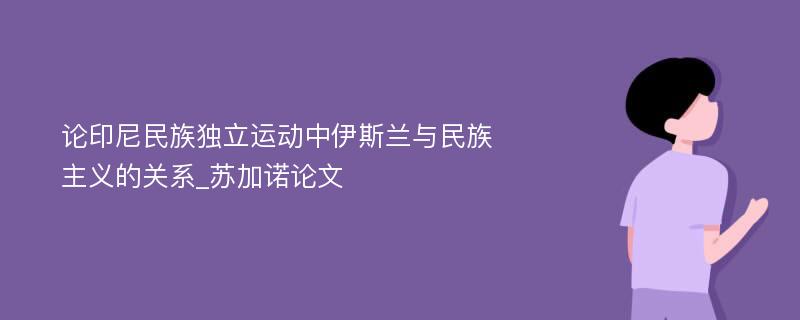
试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印度尼西亚论文,民族主义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4.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6099(2006)04—0047—04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是两面重要的旗帜,伊斯兰教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是两股重要的领导力量,双方在抵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上目标一致,相互合作;但在领导权和立国理念上意见相左,互有冲突和争论。最终民族主义占上风,建立了以“潘查希拉”为基础的共和国。
印尼穆斯林人口约占88%,伊斯兰教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合作与冲突不仅对印尼独立运动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影响到独立后印尼的政治发展。但对这一问题,中国学术界较少研究,国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也较深入①。本文主要探讨印尼独立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重点在于双方的争论和结果,并分析其根源。
一 伊斯兰教与印尼民族主义的兴起
印尼民族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是在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激发下兴起的,正如研究印尼民族主义的学者指出,伊斯兰教架起了团结全国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情感桥梁。卡汉认为:“穆罕默德宗教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联合,它是一种内在的象征:反抗外来侵入者和异教的压迫者”[1]。另一个学者冯德麦登在其博士论文《印尼伊斯兰和民族主义的崛起》中认为:“对于建立民族团结和脱离荷兰精英统治者,伊斯兰教是一种最见效的方法,荷属东印度群岛从来没有作为一个语言、文化和历史实体存在过。直到20世纪初始,最后一些地区才屈服于荷兰的统治下。因此,存在不同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地理环境,在殖民统治之外,唯一一种普世的占上风的是伊斯兰教。”[2] 因此,伊斯兰教是民族独立运动最有效的动员工具。伊斯兰教联盟是印尼第一个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也是较早的民族主义组织②,该组织在最初致力于通过教育、出版、宣传等方式纯洁伊斯兰,后因有社会主义者的加入,而转向民族独立目标。1917年该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指出,伊斯兰教联盟的目标是达至自治;否认一个民族有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权利;要求取消所有妨碍伊斯兰教发展的规定;反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等[3]。该组织吸引了不少人的支持,成为印尼早期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组织,“伊斯兰教联盟构成了印尼民族觉悟的中心”[4]。著名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纳席尔(Mohammad Natsir)也曾高度评价伊斯兰教联盟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正是伊斯兰教联盟第一次发起通向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撒播了印尼团结的种子,打破了不同岛屿地区的孤立联系,第一次因共同信念在印尼与非印尼国土外的人士,撒播了兄弟情谊般的种子”[5]。但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在理念上有本质区别,不可能长期合作,以哈支·阿古斯·萨利姆(Agus Salim)为代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坚持伊斯兰教是联盟的指导思想,最终社会主义者被逐出联盟,这是印尼民族运动史上第一次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分裂,1923年联盟改名为伊斯兰教联盟党。此外,其他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也追求民族独立目标。30年代米南加保的印尼穆斯林联盟的思想纲领是“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该党领导指出:“安拉要求我们尽可能努力地为伊斯兰教的利益及宗教发展而工作,但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民族做更多的工作。”[6] 可以说,伊斯兰教为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7年苏加诺和库苏马领导建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该组织是世俗民族主义的代表,后来成为领导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力。自此,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形成两股力量,一个是伊斯兰集团(golongan Islam),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团体(golongan kebangsaan),双方在反对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前提下进行积极合作,但在斗争目标和立国理念上,尤其在谁占主导地位等问题上双方意见并不一致,展开激烈争论。
二 伊斯兰集团与民族主义关于领导权和立国理念的争论与斗争
在以苏加诺为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看来,伊斯兰教法(沙里阿法)是过时的,“根本不适合于20世纪的东印度”[7],世俗主义才是未来印尼的方向。苏加诺出身于爪哇的名义穆斯林(Abangan),他的思想来源十分庞杂,既有爪哇神秘主义,也有西方民主思想,他对西方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杰斐逊、华盛顿、林肯、卢梭、伏尔泰、马志尼、加富尔等人的思想和活动钦佩不已,认真钻研[8]。这些不同的思想来源被他以调和的方法溶为自己对印尼民族独立的看法,早在1926年他在《青年印度尼西亚》上发表的《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一文既是他对自己立场的一个声明,也是调和各种思潮的产物。他认为构成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各派别的三个主要思想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三种思想可以在殖民统治情况下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精神——团结的精神[9]。他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人民的一种信念与意识,它能团结一个团体,一个民族”[10]。尽管他自己曾表白:“如果剖开我的胸膛,观察我的心,各位将看到我的心无非是伊斯兰教的心”[11],但伊斯兰教从没有内化为他精神追求的一部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J·D·莱格所指出的,苏加诺对伊斯兰教缺乏足够的了解,他对伊斯兰教问题的关心,“自始至终是属于政治上的关心”[12]。因为伊斯兰教是促进印尼民族独立的一支重要力量,苏加诺需要这支力量,但作为世俗民族主义者,他不会让伊斯兰教超越民族主义。
而在伊斯兰教集团看来,伊斯兰包罗一切,民族主义只能置于伊斯兰的框架之内,萨利姆认为,苏加诺的民族主义导致人们将国家奉为崇拜对象,降低了人们对安拉的忠诚,因此,他认为,民族主义应该置于“为安拉奉献”这一思想框架之下,这种基本信念应该是伊斯兰教[13]。纳席尔认为苏加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蒙昧(ashabiyah,指前伊斯兰时代),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狂热,割裂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穆斯林兄弟同胞情谊”,他认为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应定位为忠诚安拉的一部分。正如纳席尔在《伊斯兰捍卫者》一文中指出:“让我们相互真情告白,因为我们各自目标不同,你们寻求为了印尼民族,祖国印尼而争取印尼独立;我们为了安拉和印尼群岛上居民的生命而斗争。”他还认为印尼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应当从属于伊斯兰教,他甚至宣称,“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印尼的民族主义,因为正是伊斯兰教第一次撒播了印尼团结的种子,打破了各个岛屿的孤立状态”[14]。
在立国理念上,双方也存在重大分歧。苏加诺为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要将印尼建为一个世俗的、强大的、独立的国家,他反对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土耳其共和国为他提供了榜样,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明确指出:“在国家的管理中,一切法律与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均依据科学为现代文明所提供的基础、形式与世俗的需要。由于宗教概念关系到个人的信念,共和国认为,将宗教思想与国家事务、世界事务以及政治分开,是我们民族在现代进步方面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15] 苏加诺对凯末尔革命和思想十分赞赏,他发表了多篇文章,指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经济、科学得不到发展,实行政教分离,建立世俗共和国是土耳其历史发展的必然,他还引用土耳其司法部长马哈穆德·爱沙德·贝伊(Mahmad Essad Bey)的话作论据:“任何时候宗教被用来统治社会,它通常是国王及独裁者手中的工具;相反,如果实行政教分离,就可以使世界免遭灾难,并保护宗教。”[16] 因此他得出结论:“现实告诉我们,在一个并不是百分百完全是穆斯林的国度里,政教合一的宗旨与民主是相互违背的,在这样的国度里,只有两种选择:缺乏民主的国家——宗教联合体,或者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17]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干脆指出:“伊斯兰教在印尼不应成为国家的事务”[18]。
但伊斯兰集团认为独立后的印尼应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教国。纳席尔认为伊斯兰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伊斯兰同时构成了宗教礼仪以及指导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安拉为我们立下了各种法规,包括人与安拉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法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有许多涉及人们在社会中的权利与义务,社会对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等,这种关系属于国家或政治事务,也受到安拉的法律的管理。但是所有这些《古兰经》及圣训中的法规和原则,没有自己履行的工具,因此,以国家为形式的权力,对于实施这些法规是必要的。”[19] 伊斯兰教的一些原则和义务必须通过国家来执行,如“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有责任交纳天课,但如果缺少国家的监督实施,这一条义务又如何能恰当地实施呢?”因此,纳席尔认为伊斯兰教需要一种可行的工具使它的教义能够得以实行,国家就是这一可行的工具,所以他指出伊斯兰教与国家应该结合为一个宗教政治联合体,他说:“对于我们而言,国家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工具。从本质上说,国家事务是伊斯兰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 这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政治观点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独立的印尼共和国呼之欲出,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成为独立运动领导人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在日本投降前夕,伊斯兰教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就独立后的国家是世俗国家还是伊斯兰教国家展开争论,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宪法基础;总统是否应该为一个穆斯林;是否设立伊斯兰教为国教;是否应该实施伊斯兰教法;是否设立伊斯兰教法庭;周五礼拜日是否设立为国家公共假日。
以苏加诺为首的民族主义集团坚持建立世俗国家,实行自由民主制,政教分离,不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而是以潘查希拉(Pancasila,亦称建国五基)为国家指导思想。他在1945年的“印尼独立筹备调查委员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潘查希拉”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未来印尼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即民族主义(印尼的统一)、人道主义、协商和代表制下的民主、实现社会的正义与繁荣、信仰神道。他特别提出国家的基础之一是信仰神,宗教信仰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宽容的基础上,“不只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要信仰一个神,而且,每个印尼人应该信仰各自的神。基督教徒应依照耶稣的指示信奉其上帝,伊斯兰教徒应依照穆罕默德的指示信奉其真主,佛教徒应依照他们自己的经典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但是,让我们大家都信仰神。”[21] 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印度教地位平等,宗教信仰自由。苏加诺还反对在民事法庭之外再设立伊斯兰教法庭,他认为:“一个普通法庭审讯所有案件已经足够了,当然,该法庭可以采纳某些宗教专家的建议”[22]。另一个民族主义领导人哈达(Hatta)尽管是来自西苏门答腊的一个虔诚穆斯林(Santri),他也认为《古兰经》不能成为国家法律的单一基础,他指出:“《古兰经》主要是宗教基本原则,并不是法律条文,今天所需要的各种法律在《古兰经》中找不到,……当然,《古兰经》确立了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公正和福利原则,但其原则仅仅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国家公民必须通过他们相应的深思熟虑建立有序的法律,当然每个人将根据其宗教信仰来表达思想。但是最终的法律是国家法律,不是宗教法。……我们不会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宗教事务要与国家事务分离。假若宗教事务同时由国家掌握,那么宗教会成为国家的工具,其主要特色也会消失,国家事务属于我们全体人民,伊斯兰事务仅仅属于伊斯兰乌玛(ummah)和伊斯兰社会。”[23]
而伊斯兰教集团追求将未来的印尼建成伊斯兰教国家,以沙里阿法为立国基础,只有穆斯林有资格出任总统,设立伊斯兰教法庭。为了协调双方的立场,设立了一个包括民族主义集团领袖和伊斯兰集团领袖的委员会,结果潘查希拉原则被大部分委员会成员接受,但仍有一些穆斯林领袖谋求在宪法草案中伊斯兰教的优先地位。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于1945年6月22日签署“雅加达宪章”,该宪章以序言形式载入宪法草案,主要内容是确定印尼人民的独立权利,确立印尼国家指导思想是“潘查希拉”,但潘查希拉的顺序作了调整,“信仰神道”被提到第一位,同时还规定未来的印尼共和国将以“信仰神道和以遵守伊斯兰教法律为该教信徒的义务为基础”,共和国总统必须是穆斯林。然而,到1945年8月印尼宣布独立时,公布的宪法草案序言里并没有包含穆斯林领袖们要求加入的那些条款,宪法中亦没有关于“印尼总统必须是穆斯林”的规定[24]。
三 为什么民族主义占支配地位
在印尼独立运动中,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都发挥重要作用,但最终确立的“潘查希拉”的立国原则表明民族主义占了上风,而伊斯兰教集团的努力遭到挫败,“这一个事件标志着伊斯兰集团试图将伊斯兰与国家建立正式合法的一个联合体的理念变成现实的第一次失败”[25]。为什么民族主义能取得胜利,能主导话语权,为什么伊斯兰集团会接受这个失败?
表层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迫使伊斯兰教集团让步。当时日本撤退,英荷联军登陆,印尼急于宣布独立,但伊斯兰教集团所提出的伊斯兰教为国教、总统为穆斯林等条款遭到委员会中基督教代表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宗教歧视,威胁要退出。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独立,伊斯兰教集团做出让步,正如一位学者指出:“革命时代不是表达他们(伊斯兰教集团)的伊斯兰观点的合适时机,对他们来说印尼独立是第一位的。”[26] 1945年伊斯兰教师联合会(NU)领导人瓦希德·哈斯伊姆(Wahid Hasyim)也说,对穆斯林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教在国家处于什么地位?”而是“我们用什么方式确保所有宗教在自由印度尼西亚的地位?我们最需要的是国家的稳定和团结”[27]。
伊斯兰集团对未来充满乐观也使他们未固执自己的主张。伊斯兰集团认为在民族国家独立后,通过举行普选,他们可以通过选票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议席在法律上确立毫不含糊的伊斯兰教国家,所以他们接受了删除伊斯兰教优越地位的宪法。
更深层的原因是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自由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潮,印尼人民更多地接受这类主张,认同的是民族的、世俗的印尼,而不是伊斯兰教的印尼,正如1928年来自印尼各群岛的青年所发出的誓言:“我们印度尼西亚的儿女认为只有一个祖国,即印度尼西亚;我们印度尼西亚的儿女认为只有一个民族,即印度尼西亚民族;我们印度尼西亚的儿女推崇统一的语言,即印度尼西亚语。”[28] 独立的、世俗的民族国家被认为是进步的,而政教合一的国家被认为是落后的、保守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受过西方教育,他们“既熟悉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又熟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策略,因而他们能够运用民族民主的思想武器,系统地揭露殖民统治的罪恶,令人信服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并为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制定可行的斗争纲领。因而苏加诺领导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战胜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力量,取得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29]
印尼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特点也是导致民族主义最终占上风的原因。印尼人口尽管有88%的穆斯林,但穆斯林以他们对伊斯兰教教义和义务的不同理解分裂成许多派别,最明显的是虔诚穆斯林和名义穆斯林的划分,而且穆斯林又分属不同的岛屿和民族,人口最多的爪哇族,分布在东爪哇和中爪哇,巽他族分布在西爪哇,马都拉族分布在马都拉岛和东爪哇,米南加保族分布在苏门答腊,马来族分布在苏门答腊等沿海地带,亚齐族分布在苏门答腊北部。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上述部族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巽他族、马来族和亚齐族对伊斯兰教信仰较为严格,能严格遵守教规和教义,属虔诚穆斯林,而爪哇族、米南加保族、马都拉族深受印度教、佛教、万物有灵论和母系氏族传统影响,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知之甚少,不严格遵守教规和教义,属名义穆斯林,名义穆斯林和虔诚穆斯林很难就伊斯兰教国达成共识。此外印尼还有约占人口7%的基督教徒。在前殖民地和殖民地时代,印尼各地域和各种族并不是政治统一体,只是在民族独立斗争中,才逐渐形成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概念,为了使其他民族加入独立后的印尼,在独立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爪哇人尤其是苏加诺发挥融合、和谐和宽容的爪哇精神,不强调伊斯兰教的突出地位,而是提出潘查希拉原则,力图囊括主要文化和宗教,达成各民族的团结,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他的主张得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名义穆斯林的支持,也得到基督教徒、印度教徒和华人的支持。
但是,独立后的印尼尽管确立“潘查希拉”原则为立国基础,伊斯兰教未被立为国教,伊斯兰教集团在谋求政治权力的道路上遇到挫折,但“雅加达宪章”埋下伏笔,伊斯兰集团在独立运动中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使它在民族国家建立后仍是一支不可小看的政治力量。20世纪50年代印尼议会民主时期,伊斯兰教政党——马斯尤美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是政党政治中的主角,与民族主义政党和苏加诺总统展开权力斗争,形成政治与伊斯兰教的紧张关系。此乃后话。
注释:
① 国内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黄云静的《印尼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运动与印民族独立运动》(载段立生、黄云静、范若兰等著《东南亚宗教论集》,曼谷大通出版社,2002年),研究了印尼伊斯兰现代主义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关系,但对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争论较少涉及。林德荣的《是“伊斯兰教”还是“潘查希拉”——印尼国家指导思想的定位》(载《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涉及立国前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争论,但过于简单。国外学术界有关印尼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有George Mc.T.Kahin,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Feed R.von der Mehden,Islam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Indonesia,Ph.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1957; Bahtiar Effendy,Islam and the State in Indonesia,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3; Howard M.Federspiel,“Islam and Nationalism”,Indonesia,1977,No,24; Deliar Noer,The Modernist Muslim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4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等。
② 1908年乌萨达创立的“至善社”是印尼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爪哇籍的官吏,目的是建立一些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学校。
收稿日期:2006—04—03
标签:苏加诺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古兰经论文; 穆斯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