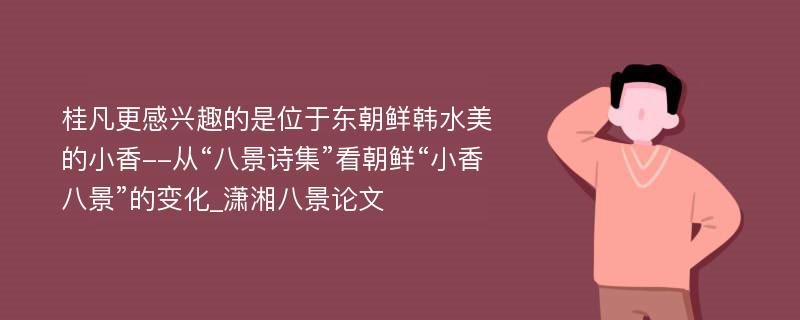
归帆更想潇湘趣,孰于东韩汉水湄——从《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看“潇湘八景”在韩国的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潇湘论文,汉水论文,八景论文,韩国论文,更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5939/j.jujsse.2015.04.017 1442年,朝鲜安平大君李瑢(1418-1453,字清之,号匪懈堂)从中国明朝周宪王朱有燉(1374-1437)所刻的《东书堂历代法帖》(成于1416年)中接触到宋宁宗赵扩的潇湘八景诗。“而因想其景,遂令其诗,画其图”,取高丽时代文人李仁老、陈澕八景诗系之,“又于当世之善诗者,请赋五六七言以歌之,学佛人雨千峰亦诗之”[1]序文,共邀集19位当时朝鲜文人题咏诗,蝉联为一卷,称为《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诗卷因宋宁宗的潇湘八景诗而发起,体现了潇湘八景从中国向周边国家传播的一个侧面。同时,诗卷汇集高丽、朝鲜两个时代文人的潇湘八景诗于一卷,是12世纪中国潇湘八景东渐韩国,并根植、再生、结果的集中呈现。这些诗歌既有对中国潇湘八景诗画意蕴的承袭,又展示出了别具韩国特色的审美趣味,溯其渊源可以考察出潇湘八景在韩国文化土壤中的流变轨迹,进而把握高丽及朝鲜时代文人对潇湘八景的接受情境及其创作特点与创作传统。 一、潇湘八景东传韩国 《潇湘八景图》最早由中国北宋画家宋迪(约1015-1080,字复古)所创作。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2]210僧人惠洪(1071-1128)最早为宋迪《潇湘八景图》赋诗,其《石门文字禅》(约成书于1124年前后)卷8收有《潇湘八景诗》,其序云:“宋迪作八境绝妙。人谓之为无声之句。演上人戏余曰:‘道人能作有声之画乎?’为之各赋一首”[3]。同时,《潇湘八景图》得到宋徽宗、米芾等人的钟爱与发扬,这为“潇湘八景”诗画的创作、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的“潇湘八景”诗画大约于12世纪初传播至高丽。当时,高丽可能通过外交活动接触到在宋朝上层社会颇受欢迎的潇湘八景题材。据《高丽史》记载,1124年,高丽画院画家李宁随枢密使李资德入宋,“徽宗命翰林待诏王可训、陈德之、田宗仁、赵守宗等从宁学画,且敕宁画本国《礼成江图》,既进,徽宗嗟赏曰:‘比来高丽画工随使至者多矣,唯宁为妙手。’赐酒食锦绮绫绢”[4]657。据《宣和画谱》记载,徽宗御府藏有31件宋迪画作,其中就有《八景图》。与李宁学画的王可训,《画继》记载其“工山水,自成一家,曾做《潇湘夜雨图》”[5]535。李宁很可能因宋徽宗、王可训之故,接触过宋迪的或其他作者的《潇湘八景图》。此外,高丽朝明宗十二年(1182年)李仁老(1152-1221)以书状官随使团入金;陈澕(约活动于1200年)于神宗三年(1200年)以书状官随使团入金。这些文人使官在出使中国北方金国的过程中也有接触“潇湘八景”诗画作品的可能。创作“潇湘八景”诗画的最早记载出自《高丽史节要》:明宗十五年(1185年)“命文臣制《潇湘八景诗》,仿其诗意,摹写为图。王精于图画,与画工高惟访、李光弼(李宁之子)等绘画物象,终日忘倦。”[6]342-343《高丽史》也有相关记载:“王(明宗)命文臣赋‘潇湘八景’,仍写为图。”[4]567二者虽可互相印证,但除了李仁老、陈澕的《宋迪八景图》的相关诗歌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高丽明宗时期的潇湘八景作品。颇有意味的是,《高丽史节要》、《高丽史》(成书1451年)的主要编撰者分别为朝鲜的金宗瑞、郑麟趾。二人正在1442年安平大君题咏“潇湘八景”活动的请赋之列,此外还参加了安平大君1447年题咏“梦游桃源图”,1450年题“倪谦、司马恂赠匪懈堂诗帖”等活动,与安平大君过从甚密,同属于以安平大君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他们与安平大君拥有某些历史共识:其一,公认高丽明宗赋咏“潇湘八景”是史实并引起了热爱文人聚会活动的安平大君的兴趣;其二,公认李仁老、陈澕的“潇湘八景诗”为古今绝唱,而将其作为韩国赋咏“潇湘八景”的肇始与彪炳。因此,当安平大君在朝鲜的宫廷中再次发起题咏“潇湘八景”活动时,便具有一种与高丽明宗命制“潇湘八景诗”活动遥相辉映的意味。这似乎是在追慕明宗时代开创的赋咏“潇湘八景”的传统,并以《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为枢纽,作为对此传统的疏通与传承。 安平大君承接的赋咏传统无疑是“宫廷化”的。他体现出更强烈的文人化创作倾向,把李仁老、陈澕的“潇湘八景诗”置于《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卷首,客观上使得李、陈的作品也被“宫廷化”了。《梅湖遗稿》中作于18世纪的《梅湖公小传》记载:“明宗尝命群臣制‘潇湘八景诗’,公(陈澕)以童丱,亦作长篇,气格豪壮,与李大谏仁老诗,俱为绝唱。”[7]270将陈澕的《潇湘八景诗》与明宗命制“潇湘八景诗”的活动联系起来看,陈澕以儿童身份参加宫廷活动是不可能的,但是后代文人在考证陈澕《潇湘八景诗》的创作时间时,十分愿意将其绑定在明宗发起的宫廷赋咏活动中。可见,这个“宫廷化”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学者衣若芬曾指出《高丽史节要》、《高丽史》的记载值得商榷。她认为按明宗赋咏潇湘八景的记载看,其先“命文臣制《潇湘八景诗》”,再“仿其诗意,摹写为图”,可以不依据图画写作“潇湘八景诗”,说明“潇湘八景”诗与画两方面发展均已成熟。在“《潇湘八景图》刚传入不久的高丽中期,恐怕还没有这种条件。”[8]164-165如果衣若芬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安平大君赋咏“潇湘八景”的活动与《高丽史节要》、《高丽史》的编撰便具备一种合谋性,这会带来更具意义的探讨。但是,笔者认为明宗时期的文人是完全可以不依据图画来创作潇湘八景诗的。因为在汉文化语境中有“诗画同源”的传统,其至高境界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与画本是不可分割的“异体同构”范式,亦即“佳诗必孕画境,妙画必含诗意”。而“潇湘八景”事先预设了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与渔村落照八个富含诗情画意的人文图景,其本身就易于激发文人墨客的创作冲动,根本无需因画题诗或由诗生画,二者本质上不存在谁为谁的创作依据问题。此外,汉诗创作中有追和的传统,由诗到诗不需要依据图画,尤其在韩国汉诗的创作传统中有追和与拟次等方法。因此,韩国“潇湘八景”诗与画的创作没有必然的依赖关系。 二、潇湘八景的韩国化 首先,“潇湘八景”的韩国化是从对中国八景原型的接受与重新书写开始的。韩国文人以自我固有的审美理想观照与审视源自中国的八景物象,对八景物象进行了重新的意象化和意境化的审美再创造。这种经过韩国文人再创造的八景意象与意境在“潇湘八景”韩国化的过程中具有奠基的功用。 据考证,韩国最早的潇湘八景题画诗创作始于李仁老、陈澕的《潇湘八景诗》,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潇湘八景”的最初接受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单就“潇湘八景”而言,是在宋迪等人的创作中成熟并得到传播的。但“潇湘八景”只是源于中国先秦的潇湘文学与唐宋山水绘画传统的阶段性产物,在“潇湘八景”东传韩国之前,中国的潇湘文化已经以文字、图像的方式流播到韩国。《文选》、《楚辞》与唐宋诗歌等大量寓含“潇湘”意蕴的文学作品早在新罗时期便已传播至韩国。在李仁老、陈澕之前,韩国山水诗中运用“江、雨、舟、雁、月、雪、浦、岚、寺”等不同意象构筑诗境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如崔致远《陈情上太尉》“客路离愁江上雨,故园归梦日边春”[9]125、朴仁范《江行呈张秀才》“兰桡晚泊荻花洲,露冷蛩声绕岸秋。潮落古滩沙觜没,日沉寒岛树容愁。风驱江上群飞雁,月送天涯独去舟”[10]30、崔承祐《忆江西旧游》“团团吟冷江心月,片片愁开岳顶云。风领雁声孤枕过,星排渔火几船分”[10]37、郑沆《题僧伽窟》“崎岖石栈蹑云行,华构隣天若化城。秋露轻霏千里爽,夕阳遥浸一江明。漾空岚细连香穗,啼谷禽闲递磬声。可羡高僧心上事,世途名利揔忘情”[10]58、朴浩《江口秋泊》“荻花如雪雁南飞,倚棹行人动所思。晚浦风微青霭合,霁江云尽碧天垂。鸡潮冷溅渔船枕,蟹火斜连岛寺篱。湘瑟未休峯自翠,钱生新得梦中诗”[10]62等。 在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韩国文人对于那些与潇湘文化有关的“鸿雁”、“夜雨”、“明月”、“渔舟”、“湘瑟”等意象及其所凝造的意境已经化用纯熟。如,“海左七贤”之一、与李仁老并称的林椿(约1152-1190)的诗歌《渔父》: 浮家泛宅送平生,明月扁舟过洞庭。坛上不闻夫子语,泽边来笑屈原醒。 临风小笛归秋浦,带雨寒蓑向晚汀。应笑世人多好事,几回将我画为屏。[9]212 诗人纯熟地运用了渔父、明月、扁舟、洞庭、秋浦、雨、寒蓑、晚汀等频繁出现在潇湘八景诗中的意象,寓含着“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等意境元素与氛围,而且“几回将我画为屏”表明诗意中隐含着画境。因此,在定型化了的“潇湘八景”范型舶来之前,潇湘八景的主要意象和意境在韩国的诗歌、绘画中已经普遍存在,而当潇湘八景中的“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诗境氛围舶来之后,作为一种审美的“召唤结构”,激发起了韩国文人固有的“潇湘情结”,潜在地满足了其审美的“期待视野”。于是,韩国文人在“潇湘八景”中重塑“自我”的山水意象,进而使得“潇湘八景”情境在韩国诗画创作中蔚为大观。 其次,“潇湘八景”的诗意空间极具开放性,激发了众多韩国文人的创作冲动,使其可以自由地驰骋自我的本真情怀、彰显自我的本质力量。文艺创作本质上是创作主体的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这种活动需要创作主体将自我与创作活动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正如鲁迅所言:“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到别人指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出的东西。”[11]497-500“潇湘八景”所蕴涵的审美“张力”与“生命律动”恰好为创作主体开拓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自我意识、进行自我拷问、呈示自我情怀的诗意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文学与生活间的距离,使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都可借由诗意想象及“高峰体验”在“潇湘”情境中反观自身,确证自我。这是因为“潇湘八景”意不在写实,而是趣在写意。如“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八个典型画面,并非实指现实,即便“洞庭”、“潇湘”也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胜境。邓椿《画继》言:“盖复古先画而后命意,不过略具掩霭惨淡之状耳。”[5]534赵希鹄在《古画辨》中亦言:“宋复古作《潇湘八景图》初未尝先命名,后人自以‘洞庭’、‘秋月’等目之。”[12]87可见,宋迪似乎只是以烟水迷濛的印象作为统领其平远山水绘画创作的主要意境,而并不强调实景的依托。这与中国绘画在宋代由写真传神向写意达情的审美取向旨趣同归。日本学者铃木敬认为:“完成八景图没有必要一定与潇湘实景有多大关系,恐怕是借云气濛濛的潇湘之地制作出八景,进而挑战水墨画的极限。”[13]274正是这种诗意传达不必遵循生活逻辑的文艺创作的规律性特征,使得韩国文人可以化用先秦以来的“潇湘”汉文学情境,自由撷取相关生活图景进行文艺创作。他们可以从湘妃啼竹、屈原流放中恨别思归,也可在庄子寓言、桃源故事里向往和美自得,将潇湘八景的体验置于无限的可能性之中,给予接受者以自由想象、率性抒情的广袤空间,不会因不能亲临潇湘实地而产生审美距离。另外,潇湘八景所提供的八种情绪氛围自成意境。八景择取了“落雁”、“归帆”、“秋月”、“渔舟”、“暮雪”、“夜雨”、“渔村”等物象并将其浑融于总体的“潇湘”情境中,对潇湘八景诗的内容表现与意象选择起到潜在的统摄与规约功能。但“潇湘”情境的总体基调并不影响八个子情境所独具的画面感与境界的情感趋向,在《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的大量诗作中,大多都对八种情境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如赵瑞康《五言排集》: 钟声烟外落,帆影浦头迟。(烟寺晚钟、远浦帆归) 夕照明渔店,经岚带酒旗。(渔村落照、山市晴岚) 雁飞依曲渚,雪洒满寒湄。(平沙落雁、江天暮雪) 水阁蟾光冷,江昏雨脚垂。[1]19(洞庭秋月、潇湘夜雨) 在此,诗人以自己的情感逻辑组织与重构“潇湘八景”,生发出异样的诗歌境界。可以说,“潇湘八景”的每个单元本身便是画面与诗情的触发点,其基本意象与时空元素相结合,通过诗人的引譬连类,感兴抒发,便可创造出极为丰富的抒情意境。同时,“八景”意象与一般山水诗的意象相融共生,因此,在中、韩两国众多的山水诗画作品中,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化用“潇湘八景”中的一个或几个片段,构筑诗境。如李奎报《江上偶吟》“滚滚长江流向东,古今来往亦何穷?商船截破寒涛碧,渔笛吹残落照红。鹭格斗高菰岸上,雁谋都寄稻畦中。严陵旧迹无人继,终抱烟波作钓翁”[9]299,便同时化用了“远浦归帆”、“渔村落照”、“平沙落雁”的意象。 再次,“潇湘八景”的形制、规模及内容在其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辅助性作用。潇湘八景为何定型为“八景”,有学者认为其受到了道教八宝妙景、八卦神景、八色光景的影响[14]142-144。南朝陶弘景《真诰·甄命授》中有“仙道有八景之舆,以游行上清”[15],驾车在天上游览与平远山水俯视视角相合,颇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衍生的过程中,“八”或许提供了适度的形制和规模,“八”与讲求雍容的宫廷文化契合度较高,可与成规模的装饰相匹配。总之,“八景”在形制和规模上符合了宫廷文化创作对规模的基本要求,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潇湘八景文学创作的三个特点:文学参与主体的文学水平高;参与群体庞大、社会影响深远;文学模式的社会效应显著。因此也就极大地推动了潇湘八景文学创作在韩国文坛的蓬勃发展。另外,从形制上看,四言八句便于记忆,长短适宜;从内容上看,“八”片诗句为一组,信息容量大,有助于参与者的情感介入。 “潇湘八景”在韩国化的进程中,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韩国古代文人的审美期待心理。这种“期待视野”主要源于两种力量的促动:其一是陶渊明的“山水田园美学”理念;其二是苏轼文学创作观以及“诗画一律”的诗学追求。韩国山水田园文学的创作价值取向以及诗艺性的表现手法都可以从这二者身上找寻到一定的渊源。 首先,潇湘八景是韩国“慕陶”、“效陶”情结的另一种演绎。文人士大夫对陶渊明的“归去来”有着崇尚但难以践行的复杂心态。他们羡慕陶渊明在自然山水中自由地追求清风高趣,如李仁老在《青鹤洞记》中便有“拂衣长往之意”[16]390与陶渊明的“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17]480的归隐旨趣相同。但事实上,他们并不能将这种理想付诸实施,既企图秉持清高与超俗的品格,却又无法忘却宦海的功名利禄,故而,常常负累于官场的羁束险恶,如金宗瑞所言“中为圭组累,役役走尘坱”[19]19,《五言古诗》。所以,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弥补了一些韩国古代文人现实中的情感缺失体验,使得他们在意念性的山水中游心骋怀,一方面获得暂时慰藉,远离现实负累与理想人生的矛盾;另一方面唤醒对道德的体悟,宣示自我的清流。而潇湘八景图作为韩国文人“缺席”的意念性山水,无疑是另一个“武陵桃源”的范本。如《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中的一些诗句:“遥忆武陵何处在,梦入异境寻神仙”[1]25,安崇善《七言古诗》“知向此间栖大隐,自怜蜗角称钟鸣”[1]29,崔恒《七言律诗》;“披却新图清兴发,渺然身在若耶溪”[1]24,安祟善《七言律诗》;“弧矢当干慕奇胜,每闻八景遥相望”[1]26,辛硕祖《长短句古诗》。 在此,“潇湘八景”被视为“武陵”、“方壶”、“若耶溪”、“兰若”、“奇胜”,隐含着韩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归隐、渔隐、仙隐等思想,流露出对世外胜境的倾慕。 其次,“潇湘八景”在韩国的流播深受韩国文人“学苏”热潮的影响。高丽时代是韩国汉诗史上学苏时代的开始。通过宋朝苏轼等人的作品了解“潇湘八景”是韩国间接接受潇湘八景的重要渠道。苏轼与宋迪交情至深,曾创作《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潇湘竹石图》等文本。但韩国文人对其《题虔州八境图》印象却更为深刻。虔州在江西赣州,与湖南潇湘之地实不相及,例如李奎报(1168-1241)的《虔州八景》八首,其中各景题旨却与潇湘八景基本相类。这是因为潇湘八景东传韩国之初常被称为“八景”或“八境”,鲜见“潇湘”二字,韩国人对于“八景”在“潇湘”还是在“虔州”的认知十分混沌。同为“八境”,苏轼之谓在韩国古代的影响似乎更大,所以李奎报误把苏轼的“虔州”误认作“潇湘”。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韩国古代文人在接受“潇湘八境”的过程中,“潇湘”二字并不是主要的。而且,即便在朝鲜朝“潇湘八景”被充分接受以后,“潇湘八景”已非原来的样貌,这就是不同文化交流中的“主体间性”特征,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误读”。如《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中的诗句:“虔州异景未曾知,一副鲛绡恍惚移”[1]22,安止《七言律诗》;“若为拂尘驾扁舟,直到虔州流华笺”[1]24,安崇善《七言古诗》;“笔锋斫取虔州地,墨池写出洞庭湖”[1]27,柳义孙《七言古诗》。 韩国古代文人依然习惯于从苏轼的“虔州八境”视角创造性地想象“潇湘八景”。此外,伴随着韩国的“东坡热”,苏轼的“诗画一律”的艺术观念曾一度被韩国文坛奉为圭臬,这也成为韩国古代文人接受“潇湘八景”时的一个主要内因,当然这也与惠洪诗序中“无声句”与“有声画”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关。在《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中,关于“诗画一律”理论的阐释占据很多的篇幅。如:“诗是有声画,斯文光焰长”[1]37,卍雨《五言绝句》;“诗为有声画,画是无声诗;世间惟诗画,状物穷妍媸”[1]34,申叔舟《五言古诗》;“有诗无画诗偏淡,有画无诗画亦孤”[1]27,柳义孙《七言古诗》;“新诗如画画如诗,终日展玩不知疲”[1]30,朴彭年《七言绝句》。 显然,韩国古代文人常常善于以“潇湘八景”的诗画创作活动,来践行其对苏轼倡导的“诗画一律”理论的认知与认同。 三、《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的诗歌世界 从李仁老、陈澕创作“潇湘八景”诗始,至1442年安平大君发起赋咏“潇湘八景”的活动,“潇湘八景”东传韩国已跨越250多个春秋。在这个历程中,融汇着不同时代的韩国文人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观念,既有前后承继,也有个人与时代的特色,它们构成了韩国“潇湘八景”丰富的诗歌世界。《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呈现的正是这一历程的两端。对比分析其中的古今之作,可以发现“潇湘八景”韩国化进程中的某些流变情况。 首先,在诗歌的艺术特色上有较高的水准。从诗歌形式和诗歌创作的技巧来看,既借鉴了中国潇湘八景诗的表现手法,同时也彰显出自我的情感世界,将视听合一、景物描写的远近结合、炼字的运用等创作技法巧妙地融合在了“潇湘八景”诗歌创作的过程当中;既继承并发扬了中国文人的创作传统,又极具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例如,李仁老、陈澕均承袭了中国潇湘八景诗一景一诗的做法。李仁老为七言绝句8首,陈澕为七言长句古诗8首,诗歌的内容均以写景为主,将自我情感与田野山水景色的自然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整个诗歌意境极具情景交融、意蕴幽远的格调特征。 李仁老诗舒展流畅,工整自然。如《潇湘夜雨》“一带沧波两岸秋,风吹细雨洒归舟。夜深泊向江边竹,万叶寒声总是愁。”[1]12视觉、听觉、感觉有机融合,使景色和幽怨情愫通过一个“愁”字相得益彰。再如《远浦归帆》“渡头烟树碧童童,十幅编蒲万里风。玉脍银芋秋正美,故牵归兴到江东。”[1]12第一句为近景,第二句为远景,远近结合,拓展了诗歌用思的空间;第三、四句自然化用张翰“芋羹之思”[18]2384的典故而不留痕迹,抒发人生适志、归隐故里的旨趣与追求。再如《山市晴岚》、《烟寺晚钟》等,诗中不带诗人任何感情色彩,体现出“无我之境”的美感风格,诗句与诗题同韵,韵律悦耳浏亮,“林间出没几多屋,天外有无何处山”、“知有莲坊藏翠壁,好风吹落一声钟”,都是自然天成的妙句,引人遐想。在《洞庭秋月》、《江天暮雪》中“欲识夜深风露重,倚船渔父一肩高”,将绘画技法引入诗歌创作,一个“高”字,穷形尽相,将历代“寒江渔翁”孤寂清绝的形象立于笔端。“渔翁醉舞天将暮,误道春风柳絮时”则借助醉翁把暮雪当做柳絮的情节,凸显雪的情状,想象奇特并富于戏剧性。此外,“晓雨初收碧洞寒”、“知有莲坊藏翠壁”、“万顷红浓数点青”、“云间滟滟黄金饼,霜后溶溶碧玉涛”等句,碧、翠、红、青、黄等色彩,具有明丽的光与影的动感。可以说,李仁老的潇湘八景诗清新富丽,尽得唐诗绝句之神韵。 据《梅湖公小传》载:陈澕“善属文,尤工歌诗。清丽雅健,蔼然有正始音。”[7]270其受宋诗影响较大,讲求炼字用事,意深言富,新奇瑰丽。如《潇湘夜雨》: 江村入夜秋阴重,小点渔灯光欲冻。森森雨脚跨平湖,万点波涛欲飞送。 竹枝萧瑟漉明珠,荷叶翩翩走圆汞。孤舟彻晓掩篷窗,紧风吹断天涯梦。[1]15 此诗工于写景状物,光被“冻”住,雨脚“跨”平湖,以及“漉”、“走”、“紧”等字,炼字很精且密度很大,把客观景物赋予主观动态,产生新奇的效果,而且诗歌对仗工整,起承转合于“吹断天涯梦”,内在情感自然流淌,题旨一跃而出。其他如《远浦归帆》“万顷湖波秋更阔,微风不动琉璃滑。江上高楼迥入云,凭栏客眼清如泼”[1]15、《渔村落照》“归来箬笠不惊鸥,一叶扁舟截红浪”[1]14、《远浦归帆》“飞禽没处水吞空,独带清光攒一发”[1]15等,“滑”、“迥”、“泼”、“截”、“吞”、“攒”等字的活用,皆注重用字穷工。其《江天暮雪》: 江上浓云翻水墨,随风雪点娇无力。凭栏不见昏鸦影,万树梨花春顷刻。 渔翁箬笠戴寒声,贾客兰桡滞行色。除却骑驴孟浩然,个中诗思无人识。[1]17 景物描写依然注重炼字,景物渲染颇有寥廓、清绝之感,最后四句用“渔翁”、“贾客”的“戴”、“滞”与孟浩然的“诗思”形成鲜明对比,表明雪后别样的凄清之美,非常人所能欣赏,立意豪放新奇。这一点带有宋诗“用事”、“点铁成金”等作诗技法的影子。 李仁老《破闲集》云:“读惠洪《冷斋夜话》,十七八皆其作也,清婉有出尘之想,恨不得见本集。近有以《筠溪集》示之者,大率多赠答篇,玩味之皆不及前诗远甚。”[19]卷上其中《筠溪集》即惠洪的《石门文字禅》。而陈澕有诗“碧砌落花深一寸,东风吹去又吹来”[7]274,此语出自惠洪《甘露集》中“绿杨深院春昼永,碧砌落花深一寸”①。可见,李仁老和陈澕都曾受到惠洪影响,从潇湘八景诗中也能发现其影响的痕迹,如:“山市晴岚:宿雨初收山气重”[3]卷8(惠洪)/“晓雨初收山气重”[1]111(李仁老);“江天暮雪:泼墨云浓归鸟灭”[3]卷8(惠洪)/“江上浓云墨水翻”[1]117(陈澕);平沙落雁:“翩翩欲下更呕轧/数行翩翩何处雁”“十十五五依芦丛”[3]卷8(惠洪)/“隔江哑轧鸣相逐”[1]215(陈澕)。 应该说,李仁老、陈澕的潇湘八景诗对中国唐宋诗歌的借鉴与化用比比皆是。如李白《杭州送裴大泽赴庐州长史》“好风吹落日”[20]587化生“好风吹落一声钟”[1]11,白居易《江楼晚眺》“雁点青天字一行”[21]525-526化生“行行点破秋空碧”[1]12,苏舜钦《和解生中秋月》“金饼隔林明”[22]化生“云间滟滟黄金饼”[1]12,苏轼《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又不是襄阳孟浩然,长安道上骑驴吟雪诗”[23]化生“除却骑驴孟浩然,个中诗思无人识”[1]17,等等。李仁老、陈澕做到了既继承借鉴前人诗意,又开拓新的审美境界,他们的诗歌即便在中国的潇湘八景诗中也是优秀之作。因此,出现了潇湘八景传播中的回流现象,元朝的赵孟頫喜欢李仁老,化用“欲识夜深风露重,倚船渔父一肩高”[1]12而为“记得太湖枫叶晚,垂虹亭上访三高”[19]197。与安平大君同代的徐居正(1420-1488年)在其《东人诗话》中评论:“李大谏仁老潇湘八景绝句,清新富丽,工于模写。陈右谏七言长句,豪健峭装,得之诡奇,皆古人绝唱,后之作者未易伯仲”[7]283,这一认知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 其次,诗歌形式以及内容的表现也极为丰富多彩。形式上五、六、七言并行,内容上既然为八景诗,与中国一样有较多的赋咏之作,韩国的八景诗创作中也有记评之作和对苏轼“诗画一律”的阐释之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韩国文人的自我情感世界及诗歌理念。1442年,“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创作是多人同题创作潇湘八景诗的一次盛会。参加活动的郑麟趾、朴彭年、成三问、申叔舟等都是朝鲜朝优秀的学问家,参与了1444年“训民正音”的创制,共同开创了朝鲜世宗时代文运昌明的气象。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在形式上更加多样,七言、五言、六言皆有。19位作者中只有姜硕德七言绝句10首、成三问五言绝句8首、崔恒七言律诗5首、释卍雨五言绝句10首采用了宋宁宗、李仁老、陈澕一景一诗的写法,其他都将八景放在一起来表现。[24]125为了便于整体表述与分析诗歌面貌,可按诗歌内容分成三类: 第一类,赋咏八景韵致。以崔恒、释卍雨的分景赋咏成就最高。崔恒诗颇具宋诗神韵,深刻透辟,舒展自如。如《七言律诗》里的“烟寺晚钟”: 点点峰峦露数稜,瞑烟分碧罩山层。依稀飞构树间寺,杳霭孤灯龛下光。 出谷鲸音吟更殷,连云鸟道响遥凌。吴王未易丹青处,要遣工诗扫剡藤。[1]29 “瞑烟分碧”炼字极精,颈联对仗工整,“鲸音”、“鸟道”用事极佳。“鲸音”指钟声,因古代刻杵成鲸鱼形用于撞钟而来,语涉元代宋褧“鲸音历历似秋清”;“鸟道”指山路险绝,同时语关同铭“举足下足,鸟道无殊,坐卧经行,莫非玄路”②的禅语,扣住主题。尾联用吴王姑苏台言山寺之美,“要遣工诗扫剡藤”,指代安平大君赋咏潇湘八景活动,此联吴王修建姑苏台的典故,暗含规箴安平大君不要学吴王贪图享乐之意,其用事可谓深远。卍雨诗翻出新语,诗意雄奇,其“远浦归帆”与“潇湘夜雨”俱为佳作: 一夜湘江雨,三秋楚客心。心应悬魏阙,通昔动哀吟。[1]《五言绝句》 此诗语言概练,触景生情,化用《庄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25]卷9,发忧国之思,慷慨沉郁。姜硕德分景诗化用前代最多,如《烟寺暮钟》: 青烟漠漠锁巑岏,林桧阴森路屈盘。试问招提藏底处,一声钟落白云端。[1]20 此诗与李仁老诗布局、意境基本一致,都以“藏”字隐藏寺院,构筑画面。后两句是李仁老“知有莲坊藏翠壁,好风吹落一声钟”的化用。第三句显示出对寺庙位置的不确定感,钟声被好风吹“落”,可知寺庙在山之高处,人在山脚,钟声从高处下来,位置一语分明。而钟声“落”在“云端”,云在高处,“落”不如“跃”,而前文“青烟漠漠”,无风吹送,不能飞跃,“落”字让空间错乱、逻辑亦不能通,姜硕德不如李仁老入境。此外,其《江天暮雪》“忽放春光满水西”[1]22化用李仁老“千林远近放春光”[1]12,《渔村落照》“渔人收网归茅舍”[1]22化用陈澕“独背晚风收绿网”[1]14,《平沙落雁》“不似玉关绘缴密”[1]21化用李齐贤“玉塞多绘缴”[7]608,《潇湘夜雨》“奈此黄陵祠下泊,蒹葭风雨满江秋”[1]21化用李齐贤“黄陵祠下雨秋声”[7]608等,貌似而诗意不及。成三问诗中常有议论,如《山市晴岚》“最好雨余天,还宜月淡夕”[1]30、《平沙落雁》“所以丹青手,殷勤作尔形”[1]33。其《洞庭秋月》:“明辉发蟾兔,静影浸龟鱼。此中忧乐意,老范不欺余。”[1]33此诗以范仲淹《岳阳楼记》立意,不着意境,略显干乏。 安崇善、尹季童是其中景致描写较为丰富的诗人,其余大都不把写景状物作为重点。如朴彭年七言绝句5首中,只有“烟岚霏霏反照红,雪月炯炯寒江滨”、“吴樯楚柁倏联翩、衔芦影接衡阳天”[1]29四句写景。这些景致描写多翻作八景题目,诗意开拓较少。通观八景景致描写,在化事用典上多有相同之处: (1)张翰思吴:玉脍银芋秋正美,故牵归兴到江东[1]12(李仁老)→千里芋鲈乘逸兴,百年钟鼎寄微沤[1]29(崔恒)/何令盛代士,遽起讨芋心[1]31(成三问)/千里芋方美,东吴客大忙[1]37(卍雨) (2)孟浩然骑驴:除却骑驴孟浩然,个中诗思无人识[1]17(陈澕)→林峦依稀如有雪,骑驴逸兴寻无形[1]27(柳义孙)/乱飘骚客吟驴去,闲漓渔人钓艇回[1]29(崔恒) (3)雁有四德:漂泊楚天长,同群兄弟行[26]33758(宋宁宗)→玉塞多缴缯,金河欠稻粱。兄兄弟弟自成行,万里到潇湘。远水澄拖练,平沙白耀霜。渡头人散尽斜阳,欲下更悠扬[7]608(李齐贤)→不似玉关绘缴密,悠扬直下莫纷纶[1]21(姜硕德)/随阳南又北,遵礼弟于兄[1]33(成三问)/相呼遵礼让,人世所钦哉[1]38(卍雨) 第二类,记评赋咏之事。因为诗歌为王子安平大君请赋之作,即为应制之诗,在记评中自然要对发起者作一番颂扬,夸赞安平大君清雅高洁。 匪懈雅量悬银河,奎光彩笔腾诗思。[1]17 俯仰情怀追造物,逍遥性气等闲人。 个中此乐谁能识,莫道公侯席上珍。[1]19 王子袖中携洞庭,照我双眼还能青。[1]29 贵人高洁厌纷华,故令此物为清观。[1]28 安平大君的确算得上儒雅风流,多次举办艺文活动,招聚文士,“或张灯夜话,或乘舟泛月,或占联、或博弈、丝竹不绝”[27]47,颇有名士风度。同时。这次活动是依据图画作诗,多有表达观图卧游的内容。如:“不出户庭看尽处,渺然清兴入新诗”[1]28;“双眸盛赏佳致,两足何劳远征”[1]25;“远游何必劳精神,对此顿胜卧游翁”[1]30;“披图清燕右,逸兴浩无涯”[1]19;“展卷寓目思不穷,依稀南塞路八千”[1]24;“我今披图赏清景,悠然兴逸羲皇前”[1]34。 所谓卧游,是中国魏晋时期盛行的具有玄学意味的审美方式,主张在欣赏山水画的过程中,将自己融入山水画之形,感觉山水之道。即“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应目会心”、“神超理得”的视觉理念[28]卷93。这种足不出户即可感悟山水精神的方式,恰好适合了韩国文人对中国之境的“缺席想象”,而在山水中体味的道正是理学中“仁山智水”的儒家之道。 仁山智水此性情,静对情窗更昭粹。[1]17 匪懈堂中常对之,仁乐山,智乐水。此中之乐难与说。[1]26 第三类,阐释苏轼“诗画一律”的理念。前文有所论述,此不再赘述。 总体来看,匪懈堂潇湘八景诗除崔恒、卍雨的八景诗可追前代外,其他的诗歌多走进理学义理思想阐发一途,其“平山落雁”的理学化、对仁山智水的论述、对人格清雅的评价、对诗画一律的阐释,均为思想、情志的直接书写,而忽视了诗歌的蕴藉含蓄与个人抒情的恣肆逍遥。 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29]499,韩国潇湘八景诗在不同的时代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李仁老、陈澕生活的年代相距不远,基本为高丽明宗时期,这一时期韩国汉文学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并开启了“学苏时代”,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成为高丽诗人学习、模仿的对象。陈澕的八景诗中注重炼字用事、讲求奇险的倾向正与此有关。但对宋诗的学习仍处于初学阶段,在宋诗技巧之外,作为宋诗的思想基础的理学尚未系统地传入高丽。因此,优秀的汉诗仍然承袭以李杜为代表的唐诗传统,李仁老、陈澕的潇湘八景诗依然保持着积极的抒情倾向。但是,进入朝鲜朝以来,统治者独尊儒教,程朱理学“文以载道”的思想为文学的社会作用重新定位,诗歌的个体抒情属性被忽视,诗歌的社会价值得以肯定,具有了更加浓重的道统色彩与政教属性。“匪懈堂潇湘八景诗”阐释义理,好发议论,与其时代氛围是密切相关的。 伽达默尔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30]267“潇湘八景”诗之于古代韩国文人亦如此。经高丽明宗时代初步接受,至李仁老、陈澕对韩国潇湘八景写作范例的开启,其间有高丽后期李奎报、李齐贤等对潇湘八景诗的开拓,至1442年匪懈堂潇湘八景诗的群体赋咏,具有其民族特色的潇湘八景书写的历史脉络已基本明晰。其总体特征如下: 一是中国的潇湘八景传入韩国之前,已经是一种定型化、模式化的诗画形态。在宋迪之前,“潇湘八景”以散乱的形象分布在前代的山水文学与山水画作品中,传递的是由个体出发在山水中体悟的人类的共同情感。但随着山水作品的大量出现,这些散乱分布的形象反复出现,便可以逐步被归纳、整理、定型。宋迪《潇湘八景图》的开创之功不在于精湛地描绘了潇湘山水,而在于对山水画中的系列形象进行了定型化的归纳与总结,而这种定型化、模式化是艺术的转折点,与艺术创作的自由属性背道而驰,但是却能推动此类题材的迅速流传。 二是韩国接受的正是流行的、被定型化了的潇湘八景。定型的“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这八类意境氛围,犹如八个作文题目规定着韩国文人不断进行着命题作文。这一点十分类似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赋得”与“试帖”,即以古人诗句作诗。由于必须扣题写作,尽管其中也有佳作,竭力翻出新意,但更多的往往是规摹前人,难以自出手眼。但这种命题写作之所以被广泛采用,在于其具备竞技的功能。一方面,命题的规定性提供了诗歌较多的可能性,以同样的内容作诗,更能比照出作者诗歌技巧与诗歌修养的优劣高下,使人更容易辨识好的诗歌技艺,进行学习或者超越,后代文人不断创作的动力似乎也有试图超越前代的驱动力。另一方面,被定型化、模式化的题材其范畴、内容更容易为大家所熟知与掌握,为多人同题赋诗竞争、娱乐提供可能,因此,形成了文人聚会同题共作竞争诗歌技艺和学问的娱乐方式。高丽明宗命制八景诗的活动与匪懈堂潇湘八景诗赋咏活动,正是建基于此的文人娱乐活动,大家同题共作,一试心性,二试捷才,自然别有乐趣。但是,同题意味着题材的狭窄,要想出众只能在技巧与学问上下工夫。韩国潇湘八景诗创作中,典故化用丰富精湛,展示了他们深厚的汉学功底。事实上,高丽时代韩国便开始科举制考试,科举考试的机制正是这种同题竞争的性质,韩国文人对此自然得心应手。 三是潇湘八景流向韩国带有时尚性。正如西方人学习喝茶,首先是从上流社会开始进而普及大众的。这是与上层社会的消费属性相连接的,他们未必是生产者,但是当生产者创造出优秀的成果时,他们的地位决定其可以最先使用、收藏、标榜、炫耀,这都是消费行为,而上层社会的消费便是时尚。宋徽宗、宋宁宗、明成祖等很多帝王公侯收藏、创作潇湘八景诗,沈括说“好事者多传之”[2]210,好事者或许指代的就是这些与艺术原创无关的人,但是他们推动了潇湘八景诗成为时尚。韩国最初接受“潇湘八景图”或许正是由于中国宋代宫廷对潇湘八景的钟爱,而将其作为时尚引入的。因此,古代韩国对潇湘八景的追捧及其创作热情似乎要超过中国。高丽明宗、安平大君举办命制潇湘八景的活动,或许正是以此为时尚来标榜自己风流儒雅和国家的文运昌明。虽然时尚不能推动产生优秀的诗歌原创,但时尚之风,自上化下,却可推动一种文学题材的普及与大量创作。在朝鲜中后期,《春香歌》、《沈清歌》、《兴夫歌》等清唱作品中出现游览潇湘八景的情节,正与时尚的下移普及相关。 韩国自12世纪始至19世纪,在长达700年的时间里以“潇湘八景”为题的汉诗计470余首,时调、歌词等有10余首,《春香歌》等清唱、小说作品频繁出现游览“潇湘八景”的情节。[31]146-158可以说,在接受潇湘八景的过程中,韩国作为文化输入国扮演着追捧、调和、丰富、回馈以及维护保存者的角色。在《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中,李甫钦写道“归帆更想潇湘趣,孰与东韩汉水湄”[1]26,这句诗颇能代表韩国接受潇湘八景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更想”可以说韩国文人对“潇湘八景”的青睐已远超中国文人,因此更有咀嚼、玩味的兴趣。同时,大多数韩国文人对潇湘的景色是想象的和文化的,可以脱离实际,以任何的山水进行吟咏潇湘,即使是韩国汉江的风物,在对江、帆、雁、月等的描述中,都可以发现潇湘的味道。当然,由于题材的狭窄,我们无法看到太大的超越,但却达到了一种题材上的精熟与普及,并将外来的“潇湘八景”化入了韩民族的民族文化血液。当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总是以民族文化进行抗拒和改造时,这一文化接受的现象似乎颇有镜鉴意义。 ①徐居正《东人诗话》云:“近得《甘露集》,乃宋僧诗也。其诗云:‘绿杨深院春昼永,碧砌落花深一寸。’”《梅湖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卷,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 ②“禅道至难,险如鸟道,鸟道者地名也,又至道寥廓,如空中鸟迹也,洞山录曰:‘我有三路接人,鸟道玄路展手。’玄中铭序曰:‘寄鸟道而寥空,以玄路而该括,然虽空体寂然,不乖群动。’祖庭事苑四曰:‘鸟道犹虚空也。’南中入志曰:‘鸟道四百里,以其险绝兽尚无蹊,特上有飞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