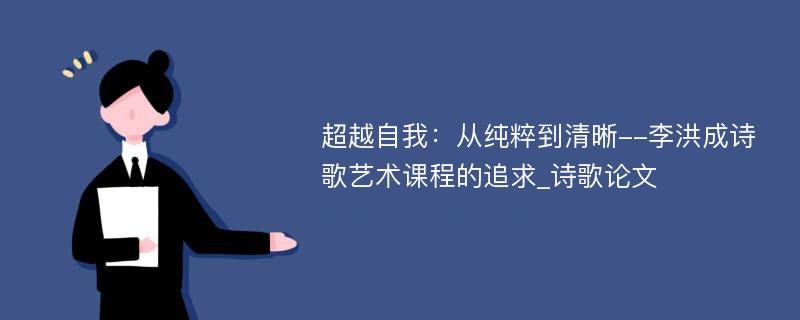
超越自我:从清纯走向澄明——追寻李洪程的诗艺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澄明论文,诗艺论文,超越自我论文,历程论文,清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代就登上中国诗坛的李洪程,已经走过了将近40年的诗艺历程。70年代,一部长篇叙事诗《斗天图》流播全国。他做为作者之一,此后经过一段艰苦的新的探索,逐渐从体现清纯诗风的放歌时期向进入澄明诗境的沉吟时期过渡。1993年,诗集《人生乐天图》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发行,标志着他继叙事长诗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李洪程是一位有着相当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的严谨诗人,从他进入新时期以来所创作的诗歌短章里,可以明显看出诗人怎样奋力紧追时代步伐超越自我,将其质朴而隽永的诗风融进更广阔的大自然怀抱,并自觉地带着对人生的深层思考,去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至情至美,终于从“斗天图”中迈进一个新的充满诗意的“乐天”世界。
一
诗人的天职决定了诗人必须赋有艺术美感,善于艺术地感受生活、表现生活。李洪程就很注重把生活提炼为独特的审美意象,并力求在艺术的陌生化与生活的平易性之间保持适度,特别是在感受政治生活时也是如此。他在经历了政治风云激荡的岁月之后,重新调理自己的歌喉,即使在带有政治抒情意味的诗篇里,也努力突出审美感受。
赴上海,他看到“一大”会址正在整修,不由得怦然心动,高声唱道“我来兴业路,瞻仰‘一大’会址,/见高高的脚手架,托起一团霞日。/敬礼!党啊,时代的建筑大师,/请接受我递上去的一片砖石……”(《写在党的脚手架上》);在南京的莫愁湖边,他怀念去世不久的周总理,而且将六朝莫愁湖的故事与当代伟人的风采有机融合起来,“我听出了您那故事的真谛,/你意在论今,我何须访古?/一千五百年间赞美莫愁的歌赋,/怎抵你长笑一声,豪情尽抒!”(《莫愁赋》)。浓郁的政治抒情意味中包含着诗人对历史的追问,对人生的反思。而对于变得愈来愈遥远的年代,他异常冷峻地自省着因为时间所造成的种种缺憾,“莫非仅仅失去了你/失去了本可以不失去的/也许失去的后面正是得到的/但愿得到的不要再失去”(《假如原来没有你》)。在一唱三叹中,低回旋转着他那执著的心声:“如今既然失去了你/可叹我的忆念未失去/最好我的忆念也失去/假如原来就没有你”。
新时期已经催开了他那迸射的勃勃诗情。他曾是河南省四届人大代表,当他庄严地执笔在大红的选票上,实行人大代表的神圣权利时,那看似平平常常的一笔圆圈,蓦然在他的眼前变成“雨后晴空的太阳。/光影满轮的月亮。/绿叶上的朝露。/蚌壳里的珍珠。”他无比深情地呼唤:“我们画圆——//圆心——人民利益。/圆周——有限与无限的空间。/民主集中制的果实。/共和国国徽的光环。”但是,诗人的思绪不仅仅停留在热烈的抒情上,他更是将一系列象征、比喻,用诗歌的语言,把“圆”的嘱托和期望尽情唱出。
李洪程的诗品与他的人品一样,他将自己的一颗诗心奉献给永远鼓励他生活的现实社会和养育他的劳动人民。早在1957年,年仅19岁的李洪程创作了《春晓》,在这首稍带朦胧意味的诗里,一颗年轻的心与太行山的早晨交相融和,“树稍挂起炊烟缕缕,/一只雄鸡在山头高歌漫步。/我正要问一声:太行,你早!/阳光已注满千万条山谷。”这里,雄鸡的形象被放大无数倍,构成特写镜头,造成美妙的意境;选择一位少年在经过战火的洗礼迎来和平幸福的春晓里,向太行问早这样一个特定的画面,虚实结合,情景相生,传达了建国初期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80年代初期,正是李洪程诗歌风格的转折期,他歌唱金秋,钦佩农民的劳动和智慧,“我真佩服老农,/打一个比方,/就浓了千顷诗情!”(《大豆摇铃》);当他在夏夜看到“露水闪”这“城里见不到的奇妙夜景”时,就“撩起衣角,且煽去一襟暑热,/真想在田埂上坐到天明。”(《露水闪》);乡村文化室也勾起他浓浓的诗情,“我的诗是采莲盆儿,/荡漾在荷塘的新秋。”(《乡村文化室印象》)。诗人是那样执著于牵襟动怀的乡土棉麦风,而这正是构成他放歌人生,乐对长天的情感基调和思想底蕴的一种重要因素。
二
诗再造语言,语言的诗性使用造成一个特殊的真实。语言使诗坚实到足以切开感觉。过去我们总是太多地看到了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某种食洋不化和对老庄学说中关于“言”、“意”之辩证观点的食古不化。如何在充分吸收这种有益营养的基础上,构建我们自己真正意义的诗学理论(而不是哲学的或语言学的),是当前诗歌语言意识强化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从总体来说,李洪程是一位以抒发山水豪情见长的,而且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诗人,他不刻意追求诗中所谓哲理的玄奥和空灵的禅机,而是在纵情放歌山水之间或是在自然美景的大写意中,去捕捉随机而来的顿悟和灵感。他喜爱引用一段很精采的话:“中国的政治诗之所以不流于口号式,原因之一是由于山水诗的发达促进政治抒情的形象化、多样化;中国山水诗之所以情景交融、意蕴深厚,原因之一是由于政治诗的发达赋予山水诗以社会内容的寄托。”〔1〕李洪程的诗艺路程最早起步于山水诗,那绵延起伏的太行山就在他的家园的北部和西部,抬头可览晴翠,劳步可登云峰。他极爱跨乡过县,结伴壮游。最令他神往的是林县红旗渠之行,他置身人造天河,恍若幻境,迤逦沿渠盘山,尽览三千华里工程宏图。正如他曾深情地谈到:“我生于平原,也热爱大山,平原养我以坦荡、平和、宽厚的心性,大山启我以奇崛、变幻、立体的美感”(《人生乐天图·后记》)。这些正是他的诗歌深植于生活沃土的力量源泉,他离不开大地,即便在他的一些飞云渡日的浪漫诗中,从那跳动着的字里行间仍可嗅到浓郁的最初与恒久的山河之恋。
他的诗第一次和读者见面的时候,就表现得是多么神往而专情于他的母亲山——太行山啊!“对于你,如花的太行,/我应该表示怎样的爱恋!/我愿爬遍你所有的山岭,/让每一块山石都留上我手心的温暖;/我愿访遍你所有的峡谷,/喝那如蜜的泉水,/让每一条溪流都流进我的心田……”(《放歌太行山水间·我愿走遍太行山》)。30余年后,他对太行山那缠绵的爱和依恋的情仍然没有丝毫消减。他无比深情地歌唱太行山,“化不开的凝思/抒不尽的眷恋/日夜守着大山总是缠缠绵绵/藏着吨吨春雷/藏着条条闪电/藏着无数神奇无数梦幻”。山之情、山之威,尽在太行山的烘托中展示出来。
跨过时间的界河,横穿历史的烽烟。八百里太行曾是“火的宣言”,三千里红旗渠曾是“水的壮歌”,而这一切都聚成了“无数新的词汇正进入新的生活/同大都市对话向世界远播”(《山词》)。此“词汇”,此“对话”,把无限扩展的时空留在了诗外。那歌咏仿佛是拂晓的一片朦胧,跳跃的旋律变幻出的山河间一派生息吐纳,物物对话的无边声响与诗人的心灵交汇,闪烁着充实而瑰丽的生命之美!
在《大野秋色》里,诗人面对“不是描眉画目的小家子气/而是让天地增色的大手笔”般的漫天秋色,联想到“红色曾被西洋称为帝王的颜色/黄色曾在中国象征皇帝的颜色”,而“大野秋色绝非单一色/秋色属于我们大地上的众生”。大野雄浑,秋色多姿,情与景得到有机统一。笔染时空,纵横挥洒。在另一首《大平原写意》中,更是将历史融入现实,将豪放汇于执著,尽情讴歌中华民族的黄土之魂,使大平原的壮阔和雄浑尽在笔下,诗情旷达而超脱,意境幽深而宏远。诗人热爱大平原与他热爱大山一样,都能和生活劳动、生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当他纵情歌颂平原日出之后,将大自然的壮美和劳动场面的优美融汇一起了。“村里的鸽群起飞了,/总爱向朝霞升起处飞个自在。/乡亲们的车马下地了,/正和旭日撞个满怀。/……”(《平原日出》)。这些诗歌语言并不费解,不需要再次解读,但在诗情画意中,无不蕴藉着日常语言所难以达到的力量。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而现实生活的结构就是一个语言的结构,人也无往而不在一种语言(日常语言)的制约之中。而诗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人(海德格尔称之为“常人”),则是因为诗人极力以诗的语言来对抗普通日常语言。诗人创造性语言之重大人类学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打破了人们日常的感觉思维方式,把人从某种散文化的现实世界的麻木状态中解放出来,在其中展示一种新的、使人得以诗意地栖居的“陌生化”的艺术世界。李洪程的诗歌语言并不讲究奇崛险怪,但他对待诗艺有着一种苦心推敲,宁可不写也决不粗制滥造的执著精神。所以在他抒写山水的诗篇里,一颗真诚的心与闪电般的灵感一经契合,便迸射出耀目的火花。
三
当然,现实主义的创作不等同于对生活的摹仿,将观察生活中所见所闻直接搬到作品中去。诗人的创作是根据自己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对世界形成的认知结构和对现实生活进行选择的结果。尽管客观世界的一切均外在于我们的主观世界,但诗人所看到的只是自己想看到的,是他对自身发现的一种解释,而读者也是依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对诗人所提供的文本作出创造性的读解。毋庸讳言,李洪程在他的诗歌语言中,在对天工造化的尽情讴歌中,无形地流淌着一泓富于辩证哲理的血脉,尽管不是他所刻意追求的,但是他经过沉思过滤的诗中气象使之然。在他的《时间》、《认识你自己》、《对语石》、《反差》、《半山亭》等清新隽永的哲理短诗中可以窥见一斑。就是在他或明丽柔曼或大气磅礴的抒情诗章里也时而体悟到一种超脱尘俗并令人解颐抚然的顿悟之美。比如他在歌唱春天之余,没有忘记:“春天有温暖/也会有寒流/春天有欢乐/也会有烦忧”。因为“识透春天的辩证法/就妙于运筹”(《贺春辞》)。他同时也歌颂秋叶,“成熟的还有你叶子/你脱落了/果实似地脱落了”,“你翻转着/旋舞着/嗒的一声/大地也微微一颤/而你的飘落/使秋树进入返老还童的过程了”。这里的秋叶不仅是寄托一般思想的象征物,体现了成熟和丰收,而更不同凡响的是诗人寄之以“返老还童”、生命复始的新意。“更令人惊奇的是/你几乎所有的秋之落叶都背面朝天(不知朋友们是否都有此发现)/你面向大地/默默地/热切地”(《秋叶》),最后点明题意。但因诗句中的能指与所指恰到好处地间隔,使人在领悟中顿生一种回肠荡气的感觉。细读李洪程的诗,可以看出他几乎对四季都有偏爱,很难分出伯仲。但他不停留于四季的表面特征,却往往能够从一般的思维中掏出令人振奋的理趣。
每一位为生活而歌的有真情的诗人,并不想纠缠诗歌起源于什么,他们所确知的是自从有记载的诗歌史以来,社会便把一种道义职责委托给了他们,使他们描述,表达和评价社会现实,并以此构成对社会缺陷的补偿,对各种有损于社会健康的社会现象加以纠偏。正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离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为了那些弱者,那些被不均等的机会所排斥的少数人,那些收入和财富地位迅速下降的小人物,诗人必须重新深入生活、深入社会,重新表现生活、表现社会。作为一名正直的诗人,为现实、为人民立言,是他的首要责任。李洪程的诗歌,不论是写普通劳动者,还是写一代伟人,都能调遣独特的诗歌语言构塑一种顶天立地的伟岸气质。他写乡亲的脊梁:“脊梁上照人,/比镜子还亮。/脊梁上滚雷,/不摇不晃。”“挺起来——/为撑起一颗正直的头颅,/不为撑起一件衣裳……”(《乡亲的脊梁》)。他写鲁迅与西湖,虽然“柳浪闻莺。白堤。苏堤。/曲院风荷。湖山宜晴宜雨。……”而“他面对湖上景色,/只说是‘平平而已’!”并且“以为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问题并不停留于此,而是用一个补缀,通过反衬来展露鲁迅人格的伟大:“(谁不知——/一个不为西湖所陶醉的人,/却在艰苦卓绝的一生中,/创造着美,/捍卫着美……)”(《鲁迅与西湖》)。怎样使政治倾向与诗歌语言巧妙地融合,李洪程用他的创作实践作出了最好的解答。他认为政治思想性是不言而喻的东西,要追求诗歌的意境,就必须用独特而充满魅力的语言艺术来表现。优秀的诗歌与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不矛盾的。
四
既然现实主义不是摹仿和照搬,那么我们就要设问,为什么现实主义诗歌可以起到对现实生活的参照作用?我们认为当代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的“图式”说对这个问题作了较好回答。他说:“作为图式的一个命题要求(1)命题中包含的名称必须与被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个体相关;(2)它们共同构成的命题必须彼此相互处于某种特定的Significant(有意义的)关系之中,有一定的逻辑结构, 表现为一定的逻辑形式。”〔2〕正是由于这样的诗意的逻辑同构与事实的逻辑同构,才能将诗歌中的“图式”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境联系在一起,起到相对照作用,即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维氏的“同构”理论不能仅仅看做是解析现代派诗的钥匙,同时也对一切标准的(典型的)诗歌语言起作用。
李洪程诗歌的风格,受古典诗词影响较大,他的作品所以雅洁凝练,气韵贯通,读来琅琅上口,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这种语言风格很适合于他的山水风物一类的题材,可以说,二者达到了相得益彰的结合。他在《无声的月歌》里长吟道:“你可以随时走进这歌的画面(但要小心碰响这一片天籁)/让喧闹着的一颗现代心/姑且净化在这无声的月歌里”。这种追求静谧和谐的韵味,恰与讲究空明灵秀的庄禅美学有了“历时”的“同构”关系,可以在无为无不为的清幽淡雅之中,去品味妙若天成的意趣。
同时,李洪程又是一位在诗艺上兼收并蓄的开放型的人。他注重创作实践,又兼顾理论探索。他善于反思自己实践,把在创作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的创作始终是在清醒的理性的引导下进行的。再加上他善于和乐于对人生进行多方位的思考,使他的作品表现出明显的理性特征。他认为当代诗歌“应以融合今天为主。但在空间的远距离融合上有时对诗歌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放出奇葩。”〔3〕比如他的山水诗大都体现一种人格化的力量, 而且很注重通感的运用。他五、六十年代的早期诗作里,就有“山歌挂满枝头”和“屋头飞不起半湿的炊烟”之类的诗句。在《伊河涉足》里,他将涉足者和伊河的情态融为一体,很难分出彼此。“经谁一声提示/便有十几双脚踏进琼瑶/伊河水霎时改变了音韵/龙门山笑倒在碧波里”;他因登临匡庐而联想起古代的诗人,“新修的如琴湖蓄满春水,/真象一路琴声,弹出花径出门。/来听吧,白司马,你是知音,/这比那浔阳江上的琵琶声,/更撩你诗魂!……”(《白司马花径》);他放舟东海,当他不由在沙滩上题赞美之诗句时,“不料海潮涌来,似有意和我嬉戏,/水摇沙平,一下子抹去了字句。/大海呀,大海,/你美丽又如此谦虚!……”(《海滩题诗》)。这样,皆使那一景一物和寻常的旅行,着上了不平凡的感情色彩,给人以开心益智的启迪。李洪程不太注意于诗外去追求技巧。他认为技巧决不是外饰的小玩意儿,它是诗本身。没有技巧不称其为诗,只是一堆儿“想法”,正象没有烘烤的面包只是一堆面团。因此,读他的诗,特别是读他的那些吸地阴之气、饮天阳之精的山水诗,无形中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如沐浴甘露,胸中尘俗涤荡一空,怡于神、美于心、畅于体、虚无纯静,如梦似幻,俨然步入一种物我两忘的极乐天地。
“白了少年头,痴情仍未了”,李洪程近40年的诗艺历程,横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同时期,而真正使他焕发诗人青春的是令人振奋的改革年代。我们感到正如一首无名诗人的诗句所描写的那样:“当我的左脚/踩住右脚的鞋带/我的身子就倾斜了/原来自己也能/把自己绊倒”。他一直在艰苦的跋涉中改变自己,充实自己,磨砺自己不老的诗情。尽管他自己并不认为他是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诗人,但他特别热爱与那些具有创新意识的青年作者交朋友。做为一位新中国培养的当代诗人,他是一个非常沉着的人,燃烧的情感和缜密的理性既给他以创作的热情和灵气,又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制约着他,使他始终在顽强地自审当中,沉潜于自己的世界。在他的全部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像通常诗人那样的直露的爱情描写。便是我们可以在他的压轴之作《白发与缘鬓》中窥见他那一颗被人间真情所激荡的心。“我半生为诗所累,/毕竟到今不悔。/纵然诗运坎坷,/终生不愿分袂。/既然与诗有缘,/就敢向白发挑战。/白发不为己生,/权当诗的桂冠!”
磨砺诗情上碧宵。诗永远伴随着他,成为他生命中的精魂。在这日益物化的纷繁尘世里,他怀着淡泊而清纯的心境,走向一个大气包举的澄明境界。
注释:
〔1〕李洪程:《诗歌艺术发展轨迹鸟瞰》, 载《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62页。
〔2〕转引舒炜光:《维持根斯坦哲学评述》第99页。
〔 3〕李洪程:《诗歌艺术发展轨迹与鸟瞰》, 载《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