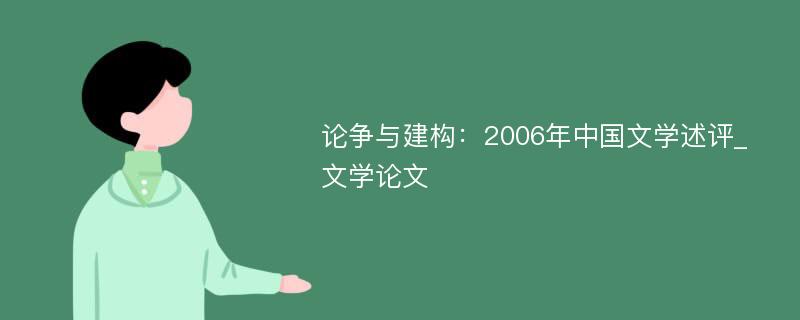
争论与建设:2006年中国文坛过眼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文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首2006年,中国文坛依然是一派战国景象。典型的事件,有3 月在知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之间围绕“文坛”与“权力”展开的“韩白之争”;4月由批评界开始的对知名作家余华长篇新作《兄弟》进行的声势浩大的、 呈一边倒的强火力“围剿”;9~10月由网民“恶搞”知名诗人赵丽华诗歌而引起的关于“废话诗”的争论;同月,针对“废话诗”事件诗人叶匡政抛出“文学死了”的言论,断言“网络互动,文学不存”,从而激起又一轮争论。入秋以来的中国文坛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10月的北方沈阳,出现先锋文学代表人物、知名作家洪峰“上街乞讨”怪现状,作家是否要“圈养”又成为热门话题。也是10月,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边缘小国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中国作家的差距在哪里”又被提上反思的桌面。在中国文坛早已经成为“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的边缘态势下,上述争论无疑为这份冷寂注入一丝血气,但某些意气之词也为文坛增添了不必要的“题外话”,意味着今后文坛将更加无序化、身体化、行为艺术化和后现代化,也将更加焦虑和意气用事。倒是值鲁迅逝世70周年之际,从2006年初开始即有学者发表纪念文章,从“鲁迅的现在的价值”入手探索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的国际性和中国性,也或明显或潜在地与当下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进行对话,产生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索、追问的话题。可以说,2006年的中国文坛既是游戏的一年也是严肃的一年,既是争吵的一年也是建设的一年。因此缩略地整理和回放这些事件,做成历史的备忘,并非没有意义。
一、鲁迅与东亚和鲁迅与当下中国
1.鲁迅与东亚。2006年第1期《社会科学辑刊》开辟“鲁迅与东亚”专栏, 发表了孙郁的《东亚的起点》、王富仁的《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钱理群的《“鲁迅”的“现在价值”》三篇文章;2006年第6期《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也发表了陈方竞的文章《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四位知名鲁迅研究专家以“鲁迅与东亚”为中心的集体性言述,主要是针对“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盛行着两种思潮:或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割裂了传统’因而主张‘回归儒家’;或者因为对西方经验,特别是对美国经验的拒绝,是中国的问题所在,因而主张‘走英美的路’……却恰恰忽略了‘现代(二十世纪)和中国’”的思想现状而发起的。这“两种思潮”导致“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的变革,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这些年孙中山之受冷遇,毛泽东之被遗忘,鲁迅一再受攻击,绝不是偶然的”(钱理群语)。这种研究现状导致中国大陆学界的“鲁迅研究本身表现出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匮乏,而且,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的整个文化和学术环境中也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难以起到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作用”(陈方竟语),因此有必要借鉴韩日学者的“鲁研”成果,加强对鲁迅的再认识与再思考,以呈现“鲁迅的现在价值”。
钱理群的《“鲁迅”的“现在价值”》从东亚鲁迅研究成果出发,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鲁迅”是谁?他认为不能把鲁迅仅仅看作周树人,而应该扩大视野,把鲁迅看作是在文学上、思想上与世界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文学家、思想家“相互映射的镜子”,因此“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的遗产”是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文学家、思想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和文学遗产,鲁迅思想是“二十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问题看“鲁迅”的“现在价值”。他认为鲁迅价值就在于在20世纪真理解体、价值幻灭、理想丧失的时刻,鲁迅“面对虚无、反抗虚无”所具有的精神启示力量。在“21世纪初的中国、东方与世界,正面临着虚无主义的挑战”的当下,鲁迅精神承担着“思想重建的任务”。在信仰的层面,鲁迅的“信仰主义”可以成为一种精神的“防火墙”与“杀毒软件”,防治中国成年人社会“做戏的虚无党”与“伪士”的猖獗及其影响到把青少年变成“什么也不相信”的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的玩世主义和“生活没有目标”的空虚与冷漠。在思想革命层面,把握鲁迅主张的“革命”是与“改革”“不满足现状”“批判”“反抗”争取“沉默”的国民基本权利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当下中国只有“太平”没有“战士”是因为知识分子主动放弃了做“战士”的权利。因此聆听鲁迅“做永远的战士”的呼唤,追随鲁迅“做永远的战士”,既是思想家的责任,也是文学家的使命。在实践层面,要继续重视和发扬鲁迅“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实践精神,要正确理解鲁迅最后十年对实践精神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方面以杂文为武器,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一方面配合中国共产党反抗国民党专制,直接参与了群众的抗议活动。但在当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些反而成为了鲁迅的“罪状”或“局限性”:鲁迅的杂文被看作“意气用事”,是“浪费才华”;鲁迅与工农运动的联合被看作是“与权力合谋”。这恰恰反映了当前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犬儒主义、伪清高、伪贵族主义的倾向。在这种精神萎靡的状态中,中国知识分子将无所作为,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孙郁的《东亚的起点》从韩国作家白乐晴的作品与鲁迅精神具有的高度一致性以及日韩学者竹内好、木山英雄、李永禧、林宰雨对鲁迅思想的深刻阐发出发,发现东亚人共有的困境以及直面这一困境的情怀。他指出日本是鲁迅的起点,但其归宿却不是日本而是世界。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经由日本桥梁而通向世界所组装的鲁迅思想,“却与中日韩三国人的命运深深纠葛着。比如主奴关系、个性主义与国家主义、真人与伪士等”。这样鲁迅就“触摸到了东亚人内心的痛处,作为一个被近代化的东方人,在迎接西洋的强势文化时,既要认同于重个性的力量,也要警惕集权主义的冲击。一句话,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的奴隶”。因此作为“东亚的鲁迅”的意义在于,鲁迅“不仅跨越了国界思考个人和自我,而且又以浓郁的中国人色调表现了反抗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气魄。这使他克服了东亚地域间的帝国心态与奴隶心态,而直抵普世意义自身。他的抨击帝国意识、大中华意识,在根本上动摇了旧有的思维模式”。因此,鲁迅对东亚存在互为主体的观念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在这个思路的延伸里,有着全亚洲的苦梦和向往。顺着鲁迅的思考方向,“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总有一天,东亚的人们将在没有仇视的氛围里构建一个美丽的家园。
陈方竞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从韩国学者对鲁迅孜孜不倦的研究并取得丰富厚实成果的现状出发,揭示鲁迅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资源而对韩国知识界发挥的巨大影响。他指出,韩国鲁迅研究者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遇到了1989~1992年的国际风云动荡,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又受到远比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冲击。他们是在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体验和认识中进入到鲁迅世界,又在反抗所置身的社会专制的黑暗中深化了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因此,他们或者是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或者是在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剥离中发现了鲁迅创作的独立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上世纪90年代在与中国新时期后的鲁迅研究的精神感应中,他们更为注重鲁迅与韩国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比较,突出鲁迅与韩国文学、学术愈益深刻的精神联系。因此东亚鲁迅研究的进一步的现实意义更在于,面对时至今日不同脉络的文化之间仍然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必须用鲁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态度进行和解,在中日韩不同文化脉络之间“求同存异”以实现“和而不同”。而其实现的手段之一,正是鲁迅提出的——“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这条道路——虽然“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联想到2006年秋天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为了写出自己心中的“南京大屠杀”而在70高龄只身访问南京,期间令人感动地大谈鲁迅对他文学与人生的决定性影响,与之相比,中国作家明显缺乏相应的自觉意识、历史感和现实关怀——笔者注)。
王富仁的《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具有一种对中国思想界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他指出“当日本学者带着一种反思精神来接受鲁迅,当韩国学者带着一种反叛精神来接受鲁迅的时候”,与其说我们“比日本、韩国知识分子少了什么”,不如说我们“比日本、韩国知识分子多了什么”。而多出的东西就是绅士意识、才子意识和流氓意识。他认为,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绅士意识造成了他们高高在上的姿态,把自己置于“高雅的位置”,并真诚地感动于自己的“真诚”。他们相信“社会上出现的所有的灾难、不公甚至战争以及各种各样的苦难都与他毫无关系”。他们发言的姿态就是“引进理论”“贩卖思想”,“或者实用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或者新人文主义,或者黑格尔哲学,或者费尔巴哈哲学”。他们也会对现实评头论足,以显示自己的高明,但从来不会与大家一道走出深渊。而现代才子是“讲情的,讲潇洒的,讲不承担苦难,讲幸福的”。现代才子有两幅面孔,一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写出诗来,并且能写出非常美、非常和谐……让人读来心里软绵绵的,非常温柔多情”;二是现代才子“带有一种进取的甚至可以是一个革命的外表,他永远是先进的,永远抓住一种话语形式”。至于流氓精神,则指一些知识分子没有立场,没有信仰,永远在变,跟着时尚走,“前天还在讲阶级斗争,我是一个阶级论者;第二天阶级斗争不时兴了,我就可以讲和谐”。在神话鲁迅的时候,他可以“给鲁迅贴上各种各样的金纸”;在鲁迅不时兴的时候,他可以说“鲁迅是汉奸、流氓,可以说他是性压抑、性变态”。这种话语的跨越,是与流氓本性联系在一起的。王富仁的发言毫无隐讳,笔锋直指中国的学院学术和学院文学。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绅士化的发展、才子化的发展、流氓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中国文化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达到的最高点。”要抵制和清除这种现象,正期待着鲁迅的出场,亟须鲁迅发出自己的声音。
2.鲁迅与中国当下。鲁迅逝世70周年也牵动着大陆知识界“新左”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脉动。这种思想脉动把鲁迅置于“今天的中国”语境中加以审视。2006年第20期《南风窗》发表专访“新左”主将、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文章《鲁迅:一个真正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2006年10月19日“学术中国”网发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王晓渔的文章《少谈些思想,多看些资料——鲁迅70周年祭》,分别从各自的立场,进入同一个思想家,来思考鲁迅在当下中国的象征性及其思想的当下意义。
汪晖认为,在今天, 继承鲁迅的政治情怀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他指出,鲁迅不是政党领袖,甚至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有一种深刻的颠覆性和激进性。鲁迅一再讽刺中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批评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北伐时代的革命气氛,但这个讽刺和批判却包含了一种“真正的革命”“永远的革命”的精神内涵。这种“永远革命的精神”应是当下中国继续“解放思想”的历史推力。对于鲁迅如何理解、处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汪晖认为,鲁迅通过文坛这一独特的空间,利用文学创新发出正义的声音是极具象征性的:“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创造了文学样式的人,他是真正实验性的,真正前卫的,真正新颖的。如果没有这种文学样式的创新,鲁迅就不成其为鲁迅了。但这种形式的创新本身并没有使他远离政治,恰恰相反,他的每一次文学创新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形式创新意味着要创造观察历史和生活的独特视角,形成一种不同以往的世界观,这不就是政治吗?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把形式创新与政治性对立起来,既不理解形式,也不懂得政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鲁迅是如何利用现代传媒成功地开辟了社会文化批评的“公共空间”,而处身当下传媒时代却不能造就“第二个鲁迅”?汪晖认为,鲁迅所在的从鸳鸯蝴蝶到闲适幽默的传媒环境与今天并无本质的区分,不同的是鲁迅永远关怀现实,坚持良知与立场,“在一个由都市印刷文化构成的丛林中打游击战”。鲁迅从不驯服,而当下的知识者却习惯于在“庞然大物”前低头——“过去是政治的驯服工具,现在是市场的驯服工具”。鲁迅在精神上是最反对驯服工具的,这与今天的知识氛围完全不同。
王晓渔则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角度,批评当前鲁迅研究的“内容大于形式”,认为鲁迅研究要从“为鲁迅抬棺”和“挟鲁迅以令诸侯”中解脱出来。只有回到鲁迅本身,才能“激活”鲁迅,因此有必要把鲁迅请回资料室,提倡“少谈些思想,多看些资料”。把鲁迅请回资料室并非隔离鲁迅,而是为了更完整、科学地了解鲁迅和他的时代,包括他的朋友与敌人,否则最终只能以崇拜鲁迅的方式埋葬鲁迅。
汪文和王文也互有“对话”,主要集中在当今时代是需要“胡适还是鲁迅”这一话题。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革命还是改良、是激进还是温和的风向标,集中体现在大陆知识界“胡适还是鲁迅”的选择上。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两个起点与两座高峰,“胡适还是鲁迅”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涉意义,是“尊胡还是抑鲁”也直接指示着中国知识社会的精神动向。汪晖虽然肯定胡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但与胡适“比较倾向于从国家的立场或智识阶级的立场来看待这个社会”相比,他更欣赏鲁迅“‘从下面’看问题的视角”。他指出在“告别革命”“否定革命”的口号之下遮蔽、回避鲁迅精神,并以这样的方式肯定胡适、贬低鲁迅,其历史观上的肤浅是不可避免的。王晓渔则认为,与其说“胡适还是鲁迅”,不如说“胡适还有鲁迅”。把“单选题”置换成“多选题”,正符合“兼容并包”的现代思想原则,两种思想的对话或交锋,更易于造成思想的进化,更有益于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他进而认为,鲁迅和胡适各有洞见也各有盲视,其思想也各自带有不同的毒素,但“以鲁迅之毒解胡适之毒,以胡适之毒解鲁迅之毒,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
二、“韩白之争”——“进坛”还是“入场”
“韩白之争”始于2006年2月24 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在其新浪博客上贴出的《80后的现状与未来》一文。该文批评韩寒的作品“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关系”,并断言“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3月2日韩寒在其新浪博客上贴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一文回应:“以时代划分人,明显不科学……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并断言:“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最后也都是花圈。”3月4白烨贴出《我的声明——回应韩寒》,指斥韩寒的“嬉笑怒骂”应受到道德的审判。随后支持白烨的陆天明、陆川、高晓松等人的先后介入,纷纷在道德上做文章,从而使一场文学之争变成网络上“挺白”“挺韩”两派的既失去体统也丢失真相的“骂战”与“群殴”。不过韩白之争依然反映了我们当下文学的困境,把“进坛”还是“入场”作为是否文学的标准,恰恰体现了我们对“什么是文学”的无知和迷茫。它使我们意识到中国文坛还是一个“身份帝国”,“代际的冲突”不是表现为文学的合乎常识的进化,而是出于内心深处对于“权力”和“利益”的隐秘焦虑。
三、“围剿”余华的《兄弟》
2005年8月,长达10 年没出长篇的余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新作《兄弟》(上),引起轰动,迄今已发行46万册;2006年3月《兄弟》(下)推出, 据说也追印到46万册。然而春风得意的余华却受到了文学批评家的集体“狙击”。虽然有人认为这些曾经的“表扬家”一夜间变换嘴脸成为“批评家”,涉嫌炒作,但以此方式集体围剿知名作家的事件确实前所未有。由批评家谢有顺、申霞艳、张颐武、李敬泽、杨栗、黄惟群、石剑峰充任控方,起诉《兄弟》的“七宗罪”——情节虚假、叙述啰嗦、主题重复、视角简单、人物扁平、认识粗浅、情趣低俗,把余华批得体无完肤,简直连文学青年都不如。当然需要把围剿《兄弟》看作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它主要是针对“作家成名之后怎么办”的“名作家”困境。“名气进步,写作退步”“高开低走,后继乏力”几成中国作家的常态。所以批评家们指出,这不仅是余华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的问题,是中国作家成名之后如何走的问题。中国作家成名后,生活圈子狭窄,在书斋里写小说,过着一种伪生活,只能靠想象力去把握这个时代。而且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之后,作家们都太迷信国外汉学家的意见。迷信汉学家而不是相信生活,就变得言不及物,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抽象,大失水准。这次事件还可视为一次批评界的“自救行动”。走出“表扬家”的客气与圆融,端起“批评家”的冷脸和硬气,尽批评家独立正直的责任,当然是好事,但从“捧杀”跃到“棒杀”,仍需警惕;片面追求“事件性”带来的超强效果,也有必要反省。
四、“废话诗”之争
2006年9月,网上开始出现对中国一级作家、《诗选刊》编辑部主任赵丽华诗歌的“恶搞”,把赵丽华推为“诗坛芙蓉姐姐”。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戏作“梨花诗”《谁动了我的花内裤》:“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难道真的会/有人/收藏/我的/没来得及/洗/的/花内裤?”9月26日到30日, 韩寒在博客上接连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文,放言“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并称诗人所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打“回车”键。这话激怒了诗人。先后卷入战团的有伊沙、沈浩波等知名诗人,《韩寒灭诗,死得难看》等檄文火药味十足。9月30日晚7时“废话教主”杨黎在北京海淀“第三极书局”举办“支持赵丽华(blog)保卫诗歌”朗诵会,但场中物主义代表诗人苏菲舒的“裸体读诗”,引起书局工作人员的怒斥,朗诵会不终而散。这表明综合“下半身写作”与“口水诗歌写作”而成的“废话诗”已经突破普通读者的接受底线。2006年9月29 日《中国诗人》特别论坛发表寒山石的文章《对当下诗坛的集体审判——从“赵丽华现象”说开去》,指出当今诗坛的五大硬伤:丧失诗意的情感宣泄、心态浮躁的垃圾生产、蔑视大众的孤芳自赏、批评缺席的无耻吹捧、权力垄断的话语霸权,并呼吁诗人和诗坛认真地进行“集体反思”。“废话诗”显示当前的诗歌越来越身体化,也越来越观念化和行为艺术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语言的俗化和诗意的放逐当然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但“推陈”有心,“出新”无力,依然是当今诗坛的软肋。面对读者大众的出离的愤怒,一向以走“民间路线”且标榜以诗歌通俗化、普及化为合法基础的“废话诗人”又祭起了“诗歌是灵魂的挥舞”“诗歌是少数人的事业”的大旗,不免自相矛盾。“废话诗”之争的特别之处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之争,不再只是诗坛内部话语的争夺,普通读者的强力介入,将成为影响诗歌进程的一种力量。但——是认真反思还是冲突升级,在无序无中心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五、“文学死了”与“文学不死论”
10月24、29日,诗人叶匡政发表博客文章《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称文学是旧时代的恐龙,“它已经死了,它的躯体正在腐烂”,包括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教授、作家协会、作家、文学奖等在内的“文学项目”都已经死亡。代之而起的是“网络互动的文本”的新生——“一份生动的语文老师的教案、一段鲜活的网络聊天记录、一篇有关婚姻问题的博客短文与回帖、一个情真意切的手机短信等等,任何形式的文字文本都与所谓的文学有着同样的地位”。文坛将迎来“没有文学等级,没有文学体裁,没有诗人、作家的身份意识,没有文学史”的时代。叶匡政“文学死了”的惊人之语引起作家周瑟瑟著文《文学不死论》进行言词“有点恶毒”的回击:“叶匡政先生死了,但文学还活着。”“互动的文本时代、网络、电视、手机、媒体等等都不新鲜,但这些东西只是生活的工具,文学会越来越凌驾于‘数字化生存’之上,成为与人类共存亡的最后的精神载体。”“网络与信息化的革命改变不了‘文学’的心灵,任何形式的传播最终将要向‘心灵的’文学妥协。”因为“文学正在滋润这个时代贫乏的心灵”。知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则从文学常识的角度,反驳叶匡政的观点,讽刺说“文学已死这个老话题早就该死”:“‘小说已死’或‘文学已死’的话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美国文学评论家提出谈论过。网络上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惊人之论,又抓住一根热闹的稻草,这实在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文学的“死”与“不死”确实是自有网络文学以来就存在的老话题,其实质是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立网络文学的合法性,但网络文学的“生”要以传统文学的“死”来做祭品,仍然暴露出中国文坛以暴力的方式推行文学革新的习惯性思维。对新生事物的“神化”与对既存事物的“妖魔化”,其狭隘,专制和武断值得深思。
六、作家“乞讨”与“圈养”危机
10月,曾被称为文坛射雕五虎将之一的先锋文学代表人物洪峰,因沈阳市文化局暂停他每月2000元工资,使其发生“生存危机”而上街“乞讨”。作家“乞讨”使文坛对被“圈养”的中国作家一旦被组织抛弃将面临何种命运表示出极大的忧虑。立足于道德批判立场,秋歌的《作家乞讨,我们时代的耻辱!》直接把矛头指向体制,认为作家乞讨是官僚意志对人文精神的强奸和枪毙,是当代体制对作家创造力的扼杀和摧毁,是汹涌而来的消费潮流对精神探索的虚化和紧张。知名作家谈歌的博客文章《中国作家,别成为“圈养”的宠物》则认为,消除圈养危机的办法只有走出“圈养”,走向“生活”;其不二法门便是脱离“体制”,回到“民间”。作家“乞讨”现象再一次对置身于体制内的作家采取何种方式“安身立命”敲响了警钟。它使作家意识到——不必依赖体制这把所谓的“保护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家必须、也只能以写作换回尊严。
七、诺贝尔奖与“中国作家的差距”
10月12日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对照其获奖的三大理由“小说情节引人入胜,故事讲述娓娓动人;语言精致优美如珠似玉;内容富于人性与哲理”,“网易文化”发表评论指出,中国作家明显有三大不如人:第一,注重叙事而不重视好好地讲故事;专注自我而无视读者;第二,写作草率,追求数量积累而不重视质量打磨;第三,以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为“人性”,以扭曲的生活为“人生”。虽然东西方文化差异大、沟通难,但毋庸讳言,中国文学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代作家如莫言、马原、余华等人,到了现在已经是中国文学界的顶梁柱,但他们的才华似乎也到了顶点,面临“文学终结”的考验。随着文学在中国日趋边缘以及年轻作家写作水准的“外强中干”,如果莫言、余华等人不能获奖,短期内其他中国作家更难有获奖的机会。“缺乏思想和视野,少有站在思索人类命运的高度上的作品”仍然是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最难弥合的距离。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作家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兄弟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作家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