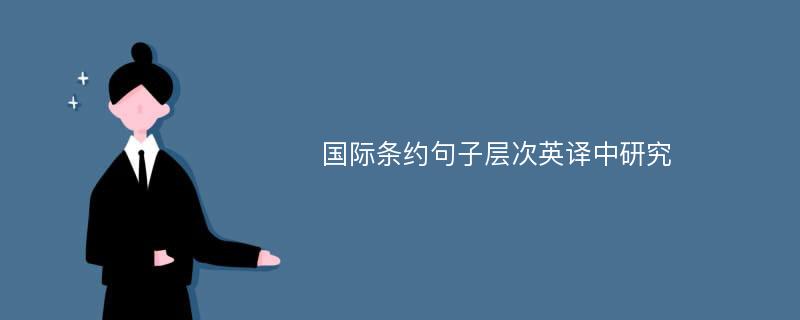
邓一恒[1]2002年在《国际条约句子层次英译中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旨在研究国际条约在句子层次上的英译中问题。 作者试图借鉴普通翻译理论和语言学方法来分析条约的翻译。确切的说,作者结合了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交际翻译法和奈达的叁步翻译步骤来构建理论框架,进行条约翻译的研究。 在法律翻译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一方面,法律翻译者应该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他也应该遵守目标语言的习惯。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不能完全满足这一要求。作者认为,法律效果作为交际翻译法的精髓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法律效果起到了连接我们翻译步骤中第一步“分析”和第叁步“重建”的桥梁作用。 通过分析对照四部国际条约的英文译本和中文译本,作者总结归纳出条约文本中各种各样言语行为的内容和功能暗示手法。这四部国际条约分别是:《联合国宪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作者通过对比原文本和目标文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际条约有其传统的格式以及较为稳定的结构。为了达到相当的法律效果,条约的中文译本应该遵守原文的格式。 第二,国际条约的翻译人员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创造性的翻译—使用与原文中的功能暗示手法不相当但却达到与原文等效的手法。 最后,对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议,作者认为二者对于国际条约的翻译缺一不可,而直译和意译的程度应该加以控制。“字译”的方法尤其不可取,然而意译的自由度也应该控制在交际翻译法的限度内。
熊德米[2]2011年在《基于语言对比的英汉现行法律语言互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外法制史和法律语言史证明,每个法系及其语言表述系统的长足发展,须臾离不开通过翻译吸收其他法系的有益成分。近代以降的中华法系就是乘着这股川流不息的“译流”,逐渐实现了从固步自封的“祖宗之法”到海纳百川改革开放之法的伟大涅盘。正是在这股“译流”恒久不变的影响下,当今日渐葳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仍然是一个“充满外来语的世界”。斗转星移,“充满外来语世界的中国法律”这个曾经近乎贬义的称谓,而今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涵义,即“外来语”被用来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法律观念的同时,也被用来向“外来语世界”翻译输出中国的法律,使一度依托“外来语”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法律,蝶化成倍受“外来语”本土世界青睐的重要法律渊源,而其母国则得以最终实现了从法律输入国到法律输出国的巨大转变。因此,与之相应的法律语言翻译研究,也由以往的“外译汉”单向关注,转为对“汉外互译”的双向关注。“基于语言对比的英汉现行法律语言互译研究”亦由此应运而生。本论文以英汉现行法律语言互译出版物为语料,从词、句、篇叁个层次进行对比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英汉法律语言翻译的优劣,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揭示英汉现行法律语言翻译的潜在规律,激发更多法律翻译爱好者参与法律语言的翻译及其研究,共同推动英汉法律语言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全文共分导论、主体和结论叁大部分。“导论”是本研究的概览,旨在廓清法律语言及其相关概念,梳理国内外法律语言及其翻译研究源流,揭示论文撰写的旨趣意义和创新点等,同时就有关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主体部分共五章。第一章是英汉立法文本词、句、篇层次上的对比。英汉立法文本基本词语的共性是准确性、模糊性与专业性并立,但英汉法律词语存在法律文化和法律历史的差异;英汉法律专业术语属于法律词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共同特点主要表现在意义单一、形式固定、语域专一、与时俱进和模糊性五个方面。英汉立法语句模式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使用授权性、禁止性、义务性叁种句法类型和预设处理型、祈使命令型、解释陈述型叁种句法形态。英汉法律语篇对比包括两方面,其一是指立法语篇的标题、章、节、款、项、目等内容要素,其二是指从现代语篇学的角度分析英汉法律语篇的语言结构差异,如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等。第二章是关于英汉法律翻译的基本原则和针对法律翻译者提出的基本要求。法律翻译既要遵守翻译的普遍原则,也要遵循一套适合法律翻译特点的特殊原则。因此,为适应“特殊目的语言翻译”(TLSP)的法律语言翻译,我们提出了法律翻译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叁个要求以及准确性、等效性、严谨性特殊原则。然后,对法律翻译者提出了四个方面要求。第叁章探讨英汉法律词语的翻译处理,其中包括法律专业术语的翻译。有效识别普通词语的法律意义,并在译文中做出恰当的表达,是法律翻译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法律专业术语翻译是法律词语翻译的重点,了解东西法律术语文化差异是做好法律翻译的重要条件。为此,我们就普通法律词语和法律专业术语的翻译提出了不同的翻译原则。第四章讨论英汉法律语言句子结构异同及其翻译。首先对英汉程式化法律单句(简单句)和复句(复合句)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法律单句(简单句)主要表现为陈述句和祈使句两种句类。法律复句(复合句)主要表为预设-处理关系句或条件-结果句,如法律英语用where或if明确表示,形式完整,极易判断;法律汉语的预设句大多数情况下为隐性预设句或用“……的”或“……者”表示,变数较大,难于判断。根据英汉法律语句的特点,我们提出了英汉现行法律语句翻译的单句(简单句)互译、复句(复合句)互译以及综合性翻译原则。第五章专谈英汉法律语篇的比较与转换,重点关注复杂法律语篇中的词汇衔接和语法衔接及其翻译。词汇衔接关注英汉法律语言中相同词语重复、同义词重复和上下义关系及其英汉互译。语法衔接重点分析英汉法律语言中人称照应的显性表现形式和隐性表现形式及其翻译转换。最后为结束语。法律翻译在每一个历史变革时期都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却一直没有引起翻译界和相关学术领域的重视,研究者至今寥若晨星,研究成果捉襟见肘,富有建树的成就更是自不待言。为此,本研究结束部分指出了目前法律语言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呼吁学界加强对法律语言翻译的关注,并就法律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进一步提高对法律翻译价值的认识等问题表达了作者的看法。
张泽宇[3]2018年在《政治外交类文本中后置定语的翻译策略—《认识国际外交》(第2、3章)的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次翻译实践报告是在政治外交文本《认识国际外交》第2章和第3章的英译中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撰写的。文本内容主要包括回顾外交发展历程、国际外交背景以及外交任务介绍。文本中包含许多政治外交类专业术语和包含多种后置定语成分的长句,给译者的翻译实践带来一定困难。本实践报告选取20个典型案例,分析并阐释上述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遇到两类问题:一是政治外交专业层面的句子在理解和表达方面比较困难;二是后置定语成分较多,结构复杂。解决第一类问题,译者借助平行文本、词典和网络资源帮助分析理解和表达;针对后置定语成分多、结构复杂的问题,译者采取分译、顺译、合译等翻译方法进行处理。通过此次翻译实践报告,译者对翻译任务有了清晰的认识,希望通过案例分析,归纳出有价值的翻译方法,为今后此类文本的翻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熊欣[4]2013年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国菜名英译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菜肴名称在跨语言、跨文化交际和对外传播中的英译原则、方法和策略的研究之重要性,随着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和相关学术机构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这种跨语言和文化的交际活动,不仅仅只是涉及语符之间的转换,而且关乎到文化之间的交融。虽然说语言承载着文化,但是,中国餐饮业的海外发展和壮大作为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涵括的菜肴名称英译就不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文本翻译行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应属于外宣性质意义上的一种对外传播活动,甚或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完全的对外经济活动,因为菜名的英译质量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到中国餐饮业在海外发展的规模和效益,从而反刍国内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就需要在菜肴名称的英译活动中运用必要的增译和凸显等翻译手法,确保译名能充分体现出菜肴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中国的民族文化是否能够在菜肴名称(尤其是对于那些纯写意型的菜名)英译过程中向译语受众充分传播,成为了衡量众多译名适切与否的一个核心要素。当然,中国菜名英译活动中,无论是从文化层面的考量还是从经济角度的权衡,都必须以语符意义(非语符的表层语义)的切近传递为归依。因此释译方法(解释、说明和补充等译法)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帮助译语受众更好地获取原语的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菜肴名称的英译活动不仅承担着语符意义的切近传递和民族文化的最大传播,同时还担当着汉语的世界推广这一重任。音译和零翻译常常被认为是对原语意义和原语文化最本真的传递和传播,它可以完全确保译文的“不失真”或“等值”。在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英译中,常常被广泛使用,并已取得了可喜成就,使许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词汇以其最本原的拉丁字母拼音拼写形式进入到了译语(英语)语言,获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可和推广。饮食,国计民生也。适切的中国菜肴名称的英译名,可以使译语受众更为贴切地了解到译出语的语言和文化魅力,在不造成理解中产生歧义和不增加译语受众接受困难的前提下,如果能辅以视觉非语言的图示,适当的音译将更加有助于原语语言和文化的世界传播。跨文化交际翻译学强调了译文对译语受众与原文对原语受众所产生的等效性。就菜名的跨文化交际翻译来看,既有其文学性和文化性,也有其知识性和专业性,更有其经济性和传播性,它涉及了翻译学的每一个层面,单纯地使用某一种翻译理论或翻译方法以穷尽该实用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是有失偏颇的。故而,在菜名的英译实践中,将中国菜肴名称按照传统的区分办法分为写实型和写意型(含实意兼顾型)两大类,结合西方菜名的表述形式和突出特点,采取写实性菜名直译,写意型(含实意兼顾型)菜名音译加释译的方法进行英译。某种程度上来说,翻译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创造,对于那些已经约定俗成之菜肴音译名直接沿用,而对于某些中国特色鲜明的菜肴名称,译者应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采取借用、谐音等手段,勇于创新,从节约的原则和品牌树立的原则出发,创造出易于为广大译语受众所能接受和传播的,如Gobelive(狗不理)、Longkudo(龙虎斗)等菜肴的经典译名。本课题的研究将从以下八个方面对中国菜肴名称的跨文化交际英译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找出其中的某些共性,区别其个性,进而使菜名的跨文化交际英译译名达到效度和信度的最佳近似。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研究目的及创新之处、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第一章: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本章主要讲述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产生的背景及差异的表现:饮食观念、社会文化内涵、原料结构和种类、菜肴名称命名特征、菜单设计、烹饪方式和刀工上。第二章: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菜名译名规范——本章内容主要分析菜肴译名研究的现状及问题,提出菜肴名称译名规范的必要性、译名规范的原则、方法与内容,并在本章第四部分专门给出了几个具体菜肴译名的分析。第叁章:菜名英译的目的与原则——本章主要就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分析菜名英译的目的定位及菜名英译的基本原则,并专门探讨了经济原则下的菜名英译。第四章:菜名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适应论——本章首先分析传播与翻译的概念,然后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菜名英译和跨文化交际适应论下的菜名英译:复合型菜名英译适应、写实型菜名直译适应、写意型菜名音译适应。第五章:菜肴制作的刀工及烹饪方法的英译——首先分析了刀工的英译(含与菜形密切相关的刀工英译和与菜形无关的刀工英译);其次,对中、西烹饪方法词的语义进行了对比及英译探讨(通过探讨火候、刀工与烹饪方法等分析了烹饪方法的英译)。第六章:菜名翻译中的跨文化策略——本章首先对释译、变译、音译、图示及翻译中的取义角度的转换等翻译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探讨,提出菜名英译中通过归化和异化的英译手段以达到菜肴译名的信度与效度;同时分别探讨了写意型菜名和纯写实型菜名的相关翻译策略。第七章:菜名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药膳名称英译——本章主要分析了中西食补观念的差异、药膳发展的历史及理论依据和药膳的功效与名称构成,提出了药膳名称英译的原则及方法及药膳译名的结构模式和处理方法。第八章:中国菜肴名称中的修辞特色及英译——主要探讨了暗喻型菜名、借喻型菜名、象征型菜名、典故型菜名和夸张型菜名等的英译问题。结束语部分指出了本研究中某些英译方法的局限,再次提出音译方法在菜肴名称英译中的重要作用,就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后学提出希冀。
费小平[5]2004年在《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系后结构研究视角,通过研读大量的第一手英文文献并兼涉部分中文文献,清理贯穿于翻译中的有意识或无意识权力层面,对中西语境中的翻译政治进行溯源追踪和学理讨论。 本论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翻译的政治问题检讨:第二章翻译中的性别政治:第叁章翻译的暴力政治与后殖民批评;第四章结语:重建翻译诗学。显然,第一章与第四章属于宏观研究,第二章与第叁章属于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宏观与微观二者之结合是本论文的特色,它们建构了互为犄角的逻辑关系。 第一章“翻译的政治问题检讨”首先简要论述了本课题建构的缘由、背景,然后考察“政治”概念在中西语境里的内涵与外延,在此基础上付诸大量篇幅讨论中西语境里翻译政治的渊源与形成问题及其研究对象,最后对整部论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进行界说。 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忠实对等论”建立在一个经验一唯心主义的框架内——一个以天真的“语言再现论”为基石的所谓“人文主义事业”之上。它有诸多不足,不利于翻译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挖掘。其实从解构主义视角来看,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本原”,即便有所谓“本原”也包含多种异质成分,并非什么纯粹的、统一的意义之源或历史(德里达语)。若据此去追寻译本之充分再现,则会陷入“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同时还有碍人们去关注翻译中隐性存在着的不对称权力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文化研究”学科和70年代初诞生的以文化范式为特征的,以荷兰学者杰姆斯·霍尔姆斯,比利时裔学者安德列·勒菲费尔,以色列学者吉登·图里、伊汉一佐哈,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式奥·赫曼斯等为魁首的“翻译研究”学科为我们提供了拯救传统“忠实对等论”的学理途径。他们一致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主观裁决的过程,不是直接的文字转换过程。翻译研究只有通过对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及译文本身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准确掌握译者在进行主观裁决时的种种考虑、译出语与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及诗学准则、译本在译入语文化文学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产生的作用,等。这一切在90年代的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印度裔美国学者伽亚特里·斯皮瓦克、印度学者特贾J斯维莉·妮南贾娜、加拿大学者谢莉·西蒙等人手中得以深层次的讨论。他们逐一涉及到了翻译中的性别、暴力、文化身份塑造等问题,而这些正是后现代语境下的热点问题意识—“翻译的政治”。它“拷问”了翻译所透视出的复杂权力关系网。 翻译的政治里的“政治”是中西语境里与生俱来的概念,指权力层面。翻译的政治就理所当然地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性别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客观因素则包含媒体、出版者、期刊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译者对原作施加的暴力、挪用等方面。它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埃及亚历山大港的 《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5中n峨岁刀t)的翻译—这里,官方赞助人及译者的专业能力直接左右着译作的成功。尔后,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后期杰罗姆的《圣经》翻译、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17世纪英国批评家约翰·德莱顿的“拟译论”和18世纪皇室支持下的俄国翻译实践均承继着这一切。不过,真正开始对其进行学理探讨却发生于充满喧嚣与动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沃纳·温特于1961年发表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可看以是这一时期的先河之作。它着重讨论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翻译活动中的种种“教务管束”及其通过将非洲、亚洲国家文学译成俄语来博得这些国家友善的险恶政治用心。1971年,法国思想家福柯推出的《话语的秩序》是后现代语境下隐性讨论翻译政治的划时代文献,于1981年被译为英文,题目为乃eOI幻七r.。厂刀咕即一。他虽然没有正面讨论翻译政治,但对于主体性断裂的论述却暗示了一个进入翻译政治的基本途径。福柯通过“断裂”敲击并取销瞬间和主体,开启了一个使瞬间从固定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缝隙,使我们能进入那个充满纷纭与不确定的“痕迹之网”。这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历史观—通过断裂的缝隙使过去、现在、将来叁者之间发生联系,拆散了线性的时间秩序,话语的不透明性因此呈现。我们因此面对着主体的非整合状态,从而面对着话语与翻译的政治。玛丽娅·妮塔·多伦与玛丽莲.伽迪斯.罗斯二位女士于1981年合作发表的《翻译的经济与政治》一文特别考察了翻译出版市场的政治。美国学者马丁·杰伊在论文集《永久的放逐》中设置“翻译的政治:西格弗里特·克拉考尔与本雅明论布伯一罗森茨威格的圣经译本”专章。进入90年代,翻译政治的讨论迈向成熟阶段。比利时裔美国学者勒菲费尔于1992年提出了“改写”式翻译为政治一权力服务的观点。1993年,印度裔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局外的教学机器》一书里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es ofTrans一ation’)命题,并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叁维空间中予以考察。她从福柯所批驳的不可靠的起点入手来?
参考文献:
[1]. 国际条约句子层次英译中研究[D]. 邓一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2
[2]. 基于语言对比的英汉现行法律语言互译研究[D]. 熊德米.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3]. 政治外交类文本中后置定语的翻译策略—《认识国际外交》(第2、3章)的翻译实践报告[D]. 张泽宇.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8
[4]. 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国菜名英译研究[D]. 熊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5]. 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D]. 费小平. 四川大学. 2004
标签:外国语言文字论文; 法律论文; 翻译研究论文; 法律翻译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跨文化交际论文; 报菜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