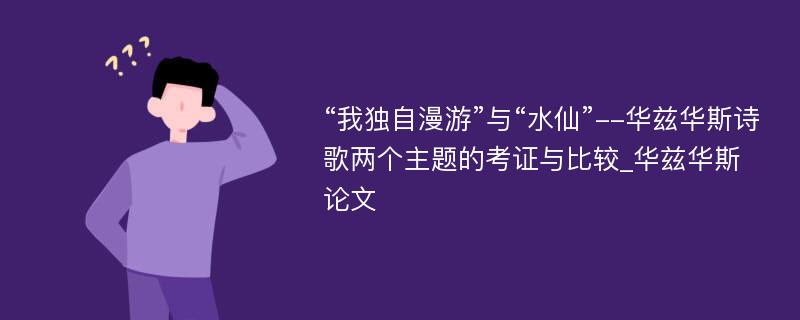
“我孤独地漫游”和“水仙”——华兹华斯诗歌两种题目的考证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兹华斯论文,两种论文,水仙论文,诗歌论文,题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1)02-0038-08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这首诗是华兹华斯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几乎所有华兹华斯诗歌选集和英国诗歌选集中都会出现这首诗作。然而,自这首诗作问世时开始,它的题目就一直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有些诗集中以这首诗的首行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作为诗的题目;有些诗集中这首诗没有题目,仅以数字代替;还有一些诗集中这首诗的题目为The Daffodils(“水仙”)。在这首诗作的汉语译文中,一般出现的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以诗作的首行作为题目,另一个是以“水仙”作为诗的题目,选用这两种题目的译文均出自翻译名家之手,也均是上乘的译作。那么,两种诗题在不同的版本中均有出现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两种题目在对诗作的理解上有着怎样的不同?在汉语译文中,“水仙”这个题目会引起怎样的联想?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出现两种诗题的版本考证
根据194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德·西林考特编辑的《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注释,这首诗作于1804年,然而诗中的经历却源于两年以前。当时诗人与妹妹多萝西从湖区厄斯湖畔高巴罗公园的丛林返回格拉斯米尔湖,途中与水仙有一次偶遇。在1802年4月15日多萝西所作的日记中她这样写道:
来到高巴罗公园那边的丛林,我们看见水边长有几棵水仙……我们往前走着,水仙越来越多;最后,在树枝下面,我们看见沿着湖岸长着一大片水仙,约有乡间大道那么宽。我从未见过那么美丽的水仙。它们和长满青苔的岩石相点缀,有的把头倚靠在岩石上,仿佛枕着枕头休息消除困倦;有的摇曳着、舞动着,仿佛湖面的微风逗得它们开心地欢笑。这些水仙看上去是那么的欢乐,光彩夺目,千姿百态……(Wordsworth,1944:507)①
1804年诗人在回忆中创作了这首不朽的诗篇。1807年,他的诗作结集出版,诗集题目为《两本诗集中的诗》(Poems,in Two Volumes)。出版之前,诗人曾经将这首诗编辑在“想象的诗”(Poems of Imagination)一组诗中,当时在这组诗的目录中诗人曾用过Daffodils来指这首诗。然而,出版之前,诗人将这首诗作编入了另一组诗“我的思绪”(Moods of My Own Mind)之中。在这组诗的目录中,该诗的题目为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在书中诗作没有题目,只有编号“6”出现在诗作的上方。原诗三节,如下: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 and Hills,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of dancing Daffodils;
Along the Lake,beneath the trees,
Ten thous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The waves beside them danced,but they
Outdid the sparkling waves in glee:—
A Poet could not but be gay
In such a laughing company:
I gaz'd —and gaz'd but little thought
What wealth the shew to me had brought:
For oft when on my couch I lie
In vacant or in pensive mood,
They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
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
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
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
1815年,诗人对此诗进行了重新修订,将1807年出版时这首三个诗节的诗作进行了修改和扩充,使诗作增至四个诗节,成为目前的定稿。在1815年的手稿中,这首经过修改增订的诗仍然以无题诗出现。
西林考特的版本根据格拉斯米尔湖华兹华斯纪念馆里的手稿编辑而成,同时参考了1807年出版的《两本诗集中的诗》。在西林考特的版本中,这首诗在目录中的题目是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在书中,诗以无题诗出现,编号为Ⅻ,下有方括弧[作于1804,出版于1807]。简言之,在华兹华斯亲自编选出版的1807年的版本中,本诗在目录中为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书中本诗以无题诗出现;1815年的手稿再次以无题诗出现;西林考特的版本作为华兹华斯诗歌的权威版本,在参考华兹华斯手稿和1807年版本的情况下,本诗作仍以无题诗出现。可见,这首诗作似乎本来就应该是一首无题诗。
那么,“水仙”这一诗题是怎样运用起来,并流行开的呢?20世纪初期,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分畅销的帕尔格雷夫编辑的《英诗金库》,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英诗金库》于1907年首版,此后直至1962年又再版三次,重印十五次。(Palgrave:Copyright Page)其影响在多次的再版和重印中得到一次次的印证。在《英诗金库》中,这首诗作有了一个题目,即The Daffodils(水仙)。之所以这样做,编者应该也是参考了华兹华斯本人最初的想法。从康内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两个诗集中的诗》中华兹华斯1807年的手稿来看,这首诗作的下方有一个Daffodils的字样。在出版之前诗人把此诗作编辑在“想象的诗”中时,诗的目录上用的是Daffodils。(Wordsworth,1983:330—31)1807年,诗人在写给鲍芒夫人的信中提到此诗时,诗人用的是The Daffodils。(Owen:114)因此,对于本诗是否使用The Daffodils作为诗题,诗人本人是有所考虑的。然而,在1807年诗集正式出版时,他最终没有使用这个诗题。不过,因为手稿上出现过Daffodils,华兹华斯本人也使用并提到过这个诗题,《英诗金库》中使用这个题目就并非毫无根据。《英诗金库》的编选原则和趣味主要面向大众读者,给诗作加上这个题目应该更符合大众的阅读欣赏习惯及审美取向。
二、两种诗题各自的内涵
对于这两个诗题,诗人本人都有所考虑,都有所提及,在有广泛影响的英诗选集中两个诗题又都被使用,但是,经华兹华斯本人编辑出版的诗集中这首诗最终放弃了“水仙”这个诗题,其中的原因诗人本人并未说明。然而,作为读者,我们可以从两个诗题中体味出各自不同的诗意及思想内涵。华兹华斯1807年版的诗集中该诗最终未使用“水仙”这个题目,而是采用了无题诗发表,而在目录上则使用了该诗的首行,这或许与诗人期待引导读者去体会他的精神状态相关。
诗的首行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作为一种陈述的展开形式,在诗的一开始就向读者揭示了他的精神和心路历程。诗以诗人的主体“我”起句,表明了诗围绕着“我”的游历进入诗境,从“我孤独地漫游”到达最终与自然、与水仙的一种交融共生。“我”的“漫游”具有客观实在性,它指的是诗人在湖区的一次偶然经历。然而,那次经历是与妹妹在一起,而诗中却道出“我”是在“孤独地漫游”,这样的描写并非不经意或随意而为,它带有一种象征的寓意,指的是诗人孤独的精神漫游,他在上下求索,寻找心灵的归宿,探求自由精神的出路。因此,这里的漫游可指客观而实在的一次真实的湖区散步,无意中发现了一大片黄水仙,引起诗人的心灵碰撞。同时,它也可指诗人的一种精神漫游。他难以排遣内心的苦闷,缺乏能与他的心灵进行沟通的精神伴侣,没有找到能激发他崇高心性的所在,因而,他感到孤寂,在孤寂中游历、找寻、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诗的首行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做题更能够使读者感悟到诗在进入诗境之初,诗人的一种困顿和苦闷的精神状态。
不少评论家认为,华兹华斯的游历总带有一种精神游历的象征意义。他的游历从18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1790年,他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就与朋友罗伯特·琼斯结伴游历了欧洲大陆和阿尔卑斯山,此次游历是他找寻精神寄托的开始。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他对学院中古板的教学体制十分不满,时常感觉到其中的压抑和限制,而欧洲大陆的游历使得他的身心都感受到大自然带给他的自由和灵性。当年,他带着十分热切的心情来到法国,对法国革命充满了幻想,期盼着启蒙思想召唤的平等民主的理想能够在这里实现。1792年,他再度来到法国,然而,革命后期的血腥与暴力迫使他在思想和情感上疏离了革命,并重新思考关于人性和心性的回归问题。1792年底,他从法国回来之后,精神上受到强烈的冲击,原先追求的通过革命来实现民主、平等的理想已经破灭,英法交战,经济拮据,远离爱人,居无定所,这些都使他面临巨大的精神危机,他的精神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他再次踏上了游历的路途。1793年,他与朋友一起徒步跨过索尔兹伯里大平原,然后独自一人徒步渡过塞汶河,进入北威尔士,开始他在革命的政治理想幻灭之后的身体与精神游历的征程。这次游历与他的欧洲之行有所呼应,他在欧洲之行中获得理想和激情,而此次游历是在革命的政治理想趋于幻灭之后精神的再次探求和追寻。在游历中排遣精神的苦闷,在游历中找寻精神的慰藉,在游历中探索人性的本真。1798年,诗人携妹妹一起再次重游威尔士,重游瓦伊河。此次游历之前,他曾和友人一起畅谈对政治和时局的看法,畅谈在法国和伦敦的经历,使得此次游历更具有了在现实中寻求精神回归的意义。而此次重游瓦伊河谷的经历则正是他精神漫游的一次重要转折,他重新找到了一条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径,寻求到了解救人性、回归心性本真的方式。(Roe:171)罗宾森(Jeffrey Robinson)在他的《徒步游历,浪漫主义意象录》中指出:“徒步游历表现出一个激进的思想中的不安情绪,从其消极面说表现出无家可归、政治逼迫,从其积极面说表现出多变性。”(52)游历在此意义上已经超出了身体游历的层面,而具有了精神游历的意义。1797年,诗人定居湖区,应该说,此时诗人的精神苦痛已经有所缓解,在定居湖区之后,他在各地的游历也有所减少,但湖区漫步又成为他的一种心灵渴求,他往往在这样的漫步和徒步行走中沉思、感悟和探寻,这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存在状态。在和友人谈到这首诗作的创作时诗人仍然表现出一种不安和焦虑。1808年,华兹华斯给乔治·鲍芒的信中谈到,有些人提起诗中的水仙倒映在波浪中这一情景时说,“我的诗的目标是纷乱和躁动,花和波浪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首诗的第一行,理解诗人未将“水仙”作为诗题发表,而是选择了诗的首行作为目录中的诗题,而诗本身以无题诗出现,读者或许更能从中体味诗人及诗中精神存在与精神求索的实质。
然而,诗人终究考虑过以“水仙”作为诗题,一些读者对于这首诗作以“水仙”为题也十分认可,这其中或也另有一番道理。“水仙”是自然中的花之仙子,每年英国的三四月份,水仙遍地开放,家家户户的门口、山坡草野之间,到处可见水仙飘洒的身影,在一定的意义上水仙已经成为英国大自然的天之骄子,有一种象征的意味。②诗人的精神漫游孤独而漫长,正在他彷徨孤寂之际,一大片水仙忽然之间闯入他的视线,更闯入他的心灵之中。水仙的摇曳舞蹈、水仙的飘洒闪烁,都成为他内心孤寂当中的精神伴侣。诗人在此次与妹妹在湖区偶遇水仙之后并未立刻创作此诗,而是时隔两年之后才进行创作,此间,诗人的心灵并未离开水仙。因此,水仙一方面为大自然中的自在之物,带给诗人心灵上的安慰、精神上的快乐,同时,水仙也时刻陪伴诗人度过漫漫的游历征程,帮助诗人排遣精神上的孤寂,引领诗人最终达到精神的最高境界。此时,水仙已成为一种灵性的存在,超出了物象本身的层面。在诗的最后一个诗节中,诗人直接表达了他与水仙在精神上的共鸣和他与水仙之间的共生:
因为,我时常倚卧在榻上,
愁思冥想,或惘然若失,
水仙就照亮我内心的眼睛,
这是孤独时欢乐的极致;
于是我的心就充满愉快,
和水仙一同舞蹈了起来……(屠岸:311—12)③
在1807年的版本中,“水仙”一词在诗中两次出现,首字母均为大写,表现出水仙作为一种自在的精神象征的特殊意义。水仙闪现在诗人心灵的眼睛之中,成为诗人在孤寂中的至高幸福。与诗人的精神相呼应、相结合、相交融,与诗人一同沉思,一同感悟,成为陪伴诗人回归心性的伙伴,其自在的状态也是诗人在精神上追寻的目标。全诗以“我”的“漫游”起句,以大写的“水仙”一词做终,“我”从“孤独地漫游”开始,而最终“和水仙一同舞蹈”,一前一后,相互呼应,结构工整,形成一个完整的精神追寻的过程。由此看来,以“水仙”做诗题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选择。
但是,对于选择“水仙”作为诗题,一些华兹华斯诗歌研究者还是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在这首诗中,“水仙”首先是一个物象,最初引起的是视觉感悟,这与以诗的首行作题,或诗本身无题,而以首行进入读者的视线所引起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首行的展开陈述向读者娓娓道来,叙述诗人的心事和精神状态。而以“水仙”作题,这个物象在读者进入诗作之前就率先闯入了读者的视觉之中,给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即本诗是在描写这花中的仙子水仙。读过全诗之后,读者可能发现,诗作的确生动地刻画出湖边美丽飘逸的水仙,但诗人的精神状态,他的精神游历从孤寂到惊讶到最终的极度欢乐的过程,这些从单纯的水仙这一物象来切入是难以表现出来的。以“水仙”作题,读者或许更多地关注到诗所描绘的对象,而忽视了诗人内心世界起承转合的变化过程。物象替代了诗人这个主体,替代了诗人内心的感悟,因而影响了全诗的整体精神内涵。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本人最终未将此诗冠以“水仙”为题的原因。
三、本诗汉语译文中两种诗题的翻译情况
华兹华斯这首诗作在国内很早就有学者和翻译家翻译介绍,并有多种译本。徐志摩的诗歌作品曾直接受到这首诗作的影响。一些早期的译本大多采用文言和白话相间的语体风格进行翻译,形式工整,用词体现出古典文言的意蕴。一方面,这或许与早期诗歌翻译尚未完全摆脱古典诗歌用语习惯有关,或许与译家的各自翻译风格有关;另一方面,这也与译家所认同的华兹华斯与中国古典山水诗之间的互通有关。早期还有一些译者甚至完全采用古体诗的形式来翻译外国诗,如学衡派推出的华兹华斯《露西》组诗第二首“她住在没人到的幽径”的八种译文均采用五言古诗的形式来完成。(葛桂录:13—14)华兹华斯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一诗的郭沫若译本为文言和白话相间之译本的典型。郭译完成时间较早,但他在世时并未发表,而是在他去世之后译本才面世。他的译本语言文白相间,韵式未依原诗亦步亦趋进行处理,诗题用的是“黄水仙花”。国内对华兹华斯诗歌的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将他的诗作与中国古典山水诗和田园诗进行比较。中国古典诗词中多有咏物诗作,以“梅”、“柳”、“菊”等自然物象作为吟咏对象的诗作极为常见,读者对此也颇为熟知。认为华兹华斯的诗作与中国古典诗词风格相近,而采用中国读者熟悉的物象作为本诗的题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此诗作出现了更多的汉语译本,不少译家在翻译这首诗作时也开始关注到从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上对华兹华斯的诗作予以理解。对版本的参考也更为丰富,此时的翻译更关注译诗如何能更好地传达原作的精神内涵。翻译风格渐趋多样,翻译原则渐趋灵活。在本诗的诗题翻译方面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译本采用的是“水仙”,比如杨德豫、屠岸、杜承南与罗义蕴、孙梁等的译本,或“咏水仙”,如顾子欣的译本。但也有译本是以原文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作为诗题进行翻译的,如黄杲炘将其译为“我独自游荡,象一朵孤云”,飞白的译文是“我孤独地漫游,象一朵云”。相比较而言,近年来采用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这一诗题的译本逐渐增多,这或许与译家采用的原诗歌版本不同相关,也与近年来华兹华斯诗歌研究的深入相联系。
无论是选用哪一种诗题,译家对本诗首行的翻译均有不同的译法。有些译文将“我”隐去,如郭译为“独行徐徐如浮云”,孙译为“独自漫游似浮云”,而这两个译本均选用原文中的The Daffodils为诗题,且译诗风格靠近古体诗诗风。其他选用“水仙”为诗题的译文首行为“我独自漫游象一朵云”(鲍屡平)、“我象一片云孤独地漫游”(杜承南等)、“我踽踽独行,像一朵孤云”(屠岸)、“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顾子欣),而杨德豫将首行与第二行合译,为“我独自漫游,像山谷上空/悠悠飘过的一朵云霓”。两个选用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为诗题的译文为:“我独自漫游,象一朵孤云”(黄杲炘)和“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飞白)。各家译本对首行均有不同处理,但从原文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的原意来看,诗行中原有“我”出现,并强调“我”处于一种孤独的精神漫游状态,译文中隐去“我”或与原诗的精神内质产生了一定差别,但如此翻译,其中亦或有缘由,本文下面一节将具体论述。首行中另一个关键词是lonely,意为“孤独地、寂寞地、荒凉地”等。一些译本将其译为“独自”,而以笔者看来译为“孤独地”更好。有些译本将形容“我”在“孤独地漫游”时将原文中的lonely一词在翻译中改为形容云朵,为“孤云”(如黄译、屠译),此为移用,也是可以的。但似不如飞白译“我孤独地漫游”更为直接。由此来看,这一行从语义、语境和诗的精神内质来看,译为“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相比而言与原文更为贴近。但此行的翻译在韵律方面无法采用“以顿代步”来体现原诗的音步,这又成为此译文中的一大缺憾。从上述多种译文来看,采用“水仙”作诗题的译本仍然较多,那么,在译文中以“水仙”为题与在英文中以“水仙”为题在对读者产生的阅读效果方面是否相同,其中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意蕴,这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四、以“水仙”做诗题对中国读者的特殊感受
“我孤独地漫游”和“水仙”这两种诗题的各自内涵在汉语译诗中同样有所侧重,前者重诗人的精神求索过程,后者重物象,然而,中国读者审视这两种诗题的感受或许与西方读者略有不同。
郭译在这首译诗的“附白”中曾表示:“只要一、二两段就够了。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画蛇添足。”(25)他的这个论断是否恰当笔者在此不予评论,但是这一断言背后所引发的潜在意义却值得我们思考。华兹华斯诗歌研究者一般认为,这首诗的最后一节是全诗最为重要的一个诗节。全诗的诗眼“水仙就照亮我内心的眼睛,/这是孤独时欢乐的极致”就在最后的诗节当中,没有这个诗节,这首诗的精神内涵可以说是不完整的。那么,为什么郭沫若先生会出此言?这里面的原因恐怕涉及到中国诗歌及诗学独有的特点。
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很多感悟自然、吟咏花草树木的诗作,比如“咏梅”、“咏柳”、“咏菊”等等,诗人对梅、菊、柳这些物象普遍采用直接描绘或吟咏的方式,诗人的主体“我”在诗中不直接入诗,诗人在诗中刻画物象,并抒写物象所引发的诗人的内心感受,诗人“我”不仅不在诗中出现,甚至所吟咏的对象在诗中也可能不被冠以任何称谓。咏梅的诗中或许可以不出现梅这个词,咏柳诗中可以不见柳字的显现。物象在诗中的命名本身有可能就是潜在的。钟嵘在《诗品》中讲到,写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这表明,诗中情感的抒发应“融情于物,借物抒情,……因而诗人情感的抒发,就必须托寓于有形的物象”。(袁行霈等:425)而物象的精神内质,便是诗人内在的精神内核。因此,虽然诗人作为主体的“我”不在诗中出现,“我”的精神追求却已经与“梅”、与“菊”、与“柳”合而为一了。此时,诗中的“梅”即是诗人精神境界的象征,隐在的“我”潜藏于“梅”这个物象之中,“我”与“梅”是不离不弃、共生相依的。这种物象与诗人主体的结合,从诗学的根本层面来说源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外物的天与人这个主体不是二元的,而是一种交融的存在,自然外物与人性本真生自一体,物象中即包含着人的精神和本性。因而,诗中诗人的主体虽然不出现,但物象本身就已经涵盖了诗人的精神内质。因此,诗人咏梅即诗人在赞美梅的过程中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内心追求和精神寄托。在此意义上,按照郭沫若先生所说,华兹华斯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为多余的一节,从中国古典诗学的角度来看确似多余。而两个在风格上更靠近古体诗的译本(郭译和孙译)的首行均隐去“我”似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考虑。由此,本诗以“水仙”为题,似有着西方读者难以体味的内蕴。
华兹华斯诗学中讲到,“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Owen:72)强烈的感情是诗人的感情,因而在他的诗中、也在大多数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中必有诗人“我”这一主体内心情感的显在表达。物我合一的概念对西方诗人和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在华兹华斯的咏物诗中,诗的题目往往有一个To,即“给”或“致”,仅To这一个简单的词就将诗所吟咏的对象与诗人的主体分开了,因为“给”或“致”必然存在一个从主体转到客体的距离,说明二者并非一体的存在。所吟咏的对象即便与诗人这一主体存在交融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并非是一种同时交叠融合的关系,诗人须通过想象来缔造这种关系。济慈的《古瓮颂》、《秋颂》,雪莱的《西风颂》中就表达出这样的关系。要缔造这样的关系,诗中必然要出现诗人的主体“我”对对象的倾诉、赞美和想象,而此时,“我”便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显在的因素。
中国的古典诗学强调外在客体与诗人主体二者为一。物即我,我即物,天即人,人即天。就华兹华斯的这首诗来说,如果用“水仙”作为诗题,它恰巧表达了诗人与水仙合二为一的精神追求。水仙已经成为他心灵中的精神寄托,他渴求这样的精神存在。诗人欲与水仙共舞,同时他也希望拥有水仙的精神,与水仙在精神上合为一体。因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以“水仙”作为诗题更能引发一种诗人与物象之关系的联想或想象,引导读者感悟诗人与外在物象水仙之间的精神契合。而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水仙”所引发的更多的是视觉形象,其中的内涵可能就不容易体味到了。但华兹华斯诗学毕竟以西方的哲学思想为其根本,因此,“我孤独地漫游”或更接近诗中所欲表达的精神本质存在,以“水仙”为题,原诗中所侧重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求索在一定程度上有被遮蔽的危险。
当然,两种诗题,各有侧重。以首行做题,侧重诗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求索的过程;以“水仙”做题,侧重精神求索的最终结果归于人在自然中的觉醒,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以“水仙”做题还可以感悟到诗人与水仙之间的精神交合关系。不同的选择可产生不同的感悟,诗本身可在不同的选择中产生不同的诗意效果,多样的审美取向也由此生发开来。
注释:
①编者为本诗所做的原注解这样写道:The occasion which inspired the poem was on April 15,1802,when W.and his sister "were in the woods beyond Gowbarrow Park," returning to Grasmere from Eusmere;and it is clearly indebted to D.W's Journal of that date.
②英国的水仙是生长在户外的,每年三四月到处可见,成片开放,并非中国人喜爱的养在冬天、放在室内的盆花水仙。
③本文中此诗的译文均为屠岸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