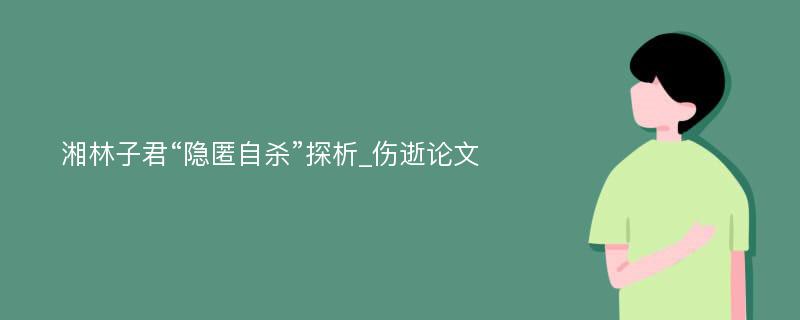
祥林嫂和子君的“隐性自杀”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性论文,祥林嫂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祝福》和《伤逝》的研究来说,祥林嫂和子君的死亡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作品没有从正面告诉我们她们的确切死因,但字里行间还是暗示给我们她们系自杀身亡;是自杀,又没有明确交代,这就是本文所谓的“隐性自杀”。本文将以此为论题展开讨论,挖掘作者之所以如此这般的隐衷,以期从这一特定视角对《祝福》、《伤逝》以及鲁迅小说做出一些新的理解。
一
在《祝福》和《伤逝》的文本中,都存在一种“前置死亡”的叙事模式,即在作品人物还健在的时候,通过预感或其他不祥预兆的书写,暗示给人们他们的结局将是死亡。这样的叙事模式有把死亡的事件提前透露给读者的作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把死亡的事件“前置”了。在不同作家作品中,前置死亡的叙事模式有不同的写作目的和功用,但就鲁迅和他的作品来说,其主要目的却是在为某种故事情节的模糊提供一定的空间,从而为“隐性”处理人物死亡创造条件。
在《祝福》中,当“我”第一次遇到祥林嫂,回答她的询问时,就隐隐感到:“我这答话怕对她有些危险,”坦言自己已经有了某种“不祥的豫感”。①这也就是说,在“我”听到祥林嫂的死讯之前,已经预感到会有不幸——直白地说就是死亡。如果说在《祝福》中,不幸预感伴随着祥林嫂一出场就来到了读者面前,那是因为《祝福》以祥林嫂为唯一主人公,不同于《伤逝》,《伤逝》是通过涓生“手记”的方式侧面述说子君遭遇的,一方面,有关子君的死只有通过涓生的视野才能告诉读者,另一方面,作品题材本身也没有让涓生与子君一接触就有不幸预感的条件。可是即便如此,不幸的预感在《伤逝》中也还是一再地得到显现。当涓生觉得他们的“生路”就在于分开时,立刻就“想到”了子君的死。②进而当涓生说出了“我已经不爱你了”之后,也很快就“想到她的死”③,当子君被父亲领走以后,再次萦绕在涓生心头的还是“我想到她的死”。④《伤逝》的“涓生手记”写作方式,让涓生的“人物行为”有两重承担:一方面,它是涓生之所作所为的第一人称记录,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完成一些作者交给它的叙事任务——这有些像一般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以拟想叙事者的话语面貌出现在作品中的语言,有些其实是小说人物说的话;同样道理,在“涓生手记”的小说文本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以作品人物面貌出现的话语也承担着一定的“叙述人”任务。涓生每每想到子君的死,在具体叙事文本中有一定的提示作品结局的作用。作品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涓生之“想到”,可能的解释是涓生已经意识到了,或者说作者想要通过涓生“手记”这一方式让读者明了,子君的最终结局将是死亡。
我们已经说过,在《祝福》和《伤逝》中,前置死亡的目的是为了便于隐性处理人物的自杀;正因如此,两篇作品都沿着大致相同的路径,进一步诠释和暗示了作品人物必将自戕的其他一些可能。在《祝福》中,作者“别有用心”地为自己叙事意图的实现,做了一个经验性的假设:“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恐怕这事也一律。”⑤果不其然,“傍晚时分”鲁四老爷就高声地议论起了祥林嫂的死:“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⑥这里我们要分析鲁四老爷的两个关键用语:“不早不迟”和“偏偏要”。我们知道,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如果说“不早不迟”是一般意义上的“恰巧”之义,那么你有什么理由认定“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即使是冥顽不化如鲁四老爷者,也还应该属于是社会上的正常之人吧?“人命关天”,“天命难测”,祥林嫂自己都没办法让自己再活下去,你鲁四老爷又有什么理由怨恨她呢?“偏偏要”的“要”字,是主动强行选择的标志性用语,只有因为祥林嫂自己决定的行为才配得上“偏偏要”这三个字,否则鲁四老爷不会犯这样的语病“授人以柄”。我们再来看子君的情形。虽然子君的死亡也可从其他人的言论中觅得死因的蛛丝马迹,但为了便于与祥林嫂做对比,有关情况我们下文再详述,这里先从叙事逻辑的角度来探讨为什么说她是自杀。一般说来,任何叙事性作品的主人公都承载着作品意向实现的主要“责任”,因此作者要赋予他一种确定的人格气质和精神志向,整部作品便围绕着主人公这种人格气质和精神志向展开叙述。他的追求或者实现了或者落空了,只要结局一出现,作品也就结束了。在主人公的精神志向没有能够实现的结局中,主人公或者转移了生活境地,“离家出走”或到别处另求发展;或者遭遇不幸,人物和人物的精神志向同时毁灭。在后一种情况下,主人公的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伴随着自己精神志向遭到打击的同时,身体也遭到相应的伤害,病殁是其典型表现形态;另一种便是自杀身亡。而不管是哪种情况,一般都不允许出现意外伤害的情节,因为那样将破坏作品内在叙述逻辑的统一,引导读者产生不利于作品主题意向表达的思考(有时好像出现了意外,其实那也是“情理之中”的另一种表现)。那么在《伤逝》中,子君的死应该属于那种情形呢?“意外”已经被排除,病殁也没有先兆,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自杀。如果不自杀就不能解释作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她到底因何而死;而如果是其他方式的死亡就与作品的内在叙事逻辑发生了矛盾,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作品的内在精神统一。
祥林嫂和子君系自杀身亡,还可从接近她们的人对她们死亡的评价中得到进一步说明。在人世生活中,任何一个个体的死亡,都不仅是个体行为,还与群体的生活期待和一般社会伦常意识表达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人们对一个已经选择了走绝路的人多少都会怀有一丝悲悯,当“我”向下人求证祥林嫂的确切死因时,“短工”没有从正面回答就是这样。“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⑦这句话一语双关:从本质上说,祥林嫂确实是因“穷”而死,“短工”的话一点都不错;但另一方面,对非正常死亡之人死因的“避讳”,尽可能不去正面议论是中国民间固有的风俗。其原因恐怕是:自杀都不是人们愿意采取的行为,表面上看自杀的责任在自杀者自己,但实际上在行为主体原本不愿意又不得不采取这种行为的困境中,总有一些可以被人理解和同情的外在因素在起作用,正因如此才形成了人们一般不愿正面回答自杀者死因的风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向一个熟悉的人打听另一个熟悉的并已知死亡的人是怎么死的时候,而他应该知道却不正面回答,那么可以肯定,那个已知死亡的人一定是非正常死亡。“短工”对“我”之询问的回答,就建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他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在明眼人看来已经等于回答了祥林嫂到底因何而死,而“我”也明白所谓“穷死的”只不过是一种“宽慰”。⑧需要指出的是,在鲁四老爷“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和“短工”“怎么死的”话语文本之后,都留有一个长长的“——”号,它表征的是有些话还没有完全说出来之意,是什么话、为什么没有说出来?自戕避讳之所为也。与此相类似,人们在谈论子君死亡原因时也可看到大致相同的思维逻辑在起作用。我们知道,在《伤逝》的叙事文本中,子君与涓生的恋情曾受到了来自社会不同层面的联合打击,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他们痛苦地选择了分手的时刻,正是这一联合阵线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刻。子君跟随他父亲回家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如果是“暴病”,那是“天谴”的最好谈资,以“鲇鱼须”和“雪花膏”之流的“胡同监察党”品格,决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是自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还说三道四,恐怕就要承担一定的“流言杀人”的责任,此时避之还惟恐不及,有谁还愿意出来做饶舌公?这可看做是作品有关谈到子君死亡情节时,人们都显得有些吞吞吐吐、三缄其口的现实原因。把子君的确切死讯告诉给涓生的是他家族中的一个“世交”,当涓生追问子君到底是怎么死的时,他也没有从正面回答,只是话里有话地应承了一句“总之是死了就是了”。⑨我们感到,此人是站在涓生立场上说话的,他不告诉涓生子君的具体死因,是因为顾及到了涓生的处境:子君的死与涓生有分拆不开的关系,如果他告诉涓生子君是自杀,不啻于在当面指责他给他以难堪。“总之是死了”的话语,也相当于在其后面留下了一个“——”号,其潜台词是:事情都过去了,再沉浸在里面、过于自责也大可不必,知道了子君的具体死因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子君的死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对涓生也是一种打击,涓生没完没了的忏悔和自责,也可看做是他为自己“自圆其说”的一种替代表现方式。
二
祥林嫂和子君的“隐性自杀”,承载着诸多繁复沉重的话题,远不是一般死亡和明确显性自杀所能揭示的;而一旦我们认定了她们系自杀身亡,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思考。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作品人物性格的深入理解和再发掘。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和对比:如果像一般人们所惯常理解的那样,祥林嫂拖着疲惫的身躯倒毙在冰天雪地之中,虽然也会让人震惊和扼腕,但显然与她在此时选择了自绝于世不可同日而语。联系到她问“我”,死去的一家是否可以见面,我们感到,让祥林嫂生不如死、生死都无法解脱的原因,真的与“穷”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相反倒确实与“灵魂”有扯不断的因缘。正像“我”所揣摩的那样,鲁镇的人们一般都对灵魂的存在深信不疑,可祥林嫂此时却对它发生了“疑惑”,⑩否则还以她曾经“捐门槛”的心态来度量,祥林嫂在那种情境下是不敢死的,她怕死后被锯成两半;也就是说此时她虽然“穷”,但对一般社会伦常并没有失去信心,惧怕死后的遭遇,也说明她对现实还存有某种希望。可是在经过了一系列打击之后,她对曾经被自己奉为圭臬的社会伦常发生了怀疑,她的精神支柱崩塌了,此时才不惧怕什么,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只有这个时候,祥林嫂才敢于自杀,她的自杀才会对一般社会造成巨大冲击。鲁四老爷骂她是“谬种”,从某一层面看,一点都不错,此时的祥林嫂确实已经不是原来的祥林嫂了,她不再顾及“鲁镇人”的那些清规戒律,就是要用自己的死给他们的“祝福”“添堵”,鲁迅想要用祥林嫂的死达到这样的叙事目的,祥林嫂也从自身的遭遇中感到自己应该这样做,否则正如鲁四老爷所言,为什么“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呢?祥林嫂的死发生在人生道路选择的一个重要“序列点”上,这个“序列点”,可以是对原有人生信条深信不疑,却又茫然无所适从之时;也可以是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不再抱有一丝希望,即所谓彻底失望之时。前者也有失望,但还有不甘心、怀有某种希望的成分;后者则不然,它仿佛明了了过去的一切都是“白绕”,一下子陷入了思想的真空地带。一般选择自杀的人,大约都或真实或虚幻的生活在后一种不能自拔的境地中,祥林嫂也不例外。而这一点对我们理解祥林嫂的性格关系极大。我们知道,鲁迅在探究中国“国民性”时,对下层民众常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厚人文关怀,(11)祥林嫂也往往被人纳入到了这一人物序列中来理解。可是在我看来,祥林嫂与阿Q和华老栓不同,在她身上,有让人“哀其不幸”的因素,却没有多少“怒其不争”的成分。相反她倒与魏连殳、《长明灯》中的“他”有相近的性格因素:为了逃避再婚,她不惜以死相抗争;为了洗去自己的所谓“不净”,她可以倾其所有去“捐门槛”……这样的女子是有烈性的,所以她才敢自杀,敢于选择家家喜庆的“祝福”之夜自杀。只是因为她视野有限,“人微言轻”,做不了什么大事,只能以死来表达自己的这份悲愤而已。她的死有某种“反社会”倾向,是一种与世俗伦常相决裂的姿态反映,用鲁四老爷的话说就是“一个谬种”!这样的祥林嫂才是真正的祥林嫂,而这一点却在以往研究中有意无意地被人遮蔽了。
自杀身亡这一作品“功能情节”的认定,对于理解子君的性格来说也同样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子君曾说出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时代宣言。(12)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当她与涓生的关系破裂、被父亲领回家里之后,这句话对她还有什么意义?曾经的代表着时代主潮的意识获得能够被轻易地放弃吗?所谓当涓生和子君同居以后,涓生感到子君有些“谨小慎微”了,具体所指是什么?现实根据在哪里?是对于“爱”的得而复失的恐惧?还是对曾经反对过自己命运的外力的恐惧?二者好像似一个问题,其实差别实在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是前者,正如同是以女性主体身份发言的萧红在遇到了感情危机时所言,“父亲是我的敌人,可他不是”。(13)在对待两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两个有联系却又有所不同的问题上,一般说来,女性在面对后者的威胁时会表现得更为坚强,当面对前者的打击时却相对“软弱”不少。子君惧怕生活的打击,本原在于惧怕与涓生关系的破裂,“她……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14)正因如此在涓生表现出一些对自己的冷淡之后,她才不断地逼迫涓生去温习旧“功课”。这也就是说,当子君与涓生的关系破裂、被迫回到父亲家时,其遭遇与“我是我自己的”信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也还与其隔着好几层。一个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后底线就是自己的生命,子君的自杀,那是宁死不屈的一种表现,在本质上是坚持“我是我自己的”最好表征。在这一点上,子君与祥林嫂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在用同样一种方式申诉着自我,也正因如此,鲁迅才用了大致相同的叙述模式交代了她们的类似结局。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人们倡导和推崇文学作品要写悲剧。对于什么是悲剧,鲁迅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5)虽然他没有过多地去重复“怜悯”、“恐惧”和“净化”等经典悲剧意念,但从“有价值”和“毁灭”中还是透露出了鲁迅悲剧观中同样具有“崇高”的因子,可以说鲁迅的悲剧意念与经典悲剧意念一脉相承。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出现了:祥林嫂和子君是不是悲剧性人物?她们都“毁灭”了什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她们的遭遇与鲁迅的悲剧意念联系在一起?以她们为主人公的作品崇高感到底来自于何处?我们曾说过,祥林嫂和子君与阿Q、华老栓不同,她们身上有魏连殳、《长明灯》中“他”的身影,甚至也有鲁迅自己的人格渗透;这种性格特点,这种人格渗透,在《过客》中有体现,在如人“无物之阵”的“这样的战士”身上也有体现,(16)可以说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一直都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显示着其特有的品格。《祝福》和《伤逝》也是如此,在家家“祝福”的喜庆氛围中,祥林嫂的自杀不啻于给鲁四老爷之流迎头泼了一瓢冷水,在几乎所有人都沉浸在“离家出走”的喜悦中时,子君的遭遇也让人警醒了不少。现在我们想要说的是:如果祥林嫂形单影只、仿佛自消自灭在了冰雪途中;子君积怨成疾、悄然化为孤魂野鬼,这与《祝福》和《伤逝》的孤愤决绝气质不是有了不小的反差吗?祥林嫂和子君都是悲剧性人物,这里所说的悲剧性人物不仅仅是用不幸遭遇的意念可以涵盖的,还与她们身上的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的意念相关,与她们身上的“不应遭受的厄运”之人的品行和“犯了错误”相关。(17)祥林嫂是“不应遭受的厄运”的人,她是个有骨气、有毅力、敢作为的人;但她犯了“错误”,她曾经相信、也不能不相信一般的社会信条,最终当她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觉察的时候,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结果她只有死。子君更是如此,她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实在不是一般人所敢作为的;但她也“犯了错误”,她没有顾及到自己行为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在这一点上她似乎更具有悲剧人物的气质,更像是一个自愿踏上牺牲祭坛的人。祥林嫂身上的坚忍烈性人格成分被“毁灭”了,子君身上的卓尔不群精神志向被“毁灭”了。如果她们能像当时社会一般人那样随遇而安,祥林嫂不去“捐门槛”,接受鲁四老爷对自己“工作”的安排;子君服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她们能“死”吗?反过来不正说明她们是自主走上了绝路吗?自杀只是一种精神象征,也只有从自杀的角度来审视她们的死,才能体会到汇聚到她们身上的那种悲剧主人公的可贵精神品格。
三
以上我们主要从内在人格气质和作品精神气质的一致性方面探讨了祥林嫂和子君的自杀行为;至于作品为什么要“隐性”处理她们的自杀,显然仅仅从这个方面着眼还不够。其实,鲁迅不仅谙熟美学之奥妙,更深通小说艺术之三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他曾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创作作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在一刹那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的作品,有时阻碍了作品情感的深入表达。(18)鲁迅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都以死亡的方式退出叙事文本,比如“以送殓始,以送殓终”的《孤独者》,(19)以人血馒头作为治病“偏方”而最终没有救得华小栓命的《药》,糊里糊涂被枪毙的阿Q,始终没有再见过面的孔乙己,等等,都是这样。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他的小说在当时能够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一方面与其慧眼独具的社会剖析有关,一方面也与其“一篇一个样”的新颖独特“格式”有关。(20)采用“隐性自杀”方式交代祥林嫂和子君的人生结局,有两个显而易见的艺术考量。第一,避开了多少已经被模式化了的流行创作风气。如所周知,在那些“一刹那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的作品中,主人公的最后死亡也是“不幸”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而很多人又都是以自杀来结束自己人生里程的。一方面,如前文我们分析过的,当一个有完整一致性的主人公行动完成了之后,便没有了继续被叙述的依据,在以失败为结局的作品中,死亡既是他们个体行为故事完整性的需要,也是作品意蕴伸张一致性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公的死亡似乎不可避免。可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许多作家受到诸多方面条件限制,在人物行为一致性方面考虑更多的是社会现实因素,死亡被从人物性格规定性层面向外推移,更多地与诸多不幸的遭遇联系在一起,而与人物内在精神追求显得有些若即若离。这样一来,主人公的死亡就或多或少退化为一种博得人们廉价同情的方式,当许多作家都想走这条捷径的时候,鲁迅小说采用“隐性自杀”方式来处理主人公的死亡,“一刹那中”还不容易被人想到,也没有能力被他们表现出来,由此拉开了与流行写作趋向的距离。第二,“隐性自杀”是鲁迅小说“陌生化”叙事手段的特有方式。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死亡没有一个是采用显性自杀方式的,它一方面说明鲁迅不屑于随俗,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在鲁迅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方式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隐性自杀”在或一层面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致,当人们的欣赏欲望被调动起来之后,在建构具体人物故事性结局时又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此时,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探讨的那样,当人们去追究作品人物的具体死因时,有些在显性死亡状态下被人忽略的叙事成分就可能引起人们一些更多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作品的深层叙事意蕴就可能得到进一步开掘。从这个意义上说,“隐性自杀”也是鲁迅小说所擅长的“著者的一个思想借着故事写了出来”的叙事策略体现,(21)是理解鲁迅小说艺术倾向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鲁迅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之所以都以死亡的方式退出作品文本,很大程度上与鲁迅所赋予作品人物身世的引申意义有关。鲁迅小说中人物的死亡,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格外强调了死亡对于作品意蕴伸张的功用。仅仅是华小栓死了,对《药》的故事来说,显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问题是被华老栓寄予厚望的所谓“药”,与医治华小栓的“病”完全“货不对板”。这样一来,不但夏瑜的死被庸俗化了,华小栓的死也被戏谑化了,从他们的死亡中,让人看到远比他们的“死”严重得多的问题。阿Q糊里糊涂的死,孔乙己不明不白的死……在鲁迅作品中,几乎所有人物的死亡都有超出死亡本身的别一种意义存在。
我们知道,现在被我们称为小说的那种文类,在中国古代主要指两种文本,一种是指文人小品笔记类的创作,一种是指流行于普通民间的讲说类白话故事。鲁迅小说的格调,显然与文人小品笔记类“小说”联系更紧密。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分析过鲁迅小说与他的小品类“文章”的文类体式互侵问题,指出鲁迅小说有小品的倾向,他的小品也有不少小说的成分,这种小说类型意识让他没有写长篇小说也根本写不来长篇小说。(22)在这里我想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小说类型意识也与主人公的死亡和“隐性自杀”密切相关,有意地淡化了必要的故事情节链,留下了太多的问题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这与写实小说是不一样的”。(23)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小说亦近诗……如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等,见之《战国策》者,皆诗人寓言,亦比兴之流。”(24)鲁迅最好的作品,“像他的《呐喊》之类,这和西方小说不同,还是中国小品文传统”。(25)而《祝福》和《伤逝》的“隐性自杀”不正是建立在用“诗人寓言”、“比兴”手法写小说基础之上的吗?“隐性自杀”和其他死亡情节的精神隐喻,在“《呐喊》之类”的“中国小品文传统”的小说类型中更容易被体现,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的“一种”小说类型原本就有这种倾向。
说到鲁迅小说的文类特性和艺术倾向,一定不要忘了,鲁迅对《红楼梦》的高度评价,一定也不能忘《红楼梦》并非是文人小品和笔记类文章。《红楼梦》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学中不多见的文人长篇叙事;但即便如此,《红楼梦》也应该归于文人的创作,是中国传统文人叙事类作品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其诗意的运笔方式更是文人“小说”的典范。“金陵十二钗”的曲词中隐含着多少耐人寻味的故事?秦可卿是怎么死的?这些都有几分清楚、又有几分迷离,由此引来众多“红学”专家的反复探讨。那么这与鲁迅小说有什么关系?与鲁迅对《红楼梦》的高度赞赏又有什么联系?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是演义故事型的,交代明白作品人物的来龙去脉是起码的要求,它要求故事线索清晰,叙事链条不能有什么中断,否则会引发读者的狐疑。《红楼梦》不是这样,鲁迅小说也不是这样,它们都在叙事链条中有意遗留了一些空白,让读者自己去充填,这是它们的共同艺术情趣使然。鲁迅赞赏《红楼梦》,也深得《红楼梦》叙事之真谛,“隐性自杀”多少汲取了一些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人传统叙事经验,就像秦可卿的死,隐含了许多“不述之作”一样,祥林嫂和子君的死也隐含了太多的“未叙之言”。鲁迅小说擅用“曲笔”,(26)与《红楼梦》走在了同一创作道路上,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中国传统文人叙事倾向的特有生命力和现代可能。
注释:
①⑤⑥⑦⑧⑩鲁迅:《祝福》,《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5、5、6、6、3页。
②③④⑨(12)(14)鲁迅:《伤逝》,《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9、130、133、134、116、133页。
(1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13)萧红:《苦杯》,《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出版杜1991年版,第1173页。
(15)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16)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
(17)亚理斯多德:《诗学》,亚理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9页。
(18)(20)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9)鲁迅:《孤独者》,《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8页。
(21)(23)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22)袁国兴:《鲁迅小说与“小品”类“文章”的文类体式互侵——兼谈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小品小说”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4月。
(24)钱穆:《中国文学论丛·诗与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2页。
(25)钱穆:《中国文学论丛·中国文学的散文小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4页。
(26)鲁迅:《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杜1973年版,第6页。
标签:伤逝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祥林嫂论文; 自杀论文; 文学论文; 死亡方式论文; 红楼梦论文; 鲁迅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小说论文; 彷徨论文; 祝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