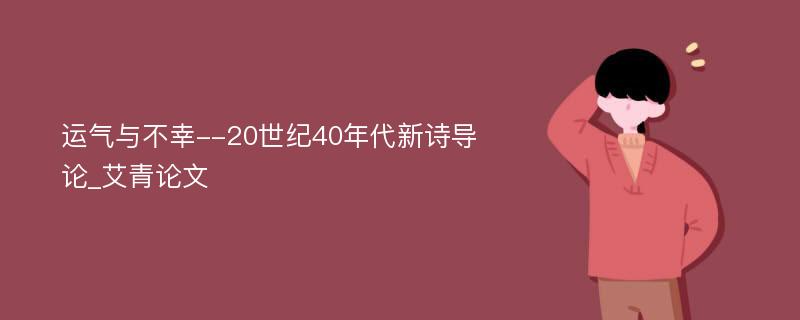
幸与不幸——40年代新诗概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不幸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中国多灾多难的40年代,诗歌的确迎来了又一次发展的机会。当年艾青就多次反复地肯定了这一点,他说:
抗战以来,中国的新诗,由于培植它的土壤的肥沃,由于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困难,由于诗人的战斗经验的艰苦与复杂,和他们向生活突进的勇敢,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多少地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充实和丰富了。
(《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
从抗战以来,新诗的收获,决不比文学的其他部门少些。我们已看到了不少的优秀作品,那些作品主题的明确性,技巧的圆熟,是标帜了新诗发展之一定程序的。那些作品,无论在他们的对于现实刻画的深度上、文学风格的高度上,和作者在那上面所安置的意欲之宽阔上,都是超越了以前的新诗所曾到达的成就的。
(《诗与时代》)
至于抗战以来的新诗,它是二十年来新诗的延续,它的成绩,无论从量上和从质上看,都不会失去了作为“更进一步的发展”的价值。许多诗人献身给战争,许多诗人为祖国的命运而呈出了自己的赤诚的心,许多诗人用无比真挚的语言诉说了对于祖国的爱……这些诗人将和祖国共存亡,这些诗篇将和祖国共存亡。
(《诗的祝祷》)
作为40年代新诗的见证人,作为新诗创作和评论的忠实实践者,艾青的这些评价应当说是准确的。其实,当时很多诗评家也都对新诗的成就持充分肯定的态度。时隔30多年后,绿原在《白色花》序中也说:“单就新诗而言,随着抗战对于人民精神的涤荡和振奋,40年代也应当说是它的一个成熟期。不但艾青的创作以其夺目的光彩为中国新诗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更有一大批青年诗人在他的影响下,共同把自由诗推向了一个坚实的新高峰,其深度与广度是20年代和30年代所无法企及的。”
纵观40年代诗歌,它有着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历史贡献。
“五四”以后,新诗与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体裁平行发展,但在40年代,诗却比其它文学样式获得了更多的参与机会。诗歌运动、诗歌研讨活动最为热闹,各种诗体的试验最为活跃。作家、诗人写诗,广大群众也写诗。诗与一切文化活动紧密相连,诗与一切现实斗争紧密相连,诗参与现实生活的热情和参与的广泛性,大大地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在40年代,诗渗透到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诗出尽了“风头”。
很多文化人士借助诗这种形式介入广泛的社会层面,通过诗歌这种形式表达出广泛的社会共鸣。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同步,诗歌经历了一场较大的革命,它在观念上强化了它的工具性,同时在形态上经历了一个脱雅入俗的过程,渐趋大众化与民间性。诗歌传播与诗歌普及的广泛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结着社会和大众,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发挥了社会“代言者”的职能,诗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与亲近,它有力地宣告了诗歌作为理性载体的胜利。
在40年代,诗歌和当时社会一样,在趋同中寻求发展。虽然那时诗歌团体不少,但真正具有流派性质的也不多,即使具有流派性质的中国诗坛派、延安诗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也并不存在像20年代和30年代那样的流派间的尖锐对立状况,并且流派之间的趋同性是明显的。如中国诗坛派、延安诗派和七月诗派都是遵奉现实主义的流派,其政治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并无大异;九叶诗派在忠实现实情感方面也与其它诗派相通。当时的诗坛求同是主导性的,而同中也有相异的部分。如果说20年代是一种“共生、皆荣”的诗歌格局,30年代是一种“冲突、并存”的诗歌格局,那么40年代则是一种“求同、存异”的诗歌格局。当然,这种求同的主导性格有利于诗歌声势的扩展,有利于诗歌社会功利作用的发挥,同时,也有利于诗歌水平的整体性上升。但是,风格迥异的诗歌流派的减少和隐退,也影响了诗歌的多方面的开拓与发展。不过,像真正具有流派特征的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在寻求流派的发展中,为40年代诗歌增添了多样的光彩。当40年代诗坛主潮把为政治服务、紧贴现实抬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内容的“革命”掩盖了诗质和诗艺的时候,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都从各自的立场感到了矫正时弊的必要,感到了诗人应该具备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品格与能力,只有把创作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压力下,把它纳入到时代与我们自身的多重关联中,才能获得一种切实的诗歌意识和一种敏锐的话语转换能力。七月诗派在坚持现实主义的时候,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使诗歌保持本体抒写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九叶诗派则以平衡的姿态,矫正诗的多种偏向,使诗回到诗那里去,使诗不失去应有的特质。正因为这样,40年代中后期诗坛更趋多元化,诗歌的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这说明,诗歌的发展,离不开流派间的竞争与开拓、趋异与协调的作用。
在整个40年代,浪漫主义一直附着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中,没有独立地生长起来,也没有形成流派。可以看到,在延安诗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那里,或明或暗地呈现出它那活动的身影,它仍然像30年代一样,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特征。在本时期,现实主义成为诗坛的主潮,很多诗人对此趋之若鹜,但沉潜其中的认真探索者并不太多,一股浮躁、肤浅之风,使其所取得的实际成就与它所表现出的声威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但从整体上看,现实主义由于得着良好的机遇,还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有成就的现实主义诗人中,也并非千口一腔,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在现实主义的同台和声中,艾青、田间、臧克家都是有着独特风格的诗人,他们的诗都是直接从现实中发掘出来的,都在真实的创造中给读者以真实的思考和感动,但也有很大的区别。田间是以人民大众的战士的燃烧的热情歌唱真理与斗争,以“年青的笔”,“养育”“斗争火焰”,其诗的直接鼓动的效果十分强烈,为艾诗所不及。臧克家与艾青一样,其诗魂依附于祖国多难的土地上,诗的激情发自于时代斗争洪流中,但其诗情在强烈的爆发中过于直泄,很多时候与田间一样是喊出来的,因而没有艾诗那样含蓄蕴藉、深沉凝重。而艾青当时对现实社会生活、矛盾斗争和人民情绪的思考与反映,却比田间、臧克家深刻,他善于塑造形象和驾驭多种表现手段,长于营构意象与意境,其以内在的诗意光彩有血有肉地再现生活的感受的艺术才能,为田间、臧克家所不及。三位诗人都是“五四”以来形成的自由诗的推动者。田间创造了新的形式,但还没有完成自己,还没有完全建立起适应新形式的机能,还未能与他所歌唱的对象完全融合;艾青是经历过所有的诗的形式的熏染,积蓄着丰富的艺术经验,达到了风格的完成的诗人;而臧克家追求形式的严谨和规范,承续中国的诗歌传统,其诗具有古典美,但它不及艾诗那样开阔、奔放与自由。三位诗人都为新诗现实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却表现出不同的内在指向性,如果说臧克家是连接着过去的诗人,田间是紧握着现实的诗人,那么艾青则是开创着未来的诗人。
现代主义虽然一度受挫,但它却在西南联大校园复兴起来,其后又蔓延至上海和燕京校园等地,在沦陷区也有不少现代主义诗人在坚持创作。现代主义由于受着外部条件的挤压,其活动的时空受到极大限制,但却在艰难的环境中获得了沉稳的发展。这时期的现代主义不但与世界现代主义潮流进一步取得了联系,而且在与民族时代生活的结合上比以前更紧密、更深入了。他们在深刻体认现代主义精神的基础上,自觉地确认“新诗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他们在现代主义诗歌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统一上进行了新的成功的探索,并由此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推向了更加成熟的境地。在现代主义诗人中,卞之琳、冯至、穆旦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不但与西方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互雷里、里尔克、艾略特等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且对中国古代诗歌也有相当的修养。他们在广采博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创造出了别开生面的现代主义诗歌。他们的创作标志着现代主义从情绪诗化到智性诗化的发展,他们那民族的大忧患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他们那激烈的内心搏斗、深层的心灵体验和对生命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给现代主义诗歌带来了理性的沉静与深化,其诗思在总体上比以前的现代主义诗歌更深沉,更博大了。在诗歌艺术风格上,三位诗人都以严谨著称,但这其中也有区别,卞之琳的《慰劳信集》相当精致,但格局太小,深厚不足;冯至的《十四行集》相当严谨、深刻,但开阔不足;穆旦的现代诗不但严谨、深刻,而且灵动、开阔、丰厚,显示出大家的气度。在他的诗中,明显透露着未来诗歌的信息。
在趋同日甚的40年代,一些执着的诗人并不墨守成规,他们在诗歌的形式与技巧方面仍然保持着探索、实验和独创的热情。因而40年代诗歌虽然在内容表达上的主导性倾向非常鲜明,但在对表现这种主导性内容的诗形的追求上,还是有一种多样化趋势,也就是说,诗人们不但没有忽略诗的存在形式,相反,在诗体的革新方面获得了较多的建树,在整个40年代,应当说诗歌的形式的解放的幅度是最大的。如前所论,40年代社会生活和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决定了诗体的全面发展趋势的形成。4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学思潮,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倡导和探索,并不限制其它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诗歌的创作。有的喜欢运用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有的学习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阶梯诗,有的写惠特曼式的诗,有的写民歌体,有的写十四行体,有的写诗剧,还有的写旧体诗词,各施己长,争放异彩。“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为中国诗人们提供了行动的节奏,战斗的节奏。它不是模仿的,而是与自己的要求相应的”。在那时,“阶梯诗是先锋派的诗,实验性的诗,它把中国汉字的力量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打出了马蹄的节拍,鼓点的节拍,金属敲击的节拍”(注: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在40年代众多诗体中, 自由诗是其主流。自由诗在形式上所表现的弹性和动力,在词句上所散发的新鲜气息和感情色彩,在形象上所反映的个人独创性和社会内涵的一致,表现了自由诗已进入成熟的境地。同时,40年代诗歌的表现技巧也大大提高了,这种提高,是指诗歌的艺术表现力的综合性增强了。可以说,这一时期真正的好诗,技巧是相当娴熟的,这主要不表现在对某一技巧的单向掘进与发展上,而是体现在诗人能融多种技巧于一炉,创造出能够反映时代生活和思想情感的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好诗,而不像二、三十年代的“好诗”那样存在一种普遍倾向:要么诗歌内容积极而艺术性则较弱(如革命现实主义诗歌),要么诗歌内容消极而艺术性则较强(如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而是二者得到了较好的统一。这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歌在现代情绪中融进了浓厚的时代内容(如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的诗),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也常常把现代主义技巧化入诗中(如艾青、田间、臧克家、袁水拍、绿原的诗)。因此,诗歌的纯粹性减少了,综合性增强了。这种综合性有利于造就杰出的诗人和推出纪念碑性的作品。
当然,在诗艺的探索上,当时的诗歌派别和有影响的诗人都有自己的侧重和选择。延安诗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正好表现了当时诗坛的三种倾向:一是承续“五四”新文学人文主义精神,真正完成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相对接的启蒙主义诗歌(如七月诗派);二是主要以现代主义为先导,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后援,刚刚展现出人本主义光亮的现代主义诗歌(如九叶诗派);三是主要借鉴苏联无产阶级文学模式,但又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集体主义理性诗歌(如延安诗派)。延安诗派诗人首先要求自己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们作诗,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战斗武器、文化工具,其次才要求它是诗,也就是说,延安诗人“服务于政治比服务于艺术更多”,因而他们的诗基本上更多政治的、文化的品格,而少的是诗的品格,在诗与非诗之间,它更多非诗的因素。经过时间的淘洗,这些诗越来越属于社会的历史的范畴,而渐渐从诗的范畴淡出了。七月诗派诗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再加上他们来自更广阔的生活领域,斗争生活的复杂性和情感的丰富性,决定了他们的诗的内容比延安派诗歌更丰富多彩。由于大家把诗当作诗来写,因而诗的艺术个性也较多样化了。他们的不少诗作将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九叶诗派是一群诗歌的缪司,他们大都熟悉外国文学,对西方现代派诗歌接触较多。他们的创作,力求写出自己对时代生活的思考,写出自己内在的思想情感的波澜。他们对诗的艺术性的执著追求使他们的诗具有了浓郁的诗性特征,具有较高的诗的含量。尽管他们的诗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并不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诗的艺术价值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整体上看,40年代诗歌的脉络,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生活与政治文化的猛烈冲击,使诗歌日益公众化、功利化,另一方面,诗歌又按照自己的美学逻辑发展,逐渐退守到诗人的内心和自己的经验世界中;一方面诗歌在时代外力驱动下,日益趋向意识形态化和非诗化,另一方面,诗歌又以顽强的生命力寻找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凡有成就的诗人,在这二极之间却能保持平衡的张力,他们的创作大都既有相当沉重的社会性内涵,又有相当的艺术质量。他们那些承载了社会历史内容的诗,并不因为“代言”而失去“诗”的品质。其中,李季的诗成为民歌体诗的佳构,袁水拍的诗成为政治讽刺诗的代表,穆旦的诗成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高峰,而艾青则是超乎众多诗人之上的大诗人。他的诗在思想、智力、感觉和感情方面提供的经验相当丰富,令人品味无穷,他的诗在意象、词语形体和内在结构等方面有许多匠心独运之处。它标志着中国新诗可以达到的某种境地,为中国新诗艺术的拓展打开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间。艾青诗歌的探索性和建设性,对于那个充满了惰性和寄生性的诗坛来说,是一种惊喜。其意义和价值越到后来越明显。特别是他在新时期复出后的创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它的影响。他的创作实践,成就了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他的诗艺道路,已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一种标杆。
40年代的苦难和斗争确实造成了诗歌的繁盛,但也要看到,在“有幸”的背后也有“不幸”的一面,或者可以说,这既是诗歌蓬勃发展的时代,又是诗歌“贫乏的时代”。因为40年代的文学在总体上是寻求一种适应性,适应那个革命战争时代,适应主流文化提示的生存空间,因而不少作家和诗人难以保持诗艺探索的热情。那时的主流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核心是功利原则,功利追求就很容易导致一种盲动的从众心理。这就难免不造成诗人趋赶潮流的局面,难免不使一些诗人在“非诗”的路上走得更远。
40年代诗人似乎大都不缺乏表达才能,也不缺乏诗的思想与情怀,但他们普遍缺乏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独特想象和理解。一些诗人常常在表达理性经验的时候能达到一定的深度,但一旦再往大处走、往深处走,就不免显得力弱。大多数诗人“没有一种自觉的精神与一份超越的或深沉的思想力,许多人为抽象的意识与外在的单调的现象所吸引,忽略了诗人自己所需要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成”(注:唐湜:《新意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再加上理性意识的强化,很多诗人减少了诗的灵性,这使得他们的诗歌与艺术的感知境界离得更远了。因此,在40年代诗坛,“最普遍的现象则是情感的不够深沉,思想力的薄弱”(注:艾青:《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同时,40 年代的诗歌体现出来题材的单调性,内在意蕴的雷同性,格调的相似性,显得十分触目。所以,40年代诗歌最缺乏的就是诗人的鲜明而突出的个性。诗人们在强调自我的群体认同的同时,对个体的自我认同的弱化,就必然导致自我的普遍化(亦即将自我视为某种普遍规范的化身),这就使不少诗人最终没有获得独特的感情表达方式,最终没有如此充满个性地发展下去。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时代使然,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命题。在40年代,诗歌的命题是什么,诗人的时代命题是什么,可说是每位诗人思考和关注得最多的问题。诗人们是从整个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角度来思考自身命题和安排自己的献身精神,而不太重视个体的创造,不太重视艺术本身的问题,这就难免出现诗歌内容积极向上,具有激人奋进、催人战斗的鼓舞力量,而艺术性则普遍不强,艺术水平普遍不高的倾向,即艺术的定位与历史的定位没有得到很好的平衡。所以那时的诗歌都是时代的诗歌——充满时代共识精神的诗歌,而诗人的个性的光亮则没有充分闪射出来。
由于40年代诗歌确实存在着很多缺失和不足,而且这种缺失和不足似乎显得比20年代和30年代更为突出,因此,有些人对40年代诗歌评价很低,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诗歌的“倒退时期”、“调零时期”。其实,从总体上看,40年代诗歌的成就并不让于此前新诗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诗歌的群体实力与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保证了诗歌质量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时期诗人之多,创作之活跃,是从前不可比拟的。尽管那时诗歌的粗制滥造者和平庸之作占了相当的比例,但如果从40年代大量的诗作中挑选高质量的诗作,可以说,在其数量上是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并且这时期诗歌与民族的命运、阶级的命运融合了,与大众接近了,诗歌所表现的现实性和集体主义理性精神,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诗歌都更普通更强烈,也更深入了。同时,由于诗歌大都集中于爱国主义这个时代主旋律上,在诗歌格调上普遍表现出一种昂奋的时代情绪,从而呈现出诗意的整体辉煌,显示出鲜明而阔大的时代诗歌的个性。这种时代个性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性、一致性特征,正是那时诗歌得以存在的价值。如同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恬静与神秘、唐诗的苍凉与豪放、宋诗的理智与做作,给人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印象一样,中国40年代诗歌的悲愤与激越的诗风,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这一点,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诗歌最可宝贵的东西,它是最值得后人眷顾和发扬的。
标签:艾青论文; 诗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革命论文; 艺术流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