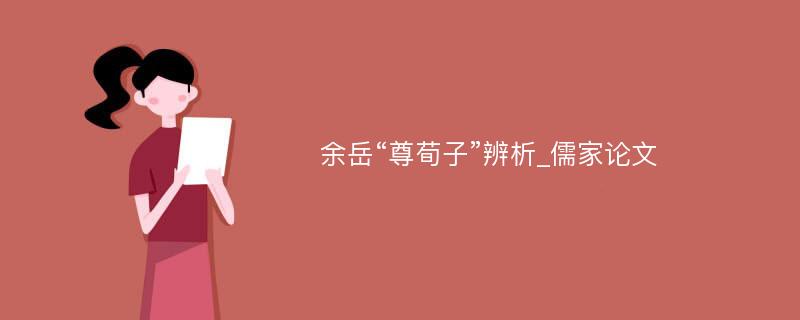
俞樾“尊荀”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俞樾论文,尊荀论文,析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是晚清汉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谨守乾嘉汉学的治学门径,在经学、诸子学、小学等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本文拟从“尊荀”这一角度,来探讨俞樾的学术和思想特色,以期弥补史学界在这方面的阙漏。
1
俞樾对荀子的尊崇,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注重对《荀子》的研究。这首先表现在俞樾的《诸子平议》一书中。该书以训诂考据为主,共35卷,囊括先秦至西汉诸子14家,其中《荀子平议》4卷,占全书的九分之一强, 而卷数超过《荀子平议》的只有《管子平议》,为6卷。在《荀子平议》中, 俞樾以唐朝杨倞的《荀子》注本为底本,在吸收乾嘉汉学家成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覃思精研,纠错改非,断以己意,力求通达《荀子》的旨意。如在解释《荀子·劝学篇》中“故不问而告谓之傲”时,俞氏认为,“《论语·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释文》曰:‘鲁读躁为傲’。《荀子》此文盖本鲁论。下文曰:‘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皆与《语语》同,惟变‘躁’为‘傲’可证也。‘傲’即‘躁’之假字。不问而告,未可与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注:俞樾《诸子平议》,卷十二,《荀子一》,上海书店1988年5月版,第226页。)相比之下,俞氏的解释要比郝懿行释“傲”为“赘”(意为不省人言)更为合理、通畅。
清代汉学尊崇古文经学,其中《诗经》为《毛诗》。在《毛诗》的授受脉络中,荀子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汉学家们依据的是唐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俞氏为了证明荀子在《毛诗》传承过程中的地位,专门作《荀子诗说》1卷。在《荀子诗说》序中, 他将这一意图表述得非常明白,他说:“按《经典释文》:‘《毛诗》者,出自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即荀子——引者注),孙卿子传鲁人六毛公。’是荀卿传诗,实为《毛诗》所自出。……今读《毛诗》而不知荀义,是数典而忘祖也。故刺取《荀子》书中引诗者凡若干事,以存荀卿诗说焉。”(注:《曲园杂纂》第六,《荀子诗说》,见《春在堂全书》,光绪刻本,下同。)在《荀子诗说》中,俞樾将《荀子》诸篇中凡引用《诗经》之处搜罗无遗,然后与《毛传》互证,大多数都相同,《毛传》几乎全部接受了荀子对《诗》的意义阐释。(注:《曲园杂纂》第六,《荀子诗说》,见《春在堂全书》,光绪刻本,下同。)同时,俞樾还用荀子对《诗》的解释来纠正《毛传》、《郑笺》对《诗》的误释,并考证出一些逸诗。在俞樾以前的清代汉学家,尽管也都推崇荀子传《诗经》的重要地位,但却没有从《荀子》中挖掘《诗》意来进行证明。俞樾对《荀子》引《诗》之文的搜集与探赜,则为《毛诗》的传承脉络之可靠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维护了古文经学的地位。
(二)对荀子思想的辩护与推崇。首先,俞樾对荀子的“性恶论”表示赞同,并为之辩解。众所周知,在儒家关于人性的学说中,以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最为显著。至唐,由于韩愈的大力提倡,孟子的地位直线上升,其“性善论”也倍受崇扬。到了宋朝,程朱等理学家更是推崇孟子为“亚圣”,其地位如日中天。相比之下,荀子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其“性恶论”也屡受攻击。俞樾则明确地宣布:“吾之论性,不从孟,而从荀。”(注:《宾萌集》卷二,《说篇·性说上》。)随后,他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孔子对于人性善恶问题并没有直言,只是认为性相近,所以不能对孟子的“性善”和荀子的“性恶”有所偏重。其次,孟子用来表述“性善论”的事实依据,如孩童之亲长敬兄、水之就下等,在推理上是靠不住的。再次,孟、荀二人虽然都认为人人皆可以成圣,但途径不同,而荀子的表述似乎更合理。因为“荀子取必于学者也,孟子取必于性者也。从孟子之说,将使天下恃性而废学,而释氏之教得行其间矣。《书》曰:‘节性惟日其迈’,《记》曰:‘率性之为道’。孟子之说,其率性者欤?荀子之说,其节性者欤?夫有君师之责者,使人知率性,不如使人知节性也。”(注:《宾萌集》卷二,《说篇·性说上》。)显然,俞樾对于荀子“性恶论”的认同,主要是由于荀子主张重视后天学习,强调礼教的约束和教化,这与清代汉学的“道问学”倾向及重视礼学的学术特色有密切关系。同时,俞樾在人性学说上的尊荀抑孟,也是其站在鲜明的汉学立场上对宋学的一种反击。
其次,对于荀子“法后王”思想的赞许。长期以来,荀子受到非议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学说中具有法家倾向,即主张“法后王”,因时变法,不拘于古。尤其是荀子的弟子李斯相秦,废置旧章,施行严刑酷法,致使秦以暴政害天下,二世而亡。人们在批评李斯的同时,罪及荀子。俞樾则认为,荀子的“法后王”思想主张秉承天意,达权知变,实际上是一种适应时势的学说,不能因秦的暴政及李斯的做法而否定荀子思想的合理性。随后,他引用《吕氏春秋·察今》中有关因时变法的言论为证,认为在“周秦之际,天固将大有变易,以开万世之治,当其时,学士大夫皆见及之,岂独荀卿与其徒一二人之私言哉!……然则因时变法,固当日之通论矣。秦虽不用李斯,而吕氏之徒固在也,以其说施于天下,则亦李斯也,岂必荀卿子哉!当战国时,守先王之道而欲用之当世者,莫如孟子,孟子之道不行,则天之意固可知矣。彼荀卿、吕不韦之徒,不可谓不知天者也。”(注:《宾萌集》卷一,《论篇·秦始皇帝论上》。)这就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荀子学说的正确,从而为荀子洗刷了污名。在《荀子平议》中,俞樾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并对“法后王”的含义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荀子所说的“后王”是指文王,并指出“后王”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若汉人则必以汉高祖为后王,唐人则必以唐太祖、太宗为后王。设于汉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谓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岂其必以文武为后王乎!……后人不达此义,于数千年后,欲胥先王之而复之,而卒不可复,吾恐其适为秦人笑矣。”(注:俞樾《诸子平议》,卷十二,《荀子一》,上海书店1988年5月版, 第236~237页。)可以说,俞樾对荀子“法后王”思想的理解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他将“后王”从文武、周公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又将其置入当朝开国之君的桎梏中,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种局限并不妨碍俞樾经世致用思想的进步性。在为葛士濬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续编》所作的序中,他说:“愚尝谓,孟子之书言法先王,荀子之书言法后王,二者不可偏废。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后王者,法其法。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法其意也。荀子‘欲观圣王之迹,则以其璨然者矣,后王是也’,此法其法也。马贵与著《文献通考》,其自序即引荀子语以发端。……皇朝经世之文,贺氏、饶氏相继编纂,而今又有葛氏之书并行于世,凡经国体野之规,治军理财之道,柔远能迩之策,化民成俗之方,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不可胜用,于学术、治术所裨匪浅,而我国家宏规茂矩,亦略具于斯,荀子所谓璨然者,不于此见乎!”(注:《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七,《皇朝经世文续集序》。)很明显,尽管俞樾认为法先王与法后王不可偏废,但在社会变革到来之际,还应强调法后王,这体现了俞樾的“尊荀”与其经世思想的一致。
(三)使《荀子》升格为经的主张。这在《取士议》一文中明确提出。《取士议》是俞樾关于改革科举考试的言论,他认为,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在第一场经义试中,“试《论语》义二道,《孟子》、《荀子》义各一道。”(注:《宾萌集》卷四,《议篇·取士议》。)其后,他陈述了将《荀子》升为经的理由。首先,尽管荀子主张“性恶”,与孟子的“性善论”明显不同,但荀子是“惧人之恃性而废学,故其书首篇即为论学,”这与孔子所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旨意一致,所以“荀子抑性而申学,正所以为教也。”(注:《宾萌集》卷四,《议篇·取士议》。)既然荀子的学说深得孔子思想的主旨,其书当然可以列为经。其次,《荀子》一书中的论说“皆近切要,又多引古礼,粹然儒者之言”,许多言论还与《孟子》不谋而合。司马迁的《史记》将孟荀合传,是十分有见地的。况且《孟子》本来也是列在诸子之中,后来才升格为经,“今若升《荀子》为经,与《孟子》配次《论语》之后,并立学官,乡、会试首场即用此一圣二贤之书出题取士,允为千古定论”。(注:《宾萌集》卷四,《议篇·取士议》。)
2
俞樾对荀子的推崇,继承了清代汉学的“尊荀”传统。#清代汉学吴派代表人物惠栋在研究《诗经》时,就十分重视荀子对《诗》的说解。而深受汉学学术影响、成书于十八世纪晚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断定“(荀)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儒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0页。)并为《荀子》一书中最受非议的《性恶篇》与《非十二子篇》作出辩解,这些无疑为清代学者重新研究和评估《荀子》开启了道路。其后,卢文弨、谢墉首先完成了对《荀子》的重新校勘,成《荀子笺释》。钱大昕为之作跋,给予荀子以很高的评价,并批驳了韩愈及宋儒对荀子的诬讥。他说:“盖自仲尼既殁,儒家以孟、荀为最醇,……宋儒所訾议者,惟《性恶》一篇。愚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宋儒言性,虽主孟氏,然必分义理与气质而二之,则已兼取孟、荀二义。至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然则荀子书讵可以小疵訾之哉!”(注: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考证上》,中华书局1988年9月第一版,第15页。)之后,郝懿行作《荀子补注》, 也认为荀子之学“醇乎又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畅,微为繁富,益令人入神而不能出,颇怪韩退之谓为大醇小疵。”(注: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考证上》,中华书局1988年9月第一版,第15页。 )而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汪中则从儒家经典传承的角度,极力论证荀子地位的重要性。他认为,除《尚书》以外,荀子是《毛诗》、《鲁诗》、《韩诗》、《左氏春秋》、《礼记》等经典的重要传人。“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是故“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经学。”(注: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考证下》,中华书局1988年9月第一版,第21—22页。)严可均也认为, “孔子之道在六经,自七十子后,绍明圣学、振扬儒风者,无逾孟子荀子,”并主张荀子当从祀孔子(注: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1),上海书店1991年10月,第1~3页。)。这样, 清代汉学家经过论证,不仅彻底否定了官方推崇的荀子为“大醇小疵”之论,而且从经学史角度反复强调荀子的特殊地位,并要求官方予以承认。很明显,将《荀子》升为经的要求已经呼之欲出了。俞樾则最终完成了这最为关键的一步,并明确主张在科举考试中用《荀子》出题。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的最重要的手段,俞樾的“一圣二贤”主张如能实现,那么,朱注“四书”长期垄断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面将会被打破,这无疑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俞樾的“尊荀”最显明的特点,是和“抑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见端倪,此处再做进一步说明。俞樾关于《孟子》的研究论著很多,他对孟子的“仁政”学说也表示赞同。但是,从整体上看,俞樾对孟子学说的辨正多于趋同,这主要表现在对孟子性善说来源的分析及对孟子学说与孔子思想之间继承关系的质疑。关于前者,俞樾认为,孟子“性善论”来源于子思所作《中庸》中的一句话,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但是,由于孟子不知道“率”字应训为“修”,而不训为“循”,故发为性善之说,违背了子思的意蕴,后来在《口之于味》一章中才有所修正。其实,“率”字之训为“修”与“循”,历来皆有明证,而俞樾之所以坚持训“修”,实际上仍与其汉学立场有关,即注重礼的约束与教化。对这一点,他毫不讳言,认为“性不一性,必率之而后为道,道不一道,必修之而后为教,率与修有功力存焉。后人训率为循,则近乎道家所谓道法自然者,而非吾儒所谓道矣。”(注:《经课续编》卷三,《率性之谓道说》。)在探讨孟子与孔子的学说关系方面,俞樾则是过多地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别。首先,他认为孔子之道兼容广大,而孟子则好辨,“孔子之道大,故无所不容也,孟子则不然,与杨墨辨,与告子辨,陈仲子一世高士,亦必与之辨,此孟子所以为孟子也”。(注:《春在党杂文六编补选》卷二,《罗陶金先生流录序》。)其次,俞樾认为,孟子学说与孔子学说侧重点不同,孟子似乎没有完全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邃。他说:“《论语》首《学而》,其教先自治,继之以为政,而后论所施。《孟子》则不然,所重在救时,知言与养气,姑弗遽及斯。”(注:《春在堂诗编》卷一,乙甲编,《读经偶得》。)如果我们联系到《荀子》首篇即为《劝学》,恰与《论语》首篇《学而》相映,那么俞樾诗文中的“尊荀抑孟”之意,昭然若揭。更有甚者,俞樾还在《偶书所见》一诗中,大量列举《孟子》所述《论语》之事与原本之间的差异,断言孟子根本就没读过《论语》,只是通过别种途径才获得孔子的思想,诚如其言:“吾疑孟子时,固当别所据,……至于《论语》书,孟子目未寓,孔孟所传授,不在此乎系。”(注:《春在堂诗编》卷十九,壬寅编,《偶书所见》。)被宋儒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竟然连集孔子思想大全的《论语》都没看过,那么,其所传的圣人之学也当然值得怀疑。其实,孔、孟学说之间的有些差异是由于时代造成的,而《孟子》叙述《论语》内容的失误,其原因也不一而足。俞樾之所以如此过分地强调孔孟之间的差别,其真正目的则是为了动摇宋学所宣扬的孔、孟、程朱道德,而重新建立起孔子、荀子的新道统,至少也要荀子和孟子的地位相同。俞樾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为了提高汉学的地位。
俞樾对《荀子》的研究和“尊荀”倾向,对其同时代及以后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较为明显的有两点:其一, 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于1891年撰成《荀子集解》一书,将俞樾的《荀子平议》全部采入,并大多表示赞同。这表明,俞樾对《荀子平议》所下功夫之深,评断之精,得到了同时代学者的认同。其二,宋恕、章太炎都曾师从俞樾,在学术上倾向汉学,而他俩都是晚清“尊荀”的鼓吹者。章太炎甚至宣称:“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注:《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后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217页。)这可以说是将俞樾“尊荀”隐藏的意义明确表述出来了。
综上所述,俞樾继承了清代汉学的“尊荀”传统,在进一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将《荀子》升格为经的主张。尽管这仍是在“崇尚经典”思维方式下进行的论述,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研究,但俞樾的工作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儒家学术发展的客观事实,即孟子、荀子都是孔子儒家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俞樾的汉学立场决定了其荀子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学术偏向。推崇荀子的同时贬抑孟子,则明显地揭示了这一点。
标签: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俞樾论文; 荀子论文; 荀子集解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毛传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