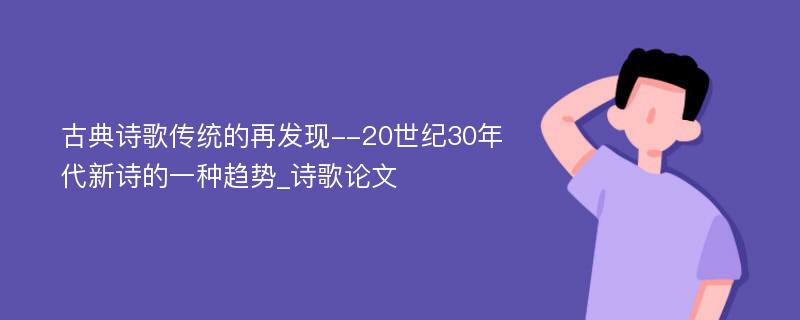
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1930年代新诗的一种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再发论文,倾向论文,古典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直以来,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被阐释为继承与被继承的线性延续关系,众多学者或致力于探究新诗与传统之间是承续还是断裂的关系,或钩沉史实、勾连诗例以梳理二者之间的承续脉络。事实上,二者的关系实质并非如此,而是一种“再认识”与“再发现”的关系,即言之,是新诗对传统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阐释而产生新的认识与发现,从而形成传统的新面貌与新秩序,形成新诗对传统的“再发现”。30年代诗坛上曾掀起一股以“晚唐诗热”为代表的回望古典诗传统的热潮,显示出诗人们集体性回望传统的积极性与自觉性,这是新诗对传统进行再发现的典型代表。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并非所有诗人对传统的姿态和与传统所发生的关系是一致的(对此,笔者另有专文叙论①),当戴望舒、施蛰存、曹葆华等曾经热衷于古典诗词尤其是晚唐诗词的诗人主要转向外国诗歌资源库寻找力量时,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吴兴华、朱英诞、南星等一批诗人却一直对传统情有独钟,这批诗人虽然西学修养亦颇为深厚,却未浸溺于外国诗歌的怀抱,亦非回归传统,而是携带30年代诗人特有的眼光和新诗建设的需求重新考察与阐释古典诗传统,重新发现了传统中一些可资用于新诗建设的优秀质素。这些质素的重新发现,改变了传统的既有秩序与面貌,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又启示了新诗建设,形成了对新诗自身的发现,从而在诗歌历史谱系中构筑出一道独特的诗歌“风景线”。
一 再发现: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实质
对于现代诗与传统的关系,艾略特曾在1917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②。艾略特明确认为传统是无法继承得到的,更无法追随、回归或墨守,只能在面对传统时“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③,在艾略特看来,传统不仅拥有“过去的过去性”,即“过去”之人对于“过去”传统的秩序、面貌的认识,也拥有“过去的现存性”,即现世之人对于过去传统的秩序、面貌的新认识。对此,艾略特更明确地指出:“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④艾略特敏锐地洞悉了现代诗与传统的关系本质。这篇讨论传统的文章于1934年在叶公超的嘱托下卞之琳将之译介并发表于《学文》创刊号上,成为现代诗歌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诗学论文,在30年代的中国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无可避免地影响了以卞之琳、废名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
根据艾略特的传统观,传统并非孤立地被悬置于已往历史空间中的固定实体,而是动态地活动于历史时序之中的具体存在物。传统并非属于已经造就的过去,而永远处于被正在造就与发明的状态中,后世之人就是制造者与发明者。当传统置于新的历史时代,其原本的传统秩序便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由于新增了上代人的作品而使传统秩序增加了新成分,更由于后人对传统中的已有作品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与阐释,获得了新的认识与发现,新一历史时代所想像与认识的传统与其上一代的传统显然不同,其既有秩序与面貌会在“新与旧的适应”中发生调整与改变。可见,新诗与传统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化的连续性,所谓继承与被继承关系,或许只是一种理论预设和心理幻觉。传统是一个动态系统,是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诠释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未完成式概念,当有着一定“时间间距”的后人对它追寻时都携带着自己文化时空的浓厚色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诠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发现。正如艾略特重新审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并非要按照玄学派的玄学风格模式进行创作,而是对之进行重新阐释时重新发现了英国玄学派诗人强调“机智”和注重“感受性”的诗歌特点,从而形成对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再发现”。因此,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决不是静止的,并非单线的继承关系,而是多元互动的关系;传统是动态存在的,一代一代人只能对之作出阐释,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中不断丰富与发展,不断形成新的面貌,发生不同的现实作用。或许正基于以上认识,沈启无曾于40年代明确提倡:“我们在一个现代文明空气之下,对于中国过去旧文学应有一个再认识的态度”⑤。事实上,早在30年代的一批诗人那里,诗人们便已实践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认识”。
二 “晚唐诗热”:再发现传统的代表
1930年代的诗坛上,诗人们一反初期新诗与传统决裂的姿态而纷纷对晚唐诗词情有独钟,掀起一股“晚唐诗热”,不仅诗人们都纷纷醉心于晚唐诗词,当时的各种刊物、论著、文章均流露出诗人们对晚唐诗词的特别感情,不少诗人或批评家在大学课堂上重点推介或讲解晚唐诗词,废名等诗人还在当时便已敏锐地对“晚唐诗热”作出了理论阐释,这种“热”度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晚唐诗热”这一诗歌现象的发生,决不仅仅意味着诗人们只对晚唐诗词情有独钟,他们在回望传统时发现晚唐诗词与自己“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纷纷亲近晚唐诗词,但这只是诗人们所回望的古典诗传统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他们的目光决不仅仅囿限于晚唐诗词,而是同时表现出对其他时代之诗词的钟爱。如废名曾自陈:“中国诗词,我喜爱甚多,不可遍举。”⑥他所回望的传统“乃指着中国文学史上整个的诗的文学而说”⑦。何其芳则常醉心于“富于情调的唐人的绝句”⑧,林庚、卞之琳、朱英诞等诗人亦都并不将目光局限于晚唐诗词。因此,“晚唐诗热”只是诗人们回望古典诗传统的一个外在视点和显在标志,是30年代诗人们集体性回望古典诗传统的集中体现与典型代表。而在这股“晚唐诗热”现象中,诗人们对待传统的姿态和与传统所发生的关系实质并不一致,而是呈现出根本性的分化状貌:戴望舒、施蛰存、曹葆华等一批诗人亦曾钟情于古典诗传统,尤其是为“晚唐诗词家及其直接后继人的艺术”所迷醉⑨,并承认晚唐诗作“使我改变了诗格”⑩,这种对传统诗词的亲近其实是对古典诗传统的拥抱与回归,当他们发觉自己为传统诗词所俘虏的危险后便主要转向外国诗歌资源寻求借鉴,并未重新阐释和再认识传统,并未形成对传统的再发现;而废名、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朱英诞、吴兴华、南星等一批诗人虽然大都出身外文系,亦熟谙外国诗歌资源,却保持了回望传统的热情,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重新回到以晚唐诗词为代表的古典诗传统之怀抱,回归传统,而是以30年代诗人特有的眼光与当时新诗建设的需要重新认识与阐释传统,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认识”与“再发现”。
所谓“再认识”,是指诗人们携带其所属的特定历史时代的眼光与审美需求,或是携带他们所遭遇的诗歌问题,或是在已有诗歌经验的基础上,回望古典诗传统时重新阐释、理解传统,如废名明确标举“重新考察以往的诗文学”(11)、林庚为新诗未来的发展而从传统“问路”、何其芳迷醉于古典诗词中寻找“重新燃烧的字”、“重启引起新的联想的典故”(12)、卞之琳在中西对照的视野中重新阐释传统等姿态,便属于对古典诗传统的“再认识”。“再发现”是在“再认识”基础上进一步的升华,即指诗人们以“再认识”的姿态对古典诗传统进行重新阐释时,重新发现传统中的一些优秀质素,这些“重新发现”的质素形成了对传统新的认识和发现,重新调整了传统的秩序和面貌,从而形成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同时又启示了新诗自身的建构,确立了新诗自身特质,并启示了新诗的发展路向,由此新诗与古典诗传统之间形成多元互动互进的关系。废名、金克木、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朱英诞、吴兴华等诗人都以30年代诗人的眼光对古典诗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和再认识,重新发现了传统,也发现了新诗自身,从而有益地推进了新诗的发展。张洁宇曾将戴望舒与废名等的区别定位于“无意识的因袭”与“有意识的继承”(13)上,其实其区别并非在此。戴望舒或许确有“无意识的因袭”,但这种无意识的因袭或继承其实是每个置身于本土文化历史序列中的人所无法逃避的,因为传统血脉的潜流是任何外在地宣称“断裂”的口号所无法阻断与遮蔽的,以废名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亦不例外。但废名等诗人对传统更有其独特姿态,他们是以“再认识”的态度和30年代诗人的眼光重新考察与阐释传统,重新发现古典诗传统中可资建设新诗的优秀质素,对传统形成新的认识,形成了“再发现”,并非“有意识的继承”。正如臧棣所指出的:“对传统的‘承继’和对传统的‘重新发现’是不同的。前者尽管在新诗史上呼吁不断,却是一个伪问题。(……)从现代性角度看,人们所设想的旧诗和新诗之间的继承关系是不存在的。(……)旧诗对新诗的影响,以及新诗借镜于旧诗,其间所体现出的文学关联不是一种继承关系,而是一种重新解释的关系。”(14)王家新也曾指出:“新诗的曲折历史已表明,它与传统并不是一种‘继承’关系,更不是一种‘回归’关系,而应是一种修正和改写的关系,一种互文与对话的关系;在富有创造力的诗人那里,这可能还会是一种‘相互发明’的关系!”(15)他们都敏锐地洞悉了新诗与“旧诗”或古典诗传统的关系。30年代以废名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与古典诗传统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继承关系,更不是回归,而是重新解释、修正、改写与发明传统,使古典诗传统形成一种新的面貌,此面貌是30年代诗人眼中对传统的独特认识,是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需要注意的是每个人重新审视传统时的眼光都带有个人的主体性、个人性和独创性,彼此各异,因此每位诗人在重新审视传统时所重新发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这或许正是艾略特那篇讨论传统的文章却以“传统”与“个人才能”相提并论的根本原因所在。显然,艾略特注意到后世诗人的个人才能与传统的关系本质,诗人们在重新考察传统对传统进行新的阐释与理解时,他们依靠“个人”的才能、见识、需求、志趣所从传统中重新发现的“风景”必然各自相异,各成其独特的“风景”,艾略特犀利地透视了诗人的个人才能与传统的关系本质。每位诗人都依靠自己的主体性与个人才能,依靠自己诗歌探索中偏离传统的教训,纠偏自己与传统的关系,纠偏新诗建设的方案,形成每个人建设诗歌的独特路径。以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们由于处于同一时代语境,拥有相似的命运遭际、处世心态、人生志趣与审美志趣,因而显示了较为接近的诗歌追求与创作取向,当他们回望传统时从传统中发现了属于他们眼中的独特“风景”。
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古典气息”或“古典倾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前者是诗人们对传统中一些优秀资源的重新发现和启用,是诗人们注意到新诗的偏离倾向后重新启用古典诗传统的优秀质素对新诗发展方向的纠偏与归位,形成了古典诗传统的新面貌和新秩序,又发现了新诗自身的面貌和秩序;后者是新诗在风格特征层面的表现特点。二者互不相碍,可能同时并存于某一诗人身上,也可能毫无关系,二者之相通处在于它们都建立在拥有深厚的古典诗学修养和重新回望古典诗传统的基础上,深厚的古典诗学修养是形成古典气息的主要来源,但却只是形成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的基础之一,对古典诗传统形成再发现的作品不一定泛溢古典气息,古典气息浓郁的作品亦不一定形成对传统的再发现,所再发现的质素是诗人们以自己的眼光新发现的,不是模仿或因袭,不是株守,不是继承,而是重新发现了存在于传统本身却未被之前的诗人们发现或重视的一些优秀质素。这些质素在30年代的被发现或重新启用,使“传统”在此后的言说中形成新的秩序,从而改变传统的原有面貌,调整传统的既有秩序,从而形成对整个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
此外,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中西融合”亦是立足于不同视角基点上的两种不同的诗歌倾向。当时的诗人们不可能完全不受外来资源的影响,因此均可被纳入“中西融合”之范畴。新诗自诞生之日起,由于它与传统旧诗决裂,只能向外国诗歌资源寻求援助,因而就此走向“中西融合”的路子。在再认识传统这一倾向中,30年代以废名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也不能排除于“中西融合”范畴之外。他们古典诗学修养非常扎实,但同时,他们的西学修养亦颇为深厚,废名、金克木、林庚、何其芳、卞之琳、吴兴华、朱英诞、南星等诗人一方面遍览外国诗歌“风景”,一方面又对传统重新阐释和再认识,再发现传统中可以重新启用的优秀质素。如废名早期曾深受莎士比亚、哈代、塞万提斯、波德莱尔以及文学史家乔治·勃兰兑斯、福楼拜、契诃夫等人的影响。何其芳、卞之琳、吴兴华、朱英诞等都曾大量翻译外国诗歌作品与诗论,显然深受外国诗歌影响,均属于“中西融合”范畴。但“中西融合”并不能囊括传统的再发现,而只是形成30年代现代眼光的一个因素,是再发现传统的基点之一。30年代的诗人们,无论是受西方影响多一些,还是受传统影响多一些,或是中西融合程度如何,他们都是站在西方修养、传统素养和中西融合的三个基点之上回望传统,那么,他们以30年代诗人的眼光重新阐释传统时重新发现了什么?30年代的诗歌发展遭遇了自身的问题,必然形成这一代诗人特定的解决问题与未来发展的要求,必然形成特定的眼光,当他们以这种眼光重新考察传统,必然发现不同的“风景”。
三 再发现的“风景”
30年代的诗人们在现代诗歌史链条的“1930年代”这一环上所遭遇的诗歌问题是“怎样建设新诗”,这一问题既涵盖了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存在却尚未解决的问题,如“什么是新诗”的问题,又囊括了新诗“写什么”、如何现代化、中国化以及如何成为好诗等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是缠绕一体无法具体指实的一个问题,即“怎样建设新诗”的问题)。在以“晚唐诗热”为典型标志与集中体现的回望古典诗传统的热潮中,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一批诗人所再发现的“风景”正是“怎样建设新诗”的优秀质素。他们带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及已有的创作经验在重新认识、阐释古典诗传统时重新发现了什么?他们对传统形成了怎样的“再发现”?笔者认为,他们从传统中再发现的“风景”如下:
首先是“诗”的内容。30年代的诗人们在回答“怎样建设新诗”时所遭逢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新诗”,这一问题既关涉新诗存在的合法性,也关涉新诗之为诗的本体问题,是自新诗以降便存在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30年代诗人中依然对之进行反复思考并试图作出回答的代表诗人是废名。他在重新考察古典诗传统并对照五四以来的新诗时发现旧诗之成其为诗所凭借的是“诗的文字”,旧诗的“内容”则并不是“诗”的,而是“散文”的;然而旧诗中也不乏特例,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等诗句正有“诗的内容”;李商隐的“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也不是散文的意义而是诗的,废名认为这些诗含有“诗的内容”,是旧诗中“例外的诗”。与此对比,废名认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所以成其为诗,乃在于“文字”的缘故。在废名看来,“旧诗向来有两个趋势”(16),即“元白”派和“温李”派,二者都是在“诗的文字”下变戏法,都属于旧诗,但“温李”派却在“诗的文字”下拥有“诗的内容”,含有当时新诗发展的趋势,因为“李商隐的诗应是‘曲子缚不住者’,因为他真有‘诗的内容’。温庭筠的词简直走到自由路上去了,在那些词里表现的东西,确乎是以前的诗所装不下的”,由此废名作出推想:“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或者正有我们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17)。显然,废名不仅认为以“温李”为代表的诗词有“诗的内容”,还将这一脉拥有“诗的内容”的诗词视为新诗发展的根据,无疑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新认识和再发现。基于此,废名还提出了彰显其核心诗观的结论:“新诗要别于旧诗而能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18)可见,废名在对传统的回望中重新发现了“诗的内容”对于旧诗之为诗的重要性,也发现了它对于新诗之为诗的重要性。废名话语系统中的“诗的内容”其实是指“诗”的内容,是与“散文的内容”相对的,是对内容的“诗”性强调,即内容要是“诗”的,显示了废名对内容的“诗”性特征的特别强调和规定。所谓“诗”的内容,即强调内容必须具有不写亦已成功、天然完整、“当下完全”(19)等“诗”性特质,其所关涉的是诗思、诗兴酝酿阶段的思维方式问题,与穆木天主张的“诗的思维术”(20)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废名自己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重“诗的内容”,他极力强调其诗成速度之快,诗意之完全(有学者将废名“诗的内容”等同于“诗意”,事实上,废名话语系统中的“诗的内容”包括情绪、情感、感觉、诗意等内容,这些内容都必须是“诗”的,因此,“诗意”只是“诗的内容”之一小部分,而且必须是“当下完全”、“不写亦已是诗”、“天然完整”的而非情生文文生情的诗意才属于“诗的内容”),极其注重瞬时性和当下完成性,他认为自己的《妆台》、《小园》、《海》、《掐花》、《理发店》、《街头》等诗均完成得极快,都是“完全的”、“整个的”(21),正印证了废名对其“诗的内容”这一核心诗观的实践。拥有特定话语内涵与规定性要求的“诗的内容”不仅是废名在重新考察传统时所再发现的优秀质素,亦折射与启示了其自身的诗歌建设,正是废名对“什么是新诗”这一问题的回答,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较之初期新诗过于注重诗体解放和新月诗派过于注重形式而均忽略诗的内容建设的倾向显然有了改进,对当时的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诗的“感觉”。30年代的新诗建设无可避免地遭遇“写什么”的问题,废名、林庚、卞之琳、何其芳、朱英诞、南星等一批诗人的回答是注重诗的“感觉”,而非“现实”、“道理”、“意义”或“情感”。当他们回望传统时,他们重新发现了古典诗词中诗的“感觉”的重要性。废名在重新考察传统时发现古今诗人对“月亮”的书写各有千秋:“古今人头上都是一个月亮,古今人对于月亮的观感却并不是一样的观感,‘永夜月同孤’正是杜甫,‘明月松间照’正是王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正是李白。这些诗我们读来都很好,但李商隐的‘嫦娥无粉黛’又何尝不好呢?就说不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那只是他对于月亮所引起的感觉与以前不同。”(22)同是一个月亮,不同诗人的感觉不同,必然导致诗的“感觉”不同;不同时代之人的观感相异,不同时代的诗也必各异其趣。诗的“感觉”不同形成了不同风格之诗与不同时代之诗。由此废名发现了诗的“感觉”对于形成不同风格之诗和不同时代之诗的重要性。对此,他还援引《锦瑟》一诗进行阐说:“我们想推求这首诗的意思,那是没有什么趣味的。我只是感觉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两句写得美”(23),此诗曾被胡适由于读不懂而讥为“妖孽诗”(24),显然,废名与胡适截然不同,他并不去推求此诗所表达的意思或具有的意义,所欣赏的“只是感觉美”。由此,废名重新发现了古典诗传统中诗的“感觉”的重要性。废名自己的诗歌创作也一直将诗的“感觉”作为其新诗建设的“主打工程”,极其注重表达“感觉”,而不注重说理或写实。在《妆台》一诗中,废名并不描摹妆台的形状、外观或性能功用,或因之而发生的故事、情感,全诗“只注重一个‘美’字”,“只注意到照镜子应该有一个‘美’字”(25)。诗中所传达的是一种“美”的感觉。《理发店》、《灯》、《十二月十九夜》、《掐花》等诗都无不如此,传达了身处30年代那个特定时代氛围中人的虚无感、无奈感、幻灭感、荒凉感等“感觉”。林庚亦极其注重诗的“感觉”,他认为感觉、情绪和事物这文学最基本的三件东西中,情绪和事物是古今一致的,只有感觉才是新的,是关系不同时代产生不同诗的关键要素。他还在唐诗研究中发现诗之为诗的关键质素在于“诗的感觉”,从而形成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质素的重新发现。林庚对感觉的重视,李长之概括为“感觉论”,并指出,于林庚而言,“感觉是诗的一切;诗人与常人的不同、诗人之间的不同、诗的进化与好坏均在感觉的敏钝”(26)。林庚自己的诗歌实践亦将诗的感觉作为核心内容,《破晓》、《夜》、《朦胧》等诗都是呈现“感觉”之美,而《风沙之日》、《二十世纪的悲愤》、《信口之歌》、《在空山中》、《沉寞》、《除夕》、《当你》、《北风》、《有一首歌》等诗呈现的内容虽然与时代现实密切相关,却并非追求“意义”,而是传达当时时代背景下被压抑的挹郁、烦闷之感。林庚对诗的感觉的注重还影响了同时代的诗人:“林庚之看重感觉,从而看清诗人的贡献和天职,是的的确确我们大家的精神。”(27)卞之琳则在翻译外国诗歌资源尤其是艾略特的诗学论文与诗歌作品时,深受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影响。而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其实是一种使“感情”化炼成“感觉”的方式和手段,目的在于表现与传达“感觉”而非“感情”。卞之琳的诗实践了“非个人化”的诗歌策略,用以传达诗的“感觉”。当他以此诗歌经验回望古典诗传统,发现“感觉”正是他个人话语系统中“戏剧性处境”与“意境”之间具有相类性的联接点,以“感觉”重新阐释了“意境”、“境界”等古典诗学中的重要概念,其实是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质素的重新发现,形成了对传统的再发现,亦是他自身新诗建设经验的折射。卞之琳的《圆宝盒》“到底不过是直觉地展出具体而流动的美感”,只能“意会”,是“没有一个死板的谜底搁在一边的”(28),可见卞之琳对“诗的感觉”的重视。他的《一个闲人》、《和尚》、《酸梅汤》等诗都不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关注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而是通过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呈现当时时代氛围下人的迷惘、无奈、幻灭、空虚和虚无等内心感觉,袁可嘉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感觉诗人”(29),正切中了其诗歌内容的主核。“感觉”是废名、林庚、卞之琳、何其芳、朱英诞、南星等诗人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重新发现的重要诗歌质素,亦是他们这一代诗歌的主要内容,由此他们将感觉作为诗之为诗的关键质素,并认为“诗是感觉”。事实上,“感觉”只是30年代以废名为代表的这批诗人诗写的主要内容,以往历史时期甚至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并不一定以“感觉”作为诗的主要内容,他们以一个时代诗人所选择的诗歌内容作为诗之为诗的核心质素,未免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但是,废名等人正是在这种偏颇中形成其注重感觉书写的诗歌特色,亦形成其对传统独特的再发现。
“想像”是30年代以废名为代表的诗人们在反思五四以来新诗一直占据主流位置并且同一时代仍在盛行的写实倾向时采用的诗歌表现方式。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诗人都重新发现了想像之于诗的重要性,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尽情驰骋想像以自由展开诗的感觉。废名在重新考察传统时发现,旧诗都是情生文文生情模式的反复自我繁殖,想像与幻想缺席,而盛唐之后的晚唐“温李”派诗词之所以能够在诗歌高峰之后别开一境,乃在于他们的诗超乎一般旧诗的表现,突破了旧诗情生文文生情模式的囿限:“温庭筠的词不能说是情生文文生情的,他是整个的想像”。“在谈温词的时候,这一点总要请大家注意,即是作者是幻想,他是画他的幻想,并不是抒情,世上没有那样的美人,他也不是描写他理想中的美人,只好比是一座雕刻的生命罢了……他的美人芳草都是他自己的幻觉”(30)。在废名看来,温庭筠的词全凭想像来展开诗的感觉,“温词无论一句里的一个字,一篇里的一两句,都不是上下文相生的,都是一个幻想,上天下地,东跳西跳,而他却写得文从字顺,最合绳墨不过,居花间之首,向来并不懂得他的人也说:‘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了”(31),废名最肯定温词之处便在于温词凭借想像、幻想一方面可以自由驰骋,一方面却又文从字顺、最合绳墨不过,他认为这是温庭筠的词居花间之首的根本原因。废名还拈出温词,与以前的诗体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发觉温词所表现的内容不是他以前的诗体所装得下的,长短句这种诗体正适合温词里要表现的内容,更适合驰骋想像。由此,废名得出“我们今日的白话新诗恐怕很有根据,在今日的白话新诗的稿纸上,将真是无有不可以写进来的东西了”(32),正是由于想像所拓展的广阔空间,给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根据”,启示新诗可以自由地驰骋想像,在想像的驱遣下,“无有不可以写进来”,此正符合废名关于“诗的内容”的标准。废名在自己的诗歌实践中,常恣意地驰骋想像。他的许多诗都以“梦”的方式展开想像,或直接以“梦”为标题,或以“梦中我……”、“梦里……”为起兴,如“梦中我采得一枝好花”(《赠》)、“梦中我梦见水”(《梦中》)、“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妆台》)等都以“梦”展开想像,传达诗的感觉。何其芳亦在对古典诗词的“醉心”之中重新发现了“想像”的魅力。他极其欣赏李商隐的《懊恼曲》最后四句(楚水悠悠流如马,恨紫愁红满平野。野土千年怨不平,至今烧作鸳鸯瓦)中的“镜花水月”:“我喜欢……那种镜花水月”(33)。而“镜花水月”源出佛教术语,后人多解作镜中花、水中月,常比喻虚幻的景象、幻觉,不可捉摸、无法言尽与指实,即“无一语及于事实,而言外无穷”(刘熙载:《诗概》)。可见“镜花水月”主要指想像、幻想中的虚幻事物、景象,因此,何其芳对古典诗词中“镜花水月”的再发现,其实是他对想像、幻想的再发现。何其芳后来还曾在谈及《李凭箜篌引》时指出此诗“想像是那样丰富,那样奇特”、“有很多奇特的想像”、“那些想像忽然从这里跳到那里,读者不容易追踪”(34),也显示了他对古典诗词中丰富的想像力的关注与欣赏。何其芳自己的诗歌创作亦追求“镜花水月”,注重想像。“梦”是其最主要的想像方式。何其芳初登诗坛就曾宣称“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35),终日沉浸于“画梦”之中。《预言》中约有三分之二的诗是在“画梦”。《爱情》一诗乃诗人于梦中所得,诗中布满近乎痴人说梦的怪诞联想,《给我梦中的人》、《梦歌》、《梦后》等诗都显示了“梦”无处不在地支配着何其芳的诗歌思维与想像方式。何其芳完全将“梦”作为现实的另一种存在,他对美、爱情、理想的寄托全附着于“梦”,在其笔下,梦便是现实,现实便是梦,梦比现实更真实,“梦”成为其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想像方式。因此,成天沉浸于“梦中道路”上“画梦”的何其芳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重新发现了“梦”的想像方式,发现了“那种镜花水月”的美,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形成了自身的诗歌建设特质。废名、何其芳等一批诗人虽然发现了“想像”对于古典诗传统和新诗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诗人个人视野的局限,他们并未意识到“想像”作为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的重要性,不能不是30年代诗人的失误。事实上,想像是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之一,它在写实倾向占据主流诗歌位置的时代被重新发现,对于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诗语魅力是30年代诗人们反拨白话化、散文化、口语化诗歌倾向时回望传统、从传统中重新发现的。何其芳、卞之琳、林庚、吴兴华等都自觉追求诗歌语言的诗化。何其芳自幼便坠入古典诗的“文字魔障”之中无可自拔,喜欢“那种锤炼,那种彩色的配合”(36)。何其芳所欣赏的“锤炼”即指诗歌语言的“精练”,“彩色的配合”则落脚于文字的色彩组配,主要关涉诗歌语言的“形象性”。因此,何其芳最迷醉古典诗词之处主要便落脚于诗歌语言的精练与形象性,他不在乎诗的含义与意思、意义,而是文字锤炼与色彩调配的精练、形象魅力,这正是他对传统的独特发现,他以自己的爱好和眼光择取了传统中他个人认为最优秀的质素,折射出其内在的诗歌艺术追求。何其芳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极其注意像古人那样精心锤炼诗歌语言,他把写诗看作“小小的苦工”,“有一个时候我成天苦吟”(37)。何其芳早期的诗歌语言相当“雕琢”,其《刻意集》取名“刻意”,便显示出他刻意雕琢语言的用心。他的诗大量吸收文言辞藻,自觉寻找“重新燃烧的字”、“重启引起新的联想的典故”(38),以达到“精练”效果。同时,何其芳非常注重“彩色的配合”,他“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认为诗“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39),他的诗“要的是颜色、凸凹、深致、隽美”(40),文字的彩色、图案成为何其芳诗歌的重要成分。何其芳凭借他对色彩的敏感和巧妙的配合而“画”出美丽的图案,形成精美、形象的诗歌语言。卞之琳则重新发现了“含蓄”的诗语魅力。他在翻译外国诗歌资料时对照中国古典诗词,发现了西方象征主义的“暗示”与我国旧诗词中的“含蓄”相通:“亲切与暗示,还不是旧诗词的长处吗?”(41)他以“暗示”重新照亮了传统中的“含蓄”质素。卞之琳自己的诗也注重以暗示手法达成含蓄效用,他曾夫子自道:“诗要精炼,我自己着重含蓄,写起诗来,就和西方有一路诗的着重暗示性,也自然容易合拍”(42)。沈从文曾指出卞之琳的诗“写得深一点,用字有时又过于简单,也就晦一点”(43)。沈从文显然掐中了卞之琳的要害:“深”,但又用字简单,这正是卞之琳诗的“含蓄”特点。卞之琳的诗虽然用字简单,但非常“深”,不可一看即懂,《圆宝盒》、《断章》、《鱼化石》、《无题》等在诗界引起反复争议和阐释的诗都正是由于以“暗示”手法形成含蓄效用,抵达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的境界。此外,林庚亦曾明确提出新诗“建设的核心便是诗歌语言的重建”(44),主张建立诗歌语言诗化的阵地。吴兴华则在其诗歌语言中适当地羼入一些古汉语的单音字、古字,与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交错,并且巧妙化用古典诗句。这些诗人对诗歌语言的诗化追求,使他们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重新发现了古典诗词的诗语魅力,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发现了新诗诗歌语言建设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韵律与节奏属于30年代诗人在诗形探索中从古典诗传统中重新发现的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新诗诗形的探索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新月诗派的格律诗实验之后,自由诗更成为主流体式。但无可否认的是,诗形的探索一直在延续,林庚、朱英诞、吴兴华等诗人对此都自觉地进行了不少探索与实验。韵律与节奏便是他们在诗形探索中从传统中重新发现的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林庚显然是典型代表,曾在自由诗王国声名鹊起的他由于意识到自由诗的局限与弊病而转向新诗形式的探索。为规避自由诗的发展弊端,林庚先提出“自然诗”概念,即一种外在的“自然”与内在的“自由”相统一的诗。他在《诗的韵律》、《什么是自然诗》、《关于四行诗》等文章中通过分析吴歌与古代诗句而发现“韵”能使日常生活中看似毫无逻辑之事成为自然的习惯,重新发现了古典诗中韵律的“魔力”,即韵律具有“自然性”,因而主张以韵律保障“自然”,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中韵律之自然性的再发现。同时他自己也践行了“自然诗”的理想,《春野》被林庚立为自己的第一首自然诗;后来他又创作了“节奏自由诗”和《北平自由诗》,这些诗由于兼有自由诗的自由和定行诗的格律,因而基本符合林庚自然诗的理想。但这类诗在林庚30年代的诗歌实验中却太少(而且这些诗并非每一首都真正完全自然)。更多的创作实践中,林庚由于白手起家无型可依,只能将参照目光投向古典诗词。虽然他本是想从古典诗词中探寻自然诗之“自然”,但由于他所看到的均为古典诗词,都是古代五言或七言的韵律诗,因此,林庚本是探寻解决自然诗如何自然的问题,侧重点本是“韵”,却无形地感受到古代诗歌中格式对于诗之自然所起的“便宜”作用,因而不顾新诗所采用的语言载体的不同,情不自禁地栽进了格律形式的“不祥的魅力”(45)之中。由此,林庚过分按照古典诗词的格式,实验了四行诗、十一字诗、十字诗、八字诗、十字诗、十五字诗、十八字诗、七字诗、十二字诗等各种定行齐言的诗体。这些诗体虽然采纳白话的语言载体,虽没有平仄、对偶这些规定,但依然有字数、句数、押韵的要求。为了遵照这些诗体在字数、句数和韵律上的要求,林庚常不惜“削足适履”,刻意为之,实际上都无意识地采用了新格律诗的形式,完全与其“自然”的理想背道而驰,因而最终导致了自然诗理想的破产,而陷入新格律体诗的形式实验中。虽然林庚的自然诗理想破灭了,但在大量的新格律体诗的实验过程中,林庚注意到诗歌的“节奏”对于诗的重要性,正如他后来在访谈中所言:“诗歌是有节奏感的,有了几言诗那种节奏,它就可以跳跃,诗歌恢复了它的自由的跳跃性,也就恢复了它的艺术魅力了。可惜很多人在这里都搞不通”(46)。林庚认为节奏是恢复诗歌自由跳跃性和艺术魅力的关键因素。林庚对节奏的发现是在其实验各种新格律体诗与重新考察古典诗传统的交叉进行中展开的,一方面林庚从实践中考察现代汉语的节奏,一方面又从古典诗传统中寻找节奏经验和规律,他携带其创作实践回望古典诗传统时重新发现了古典诗中节奏的魅力,这正是诗之为诗的灵魂质素。虽然林庚并非最先注重“节奏”的诗人,但却是对之第一次进行如此大批量实验与探索并以之形成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的第一人。林庚有关节奏的诗歌经验或许由于其所采用的新格律诗体式而难免偏颇,但他在自由诗为主导的时代对节奏之于诗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却不无意义。因此,虽然林庚的自然诗理想破灭,新格律诗实验失败,并擅自私设了诸多不具通适性的诗学概念,最终亦并未能为新诗找到一双“合自己脚的鞋子”,但他在大量实践、摸索中重新发现了“韵律”与“节奏”这两个古今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无疑是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对新诗的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30年代以废名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们从古典诗传统中所重新发现的这些建设新诗的优秀质素,都是他们回望古典诗传统时收获的“风景”,这便是30年代以废名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们眼中的“传统”,是他们对古今相通的“诗”传统的再发现,组构出他们眼中古典诗传统的面貌与秩序,形成了他们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同时,这些质素正是新诗建设所需的基本质素,反映了新诗建设在思维方式、内容、表现方式、诗歌语言、传达方式、形式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因而,他们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其实又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是对新诗“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建设方案的发现。
总之,身处新诗发展新的十字路口,30年代以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吴兴华、朱英诞、南星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们在以“晚唐诗热”为代表的回望古典诗传统的热潮中,重新阐释和再认识传统,重新发现了传统中可资用于新诗建设的质素,发现了在他们眼中古今相通的“诗”传统,对传统形成了“再发现”,也发现了新诗自身,发现了一条被初期新诗发展所否定和忽略的新诗建设的“僻路”。在这条“僻路”上,废名等诗人所发现的“风景”并非传统的全部,甚至并非传统的真实面貌,但这正是他们眼中所看到的“传统”。他们所发现的这些“风景”和这种“再发现”传统的诗学倾向对于建设新诗起到了重要作用,构筑了30年代诗歌的一道独特“风景”,并对40年代及后来以至当下的诗歌建设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与诗学意义。
此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倾向研究’”(课题编号:12YJC751057)和“广西师范学院博士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详见陋文:《“晚唐诗热”现象的诗学启示透析》(《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晚唐诗热”之意义探析》(《唳天学术》第7辑,学苑出版社2011年8月)。
②③④艾略特:《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卞之琳译,《学文》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
⑤沈启无:《大学国文·序》,《大学国文(上)》,新民印书馆1942年版。
⑥废名:《随笔》,《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37年5月1日。
⑦(18)(22)废名:《新诗问答》,《人间世》第15期,1934年11月5日。
⑧何其芳:《写诗的经过》,《关于写诗和读诗》第117页,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诗刊》1980年第5期。
⑩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写于1933年5月),《灯下集》第7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
(11)(17)(23)(30)(31)(32)冯文炳:《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谈新诗》,第39页,第28页,第36页,第30页,第34页,第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
(12)何其芳:《论梦中道路》,《大公报·文艺》第182期,“诗歌特刊”,1936年7月19日。
(13)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第1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1997年武夷山现代汉诗研讨会论文汇编》,第92页,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5)王家新:《一份现代性的美丽》,《诗探索》2000年第1辑。
(16)冯文炳:《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曾载北京《文学集刊》第1集,1943年9月),《谈新诗》第26页。
(19)冯文炳:《尝试集》,《谈新诗》第6页。
(20)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16日。
(21)此前所引参见冯文炳:《〈妆台〉及其他》,《谈新诗》第217—221页。
(24)出自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写于1922年3月3日,原载1923年2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此处依《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第11页(1935年10月15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25)冯文炳:《〈妆台〉及其他》,《谈新诗》第219页。
(26)李长之:《林庚的诗集〈夜〉》,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10月25日。
(27)李长之:《春野与窗》(写于1935年4月28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第9期,1935年5月1日。
(28)卞之琳:《关于〈鱼目集〉》,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42期,“星期特刊”,1936年5月10日。
(29)袁可嘉:《诗与主题》,《论新诗现代化》第72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33)(36)(38)(39)何其芳:《论梦中道路》,《大公报·文艺》第182期,“诗歌特刊”,1936年7月19日。
(34)何其芳:《诗歌欣赏》,《何其芳全集》第4卷,第40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5)何其芳:《燕泥集·柏林》,《汉园集》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7)何其芳:《〈刻意集〉序》,《文丛》第1卷第4期,1937年6月15日。
(40)刘西渭:《画廊集——李广田先生作》,《大公报·文艺》第190期,“书评特刊”,1936年8月2日。
(41)卞之琳:《〈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译者识》,《新月》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
(42)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雕虫纪历(1930-1958)》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3)沈从文:《关于“看不懂”》(二),《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年7月4日。
(44)林庚、龙清涛:《林庚先生访谈录》,《诗探索》1995年第1辑。
(45)林庚:《漫话诗选课》,《宇宙风》第130期,1943年3月。
(46)张鸣、林庚:《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