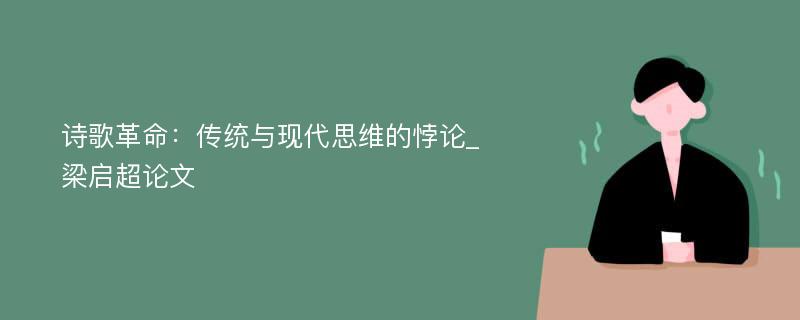
“诗界革命”: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思维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11)05-0057-04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五四”时期能够成功推进新文学运动,与近代文学持续不懈的探索实践——特别是诗、文、小说、戏曲诸革命——密不可分。而新文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前提——对于旧文学的批判和革新,又始终纠葛于近代改良主义文学既想维护旧有秩序,又要革命传统的矛盾姿态。从思维方式来看,近代文学革命者多用正统封建文化思想来阐释新文化的变革道理,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托古改制”的沿续。近代文学八十年的发展并不均衡,前期的启蒙文学和后期的革命文学发展都不够充分,中间的改良主义文学则占了绝对优势。虽然认识到旧文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影响现代文明的传播与接受,但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局限以及两种思维模式的难以调和,近代文学革命只是在原来的框架内进行有限改良。表面上反对旧传统而骨子里是皈依旧传统的矛盾姿态甚至代表了整个近代文学革命思维的主流,这是其陷入文化革新困境的内在原因。
今天,“诗界革命”无疑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可以清晰观照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悖论对近代文学革命所制造的影响。从“新学诗”到“新派诗”再到“新体诗”的探索阶段中,无论是理论家梁启超从“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构想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让步,还是创作旗帜黄遵宪由于局限在传统诗歌范围,前后各有侧重的诗歌创作过程——从堆积新名词到追寻新思想,再到留恋旧风格,都清晰地折射出这种思维悖论的内在精神线索。
一、“诗界革命”的复杂探索和调整
“近代中国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1](页288)近代“诗界革命”为“五四”新诗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探索和创作的基础,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它不仅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使作家关注和反映新的时代思想,还使得语言不再受旧体格律束缚,解放了诗歌表现力。“诗界革命”尽管最终也未能开创出成功的新诗体,但在实践探索中发现了古典诗歌现代转换的矛盾,培养团结了具有现代思想和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
鉴于学术界对“诗界革命”定义和分期的不同认识,这里有必要对“诗界革命”的复杂探索历程先作一个简要的梳理,以作为本文讨论的基础。早在1895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常在北京讨论诗歌革新问题,后虽因梁氏去《时务报》工作而中断,但是由夏、谭所代表的“新学诗”却产生了。所谓“新学诗”,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2](页49)梁启超曾回忆道:“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3]一开始他们就忽略了一点:生拼硬凑新名词,不仅会破坏诗歌含蓄蕴藉的韵味,也不能产生明白晓畅的情趣,只会减弱诗歌的文学性和审美功能。
于是,黄遵宪在1897年写的《酬曾重伯编修》中云:“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又提出了“新派诗”的概念。但它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保持古典诗歌的韵味和形式美,却囿于传统的诗美观,未能在诗体革新上有所突破。“新派诗”作家多具维新思想,有黄遵宪、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邱炜禐、麦孟华、狄葆贤等人。尽管他们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但是多是语言的非规范性拼凑,使新派诗走上怪癖的歧途,所以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
“诗界革命”的口号,最早是梁启超1899年12月23日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也正式把诗界革命纳入“新民”事业的体系,随之便产生了对于文学的直接而急切的甚至还有点简单化的期待。梁启超在文中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根据这三条标准,梁启超检讨了“诗界革命”以来“新学诗”、“新派诗”在美学上的得失。对“新学诗”梁氏作了明确的否定,他说:以夏曾佑、谭嗣同为代表的“新学诗”虽“皆善选新语句”,但“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4]对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梁启超则是肯定的。他说:“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4](页189)梁启超肯定了“新派诗”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又指出了这类诗“新语句尚少”,同时梁启超也看到了“新语句”与“旧风格”的矛盾。但由于梁启超受传统审美观的制约,也由于古典诗歌形式规范潜在的艺术魅力,他还是看中了“旧风格”,这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共同的局限。梁启超最终让渡出了“新语句”,而保留了“旧风格”,希望以此来迎合大众的传统审美观念,从而确保承载改良启蒙意图的“新意境”深入民众。新意境是为实现思想观念的西化,旧风格则是传统形式的继承,这是思想启蒙与诗体建设相互妥协达成的新契约,也是梁启超在总结失败后的努力校正,并想借此来扩大革命的阵线以便继续探索出路。
之后,黄遵宪“新体诗”的提出可以看做是对“诗界革命”中诗体改革的新探索。1902年,梁启超继续在《新民丛报》中通过《饮冰室诗话》宣传“诗界革命”,并给黄遵宪的诗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尽管如此,黄遵宪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旧风格”与“新意境”存在着矛盾,于是提出诗体改革的新主张:“报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徘如徘伎辞,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于题目,如梁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子之纳职,侯选道之贡物,皆绝好题目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5](页1245)这是黄遵宪经过长期思考而提出的诗体改革方案,已达到了“诗界革命”在诗体改革方面的最高成就。
从“新学诗”到“新派诗”到“诗界革命”再到“新体诗”,“诗界革命”的探索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内容层面上,“诗界革命”是从宣传新学、描写新事物、表现新思想开始,继而又以描绘时代风云、反对封建专制、弘扬爱国主义、礼赞民主革命为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从“挦扯新名词”开始,逐渐过渡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再到借鉴民歌形式,力求冲破旧格律旧体制的束缚而提出了“新体诗”。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诗界革命”理论探索和调整反映了新派诗人追求新思想和新事物的不懈尝试。
二、“诗界革命”的思维困境
今天看来,“诗界革命”最终也没能解决好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使得“诗界革命”只是旧瓶装新酒。新内容要求创造出新的形式,如果强调保持旧风格,就会束缚住手脚。如果说以堆积新名词取胜的“新学诗”是使用传统思维反传统,对诗歌传统形式的突破尚未自觉,那么“诗界革命”在努力实现传统审美趣味的要求时,传统与现代思维的悖论无疑就造成了更大的文化选择困境。由于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既参与领导了近代启蒙维新的政治运动,又致力于诗歌的革新运动,所以其理论中,所谓新意境,基本是指以改良思想构成的新内容,所谓新语句,就是加入一些翻译引进的外来词,肯定会造成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的困难。正是一开始就是迫切的维新政治需要才催生了这类过于急功近利生拼硬凑的“新诗”,最后是不但破坏了文学的形象性特征,而且弱化了诗歌的审美功能。
梁启超总结前期诗界革命的缺点,认为一在于“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二在于“不备诗家之资格”,因而将“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试图以此来纠正前期的形式主义偏颇。以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为里程碑,他从第四期起连续四年刊出的《饮冰室诗话》,使得“诗界革命”真正形成了广泛的文学运动。黄遵宪赞扬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6](页49)《新民丛报》设“诗界潮音集”专栏,《新小说》设“杂歌谣”专栏,集中发表改良诗作。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则为诗界革命提供纲领理论和舆论上的支持,他又排出“近世诗界三杰”的名单,“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实际上起了组织“诗界革命”阵容的作用,但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诗界革命”的症结所在。
从根本上讲,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是“诗界革命”的两大使命,然而在具体操作中经常处于思维悖论之中。首先,诗体革新是在启蒙任务之下进行的,诗体革新缺乏独立性,始终从属于启蒙运动的政治要求;其次,思想启蒙与诗体演进二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促进,却又存在着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关系。“诗界革命”正是在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之间不断寻求二者的平衡点,不断重新调整、确立变革的途径与手段,试图将社会变革与文学变革协同一致,共同开创改良派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诗界革命”发生在文言尚且一统文坛之际,语言革新这一环节尚未成熟,从而出现了思想先行、诗体滞后的现象,而诗体反过来又制约了思想的深入与传播,二者相互牵制,大大削弱了启蒙的力度与效果。[7]中国近代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早年都受过正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在参与近代文学变革之前,已形成固定的正统汉文化思维方式,在参与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的建构时,主要是进行表层的社会政治批判,而未进行深入的传统文化批判,这就表现出他们的不彻底性。
以黄遵宪为例,他曾从1877年到1894年,历任清廷驻日、美、英等国的外交官,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大受西方学术启发。但他在“诗界革命”中也只是反对“祖汉媚宋”之类保守的学术思想,其思维定势丝毫没有偏离传统文化的轨道。《人境庐诗草·自序》中有言,“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嘎嘎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8]此文被誉为黄遵宪诗论总纲,而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超出传统诗学的既成规范。黄遵宪创作中多以古典的格调容纳新事物,以此来感染读者。只能说这种创作风格与创作策略比抽象的思想启蒙更容易被民众接受,他也更为看重把西方文明潜移默化于日常生活的理念之中。
黄遵宪的诗论典型体现了近代维新者以西方观念改造和完善传统文化的思考抉择蕴涵的内在困惑。面向世界时,他们可以冲破封建的等级规范;而内省自身时,却依然无法摆脱传统的价值观念,黄遵宪晚年的作品更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诗中运用的大量典故多以封建伦常为评判准则。
“诗界革命”的实践者在接受西方文化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精神、探索深度和革新勇气,然而在深层意识中却始终认同于士大夫的身份地位。这就形成了近代文学变革“穿新鞋走老路”的基本模式。这种矛盾的特殊心态左右着他们的人生道路,真正把封建伦常纲纪从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中排除,还有待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转变。
三、“诗界革命”的反思与启示
“诗界革命”是清末资产阶级文学家和进步诗人,适应维新、革命运动发展的社会潮流和民主、民族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在古典诗歌基本形式范围内,突破传统创作原则,转换诗歌发展方向,革新诗歌内容性质,寻求语言和某些形式解放的一场诗歌变革运动,是诗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今天反观“诗界革命”的探索历程,我们看到了近代文人心态的“一步三回头”。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封建士大夫文人,他们自身思想观念要更新必须经历在觉醒中趋向更新、在探索中有所开拓、在迷茫中产生蜕变的螺旋式衍变,从而走完从封建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历程。“诗界革命”算不上一场真正的彻底的文学革命,很大程度上带有改良主义性质,不仅形式和风格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传统束缚,理论观念也常常带有新旧交替的印迹。[9]
从社会学角度看,“诗界革命”作为维新启蒙的一部分,其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启迪民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它不是文学近代转型的主动诉求,而是因为形势所迫,被动进行文化选择的结果。所以,变革者们既不能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掘出可以与西方进步文化交流融合的精华,也未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西方进步文化的精髓,并恰当地引进、采纳、消化、吸收,以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他们面对异质文化时暴露出来的集体无意识中的思维弊端,强调的是一种文化中心感支配下必然的文化选择行为,成为传统“经世致用”思潮的集中反映,可视为“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策略验证。[10]可以说,这种从诞生起就伴随着的文化认同的矛盾与两难,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启蒙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基本文化心理。
从文化学角度看,“诗界革命”表面上的特征是新旧杂糅,其实质是激烈的文化冲突,启蒙者拓展文学载道内容的内涵与外延,是欲借用诗歌宣传精英思想。“诗界革命”观念中的传统因素和实用理性精神依然,仅是要求诗歌承担起改良社会政治重任的反传统姿态而已。后来梁启超逐渐少了对新名词的鼓励,多了对古风格的珍爱,明显说明了其创作动机还是传统思维方式,也显示着近代诗歌转型的内在被动。显层的特征就是,这种思维悖论使得使用新语句与制造新意境之间时常捉襟见肘,努力保留“旧风格”更是进退维谷。梁启超最终认为“用新意境入旧风格”才是古体诗新生的唯一途径,也很能说明传统思维羁绊和近代诗歌发展的难以协调。
所有矛盾的焦点最后都要集中在传统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根本就没能在启蒙运动中转换这一问题上。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这一现象归根于尝试阶段所具有的“学问饥饿”,是不无道理的。“诗界革命”的思想启蒙性质只是在救亡图存的危机下,知识分子试图保国保种所采取的民族生存策略,绝非民众的个性觉醒,不能等同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同时也预示着在三四十年代民族救亡压倒个性启蒙的必然趋势。[7]启蒙意识缺乏个性解放,诗歌新意境有了西方新事物而失去了西方新思想,一切都笼罩着古典诗歌的阴影。或许,进行诗界革命的诗人们只是想成为优秀的旧诗诗人,想成为源远流长的汉诗传统的维护者也未可知。
客观地讲,“诗界革命”的文学史意义不在其本身,而在对后来新诗运动的影响上。这场“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都为五四白话新诗的崛起做好了先导和准备。在诗体变革的总体进程中,近代的“诗界革命”正处于传统旧诗向五四白话新诗转变的中间阶段,因而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它既动摇了旧诗的阵脚,也为新诗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所以其成就能为新诗运动提供滋养和动力,其失败也能为新诗运动提供经验和教训。
标签:梁启超论文; 黄遵宪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饮冰室诗话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诗体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