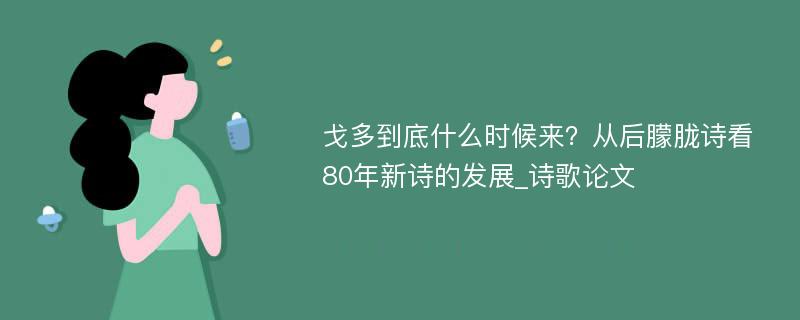
“戈多”究竟什么时候来?——从后朦胧诗看八十年来的新诗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朦胧诗论文,什么时候论文,新诗论文,十年来论文,戈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晓明:(以下简称王)八十年来白话诗歌的困境大体依旧,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却是诗歌突破这种困境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个可能性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它牵涉到语言和诗歌层面以外的许多东西,并不是单靠语言和诗歌层面的分析,就能够清楚地把握住的。但我想,我们的讨论似乎还是只能先从诗歌和语言层面入手,譬如,今天的白话诗如何面对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罗岗:(以下简称罗)由于白话和文言的截然分野,我们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中国古代诗对白话新诗人的影响。这里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五四”以来的具体语境中,“白话/文言”早就溢出了固有的语词轨道,成为特具涵义的意识形态符码,在它们背后,可以不断翻转出诸如“新/旧”、“传统/现代”、“保守/进步”、“正统/民间”之类的二元对立。这为我们的谈论增加了难度,我只要稍微提一下五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曾有过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倡导,大家就一定能意识到其中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白话新诗人想从古代诗中直接开发新颖的意象和语言,这样做的可能性十分有限。诗人努力的方向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对古代诗的“重写”,让白话突入到古典意境中,产生某种类似于“震惊”的美学效果。萧开愚这样改写李白的《静夜思》,“床前的光,是月亮发出/还是霜所吸附?/悬空的人/被月亮拒绝,也被大地拒绝/──侧倾的身体多么黑暗!”除了诗人心思的机巧和有意为之的颠覆外,改写没有比原诗提供更多的东西。另一种则是企图从古代汉语中汲取诗语言的源头活水。“‘我便是那桃花下的弄箫人呢!’/纸绣郎,换了绫花心么?/当我要钻你袖笼时,/你可变成梧桐雨?……落英小神,暗藏的弓履,/谁设计了这莫名的尺寸?/一张莺声喋喋的、憔悴的银床,/我精心弄箫给谁听呢?”(钟鸣:《井鬼》)文言与白话词根的羼杂使用,给人一种夹缠不清的感觉;混沌暧昧的古典意象反复出现,使诗句散发着腐败的气息。很难说钟鸣故意追求这种气象,但语词的堕性往往带动诗人身不由已地向下滑落。萧开愚说:“话已被前辈说完”,“我们写诗不过是抄写”。流露出比一味在新诗中寻找古诗的影子深刻得多的“影响的焦虑”,它暗示传统不需要人们费力去寻觅、捕捉,而是完整地在人们体内生长,在血液中流淌。文言和白话尽管有着许多区别,却同属于汉语系统。白话,也许像某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有一个自我生长的完整脉络,却也不能否认几千年的文言文构成它的“前历史”。只要承认新诗写作是在汉语系统中完成,传统的影子就无所不在。诗人并没有在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进行任意选择的自由,他们在诗句中认真摆弄每一个字词,字词固有的对传统的记忆必然会将诗人引向过去,声调、顿挫、韵脚、意象……都会被打上传统的印记。我认为,诗人之于传统的关系,一方面应该在现实的境遇中加深对传统的体味;另一方面,则又要从这种体悟中抽身而出,予以返观和省思。一头扎进传统的怀抱里,只是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把几十年的传统视为沉重的包袱,也未免有些可悲。传统也是一种时间的动感,死亡与生命的两种可能在其间转换不已。真正拥有传统的诗人,总是从死亡走向生命,犹如顾城的诗句所言:“死亡是没有的,/我已在生命中行走千次。”(《诗.生命》)
倪伟(以下简称倪)在我看来,当代诗歌应该在以下两个层面上来创造性地继承传统。首先是要在诗学精神上寻求与传统的契合。传统诗学精神最具特色的精华便是那种超然物外的静观的创作态度,这种以物观物的创作态度拉长了诗人与诗歌对象之间的距离,使诗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静态的共时性风貌,意象与意象之间通常缺少知性的逻辑联系,而是同时展开,通过不同意象的组合酝酿诗情画意。杜甫的这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便颇能表现出这种传统诗学精神。美学精神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而且也折射着时代精神的光芒。在变化急遽的现代社会,这种东方式的静穆的诗学精神显然已不可能被全盘搬用了,因为作为其诞生土壤的农耕社会早已烟消云散了。但是这种诗学精神毕竟是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孕生出来的,仍然值得我们创造性地继承,以丰富当代诗歌的表现手法。只要运用恰当,就能使诗歌别具一种蕴藉婉转的风韵。柏桦的《春日》便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这首诗以一种略含忧伤的语调委婉地描述了诗人在一个春日的午后独立远眺时,内心涌起的春水般绵邈飘忽的思绪和感觉,意境清丽幽远,颇具晚唐诗和北宋小词的风致,但已与“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式的古典意境全然不同,因为诗里溶进了一个现代人对生存的忧思和独特感觉,在平静的诗句里,我们仍然能够体味到一种拂拭不去的生存的焦灼感和惶惑感,这确实不是旧诗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其次是可以提炼旧诗的句式结构,运之入诗。中国古典诗词注重感性直观的表现方法,与西方诗歌那种分析性的演绎性的表现方法迥乎异趣。在古典诗词里,意象的组接是跳跃性的,类似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意象之间通常不需要分析性和说明性的文字如系词等的联系,因而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自我呈现式视觉效果。这在语言上便形成了旧诗特有的句法结构,简洁凝练而又意味深长,这种与汉语本身特点相吻合的诗的句法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恰可以弥补欧化的白话的某些不足之处。像“春风释怀,落木开道”(柏桦:《骑手》)这样的从旧诗中脱胎而出的诗句,简练有力,使诗的境界豁然为之开朗,确实能够给诗歌增色不少。
毛尖(以下简称毛)不过,我有时感到,朦胧诗仿佛在阻挠我们逃向具有参照性的古典时代。尽管他们的诗中也不乏“李后主”、“楚王”、“宫女”、“环珮”、“蒲团”、“羽纱”这样的词汇,但这些随便出没的意象对整首诗而言,常有不负担任何责任的来去自由,它们可以被替换,可以被消解,因而它们往往一诞生也就死了。而我想,诗人对这些语词的征用,也主要是为了传达创伤的“不朽”。所以,后朦胧诗人对古典意象的选择更像是出于一种科学上的考虑。而在他们对魏晋南北朝知识性的追忆中,诗歌只是方便了他们对古典时代的功利性攫取,至于读者的想象力,也就在这些空荡荡的意象中凋零。因此说起来,我倒是觉得在承接传统诗性的努力中,戴望舒当年的《雨巷》是一条道路。在“丁香空结雨中愁”与“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之间,白话诗歌与古典意境相互融合,交换着音乐与心情,私语着忧伤与美丽。
陈金海(以下简称陈)另一个问题是,后朦胧诗人中有许多人对西方诗歌患有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他们很轻松地就自以为“进入”了西方,然后迅速地就开始了“西方式”写作,比如海子的后期长诗,诗人似乎可以随意地“出入”于希腊史诗传统与印度史诗传统之间,自以为拿到了通向诗神之门的钥匙,结果诗人只能把他的长诗在情感上写得热血奔涌而实质上却空洞松散。如果说新诗需要借鉴西方的话,不如把视点放到西方诗歌传统得以形成之前的那个原初的点上,从那里反观新诗,再去图谋新诗发展的可能性。
罗:当年胡适称之为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的《关不住了》,其实也是首译诗,译自美国诗人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rs。是译诗也就罢了,有趣的是,这是首直译甚至“硬译”出来的诗。参照原诗,可以发现译诗很少出现缩略或改装原文语词及语序的现象,甚至连“as”、“that”、“but”、“and ”等一些指示语句之间逻辑关系的介词和连词,也一丝不苟地被转换成相应的汉语白话词汇(“像”、“叫”、“但是”、“更”等)。这确实是首具有“纪元”意义的诗,似乎预示了以后新诗与译诗宿命般的联系。那种用汉语词汇着意将外来语中某些无关紧要的部分固定下来的做法,暗示着某种语言等级制度的滋生,汉语成了外来语(主要是西方语言)的附庸。用译诗的意象代替自己的意象,用译诗的节奏代替自己的节奏,却是现在诗歌写作普遍存在的现象。也许开始还是有意地模仿和借用,以求找到一条便捷的通道传达自己的感觉。这种做法的背后依然是把诗当作手段而非目的的观念在作怪。渐渐的,译诗的感觉取代了自己的感觉,到最后也不清究竟是为自己的感觉还是译诗的感觉而写作。从二三十年代诗中频繁出现的夜莺、云雀、百合花等意象,到今天诗中充斥着的军舰鸟、防波堤、加乌乔、出浴的裸女、翠绿的陶罐……这样一类意象。我不明白为什么诗人热衷于使用从书本上读来的、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意象。他们并不是不懂得“书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用这样的意象来契合心中的诗情终究“隔”了一层。还有,外来的意象天然地带着“移植”过来的外来语的痕迹,如果将它们强行植入诗中,诗人会不会有“从一个象形的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欧阳江河:《汉英之间》)的危险,最终丧失语言的家园,“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汉英之间》)
毛:我看“汉英之间”的旅行到现在大多是有去无回了。虽然诗人一方面无比恐惧变成一个拼音的人,一方面还是控制不住地一首接一首写着中文版的外国诗。而“后朦胧诗歌”,作为又一次诗歌命名方式,就像五四时候各种名目的“浪漫派”、“象征主义”、“意象派”、“现实主义”诗歌一样,也是从国外移植来的命名策略。而我们传统的对诗歌的命名方式就要纯粹许多,主要就格律而言,比如“辞”、“诗”、“词”、“曲”、“令”等等。因此,和外国诗歌接轨的中国白话新诗的身份是暧昧不明的。它所制造的一个又一个“戏剧性景观”其意义对中国读者而言是陌生的,往往既不能帮助我们回忆生活,也不能促使我们展望前程。所以,它们永远是纸上的陷阱,或者说,这陷阱已被作者们自己所填满了。
李念(以下简称李)尽管任何形式的借鉴都是合理的,但是,刻意的模仿总会走到必然的死胡同里。30年代“新月派”对格律诗的重提与实践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徐志摩、闻一多等出于对诗本性的认识,强调诗的格律性。在实践中,他们模仿西洋诗来限定音数。但是西洋诗的节拍,一般音数也即等于拍数,而白话新诗因为失掉了平仄限制,很难维持古体诗歌两音一拍的原则;且现代汉语常由几个音组成一个意思,音数造成的拍子与意义造成的音节停顿是不相等的。所以,“新月派”诗人尤其闻一多在对西方诗歌的执著模仿中,反而使得中兴诗歌的努力涂上了灰暗的结局。后期“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等重写自由诗,也是因为意识到了中英诗歌其间的不一致。因此,外来诗与我们古典诗歌都只能提供一些借鉴,并且知其然往往片面,必须应知其所以然。这确实也是个难题,但是我们的信心总该有,毕竟新诗还很年轻。
王:其实,对当代诗人来说,中国的古典诗歌也好,西方的诗歌也好,都是别人的东西。即使要从中获取有益的帮助,也首先得确立自己的存在。借用鲁迅“拿来主义”的说法,就是先得有一个拿来者,然后才谈得上拿来。因此,今天诗人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从当下的生存体验中,去获取真正属于自己的诗情。这种诗情当然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闪烁在许多日常的词句、图景和事件之中。要想有力地把握住它,诗人就必得要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日常经验。因此,我们也就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就在一些诗人努力从前人的诗集当中去寻找资源的同时,另一些诗人却转向口语,想以此来确证自己的诗性存在。
我想,大家都不难理解这些诗人的用意,但他们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口语并不是天生就适合入诗的。它当然有一些与诗性语言相近的性质,譬如它的不断变化,不断生成新的语式和语义。但它也有一些似乎可以说是“反诗性”的因素,比如它的啰唆,它的过于强大的交际性,尤其是它的粗鄙化倾向。这不但体现在某些具体的词句和语式当中,而且贯穿在整个口语活动中,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口语的一种基本品格。
陈:口语的品质在本质上的确是反诗性的。口语芜杂的形态后实际上包含着一种世俗的精神,与诗形精神向上的指向相比,它是堕落的、庸俗的。完全用口语写作只能是迫使新诗在精神高度上降位。后朦胧诗中就有一批口语诗,像于坚、丁当、韩东等都属于这一类口语诗人。语言问题一直是新文学发展中被关注的一个焦点。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论争,这些都是文学语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口语的职能应该局限在承担交际职能的功利层面上,它不能成为新诗语言的主要资源,诗歌语言与口语,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倪:我总觉得,在提倡诗歌语言口语化的口号里,我们似乎不难窥见西方思想传统的幽影。就像德里达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就是语音中心主义,它认为说话优于写作,言语是实体、理念、本质的真实自然的呈现,而文字则只是对言语的极其不完备甚或是歪曲性的再现。文字只是一个补充附加物,它依附于鲜活的自我呈现的言语,就像手淫依附于所谓的正常性经验,文化依附于自然,邪恶依附于天真,历史依附于渊源,而言语又依附于实体、理念、本质等直觉的呈现。由此可见,语音中心主义的全部潜台词无非是将某些理念或价值意义捧抬到先验的本体性存在的地位,然后在它们的指引下建立起一整套上下等级森严的价值意义体系。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可以说就是这种语音中心主义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反映。对于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者来说,强调新诗应明白如话,即所谓的“我手写我口”,是极其自然的,诗歌语言向日常口语靠拢,无疑可以缩短诗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且更易为大众所接受,成为一种较为理想的载道工具。因此,诗歌口语化的要求是他们整个文化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也是他们欲求冲决封建价值体系罗网,建立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价值体系的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环。从表面上看,当代诗歌中的口语化实验似乎是胡适等人主张的历史延续,其实不然。胡适他们提倡诗歌口语化是出于启蒙的需要,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而在当代口语派诗人那里,这种历史的动机和合理性已然消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口语派诗还明显地具有一种强烈的反精英倾向,在诗中我们以普通人自居,反复叙述和倾诉的也只是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琐碎的题材和卑微的情感使得这些口语诗彻头彻尾地散发着庸人的气息,沦为一种令人生厌的自我絮聒。
其实,诗歌语言口语化只是一个虚妄的幻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书面语言与日常口语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无法弥合的,书面语并非是借助文字符号对言语的直接记录,它有一套与口语不完全相同的语法规则,口语一旦转变为文字语言,就必然要发生某些变易,因此追求言文一致就如同水中捞月、镜里摘花,怎么做得到呢?
罗:不过,对白话新诗人来说,古代诗和译诗是离他们更远,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利用的写作资源,而口语则是环绕着他们的语言现实。因此,不管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口语对他们写作语言的影响乃至干扰,是不言自明的。但笼而统之地将诗歌语言归入书面语,似乎过于简单化了,标准书面语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它由报纸社论、官方文件、学术著作、以及被视为经典的白话文作品共同构筑而成,整个社会话语系统在它的制约下才能正常地运作。诗歌要想有共通的可理解性,仍必须借助于标准语的规范,但根本上诗歌语言是“反规范”的,它着力于松动、颠覆结构僵硬的书面语系统,力图重新恢复话语的活力。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称波德莱尔为一个“同语言一道密度策划的人,他在诗行里调遣词句,计算它们的功效,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暴动的人手。”(《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诗人的每一次写作都是一场在纸面上实施的语词暴动,一旦诗歌语言放弃与标准书面语的对抗,它就极有可能被吸附过去,成为标准书面语的一部分。只是诗歌语言对标准书面语的疏离,不能“无中生有”,必须借助外力的作用。生生不息的口语则是诗歌语言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之一,口语的鲜活、流动和当代性正足以松动书面语的凝固、强制和持久。但口语由街谈巷议累积而成,村夫野老口口相传,必然带有浓烈的日常生活色彩和世俗市井气息,这是口语“反诗性”的一面。如果诗人对此毫无警惕,以为尽力描摹口语就能带动诗歌语言的进步,结果只会留下像“谭运长在我对面,手指伸进嘴里摩擦/发出呜呜的语音,他很快活。宋琳在隔壁/用圆珠笔写文章”(张小波:《一条很长的布裹住冬天的窗子》)这样鄙俗而不可理喻的诗句。因此,诗歌语言在汲收口语的同时也在偏离口语。如果将标准书面语和口语视为两个话语中心,那么诗歌语言应该处于两个中心的边缘、过渡地带,它偏离于两个中心,在静态上趋向标准书面语,在动态上接近口语,这个有利的位置使诗歌可以自如地出入于两大话语系统,离开了这两大话语系统,诗歌语言只是子虚乌有之物。诗歌处心积虑追求的效果,应该是让语词从实用中摆脱出来,恢复其原有的初始性、独特性和纯粹性,并把这种新鲜的感觉直接带入行文中。在这种语言中,存在的本真向人们涌现出来,你第一次感到“诗意”的气息扑面而来……
毛:我想,在这种意义上讲,口语就像一场雨。它对常人只提供雨水的实际意义,却向诗人呈现潮湿和情感之间的隐喻关系。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日常语言也以其泥泞的质地筛选着诗人。那些抗拒不了习语诱惑的心灵就粗糙了,而好诗人则不仅阻止了自身向世俗的沉沦,而且从口口相传的日常语言中挽救和恢复了词的自发意义。
王:话说到这里,我们事实上已经触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个诗歌与语言层面背后的东西。无论古典诗、西方诗还是我们自己的口语,都只是诗歌和语言层面上的东西,而就在这个层面上,它们也只是构成了诗歌走出困境的外在的助力,而非诗歌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我觉得,今天的诗人能否创造出真正优秀的诗歌,关键是在他能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深切体验到来自他今天生活中的诗意,他的整个心灵能否因此而猛烈燃烧,酝酿出表达这种体验的充沛的诗情。只有当他拥有这样的体验和诗情的时候,他对前人的诗歌传统的借鉴,他对当下流行口语的汲引,才真正能具有意义。也只有当他拥有这样的体验和诗情的时候,他才真正能脱出那种盲目破坏的心态,全身心地投入诗歌的创造。我总以为,对一个诗人来说,那种想要表达他觉得唯有自己才能表达的东西的欲望,才是最重要的,也唯有这样的欲望,才能成就真正的诗歌。当诗人为这样的欲望驱迫着投入创作的时候,他大概是既不愿分心去权衡如何对待传统诗歌之类的问题,也无暇去谋划“颠覆”既成诗歌模式之类的事情吧。说到底,这样的“颠覆”只是一种效果,它不应成为诗歌创作的动机,如果你不能成功地创造出新的诗歌形式,无论费多大的气力,你都不可能真正颠覆掉原有的诗歌形式。单纯的“颠覆”完全可以靠理智来进行,可如果要说到创造,那就非得有全身心的投入,有整个心灵的激动、神往和沉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今天的诗歌需要的不仅是才气、熟练地调词遣句的能力、对古代或西方诗歌的修养、对“颠覆”之类策略的兴趣,而更是一种原初的能力,一种在生活刺激下不断磨擦出诗性火花的能力,一种以这一点点火花便连锁爆炸的能力,一种仅仅是热爱诗歌而不是热爱与诗歌有关的其它东西的能力,一种一旦投入用诗句来记录自己对诗之天国的隐秘感受的艰苦劳作,便忘怀一切、无暇他顾的能力。
倪:作者的人格修养对于作品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甚至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品位,而环顾当今诗坛,我们却不能不感到些许失望,当代诗人中有不少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装扮出一副佯狂高蹈的名士派头,放浪不羁,蔑视群伦,自以为文采风流,而事实上却只是个心灵空虚、灵魂苍白、神经紧张的可怜虫,还有些人则视写诗为一件技术活,锻字炼句,拆东补西,仅仅满足于当一个制造诗歌赝品的诗匠,而真正热爱诗歌、献身诗歌的诗人实在太少。由此可见,当今诗歌的没落也是宜其所然。当然,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诗人身上,未免太苛刻了些。归根到底,畸形的人和事物都只能是畸形的社会和时代的产儿,在金钱吞噬一切,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文化已不可避免地江河日下,浅薄取代了深刻,卑琐取代了高贵,物质取代了精神,在这样一片满目荒荑的精神废墟之上,又怎能企望长出艳丽夺目的诗葩呢?
毛:你说得也未免太悲观了吧。尽管这绝不是一个可以抒情的时代,“诗外的功夫”也的确越来越难做,但是,总还有那么些诗人以持续的热情在回忆家园。而且我认为,诗人或诗歌应该有另一个世界,有他们自身的命运,在那里,语言以其最初的光亮引导诗人永远上升,而他们身外的世俗世界对他们再不能“有所作为”。
罗:对了,我注意到近来一批诗人对抒写南方诗情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兴趣。戈麦在他自沉万泉河的1991年,竟写了三首关于南方的诗:《眺望南方》、《南方》和《南方的耳朵》,戈麦说:“戈麦寓于北京,但喜欢南方的都市生活,他觉得那些曲折回旋的小巷深处,在那些雨水从街面流到室内,从屋顶上漏至铺上的诡秘生活中,一定发生了许多绝而又绝的故事。”(《戈麦自述》)第二年秋天,上海诗人陈东东创办《南方诗志》,迅速成为一批有实力的诗人诗作的集结地。陈东东发表具有宣言性质的随笔《在南方歌唱》:“在南方歌唱,我是那眼含热泪的雨燕放送者,我更是那已经被放送的白腰雨燕。”从“眺望南方”到“在南方歌唱”,戈麦和陈东东乃至《南方诗志》诗人群是背景非常不同的诗歌写作者,但“南方”意象在他们的诗作、诗论和诗刊中反复闪现,的确意味深长、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版图上,“南方”一直处于“边缘”或“外省”的位置,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诸如南宋、南明之类,“南方”又带有一种苟且偷安、负隅顽抗的意味。另一方面,“南方”不是一个实在的地理概念,它是一种“不可返归的浮华的想象”(戈麦:《南方》),由于拒绝世俗社会的侵扰,散发着孤芳自赏的文人习气,对喧嚣市声的逃避,又使它带上躲入书斋、湎于沉思的色彩。“南方”,作为含意明确的象征,标志着诗人对自身处境和诗歌写作的自觉定位。诗歌写作对政治中心和世俗社会的双重偏离,正奇妙地应和着相对于标准书面语和口语而存在的诗歌语言的位置。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今天诗人们匆忙变动的步履,或许会因为过分纷繁而使人眼花缭乱,但我们有理由期待,诗人在写作中对汉语诗性成分的各种试验,也许预示了将来汉语写作可能的努力方向。
王:我觉得我们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相信诗歌走出困境的可能性并不仅仅存在于诗歌和语言的层面中,另一方面,我们又只有通过诗歌和语言层面上的分析才能最终触摸到它。同样的矛盾也表现在前面大家谈到的另外一个问题上,对原有的诗歌形式的破坏并不就等于新的诗歌的创造,但有时,尤其在一种新的诗歌发展尚未成熟的阶段,创造常常确实以破坏的形式呈现出来。
作为读者,明知道整个社会的精神状况很难孕育出真正伟大的心灵,却依然仔细地阅读和分析诗歌,希望捕捉到至少是力图“伟大”的心灵的跳动;明知道现在有太多的诗人误将破坏当成了诗歌创作的全部,却依然认真去看待那些形状古怪的诗歌,努力从它们当中辩认哪怕是微弱的新诗歌的光亮──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是不是也能对中国白话诗歌的新的可能性的壮大提供我们自己的一份助力呢?
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把戈多设计成一个似乎是永远也不会来的人物,一个虚空的象征。恐怕不可否认,我们对诗歌的可能性的期待有时候确实有点像是在“等待戈多”。但我想,戈多能使人长久等待,就说明他终究不是一个空物,而他最终是否会来,大概也不仅仅取决于它自己,而同时也取决于那些等待他的人吧。作为文学读者,我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新的可能性的顽固的等待者,而且不光是等待,还尽力用我们热切的目光鼓励“戈多”向我们走来,减少他的孤独,使他的哪怕是微小的意愿都能获得及时的反映。这样,即使他最后还是被什么更大的力量拦阻住了,我们也能够心安:我们确实是热切地等待过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