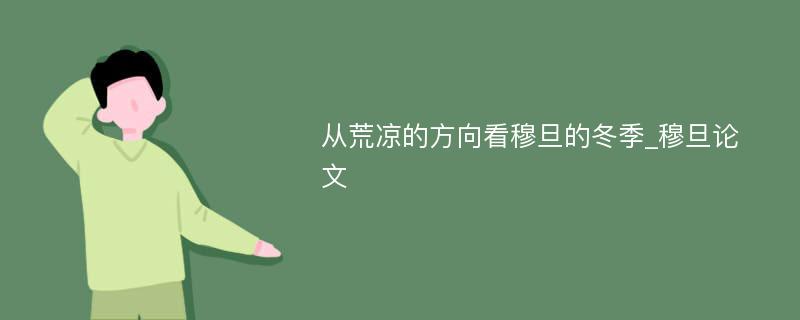
从荒寒的方向看——穆旦的《冬》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向论文,穆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在他的《西风颂》一诗中曾写下“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在相当长的时段里,我们都是从“积极浪漫主义”范畴理解这句诗的,从中获得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但在常识语境中,“冬”给人的感觉是荒凉与寒冷。穆旦在此并不回避而是直面这一常识,在此前提下展开他的抒情与思考。
在形式上,第一章是较为整饬的:共四节,每节以“我爱”始,以“严酷的冬天”终(注:此诗首次发表的版本(《诗刊》1980年第2期)上,这一章每节均以“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结尾,复沓性更为显著。)。以“我爱”开头并造成诗句某种程度的反复,在诗人以“查良铮”本名翻译的普希金的诗《水与酒》中也可见到:“我爱在炎热的日午/从小溪里掬一盅清凉,/我爱在僻静的树荫中/看水流如何泼溅在岸上。”(注:《普希金抒情诗选》,查良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91页。)
“我爱”是一个具有明确情感指向的词,主语代词和谓语动词简练而确定的结合流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作为一个具有正面情感内涵的词汇,“爱”给人的感觉是明亮和温暖,它指向的是自然人生中被赋予了某种肯定意味的领域。“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中,“淡淡”“短命”这些词一方面与冬的寒冷特征符合,“淡淡”除了有阳光清冷的内涵外,还有着静寂的意味,处在“太阳”和“日子”之间的“短命”在此也有了双重指向性:短命的太阳、短命的日子。另一方面,这些词汇也大致勾勒出反映在诗句间的基本色调:温暖(“太阳”),但更多的是冷寂。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冷寂、宽阔的感喟。“临窗”二字表明诗中的抒情主体所处的空间并不封闭,因为有窗,可以无障碍地看,对应了第一句中所描述的“淡淡的太阳”。“喜爱”一词虽然作为“工作”的修饰语出现,但和“静静”一起运用可令读者感受到诗人在一个冷寂环境中的坚守姿态与从容心境。尽管对于冬天的冷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它依然超出了诗人的心理预期,“冷”和“昏黄”再次对应“冬”的主题,一个“才”字与两个“又”则流露出诗人隐秘的怨怼。“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一句中出现了两个“我”,前者作为话题提出者,后者则限定了动作接受者,“酒”和“灌溉”的有效性因而被限定在两个“我”的前后夹击中,行文如此狭隘,令人顿感逼仄。“心田”一词中,“心”引发的联想依然是内向和私人性的,但“田”却很容易让人想到与宽广相关的土地、田野等意象,从而稍稍缓解了两个“我”造成的逼仄感。“灌溉”与“田”的意象架构出一个干渴者的形象,置放在“冬”这一语境中,它很自然地转化为对温暖与明亮的渴望。“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一句则将诗作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使之与人生/生命的命题相关,“冬”也因此成为生命之冬/人生暮年的隐喻。“多么快”又透露出诗人对于时间飞逝的叹惋之情。身处暮年,又面临有着复杂内涵的严酷冬天的诗人,此时此刻又会思考些什么呢?
“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勾勒的依然是一幅典型的冬天场景。“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中,“独自”意味着“凭吊”一词涵盖的内容是诗人更为个人化、私密性的领域,在中国文学语境中,“独自凭吊”更容易令人想到“孤独者”意象,从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晏殊的“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一直到鲁迅的“孤独者”都赋予了这一形象“孤独的清醒者”内涵。主体的清醒和理性使得“凭吊”获得了可靠性,“已埋葬的火热一年”就不仅是和冬天场景相应的具体季节,更包容了诗人对人生与自然的所有思考。“已”在此可以指向过去时间段,“埋葬”则更多搀杂了诗人的情感取向,“埋葬”这一动作主语的缺席更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空间:是谁/什么埋葬了“火热一年”?“凭吊”与“埋葬”的联手不仅蕴含了诗人的叹惋之心,而且也暗示诗人对匿名之手的隐在愤懑。“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用“小”“低语”“听不见”来修饰冬季冰层下流动的河水,字里行间有一种明显的强弱对比,用词如此谨慎,与原稿“似乎宣告生命是多么可留恋”结合起来读,更可窥见诗人对于弱小生命的温柔爱怜之心及叹惋之情。“呵”字如此轻柔,别有一种悲凉与无奈的味道。“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这里的“也”与上句的“只是”一起微妙传达出诗人的复杂心境:强弱对比之下,那一份挥之不去的隐秘愤懑和叹惜爱怜。这一节中,“枯”“死寂”与“火热”,“冰冻”与“流”,“听不见”与“跳动”等语汇都有一种对立场景的比照,因而使诗句间呈现出一种张力,从另一个侧面启发读者去体味诗人的复杂心情。
从绝对的角度认为这首诗仅写了诗人对冬天的否定是片面的,接下来的一节也反驳了这一点。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以“我爱”领起的这一节,似乎描写了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温暖的炉火”仅相对于“冬晚”才更为突出地存在,而在真正“温暖”的季节,它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对“快乐无忧”的往昔的回忆在此成为一个小小的话题,和冬天温暖的炉火一起,构成了或可慰藉诗人心灵的一点点暖意。但即使在这样明显的场景中,诗人的沉忧隐痛依然无法完全释然。“昔日”“回忆”“往年”等指向过去时间段的词汇与“会心”“快乐无忧”紧密相连,从而暗含了对当下某种不欲明言的不满。同时,“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的阴影也像梦魇般掠过貌似欢乐的一帮朋友们。最后一句将“人生的乐趣”与“严酷的冬天”对举,不仅回应了这一章的反复技法,也在这幅温馨画面中注入一丝不免有些自嘲的语气,在这样的自嘲中,快乐如此难得,而严酷的就不仅仅是自然的冬天了。放在一九七六年的中国背景下结合诗人自身的遭遇去看,这一点恐怕更为突出。
最后一节在一连串可能引起疑问的诗句中,诗人以一种责任承担者的姿态直面“冬”的主题。“不眠之夜”引发的联想,“尚存”一词隐含的嘲讽口吻,虽然延续了第三节的某些意绪,但在更大的命题下,这些似乎都不那么重要。“雪花飘飞”“茫茫白雪”依然指向双重意义上的“冬”,“死去”“尚存”“遗忘”则勾勒出在白雪覆盖之下的另一重世界,它不仅仅与诗人的个人体验相关。“茫茫白雪铺下”的“遗忘世界”指向的是一个过去世界的“空白”,这样一来,“不眠之夜”的“珍念”不仅仅是为了对亲人的怀念,更是对被覆盖被遗忘的过去世界的打捞与保存,诗人以“感情的热流”对抗“严酷的冬天”,以凡夫俗子的血肉之躯对抗自然与社会的荒凉与寒冷。“我愿意”更是以一种承担者的姿态表明诗人在荒寒时刻的誓言般的决心与勇气,这样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与第三节的“回忆”一起再次确证了这一章的主题:在人生暮年之际,对于这冬天和曾留给这冬天记忆的世界的记录。这或许是诗人寄予这首诗最低调的预期。
二
第二章从自然界的角度写冬天。整章用了拟人的手法,但令人时时有一种抒情主人公在场的感觉。
第一节写寒冷。第一句用两个“寒冷”强调了这节的主旨,接下来的“尽量束缚”“用冰封住”“都沉寂”“勾销”等谓语动词的主语仿佛都指向自身,给人一种自我封闭的印象,同时,在潺潺、盛夏、笑闹、蓬勃等对比性的句子中隐现出被冬天禁锢之下的某种真相。
第二节以“谨慎”命名,拟人性更为明显,谨慎是因为有所恐惧有所防范,所有的描述便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生命受到挫折,血液闭塞住欲望,太阳犹疑不决。对“花”和“绿色”质问式的呼唤中,流露出一种欲挣扎和摆脱现状的渴望。“经过多日的阴霾和犹疑不决”“才”“漏下”等词句更是形象细致地描绘出一种谨小慎微的心理。
在这一章中,交织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字面上的,合于跟“寒冷”“谨慎”这样的词汇相关的心理领域,它尽量真实地展示了自然和社会双重层面上的冬天特征;另一种声音则隐藏在这种对冬天的描述中,并时时煽动着新的叛乱,比如第二节中对“花”和“绿色”的追问。这一点在第三节中更为明白。“奇怪!”干脆利落地道出了诗人心中的疑惑和不满。“哪儿都无”“都怕”这样牢骚般的表达方式在前两节中是不常见的,却比较淋漓痛快地体现出诗人隐藏已久的某种批判立场。“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句与深深隐藏害怕峥露头角的春天相似,写的是生命的暮气,“仿佛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一句则将在前两节中还不甚分明的主语显露出来,打破了读者心中曾经的含混,“仿佛”再次表明诗人试图以真相示人、对这样一个禁锢人的冬天有所背叛的努力。
三
第三章继续在个体人生的层面上将“冬”的主题推入了一个极端的境地。诗人在此引入了一个“你”的视角,某种程度上,这个“你”可以认为是诗人的自指,就此从抽象和具象的侧面上探讨在冬天可能的境遇。
第一节中,爱情、书信指向的是需要和他人交流才存在的情感层面的东西,而在肃杀的冬天,情感像自然万物一样面临被杀戮的命运,爱情被停止分赠、写了一半的书信也被停下,一个抽象——爱情,一个具象——写信在这里并列提出,使得诗句有了更广的涵盖面。
第二节诗人又使用了一个比较抽象的词——心灵(注:一般来说,抽象词汇的运用易于使诗歌变得说教,淡化其形象感,在穆旦诗中,抽象词汇的使用是比较多的,有很多研究者将其认为是穆旦诗的“智性”特色。)来描述冬天的残酷性。在夏季常见的蜂蜜、果品、酒在冬天自然成为“礼品”一样稀少的东西,对于大匮乏的冬天的“你”来说,坐在炉前品尝这些夏季的礼品成为一种奢侈,“慢慢”一词更是细致描述出诗人对于这种奢侈的珍惜。最后一句则表明这种“慢慢品尝”不仅出于口腹之欲,更是一种心灵的饥渴,品尝也因此具有了双重指向——既是对盛夏美景的回忆,又是对荒寒冬天的某种弥补,而这样的回忆和弥补,当然不仅仅是自然物质层面上的。
第三节诗人尝试用“白日梦”(注:弗洛伊德说,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那么可不可以说对文学的阅读是读者的白日梦呢?)的不可能来衬托冬天的荒寒特征。躺在床上读小说是一种温馨舒适的室内场景,诗人获得了一个可短暂逃离现实的机会,有了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可能,却也使“封住了你的门口”的冬天的形象更鲜明地凸显出来。而另一个疑问也会浮现在读者心中:冬天封住的,何止是“门口”?
而当“梦”真的来临,诗人是否会有片刻的安宁呢?第四节从一个较为日常化的细节——睡眠着手否定了这一构想。疲劳后的休息,是人的正常需要,但在连树木和草石这些原本象征自然界美好一面的物体都要“嘶吼”的冬天,诗人不胜其寒,简直是不得不逃进梦乡,而梦本质上的虚幻性终将使诗人无法真正躲开一切,获得心灵的安谧,“梦”也不过是一个难耐风寒的场所,睡眠成为另一种疲劳的开始。在这句诗中,占据主体位置的不是可能会取代/补偿现实残酷性的“梦”,而是以刽子手形象出现的“冬”。“刽子手”一词再次出现,使“冬”的形象更为狰狞。如果说感情寓示了现实中温情的一面,梦想则是现实缺憾的某种寄托和弥补,对感情和好梦的扼杀便切断了诗人在生存的时间和空间、真实和想象层面上的可能,在这样困窘的境遇中,绝望的诞生非但不可避免,而且将无止境地蔓延下去。
四
在整首《冬》中,第四章的存在是有些出人意料的。无论是这一章的整体调子,还是它所写到的场景和人物,都与前面三章有着某种游离的地方。在这样的游离中,读者得以窥见诗人对“冬”这一既定主题上试图有所摆脱有所改变的努力。
这一章主要截取了马车夫们在冬天的一个生活片断(注:与诗人的身份相比,马车夫显然是全然不同的一个群体,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下,诗人对马车夫们生活场景的描述其实是对自己可能经历的另一种生活的“想象”。按照当时对出身、阶级、成分的某种认定,前三章中诗人对“冬”这一主题毫无“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描述完全可能源于他的诗人身份。因此,对马车夫们生活的或真实或想象的书写显示了作者对当时体制的某种“顺应”。)。第一节以“沙沙”吹动窗纸的风、马车夫们带着雪的脚勾勒出冬天的特征。第二、三节描述马车夫们在小土屋中休息时的一些场面,加柴、烘干衣服、抽烟、喝水、哼小曲、聊天。他们似乎享有着普通人的快乐,但即使在整个比较写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一句依然泄露了诗人自己的某种声音和眼光,对马车夫们来说,他们不是没有对于“枯燥”的感知能力,而是在近乎惯性的生活中,日益淡化了这种感知,诗人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枯燥”来强调对日常生活某种磨损作用的有限抵制,不是没有一种无奈和焦躁在其中的。
最后一节有着某种残忍却真实的意味。“几条暖和的身子走出屋,/又迎面扑进寒冷的空气。”马车夫们在短暂的休息之后,依然要投入长久的寒冷中,这两句的形象感非常鲜明,“原野”一词在最后两节一再出现,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枯燥的原野,不可知(“一望无际”)的原野。它更分明地衬托出个体的渺小,即使在诗人试图有所摆脱的时候。马车夫的生活场景本来多少冲淡了前三章对冬天的悲观描述,他们近似常态/永恒的生活状态,对前三章仿佛是一个小小的反拨,冬天寒冷的风、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逐渐成为背景。在这样短暂的休息和温暖中,整首诗有了一点亮色。但如此显著的温暖反而更衬托出寒冷的底子,暂时温暖的身子是无法对抗永久的寒冷的,“又”字再次表明诗人无能为力的心态。正是在最后这两句诗中,诗人再次返回到“冬”的主题,这种经过一番努力和挣扎后的返回无疑有着某种貌似妥协实则坚持的意味,漫长的荒凉和寒冷注定是诗人赋予这首诗的永恒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