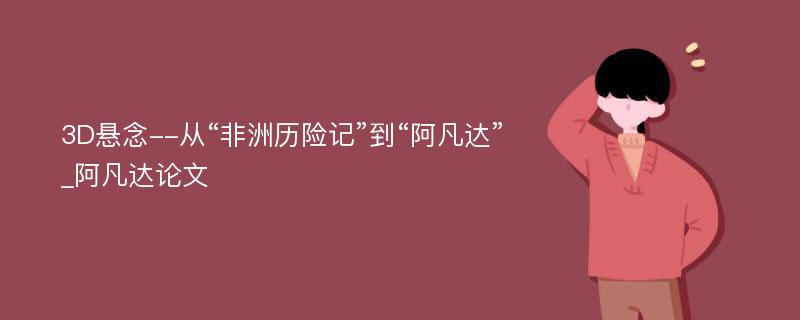
3D悬疑——从《非洲历险记》到《阿凡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历险记论文,悬疑论文,阿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次3D算是扎根了——至少好莱坞正竭力希望我们相信这一点。这次跟1950年代初不一样啦,他们说,那时候要戴笨重的双带定色眼镜,很不舒服,导致立体电影兴旺了几年就遭到终结。跟1980年代初肯定也不一样,那时候的放映系统是更简单的单带定色,但这种格式顶多就是用来拍一些惨淡的定向开发片(如《枪手哈特》[Comin' at Ya!,又译《来者不善》])或者一些才思枯竭的名片续集(比如《大白鲨》3D版)。
某些情况表明,这次制片公司可能是说对了。此次新一轮立体技术风潮——时间刚好是30年后,一个标准的革新换代时间间隔——靠的是全新的数码科技,基本上只需要按一下按钮,清晰、生动的三维影像就已经做好了。原来那些设备操作起来不比驾驶一辆12轮拖车来得轻松,现在随便从大街上找个人就可以用,只要他有一根手指头就行。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形势在催促新技术的革进。自爱迪生时代以来,笨重、脆弱、昂贵的35毫米胶片一直是工业标准,制片公司早就想把它们换成轻便的DCPs(数码摄影包)了,他们在向影院老板们竭力推荐数码放映机。但影院从这些昂贵的新装备上得到的利益可不像发行方那么多,所以他们对数码放映系统的反应比较迟钝,整个产业正举步维艰,这套新系统带来的成本压力是相当可怕的。
然而如果数码3D成为标准,影院就会被迫大力购进新设备,除非他们不打算放映最新的大片。单从票房收入上看,很难说清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成本投入有多大(福克斯公司宣称成本为2.3亿美元,坊间流传的数字是5亿),但卡梅隆的传奇如果能迫使主流院线转向数码,那么福克斯收回的可不只是那些前瞻性的投入(以及整个行业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就这样,制片公司开始争先恐后地推出3D片——其中除了《飞屋环游记》(Up)、《阿凡达》、《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等拔山扛鼎之作外,也不乏恐怖片《我的血腥情人节》3D版、《死神来了》3D版(The Final Destinationin:3-D)或者音乐会纪录片《乔纳斯兄弟:体验3D音乐会》和《和戴夫·马修斯乐队一同体验非比寻常的3D世界》等意图分一勺羹的小制作。在制作大片的同时,还要用小制作把整个流水线充分利用起来,只有这样好莱坞才能把立体电影变成寻常玩意——就像声音和彩色那样,把它变成一种标准,一个习以为常的观影元素。
一些观察家表示,希望《阿凡达》能成为3D电影的《爵士歌王》,一次彻底改变产业模式的革命。不过,多亏了唐纳德·克拉夫顿(Donald Crafton)这样的史学家,我们现在知道《爵士歌王》一夜之间让整个行业旧貌换新颜的事不过是媒体的幻觉:从默片到有声片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耗去了多年时间,没有哪一部影片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确是这样,在教科书里,电影史就是一系列突破性的进步,一转眼就有了声音、彩色、宽银幕和3D的“革命”,这些不过是在西方文化里泛滥成灾的进步论神话而已。
黑白默片不是哪个人一手创造的。在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电影发明家们心目中,制作让人身临其境的电影一直是最高理想。在雷伊·佐内(Ray Zone)那本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立体电影以及3D电影的源起1838-1952》中,色差3D技术——将左右眼看到的画面分别用红、蓝镜头进行过滤——的发展可以一直追溯到电影尚未降生的19世纪初,当时是在魔灯秀上使用的。
在众多先驱者中,美国的爱迪生、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以及英国的威廉·弗莱斯—格林(William Friese-Greene)都把电影设想成一种有声音、色彩、景深的东西,并且都针对这些设想进行了实验。埃德温·S.波特(Edwin S.Porter)在这方面居功至伟,他于1915年6月向媒体展示了他的色差系统。“画面比以往有了显著的提高”,《移动画面世界》杂志的林德·德尼格(Lynde Denig)说(引自雷伊·佐内著作的引文),“在场的许多观众认为自己见证了一个电影现实主义全新时代的到来。这个发明什么时候能应用在主流电影市场尚不得而知,不过波特先生相信在这样一个进取的年代,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事实并非如此。类似的实验仍在继续(史料中未曾记载波特的计划为什么没有了下文),1922年9月27日,导演、制片人、摄影师哈里·K.费娄(Harry K.Fairall)为媒体放映了第一部色差全长片《爱的力量》(The Power of Love)。影片讲的是发生在老加州的一段执着的爱情故事,此后并没有投入商业放映,拷贝今已不传。同年12月,《纽约时报》对塞尔温影院的一个电影放映计划(其中包括一部情节设定在水星上的短片!)给予了好评,这些影片是用色差技术的竞争对手——电传信息技术(Teleview)拍摄的。
对3D的前景颇为看好的格里菲斯也在这一年的《时代》杂志上宣告:“真正的立体效果会大大改变电影的样子。它将超乎所有人想象中的、最有力的表达媒介。”但他同时也提出一个警告:“如果有力的剧情被放到绝对立体化的奇观里,我相信没有一个观众能受得了。假设要把一把匕首猛地插向观众的脸,那会怎么样?……多吓人啊。”
雷伊·佐内的书记载了1920、1930年代的一系列专利申请,这些发明偶尔能在影院里露一下脸(米高梅在1930年代中期发行了一系列“立体画”短片),到了1930年代末,世界各地的博览会和节日庆典用3D电影来吸引眼球已经成了标准的手段。埃德温·H.兰德(Edwin H.Land)的偏振镜头取代了红蓝镜头,让色彩还原更加可信,画面也更亮丽。
1952年,两位好莱坞摄影师洛思罗普·沃思(Lothrop Worth)和弗兰德·贝克(Friend Baker)开发出了一种实用的3D系统,并卖给了编剧米尔顿·冈斯伯格(Milton Gunsberg)和他的兄弟朱利安(贝弗利山的一位眼科医生)。独立制片人阿奇·奥博勒(Arch Oboler)就是用这种被命名为“自然视像”(Natural Vision)的技术拍摄了《非洲历险记》(Bwana Devil)——这部低成本丛林历险片基本上是在马利布①的,10月在影院上映后打破了票房纪录。3D热潮从此兴起。
《非洲历险记》没有把匕首插向观众的脸,不过还真是捅了许多别的东西,包括长矛、填充玩具动物以及芭芭拉·布里顿②。不过观众没有像格里菲斯预料的那样被吓得魂飞魄散,反倒是很开心。它新奇、惊人,而且——这是充满恐慌的1950年代电影工业最需要的——在电视上绝对看不到。
《非洲历险记》是一部如假包换的定向开发片——传单上信誓旦旦地写着“狮子坐你腿上!爱人躺你怀里!”——生于罪恶,此生都难逃罪恶。考虑到《活力之声》(Vitaphone)的成功经历,华纳兄弟成为第一家认可“自然视像”的大制片公司,并且很快就把这项技术应用在重拍他们的摇钱树《蜡像馆的秘密》上,这部影片在1933年已经尝过特艺七彩(Technicolor,又称染印法彩色)双带定色的鲜了。改名为《蜡像馆》的1953年重拍版由原华纳B级片组负责人布莱恩·福伊(Bryan Foy)担任制片,导演是安德烈·德托斯(Andre De Toth)——他是个有才华的电影人,但恐怕不是最适合这项工作的人,因为他一只眼是瞎的,没办法欣赏到这种置美学追求于不顾的景深效果。
《蜡像馆》的效果既有胡闹(马路边叫卖的小贩把一只板球直接打向了观众的脸),也有相对不可思议的地方(在高潮段落的打斗中,一个明显像是从观众席出来的人从前景升起,爬到了场景中)。德托斯直觉地发现3D最主要的表达模式有两种,他称之为“内凹片”(innies)和“外凸片”(outies)。“外凸”(1953年的3D版“三个臭皮匠”短片《吓人!》里一个镜头是“外凸”的最佳典范,在这个镜头里,一个科学怪人拿着注射针头往观众的眼睛扎)很快就被视为立体电影粗俗而功利的象征。对影评人来说,这些肤浅的效果只会把观众的注意力从微妙的剧情和人物引开,这是应该加以检讨的。
外凸片是给日场观众看的——主要的形式有西部片(比如巴德·伯蒂歇尔的《鹰之翼》[1953]),恐怖片(约翰·布拉姆的《疯狂魔术家》[1954]),科幻片(杰克·阿诺德的《从外太空来》[1953]),惊悚片(鲁道夫·马泰的《第二次机会》[1953]),还有冗长的音乐片(罗伊德·培根[Lloyd Bacon]的《法国航线》[1953]),该片是在霍华德·休斯的监督下制作的,当时的广告语承诺这部片子会“把你两只眼珠子都打出来”。
而内凹片则试图拓展空间的外框,其手法和威尔斯、惠勒、托兰德(Gregg Toland)等人的透视性线条和极端景深差不多。媒体觉得这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技术(可能是它在潜意识里让人联想到舞台剧吧——那可是比电影要体面得多的艺术形式)。
随着外凸的新鲜感逐渐消失(不可能就这么一直靠折磨观众的眼睛度日),片厂意识到是时候把这个格式推向下一个阶段,以求得舆论的尊重以及长期效应了。一些高成本的电影开始出现,还请来了丽塔·海华斯(《莎迪·汤普森小姐》,1953)、马丁和刘易斯(《家里的钱》,1953)和约翰·韦恩(《洪多》,1953)等明星。这些更豪华的制作大多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狮子坐你腿上”,比较偏爱老式的、加强景深的长镜头。显然,3D必须融入到好莱坞现实主义的语汇中——就像原本各自为战的声音和色彩被捆在一起加以中和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那些杂耍性的奇观。
然而正当这类影片开始出现时,3D的热火突然之间熄灭了。20世纪福克斯的“影景”技术——初期的广告宣传是“不用眼镜就能看”——可以营造出电视擅长的那种视觉奇观,同时还不必忍受看3D带来的肉体折磨。福克斯很聪明,在启用这项技术时没有选择《蜡像馆》这样的廉价类型片,而是投入大笔资金来制作1950年代初最体面的好莱坞电影类型:圣经史诗。
3D技术眼看就要进入某种成熟阶段了,但《圣袍》(1953)的成功导致其他片厂搁置了手头的3D计划。希区柯克的《电话谋杀案》(1954)只使用了一个(但触目惊心的)外凸效果:在勒杀那一场中,格蕾丝·凯利将手伸向观众,仿佛是在求救。《电话谋杀案》可能给未来的立体声电影提供了一种模型。(乔·丹提在2009年那部尚未发行的出色3D全长片《洞》③中明智地走了希区柯克的路线。)但第一个吃螃蟹的华纳兄弟公司最终决定以平面的、传统的格式发行这部影片。希区柯克的版本直到1980年才与世人见面,此时华纳用一种称为“立体像”的简化单带定色技术对影片进行了重新制作,这种技术用变形镜头把左右画面压到了一格里。
立体电影直到1960、1970年代还在发行,不过基本上都是开发片了——甚至是明目张胆的色情片。(首次使用“立体像”技术的是1969年一部自封为X级的轻色情片《女管家》。)从此这项技术基本上就一直被固定在了这个层次上,顶多每隔10年或20年活过来一次,拍出《艾曼纽4》(1984)或者《黑色星期五第3部》(1982)之类的片子,它的形象和肉感烂片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很难吸引到像样的投资。
不过在1980年代中期,它意外地赢回了尊重。专为博物馆、博览会制作高规格胶片电影的IMAX公司发现他们的65毫米格式特别适合制作有力的3D影像,尤其是和所谓的“快门镜”——一种用液晶板制作的镜头,可以以每秒96次的频率遮挡左右眼的画面。这种效果比标准的偏振镜头要明亮、稳定得多;可惜的是,当然也复杂、昂贵得多。在应用了几年后,IMAX显然已经放弃了快门系统,重新开始往偏振镜方向努力。
然而在快门3D技术尚存的那段时间里,IMAX既做到了惊人的画面效果(比如1995年让—雅克·阿诺执导的40分钟剧情片《勇气的翅膀》),也实现了文化内涵。IMAX用以旅游片和科普片为主的影片确立了一种面向家庭的路线,让3D跟那些瞎胡闹的空中乘务员、挥舞着刀子的连环杀手划清了界线。立体技术再一次引起了主流制片商的兴趣——尤其是那个詹姆斯·卡梅隆,他用IMAX技术拍摄了关于泰坦尼克号的60分钟纪录片《坠入深渊的鬼魂》(2003)。
在《坠入深渊的鬼魂》里,卡梅隆和他的摄制组坐着一个救生舱似的潜水器潜入海底探寻沉船残骸,拍出了可以说是21世纪初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影片。在卡梅隆1997年的超级热卖片《泰坦尼克号》和第一次使用数字3D技术制作的《阿凡达》之间存在一个共通点,它们都是用一种由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拍摄系统——“佩斯合成”④(Pace Fusion)——拍摄的,这个系统把两部索尼高清摄像机连接在一起进行拍摄,《阿凡达》中使用的是一种改进版。影片的第二部是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一次虚拟游览,用CGI技术重现了巨轮。从那时起,卡梅隆就一直在努力把3D和数码动画技术合为一体,让3D格式重新焕发活力。
3D电影的影院放映总给人一种木偶剧或者杂耍片的感觉——这是颇有些诡异的现象,好像一旦加强景深,影片的层次就降下来了。一直以来,3D电影里的人物似乎显得比真实生活中要小,是一些在小舞台上表演的小人,而且人物本身也很受限制,好像一些二维的剪影似的。
立体片里的空间显得缺乏连续感,好像是用一系列平面堆叠起来的(总让我想起迪斯尼的复平面摄影机,把一组单帧的平面动画叠在一起创造一种景深的错觉)。1950年代的技术局限也许加重了这种感觉:巨型的特艺七彩3D摄影机(其身材跟《阿凡达》里的机器战士一样伟岸)移动起来非常麻烦;相对较慢的电机转速导致现场需要非常强的光线才能拍出足够的景深;镜头焦距必须足够短,这样才能实现曝光最大化和抖动最小化。面对这样的现实,多数导演会选择最简便的方案——固定的舞台剧式构图,偶尔使用一些特写来进行强调。
2003年,罗伯特·泽梅基思在《极地特快》(The Polar Express)的摄制过程中发掘出了数码动画技术,扫清了这一切的困扰。泽梅基思和他的制作团队为动作捕捉技术拍摄下来的表演制作了复杂的CGI环境,自打有电脑以来,3D领域一直在利用这项技术;只需要做一些再编码就可以制作出某个动作的另视角画面,这一点以前可是需要分别负责左眼和右眼两台摄影机来完成的。CG虚拟摄影机不存在自身重量和尺寸的限制,可以穿过钥匙孔,可以像鸟一样飞翔。当人物不再是真人而是动画时,那种被缩小、压平的效果就没那么碍眼了:如果说3D让人显得更小,那么它会让卡通形象变大,变得更真实。
2005年迪斯尼推出了3D版《小鸡快跑》,影片是用Real D技术(一种更廉价的,以宝丽来相片为基础的3D技术,是IMAX快门系统的替代品,问世后很快在市场上得到普及)制作的。泽梅基思的公司2006年针锋相对地推出了《怪兽屋》,从此开始了一场3D竞赛:亨利·塞里克(Henry Selick)的定格动画《圣诞节前的噩梦》2006年发行了一个用电脑转制的3D版,之后还有《拜访罗宾逊一家》和2007年泽梅基思的一部逗趣的照片写实主义影片《贝奥武夫》,以及2008年的两部不起眼作品《雷霆战狗》(Bot)和《带我去月球》。2009年,3D影片的产量发生井喷式增长:塞里克的《鬼妈妈》(Coraline),梦工厂的《怪兽大战外星人》,独立制作的《泰若星球》,皮克萨(Pixar)公司的《飞屋环游记》(在制作过程中转制为3D),福克斯的《冰川世纪3》,索尼的《美食从天而降》以及皮克萨的《玩具总动员》和《玩具总动员2》的3D转制版。
这一年的压轴大戏是两部迄今为止最为震撼的3D制作,泽梅基思的《圣诞颂歌》和卡梅隆的《阿凡达》。两部影片表面上很相似——都使用了大量的表演捕捉和3D技术——但在格式上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观念,我认为在未来这两种观念将代表两种3D的基本手段。
在泽梅基思这一方,《圣诞颂歌》极致地体现了导演对深焦和长镜头的钟爱,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他可以拍出以往无法想象的长度。影片描绘的1840年的伦敦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个无限的世界,一丁点儿小的细节都是清晰可辨的。他的虚拟摄影机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地运动,掠过屋顶,在下水道里游动,向前猛扑的特写,或者拉出成为一个大全景。影片最长的一个镜头是12分钟的“往昔圣诞节的鬼魂”片段,不过,整部影片用一个连续运动镜头来拍,从技术上讲也没什么问题(这一点泽梅基思是考虑过的,但为了不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所以放弃了)。
另一方面,《阿凡达》很少用长镜头。卡梅隆是他那个年代的典型导演,喜欢快切、浅焦,这些风格特点他都带到3D影片里去了,只是做了细微但重要的修正。他的数码摄影机(相对)更轻更小,让他可以用1950年代导演想也不敢想的方式去运动,影片充满了当代手持拍摄技术的随机性和即时性(这当然是个错觉,因为每一次看似随性的摇移和变焦都必须整合到密实的CG效果中)。在《阿凡达》开头有一个大特写镜头,是萨姆·沃辛顿饰演的杰克·萨利睡在冷冻箱里,想想从《非洲历险记》到现在,3D视效发生了多么惊人的改善:萨利的脸并非模糊背景上的一个平面,而是一个完整的物象,在面颊和眼睫毛之间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泽梅基思的技术是以画面合成为本的,因此在看《圣诞颂歌》的运动画面时,观众还是会感到有一个明显的画框存在着。而以动作为本的卡梅隆竭力想抹掉画面的边框,他的运动轨迹松弛不定,比起和被摄物体的关系,他更关心运动的向量。单个的镜头往往使用的是当代电影常用的极浅焦;3D效果不是靠蒙太奇来产生的,而是靠多重视角的高速整合。可以想象,泽梅基思也许会很乐意回到用单机拍摄的摄影棚时代;而卡梅隆想要的则是一大群摄影机(无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在他的拍摄对象上空盘旋,在同一时间里,从一切可能的角度,报道这个电影事件。
《阿凡达》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到《坠入深渊的鬼魂》,最显著的可能是潘多拉星的雨林里那些伸着触须、发着磷光的动物:它们仿佛是卡梅隆坐着潜水舱从大西洋深处带出来的。在他对影片3D空间的处理中,还有一处体现了海底世界的特征:物体与物体的间隙充满了连续性的运动粒子——尘埃、昆虫、雾霭——这些都给看似空荡的空间带来了一种视觉密度。所有东西好像都游动在同一种三维空穹之中。这种效果消除了一系列平面组合在一起会形成的那种木偶剧感,创造了一种连续的、感性的整体。卡梅隆的这种粘性空间是这个领域里前所未有的。前景和背景的对比不再像1950年代3D片那样突兀和可疑;所有东西都不偏不倚地、整体地向我们靠近,就像我们在感知真实世界一样。
如果这种效果可以应用到实拍立体技术里,那么好莱坞可能终于找到了让3D标准化的方法,它将和色彩、声音一起为好莱坞现实主义服务,消除那些不可信的地方,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成为分散注意力的东西。3D技术只有在卡梅隆等人的努力下实现了这一点,才算是真正摆脱了雕虫小技的身份,成为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电影元素。我们用了一百年时间达到了今天的成就,但前方尚有一段未走完的路。
本文译自美国《电影评论》2010年1—2月号。
注释:
①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的一座小城市。
②该片女主演。
③该片已于2009年9月首映。
④卡梅隆和文斯·佩斯(Vince Pace)发明的一种叫做“Pace Fusion 3D”的数字摄影机,这种有两个高清数字摄像镜头的摄影机使3D电影的画面由过去的两个层面增加到四个层面,更具有空间层次感。
标签:阿凡达论文; 卡梅隆论文; 非洲历险记论文; 电影论文; 圣诞颂歌论文; 影视论文; 3d论文; 3d技术论文; 3d电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