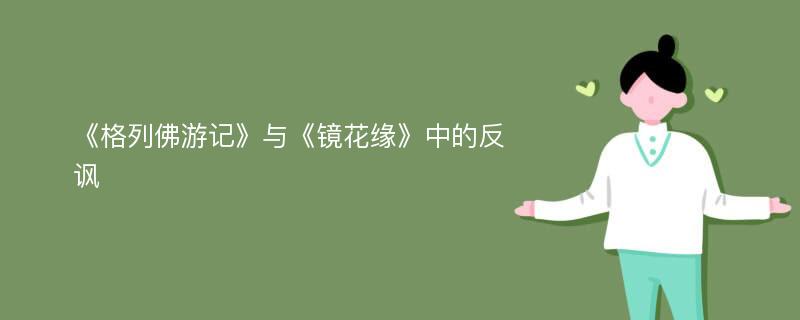
江舒桦[1]2004年在《《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中的反讽》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的主旨在于研究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和中国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的反讽现象。反讽存在于“表面的”、“显在的”意义与“内在的”、“隐藏的”意义的分歧之间,是一个涵盖甚广的概念。研究这样来自不同文学传统的小说中的反讽和反讽意象,在比较文学研究和批评方面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斯威夫特是一个众所公认的反讽高手,其反讽思想和技巧在《格列佛游记》中彰显无疑。《镜花缘》则是一本和《格列佛游记》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中国小说,据我所知,至今未有人正式地探讨过《镜花缘》中的反讽,更不用说将这两部小说的反讽现象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了。 本文引用的反讽理论来自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来源是D. C. Murcke和Wayne C. Booth。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了反讽的概念、这两部小说的基本内容以及我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反讽理论、有关于这两部小说的批评理论,以及对于它们的反讽的一个初步探讨。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分析了《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中的反讽现象,其分析框架根据两书的特点略有不同。第五章给出了简短的结论。
唐爱玲[2]2016年在《从符号—结构阐释《格列佛游记》的讽刺和幽默手法》文中指出斯威夫特是英国十八世纪讽刺大师,其代表作《格列佛游记》是英国讽刺文学里程碑式的着作。历来关于《格列佛游记》的研究不计其数,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本文将采用符号结构诗学方法,阐释《格列佛游记》的讽刺和幽默特点。《格列佛游记》文本中充满大量的讽刺以及幽默手法为学界认可,但遗憾的是大多没有从整体出发对其丰富的讽刺幽默艺术技巧与手法进行梳理研究,而是孤立、局部地讨论小说讽刺幽默手法的某个方面,本文尝试用符号结构方法探索《格列佛游记》讽刺幽默手法在不同层级之间的嵌套关系,从而从整体把握小说讽刺幽默手法。论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最小文学手法出发考察《格列佛游记》不同文学手法使用情况。通过对《格列佛游记》文本中的两个片段:《内务大臣与我对话》、《我与主人关于战争的谈话》的最小文学手法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在《格列佛游记》这两个片段中,较多使用叙事手法和议论手法,较少使用描写手法,几乎没有使用抒情手法。叙事和议论不仅使用频繁,而且类型丰富,也是具有讽刺幽默功能最多的手法。不过,《内务大臣与我对话》以荒诞、幽默叙事为主,《我与主人关于战争的谈话》以反讽的议论和一般叙事为主。第二部分:从整一文学手法、文本文手法考察《格列佛游记》不同整一手法使用情况以及文本结构布局、人物形象塑造。在整一文学手法层面考察,在《格列佛游记》四卷中,前叁卷以事件为主,最后一卷虽然仍以事件为主,但内心意象骤增。讽刺幽默手法在前两卷以逗笑为目的的幽默事件为主,讽刺力度较轻;在第叁卷以嘲笑为目的的荒诞、暗讽事件以及内心意象-议论为主,讽刺力度加大;在第四卷以嘲笑为目的的暗讽事件和内心意象-议论为主,讽刺力度达到最大。从文本文学手法看《格列佛游记》,作为一部游记体小说,《格列佛游记》文本事件是主人公格列佛医生离开英国,先后游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诸国以及慧骃国,并最后回到英国,小说呈现出离乡-远游-返乡的U型结构,即小说文本事件并不是一直呈直线发展,而在第四卷发生了突转。同时,主人公格列佛的情感态度也随着游历地域的扩大,文本事件情节突转而改变,最后由赞美英国现代文明以及人类社会转向批判英国现代文明及人类。
刘莉莉[3]2013年在《《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美国的COLLIER大百科全书称《镜花缘》为“中国的《格列佛游记》”,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这样评价:“《镜花缘》与略早的西方小说《格列佛游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部小说产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却是极为相似。本论文意在运用现代叙事学等理论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全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引言部分概述二者比较研究的现状,阐述本论文的写作动因和构想,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叙事学理论从背景、情节、主题和叙事模式四个方面对《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的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最后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和方法。第二章介绍《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的作者和写作背景。二人生活的年代和国度不一样,他们都是出自本国的情况触及到了海外贸易和旅行这个当时很有意义的题材,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他们当时的社会环境,才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第叁章对《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的情节进行比较,这两部小说的情节大致相似,都是主人公从现实世界进入到虚幻奇异的世界。在相似的情节中,两位作者运用想象和虚构使作品有着共同的强烈奇幻色彩;在具体的情节上又有不同的地方,从这些差异中可以透视出两个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及文学传统。第四章内容是对两部作品主题思想的比较。二者都采用游记的体裁和幻想的形式,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表达了比较进步的社会理想。但两位作者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批判程度上又有所不同。第五章内容主要是运用现代叙事学理论,从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叙述者四个方面分析比较两部作品在叙事模式方面的异同。这部分内容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自己浅薄的看法。结论部分概括总结全文。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中西方文学有着共同的审美特性,这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根本价值,由于受到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中西方文学自身也存在差异。
王向辉, 王丽丽[4]1995年在《从《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看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文中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末一部百回优秀长篇小说《镜花缘》写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英国杰出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完成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两书产生的年代相去不远,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书都用了海外游记的形式。《镜花缘》主要根据《山海经》的记载驰骋想象,在八到四十回中描绘了林之洋、唐敖等人游历叁十多个海外国家的情形。《格列佛游记》则写了外科医生格列佛
参考文献:
[1].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中的反讽[D]. 江舒桦. 清华大学. 2004
[2]. 从符号—结构阐释《格列佛游记》的讽刺和幽默手法[D]. 唐爱玲. 重庆师范大学. 2016
[3]. 《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比较研究[D]. 刘莉莉. 信阳师范学院. 2013
[4]. 从《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看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J]. 王向辉, 王丽丽. 外国文学研究. 1995
